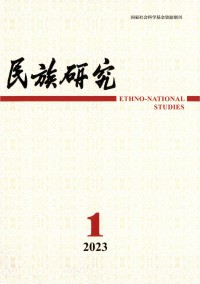民族形成与国家起源

[论文关键词]国家民族部落联盟酋邦
[论文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国家学说的重要文献,在《起源》中,恩格斯通过对民族和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指出了民族与国家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文通过对《起源》的重读,简要分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对北美易洛魁氏族、希腊氏族和雅典国家的产生、罗马氏族和国家以及德意志国家的形成的研究,并总结人类社会三次社会大分工中国家的产生,指出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民族,国家和民族是在生产的社会大分工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家庭的变迁、氏族部落制度的变化的基础上的必然产物。虽说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正如恩格斯在《起源》第五章雅典国家的产生中所提到的那样:“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是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不能参与这种管理。”“这就扰乱了氏族支付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在雅典设立了中央管理机关,……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总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同意的民族所代替了。“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这表明那种单纯的部落联盟被民族和国家所代替是必然的,民族和国家是两个共生性的社会共同体。
一、民族对国家的影响
当人类在其分化阶段完成了不同民族的孕育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变化开始缓缓流动,而农业最早发生地区展示的良好生存环境驱使他们纷纷向这些地区汇集。于是,民族过程的聚合阶段到来了。民族之间的交换、联合和战争也造就了以阶级对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分层和军事化的政治体制,为国家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和组织基础。国家起源于民族聚合,在于这种聚合带来的社会冲突和为解决冲突引发的政治变革。民族聚合过程带来了由民族碰撞激发起来的社会震荡,也创造了平息这种震荡的工具国家。
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到:“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精密地团结其爱。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从恩格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部落融为民族的直接的原因是为战争。“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得财富已成为主要的生活目的之一。……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由于战争,“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这种族体的联合,恩格斯称之为“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有亲属部落的联盟,也有非亲属部落的联盟。它的特殊点在于各组成部落之间的平等联盟关系。但实际上,除了部落联盟之外,“酋邦”也是这种族体联合的形式。酋邦的形成或经过部落之间的征服,或经过部落联盟的演化。所以,不论酋邦还是部落联盟,都是族体的联合或增大。这种联合或增大都是与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的加剧同步而行的。这为社会冲突的发生增添了更大的可能,也为维持这种正在形成的社会提出了政治变革的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体制上的军事化。恩格斯将其称作军事民主制,认为每个进入国家的文化民族都曾经历过军事民主制时代,如雅典的“荷马时代”、罗马的“王政时代”等。由于酋邦社会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不宜再提“军事民主制”。的确,恩格斯讲到的军事民主制是和部落联盟对应的制度,这种制度都有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军事首长三种机构。而这些在酋邦那里只剩下后两种或最后一种了,已没有多少“民主”色彩。但无论如何军事制度的痕迹十分浓厚,酋长也即是战时的军事首长,这和恩格斯讲的部落联盟没有不同。部落联盟和酋邦都可以成为国家的过渡形态。
前者因民主制度较浓,可以使过渡后的国家呈现共和的体制,如雅典和罗马。“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只能够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说:“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的详情的。”
而后者,因民主制度消退则可能走上专制了。恩格斯对德意志国家形成的叙述为此提供了具体事例:“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恩格斯在这里仅提到了军事首长向王权的转化,但却是最具本质的转化。因为只有王权才最深刻地体现着集权和强制,体现着国家和前国家政治机构的区别,其下属政权机构的专门化也只有随着王权的确立才能确立和扩展。
二、国家对民族的影响
人类的族体观念,在原始社会前后,有过一个大的飞跃或变化。这种飞跃或变化经过了一些关系复杂的较长的过渡时期,但原始的血缘性的族体概念最终还是为地域性的超血缘族体概念所取代。例如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成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而引起人类民族过程中这种飞跃或变化的主要原因正是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形态的发展或者说是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促使文明民族的出现。
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之所以会导致新的族体观念的出现,其原因是由于早期国家与原始社会中的血缘性的政治组织(如部落、部落联盟等)不同,它具有控制和指导族源复杂的各原始社会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以及早期国家对于旧的血缘联系的有意识的打破,而使在它控制下的居民按照地域和政治的原则重新进行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部落联盟和酋邦。
由于部落联盟与酋邦在政治组织性质上的差异,它们作为早期国家的前身,对于民族过程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部落联盟在政治上的民主与平等的特征,是以它仍然具有血缘团体的性质为基础的。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就是“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完全平等和独立为基础”结成的“永世联盟”。恩格斯强调指出:“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这就决定了在部落联盟的范围内,那种打破旧的血缘关系限制的新的、超血缘的族体概念,从整体上说还没有形成,只有在部落联盟转化为国家之后,随着国家政治职能作用的发挥,新的族体观念才得以逐渐形成。这在欧洲早期的民族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恩格斯在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曾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在罗马国家的作用下,由于“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因而出现了一个“民族性缺乏”的时期,虽然“新民族的要素到处都已具备,……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的力量”,只有当德意志各原始民族“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了新的国家”之后,才“养成了新的民族”。
然而,对于酋邦来说,新的族体观念的形成过程,却早在酋邦衍变为真正的早期国家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主要是因为酋邦对于部落的结合并不严格地遵循相互间具有血缘联系的原则,即酋邦并不像部落联盟那样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其基础。它形成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征服。酋邦在政治上所体现的专权或专制的性质正是这种征服的特征的反映和直接后果。酋邦的征服使不同血缘渊源的原始民族开始出现了融合为一种新型的、超血缘的族体的趋向。通过合并而形成文明民族的各原始民族,一般在地理上是毗近的,且在文化发展上处于相同或相近的水平,使用相同或类似的语言,并且在族源上是相对地同种的。如恩格斯所强调的“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精密地团结其爱。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民族方始产生。”从中也可以看出,酋邦在吸收族源不同的居民方面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与潜力。当然,相对地说,“同种”的居民是更易于被吸收的。但作为存在和形成的原则,酋邦并不拘泥于共同血缘关系的约束。这是历史上经历过酋邦时期的民族比从部落联盟过渡到国家的民族能够更早形成他们的新的族体关系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1
[2]何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导读》[M],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1
[3]谢维杨,《早期国家与民族形成的关系》[J],探索与争鸣,1991.1
[4]王希恩,《国家起源与民族聚合》[J],民族研究,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