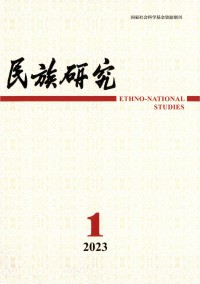民族文学叙事模式演变研究

正名叙事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意识形态出现的重大变化,阶级斗争学说逐渐淡出主流,少数民族文学的阶级斗争叙事明显弱化。1984年,中国文坛兴起寻根文学思潮。对于汉族作家而言,文化寻根或许只是中国文学试图获得世界文坛认同的一种手段。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文化寻根则成为民族意识重新唤醒的一个机缘。这一时期,张承志的创作可以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一个典型个案。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和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心灵史》显示出张承志民族意识演变的三个阶段。《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虽然以蒙古族生活为题材,但作者的关注点并不是蒙古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生活历史。作者通过讲述三个故事,塑造了一个蒙古族额吉(母亲)的形象,进而回答“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个问题。第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场春天的白毛风(“暴风雪”)突然降临,知识青年“我”正在草原放牧中,随时可能被白毛风吞噬,在万分危急之际,额吉骑马赶到,用自己的山羊皮外套为“我”挡住了白毛风,自己却因为受冻而下肢瘫痪。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牧场发生了火灾,两个北京知青烧伤了,其中有一个姑娘,伤势比较严重,额吉听说了这事后,不顾自己下肢的瘫痪,立刻赶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姑娘,给了姑娘巨大的精神安慰。第三个故事说的是草原摔跤手班达拉钦被宣布为阶级异己分子并被撤销了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他从小在牧主的蒙古包里长大,是牧主的养子。额吉得知此事后,告诉“我”草原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一顶蒙古包下面,有穷人和富人两种人”,也就是说,作为牧主的养子,并不意味着就具有牧主的剥削身份,额吉提供的经验经过知识青年们的理性思考,使他们得出结论“,蒙古族社会的剥削现象,经常是在家庭的掩蔽下进行的!”换言之,养子虽然住在牧主家,但他却是牧主的剥削对象。“养子这种剥削方式是蒙古族社会的一个历史特点”。这种理性认识使班达拉钦的冤屈终于得到纠正。这三个故事的性质接近,第一个表现了额吉对住在自己蒙古包里的知青的爱,第二个表现了额吉对自己不认识的知青的爱,第三个故事表现了额吉对蒙古族阶级同胞的爱。三个故事共同表现了蒙古族母爱的博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说中的第三个故事,涉及到蒙古族阶级问题。虽然小说中专门为班达拉钦平了反,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否认了阶级的存在。当然,这个小说的主旨既不是表达蒙古族意识,也不是表达阶级意识,它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主题:“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显然,在这个小说里,作为回族的张承志,并没有明显的本族意识;作为内蒙古草原的插队知青,他也没有代蒙古族立言的意思;他努力表达的,是一个超越民族的思想,即“母亲———人民”。可以看出,1978年的张承志,还没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反而有明显的阶级意识。这与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还是很合拍的。到了《黑骏马》,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总体上看,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比,《黑骏马》的创作意图发生了重要变化。《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表现的是“母亲———人民”主题,这里,无论是“母亲”还是“人民”,都只是一个多民族概念,泛指整个中华民族。但是,到了《黑骏马》,民族意识已经明显浮出了海面。作者试图思考“蒙古民歌的起源”、“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试图探求“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①,试图讲述“草原古老的生活”①。显然,这些都是独属于蒙古族人的,不像《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那个升华为人民的母亲更带有泛指的性质。其次,小说里有几个细节,专门写到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有关“血缘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心理活动。那是当白音宝力格得知索米娅怀上别人的孩子而与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喊一声坐在身旁冷眼旁观的奶奶,竟喊不出来,他感到了他与奶奶之间的隔膜,“一种真正可怕的念头破天荒地出现了:我突然想到自己原来并不是这老人亲生的骨肉。”②这里,白音宝力格的血缘意识被激发起来了。而在奶奶跟他说了一大番人生的道理之后,他无法认同无法接受,小说写道“:也许就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③这两段心理描写表明作者有了明显的民族意识,亲生骨肉代表着血缘,土生土长代表着文化,白音宝力格从血缘和文化两个因素否定了他与蒙古族的认同,而这两个因素,恰恰是民族构成的核心因素。张承志在文坛最有影响的小说都是以蒙古族生活为题材的。饶有意味的是,张承志并不是蒙古族人,甚至,也不是汉族人,而是回族人。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个小说中,张承志几乎是没有民族意识的,他更多是以一个知青的身份,去体验他所插队的地方的百姓的品质。可是,在《黑骏马》中,他因为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体验而产生了民族意识。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时候,张承志笔下白音宝力格的民族意识并不是他的回族意识,而是“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陶冶了我的另一种素质”,即我们可以想象的主流民族或者说是汉族素质。以这种主流素质看,在草原之外,还有一种“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④1984年,张承志走进了大西北。在之后六年的时间里,张承志自称他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⑤。这个“脱胎换骨”的标志,可以理解为他找到了“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⑥;可以理解为“一九八九年秋,我宁静下来,开始了我的人生尔麦里”⑦;也可以理解为,他成为哲合忍耶的一支笔,写了一本“他们会不顾死活保护的书”⑧,那就是长篇小说《心灵史》。《心灵史》的出版,表明张承志的回族意识得以复苏。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⑨与《黑骏马》相比,《心灵史》的最大变化就是张承志显示了他作为回族的强烈的身份认同,有了回族的文化自觉。这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他对自己原来所接受的主流文化影响有所反思,他获得了一批回民民间“秘藏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下的内部著作”、“近一百六十份家史和宗教资料”①“、一些文人界外的大作家的秘密钞本”②。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对他理解历史、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承志的文化转向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作家。如果说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等作家文化寻根的终极目标是深化和壮大中国文学的文化根本,其目的仍是文学追求;那么,张承志的文化寻根则越过了文学,他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录和信仰宣言,从而使文学批评在他的文本面前变得“失语”。③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而言,一方面,寻根文学用文化叙事取代了政治叙事,将文学从单一的政治叙事引向了丰富的文化叙事阶段。今天来看,寻根型的少数民族文学有一种为其族别写作正名的冲动。它要找到其民族文化根源,传达其民族意识,实现其民族认同,将其族别文学从共名状态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寻根文学可能导致当代少数民族存在脱离现实、走向封闭的地域文化或民族历史的倾向。从近2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形,一些作品自我封闭于民族历史,割裂了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联系,基本脱离了同时代的主流文化叙事,虽然在展现文化的多样性方面有较多的成绩,但对文化融合,文化包容的一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匿名叙事
为什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阶段能够形成与当时主流文化高度认同的共名叙事?根本原因在于,“建国初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展了‘’和民主改革运动,得到翻身解放、无偿分到土地的那一代少数民族民众从内心感激共产党和中央政府。”④阶级斗争理论在当时确实越过了民族意识的籓篱,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普遍认同。为什么第二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正名叙事?这也可以从1976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中寻找原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最初,这种转型是全社会受惠。然而,好景持续十多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原来财富相对均衡的社会出现了各阶层的分化;另一个层面是原来相对平衡的社会出现了欠发达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分化。落实到少数民族这个问题,确如马戎所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就业难和生存难。由于汉语水平低和就业技能弱,他们在与内地来的汉族农民工和汉族大学生竞争时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斥……”①阶层的分化和地区的分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从主流叙事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虽然它有表现文化多样性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分离长期持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将会产生消极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阶层分化和地区分化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阶层分化和地区分化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重视,但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阶层分化、地区分化往往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一些少数族裔及少数民族地区就在这次社会分化中沦为赤贫,并且失去了社会所应该给予的保护。这种生存现状使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更加疏离,就像马戎所指出的:“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生存困境与族际差异联系起来,这就使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与民族隔阂叠加在一起,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化。”②也就是说,如今,中国社会几个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如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东部与西部的差距,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的差距,这些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都可能隐藏有民族问题在其中,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使单一的社会问题变成了复合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备受媒体关注的现象。其一是农民工犯罪现象,比如这些年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广西天等县温江村“砍手党”在珠三角的犯罪事实,人们普遍注意到温江村的贫困、温江村人受教育的程度,但有一个情况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天等县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超过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八。③其二是拐卖儿童以及流浪儿童现象,其中新疆维吾尔族流浪儿童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其三是乡村正在沦陷,显而易见,这些正在沦陷的乡村,又以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首当其冲。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关注的这些社会现象之前好些年,一批作家已经写出了相当有影响的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与上述三种现象相关,正好有三个中篇小说涉及了当下媒体关注的领域。它们分别是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凡一平的《扑克》和李约热的《巡逻记》。《被雨淋湿的河》④描写了一个叫陈晓雷的农民工,因为各种社会不公而最终走上了抗争与犯罪的不归路。这个小说的责任编辑李敬泽曾经撰文回忆他编发这个小说时的心情,当时的他认为,“鬼子对‘现实’的‘描写’是偏僻的、刺耳的、可能‘越界’的……”,然而,经过六年的多次重读,他不得不承认,这部作品“拓展了我的世界观,使我得以接近和理解‘遥远’的人群———对我来说,他们是遥远的,远在我的生活疆界之外———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灵,并且意识到那些遥远的人群隐蔽而确凿地参与了我的‘现实’的构成。”①李敬泽的话也许有些费解,通俗的理解,大意就是后来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印证了鬼子小说中的描述,也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巡逻记》②写的是一个名叫宜江的乡镇,这是一个只生长赌徒不生长粮食的地方,男不耕女不织,少不读书,老不安逸。2010年评论家梁鸿出版了纪实作品《中国在梁庄》,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读《巡逻记》以及李约热其他的小说,会看到梁鸿的观察早已在这些小说中有更细腻、更深入的叙述。李约热给宜江的取了个颇能给人联想的名字:珠穆朗玛,套用梁鸿的思路,也可以说“中国在珠穆朗玛”。《扑克》③写的是一个被拐卖的儿童王新云的命运遭际。小说并不像许多相关题材的叙事那样将重心放在被拐卖儿童丧失亲情的悲惨,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失子父亲寻找儿子的过程,以及被拐儿童成年后知道自己身世时的复杂心理。就后者而言,小说的责任编辑李倩倩说过一段话“:‘王新云’一直是处于隐匿状态的,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世,且隐蔽在一段越轨的爱情当中。这又恰恰说明了,在个人私密空间日益缩小、社会信息空间日益扩大的今天,隐匿是现代城市人的一种生存状态。”④隐匿是现代城市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李倩倩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重要提醒,提醒我们注意上面三部作品作者的身份。《被雨淋湿的河》的作者鬼子是仫佬族,《巡逻记》的作者李约热和《扑克》的作者凡一平都是壮族。然而,阅读这三篇已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人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借以判断是否少数民族文学的元素基本丧失。作者的民族身份大都隐匿,主人公的民族身份未加说明,作品失去了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域标志,也没有相应的民族习俗或者民族符号作为提示。然而,如果深入了解作家的生平以及作家的成长经历,会发现,他们自身的经历以及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和环境,或与民族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的生存生活状态与过去相比有了巨大的差异。沿用传统的思维,将少数民族圈定在传统的聚居地和传统的文化圈中,无异于画地为牢或者刻舟求剑。我们必须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匿名的存在,注意到少数民族在新时代的新变化,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发现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看到新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看到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在建构中华民族国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李咏梅黄伟林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