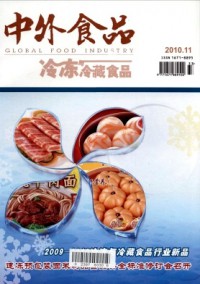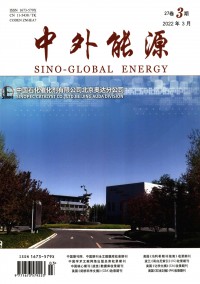中外作品的底层叙述

海德格尔认为“:常人本身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③“此在的本质是共在。”④“底层”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每个“常人”的生存活动交织而成的,底层叙述展示这种庸碌的平均状态。生存总是取决于每一个此在自己可能挑选的抓紧或延误的生存方式。底层的生存状态通过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得到复杂地呈现。老舍和纳拉扬的小说刻画了一系列个性十足的底层人物,它们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传承、地域环境与日常经验的土壤,同时又是世界范围内这类形象的缩影。对剧变时期社会历史题材的选取与开掘,人物现场感的营造以及民间语言的细腻描绘拧成一股绳,成功实验了一种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底层叙述”。
老舍以善于描绘城市贫民著称。樊骏在老舍诞辰八十周年时撰文评论他“不只是记述个别人物的生活经历,而且真实地再现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⑤他不似鲁迅那般“横眉冷对”,也不似沈从文那般遗世独立,对底层生活有切身体会与丰富经验。老舍是“京味”文学的鼻祖,几乎所有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都是在北京市民社会中展开的,北京风物、人物描绘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老舍小说不刻意展现作者姿态,和小人物对话而非完全操控他们,读者通过人物和作者对话,几乎没有距离感。很少做大段社会背景的描写,却往往系之于人物的眼睛不经意看到的一隅。
满族身份为老舍带来对满族贫民生活的特殊体验———清末以来满人特权丧失后生存的无力感。他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最底层人物———“大杂院”里的那些人———与这种体验有关。血汗榨干后归宿是乱坟岗子的洋车夫,风里雨里站马路而收入地位低下的巡警,“一辈子作艺,三辈子遭罪”的民间艺人,本性善良纯真被逼良为娼的妓女,窝脖儿的,打杂的,捡煤渣的……处在层层剥夺、彼此干扰的生态链的最末一环。他们没有尊严、失却理想甚至道德底线,是一群无根也没有明天的人。老舍揭示压迫他们的因素主要有恶劣的社会、自然环境和内在的劣根性。老舍对他们投以理解和同情的眼光,费尽笔墨写他们的挣扎与沉沦,即使讽刺也是极善意的。
此外是在底层与中间阶层沉浮着的小人物,基本解决了温饱,但常常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如各色小知识分子,投机商人,伪教育家,伪稽查长,盲目的革命者,庸俗的小市民等等。他们中有的因坚持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而受辱(《骆驼祥子》曹先生,《大悲寺外》黄先生,《四世同堂》钱默吟);有的在新旧文化之间不土不洋,不伦不类,(《老张的哲学》、《离婚》老张,《二马》二马父子,《牺牲》毛博士);有的因为仅有的那点爱好而受制于人(《恋》庄亦雅)。老舍警醒盲目的革命者,戏谑见风使舵者,深深理解和钦佩保有气节者。善于将各个层次的人放在一个特定环境里,展示他们互动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底层与上层的矛盾归根结底是钱与权的力量冲突。底层内部各层次之间既共生又互相干扰,如《老张的哲学》李静的姑妈既可怜李静被迫卖给老张为妾的遭遇,又不允许她自由恋爱而催促她走上那条不归路。
“悲剧性是新世纪底层小说最重要的美学品格之一,一个底层作家对悲剧的理解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表达效果。”①老舍在上世纪就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他塑造的底层人物悲剧是东方式的,几乎没有英雄,没有崇高的场景,是笑与泪的混合体。他们身上有勇敢、勤勉、正义、善良、隐忍、团结、爱国等美德,也有懒惰、愚昧、守旧、麻木等缺陷,集中体现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思索。环境往往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人物陷入无法逃脱的状态。王德威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写实主义———茅盾,老舍,沈从文》中以“恐怖的闹剧”描述《骆驼祥子》,认为最恐怖的戏剧性在于祥子感觉到但不能彻底理解他正在对付的那一台臭名昭著的社会机器。②
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畸形,受外力冲击而不能自然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城市存在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加剧、产业结构失衡等。老舍为儒家传统道德的丧失和新秩序的未建立而焦虑。新旧交替的文化背景使处在夹缝中人们的冲突矛盾和在混乱中生存的荒诞感加剧,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新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目标。有人自动循环,有人自觉反抗,但结局都是黯淡。这种悲剧是全人类意义的。老舍以幽默与温情赋予底层人物可爱、天真与热情向上的一面,使灰暗的基调中闪过一丝亮色,也不忘给他们一点琐细的安慰和希望。老舍善于把握作品节奏,造成跌宕起伏的戏剧效果;善于通过互文重构一个更丰满的形象。如人力车夫形象:《骆驼祥子》祥子与《老张的哲学》赵四就是写实与理想性格的互补。
纳拉扬是印度早期文学的三大代表作家之一(其他两位是安纳德和拉迦•拉奥),三位作家中唯独他没有长期留学、旅居国外的经验,他没有外国人那种习惯性的眼光。“以自己对南印度日常生活的写实,向读者展示一个世俗但真实的印度。”①纳拉扬生活的时代如同现代中国那样动荡不安并存在更明显的文化移植现象,保守与开放势力进行着激烈交锋。
英人殖民统治后,传播西方思想,抨击印度教习俗,努力实现印度基督教化。现代性与印度文明产生溶血反应,对印度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是多方面的。然而,由于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是大多数人都不会说的知识分子语言,所谓现代性、所谓英语文学与底层民众认同之间的距离可想而知。漂泊的印度人后裔奈保尔使用了“受伤的文明”和“幽黯国度”来概括西方人眼中的印度,并感叹纳拉扬以本土视角“深切思考着那些在底层继续的卑微生命”②。纳拉扬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若干。其底层叙述体现出作者对20世纪社会大变革中种姓、宗教、性别等问题的尖锐洞察与深邃把握。
纳拉扬小说多数以虚构的南方小城马尔古蒂(Malgudi)为人物活动场景。这个小城封闭、安静,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印度传统社会文化缩影与作者理想的结合体。它不时受到外来事物打扰,慢慢发生着变化。比如通了火车,修了新的商铺,有了光怪陆离的商业社会景象,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巨变。这些是印度受殖民统治前后社会现实的记录式反映。与热闹的老北京相比,这个小城具有更浓厚的乡土气息,保留了更多传统(比如印度种姓制度、印度教等)的影响,与西方文明的对立、冲撞也以更为激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同老舍相似之处是,纳拉扬擅长在南印度日常生活场景中塑造人物,而与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保持一定的疏离。底层的个体是印度传统文化最厚重的承载者。他声明“:我只对个人感兴趣,且我对‘民族热情’此类词汇十分怀疑,它是做作和虚伪的。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且生活也应是丰富多彩的。
如果你谈论一个人的问题、希望和热情,你会离目标更近些。”③他们站在同样的文化批判立场,展示人性的复杂面。比如接受现代文化又受传统家庭重压、追求自由恋爱而不得的小知识分子钱德拉(《文学士》);自传式人物克里什那,他承受丧妻之痛并引发对生与死、存在与孤独的追问(《英语教师》);经历过一系列琐碎痛苦后无意中成为圣人的拉朱(《向导》),引发对凡人与圣人的思考。纳拉扬的人物塑造既异于现代小说中的边缘人、局外人,又同社会现实主义保持距离。他退在一旁观察,敦厚地理解和承受发生的事件,他的思考世俗、狡黠、睿智,善于在“变”中把握“不变”:维系印度人心灵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后殖民文学理论家博埃默总结得很透彻:“尽管纳拉扬的小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明显的政治话题,然而民族主义、神话般的印度教仍然植根于小说叙述之中。作家要召唤一种清静无为的印度生活方式,它先是放弃,但最终却要把历史的力量吸纳进来。”①1947年印度独立后宣布在法律上废除种姓制度,但其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广袤乡间。纳拉扬小说中底层人物痛苦的一重根源就是种姓歧视。《向导》中拉朱的母亲和家族坚决反对他与离异且种姓低贱的舞女罗西叶结婚,最后不惜断绝母子关系。甚至听到名字就贵贱立判:“当听到‘罗西叶’这个名字时,她颇有些吃惊,她本期望听到一个正统些的名字。”②各个种姓内部职位世袭,互不通婚,保持严格界限。低种姓的、被驱逐的和失去丈夫的妇女都被看作贱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当这些旧习与现代观念发生碰撞,激起的人心的痛苦和反思就更为激烈和深沉。
纳拉扬笔下人物的悲剧还表现为社会转型期新旧冲突带来的迷茫、心灵挣扎的痛苦。他既批判底层民众愚昧地坚持陋俗、旧观念,表现出对一切都视而不见的冷漠(中国20世纪初的乡土小说也有类似描写),又批判全盘西化,受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影响而行差踏错者。人应该怎样活着?这锥心的刺痛和对人生道路形而上的极度追索,比生与死的抉择更为艰难。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坚守印度教传统“:印度人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轻蔑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崇尚内在的、精神的东西。”③小说人物如知识分子室利尼瓦斯(《萨姆帕特先生》),闲人纳噶拉吉(《纳噶拉吉的世界》),糖果贩贾甘(《糖果贩的故事》),印刷商纳特拉吉(《马尔古蒂的吃人者》)等,无不是在体验现代性之后又回归传统的。老舍小说中对新旧市民的心理矛盾也有重点表现。他总是对地道的传统知识分子多一些赞赏,钦佩勇于冲破旧束缚的青年,同时对一些过激者予以批判。表露对崇洋媚外者、实用主义者、投机者和盲目革命者的讥讽。印度教轻视物质,崇尚精神的观念,使纳拉扬找到了一条引导相信它的人得以从混乱俗世的悲剧中解脱的路径,为小说增添了一抹理想主义色彩和来世的神秘光圈。而老舍笔下的人物则是坚定地入世,于欲望交织的苦海无从解脱。流露出自己、自己的子孙都可能逃脱不了的那种悲怆。也有个别逃遁者如《老张的哲学》中的李威,但结局都不了了之。可见老舍内心的矛盾和对于前路的迷茫。
纳拉扬和老舍都花大笔墨书写20世纪本国妇女的命运悲剧。妇女身上往往集中了社会底层的各种苦难,并且以更为特殊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女性要遵守“三从四德”。女性不能独立,地位低下。印度妇女的命运更是不幸,背负童婚制、嫁妆制、萨蒂制等传统习俗的重压。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其生存状况趋向分裂化、复杂化。二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十分传统保守的女性,逆来顺受,没有主导命运的能力。老舍《柳家大院》中的王家小媳妇、《月牙儿》里的“我”、《微神》里的“她”、《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等,纳拉扬小说中的加纳玛(《黑房间》)、玛拉蒂(《文学士》)等都很典型。
他们同时表现出对女性传统美德的认同。第二类,在新旧文化影响下动摇、挣扎的女性,这类过渡角色最有现实感,也最丰满。如纳拉扬《黑房间》从家庭的“黑房间”出走最终因经济原因回归的莎维德丽。因为已经开始清醒,但受制于现实条件心理最纠葛,感到的痛苦也最深刻。老舍则对有点觉悟的知识女性持保留态度,怀疑她们的浪漫自由,并安排了不乐观的结局:或受骗、堕落,或死亡,至少也是事与愿违。如《离婚》秀真、马少奶奶;《鼓书艺人》秀莲;《赵子曰》王灵石;《老张的哲学》李静和龙姑娘。由此可以推测老舍的女性观相对传统、停滞。第三类,相当强势、自我的女性形象,在现实中处于边缘状态。纳拉扬小说塑造了张扬女性主义旗帜,追求自我实现的新女性。如《画广告牌的人》中的黛西“是一个很强大的人物”①,印度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到70年代的产物,完全超越了家庭依赖和男性崇拜。纳拉扬对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经历了从怀疑到积极肯定的心理历程。有批评者怀疑其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老舍则大大不同,表现出保守、男权意识较重的一面,这在对大赤包(《四世同堂》)、牛太太(《牛天赐传》)、大姐婆婆(《正红旗下》)、虎妞等形象的厌恶、对“贤妻良母”系列的激赏中可窥端倪。读者发现这些女性积极的一面被刻意忽略了:坚韧、顾家、有主见等。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存在是“此在式的存在”②。恰点出印度和中国语言思维的特质,老舍与纳拉扬将这种特质发挥到淋漓尽致。纳拉扬(母语是泰米尔语,英语是习得语)在民族土壤中锤炼自己的“言语”:语言与生存活动本身骨肉相连的思维和话语方式。比如,梵语语法常用“那个……的,就是这个……的”句式,其形而上意义是:在不同时空中以不同形态出现的事物,实际就是同一个。纳拉扬表述着印度民族生活的几乎凝固的内在时间。
《向导》就是一个“相同主角、不同转世”的本生故事。不管是做向导的拉朱,罪犯拉朱,还是被奉为圣人的拉朱,都具有一贯性。这凝固的时间并非均质的,机械的,而恰恰体现着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瞬间照亮”的价值时间观。语言本身就是底层生活形态。尽管许多英译本很难将老舍语言原汁原味地再现,但民间化的比喻和意象像烙印一样宣告:这是老舍的语言,这是中国人的生活。
老舍和纳拉扬的语言风格都较轻快、温情、幽默。或许根源于对东方民间智慧、表达习惯的心领神会:“寓教于乐”,这在古印度民间故事和中国神话里可见端倪,轻快的叙述语调、话家常的亲切感是底层民众喜闻乐见的。纳拉扬的幽默与老舍如出一辙,这或许可以追溯到性格上的相似处。老舍在《谈幽默》中谈到幽默与讽刺、滑稽的区别:幽默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幽默的语言形式未必通向一个明确的道德目的,不显示作者思想的优越,但比只是逗笑的滑稽透着点“笑的哲人”的态度,比讽刺多一点想象。③
幽默是看出人间的缺欠,对着底层的小人物,冷眼嘲骂与赶尽杀绝是不必的。他们暗示小人物的真诚与伟大处,同时善意“指出世人的愚笨可怜,也指出那可爱的小古怪地点。”①一些学者已经看出老舍的幽默(或讽刺)与中国同时期的其他讽刺作家不同。
二人善于调遣方言,尽量让底层人物使用符合真实身份、习俗的口语说话,并通过细节展现浓厚的民族特色。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黄俊杰、张普等人使用计算机对《骆驼祥子》进行语言自动处理的结果表明,只要学会621字的小学生即可阅读它的90%。②由于浸淫的文化传统不同,如果说老舍主要倚赖对地域风俗人情的工笔写实描绘,纳拉扬的民族特色则深深植根于印度教文化传统,蒙上一层奇幻的轻纱;老舍小说体现为类似《清明上河图》般铺开的卷轴,具有浮世绘特色,儒家的世俗性、真实性压倒神秘性、梦幻性;而纳拉扬则像在真实事件的表述过程中,吹入一股无孔不入的风(气韵),氤氲着神秘和崇高的光晕。叙述染上更加浓厚的宗教色彩,人被一种高于一切的力量追问和召唤。国外读者往往需要有具体的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作为背景才能体会个中滋味。
在当代中国,伴随农村问题突出、农民工群体壮大、城市底层新建构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呼声,“底层写作”的意义日渐凸显。资料显示,目前创作主体呈现出较为分散、题材喜欢追赶潮流、创作内容单一、思想深度挖掘不够、创作技巧贫乏、形式粗糙等弊病,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不多。老舍与纳拉扬的底层叙述最值得当今的“底层文学”借鉴之处在于:第一,二人多采取平视的视角,尽量避免以启蒙指导式的俯视和美化式的仰视作品人物。让人物在生活现场自然叙述有缺陷的自己,为谁代言的痕迹不明显。第二,尽量避免形而上的概念表述与个人偏见,各阶层的读者都较容易读懂。“底层叙述”与底层的距离是衡量其成败的关键因素。这是叙述的“逼真性”问题。第三,他们的写作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阶级、时代、身份、题材束缚,甚至庸俗的道德评判、政治功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抗拒着任何包括“底层叙述”在内的标签。以上特点终究通过二人对底层生活的切身体会、深刻洞察与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实现了底层叙述的逼真性。当然,“完整的原生态底层声音的承诺,与不带偏见的纯粹生活叙述的承诺一样,都是乌托邦”③。
本文作者:续静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