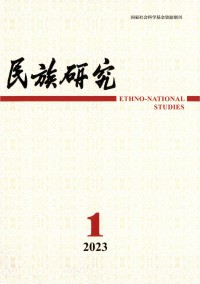民族与语言的关系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 :中华民族的语言艺术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根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音乐与语言的结合体,民族语言音调同民族音乐中的诸多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民族声乐中民族语言的运用,使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特征更加生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沉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声乐是民族语言文学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民族声乐艺术中,民族语言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族声乐艺术在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环境下的发展不仅受着民族音乐的影响,民族语言中独特的民族个性和语言特性也会对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化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民族语言与民族声乐的关系
语言本身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以民族语言创作的声乐作品在艺术的表现上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化的倾向。在不同民族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声乐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特征。语言音调因素分为表情因素和表意因素。表情因素是人类音乐共同拥有的因素,如悲哀的音调多为慢速下行,欢乐的音调多为跳动的行进等等,这就是音乐中感情表达的共通和共识性。而表意音调是基于人们语言归属的不同,表意音调也就不同。表意音调的升华,就形成音乐旋律风格色彩的不同。这就是声乐作品的民族性。它往往受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影响,如我国藏族民歌中具有高亢的装饰音,内蒙古民歌中迂回婉转的音调类似马头琴颤音的旋律装饰,以及维吾尔族民歌中热情、奔放、诙谐的特点等,都同各自民族的语言有着共同之处。
中国声乐作品的民族性表现不仅在音乐风格的民族化,作为一门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相结合的音乐表现形式,在同中华民族的语言习俗和语言文化结合时,民族歌词的语言特征在表达作品时也形成声乐艺术风格的民族个性。声乐是语言与音乐结合的艺术,同歌曲中词曲结合一样具有“诗乐合璧、调曲交辉的艺术魅力和音乐与文学融合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在不同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声乐艺术的语言表达有着更加具体和生动的民族特色。我国的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如:汉语发音单位由音节、音素、声母、韵母、收声等步骤及单位组成,从而形成了中国声乐演唱艺术自成一体的特点。因此,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一定要与中国语言文化相结合,使其在创作和演唱中更具有中国作品风格的艺术完整性,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具有语言独特性的作品中,语言艺术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民族声乐作品中常见的衬词、衬腔等,就是在民族民间丰富的语言文化及民族习俗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如《阿妹出嫁》《山里女人喊太阳》等都是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创作上运用的成功之作,而其中衬词、衬腔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特点。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声乐作品的风格表现就必须对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民族语言的音调与民族音阶、调式、节奏的关系
语言的表达和音乐的表现都依靠声音,二者有着共同的音调基础。中国各民族语言音调有着极丰富的音高概念,各民族语言的音调有着强烈的民族个性,由于音乐起源于语言的表情,属于表义音调,不同的民族音乐带有各自的民族特征。如我国四川语调中,多有la、do、la音调,四川音乐中多用羽调式。所以,一个民族或地区惯用的某种音阶,调式、节奏多与各民族语言或方言相关。“音阶”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音乐实践而形成的,有特定组织结构和完整体系。我国各民族的音阶关系不完全一样,就汉族的各大方言系统来说,音阶也不完全相同。如中原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变徵音级的七声音阶;北方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清角音级的七声音阶;西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闰音级的七声音阶;齐鲁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角或变宫的门声音阶;江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五声音阶等等。由于各语系所用音阶的不同,所以,音阶和音律,是划分音乐风格系列的最主要标准。“调式”在音乐中有着特定的组织结构,在调式中有一个主音,其他音与主音之间形成不同的音程和稳定关系的乐音体系。调式根植于音阶,是音阶中的不同音级在音乐作品中各自为主音而形成的调式体系。所以,谈到调式,必定是某种音阶中的调式,不同的音阶产生不同的调式。谈到音阶,又多是与调式相联系,即调式音阶。而同一音阶的不同调式,也令音乐产生不同色彩。我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是一个有着丰厚音乐传统积淀、能歌善舞的民族。由于各民族杂居的生活环境,使维吾尔族音乐融合了中国、欧洲和波斯(阿拉伯)3种不同的调式特色,风格奇特、色彩斑斓。如《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曲调就属于欧洲音乐体系中的弗里亚调式,以“mi”为主音,这种调式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民歌中很常见。音乐是时间和音响的艺术,节奏、节拍以及与此相关的速度是音乐的时间形式。音响运动中的轻重缓急、强弱长短的不同连接方式和组织方式,构成不同的节奏和节拍形式。节奏是指时值长短各音的连接形式。节拍是指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节奏关系的体系。节拍、节奏的形成,除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有着音乐的文化背景,尤其和人们的语言、行为以及长期的艺术实践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在生活语言中,节奏听觉惯性影响着不同民族音乐中的节奏特点。
三、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的表现
在中国民族声乐中,除了直接表现歌曲思想内容的正歌词外,也常常插入一些语气词,它们大都与正歌词没有关联,但如果和正歌词编配在一首歌曲中演唱时,它们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情感色彩,成为整个歌曲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衬托性的词句统称为“衬词”,衬词的曲调就称之为“衬腔”。衬词和衬腔的运用具有加重语气、活跃情绪的表现功能,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民族色彩。在中国民歌中,衬词与衬腔的地方区域性划分得相当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衬词与衬腔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语言特点,是民族语言在歌曲中的直接体现,传递着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的信息,表现着一定的民族气质。而汉族民歌中,也以区域划分出细致的地方语言特点,如湖南的《溜溜歌》、湖北的(转第73页)(接第61页)《得得调》、浙江的《里郎歌》、江苏的《杨柳青》、青海的《呛嘟哪令》、广西的《叮咚歌》等等。衬词和衬腔的加入,使我国各民族声乐作品的民族风格更生动、具体,更具有口语化、生活化和鲜明化的音乐表现力。
四、中国民族声乐表演中唱腔的民族化
如果说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基础雄厚、力量强大、影响越来越广泛的声乐学派”的话,那么滋养这旺盛生命力的歌唱艺术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直接作用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是民族的情感、民族的音乐风格和丰富的民族语言。声乐,是一种以人声来表现的音乐艺术形式,声乐的发声技巧和产生的音色是表现作品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民族声乐作品,在演唱形式上要求带有本民族语言的表现风格,甚至在音质上也要求人声具有形象感,所谓“竹不如丝,丝不如肉”。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语言特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特点,中国声乐有的民族唱法,是以地方语言(语音、声调)相结合的发声为基础,以风格化吐字运腔和保持嗓音的自然状态为枢纽,从而获取一种真实、朴实且丰富多彩、富有浓郁地方风味的独特性的音色。而歌唱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声,更要注重情感的表现,民族声乐作品中情感表现内容同民族语言的处理是密不可分的。在民族声乐作品中,民族语言同民族音乐的结合会使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加动人,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以字领腔(音),字正腔圆,韵味浓郁,唱演均重,神情兼备,真切动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民族声乐的广义概念,换句话说,“唱情”是民族声乐的一个本质特点。否则,作品的情感与词意就不能相得益彰,甚至会使词意与情感背道而驰。作为民族声乐的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民族声乐演唱人才的重任,在唱好和掌握好以汉语语言为基础的各地区民族声乐作品的同时,还要多掌握一些各民族的语言。经过实践证明,这些年培养的民族声乐人才活跃在我国的音乐舞台上,深受各地区、各民族广大人民的喜爱。在他们演唱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情感,而中国民族语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情感表达形式,地方腔调同地方的民族音乐在长期磨合中产生了大量艺术表现手段,形成了丰富的、生动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
[1]袁静芳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第2篇
一、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意义
我国境内的语言约有129种,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推行正确的语言文字政策,尤其是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呈现出较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需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必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具有提升语言学科研究活力的学术价值。过去我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注重对语言内部系统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相应地对社会生态环境对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民族语言生态系统等研究不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基本写法是先简单地介绍某一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如人口分布、地域分布、地理文化等),然后主要描写某一少数民族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前者虽然涉及语言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但语焉不详,所占篇幅很少,后者是主体,描写也非常具体、全面。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就是用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系统,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生态的各种变化。语言生态学(也称“生态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实用性强、富有活力的学科,它对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无疑提升了语言学科的整体研究活力。其次,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的关系、单一语言研究与不同语言比较研究的关系、语言本体研究与非本体研究的关系、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①。(1)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的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是一个变量,语言生态也是一个变量,它们之间是“共变”关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仅用共时描写是不够的,必须将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结合起来。如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曾是语言活力很强的语言(如满语),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具有很显要的生态位,而到了当今,却演变成为即将消亡的濒危语言了。这类语言的语言生态问题,如果没有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不可能找出它们从盛到衰、从强到弱甚至濒危消亡的真正原因。(2)单一语言研究与不同语言比较研究的关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应该认识到,我国的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把一种民族语言放在这个系统中进行语言生态研究,自然会考虑到这种民族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了。例如,在我国语言生态系统中,谈到语言接触问题,我们至少会遇到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的接触、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内部各方言的接触等现象,在频繁的语言接触中,语言生态的变化是复杂多样的,有的语言在接触中语言活力变强了,有的语言变弱了,语言替换、语言转用、语言兼用、双语、多语等现象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一句话,语言生态发生了改变,这些仅从单一语言上孤立地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不同语言放在语言生态系统的框架内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说明问题。(3)语言的本体研究与非本体研究的关系。语言本体研究是指对语言体系内部语音、词汇、语法等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里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语言的非本体研究是指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研究,包括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生活、语言与应用、语言与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戴庆厦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如除了在少数民族语言本体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之外,他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对语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对双语问题的研究、对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研究、对语言教育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4)借鉴与创新的关系。语言研究贵在创新,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是一个新课题,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学习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在新常态下应有新作为和新担当,要开辟一条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新路子。
二、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机遇
1.社会生态环境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创造了条件现阶段,和谐社会的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给我们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创造了最佳氛围。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是语言和谐,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和谐、文明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汉语与民族语言之间、民族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民族语言与外语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语言生态环境也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指出“:中国的语言,处在各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生态环境中,其发展既有语言的分化,又有语言的融合,两者交融一起难以分清。”②戴先生所说的各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生态环境正是现阶段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环境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新视野。语言接触会带来语言的一系列变化,会对语言的功能和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以黎语为例。黎语是黎族人民的母语,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海南省。海南省黎语的生态环境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前,由于四面环海的独特地理环境,黎族人民与外界接触较少,黎族社会基本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黎语与岛外其他语言(包括汉语普通话等)的接触相对较少,因而黎语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受外界影响较少、独自运用、独自发展的面貌,黎族人民运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族内交际,兼用其他民族语言的人并不多。正如欧阳觉亚、郑贻青两位先生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黎语调查编著而成的《黎语简志》一书所指出的那样:“除琼中东部靠近万宁和琼海两个县的部分地区和白沙县西北部靠近儋县的部分地区有少数黎人使用汉语外,其余各地的黎族居民都用黎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海南建省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创建以来,海南黎族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黎语的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增多了,黎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更加密切了,黎族人民使用黎语的情况也发生了改变。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在《黎语》部分(郑贻青执笔)中说:“21世纪以后,随着海南的进一步开放,外来人口不断增加,黎族操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黎族地区正朝着双语制的趋势发展。”④郑先生所说到的黎族地区发生的语言接触、语言转用、语言兼用和双语现象等正是黎族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给黎语生态带来的变化。这给我们研究黎语语言生态带来了良机。从理论上讲,语言接触使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态度、语言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改变,而随之出现了语言替换(语言转用)、语言兼用、语码混用等现象,而从民族语言整体上看,语言濒危、语言衰变等也不可避免。美国语言生态学家萨利科科•萨夫温说“:生态环境是语言演化和形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门语言的演化通过个体使用者以及他们的话语和习语得以推动,同时在各种个体语共存的情况下,由生态作用于变异。”⑤从黎语社会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角度研究黎语生态及其发展是切实可行的。
2.以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供了借鉴以20世纪50年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为代表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其基本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单一的少数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以民族语言本体为核心,描写其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等。现在看来,当时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有几点:一是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当做国家大事来抓,当时在国家经济尚不宽裕的情况下,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分成7个调查队,深入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二是一大批专家学者以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为己任,具有吃苦耐劳、勤恳奉献、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如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当年还是个年轻人,随第3调查队深入哈尼族、景颇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年,这种多年如一日的融入式调查研究,使戴先生成为景颇语、哈尼语研究的权威专家,也使得我国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得到世界同行专家的认可。三是讲究科学方法,强调协作精神。当时为了做好大调查工作,组织了全国性的语言调查培训,特别注重国际音标记音训练,要求语言调查者应掌握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掌握田野调查的方法,搞好民族关系,搞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搞好调查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协作精神。四是精益求精,旨在推出精品。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大调查是一项重大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这项工程“打磨”出的学术精品。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除了继承这种语言本体研究的优良传统之外,还要重点研究:第一,少数民族语言的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萨利科科•萨夫温认为研究语言演化生态学,“不光要关注一种语言所涉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种环境(其外在生态[externalecology])……还要关注语言系统在变化前及(或)变化中各个语言单位和规则相互共存现象背后的本质(其内在生态[internalecology])。……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在决定一种语言的演化轨迹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⑥第二,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主体。人是决定语言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主体即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者,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选择、语言能力等是决定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能否生存、能否保持语言活力,发挥交际功能的关键。在《语言生态学引论》中,我们强调人在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指出:“人是语言的运用者、操作者,人类社会中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也是民族的凝聚物。一个民族的语言如果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失去了它应有的位置,它可能会消亡,可能会出现濒危,等等。这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例如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对官方语言的选择、对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的选定等,都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⑦。3.语言和谐共存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出了挑战我国语言政策的目的是语言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和谐共存。国家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允许地方方言的存在和发展;国家把汉语普通话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同时,也鼓励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这种语言政策为我国的语言和谐共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也是我国建构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肥田沃土。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现阶段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一个重点。语言与语言之间,不论是强势语言还是弱势语言,不论是使用人数多的语言还是使用人数少的语言,不论是兴盛的语言还是衰变甚至濒危的语言,都应该是平等的,语言平等原则是我处理民族语言关系最重要的原则。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时,我们应该运用这条原则指导具体的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评价,决不允许歧视弱势语言,歧视使用人数少的语言,歧视衰变语言和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是现阶段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一个难点。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濒危,还有的语言处于衰变之中。“赫哲语、满语、普标语、义都语、苏龙语、仙岛语等,使用人数已不足百人。如今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上述六种以外)有15种。这些都是‘濒危语言’。”“在我们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语言的消失不会是由于人为的压制;但是一种语言的消失,终归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消失,抢救濒危语言也是当前我们能做和应该做的一项紧迫任务。”⑧
三、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路径
既关注语言本体的研究,也重视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研究语言本体,注重揭示语言结构体系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和规律,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所在。从语言的发展上看,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会给语言带来变化。因此,弄清社会生态环境及其对语言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周国炎先生的《仡佬族母语生态研究》一书研究已处于濒危状态的仡佬语的生态环境,提出保护仡佬语、维护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主张。熊英的《土家语生态研究》一书同样以濒危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土家语的语言生态方面探讨该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濒危语言、衰变语言是世界语言发展演变中的一种易发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虽然跟语言的内部结构有联系,然而更多地与语言的生态环境以及这种生态环境带来的语言功能的变化、语言活力的增减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及使用人数等有密切关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深入民族地区,做好田野调查工作。20世纪50年代语言大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田野调查工作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可以说,没有扎实的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就没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就没有学术精品。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不做基本的田野调查工作,是无法取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成果的。戴庆厦先生指出“: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才能真正体会语言是什么。语言在实际生活中发生变化,不到群众中接触语言,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语言的存在和变化。一个有作为的语言学家,对语言要有感性和理性两方面的认识,如果缺少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就没有根基;如果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理性认识,认识的层次就得不到升华。田野调查是语言学家获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取之不尽的源泉。”⑨戴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来,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不少于50次,成果丰硕,即使现在他80岁高龄,还常常奔波在田野调查的第一线,我们应该学习戴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了解民族语言生态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生态特征,即使是同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内部也可能会有若干种方言,方言与方言之间也会有不同的语言生态特征。如黎语具有鲜明的语言生态特征,黎语内部的五个方言的生态特征也有差异。由于黎语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从宏观上看,海南岛四面环海,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新中国成立前黎语受岛外语言的影响较小,这一方面有利于黎语的传承、保护,另一方面也使得黎语相对封闭,与岛外语言的接触相对少一些,由此引起的语言生态变化也相对小一些。从微观上看,黎语内部的五个方言(哈、杞、美孚、本地、加茂)中,使用人数多少不等,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语言内部系统也有差异(加茂方言与其他四种方言差异较大),各方言的语言活力、语言功能等也有所强弱之分。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研究黎语生态就可以根据其生态特征有的放矢,真正弄清黎语及其方言的语言生态面目,以免漫无边际,盲目行事⑩。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作 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55-005
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an Zhiman
Abstract: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a crossing subject. It emerges and develops in the background of Anthropology. Wester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goes through several periods, such as field-work,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ethnic groups and many languag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as a wide base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y subject. Meanwhile, it holds important meanings to protect the diversif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make different language ethnic groups respect each other, and to make language ethnic groups dialogue harmoniously.
Key words: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ulture, Subject construction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 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 Phi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 kSalzmann.Language Culture & Society--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Westview 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第4篇
一、同与异的关系
同与异的关系存在于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比如在语言上:同一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这是同;使用不同的语言,这是异。在新词术语的选择上,有些语言采用同一来源的借词,这是同;而有的语言各自使用本语固有的词,这是异。在文字上,不同民族有的使用相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而有的则使用不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即使是同一民族内部,有的只使用一种文字,而有的则使用几种不同的文字。有的文字与现在的口语一致,而有的已经脱节,等等。民族心理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同和异,往往因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时间而有不同的选择,其不同的态度受着不同社会特点的制约。
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认同感,所以一般都会认为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成员在民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上应是相同或最好是相同的,而且总希望相同的成分越多越好。因而,民族心理所表现出的状态往往是趋向于同,即愿意看到共同点,对共同点估计得比较充分,而不愿看到相异点,对相异点的估计往往偏少。如对待语言归属问题,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同一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总想把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语言看成是方言的差别。这样一来,受民族心理制约的感性认识与对语言的科学认识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以我国景颇族使用的语言为例:景颇族内部存在支系的差别,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些语言中,景颇语同载瓦语等语言差别较大,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载瓦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相互间的同源词不到1/3,一些常用的基本词也不同源,而且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很不严整。其次,在语音、语法上也有一些差异。国内外研究景颇族语言的专家通过语言比较,几乎都认为景颇语和载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由于景颇语和载瓦语相差较大,原有的景颇文(创制于19世纪末,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难以适应说载瓦语的人们使用,客观上需要创制一种适应载瓦语特点的文字。但在景颇族内部,许多人出于统一的民族心理,不愿承认景颇语和载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尽量强调景颇语和载瓦语的相同特点。这种心理与语言文字使用的客观规律是不一致的,而人们决定怎样认识景颇族语言以及怎样解决他们的文字使用,则只能遵循语言文字演变的客观规律。
又如,对云南蒙古族使用的嘎卓语的归属认识,统一的民族心理也有过强烈的反映。嘎卓语是云南蒙古族使用的语言,它不是蒙古语,而是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种语言。云南蒙古族为什么使用了彝语支的语言呢?元朝忽必烈率十万骑兵于1252年进攻云南,由于1381年明军击溃了忽必烈军队,使得这部分蒙古族官兵在今通海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主要民族彝族的女子通婚,以致出现了语言转用,由原来操用蒙古语转为彝语。后来,他们操用的彝语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嘎卓语。但由于嘎卓人还清晰地知道其祖先是北方的蒙古族,因而与北方的蒙古族存在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的支配下,他们希望自己现在使用的语言也是蒙古语,而不愿认为自己操用的是一种接近彝语的语言。当他们听到有的语言工作者提出嘎卓语有蒙古语底层的见解时(后经比较研究证明,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感到非常高兴,很快就接受了这种错误见解。他们甚至用嘎卓语和蒙古语相同的“宾动型”语序以及某些词偶然的语音接近,来论证二者的同源关系。后来的比较研究成果,已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嘎卓语既不是蒙古语,也没有蒙古语的底层,而是一种属于彝语支的语言[1]。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个民族在对待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上,存在着“求同”的趋向,而对待自己的语言文字,又存在“存异”的心理。所谓“求同”,就是希望各民族语言文字能增长共同成分,以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这种统一的心理,在1957年12月10日国务院批复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中作为民族语文政策得到了具体体现。其中包括: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字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者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各民族的文字,特别是语言关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的形式和拼写规则上应尽量取得一致。”经数十年的新文字的试行和推行效果证明,这些基本原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语言文字使用规律的,是受到各民族普遍欢迎并得到认可的。我们的国家,不同民族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在设计新创文字时,若能在字母形式和用法上尽可能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或汉族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对于新创文字使用现代化手段,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必将会造福于子孙后代。当然在具体贯彻这几项原则时应适度,不能影响文字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即不能为求“同”而“削足适履”。
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民族仿照汉字创造了类似汉字的文字系统,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哈尼字等,这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求同心理。这些以汉字为基础创制的文字,形成了一个“仿汉字”的文字系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仿照汉字创造文字的做法还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这些国家也以汉字为基础创造了适合自己语言特点的文字。不同国家的人能够采取相同、相似的文字形式,这与邻近国度人们之间的求同心理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对待语言文字除了“求同”的心理外,还存在“存异”的一面。“存异”,指的是各民族都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字,都要保存自己语言文字的特点。不管哪个民族,都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对语言文字的不尊重,都会被认为是对民族的不尊重。求同和存异共存,是辩证的统一。
即使是属于同一民族而分布于不同国家的跨境语言,在使用什么文字的问题上,民族心理也趋向于“求同”。如苗族除了在我国主要聚居分布外,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菲律宾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也有分布(其中大多是移民造成的)。国外苗族主要使用苗语川黔滇方言。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不同特点,其语言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而且在文字上也有差异。可以预计,这种差异在今后还会加大。但是,不同国家的苗族普遍存在着“求同”的心理,希望“国内与国外之间应加强互相交流与学习,以缩小二者之间的差别,促进双方的发展。”他们还希望能共同使用一种相同的文字[2]。当然,这种愿望至少在近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语言文字的分化与统一是受社会各种条件制约的,而且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民族语文工作中,虽然要注意“求同”的民族心理,但求同的原则不宜泛用。在有的条件下,求同是可行的,而在有的条件下,则是不可行的。之所以不可行,或是因为违背语言文字演变规律,或是时机不成熟。下面所举的就是不可行的例子。
对于少数民族文字中汉语借词如何拼写的问题,过去曾一度出现过“求同”的做法,即:使用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拼写汉语借词时都照抄普通话拼音词形。以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向汉语靠拢,而且可以做到各民族借用汉语借词在拼写法上取得一致,尽可能增长各民族文字中的共同成分。这种愿望是良好的,如果能够做到对各民族是有益的。但是经实践证明,这样做违反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应用的规律,而且给少数民族拼写自己的文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各民族语言从汉语借用自己所需要的新词已有很长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我国民族团结的不断加强,各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少数民族语言从汉语里吸收借词的数量比过去更多了。如果新老借词怎么说就怎么写,在使用中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而如果硬性规定借词按普通话拼写,在书写时就必须分清哪些是汉语借词,哪些是本语词,还要分清哪些是老借词应按本语读音拼写,哪些是新借词应按普通话拼写。这样做,在文字拼写上就出现两套拼写规则:一套用来拼写本语词和老借词,一套用来拼写新借词,势必造成学习、使用上的困难。1958年以后我国试行的几种新文字遭受挫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硬性规定汉语借词照抄普通话和大量使用汉语借词。这种不看条件的求同心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愿望,以为这样做是好事,但后来经过实践才逐渐使大家认识到其危害性。
二、变与不变的关系
语言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总是随着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当然,语言文字的变化是缓慢的,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它的变化。在对待语言文字中变与不变、怎样变的问题上,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持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语言文字的使用。
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变化,民族心理在多数情况下趋于保守。如:一个新词使用后就不愿改动;不愿改动与口语不一致的文字;不愿改换原有的拼写法等。要对语言文字做些改动,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是不愿改的。
藏文创制于7世纪,拼写的是当时的藏语语音。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藏语语音有了明显的变化,如复辅音声母简化为单辅音声母,辅音韵尾也出现了简化等。这样,藏文就与现在的口语出现了脱节现象,给藏族学习藏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大量的词语要靠死记才能拼写出来。尽管如此,藏族并无改革文字的要求,普遍对这种与口语脱节的文字含有很深的感情,甚至有不少人还认为这种文字是不能改变的。藏族对藏文的这种特殊感情,既与藏族长期使用这种文字有关,又与藏文记载大量宗教经典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形成了藏族不愿改动藏文的共同心理。
景颇文从创制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经推行实践证明,景颇文大体能反映景颇语的特点,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缺点是:代表音位的双字母和三字母附图过多,造成书写和印刷上的不便。所以从50年代起,民族语文工作者多次有过修改双字母和三字母的考虑,但都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坚持不改的人,习惯于现行的字母,认为双字母、三字母没什么不好,无非是多写了几个字。特别是分布在缅甸的景颇族,由于人口多,比较聚居,景颇文使用的范围比较广,更不愿修改文字方案。他们强烈希望我国不要改革景颇文,以保持两国景颇族使用文字的一致性。1956年中缅两国在芒市举行的边民联欢会上,缅甸吴努总理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中缅两国景颇文应保持一致的建议,周总理当即表示同意。现在看来,景颇文方案没做重大改动是对的。
几十年来民族语文工作实践经验证明,改革文字应采取慎重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曾帮助四川凉山彝族设计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耗费了不少人力、财力。这种文字几经试验推行,都未能扎根下来。原因何在?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彝族原有音节文字的作用估计不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文字在试验推行期间几经修改,丧失威信,致使群众对这种常变的文字失去好感。而彝族原有的音节文字,曾在历史上长期使用过,彝族对它已有一定的感情,很容易接受它。所以当这种规范的音节文字取代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之后,很快就在彝族地区普及开来,取得了预想不到的好效果。
文字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与宗教、风俗、习惯密切相关。文字一旦出现,就成为该民族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久而久之,人们就对文字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赋予它一种神圣感或神秘感。特别是对一种历史悠久、记载过历史文献的古老文字,人们对它都有一种崇敬的心理,自然是不愿轻易改动。即使看到它有某些缺点,也甘愿“委曲求全”。至于主要用于宗教的文字,更是神圣不可侵犯,再难也要去学。总之,文字改革常常遇到阻力,或者遇到挫折,或者走回头路,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对文字的保守心理状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语言中的一些词语,如果在造词中所含意义不当,或后来所指对象有所变化,人们也不愿轻易加以改动,往往赋予它以新的意义继续使用。景颇语的“中国”一词,很早就用mi[31]附图(即“汉人国”义)表示。现在看来,这个词所包含的词素意义不符合人们后来对“中国”的理解。所以,过去曾有人提出不用这个词,最好改为汉语译音词,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不改的人认为,这个词已被群众所接受,其意义已由“汉人国”转指整个中国。“黄狗”一词,景颇语称kui[31]khje[33](即“狗”+“红”),因为景颇语的颜色词系统在最初只有“红”色,而无“黄”色,“黄”色用“红”色表示,到后来才出现了thoi[31]“黄”一词。但人们并不把“黄狗”改为kui[31]thoi[31],而仍然使用kui[31]khje[33]。这就是说,某种语言形式一旦被人们长期使用,要改就比较困难。由此看来,要人为地改变语言的某一形式或意义,一定要慎之又慎。
我们说民族心理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变化趋于保守,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或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人们对语言文字中的变化相对会开放一些。比如在我国建国初期,各少数民族语言都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甚至有些是本语中已有的词也用汉语借词代替。变革时期语言文字的变化,有时会猛一些,其中有的变得合适,也有变得不合适的。变得不合适的,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还会通过语言文字的内部规律得以调整。
三、纯与不纯的关系
世界上的语言,相互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不受别的语言影响的纯语言是不存在的。不过,语言影响有大小之分,有的语言受别的语言影响大些,语言中夹杂外来成分多些;而有的语言受别的语言影响小些,语言成分相对纯些。我国各民族语言之间都存在语言影响关系,特别是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带有普遍性,语言影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的变化均起到重要的作用。怎样对待语言影响,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而持什么心理也会影响到语言文字的使用。
就多数情况而言,对语言成分之“纯”与“不纯”,民族心理一般偏向于“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情感,都注意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看待自己的语言,自然是希望母语中固有成分越多越好,不愿被人认为母语中外来成分比重很大。“你说的是一口纯正的话”,往往含有褒奖之意;而“你说的话怎么有这么多外来借词”,常使听者感到不悦。受外族语言影响大的语言,操这种语言的人大多不愿承认自己的语言是混合语。但是,人们又无法抵挡别的语言的影响,别的语言的词语总会源源不断地、不知不觉进入自己的词汇系统,甚至还会夹进某些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这就构成了民族心理的愿望与客观实际的流向存在不一致的状态。一种语言吸收外来语成分,总是在民族心理偏向于“纯”,而客观上则需要外来成分补充的对立矛盾中逐步进入的。
虽然民族心理对待外来语成分一般偏向于“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条件下,其程度会有所不同。当一个民族受到异族侵略或歧视、处于不公正的地位时,会出现抵制外来语影响的情绪,即使是已进入本语的外来语成分也要设法将其“清除”出去。20世纪50年代英语外来词难以进入汉语,包括在此之前已借入汉语的英语借词也被汉语词所代替,固然与汉语不易吸收外来语的特点有关,但还与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孤立中国的心理有关。新中国建立后,汉语借词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是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友好关系不断加强、少数民族日益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分不开的。少数民族对待汉语借词都有一种亲切感,都愿把它当成“家人”对待。汉语词进入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两种语言的词汇交融在一起,在不同的层面上(语素、词、词组、句子)汇成一体。由于吸收了汉语借词(有的语言还吸收了别的语言的借词),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更为丰富,由相对的“纯”变为“不纯”。汉语借词丰富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提高了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表达能力,无疑这对少数民族是有利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民族语文工作中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不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客观规律的倾向,使得一些民族出现了逆反心理,不愿接受汉语借词,甚至还要把已在自己语言里生根的汉语借词改为本语词,片面追求语言的“纯”。两种心理,两种做法,造成民族语文工作的一次反复。
民族心理是一种社会范畴,又是一种历史范畴,它是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积累到一定时间后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由于民族心理是民族历史某一阶段的产物,而又与民族的其他特征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稳固性的一面,不易改变。但由于民族是发展的、变化的,因而民族心理也是可变的。所以对待语言文字的民族心理具有两重性:稳固性和可变性。民族心理有的符合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有的则只能是一种不能实现的(或在短时期内不能实现)的主观愿望,甚至与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不一致。民族心理会随着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有可能从一种认识转为另一种认识,由一种不符合客观规律(或不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愿望转为符合客观规律的愿望。所以,我们在制定民族语文政策或处理民族语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时,既要考虑民族心理的因素,又不能完全以民族的一时愿望做为依据。而应具体分析制约语言文字的各种因素,正确掌握语言文字演变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判断。凡符合语言文字演变规律的民族心理,应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而不符合语言文字演变规律的,则应因势利导,说服等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民族的根本利益(注: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对于什么是民族心理,现在的认识还不一致,这是民族理论中尚未解决好的问题。)。
参考文献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26-05
引言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语言资源由语言本体和语言应用两部分构成。语言本体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系统,是语言资源的物质基础;语言应用包括人类社会对语言的各种使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是语言资源价值的具体体现。贵州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蕴藏着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目前贵州省的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中,除了土家族、回族转用汉语外,其他都有自己本民族语言。全省14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有900多万人口以母语(即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交流工具。但目前少数民族语言的消失总体上呈加快趋势,仡佬人口中仅有1000多人会说仡佬语。可以说,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贵州少数民族语言不但是贵州省少数民族群众日常交际的重要工具,也同样承担着传承各少数民族灿烂文化的光荣使命。这些不同特色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也同样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一、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义
虽然总的看来,我国由于在民族关系、语言关系上坚定地执行了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方针、政策,各民族语言不分使用人数多少一律受到尊重,民族语言从主流上说是和谐的。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发展,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特色正在加速褪色,年轻一代已经日益远离自己的母语,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附丽于语言之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在日益同质化,同样面临着消失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系统研究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加强民族语言研究是增进民族间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保障祖国统一的重要措施。但是,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里,不同的语言共存于一个统一的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竞争。正确处理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2.贵州少数民族语言有着多方面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贵州的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但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对语言谱系分类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本体研究上,也体现在文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上。抢救、记录和保护濒危语言,维护语言生态多样性,对学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维护我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格局都至关重要。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这一工作的迫切性更加突出。
3.为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一种思路和借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随着各种媒体现代化速度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随着一些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地区、族群的迅速开放,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传播力度的加强,一些弱势语言的功能将更加减弱,面临消亡的危机。在这种人文和经济环境下,如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来传承民族文化是一个重大问题。目前,大多数地区都把文化旅游当作一种开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普遍模式。但是,以旅游的方式来开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资源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它往往会因经济利益问题而使很多行为显得短视和功利,不利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系统保护。应该构建一种能够在经济浪潮中系统地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模式,争取做到在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过程中也系统地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二、目前的研究
我国有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数不足一千。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关注,可以说是从罗常培先生开始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罗常培先生就利用应邀到云南大理帮助重修县志的机会记录少数民族的语言,并在1950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就已经讨论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中所反映的造词的心理过程与民族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
自1979年5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学者们却没有料想到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少数民族语言会面临如此严峻的生存现状:从意气风发地讨论民族语言调查和民族语言文字创制及设计问题,到讨论的是濒危语言问题。几十年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和反差,是学者不曾想到的。
目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已渐趋与语言濒危现象研究结合起来。虽然对“濒危语言”的界定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语言活力的9项评估指标进行评估,我国境内的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都可以归于濒危语言之列。因此,目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也多是从研究濒危语言的角度出发的。在濒危语言研究中,人们比较重视濒危语言产生原因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有助于对语言的发展前景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对于制定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也同时着眼于寻找不同的濒危语言中的共同点,试图发现语言衰亡的一般规律。可是,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并不是那么简单,人们发现有同样系属关系和历史背景、使用人数接近的语言,生存状况常常有很大的差异;而一些系属关系、历史背景不同的语言却存在着逐渐衰亡的共同趋势;有些语言在衰亡的过程中能够发生逆转,而有些语言的衰亡趋势却无法遏制。这说明导致语言衰亡的原因并不是同一的,需要通过全面、综合的分析,寻求各种语言消亡的共同原因和具体语言中的特别原因。事实上,导致濒危语言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家的文字政策、生存环境、社会转型、有无文字等诸多原因都可能导致某种语言的衰亡。
但是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并不能涵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全部,它缺少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关怀,缺少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尤其是利用方面的研究。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所以还应该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积淀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也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模式。因此每一种语言自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研究应该和文化研究相互参照,应该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着手,多角度多方面地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如从语词语源的角度,从文化变迁与传承的角度,从造词心理与民族文化程度关系的角度,从地名变化与民族迁移关系的角度,从亲属称谓与民族婚姻制度关系的角度,等等。这样多角度的研究可以使语言研究与文化充分结合起来,使语言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社会责任 感,具体体现人文科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弱势语言的陆续消亡,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全球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濒危语言问题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个方面,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就是把语言看作一种资源,合理地加以开发利用。就语言研究层面而言,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对印第安语资源的广泛研究和充分利用。从国家政策的层面来说,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把国民经济发展、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创立了将贸易与语言学习尤其是外语学习密切联系的模式,并把平等(Equality)、经济(Economies)、丰富(Enrichment)和对外(External Engagement)作为语言政策的社会目标。这种语言政策被国际上认为比较成功的一种语言政策,也是语言研究成果在国家语言政策上的积极运用。
三、如何保护和利用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
1.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视角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角度的不同对于观察结果的重大影响。因此,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选择怎样的研究角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贵州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应该坚持文化语言学的视角。文化语言学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语言学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一个交叉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某一社会内部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的文化类型和语言类型的异同;重视语言和文化的现状,更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法国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A.梅耶(Antoine Meillet)曾经说过:“不明白使用那种语言的民族生活情况,就不能了解这种语言;不了解那些人的语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习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是文化语言学的直接目的,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只有与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研究联系起来,才能立足于深厚而鲜活的土壤,才能真正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的奥秘所在,也才能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社会文化资源,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本体研究上,也体现在文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因此,应该站在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把少数民族语言中所蕴涵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都纳入研究视野,通过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整体性研究,整体把握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全貌,在研究其存在状况的同时也研究其存在方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如何有效保护这些少数民族语言资源。
2.语言之间的共生机制
人类社会的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共生机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已经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的巨大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不仅依赖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也依赖于人类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在语言领域,这种文化多样性充分体现在各种语言中的借音、借词和语法形式的借用等层面。在词汇层面,各种语言中的借词和译词都是受其他语言影响而产生的新词。汉语的借词和译词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国内各族的,另一种是来自国外的。中文里受欧西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借词和译词,除多来自英语外,还有来自德、意、法、俄、葡等语言。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也有非常多的外来词汇。在句法层面,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欧化句式,其原因则是受到欧洲语言,尤其是翻译的西方小说语言特色的明显影响。
语言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不光是汉语受到英语等其他语言的影响,其他语言也受到汉语不同程度的影响。如马来语中的angkin借自汉语闽南语的“红裙”,bami借自闽南语的“白面”,tehkowan借自闽南语的“茶罐”;印欧语里关于“丝”的语词则无疑是从中国的上古音*siag借去的。而现代英语中long time no see(很久不见)、drinktea(饮茶)等典型的中式英语(chinglish),已经成为标准的英文词组。据统计,《牛津英语词典》中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汇有1000余条,涉及范畴包括饮食、生物、宗教、哲学、政治等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英语”是世界语体系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个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中,大批研究报告开始发表,各种新技术新观点被应用,形成了诸多的分支,对语言学、二语习得、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语言之间的共生机制也反映在语言谱系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上。一般说来,亲属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同源成分必定具有明显的成系列的对应特点,但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的形成,虽然有语言自身发展变化的影响,但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也同样关注不同语言之间的类型的相似性,并试图解释这种类型相似性的产生原因。这种类型相似性除了语言谱系上的同源性以外,非亲属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所谓的语言同盟现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反映。
这足以说明,人类语言的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共生机制。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一个黑暗中的独行侠,而是一位拿来主义者。只要是对自身的发展有用的东西,他都不会错过,而是大胆地拿来。反过来看,在进行语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关注这种“拿来主义”,关注语言之间的共生现象。
3.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对贵州境内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首先要对这些语言资源的存在方式及状况作以整体性调查研究,并尝试构建某种有广泛适应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这种模式应该既是对目前以旅游为主导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分享的扬弃,又是对把少数民族语言单纯地作为一种濒危语言进行研究的扬弃。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依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但要考察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语言形式,而且也考察各种能够反映或蕴涵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变化或存在状态的文化形式,如民歌的原生态唱法、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品等等。尤其是民歌原生态唱法,这种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民歌正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历史的传承方式,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是语言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这个方面却一直被传统的语言研究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把民歌、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品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都纳入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研究这些文化艺术形式中所蕴涵的语言因素。同时,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共生现象也纳人研究视野,通过研究语言共生现象来探索其中所蕴涵的人类社会和平相处的共生奥秘。这样,将有效地扩大传统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利于更好地发现少数民族语言的某些本质,发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某些特质,从而也将更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系统的保护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