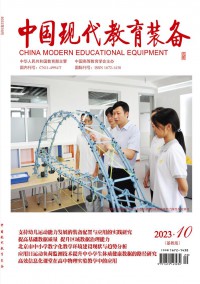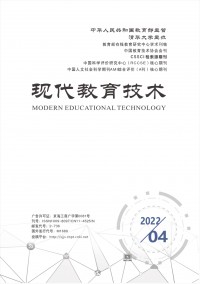现代教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时,在与他的英文教师亚丹进行的一番中国教育现状的谈话中,亚丹所说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的一席话对胡适启发颇深①,让胡适领悟到大学教育对之于一种新型文学创造的支撑作用。事实上,从中国新文学生成史来看,大学海纳百川的文化集成和引领社会文化风尚的特征,以及文化创造的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对文学写作无疑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采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延揽人才让大量的新文化倡导者进入北大校园为新文学提供生长的土壤关系甚大。蔡元培的举措不仅使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新文学的创始人借助校(北京大学)刊(《新青年》)结合所开创的文化空间具备了新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学校园文学写作的新生阵容也得以萌生,如北大学生组成的新文化团体“新潮社”及其创办的刊物成为新文学草创时期的一支主要力量,“新潮社”的小说创造与同时期鲁迅的小说创作相映成辉,展示了新文学最初的实绩。
从某种意义来讲,在新文学初始阶段,大学校园的师生充任了新文学创作的主力。发出“文学革命”先声和最早进行新文学写作尝试的是北大的师生,“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冰心,以“问题小说”引起文坛瞩目时还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作为舶来品的“文明戏”之所以能在中国形成气候,南开的戏剧活动开展的活跃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20世纪20年代初期女性写作中非常活跃的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等都与她们接受的新式教育有关。据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介绍,20年代中国的文学社团绝大多数为在校的青年大学生组成,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地区如此,文化边远地区同样是在校接受教育的学生扮演了当地文学写作的主要角色。恰是新式教育所培植的富有现代意义的思想、价值理念,勇于开风气之先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白话作为“国语”的身份确立所带来的教育革新都为运用现代文体表现现代人情感的新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现代教育之于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从事教学活动,特别是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大学讲台上传播新文学,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这实际上就是在为新文学写作不断地挖掘活水源头。1928年,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讲授中国现代文艺,1929年春,朱自清首次将《中国新文学研究》引进清华大学的课堂,其他如周作人、闻一多也都有在大学讲授新文学的经历。他们以新文学知名作家的身份直接面对学子,其价值或许主要不在用“知识”的品格与占据着当时大学文学教育主流的传统文学课程相抗衡,而在于以现身说法和言传身教的方式展示了新文学的魅力,培植了学生对新文学的兴趣并进而影响他们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从上述简要描述与分析中,不难看出现代文学写作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教育体制的血肉关联,正是现代教育培植的精神特质、文化品格、开阔视野,以及薪火传承的文学思想和技能,促使校园不断地生长着推动文学发展的原始动力。
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现代教育在“现代文学”成为一种知识类型即成为一门研究学科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上面提及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任教,在课堂上引入一些新文学的内容,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开设赏析性的或语文习作示范性质的课程是这一学科建立的契机。事实上,在晚清新政中应运而生的中国新式教育,在注重事功教育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科教育中的“虚文”不可或缺,但绝非在课堂上培养“能工诗赋”的功夫,课堂讲授的应有之义应是“文章流别”与“史”,参照西方学科建制,“文学史”逐渐成为文学教育中最重要的知识类型②。知识在原始的层面上是对经过检验的事实的陈述,文学史原本也应是对文学历史的真实呈现,因此,将文学史视为最理想的文学知识类型倒也情通理顺。正是大学教育机制中重视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促使以史的叙述为基础的新文学的学科建制初现端倪。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分外重视建国前那些力图将新文学史引入课堂的努力与尝试。最早将新文学史进行条贯梳理,将其作为一种“知识”引入大学文学教育体系的是朱自清,他于1929年春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编写了一份作为讲义的“纲要”,试图对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新文学历史进行全景式的勾勒,他从晚清文学的变革入手分析了新文学产生的历史缘由,继而描述了“五四”文学秩序的建构并在此框架中对具体作家创作进行了解读,因为所讲述的文学历史还未经过更长时间的沉淀,他在作判断时尚显拘谨,但结合社会的变革和文化思潮的演进讨论一种新型文学的生成和以文体分类结构史的叙述还是呈现了较为完整的知识形态,竭力靠拢着大学学科设置的基本要求。虽然本课程在清华开设的时间不长,但却筚路蓝缕,为新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和形成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此后,30年代初,周作人在辅仁大学的讲演对新文学源流的阐释,以及周扬在延安鲁艺将新文学运动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对其发展脉络的勾勒,都可视作是借助教育将“现代文学”学科化的努力,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在“史”的叙述中突现了新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以大学的课程模式规范着文学知识,使之成为一种有机的具备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知识结构来适应现代教育体制的要求。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真正建立是以50年代初新政权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准则改造大学文科课程设置为契机的。1950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文科课程草案中将“中国新文学史”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目,任务是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新文学的发展史,突出“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的介绍。随后,李何林、老舍、王瑶等人根据教育部精神编写了“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确定教学目的之一为“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③。很显然,成为学生必修课程的“新文学史”责无旁贷地肩负着从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来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使命。紧接着几部用新民主理论阐释新文学运动和作家创作的文学史问世,而这些奠定了学科基础的史著几乎全是顺应大学教学的紧迫要求编写的。因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科调整和急于满足将新文学纳入新的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而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向新文学教学、研究的王瑶,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写恰是因为各大学要推出新文学课程且无蓝本可以依据而纷纷向他索取讲义的缘故,这本第一部全景描述新文学史著作事实上是以教育部的课程设置要求和文学教育的教学要求为内核的。此后,许多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大学文学教育的教科书的面目相继出版。正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教育机制的保障,新文学学科形成是水到渠成,并且完成了由“新文学”向“现代文学”命名的转换,其作为大学汉文学专业二级学科的身份得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在建立之初受到了其他文科学科无法比拟的礼遇,这一学科所规定的教学目的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虽然从1917年诞生的新文学,短短的30年历史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学相比,既无历史积淀的深邃感,也无审美积累的优势,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同步的,现代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描述的形象历史即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写照。课程按照中国现代革命的线索,把无产阶级文学即20年代出现的早期普罗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的脉络延续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潮,对具体作家的分析、评价也充斥着诸如阶级、革命、进步、反动等价值倾向鲜明的术语。整个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渗透着50年代官方权威的政治革命话语,被严格限定在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图景之中,文学史知识因此丧失了历史的客观性而烙印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痕迹。
文学教育之于“回到现代文学”的意义
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显学”,在新时期的重归五四启蒙立场的语境中倍受甘霖滋润,焕发出勃勃生机,甚至一度在文学研究诸学科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在大学课堂上也是倍受学子们青睐的课程。然而,曾经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以及学科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学教育,此时也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某种裂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陈平原先生所说的大学课程设置与学术研究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即课程设置规范要求与学术研究突破规范的创新要求之间的矛盾④。如果说大学课程中的现代文学以传播文学史知识为主要内容,是在日益强调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学科建设的学术氛围里自然生发的结果,是在确保建立在特殊观念上的知识类型的相对稳定性,而研究者可能借助另一种文化视野,窥见了这一知识类型的不可靠性而力图拨开迷雾再现真实,但去蔽的任务却几乎不可能完成,波普尔曾说,知识一旦构成便有了其自主的力量,有了自我生长的和客观性的力量。因此,建立在强势话语根基之上的知识往往会深深楔入人们认知的经验之中难以消除,这也就是为什么直至今天,我们不断地在研究中拆解着以往充斥着政治话语的现代文学历史叙述,却无力撼动课程内在架构,超越其所规定的基本范畴的根本原因。从这个层面来讲,大学教育中的现代文学非但不能成为本学科保持活力的动因,反而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的窒障。如何发挥现代教育中文学教育的特殊功能,继续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贡献新的推动力量,则是当下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关系中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文学陷入某种窘境的时刻,学界适时地提出了“回到现代文学”的治学策略,成为本学科摆脱困惑和焦虑的一条可行途径。本人曾经撰文《现代文学研究“应回到现代文学”》(发表于《飞天》,2009年2月),分析了“回到现代文学”意味着对现代文学本体的重视,“本体”在此所指并非哲学意义上的与现象对立的“自在之物”,而是指构成现代文学感性形态的原初情景、文学事件、作品文本,换言之,就是现代文学的事实展示。现代文学本体是研究的根基和资源保证,应当用考据和实证方法来还原其血肉丰满、生气贯注的原初面目。“回到现代文学”还意味着确立以文学为主体的研究观念。所有选择不同理论资源、综合多学科的研究都应以揭示文学事件、作品文本的意蕴为旨归,而不是漠视文学自身的价值与特征将其充作其他学科、学说的证据材料。在“回到现代文学”的过程中,大学中的文学教育将扮演何种角色?回答这个问题的应当首先明确现代教育体系中文学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校政时期,将学术研究的目标之一规定为“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⑤,显然培养高尚的人格操守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目标,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宗旨就是养成人们优美的、健康的、富有道德的情感。同样,这也是西方的有识之士对于大学人文教育的本质的认识,20世纪初叶,美国“新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在以《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的系列文章中,对美国大学在严格的学制限定下逐渐被技术主义剥离了重视情感和人格特征的人文教育的弊端进行了抨击,重申文学教育与功利主义无关,应当是经由对经典作品的研读而唤起人们的理性和想象,引导人们倾向于类似宗教的情感,从而完善人格和精神。显然,这些中外贤士都认为借助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的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文教育遵循的目标。从这一角度,审视作为人文教育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价值,并确认在“回到现代文学”这一创造性转换的研究思路中教育可能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在现代文学教育中,不仅要揭示文本所承载的社会历史内容,依据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归纳出一系列评价、筛选文学经典的标准,而且更要揭示现代文学的语言形式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国人精神、思维、审美经验的影响,更要解决的是以现代文学的语言形式为主体的全民基础的语文教育,在何种程度上培植了人们的感情方式和个体修养的问题。
王晓明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堪称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主要形式”⑥,那么,20世纪国人追求自由和生存的艰辛、迈向现代化的曲折,在此过程中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的丰富信息可以说都包容在了现代语言与现代文体的文学写作之中,加之其所涉及的问题以一种历史的惯性或隐或显的与现实发生着联系,使之有一种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将这些丰富的资源引人教学,不仅可以使接受教育者窥见启封的历史的真实,对今天的中国人“生从何来”的历史有更加清晰的理解,而且借助于对现代文学美学意义的挖掘,感悟国人在20世纪的艰难时世中向富有尊严的精神境地突进的努力,从而培植具有人性关怀力量的美好情感。可见,培养健康完整的人格才是人文学科教育的最终目的。所以,我们再次重申文学教育的本质是审美教育,是情感教育,讲授现代文学的历史知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据此建立现代中国的审美经验,并由此影响接受教育者的精神、思想和情感方式。这应当是在当下教育活动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作者:谭杰肖放亮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