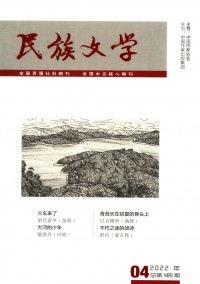莫言文学论文:浅谈莫言对文学教育的价值

本文作者:张西芳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叙述视角
莫言笔下的中国乡村世界是那么真实,真实得极端残酷,他的语言是悲伤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着泥土腐味的语言。如果说他具有“民间”色彩的话,那也是中国特色的民间,而不是巴赫金笔下的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莫言的小说叙事,是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是白话汉语文学经历了100年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最新果实。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莫言的文体,是一种生长在真正的“民间”土壤上的“欢乐文体”。他对民间悲苦的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记账式的恐吓,没有给人制造压力,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凸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息,或者它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的“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小说在叙述人称上也很有特色,主要以“我爷爷”“我奶奶”来展开叙述,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迭合,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方式使叙述的主观性得以实现,小说中的“我”是操纵和控制叙述的主体,通过“我”之口把“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纠葛讲述出来,这就使故事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不可靠性,而且这种叙述又使“我”的处境与“我爷爷”“我奶奶”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逼真的细节带上了虚幻的色彩,幻想和想象的成分融入叙事,理想和想象与现实的冲突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从而使小说获得了“喧哗自嘲”的反讽效果[2]。作者巧妙的运用了这样的叙述方式,获得了双重收效,这种叙述方式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红高粱》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我奶奶”戴凤莲﹑刘罗汉大爷﹑孙五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农村普通劳动人民的代表。特别是“我奶奶”戴凤莲16岁被高密东北乡富甲一方的单廷秀看中,被迫做了麻风病人的媳妇,三天回门路上,与“我”后来的爷爷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后来又与“我爷爷”余占鳌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并且还支持“我爷爷”去抗战,最后她自己也壮烈牺牲了。她虽是一个苦命的女子,但勤劳善良,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人物形象
这部小说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冷队长、刘罗汉大爷等。本文挑选其中两个比较典型的人物对其进行分析,男主人公余占鳌、女主人公戴凤莲。男主人公余占鳌具有土匪、英雄、情人三种身份,粗野﹑狂暴﹑激情和狭义集于一身;女主人公戴凤莲她丰腴﹑热烈﹑她果断﹑泼辣﹑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表现出无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命存在,以较弱之躯拥抱爱与自由,崇尚力与美,承受着全部的疼痛与欢爱。他们都是来自高密东北乡,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有着同样的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他们集善恶于一身,作者也并没有因其浓厚的“土匪味”与离经叛道的行为而对其进行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评价,作者旨在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对人物的生命力的张扬,并歌颂那些奋勇杀敌,流血牺牲的另类英雄们,同时又说明英雄也有其复杂的一面[3]。作者笔下的人物虽是农民,但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他们却奋起反抗,将生死置之度外,积极同敌对势力作斗争,这都表现出了他们英雄的一面,他们身上那些看似原始的不合理世俗伦理观念的“野性”,也自然成了作家对自由生命﹑原始生命力的追求,更是对血性和力量的呼唤。
语言特色
在语言运用上,《红高粱》追求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切都服从主体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而不惜偏离常规,不管是政治﹑文化的约束,还是美学﹑道德的框架。按照莫言自己的说法是,“为了要写大的气魄,在很多地方都不管语言是否规范,情之所系,任其自然的写法”,以致“披头散发,枝叶横生”。这部小说使用惊耸的语言,描述暴力、偷情﹑野合、酷刑等,使其极富感染力。并且还注重感觉的呈现,文中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色彩鲜明而丰富,努力表现意识的流动和心理的跳跃,从而意象纷呈。同时莫言还注重对语言色泽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4]。此外,这部小说在很多地方还使用了方言,看起来给人一种土里土气的感觉,却给人一种亲切感,表现出那里最淳朴的乡土民情,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对高密东北乡人民性格的真实写照,通过人物的话语,我们可以了解到高密东北乡人那种粗犷﹑豪爽﹑狂荡不羁的性格。例如:余司令对大家说:“丑话说在前头,到时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
追忆
整部小说都是以一种追忆的形式在展开故事情节,即把故事置于“过去”的时空里,又映照在叙述者“当下”的时空里,让故事情节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之间交替出现,让“我爷爷”“我奶奶”的敢爱敢恨,惊天动地,活力沛然与“我”这一代人生机萎缩,活得局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表现出作者对现代“种”的退化的担忧,对“过去”先辈生命辉煌的寻求,即回望过去先辈的辉煌成就又反思现代人的不足之处。小说中的“故事”是以“非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它通过叙述者“我”在现实与过去的“追忆”之间的自由穿梭,将完整的故事情节肢解开来,情节的逻辑结构就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淡化,从而使叙述显的自由散漫,了无拘束且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