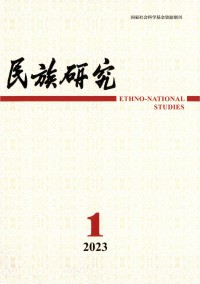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一、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二、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斯大林;民族;民族识别;反思
【作 者】邓思胜,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王菊,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副教授。成都,610041
【中图分类号】C95;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016-005
Study On the Stalin’s “national” Definition Affect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Deng Sisheng, Wang Ju
Abstract :Stalin’s“national”definition have affected China’s national work, especially in the mov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50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became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nrecognizing ethnic identity and dividing ethnic groups. However, we have to rethink this issue duri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Stalin;nationality;national recognition;reflection
民族识别,这项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影响中国民族政治生活的重大举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会影响到数代甚至数十代的政治运行和国家安定。时隔五十年以后,众多的学者(包括当时参与民族识别的一些学者)对当时的民族识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当时实行“民族识别”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边疆地区,族群情况比较复杂,如我国西南的滇贵川桂地区,过去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族群缺乏长期、科学、系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和识别他们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对他们现时社会组织发展形态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使他们逐步整合进入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条件。二是1949年以后,我国参照前苏联的做法逐步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贯彻少数族群优惠政策。”①“在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中国当时民族状况不清、族群认同混乱的现实情况,中央及时提出了明确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进行民族识别问题研究的任务……当时提出民族识别任务的宗旨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②而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主要是民族特征与民族意愿。③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了当时中国政府作出“民族识别”政策和依据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和定义民族理论研究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是斯大林的原名,他关于民族的研究论著有《社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曾在1913年发表的《与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什么?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④他认为民族这个共同体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⑤这个概念和定义是斯大林在研究分析欧洲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仅影响了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而且也影响了中国的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一系列民族政策。
这一民族概念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四个特征。“共同语言”是族群认同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和现实的客观基础,是族群的文化标识之一。“共同地域”,是一个共同体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具有各种联系的空间条件,从而能让人类社会由血缘关系转为地缘关系,“语言界限和自然疆界所决定的地域范围,无疑是推动共同生活的重要基础。”⑥为民族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共同的经济生活”,族群内部的经济联系把民族中的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共同的心理素质”,这是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机制。这四者的总合构成了民族。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念和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理论对苏联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指导作用具有权威性。其民族思想主要表现在:(1)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族、由部族到民族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三个演进阶段;(2)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伴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形成的共同体,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民族”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3)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旧式的“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出现了新式的“社会主义民族”,它更具有“全民性”;(4)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前资本主义部落、部族,他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改造下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构成体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5)在苏联各个共和国中存在着脱离了其民族母体而同其它民族掺杂在一起的移民性群体,称为少数民族。……⑦斯大林所论证的民族是形成民族国家后所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民族,也就是不分部落、不分种族的全体居民构成了一个民族。
二、“民族识别”中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运用
从上分析来看,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是他在对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的民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就现代民族而言的。但是并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提出一个科学的总结。而中国当时的民族情况是,还有许多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所以并不具备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的四大特征,而且情况还更为复杂。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中认为:“在当时的民族识别中存在着说同一种语言的可以是不同民族的情况;同样操两种语言的可以融合为一个民族。……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性程度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发达民族,这主要指同一语言中方言多,差别大,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一个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是与共同的生存居地分不开的,我国少数民族具有交错杂居的特点。但是不同的民族交叉分布的大边际或小边际大多是清晰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地域的共同性。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交错杂居在一起,经济虽不发达,但联系却很密切,因此很难具备单一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而是出现多民族共同的集市与经济中心,但却没有消除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心理素质在形成和维护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中起了巨大的聚合作用。在识别工作中,生产方式、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历史传说、、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应注意考察。这些具有全民族性的、表现在文化上的特点,也就是区别其它民族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掌握四大民族特点并运用于民族识别工作中,是严格的科学性的体现。然而这是不够的,还要对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充分利用史料、传说以及各种有关资料,为民族识别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⑧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民族这个共同体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分化或融合的现象,甚至有的族体正处于“分而未化”或“融而未合”的过渡阶段,这样他们就会在构成民族特征方面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在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对在任何一个或几个特征上表现出来的显著共同性,都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同时,民族特征正是相互往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在把各个民族特征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有时是那个特征,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所以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不是孤立地去看民族的每个特征,而是历史地把民族诸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地、综合地进行分析,把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的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考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以确定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属性。⑨
“民族学家们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与有关民族作比较研究,既从斯大林的民族特征出发,又考虑了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形;没有照搬四个特征,在许多民族的识别中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办法,把共同文化特点作为民族识别的最重要特征,并且采取了‘名从主人’的做法;充分考虑各民族族体群众的意愿,也就是注意了群众的群体意识。”⑩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称的“民族意愿”,具体又分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两个部分。B11民族意识是族体成员对本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文化的一种认同感;而民族愿望是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的主观愿望。根据民族学家林耀华的观点,“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代替各民族决定应不应该成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便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体最后确定族称和归属。”B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由代表性人物正确识别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B13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所遵循和依据的识别标准主要就是所谓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两个标准。这是为了实现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繁荣”的目标而对各族群的身份进行界定和划属进行的重要举措。自“民族识别”以后,中国境内的所有人群被划归于56个族体当中,各族体身份被固定下来,成为了制度化的结果。
三、民族识别=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其已形成的民族格局和政治制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在识别的过程中和过程后所带给我们的反思:
(一)“民族识别”工作的特点:
1、根据马戎的研究认为,民族识别工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差别并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愿望给予特别地的重视。B14
所以,“民族识别”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学者根据各族体的文化表征来进行的对不同人群的分类活动,具有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因为“尽管许多学者意识到应当尊重本民族意愿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则是更高利益,由于各主管部门和从事调查研究者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出现了对族群认同注意和分析不足的现象。如将不同支系并在一起,用人们对其中一部分族群的他称作为统合各支系的族称,往往会产生某些支系在一定时期内不承认国家确定的族属的现象;过早地由政府规定还没有发展出更高认同的“民族”,引起一些族群的不满;操之过急,对族群的认同,或者说心理素质似乎考虑不够。”B15
这样一来,表面上所遵循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的原则只是部分地、并不彻底地遵照和执行着。民族识别仿佛成为了政府和学者的事,各族群的人们对自己的族体归属只是较为旁观地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而已,因为对自己所属族体的族称是由各学者从客位的角度最终确定的;因为整个民族识别活动是在政府为了今后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民族识别只是整个民族政策制定的一个基础,所以在整个识别过程中,政府的意识再加上各族群精英的意识成为了确定各族体名称归属的主要因素……而且,整个民族识别中,并没有采用客观的科学依据,如各族群的体质特征的测量和鉴定等等。所以,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的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是很明显的。
2、教条化和片面性的特点。在民族识别过程中,片面强调民族的四个特征,教条地运用经典理论来套用于具体的民族族属的确定问题;片面强调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族源等文化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片面地将同一民族因为识别的行政区划不同、识别的时间不同而划为不同的民族等等……这些无疑为民族识别工作遗留下了许多问题。
3、固定化和制度化的特点。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确立下来的56个民族身份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56个民族的关系成为了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出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理论基础是为了表现并贯彻‘民族平等’政策,避免少数族群成员由于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敢表明自己的族别,而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是为了落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群的各项优惠政策,因为不明确人们的‘民族成分’就确定不了落实政策的具体对象。”B16在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确立下来的民族身份,似乎成为了民族自我的界定和归属,而且仿佛是不能改变的。
(二)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是同一的吗?民族理论研究
在上述的民族识别的特点中,我们对民族识别的客观性产生了质疑。民族识别应该是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少数民族,应该称为族群。在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主编的《族群与族界:文化和差别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指出,族群区分的最重要的特征包括自我认定的归属(self-ascription)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ascription by others),所以文化只不过是用来表明他们族属不同的标志而已,而不能作为族界划分的依据。
结合中国的民族识别来看族群认同,我们可以发现:(1)民族识别的确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中的一个构件,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国家的权力在中央、地方、基层、民众之间加以运用的一个最明显的个案。因为,从民族识别的目的来看便是为了国家今后的较好运作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当然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从族名的收集、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到族籍的最后确定都是政府在起着积极和主要的作用。就算有珍重民族意愿的原则作指导,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举措无不烙下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2)民族识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主要以文化作为族群认同的标识而客位地确定各族体的族称的举措。识别开始的时候试图以一种族群的原生情感来带动和促进整个民族识别的进行,而识别结束后又力图以一种国家公民情感来替代各族群的原生情感。(3)民族识别使全国各族群民众在个人感情、实际需要、共同利益和面临的义务等等之间进行选择。结果仿佛是实现了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这种“民族团结的取得越来越不是通过诉诸血缘与地缘,而是通过诉诸含糊地、间断性的也是规范化的对公民国家(civil state)的忠诚,这种忠诚或多或少由政府运用警察力量与意识形态规劝予以加强。”B17
所以,民族识别是在以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而实现的一项政治举措。族群认同,在族群内部是更倾向于文化性的,而民族识别是在族群认同之外更倾向于政治性的。而且不可否认,民族识别从外部更强化了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国家政府认可的范围内对自身族群身份的强调、对自身族群优惠利益的争取、对自身族群文化的彰显等等……但是,在识别过程中遗留的一些问题或者根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认同的族群意识增强以后会否定或部分否定民族识别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族群认同和民族识别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在由国家划定了民族身份以后,是否获得民族身份的各族群就会实现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呢?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主要是通过认同意识而表现出来的。而民族认同意识主要有两种:
第一,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既有通过抽象的、不可触摸的“民族精神”、国民性、行为与思维方式等来表现的场合,也有通过艺术文学作品、习惯、礼仪、制度等具象性的文化项目来表现的场合。两者不是相互排他的,后者有时可作为前者的具象化之物来理解。……第二,民族自我认同意识被社会整体共有时,既有通过某种文化特性而整体论式地表现的场合,也有通过社会的各种制度而制度论式表现的场合。以上第一分类与第二分类,如抽象的=整体论式的、具象的=制度论式的那样,是相互密切关联的。B18
一方面,获得国家认可的民族以自己族体具象性的文化事象和文化特征来归一着本族成员的认同感,在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双重的张扬中,促成了被划定的民族人群的认同,同时也逐渐培养起了强烈的族群意识;另一方面,国家的意识形态竭力推进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而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等等,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族群的发展现状镶嵌在了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事业中,各族群成为了国家公民性的载体而部分实现着对国家的认同,这是一种外在的强加在族群认同之上的高于个体、族群集体的一种在现代国家中对国家实体的认同,这是族群向政治化民族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两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虽然在民族识别后,一些族群对自己的族称划属的认同仍有分歧,但是在国家认同的方面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族群认同并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也并不能确定族群认同就没有问题。
注释:
①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9―90.
②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7.
③ 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1.
④ 华辛芝、陈东.斯大林与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92.
⑤ 《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91.
⑥ 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5.
⑦ 郝时远.苏联的构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阐发[C].引自王建娥、陈建樾等著:《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0―111.
⑧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⑨ 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⑩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17.
B11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02.
B12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B13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B14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1.
B15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27.
B16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4.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第3篇
土族服饰既是土族显著的标识,蕴含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同时也是土族特有的审美追求和审美心理的自然体现。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具有原生态性质的群体性艺术,土族服饰凝聚着土族的族群特征、审美意识,涵盖了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气息,从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一种历史符号,它的世代传承也就意味着土族文化的世代传递。土族正是在对这种“独具特色的、活态流变的文化的世代传承中,不断透露着这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1]
一艺术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中国古代的“艺”是指技艺,孔子所说的“游于艺”就是指古代的六艺。在西方,艺术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art”,原义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用手工制作的艺术品。到了古希腊时期,艺术的概念仍是与技艺、技术等同的,这个时期实用的技艺与非实用的艺术尚未具体区分开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期法国美学家巴托关于“美的艺术”概念的提出。当美的艺术概念体系正式建立后,艺术就成了审美的主要对象。艺术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的审美价值,这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表现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接受者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美感,并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因此,现实、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构成了艺术的基本要素。基于以上的理论,我们可以说土族服饰也是一种艺术,只是与现代艺术(即纯粹的艺术)相比,它更明显地倾向于古代艺术(即艺术与技术)的范畴。这主要表现在:
(一)从构成服饰艺术世界的创作者—作品—接受者(即使用者)三者的关系来看,土族服饰的创造者与土族服饰的使用者通过土族服饰这个作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土族服饰作品本身与土族服饰的使用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
(二)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看,土族服饰艺术产生于土族社会,以现实空间为其存在的场所,直接参与土族民众的生活。
(三)从与人们观念意识的关系上看,土族服饰艺术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直接反映土族民众的历史现实情感,体现人们的集体情感和意识,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因此,土族服饰作为高度自主与开放的艺术世界,比较完满地具备了艺术的功能。[2]
二土族服饰作为一种艺术,不仅凝结着土族人民的精神风貌、生活理念和审美情趣,而且还衍生出以下一些艺术表达形式:
(一)实用与审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服饰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是在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对于古代服饰的创造者来说,他们创造服饰,首要的目的,是生命意识的趋动,是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可见,服饰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实用性这一基本要素。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土族先民也是为了遮体、保暖及其它特殊需要创造出了最初的土族服饰。服饰的方便、安全、自然性能便于人们更好地适应自然。土族聚居的青海河湟流域平均海拔2800米,年均温度只有5摄氏度,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决定了土族服饰必须具有抵御寒冷和遮风避雨的功能,这样,羊毛和羊皮为主要制品的土族服饰便油然而生。土族先民系马背上的民族,其装束显然适应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今天的土族继承了其先民的服饰,采用长袍款式肥大、两侧开衩也是为了便于骑马和劳作。所穿腰靴和所扎的绑腿带不仅可以御寒,还可以防止长期骑马磨损小腿肚,这也顺应了古人所说的服饰“适身体,和肌肤”的理念。人类自远古洪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服饰也逐渐由实用性转向了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胡经之在《文艺美学》中说:“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是人类特有的辨别美丑悲喜等审美现象的精神活动。当社会发展到人们不以直接的功力态度、实用态度对待自己的产品时,才出现了比较成熟、比较纯粹的审美关系。因此,人对自然美、社会美的审美,是由物质功利性到精神功利性的发展。”在土族服饰艺术中,这种从物质到精神,从实用到审美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同仁年都乎地区的土族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后人,所以其所穿的“多才”的大翻领袍子和将两袖在腹前相系的习惯,保留了马背民族善骑的特质。在之后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由于受藏文化的影响,装饰水獭边的袍子逐渐成为土族礼服的象征,每到六月会期间,这种礼服的展示也成为当地土族群众夸富心理和审美意识表达的媒介。又如,土族头饰“扭达尔”上的矛、盾、箭等组成元素,均为冷兵器时代的主要战争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将它转化为了一种装饰品,凸显了其审美功能,而其在用材上也逐渐由铁质转化为银质,制作更加精美,后来人们又在上面镶上珊瑚、松石、玛瑙等饰物,可以说其观赏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价值。所谓“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土族早期的服饰是为了适应生活的需要,那么现在的服饰则是为了适应审美的需要。土族人在负有历史情结的民族服饰上通过认知附加了审美功能,并使之不断强化,突出了他们对服饰艺术的审美特质,也使得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当然,在土族服饰中实用与审美是辩证统一的,这也是土族服饰审美的根本性。这个本质不仅反映了土族造物的根本要求和终极目的,规范着他们的造物行为和思想,而且决定着土族服饰审美的适宜之度,决定着服饰的形象和整体标准。从土族人把自己的智慧、才能通过一定的物质材料进行创造,使之成为一件工艺品时,这种本质就已经存在,剩下的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美与实用哪一方面轻、哪一方面重的倾向性问题了。
(二)形式与内容。“艺术形式是以实践的历史积淀为基础经由心理积淀而形成的,是对自然形式规律的某种概括和抽象。”[4]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土族人在对自然的“观物取像”中“立像尽意”,能动地创造了与自己的观念和目的性相应的物化形态,而服饰就是这种物化形态最重要的载体。土族服饰作为视觉艺术,具有形式美的一般规律。它由形态、色彩、质感这三个美学基本元素构成。其中形态是指土族服饰的基本造型,包括长短、曲直、各部分附件的配置(如领子、袖口)、色彩组合,以及纹样图案、装饰点缀的安排。色彩是“一切生物都向往的颜色”,也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服饰本身是有色彩的,而这种色彩往往会造成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色彩美的产生。服饰的色彩美又通过面料、配件的色彩选择及色调的配合反映出来,因此材质又显得非常重要,其质地、手感、光泽是反映服饰美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由图案、色彩、质感和材料加上统一、对称、均衡、韵律等的美学法则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土族服饰的外在形式。但是,服饰的形式只能体现出服饰的本身之美,这也只是一种单纯的美。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显象表征,它又必须是有内涵的,这就是服饰的内容。通常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服饰美是历史的美,是相对的美,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文化特征。早期的土族以游牧为主,所以其服饰材料多以野生兽皮或牲畜皮毛制品为主,明清以后土族经济逐渐由畜牧业向农业过渡,这也促使了土族服饰材料的转变。青稞、小麦、大麦、油菜、胡麻等农作物的种植为传统的布料提供了原材料,随着手工业的出现,互助和民和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以手工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毡匠、鞋匠、裁缝、剪毛者、编背斗者,于是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纺织品。随着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和商业的兴起,棉麻纺织品在服饰材料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商业的兴旺,尤其是地处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便利条件也促使很多内地的丝绸制品出现在土族服饰中,成为人们盛装礼服的贵重材料。可见,土族服饰的材料经历了皮、毛制品到麻、布制品再到绸缎制品的过渡,这反映了土族牧业经济到农业经济的转化,也体现了其生产力水平发展变化的内涵。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社会制度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p#分页标题#e#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第4篇
一、新疆传统文化的特异性
(一)新疆文化产生的独特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新疆地域的独特性,使新疆文化作为完整的文化单元,其构成呈现出强烈的大漠绿洲复合风格。新疆境内天山山脉横亘中部,南北疆地理环境各具特色。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北疆地区,地势高而平坦,气候寒冷。两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河流经过处形成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地区。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南疆地区,其中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大小绿洲,由雪水灌溉形成良田,以农业为主。这些被沙漠阻隔的绿洲,彼此往来困难,在相对孤立、分散的情况下发展,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应相对低下,很难形成统一的经济实体,也无法形成大的邦国。新疆文化的发源地是高山大漠和夹诸其间的绿洲、大河。同中原农耕文化环境相比,终年经历风沙干旱,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寒风割面,一日之中冷暖多变。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以沙漠、戈壁为主,人们不得不退居河流两岸、山麓地带的湖泊泉水处以求生存。地理环境使游牧民族无法产生安定、依赖的心理,却在迁徙中培养出同恶劣环境抗争的意志,具有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征服欲。与之相应,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流动中缺少经验积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不断迁徙的族群又使政治统治处于松散结合状态,人的精神生活自由少拘束,民族内部文化规范较严谨,而社会公共规范的意识则比较淡薄。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东西方相接。除了古丝绸之路,天山北麓还是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这里是东西方商业贸易、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发展的平台。物流、人流,商旅、游牧,把“走”的文化因子深深植入新疆各民族的血脉里。现代,牧民虽然有了定居住房,还是钟情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农耕民族在商业贸易的过程中也实现着“走”的愿望。
(二)新疆文化基因的多元融合历史上,新疆地区是多种族多部落繁衍生息的家园,在各民族交互影响、共同繁衍的过程中,形成多层次文化并存、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态。多元是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相互有别的;而一体则指各民族在参与建设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相互学习、广采博纳,形成交融的文化关系,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开放性成为新疆文化鲜明的特质。史前阶段新疆地区的居民,种族多源民族纷杂。“在新疆大地,古代居民的种族特色是很不一致的,不仅存在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的差异;而且,即使同为白种人或黄种人,其中也存在不同支系、地区的特色”。①新疆地区的民族是不同种族融合而成,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种族体质上,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影响到文化的定型。新疆居民从汉代开始才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疆地区大规模、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原始土著、呼羯、姑师、高车、丁零、鲜卑、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等民族人口的迁移变化不断,不同时间由不同民族轮流控制这一地区。先后活动于此的几十个游牧民族,逐渐形成草原文化的基本框架。对于新疆这种边远空旷、人口稀少的地区而言,人口迁入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西汉拓展西域以来,汉族及汉文化对新疆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发展演变,才逐渐形成新疆十三个主体民族世居的民族分布现状,而多民族成份的汇聚变迁,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任何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文化的扩散与整合过程,通过文化系统各要素的整合,实现文化层次的跃进。新疆文化的多元性主要基于民族性、地域性及其变异性。民族文化先形成局部区域文化,而后形成大的地域文化。新疆地区不同草原文化之间的相互扩散与交融、草原文化圈与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整合,使不同文化经过碰撞、交流、吸收、补充、整合而趋于一体化。在融合各民族、接纳各种异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文化,具有一种单一文化所不具备的博大宏阔,既保有本土文化的特质,又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接纳不同文化因子。新疆,将各种不同文化进行熔铸并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新疆地域文化。
(三)新疆文化内涵的庞大丰富从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层面审视新疆文化,它属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宗法制度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北疆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经历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时期,清朝以后农业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从早期赛人、乌孙的原始部落文化,到突厥文化以及蒙古、哈萨克游牧文化,各种文化间存在承继和整合的发展轨迹。南疆以绿洲文化为主,在原有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逐渐形成新模式的文化。数千年频繁的民族迁徙、融合,使得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其丰富。由于民族、宗教、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诸多因素的极大差异,新疆文化呈现出不同文化并生、共荣的特征。既有极强的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同一地域各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还有同一民族在不同氛围中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文化、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古希腊及罗马文化都在此交汇碰撞。以龟兹佛教艺术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佛教文化经过吸纳与调适、交融与变异之后熔铸、成熟的痕迹:建于公元4—5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2窟,壁画中的国王、王后均上身,颈、臂、手腕部有装饰物,与当时龟兹国王与王后的装饰不同,具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特征;创于公元7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05窟,国王、王后服饰与同期龟兹人服饰完全一样。“越到后期,表现就越少。这是外来艺术在融入本土艺术过程中的适应性变异,但终究是本土审美意识占了上风。成熟期的龟兹佛教雕塑已形成本土化的造型风格。”②外来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于这块土地上,而是在对本土原有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的基础上,经过自身调整、取舍而扎根。此外,新疆多样的原生态文化环境本身,就具有对外来文化过滤和重整的作用。在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外来文化,基于本民族文化的框架,修正或改造外来文化,使之适合和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多民族对同一(不同)外来文化的不同需求与吸收,造就了新疆文化鲜明的个性化和差异性,这正是新疆文化的魅力所在。从新疆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看到:多种民族在此生活,多种宗教文化并存,使用多种民族语言,存在多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在纵向承继与横向整合中形成新的模式,而通过个性化与差异性更加彰显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张力与个性色彩。
二、新疆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新疆的传统文化,从地域上可以粗分为:天山北部的游牧文化圈;天山南部的绿洲农业文化圈;天山东部、北部的屯垦文化圈。这只是粗略划分,新疆各地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屯垦文化成分互有交叉、各有侧重又同时并存。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到电子传播等各种方式共存的发展变化,这同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
(一)绿洲农耕文化圈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绿洲农耕文化圈以维吾尔族为主,维吾尔族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村社组织,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牧养牲畜作为重要经济补充形式。在天山以南大小绿洲进行农业生产,而山区草场则供放牧牲畜。维吾尔族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不仅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商贸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北部游牧民族相比,维吾尔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政治制度是伯克制,各级伯克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以及附属于这些土地上的农户,并对依附的农民拥有进行劳役制剥削的封建特权,这种封建地主统治又往往和宗教统治相结合。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稳定性,在物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其传播媒介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维吾尔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方式以文字传播为主,大量的典章、制度、文学作品使文化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影响力更为恒定、久远。政教结合的封建政治制度使传播的类型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其中宗教场所进行的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维吾尔族的传统贸易集市“巴扎”在今天依旧是人际传播的重要场所。每逢“巴扎”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流、物资云集,从一般农副产品到昂贵的工艺品,应有尽有。“巴扎”的人数甚至可以达到二三十万,周围的维吾尔族群众从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以外,赶着毛驴车拉上全家人赶赴巴扎。“巴扎”已经不仅仅是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也是各种信息交换的平台,有些人甚至不是为了买卖商品,而是为了约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感情而去“巴扎”“,巴扎”成为维吾尔族民众极为重视且极富民族特色的人际传播形式。
(二)游牧文化圈以人际传播为主游牧文化圈以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为主,其中,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人的传统社会组织保留了较多的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形式,以牧业经济为主,狩猎和农业作为畜牧业的副业,牲畜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作物一般在冬牧场种植,靠自然生长,秋季收割。这种按季节迁徙移动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耕文化表现出的稳定性截然不同。其文化的侧重点不在于典章制度、物质积累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更多的表现在精神气质、歌舞传习、史诗说唱、民间故事、风俗习惯中,因而更具有流动性、易逝性、变异性。这种文化的传播方式以口语传播为主,其传播媒介具有单一性,传播的类型是人际传播。氏族部落制度在这三个民族中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在这样一个原始的部落群体中,人们缺乏社会意识、公共意识,更多的是原始部族的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在政治制度、典章法律相对落后的部落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较少规范约束,而社会组织的不完备又使得社会对人的控制相对薄弱,个体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力量,对群体的依赖心理较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因而在传播活动中具有更多的随意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它是“哈萨克民族传统文艺的一个典型形式,它代表着哈萨克族独有的民间文化特色”,“盛行于哈萨克人中的习俗歌、民歌、谜语歌、马歌、山歌、水歌、地歌、牧歌、渔歌、宗教歌、戏谑歌与大量的歌谣,无不包含在阿肯弹唱中”。①阿肯弹唱中包含了哈萨克族历史源流、社会经济生活、律法礼仪习俗以及家庭婚姻观念,两个阿肯在众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在具有竞争性质的对唱中,大量即兴式创作,阿肯们自编、自唱,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形式上是诗、歌、舞、弹融为一体,内容上则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弹唱中优秀的唱词会以创作者的名义在哈萨克族民众中口口相传,广为传播,不仅起娱乐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元素和信息元素的传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弹唱的内容日益翻新,这种以“阿肯弹唱”为载体的文化活动,具有极强的“为人的需要”而服务的趋势。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第5篇
“原生态”民歌之所以成为一种“临界文化”,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其一,原生态环境之临界点。“原生态”音乐文化就像那清冽的泸沽湖水,原本静静地躺在山野,自由呼吸生长。近年来,当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重新认识到原生态民歌的艺术魅力时,各种发掘、宣传和炒作活动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大小村寨。在主流文化理念的支持下,人们或者挥舞着大笔,在山清水秀之间任意涂抹,或者直接以强势媒体为依托,将那原本鲜活的生命从土壤中连根拔起,移植于光怪陆离的城市舞台,继而在城市人猎奇般的掌声中升至沸点。于是,一时间泸沽湖水云蒸雾绕,面目全非了。
原生态民歌之生态环境,包括当地原住民的居住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以及宗教和种族信仰等内容,其中尤以人们的宗教和种族信仰为重要内容。①千百年来,华夏祖先正是在这种强有力的民族信仰的基础上,固守着自己的母源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生不息地传承着本民族固有的音乐文化――原生态音乐。在这一点上,仪式音乐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自然民族中,音乐有各种功能分类,被用于有关人的生死、各种仪式及工作等社会活动之中。特定的音乐,被用于这类活动中。同时,还有这种情况存在:若欠缺某种音乐,某种活动,本身便不能成立……在以西方和日本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几乎在一切场合,音乐都与社会活动分离。就连基督教和佛教音乐,也常常与宗教仪式无关,为非信徒所聆听。”②从中可见,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与社会活动的关系是有很大差别的。生动的例子如贵州安顺地区的“傩”舞,原本是在特定时间举行的祈福驱邪的仪式,它包含富有特色的仪式形式与表演。当全体信众还虔诚地相信这种仪式的驱邪功能时,观众和表演者都沉浸在一种热烈而神秘的气氛中。但今天参观“仪式”的观众,其成分、心态却与以前大不相同,由于记者、民俗学者和旅游者的介入,使观众与“表演者”、仪式本义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仍然是一种群体参与,但它和达到自觉意识以前的群体参与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贵州安顺地区的“傩”舞生态环境已经趋于临界状态并遭到破坏。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滞后,其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接近于自然状态,音乐与社会活动的联系十分紧密。它对社会生活的依赖性很大,多具有实用、宗教、交际、娱乐、教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重社会功能,以及音乐创作、表演、接受“三位一体”的特征,往往音乐的创作者就是音乐的表演者,也是音乐的接受者。如今,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逐步向城市化趋近,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也在悄然蜕变。笔者在研究壮族“布偏”支系的音乐――“天乐”的实地调查中就深有感触:原本的民族服饰已完全汉化;原有的高栏建筑已改为土石结构的平居;原先为男女老少所喜闻乐见的“天乐”,如今已很难引起年轻人的兴趣……显然,当人们的意识、信仰等因受外界的影响而日益走向开放,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削弱了群体意识,增强了个体意识时,那种集体性参与音乐的生命力将会因其所依附的传统社会活动(民俗活动)的逐渐减少乃至消失而逐渐减弱甚至终结。原生态音乐环境的这种临界状态在我国民间极具代表性,因此,要科学对待原生态民歌目前所处的这种临界状态。要想从根本上、整体上实现原生态民歌“活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将原生态民歌的这种临界状态导向良性的归属。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社会,尤其是我们的学者、专家们应该有一点反熵精神:多一分冷静,少一分盲从;多一分思考,少一分鲁莽。尤其是在原生态民歌处于这样一种临界状态的特殊阶段,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反熵斗士和反熵英雄,需要一种坚持真理、甘于寂寞的反熵精神,这样,原生态音乐才不至于丢掉最后的净土。
其二,原形态特质之临界点。由于原生态环境的临界状态,原生态民歌文化特质的载体――音乐形态也随之达到临界点,原生态民歌的文化功能也随之萎缩。笔者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2006年央视“青歌赛”上,彝族青年李怀秀姐弟的一曲《海菜腔》,直观地看它仍然还保持感染力极强的纯朴自然之态,致使观众和评委们纷纷起立鼓掌。但是,我们当前所看到和听到的这首《海菜腔》,不仅它的生态环境已经有所改变,而且艺术形态上也已经不是当年的《海菜腔》了。从形态上看,此歌是由悠长的和欢快的两个对比性段落构成,而这两个段落,其实是目前仍存活于异龙湖边(云南省建水、石屏一带)两种有着不同族群文化背景,在不同地域流传的民歌。这新的《海菜腔》里,较悠长的一段是脱胎于当时湖边彝族所唱的《海菜腔》,原曲很长;另一段较欢快的,则是附近山区花腰彝族的玩耍调,是一段短小的旋律,可随意反复。如今,也许是为了增强民歌演唱的对比性和可欣赏性,或者为了提高歌曲本身参与比赛的竞赛性,而人为地把它们各取一段嫁接到一起,成为一首浑然天成的艺术歌曲。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已非但是“原生态”,就连“原形态”也谈不上了。这样的案例在当下的原生态民歌炒作当中俯拾即是。陈哲自1994年起长期深入广西、云南的几十个少数民族的村村寨寨,去施行他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化传承”计划,即“土风计划”。关于原生态民歌音乐形态的这种临界现象,陈哲先生有一个很形象的论断,即A、B、C理论。陈哲认为,从音乐形态上来划分,原生态民歌包括三个层面:A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B是在忠实于A的基础上被挖掘,搬上舞台的原生态,C是一些被转化成主流商业的原生态。陈哲认为,对待每个层面要有不同的传承和评价标准,一些有抗体的终会存在,一些快消失的要赶快一方面组织录音记录整理存档,另一方面积极实施“活化传承”工程,最终使民族音乐资源生生不息。
其三,艺人观念及其文化内涵之临界点。由于上述现代媒体的多样化、快速化和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共生共存,历来就受都市流行文化和上层文化影响的民间基层传统音乐的缔造者――民间艺人,在强大的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其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而达到一种临界状态,艺人们也在身不由己地或下意识地进行着自我文化的抛弃和新潮式文化的“模仿”。面对“土生土长”的本来是由自己创造的口头文化,反而“自觉形秽”,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和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态意识和倾向,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对当前开展的“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工作的开展,亦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它最终导致本土音乐在与外来音乐的竞争中丧失大量原有的受众群。③由于民间艺人的从艺观念而艺人们这种对于自己母源文化价值观的迷失,必将导致其文化身份的转型与嬗变,也终将诱发其族根文化的重构与变异。目前,原生态音乐文化内涵也在其原生环境与民间艺人从艺观念的临界状态中渐次达到一种新的临界状态。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原生态民歌持续升温,一些民间艺人的思想观念又在悄然发生转折,在种种“原生态热”面前,在一阵又一阵的狂呼呐喊声中,艺人们似乎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他们在把原生态民歌带到城市的舞台的同时,更多的可能是为着奖杯和名声,还有现代都市灯红酒绿的富足生活。这原本无可厚非,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也都有追求现代社会富裕生活的本能,然而不能因为这一堪称圆融的解释,我们就忽视了这一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民间歌手作为某种文化身份的代表,原生态民歌作为某种文化信息的代码,都负有着其自身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这种文化责任表现在他(它)们对华夏传统文化求真务实的表达,以及对这一文化内涵的正确阐释,和对广大受众(华夏子孙)正确的文化引导上。比如,上述彝族四大腔中的《海菜腔》,有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俗内涵,它原本是彝族的尼苏支系中青年男女传统风俗性的社交和爱情活动――“吃火草烟”时所对唱的歌曲,其演唱者双方的关系和身份,演唱的时间、地点与内容等皆有严格的限制,一定是相爱的青年男女双方,傍晚时在郊外祖祠或村头的公房内进行,演唱的内容多为男女私情或儿女情长。然而我们在央视主流媒体的银屏上所见到的是李怀秀和李怀福两姐弟在表演《海菜腔》,这无论是从演唱者双方的身份,还是演唱的内容、演唱的场合与时间等等方面来看,都是犯了大忌。这一点在我国民间音乐当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当中非常典型,诸如摩梭族的走婚歌、普米族的撞胯舞、苗族的游方、壮族的歌墟等等,都受当地民族信仰和民俗规约的严格限制,有其自身特定的民俗文化内涵。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表演”,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信息的代码,它给全国观众所带来的文化学意义上的误导着实不可忽略。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以承载当地文化信息和民族特质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文化形式,其主要的生命特质究竟是“艺术表演”还是“文化代码”?试问:如果剥除了其背后积淀深厚的文化内涵,原生态民歌还剩几何?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文化内涵是原生态民歌不可或缺的生命特质,那么上述种种“技能表演”又得有几何?失有几何?
当下,由于某种文化诱因的影响,上述文化事象可谓比比皆是,归根结底也就是艺人的文化观念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所达到的一种特定的临界状态,由此导致原生态音乐文化内涵出现一种特有的临界状态。笔者在此将这一问题提出,并非对上述音乐事象的蓄意贬低,只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具体实施文艺的薪传工程时,尤其是在对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基和内涵的传统文化进行宣传普及时,切不可舍本求末,厚此薄彼,否则,我们可能不是要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而是掘墓人了。
当下,在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在主流文化和强势媒体的造势下,原生态音乐俨然成为一种临界文化。客观来看,这一临界点是原生态音乐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于文化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再生性,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原生态”民歌目前这种临界状态?如何正确处理和因势利导由于“原生态”民歌临界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值得业界深思的问题。我们应该严肃而有责任感地对待原生态音乐文化,而不是使之迅速庸俗化。
相信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扶持下,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积极引导下,广大民间艺术家和千千万万华夏子孙的热心参与下,我们的社会就一定能形成一种对原生态音乐特有的人文关怀,发现并寻找到属于自己也属于人类的“新语汇”,做出独特又契合时代的表达。而原生态音乐也一定会很快地、安全地渡过这一临界点,走过适应期,进入一个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①伍国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考》[J]. 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第34页。
②德丸吉彦[日].《音乐社会学》[A]. 音乐词典词条汇集[Z].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③伍国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考》[J]. 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