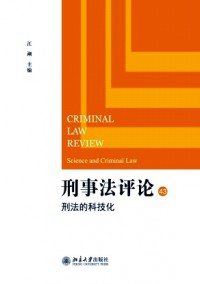刑法所有条例

刑法所有条例范文第1篇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无变革。此处以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为比较对象,探索它们对唐律的主要变革及其原因。
一、体例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体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主要是:
1.卷条的变革 卷条是我国古代法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卷条数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法典内容的繁简。一般来说,多易繁,少则简。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定本时为五百条、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载:“(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一卷条数比以往之律大为减损,故《旧唐书·刑法志》说,凡削烦去蠹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诏长孙无忌等撰编律疏,《唐律疏议》,即为三十卷,条数依旧。宋刑统为五百零二条、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条是把唐律的职制律与斗讼律中各一条分为二条,此与现传《唐律疏议》一致。宋刑统在卷条安排上与唐律的主要区别是,变动了一些卷中的条目数。变条数的卷有五,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变动情况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条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条,刑统移末条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条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条,刑统移前四条入上卷。”②还有卷九、十也有类似情况。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条,刑统前移入上卷一条,后移入下卷四条。”③卷条的位移,说明卷中的内容有变,宋刑统就是如此,下文会涉及此问题。
大明律虽仍为三十卷,但仅有四百六十条,比唐律少四十条。不仅如此,在卷条的分布上,大明律也与唐律有较大的区别。大明律的名例律为一卷,四十七条;唐律则为五卷,五十七条。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条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条则被十一律分享。从这一区别也可见大明律在体例上与唐律有较大区别。
大明律例卷条情况更接近于大明律。它有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条。这四十七卷除增加了律目、图、服制、总例、比引条例等共十一卷外,还把大明律中的一些卷一分为二,如名例律在大明律为一卷,而大清律例则为二卷。其条数比大明律的少二十四条。其中,吏律少四条,户律少十六条,兵律少四条。
从以上三部法典的卷条状况来看,宋刑统与唐律的差异很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比较接近,而与唐律有一定距离。
2.篇目结构的变革 唐律的篇目结构比较简单,仅分为十二篇,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以后唐高宗时撰修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只是在律条后附以“疏议”,起到阐发律意,使人明了的作用,并无更复杂的内容。
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篇中分门,每一门中含有数条律条。共有二百十三门。《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名例律有二十四门,卫禁律有十四门,职制律有二十二门,户婚律有二十五门,厩库律有十一门,擅兴律有九门,贼盗律有二十四门,斗讼律有二十六门,诈伪律有十门,杂律有二十六门,捕亡律有五门,断狱律有十七门。其次,在律条后附以令、格、式、敕条和起请等法条。宋刑统是宋代刑律统类的简称,故除律条外,还附有上述一些法律形式中的相应条款。《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七,起请条三十二。”唐律则无,只是在“疏议”中引用令、格和式的某些条文,来说明律条的内容,与宋刑统另附在后并成一种综合性法典的形式不同。最后,唐律中的“疏”与“议”总是连在一起,不单独存在。宋刑统则常把“疏”与“议”分列,各自阐述自己的内容。其中,“疏”的内容为律条文,“议”的内容为解释文。后者更近似唐律中的“疏议”。《宋刑统·擅兴律》“私有禁兵器”门的“疏”说:“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注云,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与律条无异。“议”说:“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此是对“禁兵器”的解释。尽管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但总体结构仍无重大变化,仍为十二篇,连篇名及排列顺序也与唐律同。
大明律篇目结构的变化较宋刑统要大。因为,它打破了唐律十二篇目的框架,仿效元典章,改用七篇,除首篇仍为名例外,其余六篇均按中央六部官制编目,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故近代学者沈家本评说:大明律“以六曹分类,遂一变古律之面目矣。”④此外,大明律还模仿宋刑统篇下分门的做法,在除名例以外的其它六篇中皆设若干目,并在每一目中又含若干律条。目的分布情况是:吏律中有职制和公式两目,户律中有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和市廛七目,礼律中有祭祀和仪制两目,兵律中有宫卫、军政、关津、厩牧和邮驿五目,刑律中有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和断狱十一目,工律中有营造和河防两目。一目为一卷。每目中的律条不等,如吏律职制目中有十五条,而公式目中却有十八条。
尽管大清律例比大明律少了二十四律条,但篇目结构仍袭大明律而成,变化甚微,主要是:一是在律条后附了例条,有的数量还较多,超过律条。如《大清律例·名例律》的“五刑”条,律条仅为六条,而附例文十八条,大大多于律条。二是在律条中附有注。此注的作用类似唐律中的“疏议”。如“五刑”条规定,“赎刑:纳赎,收赎,赎罪。”在纳赎后有注:“无力依律决配,有力照律纳赎。”在收赎后有注:“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在赎罪后亦有注:“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律赎罪。”经过“注”的说明,把纳赎、收赎和赎罪都区别开了。
以上三部法典的篇目结构显示:宋刑统虽有改变之处,但仍离唐律不远;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十分靠近,但均离唐律较宋刑统为远。
法典的体例只是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与法典的内容息息相关,可直射内容的轮廓。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体例的改动程度,与它们对法律内容的改动程度一致。
二、一般原则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把一般原则规定在名例律中,但它们又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取消一些原则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取消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唐律疏议·名例》“皇太子妃”、“官当”、“除免比徒”等条规定的一些原则均被废除。其中,有的是因为已被其它规定所取代,如“皇太子妃”条中确定的“上清”已被“取目上裁”等规定代替,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易起反作用,如“官当”条规定以官品代罚的原则不利于治吏,故弃而不用;有的是因为不适时,如“除免比徒”规定以除名、免官比照徒刑的原则已不适应明、清的情况,所以也在废除之列。
2.合并一些原则 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合并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宋刑统·名例律》“老幼疾及妇人犯罪”条把《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和“犯时未老疾”两条中规定的原则都归并在一起,既规定各种老、小和疾人员犯罪可享受赎、上清、不加刑等特殊处理方法及不适用这些附加条件,又规定了老疾人员犯罪时年龄、条件的折算方法。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把《唐律疏议·名例》中“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和“死刑二”五条,合并为“五刑”一条,内容基本相同,都规定唐律中五刑的刑种、刑等等。经过合并,唐律中一些较为相近的内容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既避免了条目内容分散的情况,又可使阅律者便于查找。
3.修改一些原则 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的有些原则还被大明律、大清律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首先,续用原律条名,但改动其中的某些内容。大明律和大清律都在名例律中设立“无官犯罪”条,与唐律同,但内容有别。《唐律疏议·名例》“无官犯罪”条规定:“诸无官犯 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其有官犯罪,无官事发;有荫犯罪,无荫事发;无荫犯罪,有荫事发:并从官荫之法。”由于明代不用官荫法,故《明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删去有关官荫的规定,为此薛允升有过评论。他说:大明律的“无官犯罪”条“与唐律略同,惟明代并无用荫之法,故律无文。”⑤大清律例除续大明律的修改外,又作进一步改动。《大清律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规定:“凡无官犯罪,有官事发,犯公罪要在处笞、杖以上的,才可“依律纳赎”;“在任犯罪,去任事发”,犯公罪须处笞杖以下的,也要“依律降罚”等,均与大明律有异。还有“以理去官”等条也属此种情况。其次,律条名与内容均有变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皆在名例律中没有“亲属相为容隐”条。与此条对应的是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条,除条名有异外,内容也有所变动。《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明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扩大相隐范围,把“妻之父母、女婿”也列入大功相隐范围,对此薛允升也有评说。他说:大明律的规定“与唐律大略相同,惟妻之父母之女婿缌麻服也,而与大功以上同律,唐律本无此层。”⑥大清律例的规定同大明律同。还有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立嫡子违法”、“赋役不均”等条也属此类情况。
4.增加一些原则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取消、合并、修改了唐律的一些原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原则。宋刑统通过“议”的形式,把原来唐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定,穿插在法典中。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名例律中非是个别,在此仅能举例说明。《唐例疏议·名例》“称反坐罪之等”条规定:“诸称‘反坐’及‘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宋刑统·名例律》“杂条”门不仅照用唐律的规定,还用“议”规定了新内容:“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流以下止是杂犯,不在除免、加役之例。若至绞,即依例除名。”“七品以上犯在枉法,仍合减科。男夫犯准盗,仍合用荫收赎。”“称以盗、以斗减一等,处同真犯。”吴兴、刘承干在校勘宋刑统与唐律以后也认为,以上内容“唐律无。”实属新增而为。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则在名例律中增加专条,增添新原则。此两律均新设“职官有犯”。“天文生有犯”条,对文职官与天文生的犯罪,作了新规定,采用特殊处理方法,皆为唐律所无。还有“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犯罪得累减”等条,也是如此。
法典中一般原则的规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国情的变化和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反映,它的改变意味着国家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也随之有变。另一方面,它是法典内容的核心,它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法典内容的变化。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在不同程度上对唐律一般原则的改变,不仅告诉人们宋、明、清与唐的情况与国策不同,也预示它们在内容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变革。
三、罪名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是刑法典,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大量袭用唐律规定的罪名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作了变改。变改情况主要有以下四大类。
1.改变罪名 这是指改变唐律设定的一些罪名。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原罪名的内容基本没变,但称谓有变;二是原罪名的称谓没变,内容有变。宋刑统在名例律的“十恶”中把唐律的“大不敬”罪名改为“大不恭”。原因是为了避讳。“宋避翼祖讳,易‘敬’字作‘恭’”。⑧但内容仍依旧。宋刑统还扩大“恶逆”罪的范围,把道士、女冠和僧、尼杀师主行为也归入此罪。《宋刑统·名例律》“杂条”的“议”规定:“杀师主入恶逆”。此被认为是“唐律无。”⑨纯属宋刑统之为。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也有上述情况。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设有“诈为制书”罪,但内容有别。区别有二:一是后者的用刑重于前者,用斩代绞;二是后者无“口诈传”的内容(前者有),仅指制书诈传。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都设定“不应为”罪,与唐律的“不应得为”有一字之差,但内容无别。
2.归并罪名 这是指把唐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罪名归并为一个罪恶名。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有。宋刑统由于采取了篇下分门的形式,一门中往往有数条律条组成,罪名也随之合几为一,故归并罪名的情况在宋刑统不属个别,在此仅举一例证之。《宋刑统·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中规定的脱漏增减户口罪是把《唐律疏议·户婚》中“里正不觉脱漏增减”、“州县不觉脱漏增减”和“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三条中规定的里正、州县不觉脱漏或妄脱漏增减户口三罪合为一体而成,内容基本没变,都把里正、州县官脱漏或增减户口的行为作为惩治对象。大明律与大清律例的律条皆少于唐律,其中有一部分也是采取归并方式,故也存在归并罪名情况。如《明律·职制律》“弃毁制书印信”条规定的充毁制书印信罪是《唐律疏议·杂律》中“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和“亡失符节求访”四条中规定的弃毁符节印罪、弃毁制书官文书罪,官物亡失簿书罪和亡失符节求访罪等组合而成,内容相差不大。对此,沈家本说:“唐目‘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亡失符印求访’四条,并在《杂律》中,明并为一条,改入此律(职制律)。”⑩罪名者因此相应合并。大清律例的此条情况同大明律。归并以后,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的一些罪名外延扩大,内容也相应增加。同时,罪名数量也跟之减少。
3.增加罪名 这是指增加了些唐律所没有的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根据本朝代的统治需要,增加了些唐律没设的罪名。从这些罪名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和打击有损专制统治的行为两大类。《宋刑统·户婚律》的“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皆是新增。《刑统跋》说:这些条目都属“唐律无”。⑾其中的内容均与经济民事法律有关。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一方面增加一些有关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如它们均在户律中新增了“盐法”、“私茶”、“匿税”等条,严禁私营盐、茶和匿税不纳等行为,违者都要受到处罚,以此来保证国家对盐、茶的专营和税收的收入;另一方面还特别增添了一些有关打击有损于专制统治行为的内容,仅在吏律中就设有“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擅勾属官”、“奸党”、“交结近侍官员”等条,对官吏的活动作出新的限制,并惩治违犯者,以此来强化专制统治,维护皇帝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经过增加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内容得到了更新。
4.弃去罪名 这是指弃去唐律规定的一些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把唐律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弃而不用。宋刑统的内容基本同于唐律,弃去唐律罪名属于个别情况。《宋刑统·诈伪律》“诈欺官私取财”门把《唐律疏议·诈伪》中“诈取官私财物”、“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和“诈除去死免官户奴婢”条中规定的罪名集于一体,独不见“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条中规定的罪名。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弃去唐律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仅在户婚律中就有不少。《唐律疏议·户婚》“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已删去不用。
罪名是唐律和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罪名的变化标志着这些法典内容的变化,而且罪名变化得越多,内容也就变化得越大,这是一种正比关系。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通过改变、归并增加及弃去唐律罪名的方式,变革自身的内容。其中,宋刑统的变革的幅度不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变革幅度较宋刑统为大,变改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改革唐律内容方面,步子迈得比宋刑统要大。
四、法定刑的变革
法定刑亦是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刑法法条皆有罪名和法定刑两大部分构成。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变革唐律罪名的同时,还变革了其中的一些法定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换刑 就是用唐律规定的五刑中的某种刑罚取代其它刑罚或用其它制裁方式换代五刑。宋刑统 与大清律例中都有换刑的规定。宋刑统有关于折杖法的规定,即用杖刑来代替除死刑以外刑罚的执行。《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对折杖法作了具体规定。适用折杖法的也不乏其例。《宋刑统·厩库律》“故杀误杀官私马牛并杂畜”门规定:故杀官私马牛者“决脊杖二十,随外配役一年放”;故杀官私驰骡驴者“决脊杖十七放”等。大清律例中有用罚俸代笞的规定。《大清律例·名例律》“文武官犯公罪”条规定:“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文武官犯私罪”条也有类似规定。此外,大清律例中还有用鞭责代笞杖的,条件是旗人犯罪。《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唐律中无这些换刑的规定。宋刑统、大清律例通过换刑,把原五刑的执行灵活化了,尽管它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灵活也是对五刑制度的一种变革。
2.两刑同罚 就是把两种刑罚同时适用于一种犯罪。唐律仅在个别情况下使用两刑同罚,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则广泛使用两刑同罚,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徒、流中加杖。《清史稿·刑法志》载:大明律规定“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具体适用的犯罪也不少,在此仅举一例。《大明律·刑律》“诬告”条规定:“若囚已决配,而自妄诉冤枉,摭拾原问官吏者,加所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清律例中有关徒、流加杖的规定与大明律同。此外,还有刺字与徒、流并用的。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在刑律的“白昼抢夺”条中规定: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计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伤人者,斩。为从各减一等。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两刑同罚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唐律一罪一罚的定制,亦是对唐律法定刑的一种变革。
3.增加新刑种 唐律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另附以没官、连坐等。唐后在此以外,另增加了一些新刑种,主要有:
①杖死。这是一种用杖处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唐律规定死刑为二,即绞和斩。宋刑统认可杖死也为死刑。《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准“十恶中恶逆以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应合处绞、斩刑自今以后,并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
②刺字。这就是过去的墨刑。唐律废而不用。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皆有关于使用刺字的规定,主要适用于一些与盗有关的犯罪。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均在刑律的“窃盗”条规定:窃盗“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
③充军,这是一种将重犯押至边远地区服若役的刑罚。它常适用于一些死罪减等者,用刑很严。《明史·刑法志》载:“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都有关于充军的规定。《大明律·名例律》“杀害军人”条规定:“凡杀死军人者,依律处死,仍将正犯人余丁抵数充军。”充军还有与杖并用的。《明律·兵律》“宫殿门擅入”条规定:“入皇城门内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大清律例对充军作了规范的规定,内容包括充军的里程发遣部门等。《大清律例·名例律》“充军地方”条规定:“凡问该充军者,附近发二千里,近边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发四千里。定地发遣充军人犯,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抚定地,仍抄招知会兵部。”律中多处适用充军。《大清律例·户律》规定:“诈称各卫军人不当军民差役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其它的不再赘列。
④凌迟。这是一种用刀脔割罪犯使其慢慢痛苦死去的酷刑。此刑在辽时入律,明清都沿用,适用于一些最严重的犯罪。《大明律·刑律》“谋反大逆”条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杀一家三人”条规定:“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大清律例的规定与以上同。
此外,还有枭首等,在此不一一罗列。以上这些刑罚皆为唐律无,也不列入五刑范围,成为一种五刑之外的律中之刑。为此,薛允升很不满意。他说:“唐律无凌迟及刺字之法,故不载于五刑律中,明律内言凌迟、刺字者指不胜屈,而名例律并未言及,未知其故。”“复枭首、凌迟之刑,虽日惩恶,独不虑其涉于残刻乎。死刑过严,而生刑过宽,已属失平”。⑿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刑制的改革不仅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唐律的框框,还有用刑渐重之势。除折杖法外,无论是两刑同罚,还是增设的新刑种,均酷于唐律规定的五刑。用刑是用法的测量计,用刑渐重直接反映用法的加重。它可帮助人们知晓宋、明和清刑事立法的概要和趋势。
五、变革的原因
法律既属上层建筑,又是国家意志,它的变革必有多种原因,唐后对唐律的变革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1.社会情况的变化 法律是一种应时性很强的统治工具,社会情况的变化是对其进行变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法律不适时,就会变成具文,失去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唐律的内容虽然很周全,集了古者立法之大成,但是唐后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有些内容不同程度地落后于现实,有的甚至已无存在的意义。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便本能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立法权,删改损益唐律的内容,制订新律,以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在这方面,有关经济民事方面的内容十分典型。唐律定本于唐前期,其中有关经济民事的规定以当时施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出发点,并以维护、执行这些制度为目的。可是到了宋、明、清,一方面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早已废除,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已露头,唐律中原有的一些规定显然已经过时。因此,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删去了唐律规定的“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目,废弃其中无用的内容。同时,根据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新增了一些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打击破坏经济秩序和有损正常民事活动的犯罪行为。宋刑统增设“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中的一些内容都直接有助于调整公民的财产关系,以适应当时日益发展的继承和典卖问题的需要。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特别设立“盐法”、“私茶”和“匿税”等条,确立国家对盐、茶等的专管和对税收的严格控制严惩违犯盐、茶法和税收规定的犯罪行为,维护当时的经济秩序。这些都是唐后社会的必然产物。唐律制订时,还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其它一些内容的变革也都与社会情况有极大的关系,在此不一一列举。
2. 立法经验的结累 立法是一种国家职能。法律由统治者主持制定,因此他们的立法经验对立法内容的关系极大,它也是法律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注意总结前人立法之得失,并根据本朝代的特点,变改唐律一些内容,使之更好地为己所用。我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三典”之说。《汉书·刑法志》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但以后的立法实践所产生的效果却各不相同。商鞅用重法,秦国大振。秦朝用重法,二世而亡。汉、唐初用轻法,得人心,国兴民安。南朝梁武帝用轻法,“每年数赦,卒至倾败”。⒀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前人用法的经验和教训,并正视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认为虽是新邦,仍需用重典。历史上也有他们用重典治国的记载。《宋史·刑法志》载:“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这在宋刑统中亦有反映,用杖死这一酷刑就是一个方面。朱元璋执政后,也主张用重典。他曾说:“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⒂大明律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者,故新增之刑无一轻于五刑,且全为酷刑。大清律例与大明律相差无几。因此,薛允升在比较了唐、明律后认为,大明律有重其所重之处。其实,这一“重”正是明初的统治需要,因为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大明律重典治国,明初的政权会得到巩固并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会有较大发展吗?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明律相对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不能简单理解为“重”,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否则,历史将会改写。当初用重典,既是统治者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总结和借鉴前人立法经验的结果。
3.立法技术的提高 立法是一个把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技术很重要。高的立法技术, 可使制订的法律准确地反映统治阶级的要求,符合时代的需求,并为司法提供正确依据。相反,法律就会歪曲反映统治者的意志,甚至破坏法制的协调,造成法制混乱,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我国古代的立法者大多重视立法技术,立法技术也因此而不断提高。从唐律到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体例的发展和变革过程,可以看到一个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唐律十二篇,内容简要明了,而且名例列入篇首,集中了前者立法之精华,立法技术高于以往。但宋的立法者并没停止不前,他们制定的宋刑统在篇下分门,分门别类,还在律条后附以其它法律形式的相关内容,以类相聚。这给查律者带来方便,易查易找,一目了然。宋刑统在立法技术上确有高于唐律之点。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不仅一改唐律的篇目结构,还减少律条,使用较少的律条规定一样需要的内容。!另外,它们还在篇目下分条,既有律篇下分条的长处,又有宋刑统篇下分门的优点,使这一体例更接近于现代刑法典章、节、条的体例结构。明、清又在立法技术方面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立法技术的提高同样成为变革唐律的一个原因。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虽对唐律进行了变革,但仍保留着唐律的指导思想和大量的内容,唐律的影响处处可见。另外,它们的变革也是以唐律为基础的变革。没有唐律,不可能有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这从又一个角度证实唐律的深远影响和它在我国古代立法中的重要地位。
①②⑧《宋刑统》第514页,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下同。
③《宋刑统》第515页。
④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1129页,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下同。
⑤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名例律》“无官犯罪”条。
⑥《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
⑦《宋刑统》第518页。
⑨《宋刑统》第519页。
⑩《历代刑法考》第1830页。
⑾《宋刑统》第508页。
⑿《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五刑”条。
⒀吴兢:《贞观政要·赦令第三十二》。
刑法所有条例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法定刑升格条件中的首要分子、多次、作为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或者报酬的违法所得数额,是不需要认识的内容;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下,只要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可以适用加重法定刑;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为严重财产损失(公共危险犯与职务犯罪除外)与其他具体违法事实(具体升格条件)的情形下,只有当行为人对之有认识时,才能适用加重法定刑,否则只能适用基本犯的法定刑;在法定刑升格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下,对构成情节(特别)严重的事实,应当具体区分为不需要认识、需要有预见可能性和需要有认识三种情形,但行为人对(特别)严重与否的评价错误,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行为人对同一法条中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事实认识错误(如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实施抢劫) ,也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
一、问题所在
我国刑法分则有许多条文规定了具体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例如,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罪规定了8种法定刑升格条件:“(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再如,刑法第318条第1款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规定了7 种法定刑升格条件:“(一)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集团的首要分子;(二)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的; (三)造成被组织人重伤、死亡的; (四)剥夺或者限制被组织人人身自由的;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 (六)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七)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wWW.133229.cOM”此外,很多条文仅将犯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不少条文仅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
上述条文所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明显属于结果加重犯。就结果加重犯而言,刑法理论已经没有争议地认为,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必须具有过失,否则不成立结果加重犯[ 1 ] ( p182) 。问题是,有关结果加重犯的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所有的法定刑升格条件? 详言之,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关于行为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认识,有以下情形值得特别研究: (1)哪些条件是适用加重法定刑时不需要认识的内容? 例如,适用刑法第318条第1款第1项时,是否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首要分子? (2)在刑法条文将人身伤亡、公共危害以外的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的财产损失(也可谓加重结果,以下简称为加重财产损失)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时,是套用结果加重犯的原理,认为只要行为人对此加重财产损失具有过失即可,还是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 例如,行为人误将价值百万元的财物当作价值几千元的财物而窃取时,如何选择法定刑(是适用数额较大的规定,还是适用数额特别巨大的规定) ?(3)对加重结果以外的具体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以下简称为具体升格条件) ,是否需要认识? 例如,行为人客观上抢劫了抢险物资,但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自己抢劫的对象为抢险物资时,能否适用刑法第263条第8项的规定? 换言之,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普通财物予以抢劫的,能否适用抢劫抢险物资的加重法定刑? (4)对抽象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以下简称为抽象升格条件) ,是否需要认识? 亦即,当刑法条文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规定了加重法定刑时,是否仅当行为人认识到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时,才能适用加重法定刑? (5)行为人在一个法条所列举或规定的不同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之间发生认识错误时,应当如何处理? 例如,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抢劫的,或者误将军用物资当作金融机构资金抢劫的,应当如何处理?
在进入下文之前,先作如下交待: (1)本文仅讨论故意犯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认识,不涉及过失犯的法定刑升格条件; (2)法定刑升格条件为重伤、死亡的典型的结果加重犯,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3)为了避免混淆与表述方便,下文在论述严重财产损失时,一般使用“数额(特别)巨大”的表述,在抽象的法定刑升格条件时,一般采用“情节(特别)严重”的表述。
二、不需要认识的内容
根据责任主义原理,故意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具有认识。国外刑法理论公认,就致人伤亡的结果加重犯而言,行为人对加重结果不必认识,但需要具有认识可能性。① 例如,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成立,以行为人认识到伤害事实为前提,虽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死亡结果,但对死亡结果必须具有预见可能性。倘若行为人认识到死亡结果,就成立故意杀人罪,而非故意伤害致死罪;倘若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没有预见可能性,就只能认定为普通故意伤害罪。但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不等于结果加重犯。所以,除了致人伤亡的结果加重犯外,哪些法定刑升格条件是不需要认识的内容,就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
笔者通过对刑法分则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归纳,认为以下几种法定刑升格条件属于不需要认识的内容:
(一)首要分子
当分则条文将某种犯罪的首要分子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时,不要求行为人对自己是首要分子具有认识,只要行为人事实上属于首要分子即可。例如,行为人甲原本在伪造货币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但他误以为自己还不是首要分子,只是一般成员。甲的这种认识错误,不是事实认识错误,而是对自己行为作用的评价错误。这种错误也不是违法性的认识错误(因为甲并非误以为自己的行为不违法) ,所以,不影响甲的责任。概言之,对于甲依然应按照“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适用加重法定刑。倘若认为只有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时,才能适用加重的法定刑,便意味着刑罚的轻重仅仅取决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主观评价,甚至仅仅取决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不合理的主观评价,这便违背了法的客观性。
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首要分子,并不违反责任主义。因为首要分子只是刑法与法官对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综合评价所使用的一个规范概念。与这一规范概念相对应的是客观事实。所以,只要行为人对与首要分子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具有认识时,就能认定行为人是首要分子。例如,对行为人适用“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的法定刑时,要求行为人在组织、策划、指挥伪造货币的犯罪行为时,认识到基本构成要件的事实(明知自己在实施伪造货币的行为) ,认识到构成首要分子的事实(组织、策划、指挥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一般不会产生疑问。换言之,只要行为人在犯罪集团中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犯罪的行为,基本上会无一例外地按照“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选择法定刑。
(二)多次
刑法将多次抢劫,多次聚众斗殴,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多次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多次强迫他人卖淫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与司法实践,多次是指三次以上。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行为人在第三次犯罪(如抢劫)时,误以为自己只是第二次犯罪(如抢劫)的,对其是否适用多次的法定刑?
如果说,只有当行为人对“多次”本身具有认识时,才能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就必然出现以下局面:倘若甲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实施过二次抢劫行为,进而认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第三次抢劫行为,那么,他便具备相应的主观要素,进而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倘若乙不记得(忘记)自己已经实施过二次抢劫行为,进而误认为自己现在是第二次实施抢劫行为,那么,他便不具备相应的主观要素,所以不适用加重法定刑。大概没有人会赞成这一结论。因为这一结论意味着记忆力的强弱可以直接决定加重法定刑的适用与否:记忆力强的,可能适用加重刑;记忆力弱的,可能不适用加重法定刑。如果要得出甲、乙都成立多次抢劫因而都适用加重法定刑的结论,就只能认为,虽然要求行为人每次抢劫时都必须具有“抢劫”的故意,认识到抢劫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但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多次”抢劫。
适用多次的法定刑时,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到多次,并不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因为多次是对各次犯罪行为的累加,只要求行为人三次以上实施相同犯罪行为即可,而且不以符合连续犯的条件为前提。与认定同种数罪时,只需要行为人对每次犯罪具有故意一样,认定多次犯罪时,也只需要行为人对每次犯罪具有故意,而不要求行为人后一次犯罪时都必须认识到自己前一次、前几次实施过相同的犯罪。
(三)作为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或者报酬的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
广义的违法所得数额,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种违法所得数额,是指取得型财产罪(包括部分经济犯罪,如金融诈骗罪)中,将他人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者占有、所有的数额。这种违法所得数额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完全一致。此时的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直接意味着被害人财产损失数额(特别)巨大(加重财产损失) 。换言之,这种违法所得是对行为对象的取得。如后所述,这是需要认识的内容。例如,只有当行为人明知所盗窃财物肯定或者可能数额(特别)巨大时,才能适用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不过,严格地说,此时不是对违法所得数额的认识,而是对行为对象与行为结果的认识。
另一种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犯罪行为孳生之物、犯罪行为的报酬等数额。刑法第170条第1款规定的“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第318条第1款所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便属于这种情形。在这种场合,只要行为人客观上伪造的货币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就应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因为与行为对象不同,犯罪行为孳生之物与犯罪行为的报酬,都不是构成要件要素。即使刑法分则条文将这种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基本法定刑的适用条件(参见刑法第218条) ,那也只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因而不要求行为人对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本身具有认识。在刑法分则条文将这种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时,更不需要行为人认识。换言之,在这种场合,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实施了使其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即可。例如,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伪造货币的行为时,只要数额特别巨大的假币是其行为造成的,就应对行为人适用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
三、对加重财产损失的认识
在取得型财产罪以及部分取得型经济犯罪中,行为人取得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即加重财产损失) ,是法定刑升格条件。适用加重法定刑时,是否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数额(特别)巨大,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甲侵入普通家庭实施盗窃行为时,没有发现贵重物品,估计被害人床头柜上的手表价值1000元左右,便将其盗走。其实,该手表价值12万元。能否认定甲盗窃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进而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
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已成为各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并已被一些国家立法化(参见德国刑法第18条) 。因为责任主义是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对于行为人没有过失所造成的加重结果当然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如同对意外事件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一样。即使认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结果加重犯,都限于基本行为通常可能导致加重结果的情形,也不排除行为人在特殊情况下不能预见加重结果的发生。所以,司法机关仍需具体判断行为人是否对加重结果有过失。
倘若套用结果加重犯的模式,认为数额(特别)巨大是一种加重结果,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过失即可成立结果加重犯,进而认为只要行为人有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对数额(特别)巨大不需要有认识,只要有认识的可能性即可,就会认为上例中的甲具备法定刑升格的条件,进而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但笔者持相反态度。
诚然,可以认为,盗窃数额(特别)巨大财物,也是一种结果加重犯。但是,这种结果加重犯不同于只要求对加重结果有过失的结果加重犯。如所周知,在国外的刑事立法中,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仅限于致人伤亡。因而可以说,在国外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中,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的原则,是就致人伤亡的加重结果犯而言的。由于过失致人伤亡本身是犯罪,所以,在加重结果表现为人身伤亡的场合,仅要求行为人对该结果具有过失,不会违反责任主义。然而,当加重结果是加重财产损失时,就不能简单套用以伤亡结果为内容的结果加重犯的模式。
首先,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分则条文都是为了保护特定的法益,其中有的只保护单一的法益,有的保护二、三种法益。犯罪结果是对法益的具体侵害事实。如果某种事实并不表现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就不能说明违法性的程度,不能作为犯罪结果。但是,某种事实是否属于罪刑规范所阻止的犯罪结果,还必须结合有责性进行具体判断。例如,罪刑规范阻止故意造成的财产损害结果(设立了故意毁坏财物罪) ;但并不阻止过失造成的财产损害(没有设立过失毁坏财物罪;具有公共危险与职务过失的除外,下同) 。既然如此,就不能将过失造成的财产损失作为刑法上的加重结果。
其次,将罪刑规范并不阻止的结果作为法定刑升格的加重结果,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支配定罪,而且支配量刑。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属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行为;不管是对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单独定罪处罚,还是在处罚其他犯罪时附带对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科处刑罚,都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最后,如果将过失造成财产损失作为加重结果或者法定刑加重的情节,则形成了间接处罚[ 2 ] ( p1229) 。即某种行为及结果原本不是刑罚处罚的对象,但由于该行为及其结果存在于某一犯罪中,导致对该行为及结果实施刑罚处罚。详言之,过失盗窃财物的行为,原本并不成立犯罪,不受刑罚处罚。如果因为甲在故意盗窃数额较大财物时,过失盗窃了数额(特别)巨大财物进而选择加重的法定刑,便间接地处罚了过失盗窃财物的行为。假定上述甲的盗窃行为,原本只应判处3年有期徒刑,但法官以其客观上盗窃了数额特别巨大财物为根据,选择加重的法定刑,判处甲13年有期徒刑。这意味着过失盗窃的行为受到了10年有期徒刑的处罚。然而,过失盗窃行为原本在刑法上不受刑罚处罚。这便形成了间接处罚。显然,间接处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应予禁止。
在本文看来,当刑法将严重财产损失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时,如果基本犯是故意,那么,行为人对该犯罪的加重结果也应限于故意。上例中的甲虽然客观上盗窃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但不能适用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因为甲由于认识错误导致没有认识到所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时,即使其应当预见到数额特别巨大,也不能认定为故意盗窃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充其量认为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有过失。但是,由于刑法并不处罚过失盗窃行为,所以,不能令行为人对数额特别巨大承担责任。因为过失造成的财产损害并不具有可罚性,如果将过失造成财产重大损失的情形也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让行为人对没有预见的数额特别巨大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属于间接处罚,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
与基本犯相比较,也能说明这一点。当行为人没有认识到所盗财物数额较大时,不成立盗窃罪。例如,当行为人合理地以为行为对象是一床破棉絮而盗走,因不知道也未发现棉絮中藏有3000元现金,进而将棉絮以5元钱卖给他人时,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盗窃罪。在这种场合,虽然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其主观上不存在“盗窃罪”的故意,只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因而不具备盗窃罪的非难可能性[ 3 ] ( p162) 。基于同样的理由,当行为人没有认识到所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时,就不能适用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因为责任主义的机能不仅体现在定罪中,而且体现在量刑中。亦即,刑罚的程度必须控制在责任的范围内,刑罚的程度不能超过责任的上限;作为量刑根据的事实必须是可以归责于行为人的事实。②
四、对具体升格条件的认识
除了致人重伤、死亡与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之外,刑法分则条文对某些犯罪还规定了法定刑升格的其他具体条件。于是,在适用相应的加重法定刑时,是否以行为人对具体升格条件的认识为前提,就成为重要问题。例如,适用入户抢劫的规定时,是否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进入的是“户”? 再如,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普通财物进行抢劫时,是否适用加重的法定刑? 我国刑法理论历来将犯罪构成要件分为基本构成要件与加重、减轻构成要件,同时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是区分罪数的基本标准。既然如此,就意味着加重、减轻构成要件不同于基本构成要件,一个行为人以a行为实现了基本构成要件,又以b行为实现了加重构成要件时,理应认为行为人触犯了两个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成立两个不同的犯罪。既然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就表明触犯的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可事实上,刑法理论与司法解释又没有根据加重、减轻构成要件确定罪名,只是根据基本构成要件确定了罪名。例如,刑法理论认为刑法第263条规定的8种法定刑升格的情形属于加重构成要件,但又不认为刑法第263条在普通抢劫罪之外,另规定了8种加重的抢劫罪名。这是很矛盾的现象。另一方面,刑法理论所确定的加重、减轻构成要件似乎又过宽,即将一些并没有改变犯罪构成要件(或者并不存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变化) ,只是单纯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规定,也列入加重、减轻构成要件。
所以,刑法理论现在要做的是,首先讨论加重、减轻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关系,其次讨论对加重、减轻构成要件应否确立独立的罪名(当然,本文不可能具体讨论后一问题) 。关于加重、减轻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关系,有必要先考察德国刑法规定及其刑法理论的观点。
在德国,基本构成要件所规定的犯罪与构成要件的变异所形成的犯罪,当然属于不同的犯罪。例如,德国刑法第212条规定了普通的故意杀人罪(基本犯罪) ,德国刑法第216条第1款规定:“受被害人明确且认真的要求而杀人的,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自由刑。”该款规定的基于要求的杀人罪可谓减轻的构成要件,但它依然必须具备普通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例如,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杀人行为并致人死亡,必须具有杀人故意等。再如,德国刑法第249条规定了普通抢劫罪,第250条规定的则是加重抢劫罪(加重的构成要件) 。实现加重的构成要件的前提是实现了普通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概言之,加重、减轻构成要件的实现,都以符合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为前提,所以,加重、减轻构成要件并没有修改基本构成要件,只是增加或者减少了不法内容。由于基本构成要件与加重构成要件所规定的是不同的犯罪,因此,在原本存在加重构成要件事实,但行为人误认为仅存在基本构成要件事实时,就属于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只能按基本犯罪处理。
德国刑法与刑法理论明确区分构成要件的变异与单纯量刑规则的通例。例如,德国刑法第242条规定了普通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第243条第1款规定:犯盗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通常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在实施行为时侵入、翻越、用假钥匙或者其他不属于正当开启的工具进入建筑物、办公或者商业空间或者其他封闭的空间或者隐藏在该空间中; (2)从封闭的容器或者其他有防盗设备的场所盗窃物品的; (3)职业盗窃的; (4)从教堂或者其他服务于宗教活动的建筑物或者空间中盗窃被献于神职或者服务于宗教崇敬的物品; (5)盗窃处于一般可进入的收集场所中的或者被公开展览的具有科学、艺术或者历史或者用于技术发展意义的物品⋯⋯。这种规定的特点是,虽然法条所列举的事例“通常”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但在具体案件中,即使存在法条所列举的通例,法官依然可能不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反之,即使不存在法条所列举的通例,法官也可能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由于存在法条列举的通例也不一定加重刑罚,不存在法条列举的通例也可能加重刑罚,所以,法条所列举的通例就不具有构成要件的特点,因而仅属于单纯的量刑规则的通例。③
不过,德国刑法分则中的量刑规则的通例,有时又是被当作构成要件要素对待的。最为典型的是,在行为人对法条所列举的通例发生认识错误时,按照构成要件的错误来处理。例如,当行为人误将服务于宗教崇敬的物品当作具有艺术意义的物品而盗窃时,或者误将服务于宗教崇敬的物品当作普通物品而盗窃时,就作为构成要件的错误来处理。④换言之,就故意犯而言,即使量刑规则的通例不是加重构成要件,行为人也必须对此具有认识。这是对责任主义的坚持与贯彻。
不承认量刑规则的通例属于构成要件,但在行为人发生认识错误时,又按照构成要件的错误来处理,这似乎缺乏理论上的一致性。于是,德国有学者认为量刑规则的通例仍属于构成要件。⑤ 但在本文看来,即使认为量刑规则的通例不属于构成要件,对于就通例产生认识错误的情形,也可以而且应当按照构成要件的错误来处理。这是因为,既然适用加重法定刑时,需要行为人对量刑规则的通例具有认识,那么,当行为人发生认识错误时,就必须根据认识错误理论进行处理。显然,在这种情形下,关于处理构成要件的错误的原理,完全适用于有关量刑规则的通例的认识错误。换言之,即使刑法理论试图对有关量刑规则的通例的认识错误形成一种独立的原理,该原理与处理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的原理,不会存在任何区别,而会完全一致。因为任何有关认识错误的理论,都是在责任主义指导下形成的。
借鉴德国的刑法理论,我国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具体升格条件(如入户抢劫,抢劫军用物资等) ,其实是加重的构成要件。易言之,对这类法定刑升格条件所形成的罪状原本应概括为独立罪名。例如,对于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抢劫罪,要么可以概括为2个罪名,即抢劫罪与加重抢劫罪,要么可以概括为9个乃至更多的罪名,即抢劫罪与入户抢劫罪等罪名。再如,对于刑法第318条所规定的罪名,也可以作相应的概括。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法定刑的具体升格条件,是加重构成要件;在适用加重构成要件的加重法定刑时,就故意犯而言,以行为人认识到具体升格条件为前提。否则,便违反了责任主义。退一步而言,即使将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具体升格条件视为量刑规则的通例,对加重法定刑的适用,也以行为人认识到符合通例的事实为前提。
有一种观点认为,就量刑规则的通例而言,也应采取结果加重犯的模式,亦即,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犯罪有故意,对法定刑升格条件有认识可能性就可以了。⑥本文认为,当刑法把致人重伤、死亡以外的事实作为法定刑的具体升格条件时,明显不能套用结果加重犯的模式,即不能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实施基本犯罪的故意,对具体升格条件缺乏认识时,也可以适用加重的法定刑。例如,当行为人将抢险物资当作普通财物实施抢劫行为时,即使行为人应当预见到是抢险物资,但只要事实上没有认识到是抢险物资,就不能适用抢劫抢险物资的规定。理由如下:
第一,如上所述,在我国,具体升格条件实际上是加重的客观构成要件,而不是量刑规则的通例。故意犯中的加重的客观构成要件,也是行为人必须认识到的内容;否则,行为人对该加重事实就没有故意。即使认为具体升格条件是量刑规则的通例,在适用其法定刑时,也必须以行为人认识到量刑规则的通例为前提。
第二,具体升格条件基本上都是客观要素,即所描述的是行为的客观内容(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升格条件也可能存在主观要素,但此时不涉及故意的认识内容问题,故不在讨论之例) 。这些要素为加重的违法性提供根据。根据责任主义原理,只有当行为人对违法事实具有非难可能性时,才能承担责任。基于同样的理由,只有当行为人对加重的违法事实具有非难可能性时,才能承担加重的责任。就故意犯而言,只有当行为人对违法事实或者加重的违法事实具有认识时,才具有故意犯或故意的加重犯的非难可能性。所以,即便将具体升格条件视为量刑规则的通例,行为人也必须对此有认识(在过失的场合,需要有认识的可能性) 。例如,就德国刑法第243条第1款所列举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以及加重的法定刑而言,倘若行为人客观上盗窃了具有艺术意义的物品,但其主观上对该特定对象并无认识,仅仅认识到是普通财物时,就不能适用该款所规定的加重的法定刑,否则便违反了责任主义原理。同样,在我国,行为人误将珍贵文物当作普通财物实施盗窃行为时,即使客观上情节严重,也不能适用“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规定。
第三,对客观上触犯重罪,但行为人仅有犯轻罪的故意时,以轻罪论处,不仅是责任主义的要求,也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唐律·名例律》规定:“其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依凡论,本应轻者听从本。”这里的“本”实际上是指犯罪客观事实。据此,犯罪的客观事实构成重罪,但行为人没有认识到重罪的客观事实时,以一般犯罪即轻罪论处;如果犯罪的客观事实是轻罪,则不问行为人认识到的是轻罪事实还是重罪事实,都依轻罪论处。这一符合责任主义的规定,出现在当今许多国家的刑法中。例如,日本刑法第38条第2项规定:“实施了本应属于重罪的行为,但行为时不知属于重罪的事实的,不得以重罪处断。”德国刑法第16条第1款与第2款分别规定:“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没有认识属于法律的构成要件的情况的,不是故意地行动。因为过失的实施的可罚性,不受影响。”“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错误地以为是较轻的法律的构成要件,可以因为故意的实施只受到该较轻的法律的处罚。”即使认为上述规定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规定,但由于这种规定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当然也可以类推适用于对量刑规则的通例产生认识错误的情形。我国现行刑法虽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根据刑法第14条、第15条与第16条所反映的责任主义原理,对行为人不知重罪的情形,不能依重罪论处。
第四,之所以不能套用结果加重犯的模式,还因为结果加重犯本身就是结果责任的残余,而且结果加重犯只要求对加重结果有过失,是因为过失造成伤亡结果的行为本身就是犯罪行为。但是,具体升格条件是伤亡结果之外的事实特征,有的是决定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加重性质的要素。所以,不能套用结果加重犯的模式处理具体升格条件的认识。
总之,只有当行为人对具体升格条件具有认识时,才能适用与具体升格条件相应的加重法定刑。虽然客观上符合具体升格条件,但行为人对此没有认识的,只能适用基本犯罪的法定刑。所以,当行为人误以为自己是进入商店抢劫,但事实进入住宅抢劫的,不能适用入户抢劫的规定,只能认定为普通抢劫;当行为人误将军用物资、抢险、救灾、救济物资当作普通财物实施抢劫时,不应适用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规定,只能适用普通抢劫的法定刑。
五、对抽象升格条件的认识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抽象升格条件,似乎处于加重构成要件与量刑规则之间,但事实上作为构成要件处理更为合适。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只要能够认定某种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就必须适用相应的加重法定刑;不允许认定某种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却不适用相应的加重法定刑。这与德国刑法中的量刑规则的通例存在明显区别。另一方面,我国的司法解释就某种犯罪的抽象升格条件所列举之例,与德国刑法中的量刑规则的通例更相似。
关于情节(特别)严重这一抽象升格条件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被评价为严重(特别)情节的事实即“情节”,行为人是否必须具有认识? 其次,行为人是否必须认识到情节“(特别)严重”? 换言之,原本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但行为人误以为情节一般或者情节较轻时,能否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
首先,由于是抽象升格条件,因而可能包含性质不同的各种具体内容,故不可一概而论,需要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分清不同情形:
第一,当具体案件中属于(特别)严重情节的事实,是首要分子、多次、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或者犯罪行为的报酬数额(特别)巨大时,应适用本文第二部分的原理,亦即,只要客观上存在(特别)严重情节,就应适用加重的法定刑。例如,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7日《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一)价值在2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获利10万元以上的; (三)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当行为人实施本罪行为客观上非法获利10万元以上时,即使其误以为自己仅获利2万元,也应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
第二,当具体案件中属于(特别)严重情节的事实,是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时,完全应当按结果加重犯的原理处理,即只要行为人对致人重伤、死亡的事实具有过失即可。例如,刑法第267条第1款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笔者的观点,抢夺致人死亡的,应属于抢夺情节特别严重。在这种场合,只要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即可。⑦
第三,当具体案件中属于(特别)严重情节的事实,是对财产造成的严重损失时,应适用本文第三部分的原理,即只有当行为人对加重财产损失具有认识时,才能适用加重的法定刑。
第四,当具体案件中属于(特别)严重情节的事实,是加重结果以外其他客观事实时,应适用本文第四部分的原理,亦即,只有当行为人对该客观事实具有认识时,才能适用加重的法定刑。
其次,当行为人认识到了属于(特别)严重情节的客观事实,但同时认为该情节并不(特别)严重时,应当如何处理? 这便要讨论这种“认识错误”是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还是违法性的认识错误,抑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错误。
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认识错误包括事实的错误与违法性的错误,前者影响故意的成立;后者只有在不可避免时,才影响责任。从事实的错误到违法性的错误之间,大致存在五种情形: (1)自然的物理的事实的错误,如将人误认为狗而杀害的情形。这是最明显的事实的错误,不成立杀人故意。(2)社会意义的错误,如行为人本来在贩卖淫秽物品,但误以为其贩卖的不是淫秽物品。这种错误也属于事实的错误。由于对事项的社会意义的认识,只要有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就足够了,所以,只有在对这样的平行评价存在错误时(以为其他人都认为该物品不属于淫秽物品时) ,才是社会意义的错误。(3)规范的事实的错误,是指对由民法、行政法等提供意义的事实的错误(大体上是社会意义的错误的一种) 。例如,对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公私”财物这一要素,如果不进行法的性质的理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行为人的所有物在国家机关管理之下时,根据法律规定属于公共财物,行为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财物而取回的,究竟是事实的错误还是违法性的错误,还存在争议。(4)规范的评价的错误,即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违法评价存在错误的情形,是典型的违法性的错误。(5)法的概念的错误(涵摄的错误) 。例如,行为人将他人的笼中小鸟放出,但误以为其行为不属于“毁坏财物”。这种情形不影响毁坏财物罪的故意。再如,误以为共同占有的物不是“他人的财物”而出卖的,也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4 ] ( p1665) 。
首先,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情节(特别)严重,但行为人误以为情节并不(特别)严重的情形,显然既不是自然的物理的事实的错误,也不是社会意义的错误,同样也不是规范的事实的错误。概言之,不能认为上述错误属于事实的认识错误。倘若将这种错误认定为构成要件的错误,那么,对于这种情形的处罚轻重,就完全取决于行为人主观上的(不合理)评价,这会严重损害刑法的正义性与安定性。其次,行为人误以为情节并不(特别)严重的错误,是在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前提下产生的认识错误。既然如此,这种错误就不再是违法性的认识错误,而是一种单纯的评价错误。但这种评价错误,并非上述第(4)种规范的评价错误,而是对事实的评价错误,充其量属于涵摄的错误,甚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认识错误,因而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
六、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
行为人没有认识到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加重事实时,是一种事实认识错误。根据前述第四部分的分析,这种事实认识错误,对适用加重的法定刑产生影响,即不得适用加重法定刑。 在此所要讨论的是,行为人在一个法条所列举或规定的不同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之间发生认识错误时,应当如何处理? 这种错误既可能发生在具体升格条件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在抽象升格条件的情形。前者如,刑法第263条规定了8种具体升格条件。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抢劫的,或者误将军用物资当作金融机构资金抢劫的,应当如何处理? 后者如,刑法第266条将情节特别严重规定了法定刑升格条件,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24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生产资料而骗取,数额在10万元以上,造成严重后果的,能否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
笔者通过对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归纳,发现这类认识错误主要是对象认识错误,难以发生打击错误与因果关系的错误。例如,很难想象行为人原本打算抢劫金融机构,但因为方法错误而抢劫了军用物资。所以,下面仅以对象错误为中心展开讨论。
刑法理论将事实错误分为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与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本来是不同的罪名,但我们将其确定为一个罪名,换言之,倘若原本是不同的构成要件,而我们将其确定为一个构成要件,就会导致将原本属于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形,当作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处理,这会导致对被告人不利的处罚,违反责任主义原理。反之,如果本来属于同一犯罪,但我们将其确定为两个不同罪名,就会导致将原本属于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形,当作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处理,这会形成处罚空隙,损害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但在刑法理论的通说与司法解释没有将加重构成要件确定为独立罪名,实际上又可以将加重构成要件确定为独立罪名的情况下,只好既从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又从不同构成要件间的错误来考虑。
首先,如果对象错误属于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不管是根据法定符合说,还是根据具体符合说,这种错误都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
如前所述,倘若将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8种加重情形概括为一个罪名即加重抢劫罪,则可以认为,抢险物资、军用物资、金融机构等均属于一个加重犯罪的可供选择的对象。在此意义上说,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抢劫的,或者误将军用物资当作金融机构资金抢劫的,就属于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错误。但是,这种认识错误并不等同于典型的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而是属于选择性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认识错误。例如,行为人甲误将a当作b杀害时,是典型的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错误。因为a与b都是故意杀人罪中的“人”,就此而言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抢险物资与军用物资毕竟不是相同的对象,而是只要抢劫其中一种物资即可适用加重法定刑。所以,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抢劫的,或者误将军用物资当作金融机构资金抢劫的,属于选择性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认识错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讨论,在基本犯中,行为人就同一条文所列举的可供选择的对象要素发生认识错误时,是否影响定罪? 例如,刑法第127条第1款规定:“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所规定的枪支、弹药、爆炸物三种对象明显属于选择要素,即只要盗窃或者抢夺其中之一便成立犯罪,同时盗窃、抢夺三种对象物的,也只成立一罪。假如行为人本欲盗窃枪支,但实际上盗窃了弹药的,是否影响犯罪成立?
笔者持否定回答。亦即,在上述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盗窃弹药罪(既遂) ;既不能认定为盗窃枪支未遂,也不应宣告无罪。理由是:其一,枪支、弹药、爆炸物是第127条并列规定的三种可以选择的对象,而不是根据不同对象规定为不同犯罪,说明针对不同对象所实施的行为都是同一犯罪行为;既然是同一犯罪行为,没有超出同一构成要件的范围,根据法定符合说,这种错误便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其二,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但同条规定的盗窃、抢夺危险物质罪属于具体的危险犯) ,当行为人以盗窃弹药的故意实施了盗窃弹药的行为时,当然具有抽象的公共危险;但当行为人以盗窃枪支的具体故意,实施了盗窃弹药的行为时,其行为所具有的抽象的公共危险性质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而是取决于客观事实。既然如此,行为人的上述错误便并不影响其行为的性质。当行为是具体危险犯与实害犯时,也应得出相同的结论。例如,刑法第127条规定的盗窃、抢夺危险物质罪,其对象包含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但必须“危害公共安全”。当行为人出于抢夺毒害性物质的故意,实际上抢夺了放射性物质,并且危害公共安全时,也应认定为抢夺危险物质罪。因为所谓抢夺毒害性物质的故意,在刑法上属于抢夺危险物质的故意;客观上抢夺放射性物质的行为,在刑法上属于抢夺危险物质的行为。有责性与既遂的违法性相对应时,没有理由认定为犯罪未遂,更没有理由宣告无罪。其三,如果认为上述认识错识影响犯罪的成立,便会给司法实践造成极大的困惑:那些盗窃了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人,都可以声称只是为了盗窃另一种对象,从而导致其行为只成立犯罪未遂甚至被宣告无罪,而司法机关对行为人主观上究竟为了盗窃哪一种对象确实难以证明,这便会不合理地放纵犯罪。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同一犯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中包含了选择性要素时,行为人在选择性要素之间发生的认识错误,与典型的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没有区别,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其一,在将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8种情形视为一个加重抢劫罪的前提下,抢险物资、军用物资、金融机构等,实际上是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可以选择的对象,说明针对不同对象所实施的行为都是同一加重抢劫行为,故没有超过同一构成要件的范围。根据法定符合说,这种错误不对犯罪的认定与法定刑的适用产生影响。其二,从规范意义上说,行为人认识到是抢险物资而抢劫该物资,与行为人误以为是军用物资而实际上抢劫了抢险物资,在客观违法性与主观有责性方面,没有任何差别。既然如此,对这两种情形,就应当作相同处理。换言之,在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为军用物资抢劫的情况下,倘若认定为抢劫军用物资未遂,违反了对相同的情形应作相同处理的正义原则。其三,基于刑事政策的理由,为了防止处罚空隙,也不应承认上述认识错误具有意义。再如,刑法第328条第1款规定了如下法定刑升格条件:“(一)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当行为人误将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当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实施盗掘行为时,这种认识错误不具有任何意义。
其次,如果将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8种加重情形,视为8种以上不同的加重构成要件,分别成立8种以上不同的加重抢劫罪,则可以认为,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抢劫的,或者误将军用物资当作金融机构资金抢劫的,就属于不同构成要件间的对象错误,即属于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
根据法定符合说认为,只要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现实的事实处于同一构成要件内,就可以认定故意,因此,抽象的事实错误原则上阻却故意。但是,抽象的事实错误并不都阻却故意,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承认抽象的事实错误并不重要。围绕这一范围,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分歧[ 5 ] ( p1228) 。本文不可能分析各种学说的利弊,只是提出以下看法:应当在具有归责可能性的范围内认定犯罪和适用法定刑。亦即,不能仅根据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或仅根据行为的客观事实认定犯罪和适用法定刑,而应在故意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范围内认定犯罪和适用法定刑。所谓“故意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是归责意义上的相符合,因而是实质意义上的相符合。换言之,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所认识的犯罪与客观上所实现的犯罪,在保护法益、构成要件的行为方面是相同的,就应认为其“故意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其一,有责性是为了解决主观归责的问题,即在客观地决定了行为性质及其结果后,判断能否将行为及结果归咎于行为人。基于同样的理由,适用加重法定刑时,要求行为人对符合升格条件的事实具有认识,是为了将加重的违法事实归责于行为人,所以,并不是所谓主观与客观的简单与机械的对应。质言之,抢劫军用物资的故意,能够成为客观上抢劫抢险物资的主观归责理由,故应认定行为人对抢劫抢险物资承担责任。其二,抢劫军用物质与抢劫抢险物资,所侵害的法益相同,而且构成要件的行为相同,所以,二者具有实质的重合。既然如此,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错误,就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总之,在行为人误将抢险物资当作为军用物资,或者误将军用物资当作金融机构资金抢劫时,不管是将其作为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具体的对象错误,还是作为不同构成要件间的抽象的对象错误,都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
注释:
①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006年版,第200页; claus roxin, strafrechtallgemeiner teil,band i, 4. aufl. , c. h. beck2006, s. 331f。
②当然,行为人对数额较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认识,不必是绝对肯定的认识,只要具有未必的认识即可;不必是精确的认识,只要有大概的认识即可。此外,行为人抱着“能偷多少偷多少,偷到多少算多少”心态盗窃财物时,完全可以按照其窃取的财物数额定罪量刑。
③以上参见[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2meiner teil,band i, 4. aufl. , c. h. beck 2006, s. 341f.
④vgl. ,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 4. aufl. , c. h. beck 2006, s. 342.
⑤vgl. , günther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walter de gruyter 1993, s. 178.
⑥德国学者zipf就采取了这种观点,vgl. ,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 4. aufl. , c. h. beck 2006, s. 507.
⑦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6日《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实施抢夺公私财物行为,构成抢夺罪,同时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后果,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但这一解释导致处罚不均衡,明显不妥当(参见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法学家》2006年第2期,第119页以下) 。
参考文献:
[ 1 ] 张明楷:“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与刑罚”,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 2 ] [德]布诺伊:“量刑における行为の非构成要件的结果の考虑”,载《东洋法学》1996年第2号。
[ 3 ] 张明楷:“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载《法学》2004年第11期。
刑法所有条例范文第3篇
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社会踏入近代已经一百六十多年了;
如果从1902 年清末修律算起,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也已经一百年有余了。
百年回望,我们当然有理由为中国社会、为中国的法制而欣慰,从皇帝专制制度、《大清律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们能够清晰的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但立足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的心情也许就不那么乐观。因为:尽管按照现念建设的立法体系、司法机构已经基本完善,但现代“法治”的理想却很难说已经大体实现。一个基本的表现是:权力超越法律仍然是弥漫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全社会法律信仰的程度依然很低。以至于让人不得不哀叹:一百年来,从根本上讲,中国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回顾百年过去,中国法律走过了艰辛的历程;前瞻未来,中国法治之路依然并不平坦。
自人类15世纪进入加速度发展的时代,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一百年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一段短的时间。因此,不管是纵向和自己的过去比,还是横向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相比,人们有理由这么认为:中国百年树法,本来应该更好。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这要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法律改革说起。
二、晚清法律改革与《大清刑律》
继1901年1月清政府决定“变法”、号召向西方学习之后,1902年3月清政府又决定“修律”,晚清十年的法律改革由此而始。一般认为,清末十年的法律改革分为两个阶段,1902-1905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法律改革主要是删削旧律,内容和工作不出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范围;但自1906年7月清政府决定“仿行宪政”、实施“预备立宪”之后,清末的法律改革便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向纵深发展,国家致力于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实行司法独立。其中,从1902年清政府决定修订《大清律例》,到1907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上奏大清刑律草案,再到1911年《大清刑律》的颁布,刑事法律的变革贯穿了晚清十年法律改革的整个过程。
《大清刑律》是中国法律史第一部具有独立意义的现代刑法典,同时也是清末各种新法中制定时间最长、争议最大的一部法律。自1907年10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和12月30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分别上奏大清刑律草案总则和分则以后,对刑律草案的各种反馈意见便纷至沓来,其中以中央各部院、地方各督抚的签注意见最为重要。正是在中央和地方大员签注的影响下,清廷下令修订法律馆会同法部对刑律草案进行修改并于1910年2月2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台《修正刑律草案》。《修正刑律草案》与最初上奏的草案相比,总体布局由原来的总则、分则两部分便成了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虽然总则17章、分则36章没有变,但条文却由387条增加到409条,在篇章名称、条文内容上也多有变化,在总则、分则之后增加的“附则”五条更是原来草案所完全没有的内容。《修正刑律草案》由宪政编查馆核查定稿后交由资政院审议,1911年1月25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清刑律》颁布。
应该说,晚清十年的法律改革,其涉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立法内容而言,一个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在内的全新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就立法过程而言,其它法律的制定相对都比较顺利,唯独刑法典的制定一波三折,1907年的刑法典草案不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且引发了绵延数年之久的“礼法之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仔细“咀嚼”的历史现象,但有一点,认为反对刑律草案就是顽固、保守的说法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同步进行的其它法律的制定也基本是移植和照搬西方的法律,就没有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而且张之洞就说过,凡是传统法律所无或者基础薄弱的法律,如商法、民法、交涉律,不妨尽用洋律。即使就刑法而言,决定对《大清律例》修订本身就是引进西方法律的过程,这一点一般意见是清楚的,“于名教纲常礼义廉耻之重,仍以中律为主。其余中律所未完备者,参用洋律。为交涉事件等项,罪名不妨纯用洋律,庶风土人情各得相宜矣”[1]。这表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并不顽固,他们懂得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的道理。但对传统法律中极为成熟和发达的刑法典,他们则当仁不让,对基本是移植和照搬西方法律的刑律草案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对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自信,希望藉此能有和西方法律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如果连这“最拿手”的东西都没有和西方平等对话的资格和机会,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有何存在的价值?斟酌、融合中西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即使今天看来,这的确也是个问题,正如苏亦工老师所言,“按照常理,清朝官方和沈氏个人如均以中西融合为宗旨,则制定刑律时,传统法律资源中可供汲取者正多,又何必舍近求远,假手洋人呢?”[2]。越来越多的迹象和材料似乎在证明,刑律草案对于中国传统刑法典中有价值的规定,并没有能够很好的予以消化吸收而留存于新刑法典之中,而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并泼掉了”。下面以《大清律例》中关于官吏犯罪和暴力性犯罪规定的积极价值被《大清刑律》废弃为例,说明草案编纂者对“本土资源”缺乏创造性转化利用。而如何正确处理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协调融合问题,是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是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以来的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病因。
三、关于官吏犯罪的规定
古代吏员犯罪有公罪和私罪之分,且私罪的量刑比公罪为重。就法律条文而言,吏员的一切活动都纳入法律的规范之内,不但故意犯罪应受严惩,与职务有关的大量过失犯罪也一样惩处。刑律草案大幅度调整了对吏员犯罪的定罪处刑,如与职务有关的大量过失犯罪不再科刑,官员的渎职犯罪被严格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对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也大大减轻。对此许多签注提出了异议,如江西签注一方面认为第一百六十四条聚众为暴行或胁迫罪中缺少对官吏人身的特别保护,“伤害实行公务之吏员,岂可与凡人同论乎?”;另一方面又认为第二百三十五条吏员明知虚伪之事实而据以制作所掌文书图样罪中应规定过失犯罪处罚的条款,“吏员有办事之权,应负办事之责。如有申告虚伪之事实者,若不查是非制作文书,虽非有意舞弊而制作错误,亦应负其责任。况虚伪之事,所关甚巨。今本案定为吏员不坐,与理尚有未协,此条应行酌改”[3]。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草案第140条仅定二三等以下有期徒刑,两广认为旧律贪赃枉法之罪处刑甚严,可至死刑,草案量刑过轻,“将使墨吏罔知戒懼而苞且之事日多,似于吏治不无妨碍”,它还认为草案第260条吸食鸦片烟罪官民无别不妥,应该重罚官弁而轻责平民[4]。湖广签注则对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告状不受理罪提出异议,认为官员不受理举报,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而应予以严惩,“查现行律例告状不受理,如告谋反、谋叛不即受理掩捕,以致聚众作乱、攻城劫掠者处分甚严,所以杜萌乱而儆溺职。现在沿江一带,伏莽甚多,或倡言革命肆无忌惮,设或有以此等事情告发,不即受理捕治,致生厉害治安,实非浅鲜。本条罪仅四等徒刑而止,未免轻纵,似应酌量加重”[5]。但修正案对以上意见,均未采纳。
传统法律固然给予了官吏以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但同时意味着比凡人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惩处,就此意义而言,传统法律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是相对公平的。草案按照近代法律精神,剥夺了官员的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同时也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单就法理而言,这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未尝没有道理。但揆诸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现实,我们看到中国行政运作从来就和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政府始终是社会的核心,官员的权力很大而事实上很少受到行政法规的约束,如果再不在刑法上就他们的犯罪行为规定较为严厉的惩处,完全有可能对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纵观近百年来中国公务员的管理,官员的各种特权和特别保护事实上仍然存在,但比凡人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惩处却因法律的取消而取消,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和看到的一些重特大事故,如重庆天然气井喷事件、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瓦斯爆炸事件以及触目惊心的假酒、假烟、假奶粉、毒火腿的横行,这其中实际上都有一个政府官员失职、渎职的问题,但却很少看到有政府官员为此承担责任,他们常常以不知道此事为自己开脱责任,这说明至少在法律上是有漏洞可钻的。以至于“一个私自成立,无任何办学资质和办学手续,学员无任何正规渠道的‘三无’假军校,(在山西太原各有关主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公开)一办就是五年”,太原市副市长范世康却说“学生被骗也有自身的原因。一些学生、家长无知无法,不按照有关招生的规章制度办事,片面听信一些人的花言巧语,结果上当受骗”[6]。呜呼,要求普通老百姓个个须有“火眼金睛”,那人民纳税“供养政府”又有何用?这是我们最不愿到的。所以,《大清律例》中对官吏犯罪的规定是有价值的,它能有效的防止因官员渎职而产生的危害超出人民可以承受的范围。关于贪污贿赂的犯罪,国外发达国家的确很少用死刑来惩处,因为它被视为经济犯罪而性质不是特别严重。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各种原因,官员的此类犯罪很多,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从来都是普通民众最恨之入骨的犯罪现象,不予以严惩就无法保证最起码的社会秩序。所以直到今天刑法里对于此类犯罪,仍有最高刑死刑的规定。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等到中国制度健全,此类犯罪现象减少,自可以与世界接轨,但在目前还不行,那就更不用说一百年前的中国了。许多签注强调对西方文化要取其利而避其害,后人也许该从中得到教训而不是不屑一顾[7]。 四、关于暴力性犯罪的规定
对一个政府而言,维护基本的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是最起码的职责。就法律体系而言,刑法在这方面责无旁贷。中国先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李悝就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贼盗”,所以《法经》首著贼、盗两篇予以严厉打击。到了唐律之中,对于故意杀人、强盗、强奸、绑架以及劫囚、反狱、聚众暴动等暴力性犯罪均视为重罪而予以处罚,到了明清朝,比照唐律“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对此类犯罪的处罚有进一步加严的趋势,几乎一概处以死刑,而且“决不待时”。刑律草案取感化主义而“酌减死罪”,结果死刑条款由《大清律例》的七百六十条降到了四十六条,对暴力性犯罪的定罪量刑随之也予以宽缓,如基本没有了死刑唯一条款[8],有的暴力性犯罪甚至最高刑只是有期徒刑。如第299条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第301条故意伤害人致死或成笃疾者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第352条强盗罪处三等以上有期徒刑、第274条强奸罪处二等以上有期徒刑、第362条诈欺取财处三等以下有期徒刑、第168条犯人暴力脱逃和第169条盗取囚人均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第164条聚众暴乱的首魁处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而骨干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一千元以下一百元以上罚金,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性犯罪,如放火、决水、爆炸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对此定罪量刑,众多签注提出了强烈异议。湖广、湖南等签注第169条时指出,“本条盗取两字,系包窃取、强取而言,窃取情节尚轻,强取即系劫囚,现行律例罪应至死,仅处以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似涉轻纵”[9];闽浙在签注第164条时指出,“此等行为即属罪干斩绞,自应将首恶分别惩治以儆不法。若概从轻减,则凶徒更肆无忌惮,势必气焰益张煽惑声乱,毫无底止后患不堪设想,实于地方治安大有关系,此两条骤难照办”[10];浙江在签注第362条则认为,“现行律例恐吓取财门内定有提人勒赎之例,节经加重,新章改照强盗律治罪。以其倚强掳足肆意凌虐勒令用财取赎,凶暴情形与强盗无异,故治罪特严。且浙省捉人勒赎之案,层见叠出。若仅处以徒刑,其何以惩强暴而望治安?”[11]。
在整个中世纪,对严重暴力性犯罪予以严厉打击以维持起码的社会稳定一直是传统法律的特点,也是优点,封建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两千多年,与此直接有关。如反狱、劫囚之罪,在中国普通人的观念里是要杀头的重罪,因为它直接对抗和蔑视政府的权威,对社会危害极大,予以严惩并无不妥,在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草案对此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与现行刑律的死刑差异过大,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维持政府权威和秩序。如强盗和强奸之罪,直接危及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也是应该予以严厉打击的,可对于两罪并发的“于盗所强奸妇女”,草案也不过处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对于犯强盗之罪故意杀人者也没有唯一死刑条款,对于当时社会经常发生绑票勒索之案,犯罪者也不过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确实情重法轻。这一点,修订法律馆诸公似乎也有觉察,修正案对于原案第168条的脱逃罪就区分了为个人暴力脱逃和聚众暴力脱逃分别定罪量刑,第169条盗取囚人区别窃取、强取、聚众劫取分别定罪量刑,两者均加入了死刑条款。于盗所强奸妇女也移入下条而可以对犯罪者处以死刑。即便如此,《大清刑律》正文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性犯罪的打击力度仍然不够。所以民国沿用《大清刑律》的内容以后,也不得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对《大清刑律》的缺陷作一定补救。如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全面贯彻袁世凯的“以礼教号召天下,重典胁服人心”的原则,“增加了对轮奸罪的规定,加重了对强奸杀人罪的处罚,对于打击恶性犯罪有积极意义”[12];同年七月颁布了《惩治盗匪法》,加重了对强盗罪的法定刑,新增了匪徒罪的规定,将七年前草案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掳人勒赎罪规定为匪徒罪而予以严惩,其量刑一般均有死刑条款而且简化了审判、执行程序。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在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了《惩治绑匪条例》、《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惩治盗匪条例》等刑事特别法以加重对此类犯罪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年刑法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一再作出《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这些都表明,自1907年刑律草案改变了《大清律例》对严重暴力性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后,历届政府在制定刑法典时皆大致上予以遵循,以免背上“开历史倒车”的恶名。但为了维护最起码的社会秩序,又不得不从现实出发,制定刑事特别法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性犯罪予以严厉打击,这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回到了《大清律例》的老路。正如苏亦工老师所言,“传统法律已经解决的问题,因抄袭西法反而感到束手无策,实践中不得不以特别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弥补,最终又回到了传统的老路,岂非庸人自扰?”[13]。
五、问题的起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有着独特法制传统的国度。儒法合流以后的中华法系,是有着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法律理念和价值标准的。但进入近代以后,在外来法律文化(以西方为主)的影响下,中华法系被迫偏离了自己的轨道而开始转型。百年来中国法制的历史,就是双方博弈的结果,但双方谁也无法战胜谁。外来因素占据了立法领域后,却再也无力向前推进;传统因素虽然退出了立法领域,却仍然实际支配着中国人的法律信仰和法律适用。这样一种独特的“共生”局面,使得中国法律出现了文本法律和现实法律的严重背离以及法律理想和法律现实的二元对立。西方的法律精神和话语已经成为中国立法体系的主流,但它却无法完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大部分只能漂浮在中国的上空。传统法律的体系和话语在形式上已经荡然无存,却仍然顽强而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并实际主宰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中外法律文化从来就没有真正融合过,它们以这种奇特的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社会当中。百年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是在法律文本、法律制度层面移植了西方法律的形式,而在实践层面保留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容。两者“脱节”“滑轮”却又“共存”的现象,是中国法律迟迟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表现。这譬如:中国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仿制了西方的机器,建设了颇有规模的大厂房,却怎么也生产不出成批量的合格产品来。其质量有的时候还不如传统作坊里的产品。这既令西方人大跌眼镜,也令中国人感到不满。这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状况,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对现代法律的信仰。它对社会危害,也许甚于“无法可依”!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外来的法律有其生长、运行的土壤,单纯的移植法律文本和司法机构并不能使它在异质的文化土壤里茁壮成长;同样的,有着悠久而独特历史的中国法律传统也并没有因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而消失,它变换了形式,依然顽强的附着在新生的制度上并主导了这个制度的灵魂。出现这样一种尴尬状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正确处理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协调和融合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不足,是百年来立法者和制度建构者的通病,以至于最后,貌似先进的法律制度为落后的政治制度的粉饰竟成了无奈的动机和选择[14]。因此,我从来认为,中国法律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本土化还是国际化这一类目标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而是如何消解中国传统因素和西方因素在中国法律上述两个层面的这种奇特“对立统一”问题。相应地,评判法律变革成效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在法哲学的逻辑和历史学的逻辑中间取得了平衡。
当然这是一个异常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我本人无力也不打算做出具体的回答。但好在中国法律现代化之初,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清末修律中绵延数年的“礼法之争”,曾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回顾并品味这段历史,也许对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启发。尽管这会让我们痛苦的意识到:百年前的一些话题,现在法学家们还在热烈讨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预示着:“我们必须承认 ,在某些方面中国依然如故地站在历史的起点 ,并没有前进”[15]。
[1] 《都察院奏折》。
[2] 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第344页。
[3] 《江西签注清单》第164、235条。
[4] 《两广签注清单》第140条。
[5] 《湖广签注清单》第145条。
[6] 《太原:五年查封不了个假军校》,北京日报2005年1月13日第九版文章。
[7] 清朝灭亡以后,《大清刑律》的内容为中华民国所沿用,但过轻的量刑显然对打击官吏的贪污贿赂及渎职犯罪不利,所以不得不在刑法典之外另立刑事特别法予以较为严厉的惩处,如1914年的《官吏犯赃条例》、1920年的《办赈犯罪惩治暂行条例》、1921年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贪污罪则按五千元、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分别量刑,对于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这表明,《大清律例》对官员犯罪采取的以赃论罪的方法和严厉打击的思路是有价值的,1907年刑律草案应该予以继承而不是摒弃。
[8] 但对于特定身份的人犯罪,如故意杀伤皇帝、故意杀尊亲属应处唯一死刑,则是极其个别的例外。
[9] 《湖广签注清单》第169条。
[10] 《闽浙签注清单》第164条。
[11] 《浙江签注清单》第362条。
[12] 朱勇:《中国法制史》第536-537页。
[13] 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第344-345页。
刑法所有条例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是指数个刑法条文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它具有三个特征,即:必须有数个刑法条文;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其原因是数个刑法条文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竞合程度与形成原因两个方面,可以分别将其分为包含型法规竞合与交叉型法规竞合和一要件型法规竞合与数要件型法规竞合。对之,在适用刑法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是: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无疑是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新法建立了诸如取消食品免检、统一食品国家安全标准、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实行食品召回等一系列制度设计与规范供给,其对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法的颁布与法的实效尚有很长的距离,其间可能存在许多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这些制度如何予以理解阐释?这些制度在施行中还存在或可能存在哪些问题?这些制度与现有的制度如何衔接、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当然需要众多学人的智识努力,其间探讨、争鸣,甚至不同意见的针锋相对也很为必要。为此,本期刊发《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初探》、《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治理模式的重构》、《食品召回法律责任研究》三篇文章,就新法涉及的一些具体制度进行探讨,以期能引起更多学人对这些问题从更为微观、更为实证的角度进行研讨分析。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国际社会普遍对之极为关注。我国当然也不例外,为了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仅相继颁行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而且专门制定了《食品卫生法》,特别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需要,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不仅对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规定了依法应当追究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而且对于其中有关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规定了依法应当追究的刑事责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8条明文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诸多条文明文规定了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究竟应当怎样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们不乏探讨。但是,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问题,人们鲜有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实践中对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正确追究。鉴于此,本文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界说
由于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问题,人们迄今鲜有探讨,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无疑属于法规竞合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要弄清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是什么,有必要先对法规竞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么,法规竞合究竟是什么呢?对之,人们有不同的认识。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法规竞合,是指行为人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且数个法条都对它作了规定,也即是数个法条竞合在一起了,其表现形式是某一法条的全部内容包含于另一法条的内容之中。[1]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是指由于法律对犯罪的错综规定,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互相存在着整体或者部分包容关系的刑法分则条文,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条文而排斥其他条文适用的情形。[2]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指一个犯罪行为,因法律错杂规定,致有数法规同时可以适用,但只在数法条中适用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成立单纯一罪的情况。[3]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是指同一个犯罪行为因法条的错综规定,出现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具有从属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4]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包容关系的刑法规范,只适用其中一个刑法规范的情况。[5]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是指因刑法对法条之错综复杂的规定,而出现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但从数个法条的逻辑关系来看,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当然排除适用其他法条的情形等。[6]综合上述各有关学者的观点,在我看来,法规竞合是指数个刑法条文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例如,《刑法》第432条与第398条,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军人故意泄露国家军事秘密情节严重的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
既然如此,我认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就是数个刑法条文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
而且,必须清楚的是,作为法规竞合的一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像其它法规竞合一样,是刑法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法律现象。因为: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包括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在内的犯罪形形色色,甚至大不相同,但是也有不少犯罪因涉及危害食品安全互相重合或交叉;另一方面,由于在互相重合或交叉的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中,其中一些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特殊性,有必要将之独立于其它犯罪加以特别规定,以更加具体地反映其特殊的社会危害性,更加突出地表现国家对其所持的否定态度,同时也更为充分地体现罪刑法定原则。
不仅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并不是纯粹基于理论的概括,而是也具有坚实的现实法律基础。例如,《刑法》第149条第2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又如,《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等等。它们都是就有关犯罪而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具体法律规定。
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特征
根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定义,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必须有数个刑法条文。也就是说,必须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刑法条文。如果没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刑法条文,或者说只有一个刑法条文,则不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问题。其中,所谓刑法条文,是指刑事实体制定法即刑法中分条用语句说明刑法规范有关组成部分的文字语言表达形式。[7]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含义:(1)刑法条文是文字语言表达形式,而不是口头语言表达形式;(2)刑法条文是用语句说明的文字语言表达形式,而不是用语词或其他非语句说明的文字语言表达形式;(3)刑法条文是分条用语句说明的;(4)刑法条文是在刑事实体制定法中分条用语句说明的,而不是分卷、分编、分节、分款、分项、分目等用语句说明的,也不是在非刑事实体制定法中分条用语句说明的;(5)刑法条文是分条用语句说明刑法规范之有关组成部分的,而不是分条用语句说明刑法规范整体的。[8]
2.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其中,无论是包含关系,还是交叉关系,都是就各有关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构成的整体而言,而不是就其中的部分要件或者要素而言。因为如果就各有关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构成的部分要件或者要素而言,那么法规竞合,就会因许多甚至所有刑法条文都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而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如果数个刑法条文之间不具有上述意义上的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就不存在法规竞合的问题。例如,规定故意杀人罪的《刑法》第232条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的竞合,以及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4条与规定盗窃罪的《刑法》第264条的竞合,就不存在法规竞合。相应地,只有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上述意义上的包含或者交叉关系,才能存在法规竞合的问题。例如,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与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4条,以及规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5条第2款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由于具有上述意义上的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因此能够存在法规竞合的问题。
3.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原因是数个刑法条文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换言之,就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的一个危害行为,同时符合数个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由此,一方面,只能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的一个危害行为。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必须是行为,即人基于意志支配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身体动静。例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玩忽职守行为等;其二,必须是危害行为,即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包括对社会有现实危害的行为和对社会有可能危害的行为。前者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玩忽职守行为,等等。后者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行为,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等等;其三,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行为。其中,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例如,在三鹿奶粉案件中,向生产三鹿奶粉的厂家提供三聚氰胺的有关农民,以及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的生产、销售单位等;其四,必须是一个行为。例如,生产有毒食品行为、销售有毒食品行为、生产有害食品行为、销售有害食品行为等。如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则属于是否构成数罪的问题,谈不上法规竞合。例如,先生产有毒食品后生产有害食品行为的行为、先销售有毒食品后销售有害食品病为、先生产有毒食品后销售有毒食品、先生产有害食品后销售有害食品的行为、先生产有毒食品后销售有害食品的行为、先生产有毒食品后销售有害食品的行为、先生产有害食品后销售有毒食品的行为等;其五,必须是基于一个罪过的行为。其中,罪过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但不能同时既是故意又是过失。如果是分别基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罪过的行为,也属于是否构成数罪的问题,谈不上法规竞合。例如,分别出于故意和过失实施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等。另一方面,同时符合数个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如果只符合一个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的,就只存在按照该条文定罪处罚的问题,而无所谓法规竞合的问题。因此,当且仅当同时符合数个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的,才存在法规竞合的问题。例如,上述《刑法》第149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如此。其中,所符合的数个刑法条文,不仅可以是同一部法律内的不同条文,而且也可以是不同法律的不同条文,但时常主要是同一部法律内的不同条文,如上述《刑法》第149条规定所涉及的各有关条文。
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分类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比较复杂,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为了方便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其竞合程度与形成原因两个方面大致对之进行以下分类:
1.根据其竞合程度,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可以分为包含型法规竞合与交叉型法规竞合两种。(1)包含型法规竞合,是指对同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规定的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关系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第140条的竞合,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第140条分别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至第144条的竞合,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分别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至第144条的竞合,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法》第397条分别与规定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刑法》第414条的竞合,都属于包含型法规竞合;(2)交叉型法规竞合,是指对同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规定的数个法规之间具有交叉关系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与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竞合,以及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分别与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法》第397条的竞合,都属于交叉型法规竞合。
2.根据其形成原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可以分为一要件型法规竞合与数要件型法规竞合两种。
(1)一要件型法规竞合,是指因一个特殊要件形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它具体又包括主体型法规竞合、对象型法规竞合、手段型法规竞合等三个亚种。
主体型法规竞合,是指因犯罪主体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法》第397条分别与规定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刑法》第414条的竞合,即属于主体型法规竞合。
对象型法规竞合,是指因犯罪对象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第140条分别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至第144条的竞合,即属于对象型法规竞合。
手段型法规竞合,是指因犯罪手段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第140条的竞合,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与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竞合,即属于手段型法规竞合。
(2)数要件型法规竞合,是指因数个特殊要件形成的法规竞合。它具体也包括一些不同的亚种。例如,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分别与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法》第397条的竞合,属于因犯罪主体与犯罪手段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分别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至第144条的竞合,属于因危害行为、犯罪手段与犯罪对象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等。
四、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适用原则
在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情况下,虽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的一个危害行为,同时符合了数个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法规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但是,由于只有一个罪过,特别是只有一个行为,因此不应当适用其中两个以上的条文认定为数罪而进行并罚,只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选择适用其中一个条文认定为一罪而予以相应的处罚。由于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无论数个法规之间的关系是包含关系还是交叉关系,在本质上都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也就是说,数个法规之间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即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因此,一般认为,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选择适用其中一个条文进行定罪处刑应当遵循的原则是: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既然如此,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而言,也不应当例外。因此,在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情况下,适用刑法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形:
1.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这就是说,只要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都应当实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因为:正是基于某种具体行为在某一事实方面具有特殊性,侵犯某一特定的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国家立法机关为对有关社会关系加以特别保护,才对之进行特别规定,以独立于和区别于有关一般规定,并且与其特殊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配置较之于有关一般规定或重或轻或相同的刑罚。因此,在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情况下,要真正符合和实现立法的意图,就必须实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否则,有关法律特别规定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2.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依法不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而采用普通法优于特别法的原则,也就是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即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法律条文进行定罪处刑。这里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是指在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情况下,有关适用普通法的特别规定,具体而言就是上述《刑法》第149条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之法规竞合的特别规定,即:“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法规竞合,根据《刑法》第149条的特别规定,应当而且必须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否则,就不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也势必使该条规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注释】
[1]高铭暄:《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218页。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3]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页。
[4]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页。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刑法所有条例范文第5篇
1环境刑法本身具备的行政从属性质
环境刑法本身具备的行政从属性质主要是指其行管的刑罚条例和环境行政法之间存在着的相互联系。具体来说在该刑法的条例中明确决定环境犯罪可罚性的判断,主要是依赖于环境行政法或该法律延伸而出的相关行政条例来决定的。对其行政从属性的研究是该刑法研究与探讨课题中的重要内容,且我国当前的环境刑法中也对行政法的遵循进行了明确的要求。所以在探讨该刑法对传统刑法观念的冲击时,首先应当对其刑法从属性质进行深入研究。环境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相互联系主要表现为一种特定的从属关系,主要是指就环境刑法本身来说,其对于环境犯罪的客观特征并没有进行明确地阐述,明确该行为是否属于环境犯罪的判断依据主要是由行政法进行确定的[1]。所以是否构成环境犯罪,主要是通过其对于行政法的违反程度来进行明确的。例如,在行政法中有关大气污染防治的条款中明确规定:“行为人违反规定,导致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并在经济财产方面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将依法进行相关刑事责任追究。”从此列举条例中可以看出,环境刑法中关于就相关条例违反行为的规定,与行政法之间存在着具有层次衔接的关联,并不仅仅局限于依赖性的从属关系。从该刑法本身的行政从属性来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是概念层面上的,这主要是指该刑法中所规定的刑法概念,如固26卷体废物等专业名词的实际解释应当是以行政法的相关规定来决定的。其次是从违反性要件的层面上来说明的,主要是指环境犯罪的行为或者程度都应当根据行政法的相关条例进行明确。所以,该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质主要表现于对相关环境犯罪的具体行为性质的认定,并且具有一定却不绝对的行政依赖性质。从环境刑法与行政法两者间的相互联系来看。该两者之间只有在对方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发挥意义。在刑法修订工作中已经就环境刑法的相关条款,实现了刑法规范性。但是就环境行政法而言,当前只是将刑事责任追究进行了简单化的规定,导致相关犯罪行为的认定依旧处于传统的行政从属性质的限制中,阻碍了该刑法的刑罚作用切实实现。所以已经有相关的学术研究者就实现解放环境刑法、将其正式引入主刑法之中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而身处于环境中的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环境犯罪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质以及潜在性的危害能力。但是就要实现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有效惩处,其必将依附于行政法的相关条例。所以就两者关系而言,行政法在一方面为环境刑法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但同时又对该刑法的相关刑罚作用进行了有效限制。在对刑法的重要保护功能进行深入探究的过程中可以明确,相关附属刑法的刑罚规定较之环境刑法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效益。这主要是由于该行政法的规定中对于相关的犯罪名称以及法定刑事处罚都进行了明确合理地规范。该方式的形成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环境秩序计划的规范性开展与实现,并充分发挥了刑法的重要核心限制功能,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该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质所导致的相关聚讼问题。所以该方式已经被多个国家广泛接受与应用。虽然就以上的环境刑法规范内容来说,其价值理念并没有被明确确认,但是该种理念的提出却对传统的刑法理念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所以,该方式是实现环境刑法修正的重要手段,能合理地对行政处罚以及刑罚处罚进行关系协调。
2当前污染环境刑法制定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对刑法理念的冲击
就当前的环境刑法来说,其针对污染环境的犯罪制定的刑法规则主要包括了重大环境污染、非法进口或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等多种形式的罪名确立。从根本上看,其主要是将相关的附属刑事条款进行了再次强调。所以就当前的环境刑法中针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相关刑法制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刑法理念对其造成的严重制约。2.1主观罪过形式的重新塑造。就环境刑法中针对污染环境犯罪立法在主观罪过形式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其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犯罪法律条款的制定上。从该条款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两方面来看,该条例难以对可能存在的故意环境污染犯罪进行制约和处理,在对该类型的犯罪进行处罚时依旧存在态度保留。这正是由于刑法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存在影响了环境刑法的深入推进与创新发展,难以切实有效地就污染环境犯罪进行处理与惩罚。根据相关条例的本身执法含义来说,在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的相关罪过形式并不能对可能存在的故意形态进行涵盖,其仅仅对该犯罪行为造成的过失危害进行考虑。虽然在修订后的刑法典中都没有就过失形态进行明确的阐述,但是其在实际理论阐述以及用法实践中都统一将该类型犯罪归为过失犯罪。这主要是根据该条例中“事故”一词存在的意义辨析进行判定的,并从心理特征以及追求结果两方面对故意犯罪形式进行排除。虽然该推理是在保证传统的立法观念上进行的,但是并不能表明立法中存在不足[2]。在传统的刑法理念中,对于过失犯罪的处罚态度并不严厉,并在追究范围以及刑法强度两方面进行了限制与制约。但是依靠传统的过失犯罪处理态度进行当前的环境犯罪责任追究,明显难以满足当前的刑事追究要求。在我国,对于过失犯罪的确定规定主要是指法律条款中没有进行明确到过失规定的犯罪行为都应当将其归类于故意成分。在其他国家的刑法中也都对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所以要保证在实际惩处判断过程中避免由于认识不清而造成的认识分歧现象,国家在进行刑法制定时就应当对过失犯罪内容进行明确。就实际发生的污染环境犯罪事件来说,其并不仅仅是指过失行为,还包括了大量的故意犯罪行为。但是在当前的环境刑法中仅仅只对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进行了故意犯罪的划分。所以,当前在针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相关刑法条例制定方面依旧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加强相关条例的修订工作是当前的重要工作内容。2.2该犯罪形式中存在的危险犯形态。环境刑法对于刑法理念的冲击作用还表现在污染环境犯罪形式中存在的危险犯形态的重要冲击作用。当前就危险犯罪形态的探究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3]。其一,主要是指危害环境罪本身存在着多种重大危害与影响因素,所以在立法中应当就该行为进行严格的惩处规定,在其体现重大危害结果之前及时进行控制和处理。其二,主要是指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明确本身是需要该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的环境污染或破坏,才能进行相应的刑法措施的开展。在该严重结果尚未明确之前,相关的立法部门应当积极采取其他形式的措施进行防治工作的展开。就我国当前的刑法规定来说,其对于危险犯已经初步进行了讨论。例如刑法中的三百三十九条的第一项规定中就这一点进行了明确,表明行为人只要违反了相关条例中关于非法进行境外固体处置的相关条例就视为已经犯罪,将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这表明我国的立法机构已经正式将危险犯行为或意图进行了法律层面的限制,但也仅仅限于该项犯罪中。在传统刑法观念中,危险犯罪直接归属于故意犯罪[4]。污染环境的危害性质是十分重大而广泛的,如果仅仅在犯罪追究过程中依靠该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来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就依旧是在传统过失犯罪观念下受到的发展制约。同时由于环境污染行为本身就存在较大的潜在性危害,并且危害结果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才能进行全面体现,例如日本发生的水俣病事件,就是在长时间下才体现出的危害性结果。虽然在科技发展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难以有效进行意外事件的避免,但是就传统刑法理念中关于过失犯罪的阐述并未将可能出现的该种情况进行纳入,将危险作为刑法责任确定的标准之一保证了相关刑法的威慑力提升,有助于刑法功效的全面体现。所以,从环境刑法对刑法理念造成的重大冲击效果的层面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其主要是将传统过失性犯罪中缺乏的危险状态的考虑进行明确补充,最大程度地促进现代刑法的价值实现,从提高威慑力以及加强刑事处罚等多方面实现了对污染环境犯罪现象的有效约束。
3环境刑法的相关保护客体
环境刑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这对传统刑法所存在的基本构造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冲击,导致架构争议性的出现。虽然现代化的环境刑法在犯罪构成和相关法律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和传统刑法之间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其在价值理念的层面上却与之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其在法律应用手段方面所存在的创新与变革。传统的刑法观念中主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对于其他生命形态或者生态系统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撑下是很难实现对传统刑法本质上的改革的。所以在进行环境刑法构建的过程中,仅仅就人本身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进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在实现刑法局限性突破的方面进行切实的创新与改变[5]。从环境刑法本身存在的多种保护客体来说,当前所存在的不足情况主要是由于其在制定上难以摆脱传统刑法模式的限制和约束。在传统的刑法规定中是没有就环境破坏进行严格的规定的,所以其惩治方式主要依靠传统的公共安全相关制度开展。但这些法律从实质上并不能对环境污染的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依靠传统的刑法理念进行环境犯罪治理难以切实的进行问题处理,同时还会进一步暴露相关的实际问题。所以,在进行相关保护客体的刑法确立时,相关部门应当切实考虑到对于环境利益的保护工作。该客体形式与传统刑法主要着眼与国家与社会的保护形式不同,其更加全面地囊括了其他生命体以及生态环境等多种要素。从建立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来说,其不仅仅是对环境行政法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将保护利益进一步扩展到人类所处的多种生态环境中,对所处其中的人类进行间接性的健康保证。在已经进行的刑法典的修订工作中,在进行相关保护客体明确时已经实现了较大的突破。但依旧没有深入刑法理念的本体部分,引起了多种针对于环境犯罪的相关侵害客体的深入讨论,观点不一[6]。除此之外,当前建立的环境资源保护制度也不能对该类犯罪行为中存在的多种客体特征进行完全阐述,没有进行本质性的探讨深入,仅仅停留在相关犯罪行为的表面社会关系探讨中。所以,也必须对此进行解决。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