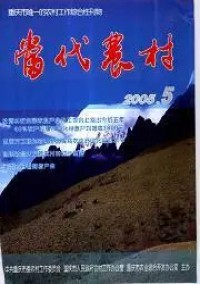农村政治缘自何方前路何

农村政治研究作为恢复和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其发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十多年中,它的生长和发展给当代中国政治学注入了一股充满生机的新鲜活力,影响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方向,丰富了它的特征。作为参与这一过程的一个实践者,我深切地感受到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清晰足迹,以及它在目前所面临着的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也都是与这一过程共始终,因此是我们这一代实践者所共同经历的。
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于历史学等学科积淀深厚,与农村社会和田野研究方法具有亲缘关系的学科相比较,作为一种自觉的学科努力,新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农村和田野的结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大胆地估计,也就是最近十五年的事,并且,作为一种着意开拓的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农村的结缘从开始来看,也并非始于一种学科主流的有意而为,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机缘所促成的一个“意外”的结果,这种“意外”反映了一种学科的集体被动与困境。
回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学刚刚恢复,就高扬民主和理性主义大旗,一路高歌猛进,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己任,一时间,其学科和社会影响力在新恢复的法学、社会学诸学科中处于领先位置,几乎可与经济学相比肩。这种显要是历史所赋予,并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以至后来者迄今也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那是一个政治学初生却激情澎湃的年代,也是政、学两界的一个蜜月时期,在那样一种百废待新,一切仿佛都需要重新认识和选择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学的基本取向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而根本无暇将处与这一结构底层和边缘地带的农村纳入自己的学科视野。
然而,历史的发展充满变数,中国政治学在九十年代便从充满启蒙理想的半空中回落到现实的地面,从那以后,历史再没有给初生的政治学提供如经济学和法学那样大展宏图的机会,甚至连它自身都在经历一个学科的重新定位,以在新的社会生态中寻找安生立命的位置。正是在这样一种急速转变之中,一些学者开始了并非起于自觉但最终却又高度自觉的学术重心下沉,暂时放弃对宏大问题的关怀,而致力于去追问促成无常历史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于是,农村成为他们进行这种试探性耕耘的一块处女地。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对回复到相对冷寂地带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学做一个整体上的评估,可以大体上归纳出两个新时代特征:一个是与国际学术相接轨的尝试。以这种取向为研究指归的学者在此一时期致力于学科乃至学术的重建,一些西方的重要学术思潮、学术范式、研究方法和学术概念,因其与转型期中国政治的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被引入,从而在外形和内核两个方面影响和再造冷寂之中的中国政治学术。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觉扬弃一贯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布道和注经式研究,从唯书为上转向实证和经验。正是在后一种取向中,对于中国农村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很快地取得引人注目的独特地位,并且因为种种国际和国内的原因而成为新时期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特例,获得了体制内的认可。结果,到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如果说在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中还能有所寄望,并受到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普遍关注的,就是这农村政治了。这一时期,作为政治学领域的跨问题公共领域,你不能不谈农村,不能不谈农村政治研究,不能不谈村民自治研究。中国政治学也因为有了村民自治研究这颗明珠,不仅重新获得体制性资源,不仅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各种资助,而且还几乎重新带动整个政治学科的重新崛起,乃至于有学者称中国政治研究在这个时候几近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上述状况无疑首先是由时代造就的,其次也是学者的努力和历史机缘相碰触的产物。明白了这两点,我们也就得以明白此一时期新生的农村政治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由宏观、高层向底层和中、微观的转向,由历史条件本身所促成,但研究对象的转变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研究者素有的研究情怀的转变,毋宁说,此一时期的农村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无能为力的宏大关怀的一种替代和移情。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替代与移情决定了其研究价值的定位,因此,此一时期的村民自治研究在实质上被看作是对更为宽广和复杂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试验和起点,因此,这种研究是村庄的,却又不是局限于村庄的,是关于中国农村的,但却更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地方。从正面影响看,具有宏大关怀的村民自治研究的影响很快就溢出村庄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乃至知识精英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公共性话语,从而带动了公共政策的变化,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于研究。而从其不足的方面看,由于其研究的价值关怀实质上在村庄之外,因此,过于强烈的宏大关怀实质上十分容易遮蔽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农村社会自身的认识,或者说使这种认识缺乏农村主位。其次,过于宏大的价值关怀与研究方法上的微观个案的联姻,在加速经验研究与学理研究结合的时候,也容易使来自于农村社会的“经验”成为论证某种先在理论政治正确性的材料,从而造成对“经验”本身的切割与拼装,违背田野研究的内在要求,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显现出个案与田野外貌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非个案和非田野的特质。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一时期的一些农村政治研究和村庄调查看似农村和村庄的,但在实际上却既是非农村也是非村庄的,看似田野的和个案的,但它在本质上却可能恰恰是非田野和非个案的,因为它的全部研究目的都在于自觉不自觉地去论证一种先在新政治理念的正确性,从而使其自身被打上了某种新的泛意识形态研究的色彩(不带贬义意义的)。
这种意在论证政治发展目的性的农村政治研究对于中国现实经验研究的最为直接的影响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其村庄研究的自然向上抬升性,二是其研究方向的水平横移性。我们注意到,这种农村政治研究在一头扎入村庄之后,尚未来得及深入,又很快地漂浮上来,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试行转为正式,村民自治正式成为我国农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构成之后,这种身在村庄,心怀中国的农村政治研究在村庄之内的使命实际上就宣告结束,继之而来的是高一个层级的乡镇政治研究。此时,各种各样关于乡镇体制改革的讨论继村民自治之后成为政治研究的新主流话语。但是,这一话语的出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乡(镇)–村关系遭遇到了远比其他诸如县–乡关系、县–市关系、省–市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更大的问题,不如说是怀抱宏大理想的农村政治研究本身具有向上提升和重新寻找研究对象的需要,是其价值情怀和政治发展路径设计的必然延续。与这种乡镇话语逐步取代村庄话语相关联的,是将村民自治研究横移向城市社区,力图在城市再造一个政治学研究的新的公共话语平台。然而,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与村庄社会毕竟相差太大,如果说“乡政村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框架,那么,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尚不充分的社区特征,则使这一努力很难成功。最终,受村民自治影响和启发而开始的城市社区研究归位于一种专业性的政治学术研究,并因此获得自己的存在空间。
然而,人们总是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无论实践者怀抱多么强烈的价值关怀,但只要面向实际,深入村庄,以某种先验理论预设为前提的农村政治研究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和转向。正是因为如此,农村政治研究也就相应出现了第三个特征:即面向农村,深入村庄,以研究和解决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实际需要为指归,以理解和阅读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特征本身为目的,力争发展出相对更“农村主位”而非绝对“国家主位”意义上的农村政治研究。这种学术取向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启发。例如,正是长期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驻村研究,使研究者体会到作为知识分子之公共话题的农村政治研究与实际改良农村政治社会状况的农村政治研究之间的区隔,体会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乡村关系改革研究与实际改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乡村关系改革研究之间的区隔,从而开始自觉地告别大话语下的乡村政治学,而开始致力于追求从乡村理解乡村,让农民自己说话,从对乡村的阅读和理解中提炼学理性知识,从乡村的政治运作实态与生态出发去思考改良农村治理体制的公共政策。同时,这一转型的出现也与此一时期农村政治研究对其他学科和研究方法及视角的吸纳有关,正是在这样一种从研究立场到研究方法的转变中,农村政治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联系的新趋势: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以描述和解释农村基层政治实态及其支配机制为研究旨趣的新取向。这种研究取向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入发掘、理解影响与支配中国乡村政治运行及其深层机制的“地方性知识”,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乡土的经验。并力图以这种经验来丰富和重构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像,最终为学理的操作提供一个真实的经验平台。这种研究看似立意不高,其实志向高远。因为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西学东渐过程,在促成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以自身所特有的视角再造和重组本土的经验,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创造新理论来源的本土经验,实际上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改造成为论证各种西学当然地具有先在政治正确性的“本土经验”,从而使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事实上也成为一个我们自以为熟悉,但在实际上却是需要花大力气去重新认识的“远去的他乡”,因此,只有重新地化“生”为“熟”,才谈得上重构理论。因此,这一尝试表现出强烈的人类学倾向,并在事实上是由政治学者自己,而不是经由人类学者的越俎代疱,开拓出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政治人类学路径。(2)以研究乡村政治及行政体制和结构为取向的研究,这种研究尽管尚未完全摆脱宏大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但它此时更为关注实际解决阻碍中国农村政治与社会发展一系列问题的努力却十分明显,它力图更加专业和技术化地去思考和解决乡村的结构问题,而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了去证明某种发展逻辑,近年来重新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种种尝试,虽不成熟,但却实际上是这种政策性研究的努力在社会运动层面的体现。(3)农村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这种研究以探讨政策绩效差异与地域和社区的关系为起点,最终落脚到着力理解转型期乡土社会的特性、原因及其走向,力图在连接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做出尝试。这种研究其实与第一类研究有接近之处,但他们之间却始终又存在明显的张力,这表现在这种研究的拟社会学特征和它始终执着地要在学理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中间地带建立明确而结构化的联接,并力图据此开拓出一个以问题带动学科的研究领域。(4)主要将乡村社会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政治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灵感来源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它更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关怀,学者们相信,作为超大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中国农村不仅是中国学术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灵感来源地,而且也必将为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做出贡献。由于其宽广的学术积累,这种研究已经越来越具有国际的视野和学术水准,而本土化的追求也成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向选择。
上述研究也同样激发出农村政治研究与其他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交叉与融合。例如,通过借鉴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不仅丰富了政治学者对于中国乡村政治的想象力,也丰富了他们的表达语汇,扩大了他们的研究视角,对政治的社会基础的重视,本身就促成了政治社会学的成熟。又如,通过借助于人类学,政治学者不仅学会了农村研究的主位关怀,更为重要的还掌握了一种新的研究文本的表达方式,而在这种文本表达方式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已经不仅是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重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直接影响甚至改变了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以及对学术本身的认识,一些学者正是通过拟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寻找和构筑起与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系。而通过借鉴历史学,也正在使当代乡村政治的研究也显示出更加纵深的学术视野。
但是,也正是这种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的转变,也给农村政治研究自身的发展提出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去思考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政治学的农村研究在方法论上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相关研究的学科界限。虽然说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自觉地界定学科分工及方法定位,却有助于学科自身地位的确定,并关系到学科的存在价值。如何处理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农村政治研究与同样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其他实证性政治研究的关系,实现研究成果的沟通与交流,不仅关系到农村政治研究自身的发展,同样也关系到整个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又如,如何处理经验性的农村研究与学理性的政治研究的关系,乃至于学理性的其他社会研究的关系,在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确立其自身的学科地位和研究价值,如何使立足于学理的研究与立足于政策的研究发生联系,而不是彼此隔膜甚至对立,等等,都是在这种研究的深入发展与转型之时所必须要思考的,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不仅关系到农村政治研究自身的发展,也同时关系到整个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成熟。当然,我也明白,这一切问题的逐步解决所要依靠的只能是众多学者长期艰苦的努力,而非又要去寻找一种更换了形式的新学术意识形态的倡导。
文档上传者
- 农村
- 农村离婚
- 农村讲话
- 农村讲话
- 农村选举
- 农村文化
- 农村改革及农村城镇化
- 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
- 农村土地信托
- 农村农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