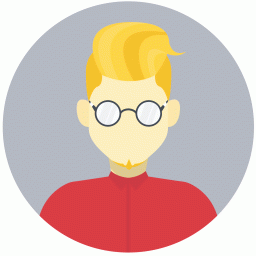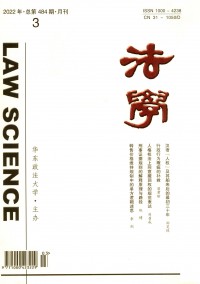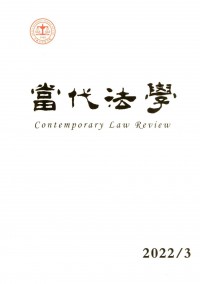法学观念

近日读梁治平先生所著《法辨》一书,颇多感触。书中收录了作者自1985年至1987年间写就和发表的大部分文章,该书最早出版于1992年,再版于2002年,作者在再版的《重印后记》中写道:“本书出版已经10年了,可以算作”旧籍“。旧籍新刊的主要理由是书久已售罄,却不曾完全退出阅读领域,而这又可能是因为书中讨论的问题并未全然过时,书中所表达的关切仍然能够触动现下读者的思绪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及以后的十余年中,是中国经济及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中国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也已写入宪法。这种变化不能不称之为巨大,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甚或法律观念又发生了多少变革呢?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提到“法”字,大多数人仍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强制、规范,而极少会想到公平、正义、制约国家权力等内容,此种意识即使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悲哀,这或许正是梁先生在《法辨》的重印后记中所发出的感叹吧。
在该书《法辨》一文中,梁治平先生剖析了中西方对“法”的不同理解及应用,中国古代“法”字的含义一是禁止,另一含义是命令。保证这种功能实现的手段则是刑罚。著名思想家严复对于中国传统法观念曾痛彻地指出,“若夫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①而西方法的基本含义则是权利、公平、正义,中西比较,法字的含义相去甚远,由此形成了迥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法即权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中国传统法文化认为法是一种统治者专政的工具,主要表现为刑,中国古代的历朝法典,无一不是刑罚。
在中国法律史上,法家以刑为核心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意识之中,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西方则认为法律乃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造成观念如此巨大的差异,自然有其社会基础,西方特有的制度在中世纪的城市中发展出了生机盎然的市民阶级,但是这种制度在中国不是根本没有,就是面目皆非。从深层次讲,对“法”概念的不同理解,正是划分“人治”与“法治”、封建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的集中表现。既然没有法律至上的信仰,而仅将法作为工具、刑罚,所产生的后果必然是对权力的崇拜,拥有了权力,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对他人进行专政,而无所谓公平、正义。梁治平先生在《说“治”》一文中对人治作出了尖锐批判:“专横的权力,暴虐的法律,以及因权力腐蚀而沉沦的人性,这些都是”人治“下最常见到的现象”。②由于对权力的崇拜,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与普通老百姓自然无平等可言,官吏享有种种特权,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表现一种身份、等级的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由于身份因素的介入,经济关系时常依据非经济的考虑来处理,纯粹的财产形式也很难出现。按照身份的法则,管理体制将人格化,官职乃至普通的职务都可以变成身份,转化为特权。在这种情形下,法律上的权利只是虚设,现实中的权力却成为礼拜的对象”。③人治导致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任意性,在“人治”状态下,个人内在的品行、修养可以决定政制的存亡。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有精辟的论述:“在上司就任时以及逢年过节都得送礼,上司的欢心影响他的命运,为了巴结上司,就得尽量送厚礼。个别官员的地位极不稳定,获得一官半职要花巨大的代价(学费、买官费、礼品费、”规定费用“),要背一身债,所以当了官就要在短暂的任职期内尽量地捞上一把,……当官就能赚钱是不言而喻的事,只有搜刮过甚才该指责”。④这些正是几千年专制体制下官吏的真实写照。表面看来,中国古代帝王尊为天子,俨然高不可攀,但越是如此,就越是虚弱,因为他不能不更多依据其臣属,以之为间接统治人民的工具。马克斯。韦伯在评价清政府统治时写道:“直到最近几十年,同外强签订条约,是地方长官而不是中央政府——它从来就没有过做这种事的机关,几乎所有真正重要的行政制度形式上都出自省的长官之手。……中央政府的条令常常被下级权力机关当做伦理示范的建议或愿望,很少当做符合皇权特点的成命”。⑤
中国几千年繁荣的封建社会造就了中国的古代文明,但同时也形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传统的顽固与强大可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势力强大的集中表现,中,“个人崇拜”、对知识分子的践踏都达到中国几千年历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将法视为“刑”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它左右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种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体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政府官僚法治意识淡薄,思想意识中毫无法律至上的观念,工作中唯上是从,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上面的意思,很少会想到是否符合法律,人民大众的意愿,更不会想到手中的权力是有限的,负有责任的。
反观西方,国家权力从来是受到制约的,沿着国家权力同其他外在的对应力量间形成的二元化道路行进的。对世俗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第一种是自然法观念的制约,自然法的地位从来都被看作是高于人定法的。第二种是监督教的制约,中世纪天主教会凌驾于世俗国家权力之上。第三种是代议制的制约,王权向市民阶级妥协的结果之一,就是等级代议制度的产生。这就决定西方的国家权力很难形成象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绝对一元化的地位。中国由于国家权力对社会组织、天地万物、时空的绝对权力,宗教在中国想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力量断无可能。马克斯。韦伯在评价中国农民起义时说:“城里人反抗官吏的起义时有发生,逼得他们逃入城堡。不过,起义的目的总是撤换某个具体的官儿,或是取消某项具体的规定,尤其是某项新的课税,从来不是争取一种哪怕是相对的、明文规定的、政治性的城市自由”。⑥自始没有自由的观念,没有须由法律来确立和保护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自由”、“平等”的基础,才会有契约关系,才会有市场经济,法律是最基本的调节模式,契约所代表的那种社会状态,也是现代社会一切法律存在的价值基础。西方传统上将法理解为公平、正义、权利,认为法律高于一切,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渡,而法就是公民制约国家权力的手段。在此理念之下就有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的名言,为克服人治的弊端,主张“以权力约束权力”。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应当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法治国家应当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应当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制度及程序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权和潜能、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程序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群体、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国家的一切权力根源于法律,而且要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和信仰等特殊情况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应与职务相连,而职位对一切人开放;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公民的权利、自由、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的法律秩序和充足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的侵害(不管是来自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合理、及时的补偿。
中国古代的法文化,由于没有横向交流,不可避免地固步自封,加上专制制度在法文化领域严格实行封闭保护的政策,使得中国传统法文化越来越变得保守,孤立排他,当17、18世纪西方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时,我们的国家依然是专制主义的国家,法治依然是完整的封建法治。细想之下,传播现代法治观念又岂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早在百余年前,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对社会所造成的束缚作用已逐渐为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所觉察,当时翻译了西方大量的政治,法律学术著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介绍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和法律制度已百余年,而对人们观念变化却收效甚微,正如梁治平先生在《法辨》一文所作的精辟论述:“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观念一旦形成,必将极大地作用于历史,即便在最初的条件已经消失、相应的制度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它也可能长久地存留下去,于无形之中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国家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表现在人们观念的现代化上,而非经济及其它表层的所谓现代化,改革中最根本、最持久的矛盾冲突必将发生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的领域,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远没有完成,现代化之路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转引自梁治平:《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②梁治平:《法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③梁治平:《法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7页。
④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1页。
⑤同上,第100-101页。
⑥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