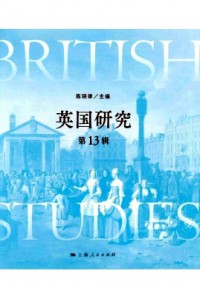英国独特气候给作家和读者带来的影响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英国独特气候给作家和读者带来的影响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个民族的文学的生发、发展和成熟与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历史条件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英国文学也不例外。在影响英国文学的众多因素中,气候条件往往容易受到忽视。实际上,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英国独特的气候条件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却又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英国人鲜明的民族性格,使英国文学逐渐形成区别于其他国别文学的相对稳定的总体特征。此外,气候还影响到英国文学的具体创作活动、阅读活动以及整个民族的文化生活。
一、民族性格与文学审美
众所周知,谈论天气是英国人见面时打招呼、寒暄的一种普遍方式。但事实上,英国人对天气的关心程度远不止此。2008年11月9日英国《电讯报》(TheTelegraph)刊登了一个关于英国人典型特点的调查结果:在所选出的五十个典型特点中,“谈论天气”名列首位。无独有偶,英国《每日邮报》(TheDailyMail)于2010年5月14日公布了LlyodTSB保险公司对两千名英国人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英国人一生中要花费六个月的时间谈论天气。英国人对天气话题的热爱胜过任何日常生活、工作或体育运动等话题。这种热情甚至已经蔓延至网络空间,仅Twitter网每日发表的与天气有关的微博文章就达五十万篇之多。英国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具有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特征,季节间的温度变化很小,雨量丰沛,特别是冬季时温带气旋更为活跃,雨天很多。潮湿的气候致使英国多雾,冬季经常飞雾迷漫,即使在天气晴朗的夏季,时常还有薄薄的烟霭。19世纪英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加重了英国的雾气,伦敦就曾经以“雾都”而闻名于世。阴雨天气导致的日照缺乏忧郁症SAD(SeasonalAffectiveDisorder),每年使五十万英国人深受其苦。此外,由于受到四季海风的影响,英国的天气异常多变。英国人常说:“国外有气候,在英国只有天气”,以此来表明这里天气的变化莫测。在一日之内,忽晴忽阴又忽雨的情况并不少见。多变的天气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经常的话题,还使英国人养成了爱抱怨天气的习惯,同时也让英国人变得格外谨慎。英国人出门随时都得带着雨伞和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某人被大家议论为“他连雨伞都不带”,就说明大家认为这人不够稳重、欠考虑。天气在这里并非只是气象学意义上的阴晴云雨温差湿度,它还关系着健康、教养、性格、习俗、文化甚至哲学。对天气话题的钟爱已经成为深入英国人骨子里的一个特点,也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对于英国人这样一个相对保守的民族来说,谈论天气是一种简单又缓和的开始谈话的方式,而且还存在一种被称为“赞同定律”的交流方式,即不管对方如何描述天气,听者都应表示赞同,这样双方才会觉得具有“共同点”,才能继续交谈下去。总之,英国独特的气候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英国人委婉、谨慎、忧郁、保守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在英国经典作家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例如,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如莎士比亚和斯宾塞等)大都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寻求启发。他们的作品风格比较婉约,常常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探讨哲学问题或进行道德教育。此外,多愁善感的性格也使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和劳伦斯•斯特恩等)成为18世纪风靡欧洲的感伤主义小说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他们的小说大多都以描写人物心理感受见长,书中的人物富于情感,常常对琐事之事感叹不止,读来有一种哀婉情调;同时,小说中对工业革命的笼统否定和对过去乡村风光的美化又反映出作家们保守的人生观。浪漫主义诗人们更是集中体现了英国人的典型性格。拜伦、雪莱、济慈等诗人无不是优雅的英伦绅士,歌颂自然、热爱自由,却又时常陷于悲观、孤独和苦闷之中。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英国文学的审美基调,也凝练出了英国古典文学中那忧郁哀怨、冷艳清绝之经典美的灵魂。苍茫的旷野,斜雨飘忽,天地一色;远树弥漫,曲径荒幽;荒野上的哥特城堡,昏暗而神秘;郊外的乡村农场,葱郁宁静却又生气勃勃。这正是经典的英国文学审美基调和背景。
二、气候差异与文学特征
气候条件不仅对人们性格、气质、情趣和追求产生影响,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文化本身的一部分,无疑也受到了气候环境的影响。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丹纳(Taine)在阐述他所发现的文学发展规律时指出,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要素或三种力量。其中环境是“外部压力”,主要指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这些条件的不同会造成人们不同的性格、气质、情趣和追求,并在文学艺术和文化创造上鲜明地体现出相应的不同特点来[1](P10-11)。在《艺术哲学》中,丹纳把“精神上的气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比作自然界的气候与植物的关系:“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了解异教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精神文明的产生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2](P42)显然,这里的气候已超越“自然界的气候”而指向“精神上的气候”。关于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法国19世纪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划分了欧洲南北文学并且将二者进行平行比较。斯达尔夫人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存在着,“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注:传说中三世纪苏格兰行吟诗人)为渊源,希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堪的那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3](P145)。她认为气候是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产生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英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形成了以下的特点:“忧郁、遐想、思想的强烈、对痛苦的深切感受、对自由的热爱、哲理倾向、对乡村和孤寂的爱、对妇女的尊重。”[3](P19)根据斯达尔夫人的考察,联系英国文学的实际状况,可以发现气候对英国文学的影响确实是明显的。第一,英国地处欧洲北方,气候寒冷,天气阴霾而暗淡,人们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因而他们忧郁伤感、喜爱沉思、富有想象力。这种忧郁气质带有民族精神的印记,同时也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本质。可以说,英国人的忧郁是与生俱来的民族气质,他们甚至以此为豪,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篇《忧郁颂》即是一个例证。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哈姆雷特的忧郁和痛苦,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英国式的忧郁和审慎。莎士比亚可谓是把哈姆雷特精神的痛苦和内心的冲突描绘得淋漓尽致,从而凸显出忧郁性格与人物命运的必然联系。与戏剧相比,英国的诗歌在表现英国人忧郁气质和内心强烈情感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18世纪中叶,以大自然和情感为主题的感伤主义诗歌风行一时。其特点是排斥理性,崇尚情感,强调对大自然和死亡意义的探索。“墓园诗派”代表人物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和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都集中体现了英国诗歌中普遍的阴郁色调;威廉•科林斯的《颂诗集》对自然美的敏感、忧郁感伤的情调都近似格雷;蒲柏的《埃洛莎致阿贝拉诗》将真挚的爱情描写得悱恻动人;爱德华•杨格的《夜思》则把死亡的感伤情绪与关于生死的神学讨论交织在一起描绘了诗人深刻而痛苦的思绪。这些作品大多都是通过对大自然景物的描写抒发孤独、哀怨、低沉的情绪,同时也表现出启蒙时代和谐理想的危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也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的确,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表达情感方面成就辉煌达到了难以逾越的高度,甚至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对忧伤与痛苦的描写还使英国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具有了严肃崇高的色彩,甚至描写戏谑场景时也摆脱不了忧郁色彩。这是一种独特而自然的戏谑,暗含着郁闷甚至忧伤的意味。“这种戏谑是英国气候和民族风尚的产物,在没有这样的气候和民族风尚的地方是模仿不来的。”[3](P174)在菲尔丁、斯威夫特、斯摩莱特特别是斯泰恩的作品中,这种戏谑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英国式幽默。加拿大心理学家罗德•马丁(RodA.Mar-tin)在《幽默心理学:综合研究》中对英国人的幽默作了专门研究,提出一种假设:幽默源于环境。他认为,英国变幻莫测的阴雨天气,密集的人口,明显的社会等级和各自为阵的社会阶层,都是自嘲内敛、尖锐刻薄的“冷面幽默”滋长的肥沃土壤[4](P254)。第二,根植于欧洲北方特定气候环境中的英国文学不仅激发了人们高尚的热情,还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正如斯达尔夫人所述,“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协调的诗歌”[3](P146)。英国诗人继承了以莪相为代表的苏格兰诗歌的风格,增加了自己的哲性思考,并且保留了喜爱海滨、喜爱风啸、喜爱灌木荒原的北方想象和厌倦命运的心灵对来世的想象。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到蒲柏的《人论》,再到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都提出了有关责任、知识和自由等人生的根本问题,也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然本质与社会中的伪善之间的对立。自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热衷于对生活进行哲学思索。爱丽丝•默多克的创作跨越文学和哲学,她的小说不仅展示了失去本质后人的挣扎与痛苦,也对现代西方人如何重新找到本质归属并结束精神流浪这一问题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哲性探索;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继承人》探讨了人性和道德,富于哲理;柯林•威尔逊的小说《必要的怀疑》《思想寄生虫》《哲学家的石头》通过文学的形式对人的潜能和意识等进行哲学思考。当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已成强弩之末时,在英国却方兴未艾,这一哲学倾向在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作品中得到了突出体现。诗歌方面则有叶芝、T.S.艾略特等。他们把现实、象征和玄思结合起来,大胆创新,引起人们理性的激动。相比之下,南方气候温和,使人耽乐少思,充分享受生活的安逸和舒服。明媚的阳光,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等生动活泼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学的南方文学。人们身心愉悦,兴趣广泛,生活安逸,但是耽于安逸的诗歌远不能和沉思默想和谐一致。所以,欧洲南方文学中体现出的思想的强烈程度和丰富性都逊于欧洲北方民族。第三,斯达尔夫人将欧洲北方民族和自己处身其间的欧洲南方作比较并且表明自己对北方文学的偏爱。她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北方诗歌与一个自由民族的精神更为相宜。虽然南方民族的文明程度较高、艺术样式较丰富,但理性的增长却导致对人性的压抑,由此产生的文学便受到诸多规矩的限制。她以南方文学公认的创始者雅典人为例,指出“对艺术的爱、气候的美”等所有赐予希腊人的享受可能比较容易使希腊人习惯于奴役;而对于北方民族来说,“土壤硗薄和天气阴沉而产生的心灵的某种自豪感以及生活乐趣的缺乏,使他们不能忍受奴役”[3](P147-148),自由独立就是他们首要的和唯一的幸福。这种精神在文学上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首先,英国文学的思想内容上所体现的自由精神,如具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民族诗史《贝奥武夫》、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都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针砭时弊的讽刺等鲜明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文学的政治讽刺传统,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享誉世界文坛且经久不衰。18世纪的《朱纽斯信札》中一系列不署名的抨击性政论文章是最为生动的讽刺作品之一,作者将讽刺手法运用至炉火纯青。18世纪英国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的《埃里汪奇游记》被认为是与《格列佛游记》齐名的一部经典讽刺作品。一直到20世纪的伊夫林•沃《一把尘土》和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作品中,针砭时弊的讽刺之风依然自由驰骋。正是其中所体现出的英国的自由气氛使这些作品读起来兴趣盎然。其次,这种自由精神还体现在文学的形式上。法国戏剧由于受到古典主义影响,其创作有很多严格的规则限制,从而能够达到恰当得体的效果。相比之下,英国戏剧创作更为自由。它超越了传统剧种风格,刻画英雄人物的同时也不隐瞒他们的缺点,使崇高与卑俗、悲壮与诙谐交相辉映。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把国王写成弑君篡位者,王后成了淫妇,王子变成了疯癫之人,但伏尔泰从古典主义兴趣出发,指责这个剧本粗俗野蛮,荒唐不堪,充满着时代的错误,尤其是在舞台上埋葬奥菲利娅的戏令人触目惊心[5](P177)。有趣的是,伏尔泰对《哈姆雷特》的这些评价恰恰反映了英国戏剧的自由之特点———美德与缺点、崇高与粗俗的并置。正是在这种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的戏谑性混合中,《哈姆雷特》实现了狂欢精神颠覆官方文化及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从而表现了莎士比亚“彻底的非教条主义”以及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进入20世纪,这种自由精神连同英国小说创作的能量在“现代主义”潮流中再度爆发,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乔伊斯、吴尔夫、康拉德、劳伦斯等文学巨擘在艺术技巧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试验,创造了一种能够传达“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6](P128)。
三、创作灵感与“感情误置”
如前所述,英国的气候条件造就了英国人忧郁伤感、自由独立、热爱哲思、想象力丰富的民族特点,为伟大作家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是一片文学的沃土,洋溢着整个民族对文学的热爱。英国作家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哲性思考,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究,赋予英国文学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也成就了英国文学的深刻、崇高和隽永。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的第十八章“天气”里指出:19世纪以前的小说对天气的关注不多,只有一些关于海上风暴的描写;而到了19世纪,小说家似乎开始关注起天气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自浪漫派诗歌和绘画开始产生了欣赏大自然的倾向,且这种倾向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对反映个性,对以下事实越来越有浓厚的兴趣:即人的感情既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感觉,同时也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7](P96)自然界直接投射于人的情感和认知,培养了英国人敏锐细腻的情感、审美的形象思维以及对自然景象和生活细节的观察能力。更重要的是,英国独特的气候条件或具体的气象事件为作家创作提供灵感来源;也可作为小说故事背景,对故事情节产生关键影响;还可以单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反映了人物的情感心境在自然现象上的投射,增强小说的感染力。关于作家从气候事件中汲取灵感的例子不胜枚举。1703年11月英吉利海峡生成的飓风袭击了英格兰南部海岸,摧毁了一万四千所民居,八千人丧生。普利蒂斯附近的灯塔被毁,十二艘战船沉没。丹尼尔•笛福正好目睹了这场灾难,他于次年发表了《暴风雨》,记录下他在那场暴风雨中的所见所闻。这次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后来的成名作《鲁宾逊漂流记》提供了素材和灵感。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这是自1500年以来最强烈的一次火山爆发,它引发了非同寻常的恶性后果———全球气候变化。这是因为火山爆发所产生的大量火山灰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烟云,进入大气层并滞留了两年之久。阳光穿透大气层的强度大幅减小而导致全球气温下降超过5华氏度(约2.8摄氏度)。在这年秋季,英国人常常能够看到持续时间很长的暗红色的黄昏和黎明。接下来的1816年天气更为恶劣,农民无法正常播种,导致欧洲和北美的农作物歉收,这一年又被称作“无夏之年”。此次极端不寻常的天气变化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的玛丽•雪莱的传世之作《弗兰肯斯坦》。1816年夏季,雪莱夫妇和拜伦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阴雨连绵,无法出门,于是他们阅读、讲述德国鬼怪故事并相约每人写一则。在丈夫的鼓励下,玛丽最终完成了小说《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出版。拜伦同样也从那个寒冷的夏季获得了灵感,写下了《黑暗》这首诗。“我做了一个梦,却不仅仅是梦境。光明的太阳熄灭了,星辰们也在无尽的天空中黯淡,昏暗、无路而又冰冻的大地盲目地摇摆在昏黑无月的空中;清晨来了又走———从未带来白昼,人们在对悲伤的恐惧中忘记了激情;他们的心全都僵冷成一个自私的祈求,祈求光明。”[8](P189)拜伦在诗中描绘了世界末日的景象,人类完全丧失了爱、怜悯和行动的勇气。整首诗弥漫着沮丧和忧伤的色调。直到1819年,这种恶劣天气才得以好转,农民也迎来了久违的丰收。约翰•济慈对此颇有感慨,这一年8月,他在给妹妹芳妮的信中写道:“我们有爽快的天气已经有两个月之久了,这是我最大的欣慰———不会把鼻子冻得红红的———不会冷得瑟瑟发抖……我最喜欢晴朗的天气,认为那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的赐福。”[9](P248-249)也正是在这一年济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秋颂》,赞美了秋天的美景和丰收的喜悦。而之后的1860年,乔治•艾略特由于从英格兰林肯郡盖恩斯伯勒的特伦特河水泛滥得到灵感,创作了她的第二篇长篇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故事的结尾是弗洛斯河泛滥成灾,玛琪独自驾船到被淹的磨坊去救汤姆,两人在危难中和解,但小船覆没,两人淹没在洪水之中。这让人联想的圣经里大洪水的故事,因而,洪水意象在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其次,气候状况在文学的结构和内容上可以起到实用性作用。莎士比亚的很多戏剧都是这方面的范例。这些作品都以暴风雨等恶劣天气为背景,甚至将其作为情节的一个重要环节。例如,在《暴风雨》中,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其弟安东尼奥篡夺爵位,和女儿米兰达公主被迫流亡到一座荒岛。十二年后的一天,普洛斯彼罗趁安东尼奥、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子乘船出游时,指挥岛上的精灵们唤起一场剧烈的狂风暴雨,让船上的人相继落水。安东尼奥等人在面临暴风雨即将给他们带来的死亡时幡然悔悟并得到了普洛斯彼罗的原谅。可见,暴风雨对故事发展和转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李尔王》中一个著名的场景就是“暴风雨”,它在结构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李尔被驱逐荒野,在暴风雨中发狂,既是前几场故事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以后一系列事情的起因之一。从内容上看,正是由于李尔身处旷野,遭受暴风雨的洗礼,他才有了对世间的新感悟:“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10](P145)可见,暴风雨是李尔王顿悟并走上救赎之路的开端,也是其转变思想观念的契机。最后,气候和天气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往往留有人的情感投射上去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主观性甚至虚假性。这也就是约翰•罗斯金所提出的“感情误置”。但戴维•洛奇认为,只要用得明智和谨慎,它不是一种暴露作者心理状态的方式,而是一种能产生特殊效果并使读者获得独特感受的修辞技巧,具有流畅和感染力强的效果,小说中缺少了这一项将会贫乏得多[7](P96)。简•奥斯丁在小说中擅长不着痕迹地运用“感情误置”这一技巧。她在爱玛的运气处于最低潮时,写道:“这一个黄昏是漫长的忧伤的。天气又尽量增添了阴郁气氛。”[11](P362)天气是人物眼中之景,打上人物的心理烙印,看似写天气,实则写人。因为爱玛发现了有关简•费尔凡克斯的事情的真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尴尬;她还意识到自己深深爱着奈特利先生,但已太迟,因为她有理由相信他要娶哈丽埃特为妻———所有这一切,使那一天成为她最倒霉的一天。狄更斯在《荒凉山庄》的首段中直接写道:“无情的十一月天气。满街泥泞,好像洪水刚从大地上退去……煤烟从烟囱顶上纷纷飘落,化作一阵黑色的毛毛雨……阴冷的下午再也阴冷不过了,浓雾再也浓不过了,泥泞的街道再也泥泞不过了。”[12](P4-5)狄更斯的想象颇富隐喻性:他把天气拟人化,谓之“无情”,用“浓雾”、“黑烟”和“泥潭”来暗指大法官法庭判案毫无定法、胡乱了事的作风。他把普通的19世纪伦敦阴雨天气的景象转化成启示录式的幻觉,让人仿佛看到英国都市沦落为原始沼泽地。同样,哈代的小说中的晴朗天气不多,“天上乌云笼罩,地上一片苍茫;时而狂风怒吼,时而聚雨如注,时而迷雾四塞”[13](P20)。天气描写为他所写的悲剧制造了荒凉粗犷、沉郁凝重的气氛。这些作家将“感情误置”这一技法运用得自然娴熟,反映了人物的情感心境在自然现象上的投射,起到了烘托人物、渲染气氛的作用。可见,用是否合乎逻辑性和准确性这条标准来衡量这种修辞手法的价值是不恰当的,正如不能用此标准来衡量隐喻一样。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英国的气候对文学读者群的培养和构成也具有重要影响。阴雨天气往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户外活动,尤其在电视电影尚未出现的时代,人们在雨天大多在室内活动,读书看报也就成了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阅读到达前所未有的盛况,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外,如前所述,英国人的气质和现实环境培养了整个民族对阅读和文学无比的热爱。在英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看来,阅读文学作品是人们重要的认知和审美活动,而阅读经典著作更是获取知识的最佳来源,因此,英国人非常乐于保持爱读书的传统。有调查显示,英国女性读书量明显高于男性,而女性的读书趣味会直接影响丈夫和孩子,极大地增加了读书传统承传的可能。成熟而庞大的读者群和普遍的文化活动又对英国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英国文学产业,包括出版、报纸、书籍、书评之发达恐怕也是因为天气太坏,人们只好在家读书看报消磨时间。事实上,英国是世界上艺术和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是对文字的擅长,不仅为世界贡献了大量的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而且每年为世界提供十万册新书,是所有英语国家的总和。就每年读者需要的印书种类,英国读者比德国读者多一倍,比法国读者多二倍,比美国读者多几乎七倍,比中国读者多二十倍。英国的读书活动贯穿全年,每年单是学校、图书馆、书店所举办的庆祝活动便已超过一千项。图书馆、书店、艺术馆之多超乎想象,仅图书馆全国就有五千多家。
四、结语
综合上所述,英国潮湿多雨、阴晴变幻的气候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英国人忧郁、谨慎、保守的民族性格;反映在文学中,逐渐形成了忧郁的遐想、强烈的情感、对痛苦的深切感受、思想的哲理倾向、对自由的热爱等总体特征;具体的气候事件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灵感,也丰富或优化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结构和技巧;英国的气候环境等条件也有利于读者群的培养,成熟而庞大的读者群和普遍的文化活动又对英国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里讨论气候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宣扬气候决定论,也非一味夸大气候对文学的绝对影响。事实上,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中,文学本体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外在的诸如自然条件、社会现实、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仅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跨越文学、文化、气象等学科,对可能影响英国文学的其中一方面的因素———气候进行探讨,旨在更为全面地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及其外部影响,同时也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次尝试。也许从气候这个易被忽视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文学一个别样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