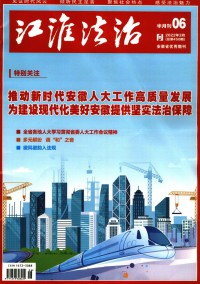法治方略对教育的启发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法治方略对教育的启发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良法的创制与合道德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构建
从动态的视角而言,法治建设是一个从法的创制到法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的创制是其逻辑起点。法治建设的形式要件首先是有法可依。没有全面而周密的法律体系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规范和保障,就难以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社会所期待的“应该”和“必须”,社会生活就难以实现稳定有序。因之,在法治进程中首先必须十分重视法的创制。自我党确立法治方略至今,我国已基本确立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正是这一系列法律的制定使得人们有法可依,从而为我国社会生活步入法治化轨道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作为实现法治国家首要环节的法之创制活动,还应进一步关注所创制的法的质量,即制定了何种性质的法律。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规定了法治必须具备的两个要件:一是全体公民守法,二是全体公民所遵守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81)按照现代法治理论,一部能够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最起码应表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和确认。这意味着就价值论的意义而言,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只有当公民认定其所面对的法律是良法、善法时,他们才可能守法,而如果他们所面对的法律在其价值评价中是劣法、恶法时,其行为表现就可能是避法、违法甚至抗法,从而法律之治、确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就不免陷入空谈。
法治必须以良法的创制为前提,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启迪。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不仅应关注其内容体系的构建,而且应进一步关注这种内容体系的合道德性。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出合道德性的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所主导的特殊教育形式,它必须引领受教育者在面对多种价值体系时进行正确的选择,也必须为受教育者设定应有的行为规范。而思想政治教育所昭示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之所以能担当引领受教育者的重任,不仅取决于其内在的合理性,更取决于其本身的合道德性。如果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对于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难以体现其积极的意义,那么它就难以满足社会对受教育者的价值期待,从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其提出的要求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实现。这具体体现为其所昭示的价值体系被信奉,其所设定的行为规范被遵行,而这又是以这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道德合理性为前提。如果一种价值体系在道德合理性上存在缺失,一种行为规范对人的规约缺少道德上的依据,它们就难以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同,从而也就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其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教育,必须得到受教育者的价值认同才可能内化为其内在的信念或信仰。而受教育者之所以在众多价值体系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昭示的价值体系,之所以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设定的行为规范的规制,是他们经过自身的思考和体悟后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的自觉认同,而这又离不开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道德合理性的认可。
二、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的要求与教育者价值信仰的确立
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立法阶段所创制的法律必须经过法的适用方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种法的有效适用又是以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为前提的。没有司法工作者对法律的忠诚,就不可能有法律的有效适用。而将忠于法律作为司法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由当代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决定的。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生活快速变化的时期。面对这种变化,法律本身固有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特点决定了其和人们变化中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的冲突。面对这种冲突,司法工作者是否应该坚守法律条文,这实质上是一个如何从更深层次理解司法活动之“应然”的问题。我们认为,司法自有它的一套程序,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即使法律不怎么完美,甚至有瑕疵,但在修改法律之前,司法工作者必须依法办案。马克思在论证“法院该是一种什么形象”时也指出,法官是没有上司的,如果一定要说法官有上司,法官的上司就是法律。这是对法院的独立性和司法本质的深刻表达,也启示我们应该对司法工作者提出这样的要求,即当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将要执行的某项法律已经滞后于时展的要求时,他也只能牺牲自己的法律感觉,以服从法律的权威命令。因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如果每一个司法工作者都忠实地执行法律,那么,法之精神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法律所欲求的秩序就能达成。相反,如若听任司法工作者在各自正义观念的支配下各行其是,那法律正义就永远无从实现,社会就会呈现出一派无法无天的景象,民众也会失去预期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安全感。所以,为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必须对司法工作者提出忠于法律的要求。
这种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的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在于,教育者必须确立并忠于与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一致的价值信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更为基础和更具前提意义,也是更具难度的可能就是教育者价值信仰的确立。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法律史家伯尔曼在谈到确立法律信仰对于实现法治的重要性时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P15-16)同样,教育者的价值信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也至为重要。其一,教育者价值信仰的确立对于受教育者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道德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极为重视榜样作用的国家。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道德首先表现为一种“政德”即领导道德。先人认为,当领导者具有了良好的德性和人格,就会对全社会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应该成为受教育者的榜样,这种榜样是无声的同时也是极为有效的教育。只有当教育者确立了坚定的信仰,受教育者信仰的确立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灌输,其有效性不仅诉诸于理性,而且更多地是诉诸于信仰。如果受教育者缺乏对教育内容的信仰,就不可能将其内化并进一步转换为外在的行为。而受教育者这种信仰的确立不仅要诉诸于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合道德性,也诉诸于教育者在信仰上的榜样作用。很难设想,在教育者自身都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体系缺乏信仰的情况下,会令受教育者对其产生坚定的信仰。其三,中国不利于信仰之花生长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确立信仰的必要性和难度,从而也决定了确立价值信仰的必要性。在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着眼的是现实的人事,其极为务实的取向从客观效应来说是不利于人们价值信仰确立的。并且,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作为一种和土地相交换而不是和社会相交换的经济形态,也养成了人们务实的取向,这同样是不利于信仰之花生长的。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尽完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等极易对社会生活产生负面效应,而这同样加大了确立信仰体系的难度。但是,不管有多大难度,教育者价值信仰的确立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积极面对的课题。因为,这不仅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也是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政治基础的内在要求。
三、法的权利本位与对受教育者利益的尊重
法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觉选择的治国方略,其最终意义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应有权利的实现,这也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之所在。例如,刑法对罪与非罪的规定以及对犯罪行为惩处的明文宣布,其要旨在于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生活和发展自身的良好环境,它体现的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对人的生命权、生活权和发展权的保护和确认;民法关于民事行为主体诚信原则的规定既是客观上对中国传统美德的一种强化,预示着立法者对诚信这一美好道德的向往,也是对民事行为主体应有权利的肯定;婚姻法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和惩处,其目的在于维护人们追求家庭美满幸福的权利。这启示我们,法律虽然更多地是以刚性的“必须”来规定人们行为的底线,但其中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对人的幸福特别是对人的应有权利的关怀等内涵却是极为丰富的。正是这种法律的内在底蕴,使得人们有可能对法律产生自觉的认同感,同时也促使我们应该以是否对广大人民群众权利的保障和确认、维护和发展的尺度去审视法律。法律就是对公民应有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法律运行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立法活动将这种应有权利规定为法定权利,再通过法的适用变为实有权利的过程。法之创制与适用的权利指向对于我们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依归颇有助益。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而言,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其重要的价值追求,因为这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全面进步。只有当受教育者确立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其观念和行为才可能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才可能满足社会的价值期待。同时,实现受教育者的价值和满足其利益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和内容都应体现出对受教育者利益诉求的认可、尊重和追求,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保证,也是其合道德性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教育者的“幸福之学”。这不仅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进步本身就蕴含了受教育者的个人利益,是受教育者实现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也因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获得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而受教育者这种正确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仅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且本身就是其最大利益之所在。在过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往往忽视受教育者的利益诉求,甚至对这种诉求予以否定,这突出表现在将个人的正当利益当成个人主义而大加挞伐。这不仅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令人生畏的活动,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实现存在缺憾,同时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性出现缺失。这要求我们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是要将受教育者的幸福和利益实现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受教育者的幸福和利益实现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其二,要确认受教育者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只要受教育者对个人利益追求的行为没有突破法律和道德的规制,其行为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对这种追求予以否定,而是应为其进行合道德性论证。当然,思想政治教育还有一个引领受教育者向更高层次迈进,即要求受教育者更多地关注他人和社会利益实现的问题。相信这种对受教育者利益诉求的关注,将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富人情味和价值合理性,从而也获得了实现自身的可能性。
四、公民积极守法与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自觉遵从
从最终的意义而言,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公民的有效遵守方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公民的守法状况关乎法治目标的实现。那么,法治社会的公民应该确立何种良好的守法道德呢?我们认为,对于公民而言,最为基本的守法道德是,不管他们对法律的理性认同程度如何,不管其在感情上是否接受法律,也不论他们具有怎样的社会身份,居于何种社会地位,行为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面对法律,他们只应有一种行为取向——遵守法律,行为“合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对守法主体往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守法行为对公民而言往往表现为道德上的他律。所以,对广大公民而言,还应进一步要求其将法律不是视为外在的强制,而是视为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理想的必要形式;将守法行为不是视作外在的他律,而是内在的自律,即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这不仅表明了公民守法层次的提升,而且直接关涉法律的实现程度。因为,“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3](P35)假如没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那就没有堪称法律义务的东西,服从法律就仅仅是暴力下的被迫服从而已。如然,法律即使在一定的时期内得以实现,也绝不可能长久地为人们所遵行。
一种社会的法律体系要得到有效实施,必须以人们头脑中自觉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感为前提。这种对公民从消极守法走向积极守法、从强制守法走向自觉守法的要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在于,应将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自觉遵从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其一,前已论及,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尽完善的阶段,其所固有的特点极易对社会生活产生负面效应。同时,市场经济充满着诱惑,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无疑是一种挑战,使得人们坚守信念、行为不逾道德和法律之矩的难度加大,这就必然要提出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要求自觉遵从的问题。其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也要求受教育者的自觉遵从。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制度予以合理性的辩护。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实证科学而是价值科学,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它必须统一人们的信念,必然需要维护某种“舆论一律”。“统一”以至某种“单一”是意识形态不可少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意识形态,也就必然要履行这种职能,它必然有不可移易的政治价值观。而这自然地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某种外在性,从而也就逻辑地要求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自觉遵从。其三,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而言,这种更多地诉诸于价值理念灌输的活动对受教育者而言具有一种外在性,甚至这种外在性有时还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特别是当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价值观念和思想政治教育所昭示的价值体系还存有差异,或者是受到自身阅历和生活经验的限制时,这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外在性甚至强制性往往就显得更为突出,这就自然地有一个要求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理性上予以认同、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努力进行感悟和体味,并在此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自觉遵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