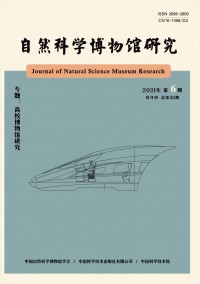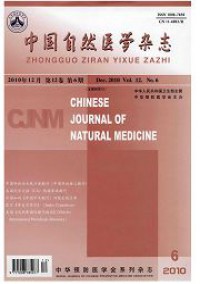自然科学与哲学原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自然科学与哲学原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自然科学与哲学原理范文第1篇
一、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中存在“重知识内容和结论,轻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重认知教学轻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的培养”的问题。新课程改革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就要求教学理念的转变。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结合学科教学特点,力争全方位地落实科学素养教育,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但是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教师追求教学设计新颖,但学生的学习方式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在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一些教师只是注重学生一堂课下来对教材基本观点的接受,对学生有创意的想法置之不理,甚至对于学生有胜过教师的独到见解也不予以鼓励。岂不知,这种教学恰恰把学生的学习引入了死胡同——为认同而学习,为标准答案而思考。这些看似正确、深刻、全面的标准答案,实际上限制了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
二、去除单一的教学模式,有效结合身边资源
政治理论是来自于对社会各种现实的包括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的抽象、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理论是落后于现实的。在政治教学中,可以运用的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是很多的,因此,搞好政治教学,应注意用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来讲解政治原理。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运用这方面的知识:
1.注重经济学的计算问题。现在的政治教材中,经济学内容较多地出现了计算的问题。如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是学习经济学所遇到的第一个计算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是比较容易的,可以运用对比、图表等形式,但学生理解起来仍然比较难,究其原因在于这个关系是比较抽象的。但如果政治老师能运用理科的相关知识,自己设计一道简单的数学或物理应用计算题,把这两者的关系容纳进去,然后以解题的形式来讲授,并于最后抽象出两者的关系,这样一来,原理清楚,并且又具有交叉性,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能达到一举三得的效果。
2.运用理工科知识来讲授哲学原理。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其实是来自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因此,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均可以从中采取大量的材料来讲授哲学原理。例如金刚石和石墨,可以用来归纳和抽象出“物质内部成份排列顺序不同会引起物质的质变”的原理。等等。特别是这些科目中的每一道应用计算题,都可以抽象出辩证法的有关原理。例如,在理科的解题方法上,我们知道每类题型均有自己的解题思路,即具有一定的解题模式,但具体到每道题中,又各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讲解应用计算题的过程抽象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等等原理。因此,只要政治老师善于和勤于探索,特别是在当前大综合科考试这种模式的条件下,如能广泛联系理科类知识进行教学,政治科地位的复兴是大有希望的。
三、教学方式、方法的转变
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理念不转变,方式、方法转变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基础;方式、方法不转变,理念转变就失去了归宿、失去了落脚点。传统的政治课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教师滔滔不绝地讲满四十五分钟,不留给学生充分的主动学习和消化的时间,这种教学方式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从而失去了学习政治的兴趣。
因此,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必须改革政治课教学方式和方法。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第一,教法和学法的开放性。
教学中,要实施教学方法的开放和学习方法的开放,尽量放手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自己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按之去进行探究活动,最终了解一些知识、学会一些技能。比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鼓励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谈自己于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让大家一起讨论研究问题之所在,并从课本中寻找解决的办法。例如,在经济生活中我们的学生会遇到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问题,甚至于会涉及到外汇的“卖入价”和“卖出价”的问题,这在高一政治新教材中就能帮助学生找到答案。
第二,从教材的利用者到课堂教学的设计者。
自然科学与哲学原理范文第2篇
一、将“理论联系实际”重新赋予新的内涵:
1、政治老师要具体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知识,研究学生的心理、生理等方面的特点;改变自己,使自己的教学方法更符合学生的实际。
2、政治老师应积极主动地研究现实,收集相应的各类数据、各类与政治理论有关的信息,并积极主动地运用于教学上去。也就是说教学内容要符合实际。如果政治老师只是按课本内容传授给学生,那这门课肯定上不好的。因为政治的内容相对于其他科目来说是比较容易看懂的。因此,这就要求教师主动去研究现实,并自己运用相应的知识分析现实现象。如在讲授商品的属性时,首先要分清楚的是哪些是商品、哪些是物品和劳动产品。对于政治老师来说,从理论上讲清楚是没有问题的,但学生是否明白就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必须结合实际,调动学生的兴趣,从而积极的投入到学习中。
3、注重社会调查,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理解所学的知识,从而巩固知识,学会运用知识来分析现实现象。社会调查是了解现实、实证理论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作为传授理论的政治老师,不仅需要自己作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同时也要带领学生深入社会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了解现实,在调查中理解和实证理论的真实性,从而激发学生学政治的热情。
二、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高考中以其基础性、能力性、整合性、实践性的强力冲击波,全方位介入中学教育,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考试方式本身,而在于对中学素质教育推动和导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注重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教师立足创新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为此,教学中我们改革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探索“主体、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教学不仅是老师的知识讲解,更多的是让学生自己主动地去探索;课堂上教师经常向学生提供时政新素材、新观点,激发学生丰富想象,增强解决问题的变通能力;引导学生敢于质疑、善于质疑,并鼓励学生敢于突破陈规,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培养学生的思维独创性;恰当使用“术语”,规范答题要求,提高学生思维的深刻性、精密性;强化学科内在联系的同时,培养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发散性和聚合性思维能力,使学生掌握更新颖、更准确、更系统的相关学科知识。
三、注重政治教学与理科知识的结合,注重运用理科知识来讲授政治,是政治教学法改革的新的生长点。
政治理论是来自于对社会各种现实的包括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的抽象、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理论是落后于现实的。在政治教学中,可以运用的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是很多的,因此,搞好政治教学,应注意用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来讲解政治原理,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运用这方面的知识:
1、注重经济学的计算问题。现在高中的政治教材中的经济学内容,较多地出现了计算的问题。如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是学习经济学所遇到的第一个计算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是比较容易的,可以运用对比、图表等形式,但学生理解起来仍然比较难。究其原因是在于这个关系来说,是比较抽象的。但如果政治老师能运用理科的相关的知识,自己设计一道简单的数学或物理应用计算题,把这两者的关系容纳进去,然后以解题的形式来讲授,并于最后抽象出两者的关系,这样一来,原理清楚,并且又具有交叉性,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能达到一举三得的效果。
自然科学与哲学原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哲学原理 化学教学 学生
新课程改革中,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列为化学课程的三维目标,以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在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寻找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用化学知识和方法认识世界,并结合化学提供的丰富素材,使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科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化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是学习哲学的资源;反之,哲学又是学习化学的工具。若教师在化学教学过程中能很好地挖掘出教材中的哲学素材,理解这些哲学原理,不仅有利于学生辩证地看待自然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化学知识和解决化学问题。
一、利用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思想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肤浅到深刻的发展过程。比如,科学家对原子结构的认识:道尔顿首先提出了“原子实心球”模型;汤姆生发现电子,提出“枣糕模型”;卢瑟福发现原子核,提出“带核原子结构”模型;再到了近代,玻尔引入量子论,薛定鄂揭示了波粒二象性规律,科学家对原子结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接近客观事实。
在教学中,我们也应该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化学学习中的问题。比如,在初中的学习中,一般都认为,燃烧必须有氧气参加,而二氧化碳是不支持燃烧的。到了高中,学生知道到氢气可以在氯气中燃烧,镁可以在二氧化碳中燃烧,从而掌握了广义燃烧的概念。显然,燃烧的概念被发展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概念和原理往往有它们自己的适用范围,而科学的发展、认识的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应以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发展的眼光来学习化学。
二、利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
许多化学事实中同时存在多种矛盾。例如,某种溶液当中可能存在多种平衡,在判断溶液的酸碱性就要抓住主要的平衡。NaHCO3溶液中既存在着HCO3-的电离平衡、H2O的电离平衡还存在HCO3-的水解平衡,这里HCO3-的水解平衡是主要的,所以溶液呈碱性。而NaHSO3溶液中也存在着HSO3-的电离平衡、H2O的电离平衡和HSO3-的水解平衡,这里HSO3-的电离平衡是主要的,所以溶液呈酸性。
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决定事物发展过程的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运用这一观点掌握从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去认识、理解问题。如浓醋酸在稀释过程中,溶液导电能力先逐渐增强后又逐渐减弱,分析这一现象时,只要抓住溶液导电能力主要取决于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大小,影响醋酸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因素有电离程度的增大和溶液体积的增大这一对矛盾,开始稀释时,电离程度的增大是影响醋酸溶液导电能力的主要矛盾,而后来溶液体积的增大转变成影响醋酸溶液导电能力的主要矛盾。
三、利用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
如化学的氧化还原反应,氧化剂的得电子和还原剂的失电子、氧化剂的化合价降低和还原剂的化合价升高、氧化剂的被还原和还原剂的被氧化,这些过程,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没有还原剂的失电子就没有氧化剂的得电子,氧化剂是被还原剂还原,还原剂是被氧化剂氧化,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两个反应既是对立的,又是同时存在的。两者是相互依存、同时存在,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又如,离子键中的静电吸引和排斥;化学平衡中的正反应和逆反应,都属于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矛盾。
四、利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在解决化学问题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在选择灭火方法时,应根据着火物体的性质。着火物质的性质不同,扑灭火灾的方法也就不同。一般的火灾可以用水或泡沫灭火器去扑灭;油、苯、酒精等易燃物质着了火,就必须用黄沙、泥土去扑灭;而金属钠、钾着火,水、二氧化碳、泡沫灭火器和干粉灭火器都不能用,否则不但不能灭火,还会“火上浇油”助长火势。又如,氯化钠溶于水形成溶液,溶于酒精就形成胶体。这些事实都告诉学生,学习化学不能死记硬背,一成不变,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问题的本质,利用化学原理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五、利用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原理
我们在讨论物质的溶解性时,一般根据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分为易溶、可溶、微溶、难溶,这个划分也只是相对的,世上并没有绝对不溶的物质。在化学反应中,有一个规律是叫“可溶的物质可以制取难溶的物质”,“较强酸制较弱酸”,如果我们以相对的眼光来看,就是“溶解度较大的物质可以制取溶解度较小的物质”“酸性较强的物质可以制取酸性较弱的物质”。这就有助于学生理解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讲到侯德榜制碱法时的一个反应:NH4HCO3+NaCl=NaHCO3+NH4Cl,用常规的思路就不能理解为什么NaHCO3会以沉淀的形式析出,因为NaHCO3是易溶于水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两者相对的溶解度,就不难理解:NaHCO3的溶解度比NH4HCO3和NaCl都要小得多,在饱和的NaCl溶液中易达到过饱和而以沉淀的形式析出。又如,实验室中可以用酸性较强的醋酸来制取酸性较弱的碳酸(H2O+CO2),用碳酸(H2O+CO2)可以来制取更弱的HClO。
另外,在讨论化学键时有离子键和共价键之分,如果我们以相对的眼光来看,实质上两者也没有严格的界线。比如,我们可以把离子键看成是共价键的极性趋向于无穷大之后形成的。而事实上,往往许多化学键并不是纯粹的离子键或共价键,而是两者同时都有。我们说某个化学键是离子键还是共价键,主要是看哪种键为主。
六、利用量变引起质变的原理
在学习元素周期律时,讲到随着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从1个递增到7个再到8个,元素从金属变到非金属再到惰性气体,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的例子。其他的例子也很多:硫酸的浓度从稀到浓,其表现出的性质就很不一样;氯化铝和氢氧化钠反应,随着氢氧化钠的量增加,产物会从氢氧化铝变成偏铝酸钠。
化学是学习哲学的资源,用化学学哲学,充分发掘化学知识中的哲学资源,促使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认识论。用哲学学化学,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知识,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与哲学原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教学改革;实践
高校开设哲学原理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理论素养及运用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高校哲学教学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哲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采取纯科学知识传授的态度对待该学科的教学,使本来具有思辨与超越性的哲学变成了枯燥与乏味的识记性学科。把哲学教学等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授、知识教育,使哲学失去了对学生的吸引力。第二,考核方式仍然是应试教育。以标准化的试卷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判断哲学学得好坏只靠分数来衡量,这与哲学的本性是想背离的。第三,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滞后。在教学上主要采取教师讲、学生记的“填鸭式”教学方法。教师因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束缚,很难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第四,只讲权威性,忽视丰富发展、忽视理论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在哲学的长河中,曾经产生过许多精彩绝伦的哲学,其中也包括哲学。但却绝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要改革哲学的教学,必须把权威与丰富发展统一起来。第四,哲学教师自身理论素质较差。为适应新的任务和要求,为了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长流水”,教师需要不断地研究、探索、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提高自身素质。第五,教学研究方面,重视教法研究、教材研究与理论研究,忽视对社会实际,尤其是高校学生思想实际的研究,导致理论研究与教学实际相脱节,教学与学生思想实际相脱节,因而教学缺乏针对性、实效性,缺乏吸引力,在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对哲学课教学改革的探索
为进一步搞好这门课的课程建设,更好发挥其功能,针对提高哲学教学质量问题对相关的重要环节进行了研究。
(一)将时代精神融入哲学教学内容中去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以抽象的形式反映着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哲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反映出哲学的这一特点,即把时代精神融合到抽象的哲学理论中去,以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哲学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被学生自觉地接受。可以说,我国高校的哲学课的教学之所以在一定范围内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脱离了社会实践以及其中所表现的时代精神,以至成为枯燥的理论教条,使学生厌烦。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抓好以下环节:首先要讲好理论,即讲清哲学的基本概念、命题和原理,准确完整地揭示出他们的主要内涵;其次根据理论内容联系实际,要使实例和原理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分析透彻,两者不能脱节、不能牵强附会;所举实例必须典型、生动、有趣并富有深刻哲理,要广泛联系自然、社会、思维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实际,尤其要联系学生学习、生活、思想、专业和就业等方面的实际。讲授中力求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用实例充分论证理论,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二是通过典型事例讲授,使学生学会善于用理论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与实践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归并,也不是贴标签式地套用,必须认真寻找理论与实际之间适当的结合点或实质上的联系。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是间接的联系,现实中的具体现象只有经过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与哲学理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哲学理论在说明现实问题以及为现实问题寻求哲学依据时,必须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否则,就会陷入牵强附会的机械比附,使人产生反感情绪,降低哲学的威信。
(二)教学中要进行大胆的创新
我们在哲学教学改革中,在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1)更新教学观念。哲学原理的教学中知识教育与能力培养是相辅相成的。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的基础,培养学生哲学方面的能力包括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学会哲学思考,并能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人生和社会现实,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善于用科学的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要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又必须以学生掌握理解哲学原理的基本知识为前提,脱离知识教育的能力培养是空洞无益的,脱离能力培养的知识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革新教学内容。讲好理论,并根据理论联系实际,把抽象深奥的哲学原理变为通俗易懂的道理,使哲学贴近生活。(3)改革教学方法。采用新的综合创新的教学法,尽力使抽象的语言文字用形、声、色结合的方法,使事物变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生动,富于感染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兴趣盎然的情境中学习。让理论充满生机活力,使课堂教学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逐渐使学生不仅愿意接受哲学理论,而且信奉、实践、运用这些理论。(4)在教学中,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哲学故事,教师将古今中外的哲学故事引入课堂,同时也将哲学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分析当前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转贴于
(三)积极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积极探索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等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与生动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去检验所学的基本理论。让学生利用假期进行调研,了解社会,关心社会,把握社会的热点问题,并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社会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加强对哲学教学的科研工作
进一步加强对哲学教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加强任课教师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并用这些科研成果支撑教学。教师用自己深刻理解和掌握了的理论去讲课,说服学生、打动学生,真正实现科学理论进学生头脑的目的。教学不仅要讲清楚基本理论观点,而且要对一些重大问题做出说明和评述,在说明和评述问题中阐述理论。教师应了解学生的热点难点问题,并且认真加以梳理和研究,从而使哲学教学受到学生的欢迎。
(五)建设体现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优秀的校园文化与高校哲学教学之间关系密切,相得益彰。而优秀的校园文化为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创造了积极的文化氛围,要建设体现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吸引力强的学术、科技、教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哲学教学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这对于提高哲学教学效果具有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六)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各种年龄段的学生都喜欢看电视,看幻灯,听录音,听广播,只要运用幻灯片、光盘、录像带等多媒体上课,学生顿时会精神倍增、兴趣盎然,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如果教师这时抓住了学生想看到本节课教师将要给他们展示什么情境的迫切心理,不失时机运用多媒体开篇或导入新课,或制造悬念等就会激发学生更加浓厚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事实证明,运用多媒体开篇,教学效果尤佳。多媒体是哲学教学的好帮手,能使课堂内容化静为动,化虚为实,直观形象地揭示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思维能力,以实现哲学课堂教学的最优化。为此,我们采用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改造、提升传统的教学手段。
《哲学原理》课程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在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真正起到了核心课程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忠言.关于《哲学原理》课教学改革的探索[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11).
自然科学与哲学原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原理;教学改革;教学实效性
根据中宜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整合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设置方案将从2006级新生开始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全面实施。其中,哲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合并为原理;两门独立的课程融合为一门课程,总学时有较大幅度缩减,这就要求教师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在有限的课时内,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师生互动实现教与学的良性循环。
总结哲学原理课教学的得失,对于原理课教学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近年来各高校哲学原理教学的总体情况看,影响本课程教学效果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二是理论教育与实践脱节;三是考试形式缺乏科学性。2003年10月至2004年12月,“增强哲学原理课教学实效性的几个关键问题”[1]课题组进行的问卷调查证实了上述问题的存在。本文针对以上问题,结合此次调查,从教学方法的改革、实践环节的强化、考试形式的改革三个方面,提出增强马克恩主义原理课教学实效性的三条思路。
一、由灌输式教学向疏导式教学转变
“我讲你听”、“我说你记”、“我灌你通”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它缺乏教育本身应有的“亲近感”、“认同感”,使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的教育主体,这就直接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同时,灌输式教学法限制了学生的积极思维,使学生习惯于获得老师给出的现成答案,久而久之形成思维的盲从与懒惰。
在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形势下,中西思想文化不断撞击,大学生的思想日趋活跃,新的认识问题不断产生。他们对简单生硬的灌输式教学法很反感,而希望与老师进行朋友式的交谈,共同探讨他们关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实效性调查中,选择“师生互动”上课方式的学生占2496,低于选择“课外实践”上课方式的学生比例34%。实现师生互动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够正确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疏导式教学法的核心。疏导就是对学生“点”、“启”、“引”,即指点迷津、启之醒悟、引出误区,做到“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2]。也就是引导学生积极思维,就同一问题给出多种观点供学生分析、参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答案。同时,要引导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并解决有关现实问题。教学要相通,理论要润心,才能激起受教育者的心灵呼唤,启开学生的心扉。因此,原理课应采用疏导式教学法,改变灌输式的僵化教学模式,这样才能增强教与学的互动性,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是实现疏导式教学的必然要求。教育的实效性离不开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充分了解。不了解学生承受教育的能力,不了解学生对知识的需求,理论教育就是对牛弹琴。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斑斯基说:“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了解学生,不会综合规划教养、教育和发展的任务,抓不住教学内容中的要点和重点,不善于选择教学方法、手段和形式的合理配合方案,那么,教学过程永远不会有成效。”[3]了解始于沟通,只有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及学习需求,才能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
然而,在“实效性”调查中,学生对“你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最不乐观的。对此问题,34%的学生回答“一般”,表明有1/3的学生对此问题不关心,也隐含着他们没有得到过老师的“关照”。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十分了解”的仅占被调查学生的9%,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比较了解”的占19%,两项之和为28%,大体相当于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不太了解”的比例——27%。而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很不了解”的学生达11%。可见,学生总体上认为“马哲”老师是不了解学生的。
近几年来,由于扩大招生,许多高校学生人数急增,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上采用大课堂授课。调查显示,100人以上的课堂占近50%,有的学校均是150人以上的大课堂。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在课堂人数偏多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实现教与学的充分交流,已成为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可回避的问题。部分高校在尝试进行研讨式教学,已初见成效。此外,设立教学信息联络员,召开教学座谈会,利用课间、课余走向学生,了解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定期答疑等均不失为师生沟通的好形式。
二、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实践环节
哲学原理理论性强、内容较抽象,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共性。多年来,一般采用课堂讲授形式,造成了理论教育与实践的脱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在原理新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做到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实践环节。
在“实效性调查”中,学生对“你最喜欢的上课方式”的回答结果如下:选择“课外实践”上课方式的学生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师生互动;再次是讲座、自行研究并提交论文、小组讨论。这几部分学生所占比例分别是34%、24%、16%、14%、12%。这个结果对原理课乃至所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广义的实践环节包括学生实地参观、社会调研、收看影像资料及主题讨论等形式,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形式。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求教师在课堂讲授中尽可能结合热点问题,以实例加以阐述;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实践中了解社会,深化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并提高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有条件的院校可建立几个相对固定的实践基地,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参观、考察,让学生从实践中感受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体会原理的时代性与实践价值。同时,针对不同的章节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如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有条件的院校可组织学生参观当地自然科学博物馆,观看录像《意识的萌芽》或电影《宇宙与人》等,通过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在唯物辩证法这一部分,可就“坚持唯物论,反对伪科学”进行课堂讨论,并组织参观有关科普展览,还可与学校宣传部门联合,举办相关内容的橱窗、板报宣传等活动。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的重要作用”、“知识经济与当代大学生”等课题,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同时,就社会调查的亲身经历,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实践论和认识论部分,可组织学生观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录像,围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自由与责任的关系”等论题开展课堂讨论或辩论。
理论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可使深涩的理论趣味化,并使学生学以致用。这对于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全面推进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三、采用科学的考试形式
一般来说,大学课程考试具有两个功能:测评功能和激励功能。原理课考试既要成为测评学生掌握基本原理以及运用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的手段,也要成为检测教师教学成效的重要途径。通过阶段性考试,学生可以发现自己学习中的薄弱方面,并通过考试成绩与奖学金、三好生、优秀班干部等评选挂钩,激励自己努力学习。教师可以通过考试宋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发现教学中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工作。因此,采用科学、合理的考试形式,是增强原理课教学实效性的必要手段。
在“实效性调查”中,关于“你的‘马哲,课的考试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40.2%的学生回答的是闭卷考试,38.7%的学生回答的是开卷考试,12.6%的学生回答的是提交论文,根据讨论给分的占1.1%,其他形式为1.6%,未回答者占5.8%。可见,多数院校采取的是闭卷或开卷考试形式。对“你认为”马哲,课考试的形式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结果是:赞成以“提交论文”作为考试形式的学生比例最高,占被调查学生人数的42.8%;其次是开卷考试,占25.3%;选择“根据讨论给分’的比例为16.4%;选择闭卷考试的仅占3.4%;其他及未作回答的各占6%。
写论文的考试形式虽然是学生的首选,但是从一些高校的实际情况看,从网上下载、学生之间相互抄袭、凑字应付的现象大有人在。同时,以此作为考评学生的唯一依据,并不能有效地促使学生认真听课学习。开卷考试往往造成学生“临时抱佛脚”的懒惰行为。闭卷考试大多侧重于对学生知识记忆的考查,因此平时不听课、考前突击背记的现象普遍存在。“实效性调查”表明,有54.9%的学生认为存在此现象!有的学生很少上课,通过考前突击复习,期末成绩反倒比平时认真听课的同学好。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另外一些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影响他们上“马哲”课或其他政治理论课的态度,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对自己认真听课的态度产生过怀疑。因此,完全采用提交论文、开卷或闭卷的考试形式都不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单一的其他考试形式也各自存在弊端,在此不一一评述。
原理是综合性的素质教育课程,考试形式应体现综合性评价原则,应将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考核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堂小测验。每学期可安排两至三次随堂测验,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督促学生自觉学习。第二,实地参观、撰写报告,根据报告质量进行等级评定。第三,课堂讨论。师生共拟论题,学生以斑级为讨论小组,或自行组队,由学生自己主持,并由学生代表组成评委,评定优、良、一般三个等级。这种方式既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又能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因而是平时考核的重要方式和成绩评定依据。期末考试除了常用的闭卷、开卷形式外,还可采用闭、开结合形式,以及知识竞赛形式,竞赛成绩优秀的学生可免考。总之,考试应成为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其不得不加以应付的负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恿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7,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