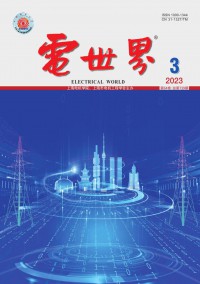世界船王

世界船王范文第1篇
1414年,长颈鹿这种神奇的动物第一次出现在大明王朝的皇宫,它的娇美让人们称奇不已,诗人为其献上诗作。这头长颈鹿是郑和带回来的。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为沿途国家带去大量礼品,也带回来了很多贡品,长颈鹿就是其中之一。沿途的部落,被郑和舰队的规模惊呆了,船队背后的王朝,真是强大而仁慈,首领们纷纷表示愿意向明朝纳贡,大家做朋友,真好。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有250艘船,运载了二万八千人。这是真正的舰队,中央的宝船长440英尺,有多层甲板和9根桅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就像今天的航空母舰一样。船队除了水手外,还有各种服务人员、翻译,甚至史官――相当于现在的随船记者,他们要沿途记下中外友好交往的故事。
这种航行,很好地展示了大明王朝的软实力,但注定不能持久,因为每次航行,差不多要耗费整个朝廷年财政收入的一半。郑和死于第七次下西洋途中,从此之后,明朝就没再出现这样的航行了,甚至一度销毁航海记录,禁止民间造两根桅杆以上的船只。大明王朝的统治者对海洋和世界本身并没有兴趣,他们的航海其实是一种自恋的表达。
长颈鹿出现在中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415年,葡萄牙人发动了对北非城市休达的战争,年轻的亨利王子指挥了战斗。在休达,葡萄牙人发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财富,其中有来自印度的香料。排行第三的亨利,对遥远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建立航海学校,研究造船技术,改进来自于遥远中国的指南针,并且派出船队对远方进行探索。
他隐居在远离首都里斯本的海边一个村庄里,远离政治,也远离喧嚣,陪同他一起的有很多著名的制图师和工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里应该算是航海史中的世界中心。精确的地图、航海课程的传授、全新的造船技术,一个个令人振奋的发明从这里走向世界。他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王子”之一,对王位没有任何兴趣,但是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不可估量。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既身在高位,又对抽象的W术感兴趣的人。通常情况下,皇帝的大儿子会被立为太子,皇帝的弟弟叫王爷――其实是相当敏感的身份,往往被皇帝哥哥提防。如果专注于钻研科学技术,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之举,但是非常可惜,中国的王爷们在这方面乏善可陈。
世界船王范文第2篇
海贼王势力分布:
1、海贼王势力主要分位四个海域,分别被四个强大海贼团所控制着,这四个海贼船长被世人称作四皇;新世界东面的统治者是BIG MAM海贼团船长毕格·纳姆;新世界南面的统治者是红发海贼团的船长香克斯;新世界西面的白胡子海贼团船长爱德华·纽盖特;新世界北面的统治者是机械海贼团船长凯多;
2、政府为控制这些海贼帝王,把新世界的中心部设立五个支部分别对应着海贼四皇,对应比格纳姆的是东方的G5支部、对应红发香克斯的是南方的G3支部、对应白胡子海贼团的是西方的G2支部、对应凯多的是北方的G4支部,四个支部的中心设立一个G1总部来控制这四个支部;
3、海军本部,主要是元帅战国和大将黄猿赤犬 青、稚、中将 。
(来源:文章屋网 )
世界船王范文第3篇
王船山在著述中多次使用“天才”这一术语,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将西方“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审验两位大师的“天才”观,具有鲜明的共相性和差异性。共同性在于强调天才的直觉能力和崇高内美的品格,而且天才之作具有自然之特质。差异性在于王船山“天才”观强调天巧或神技,富有灵心的“天才”能够领悟天地神理,在诗境中呈现“天人合一”的妙合意旨。王国维“天才”观推崇绽出的存在性向,“天才”心灵对此在生存予以观照,呈现出“忧”“畏”“罪性担荷”等价值维度。王船山“天才”观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场域的内质元素,王国维“天才”观则凸显了西方存在主义场域的价值符码。
关键词:王船山;王国维;天才观;天人合一;存在主义
学界关于王船山和王国维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多,但是对两位大师“天才”观的研究尚付阙如。“天才”观是两位大师诗学中极其重要的美学范畴,是管窥其美学思想差异性的重要窗口。我以为廓清王船山和王国维有关“天才”的价值定位,不仅有助于把握王船山文艺思想对于王国维美学理论的深度影响,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够厘清其诗学追求的共相性和承续性。当然,由于时代语境、个人经历、生命体验和思想资源的不同,王国维和王船山的“天才”观又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如果能够客观地辨析两位大师“天才”观的异质性,就能够弄清楚王国维“境界”说与王船山“意境”论内在性向到底有何不同。由此足见,论述王船山与王国维“天才”观的异同,不仅能够理清两位大师文艺美学观的脉络关系,而且对于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殊异性内涵也有启示意义。接下来,我们首先论析其“天才”观的内在相通性。
一、相通性
王船山和王国维作为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极具份量的人物,其美学观存在着共相因素。特别是有关“天才”内质性向考量上,他们都强调“天才”具有深湛的觉知能力及崇高内美的人格精神。王船山在著述中明确使用“天才”这一术语达十多次。比如“屡兴不厌,天才欲比文园之赋心”①“行路难诸篇,一以天才天韵吹宕而成,独唱千秋,更无和者”②。在具体诗作的评价上,王船山关注“天才”的审美感兴能力。他认为:“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③王船山言及的审美感兴能力,实际上是一种深湛的生命体验。王船山用“适目当心”“寓目警醒”“触目生心”来描述“天才”的异慧能力。在他看来,“天才”皆“才授自天”,涵摄灵心将古今巨细入其兴会,道尽天理物情,从而呈现天地之妙,坦露自我的怀抱气序。“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余生一尽万重悲,谁望含饴未死时”“从知生死一浮沤,大誓宏深不易酬”,从船山先生的诗性语句中,也能够管窥他对真正“天才”的价值定位。王船山指出:大凡“天才”式诗人能够了悟宇宙人生的真谛,“生亦不可期,死亦不可悲”“大彻悟后,自不留一丝蹭蹬,只此是正法眼藏”,从而“心悬天上,忧满人间”。深湛的觉知能力和醒觉视野让“天才”实现了对生命价值和精神意义的超越。船山先生有言:“抑夫生人之役,荣凋欢恶,咸有二三,唯一而不两者,死而已。”④死与生、生与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天才”的穿透力和洞察力也体现在此。船山先生推崇“天才”的深湛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兴能力,和王国维的“天才”观是一脉相承的。王国维认为:“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唯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⑤他肯定《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正在于曹雪芹笔下人物具有超越时代的人类性特质。王国维指出:“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⑥所谓“特别之境遇”“特别之眼”,兼指存在的本源性感受,诸如有死性迫压,对人类存在的悲剧性感受等等。诗人用无量的“天眼”洞穿了人类孤独境遇,从而具有了至高视域和认知境界。王国维认为:“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尤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⑦由此看来,船山先生和王国维都看重“天才”诗人的醒觉维度和精神视野,而“天才”式的精神痛苦大抵源于忧患与苦厄的生命体验。
其次,王船山和王国维皆推崇“天才”的高尚人格和澡雪精神,皆认为自然是天才佳作的首要特质。王国维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的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⑧夏中义总结了王国维“天才观”由三个环节的有机构成:“从‘内美’与‘修能’,到‘入乎其内’与‘出于其外’,到‘独能洞见’与‘独有千古’。”⑨我以为上述分析是恳切的,指出了“天才”所具有的精神特质。王国维认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⑩此四人的人格魅力彪炳青史,自足千古。换言之,真正的“天才”具有火热的“赤子”情怀,拥有一贯本真自我的无畏愿心,拒绝任何外物异化的质朴之心。王国维指出:“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盖人生至七年后,知识之机关即脑之质与量已达完全之域,而生殖之机关尚未发达,故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一言以蔽之曰:彼之知力盛于意志而已。即彼之知力之作用,远过于意志之所需要而已。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B11佛雏认为:“一般地讲,把‘天才’诗人比作‘赤子’,这当然只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比拟。当年马克斯恩格斯曾嘲笑过德国斯蒂那之流企图把‘儿童立即变成力求洞察事物底蕴的形而上学者’,仿佛儿童心爱‘事物的本性’更甚于他的玩具。这种批评,无论对叔本华还是王国维,也当然都适用。‘阅世愈浅’,势必愈削弱艺术的丰富的现实内容,从而导致艺术的主体、艺术境界的狭隘化和贫困化,其不足为训亦甚明显。但王氏意之所重,在于那个‘性情愈真’,在于从儿童身上我们复活了我们自己。从这点来看,王氏的‘赤子之心’说,实隐伏着某种跟封建思想桎梏相对立的个性的‘自由’,艺术的‘自由’。”B12“天才”的人格魅力源于自由精神,其崇高人格的坚守必然以超越性向作为价值支撑。 王船山同油瞥纭疤觳拧钡哪诿廊烁窈统越精神。他认为“深思远情,正在素心者”。唯有“素心者”方能心无挂碍,超越物役俗尚,具有涵神澡魄的高贵襟次。也唯有“素心者”涵摄审美能力,才可能吟魂诗心:“全无正写,亦非旁写,但用吟魂罩定一时风物情理,自为取舍。古今人所以有诗者,藉此而已。”B13王船山认为大凡“天才”之作具有天成风韵的特质。所谓“天成风韵”,是源于诗人的一颗灵心,这种灵妙的艺术特质和王国维所言及的“自然”具有一致性。王国维多次以“自然”来称誉天才的创作。《人间词话》中,王国维高度评价纳兰容若的词作,真切地道出其词作有境界的缘由:“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之风,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B14除了纳兰容若之外,王国维对李后主之词也推崇备至。夏中义认为:“个性至深,人性始呈。这便是李煜‘天才’之所在。而要达此大境,亟需两种性情之真:天真与纯真。不懂世事而真曰‘天真’,透视人生而真曰‘纯真’。天真因其稚嫩而凋零,纯真因其磨砺而永恒,故能深谙人生何为贵。诚然,就其审美性而言,天真与纯真根子归一:皆离世务俗趣甚远,未被功利虚名所沾,故皆如出水芙蓉,一尘不染。――王国维对此看得甚准,故对两者皆冠以‘天才’。”B15这些概括是准确而富有学理的,指出了“天才”作品之精义乃自然。总而言之,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到王船山和王国维在“天才”观上的共相特质,接下来我们再具体分析两位大师“天才”观的差异性。
二、差异性
王船山和王国维毕竟生活在不同年代,其精神资源和审美取向有别,故在“天才”的美学旨归上存在差异性。王船山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特别是对于儒道释文化本质的领悟与参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王船山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天才”观同样打上了中国古典文化精粹的价值烙印。
王船山“天才”观的哲学基石则是气一元论。他提出:“观者,天之神道也,不言不动而自妙其化者也。……天以刚健为道,垂法象于上,而深存乎其中。四时之运行,寒暴风雷霜雪,皆阴气所感之化,自顺行而不忒。圣人法此,以此设教……而天下服矣。”B16王船山作为文化大师,他深谙“天”的至真蕴含与道德牵引力。从价值溯源来看,《周易・观・彖》提出:“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孔颖达《周易正义》疏:“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刘勰《文心雕龙》有言:“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王船山的“神理”观与上述言说是一脉相承的。“天才”能蛭诺馈爸撂臁保并且将自我与至真之天达到契合同一:“无以知天,于事物知之尔。知事物者心也。心者,性之灵天之则也。”正因如此,他对“天授”或“神授”尤为看重,比如:“神韵所不待论。三句三意,不须承转,一比一赋,脱然自致,绝不入文士映带。岂亦非天授也哉!”B17“才授自天,岂可强哉!”B18“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殆天授,非人力。”B19王船山认为,天才贵在揭示神理。神理内含着神化之理或传神之理,重在突出心神与神理的和合关系,是诗心对道的领悟与传达。诗歌中一旦神理共契,则体天地成人道,大气独昌,见化工而恰得自然。
王船山认为:“天地之生,莫贵于人矣;人之生也,莫贵于神矣。神者何也?天之所致美者也。百物之精,文章之色,休嘉之气,两者之美也。函美以生,天地之美藏焉。天致美于百物而为精,致美于人而为神,一而已矣。”B20王船山作为《易》学专家,信奉神化之理应验于灵心,遂衍生出礼乐等人文现象。神或“一物”乃世界本体,所谓体天成而成人道,更多强调的是个体精神对宇宙之“道”的认同与“依附”。所谓“致美于人而为神”,指出了个体生命对宇宙神理的认同,则是获取审美自由的根本途径。他提出:“神则合物我于一原,达死生于一致,s合德……神,故不行而至。至清而通,神之效也。盖耳目止于闻见,惟心之神彻于六合,周于百世”B21“神则内周贯于五官,外泛应于万物,不可见闻之理无不烛焉,天以神施,地以形应,道如是也。……明乎此,则穷神合天之学得其要矣。”B22真正的“天才”可“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能够体悟不可见闻之理,将神理与物象统摄其中,神动天流,使心之神与物之理有机契合,从而达到“形神合一”“穷神合天”的致高旨趣。
换言之,王船山关注“天才”的诗歌维度,其聚焦点和最终旨归都指向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至境,而含蓄美则是推崇备至的美学性向。王船山“天才”观强调天巧或神技,富有灵心的“天才”能够领悟天地神理的同时,在诗境中呈现“温柔敦厚”的妙合意旨。王船山认为,真正的“天才”具有即景会心、即目成吟的“灵心”禀赋:“天壤之景物、作者之心目如是,灵心巧手,磕着即凑,岂复烦其踌躇哉?天地之妙,合而成化者,亦可分而成用;合不忌分,分不碍合也。”B23“大音稀声,其来久矣”,王船山倡导在审美感兴中追求“中和”的法度美,提出“合化无迹者谓之灵,通远得意者谓之灵”B24,真正的“天才”诗作示之意象,能够使人感而契之、思而咀之,所谓诗之大致莫过于此。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北大知名学者张世英先生认为:“王夫之提出的‘彻于六合,周于百世’‘廓然于天地万物大始之理’,这简直是对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的绝妙描写。”B25如果说王船山的“天才”观是中学场域的美学义理使然,那么王国维的“天才”观则明显受到西学精神的影响。
王国维身处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他在20世纪初将“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其内质结构与嵌入状态打上了鲜明的西学烙印。西方的“天才观”诞生于两希文化的背景下,最终形成于近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天才”能够对“整一性”予以观照,内含有对存在本体的统摄,对崇高事物本质的直觉透观。“天才”的心相潜质不依赖大脑的理与逻辑推理,客体本质将在主体去蔽状态下得到揭示。古希伯来文化强调个体与罪性的互涉关系,生存个体愈感到存在罪性,也愈具有天才的症候。天才往往是上帝的“选民”,意味着聆听圣言启示,走上自我救赎的“荣耀”之路。西方现代的“天才”观念则由康德确立。康德认为,自然通过天才为艺术立法。他认为“天才是一个主体自然禀赋的一种自由地运用他的认识诸能力的典范性的原创力”B26。他将事物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后,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解放。康德认为“天才”的特质是通过质料和形式构建起一个审美世界:“诗人冒险将超感性之物的理性观念感性化,如极乐世界、地狱、不朽、创世等;同样也在超经验的领域将经验中的事物直观表现出来, 如死亡、嫉妒、各种罪恶、爱、荣耀等,赋予它们超自然的完美,他凭借的是为了达到无限而与理性的优势竞赛的想象力。正是在诗歌艺术中,审美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它的机能。无疑,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机能实际上只是一种(想象力的)才能。”B27由此可见,康德推崇“天才”的艺术想象力,能够触及事物的本质和核心。越具有想象力的作品越深奥、玄幻、神秘,并与艺术家的道德情感相互作用。席勒的“天才观”基本上来自于康德。席勒指出“天才”是“一种性格,它感情炽热地拥抱一个理想,逃避现实,以力争达到一个虚无的无限境界。它到身外去不断地寻觅着它在自身内部不断地破坏着的东西。对它来说,惟有梦境才是真实,而现实体验不过是束缚。它最终直视其自身的存在为一种束缚,而且也撤除了它、冲破了它,以达到真正的现实”B28。“天才”所具有的活力原则,激活了创作素材,从而产生了真正的美。席勒的“天才观”蕴含着主体的归真返璞,审美静观则是其独具的禀赋。谢林的“天才观”则深刻地影响了叔本华和尼采。由于叔本华、尼采对王国维“天才”观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简单谈谈谢林的“天才”观。
谢林以研究先验唯心论而驰名,其后期哲学发生了转向。他致力于研究黑暗意识,探讨本原中那些非理性的精神力量,诸如“黑夜般的”深渊意识、直观的洞察力、自然的深度等等。谢林认为:“所有的诞生都是脱离黑暗,临近光明,从非理性的黑暗中才成长出闪光的思想。”B29“到底有什么东西能比那深沉黑夜的意识更强烈地驱动人们竭尽全力地追求光明。”B30他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强烈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的艺术家,才能观察仔细入微,深邃地体验到何谓世界的真实。同时,谢林哲学对存在根据中非理性要素的重视,引起了叔本华和尼采两位哲学家的高度关注。谢林指出:“一个动物不可能是‘恶毒的’,即使我们有时用这些术语来表达。实际上,属于恶毒的是精神。……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能翻转那构成其本质的元素,能翻转其存在的接缝和裂缝。……恶的根据因此存在于第一基础的原意志的表现之中。”B31谢林谈到的“裂隙”是指强劲的精神触角导致了大地“崩裂”,生存主体陷入形而上无家可归的境地。自我精神在这种内在困厄之中“燃烧”、放逐,“涌向天空”,返归本己。毫无疑问的是,谢林关于精神之“恶”的相关论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后来德国唯意志论哲学的兴起。
叔本华和尼采被王国维誉为十九世纪德国哲学界的两大伟人。唯意志论哲学的心相本质源于谢林所言的“深渊意识”或“为恶的精神”,这是理解叔本华和尼采有关“天才”的核心价值观。叔本华认为:“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原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付可怜相,而油然兴起悲哀之念。”B32故“天才”处于“裂隙”的撕裂中,“恶”的精神在回撤中被铭刻了下来。其本己的罪责承担滋养了精神性的火焰,一种本源性的体验被显示了出来。故“天才”处处揭示天命,揭橥人类生存的终极困境,描摹超越时空的人类性情感。“天才式”的痛苦指涉普遍感知的人性,是人类“原初悲哀”的摹绘者。王国维首次将西方的“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推崇“本真存在”的现象学描摹,重视通达时间本源的精神坦露,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性向。存在主义性向是超越历史学、社会学的价值范畴,是对自我生存的植根性追问。“天才”通过其独特“现存状态”的彰显,呈露出“忧”“畏”“本真自我”“罪性与自由”等精神镜像,这显然和王船山“天才”观崇尚“天人合一”的审美取向有着本质性的差异。肖鹰认为:“以王国维的诗人观为中心,探讨‘天才观’在引入中国诗学后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是一个深化现代文学革命研究的重要课题。”B33回望百年中国学术界,对王国维“天才”观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其“天才”观所涵摄的思想元素,对于阐释并理解王国维的“境界”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提出:“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B34天才之不幸与“蚩蚩之民”不同,源于对生命本体痛苦的天眼洞见。“天才”大多具有原初性感受并扎根于存在深处,都有其第一性的直觉。他们被生存的“罪过”所迫压,其精神元素中呈现出烦、不安、恐惧、忧、有死性的焦虑,这些都是本体论问题,而不是心理学问题。王国维认为,“天才”重在对真理的追求:“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或以记号表之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B35凡“天才”者,皆是追求真理之士,其存在领会源始地在真理之中。由于其本己的展开状态乃是生存真理,它的本质存在就是“真的”。海德格尔把这种在“真理”中展开的最本己状态叫“此在”。我认为这个概念传神贴切,能很好地概括王维“天才观”的实质。进而言之:“天才”是“此在”的展开状态,而“此在”在“真理”中。有学者指出:“王国维不仅首先把‘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而且在他的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诗人观建构中,呈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诗学文化的深刻复杂的交融活动。”B36我以为探讨王国维“天才观”,必然要和“境界”说联系起来。因为“境界”说毕竟是王国维美学成就的高峰。
王国维“境界”说的内质构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概念的构成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既具有传统美学的元素,也涵摄超越本土美学的价值性向。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高度重视“精神痛苦”的诗性显露。王国维认为精神苦痛之大小和天才性具之大小成比例关系。“天才”的苦痛来源于有死性迫压所造成的内在紧张。“天才”遭遇了存在有死性和无根性,其精神呈现出“裂隙”之苦与“被抛”状态。故“天才”触及文化生活领域的“大事件”,它是一种“向死”之思:“‘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忘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B37“忧”使得此在生存具有了当下性。对于追求“真实”存在的“天才”而言,“忧郁”“操心”“焦虑”,这些情绪具有本体性维度。王国维认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也。”B38王国维谈到南唐后主李煜之词时,用了‘担荷人类罪恶’,包括叶嘉莹在内的许多学者均认为乃‘不伦之喻’,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王国维的“天才”观和“境界”说紧密相连,如果完全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法度来衡量“境界”说,显然是无法把握其殊异性特质。王国维肯定李煜之词有“境界”,其词境的本真性流露,不仅反映了诗人的精神受难,而且揭橥人类存在的偶然性、历史性与时间性。李煜之词内含“缺欠”意识,是对生存无根性的无名恐惧。李煜之词彰显的“境界”也正和其“畏”之情感显露相关。天才之“畏”表明“此在”终有一日将完结并随之消逝。常人皆逃避“畏”,而“本真性的此在”则勇敢地面对有限性和必死性的绝对界限,遭遇本己的“向死存在”。“天才”以“忧”“烦”“痛苦”“畏”等本己性的内在结构,确定了具有源始意义的存在维度,其“境界”也就由此而彰显了出来。佛雏认为:“王氏‘赤子之心’说,颇受‘西学’浸染,它跟诗人及其创作挣脱封建束缚而获得某种‘独立’与‘自由’断断不能分开。”B39我以为,“天才”所具有的“本真性独立”,与“封建束缚”关涉不大,与“天地束缚”联系紧密。“天才”能担荷本己罪责,在存在论立场避免日常性的沉沦,在有死性的终点把握他自身的总体和意义。由此看来,“天才”体验到一种原初“罪过”,召唤其进行本真选择,并承担了他个人与人类的命运。王国维所言之“天才”,实乃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良知呼喊,这种操心与呼唤提供了本体生存的现象结构。“天才”对此在生存予以观照,诗学性向中呈露出“忧”“畏”“罪性与自由”等价值维度,这种绽出的“不和谐”是和王船山倡导的“高级天人合一”明显不同的。
三、余论
综上所述,两位大师在“天才”观上的具有共相性,都强调天才的创造性直觉和内美的崇高品格。不同之处在于王船山“天才”观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强调天巧或神技的同时,认为“天才”诗境当采纳“用晦”之道,唯有“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方能达到艺术至境。王国维“天才”观确立了全新的自由维度,超越对“天”的依附,坦露出“本真”的独立性向。如果说王船山“天才”观彰显出中国传统美学场域的内质元素,那么王国维“天才”观则凸显了西方存在主义场域的价值符码。王国维“天才观”内蕴的本真存在与自由精神,表面看与中国现代诗学转型的主旨具有一致性,实际上是超越时代架构的存在论命题。
【 注 释 】
①②B13B17B18B19B23B2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494、534、1449、483、738、503、733、1054页。
③B21B2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479、92、60页。
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24页。
⑤⑥⑧⑩B11B14B34B35王国维著,林文达选编:《王国维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3、24、24、15、44、156、118页。
⑦B37B38王国维著,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15、105、98页。
⑨B15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北京大W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3页。
B12B39佛雏著:《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307页。
B1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00页。
B2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三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513页。
B25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5页。
B26B27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9页。
B28席勒:《席勒文集・理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B29B30B31谢林:《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8、73、142页。
B32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9页。
世界船王范文第4篇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发现的前提条件是其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其思想的大力提倡,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居功甚伟,但真正揭示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谭、梁船山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紧密相联,从而使船山研究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品格。
关键词: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谭嗣同;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14-04
晚清,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由于湘军系人士的大力提倡,王船山之名传遍大江南北,船山学亦成一时之显学,但是,王夫之思想的现代价值并不是立时显现,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其中,谭嗣同、梁启超的船山研究对其思想现代价值的开掘起了关键作用。
一
中国由1840年鸦片战争而进入近代社会,但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里并未有太大变化,因而此时人们对王船山思想价值的揭示主要还是在其传统意义一面。众所周知,王船山思想研究之风的兴起,与曾国藩刻印出版《船山遗书》有关。曾国藩为何要刻印《船山遗书》呢?学术界有许多不同意见。章太炎最早提出了“悔过”,然后自己觉得不妥,又提出“攘夷说”[1],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尽管《船山遗书》刊刻的政治寓意有争议,但都肯定其对于王船山学术思想传播的意义。许冠山在《船山学术思想生命年谱》中说:“盖以当时正值湘军初复金陵,曾氏兄弟权倾一时,此书一出,天下书院,学署与书香世家,莫不争相购备。” [2]另有论者说:“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在客观上固然发扬了船山的民族精神,主观上恐怕未必没有借此发泄私怨的用意。” [3]
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与他对王夫之思想价值的认识密切相关。曾国藩欲调和汉宋,实际上是尊宋,所以也强调王船山“专宗洛、闽”,深悟“尽性知命之旨”,其功用在“弥世乱”。[4]这就是曾国落所揭示的王夫之思想之价值。无独有偶,郭嵩焘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5] 极力主张王夫之从祀文庙。
如果说曾国藩面对内乱而以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平定之,但是随着外侮日甚一日,传统的理论和方法都显得不堪一击。所以,思变的思潮风起,起先是办洋务,随后就有所谓变法维新的运动的发生。在这一时期,谭嗣同、梁启超对王夫之思想之现代价值的开掘尤引人注意。
二
对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来说,谭嗣同在其中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他自己深喜船山思想,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船山思想以及其他思想理论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二是通过自己的宣传、影响使船山思想得到更广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影响。
谭嗣同何时在何地开始读王船山的著作,现在很难作出明确的回答。因其时曾刻《船山遗书》已出,谭家为湖南有名的士绅之家,家中藏有《船山遗书》是情理中事,由此推知谭嗣同有可能比较早接触《船山遗书》。《三十自纪》谓嗣同于同治四年春二月己卯生于京师,光绪元年春随任北通州,犹往京师。三年冬归湖南,取道天津至烟台、上海等地,……十五年春、夏两至京师,十九年夏又赴京师。据欧阳予倩《上欧阳瓣薑师书序》,谭嗣同十岁就师从欧阳瓣薑。[6] 这个时间与谭嗣同自述光绪三年归湖南的经历有一点出入,相隔两年。从《报刘淞芙书》来看,似乎他是在至京师后才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的。所称的“蔚庐”是指同县的刘艮生,即刘人熙,善琴。[7] 谭嗣同游踪甚广,也大量阅读了当时翻译的西方书籍,吸收了西方思想,因而常从王夫之的言论中寻找出一些与西方学术思想相合之处。如他在《仁学》中说:“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独不见夫雷乎?虚空洞杳,都无一物,忽有云雨相值,则合两电,两则有正负,正负则有异有同,异则相攻,同则相取,……王船山邃于《易》,于有雷之卦,说必加精,明而益微。……” [8] 从政治思想方面寻找共同点,可能是谭嗣同更热衷做的事情,所以他认为王船山先生是兴民权的,而黄宗羲、顾炎武皆不及。不仅如此,谭氏还从远古君民关系的演变,而明示君主立宪是中国古以有之,王船山等先贤也有此意。[9]在寻找和重新诠释中,王夫之思想之现代价值即重视科学与民主的观念被发掘并加以放大,使其进入现代思想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是谭嗣同船山研究的突出贡献之一。
与谭嗣同相较,通过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的王船山研究意义一方面体现在从学术史上揭示王夫之的地位,对王夫之思想意义在学理上进行阐述;另一方面,梁启超又以其在学术界的强大影响而确定王夫之思想和王夫之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谭嗣同、梁启超的王夫之思想研究有其个人因素,亦有着社会因素的推动,正是两人的合力将王夫之思想研究予以光大。正如前所论,谭嗣同是湖南人,其父与湘军系左宗棠也有联系,其师又深喜船山学说,所以谭嗣同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与传播自然显示其个人的特点。谭嗣同在三十岁以前比较保守,三十岁以后有所变化,尤其是“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盛言大同,运动尤烈”。崇拜王船山,谭嗣同前后期都是一样的,但在后期因受梁启超的影响,显然有了新的认识和阐述。梁启超也承认自己“受夏、谭影响亦巨”[10]。 正因为这样,谭嗣同的对王船山思想的崇拜也影响了梁启超和其他维新党人。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将船山思想的影响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1] 梁启超、谭嗣同二人是朋友,而且还是倡导变法维新的同志,谭嗣同临死前将自己的书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保存整理,而梁启超也未辜负谭嗣同的嘱托,致力于谭嗣同的学说、船山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还要强调的是王夫之思想研究因应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才有可能突显王夫之思想的现代价值。
谭嗣同所处的时代为“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与船山所处的时代有相同之处,因此,他对船山学术思想的学习和利用与时事紧密相联。如他说:“然今之世变,视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徵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若徒著立说,搬弄昌平阙里之大门面,而不右施行于今,则何贵有此学耶?闻曾发变法之论,伏望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此日之衔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上下可以辅翼朝廷,次之亦足供河西、吴越之用。即令付诸衡阳王子《噩梦》,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纵然春蚕到死,犹复捣麝成鹿。谚曰:‘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 [12] 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所处之时代与王夫之所处之时代有相同的地方,所以特别学习王夫之的学以致用,要“变法”,要明“救败”之道。他认为船山在评史时也注重实用,他说:“王船山尝恨两汉史官昧于政体,时承大乱之后,归降动至百数十万人,其用兵之数,当不止此,皆不农不耒,无业游民也,一旦归休,如何劳来,还定安集之,又操何术,使有执业,足自给而不为乱,当时至大至艰之事,宁有过于此者?而史官一字不及,真可谓无识焉耳。……” [13] 甚至引用王船山观点批驳反对变法维新者。他说:“来语:‘将讲洋务之术尚未精,必变法以图治欤?抑中国圣人之道固有未可尽弃者欤?’……衡阳王子申其义曰:‘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 [14]
在维新变法的各种活动中尤其是在当时写的许多文章中,梁启超是比较多的政治化使用船山言论。光绪二十二年写的《变法通议》[15]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南学会叙》 [16] 以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的《读春秋界说》[17] ,均有引用船山言论佐证改良之必要或直接指出船山是改良运动所要借鉴的。
谭嗣同、梁启超二人对于现代船山学的贡献就是他们发掘了王夫之思想的现代价值,确定了王夫之研究的基调。
由前所论,我们知道,谭嗣同、梁启超的王船山研究注意揭示王夫之思想中科学与民主思想。众所周知,科学与民主思想的高扬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价值。从这一点说,谭嗣同、梁启超的船山研究正是确定了此后船山研究的基调。
三
对于谭嗣同、梁启超的船山研究,在当代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谭、梁二人的船山研究中有对船山思想的误读。从宏观角度来看,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还原,都有一定的研究者的主观成分在内,谭嗣同、梁启超也不会例外。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他们不是有意打扮他们的研究对象,而是有其内在逻辑。谭嗣同喜言科学思想,一时兴起。谭嗣同自己对西方科学知识有比较广泛了解,如他说:“西人分舆地为文、质、政三家。……故西学子目虽繁,而要皆从舆地入门。不明文家之理,即不能通天算、历法、气学、电学、水学、火学、光学、声学、航海绘图、动重、静重诸学;不明质家之理,即不能通化学、矿学、形学、金石学、动植物诸学;不明政家之理,即不能通政学、史学、文学、兵学、法律学、商学、农学、使务、界务、税务、制造诸学。” [18] 他自己对算学、对格致学都作过探讨。谭嗣同还认为中国有一个科学传统。他说:“三代学者,亦皆有所专习,切近而平实。自秦变去古法,学术亦与之俱变,渐无复所谓实学,而今滋甚。即如算学为中国最实之学,中国往往以虚妄乱之,……格致之理,杂见周、秦诸子,……” [19] 这里说中国自古有所谓“实学”,这种“实学”指的就是科学。谭嗣同这种说法并没有错,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因此英国李约瑟作了一部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既然中国自古有科学,王夫之有科学思想就完全符合逻辑。正因为谭嗣重视科学,有时候对王夫之亦有所批评。他说:“嗣同夙愤末世之诬妄,惑于神怪杂谶,使民亹亹乎事业,坐为异邦隶役,读衡阳王子辟五行卦气诸说,慨焉慕之。独怪乎《河图》、《洛书》、《太极图》等,何复津津乐道。” [20]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是谭嗣同鲜明的主张,他崇敬王夫之,也崇敬王夫之的科学思想。
谭嗣同对民主思想的认识亦是如此。首先他认为民主思想是古亦有之。他说:“即如君臣一伦,人人知其有,不待言矣。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视中国秦以后尊君卑臣,以隔绝不通气为握固之愚计,相去奚止霄壤。”[21] 关于这一点问题,他在《仁学》阐述更为清楚。他说:“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 [22] 对民主的肯定,还否定伦常。他说:“方孔之初立教,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且即以据乱之世而论,言伦常而不临之以天,已为偏而不全,其积重之弊,将不可计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枘,以苦父天母地之人。无惑乎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而亟劝其称天以挽救之,至目孔教为偏畸不行之教也。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23] 对伦常,对三纲都进行抨击,甚至提出要“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24]这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号角。由此看来,谭嗣同认为王夫之倡“民权”就完全不奇怪了。
或许谭、梁的船山研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运动有着紧密联系。
四
综上所述,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揭示与确定,有其特殊的原因:或因是同乡之人,或因是同志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中,王夫之著作的出版与传播恰逢其会,又因谭、梁的传播而影响日大,成了近代改良、启蒙的重要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篇》卷二《书曾刻船山遗书后》,转引自《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95-796页。
[2]许冠三:《王船山致知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3]许山河:《论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船山学报》1988年增刊。
[4]《致潘黻庭》,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转引自《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60页。
[5]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82页。
[6][8][9][13][14]《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4、55-56、338-339、227、366页。
[7]《谭嗣同全集》(增订本)。《论艺绝句六篇》之第六篇及其自注,中华书版1981年版。
[10]《说动》,《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11]《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2页。
[12]《儒家哲学》,民国十六年(1927)讲演记录,专集之一百三,见《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15]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08-209页。
[16]《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页。
[17]《南学会叙》,《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18]《读春秋界说》,《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19][20]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33、231-232页。
[21][22]谭嗣同:《思纬壹台短书·叙》,《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07、210页。
世界船王范文第5篇
郑和的船队,人员超过2.7万人,随行的船舰多达200余艘,最大航程1500海里。如此庞大的海军队伍,如何组织有序,如何保证安全,完成使命,都考验着郑和的组织领导能力,也反映了明初国家能力所达到的高度。
郑和船队组织严密。2.7万多人的队伍,据《郑和家谱》“随使官军员名”记载,领导管理团队中,有“钦差正使太监七员”,首席钦差正使自然是郑和,《明史》卷304《郑和传》说,“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这里的“其侪王景弘等”,应该就是太监七人中的其余6人。此外,还有副使监丞10员,少监10员,内监53员。这是一个80人的领导团队,分为4个层级,其中正使、副使(监丞)、少监等27人构成核心领导层,内监53人是执行领导层。
专业执行团队中,有负责对外交涉采办的官吏,有鸿胪寺班序二员,以及买办、通事等;负责内部财务管理、文书账簿的有户部郎中、舍人,负责医疗治理的有医官、医士等。
各条船只有负责海航和船务工作的专业团队,有火长(船长)、舵工(操舵手)、班碇手(起落船锚)、民梢(升降帆蓬)、水手(划桨)等。阴阳官、阴阳生则负责观察和预报天文气象工作。护航军事工作的有都指挥二员、指挥93员、千户104员、百户103员。其余则是多达2万多人的旗校、勇士、力士、军士等。
郑和船队的七次航行,前3次最远到达的是印度卡利卡特(即古里),后面4次则远至波斯湾、红海,最远到了非洲东部海岸。我们从《郑和航海图》中可以发现许多我们今天熟悉的地方,却被冠以不熟悉的古老名字。比如他们去过旧港(Balenbang),今天印尼苏门答腊南部城市;去过淡马锡(Temasek),这是新加坡的古称;去过官屿,即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去过忽鲁谟斯,即霍乐木兹(Hormuz)。此外还有满剌加(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西侧)、锡兰山(斯里兰卡)、柯枝(即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古称盘盘国)、古里(即今印度卡利卡特,郑和在此逝世)、撒地港(孟加拉国吉大港)。
到过的非洲东岸地区,则有木骨都束(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慢八撒(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孙剌(莫桑比克索法拉河口)、比剌(莫桑比克港)。这些地区大多见于《明史・外国传》,该书卷326《外国七》记载往来各国时说,“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说明郑和船队远到莫桑比克海峡,东非莫桑比克索拉法省及其河口,大约是郑和航行最远之地了。再往前进一步,就是南非海岸了。
郑和船队在东非海岸探索的时候,他有一个欧洲的对手―葡萄牙王子亨利(1394~1460),一位比郑和年轻20岁的“航海王子”,也在非洲西岸从事伟大的航海事业。
同样是航海家,郑和更像一个政治外交家,葡萄牙的这位亨利王子,则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样是皇家资助的航海事业,郑和是在完成天子的政治外交使命,亨利王子则于宗教狂热、经济利益追求之外,对于航海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探求,是他痴迷于航海探险事业的重要原因。
亨利王子终身未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远离首都里斯本的尘嚣,是在葡萄牙西南海角的边陲小镇萨格里什度过的。在这里,他创建了地理研究院、航海学院、天文台,收藏地图和手稿的图书档案馆。他不仅广泛搜集了地理、造船、航海等各种文献资料,而且极其包容地网罗了具有不同信仰的地理、天文、制图、数学方面的学者。亨利自任航海学院校长,讲授地理、天文和航海方面的课程。他们孜孜以求地探讨,能够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到香料群岛吗?人类能在赤道地区居住吗?地球究竟有多大?为此,亨利王子组织了一次次西非海岸的航海探险,不断搜集航海资料,改进造船、制图和航海技术。
有西方史家把亨利王子对航海事业的热情,称之为一种“前科学的好奇”。把对航海科学和海洋知识的探求本身当作目的,这是郑和的航海活动所不具备的。
亨利王子要求派出的探险队,把新发现地区的地理概况和资源情况详加记录。比如有关海潮、风向,鱼和海鸟运动的报告,他们把这些资料搜集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1434年,他的探险队成功地越过博哈多尔角(过去一向认为人到此就会变黑),了解到北大西洋的风向和洋流规律,发现只要离西非海岸向西北航行,就有能把他们带回葡萄牙的西风。这就大大地鼓励了葡萄牙人穿过赤道、绕过非洲南端的航行勇气。哥伦布的西行,也得益于这种关于大西洋风向和洋流的知识。
亨利王子的探险队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的同时,就在绘制关于非洲海岸的航海图。亨利王子的哥哥佩德罗1428年从威尼斯带回一张世界地图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对亨利王子的航海制图起了积极作用。亨利王子制作的航海地图,以弗拉・莫罗的《世界地图》最为知名。该图的非洲部分,就是在亨利王子的著名探险队长卡达莫斯托的帮助下画出的。葡萄牙人把对航线的探索,变成航海科技;郑和的海航记录只是马欢、费信、巩珍等随笔式的文人游记。
郑和的海航结束了,明朝中国的航海事业就结束了。但是,亨利王子去世后,亨利王子开创的葡萄牙航海事业,却依然发扬光大。萨格里什的航海学院,西非海岸的探险实践,都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富有经验的水手和海员,其中包括迪亚士等著名航海家。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蓝图,也是在这里酝酿形成的。15世纪每一个由陆路或海路从事地理发现的人,多少都受惠于亨利王子的航海研究事业。
就郑和航行船队的规模,航行里程的长度而言,可谓世界上空前的壮举。它的成就突出地显示了“举国体制”的宏伟、高效、壮观。亨利王子的航海活动,则包含着精明的算计,科学的热情和经济的追求。郑和下西洋以政治目标为准,基本上不是为了贸易经营。《明实录》记载明成祖登位不久,在给南洋诸国的诏书中,是这么说的:太祖高皇帝之时,诸番国来朝,我大明王朝都待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误有干犯宪条之事,也皆予以宽宥。诸番国前来“市易”,是朝廷对于诸番国的恩惠,是巩固政治互信的手段。
郑和在南海的行动,总体上是和平使者,每次出行,都洒出大笔的钱,引导南海各国向风慕义,朝觐大国,不搞殖民地,不做人贩子。郑和曾经帮助途中的国家稳定其统治秩序,对于在南洋的华人,则尽力要求其返回中国。亨利王子派遣的葡萄牙船舰,却是殖民行为,1419年占领马德拉维,宣布为殖民地,1427年发现亚速尔群岛,并于5年后宣布为殖民地。1441年,葡萄牙船长贡萨尔斯,从布朗角上岸,带走10个黑奴。1445年,迪亚斯在塞内加尔河口掳掠235名黑人,并带回葡萄牙,进行拍卖。此后,葡萄牙经常派一些人去西非海岸,掠夺黑人为奴。有统计称,15世纪整个下半个世纪,平均每年从非洲掠走的黑奴,大约500~1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