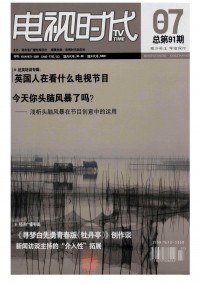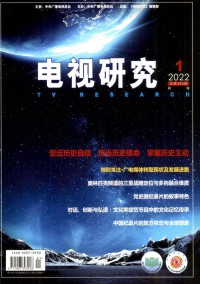电视数字化产业政策均衡思考

摘要:中国数字电视推行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广电总局不仅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规划了有线电视数字化的发展,啦技术、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时,还通过传媒予以强势传播。
从政府政策的推进力度来看,数字电视产业政策显然是一个强制性的传媒产业制度变迁。政府力图通过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改变长久以来广电行业产业化进程波澜不惊的现状,释放市场活力。而推广数字电视隐含了一个竞争意图,那就是广电业欲同电信产业争夺数字市场。
一、数宇电视推行遭遇瓶颈
但是,政府强力推进的产业制度其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数字电视的推广不仅遭到来自行业内的强大阻力,受众也普遍表示难以接受。
数字电视产业推广的艰难表现为:技术标准未出台,直接影响国内数字电视终端生产商未来的规划;内容匮乏,内容提供商的缺席被视为数字电视最大的软肋;用户数量远没有达到规划目标,数字付费电视既有的盈利模式与中国电视受众的接受程度矛盾。此外,运营商的收入也难以保证。
新的盈利模式还只是个概念,这成为市场难以启动的主要原因。原本开发数字付费电视市场的重要动力就是因为电视依赖广告的赢利模式基本走到极限,而如果数字电视节目中又充斥大量广告的话无疑会使新的市场重新陷入困境。
数字电视推行困难表面上看是技术障碍、资金障碍和受众接受度障碍,实际上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打破了旧有的利益格局,在新制度与旧有利益格局“共存”的过渡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制度安排的预期收益高于制度安排的成本。对于既有制度内的利益集团而言,只有在看到制度外的潜在利润并且在交易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对制度安排的创新能力。
当数字电视以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方式予以实施的时候,制度内各集团的原有利益均衡就被打破。这是就会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惯性而宁可保持旧有的制度均衡,即便旧有制度低效于新制度。在难以估计新制度推行成本的情况下,对旧有制度的维持利益风险较小:另一种情况则是,在既有制度均衡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并享有旧制度给予的外部性,那么新制度的推行必然遭致这部分利益集团的反对。虽然数字电视制度面进行了引导,同安排及其实施由政府来担当制度创新主体,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新制度的推行受阻挠的格局。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固有的“路径依赖”对于制度变迁的掣肘作用。
从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以往经验看,新制度的推行往往都以渐进的方式,并采取试点的手段在“试错”中校正新制度的偏差,通过与旧制度的反复博弈,最后在博弈均衡的状态下新制度实现效率。
在数字电视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同时采用了试点的方式,但是,这一制度在遭到旧有制度的阻挡时,由于未能采取相应的制度互补,以至于在博弈中反复出现不均衡。
二、对数字电视产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审视
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总是有效。以诺斯的观点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常常受许多因素的制约,“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政府的生存危机”。曙经过努力,政府可能降低一些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克服其他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约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尽管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但它可能违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则,因此存在制度低效或无效的可能。在数字电视产业政策的推广中,强制性制度安排之所以受到各方行为主体的反对,就是因为其对“一致性同意原则”的违背,以及旧有制度框架产生的“锁定”效应。对于如何使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得以发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比较研究给出了解决方案。
新制度经济学派中,青木昌彦在制度比较研究中作出重大的理论贡献。他认为,“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在各种社会经济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正因为如此,如果自己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而且在一个社会领域里产生的平衡与在其他领域里产生的平衡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被青木称为“制度的互补性”。
青木昌彦把一个社会看成是一个“游戏体系”,制度就相当于游戏规则。制度除具有法律基本含义之外,还源于人们的“共同观念”。正是因为这种“共同观念”,从而使制度成为具有自我约束作用的政治经济规则。因此,如果经济主体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因此,在各种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制度,也应该是平衡的。
以“制度的互补性”来看,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安排,来实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安排的补充。诱致性制度安排与强制性制度安排均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却面临着政府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的困扰。那么,通过诱致性制度安排与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相互补充,产生平衡,就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制度的互补”。
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解决诱致性变迁易导致供给不足、强制性变迁易忽视初级行为主体利益的难题,才能一方面化解强制性变迁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另一方面化解诱致性变迁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制度安排是由政府担当行为主体,强力干预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核心制度”,它需要诱致性制度的配合。
三、两种制度变迁互补的“中国经验”
事实上,如果检视20年来的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就可以发现,这一制度变迁是一个对多种互补性制度不断选择的渐进变迁过程。各种制度间不但存在互补竞争关系,而且其间的替代也注意寻找交易成本低的变迁路径。
所以,对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制度出现的制度困境,可行的办法就是继续推进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配合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两者的互补,才能使新制度最终发生变迁并产生效率。
其次,外部力量对数字电视产业政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因素。在探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进程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力量——技术。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因为技术,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变。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或许不是技术本身,但技术所带来的意义却并不仅止于技术层面。当我们试图找到技术对于传媒经济发展的推动逻辑时,集中讨论的焦点就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如何推动了产业制度变迁?
“外生技术决定论”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无法决定技术进步的方向、速率、结构,相反。后者可以决定前者的方向、速率、结构。
而“内生技术决定论”则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速率、结构都是内生于社会的,是由社会特定的经济激励机制、政治权力结构、文化演变方向决定的。
诺斯的观点是,制度变迁相对于技术进步而言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正是制度决定了技术进步的实际速率和一个经济的实际绩效,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技术进步对制度变
迁的重要影响作用。到底是技术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技术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未有定论。而技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制度变迁发生作用,则更无法在当下得到清晰的解答。
但是,正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处于对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同身受的时期,我们必然关注技术对我们的实际意义。至少,它的确能够解决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中的一些问题。
如前所述,数字电视产业制度安排的一个现实动因就是广电产业受到来自电信产业的挑战。事实上,这种挑战是针对双方的。两个长期垄断的产业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技术冲击并将发生巨大变革。就目前来说,至少,技术变迁对原有两个不合理的市场结构直接带来挑战,打破行业垄断,并促成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的产生。而打破垄断,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一个节点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是否可以引发继续的思考:技术的发展,对于传媒产业制度变迁而言,会不会产生比市场或者产权更有效的制度?这个问题是属于未来时态的。就目前对中国传媒产业
发展而言,市场或者产权各自也都还没有展现出自己全部的优点和缺点,改革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和“纠偏”的过程。
注释与参考文献:
(D中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的时间表。中国广电总局制定的<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lO年远景规划》提出:到2005年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超过3000万户,20lO年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