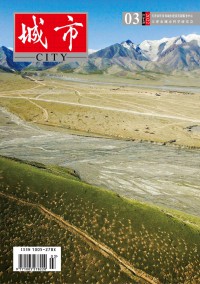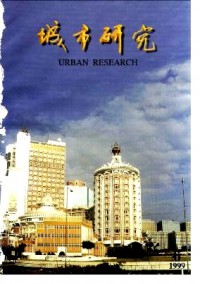城市管治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城市管治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市场经济改革改变了社会管治的基础。近来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地方政府的研究。但多数局限于政府机构的变化,属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尤其缺乏对政府基层政权的研究。近来随着对社区的重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本文力图分析改革后管治基础的演变,以揭示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危机,由此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以加强其对社会的管治能力。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1]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1).
[2]刘君德.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制度的创新与思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3]JESSOPB.1998.Theriseofgovernanceandtherisksoffailure:thecaseof
economicdeveloment.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155,29-45.
[4]LARDYN.1998.China''''sUnfinishedEconomicRevoluti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Institution.
[5]WALDERA.1995.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norganizational
analysisof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263-301.
[6]WUF.1999.The`game''''oflandedpropertyproductionandcapitalcirculationin
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withreferencetoShanghai.EnvironmentandPlanning
A,31,1757-1771.
[7]WUF.2000.Theglobalandlocaldimensionsofplace-making:remakingShanghaiasaworldcity.UrbanStudies,37,1359-1377.
[8]YEHAG.WUF.1996.Thenewlanddevelopmentprocessandurban
developmentinChinesecities.InternationalJournalofUrbanandRegional
Research,20,330-353.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