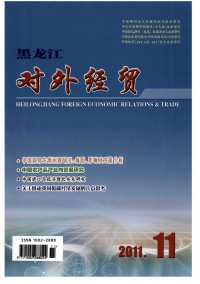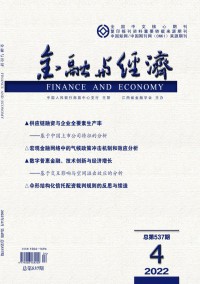我国最早的诗歌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第1篇
中国的“朦胧诗”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的发轫之作是舒婷于1979年发表在福州《兰花圃》上的一批诗,其中有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等。其时真名叫龚佩瑜的舒婷还是厦门灯泡厂的一名女工。她的诗作以新颖的构思、神奇的意象和独特的比兴,给在“”时代压抑已久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这使众多诗歌作者和读者深受鼓舞和喜爱,同时也引来不少非议和反对。
由此,《福建文艺》(后更名《福建文学》)编辑部于1980年2月率先在全国组织了一场新诗大讨论。围绕诗歌可不可以抒发个人感情;抒个人之情与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关系如何;怎样扩大诗歌的题材;怎样看待诗歌的社会职能;新诗应如何吸收外来形式,它与民族化、大众化的关系如何等等,每一期都辟出专版刊登争鸣与商榷文章,时间达一年半之久。这期间,诗歌界著名的“三个崛起”先后问世,即:谢冕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上的《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发表于1981年3月号《诗刊》上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发表于1983年第1期《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此前,孙绍振更早在1980年4月号的《福建文艺》上最早在理论界发表了支持舒婷的文章《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福建文艺》及紧随其后的《诗刊》的新诗大讨论和“三个崛起”无疑给起步中的舒婷、北岛、顾城等新诗人以极大的支持和肯定。但反对派的声浪也正一浪高过一浪。
最早的反对派代表人物是公刘、章明等。章明以《令人气闷的“朦胧”》――发表于1980年8月号《诗刊》上的文章而“名满天下”:“也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此前,舒婷北岛的诗先后被人叫作“新诗”“难懂诗”“晦涩诗”“古怪诗”“某种品类”等。自从章明的“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之后,“朦胧诗”一词迅速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并传扬开来。由《福建文艺》首开先河的各种新诗大讨论也在全国相继开展。但是,很快,一场全国性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给“朦胧诗”以极大肯定的“三个崛起”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尤其因为孙绍振(当年才45岁)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新的美学原则,以其思想的大胆,理论的尖锐还有对传统美学观念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不驯服姿态,既引起全国理论界的关注,又受到最严厉的批判。断章取义截取的批判论据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和我们50年代的颂歌传统和60年代的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孙的这最后一段文字被批得最多最狠,几乎达到体无完肤的地步。
但是,无论怎样大棒挥舞,“三个崛起”反而越批知名度越高。“朦胧诗”更在全国诗坛奠定基础,从此走向世界。这正如诗人蒋夷牧在1980年《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文中所言:“十几年来,诗歌在宣传大话,编造假话方面充当了很不光彩的号手角色。暂且撇开内容不说,就风格和流派而言,诗坛几乎只能听到一种乐器――小号的声音。言不由衷的高调,声嘶力竭的呼喊早已使人厌烦。而舒婷同志却操着自己的琴弦,吹奏着富有自然气息和人情味的木管进入了诗坛……”
(选自2006年8月2日《天涯论坛・散文天下》,有删节,作者为福州大学教授)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第2篇
一、从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说起
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是他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的演讲,原稿是英文。选入教材的文章,是作者自己根据讲稿节译的。钱先生在文章中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谈了他对中国诗和外国诗的理解以及认识,归纳起来,就是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没有史诗,中国最好的戏剧诗歌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歌之后。中国诗歌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歌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二是中国诗歌“短”,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三是中国诗歌富于暗示,也就是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四是中国诗歌笔力清淡,词气安和。五是中国的社交诗歌特别多,宗教诗歌几乎没有,如是而已。钱钟书先生在文后说,中国诗歌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歌只是诗歌,它该是诗歌,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从钱钟书先生的文章出发,我们再来看白茂盛老师以及程环老师执教的课,也就方便得多了。
二、总体印象
不论是白茂盛老师执教的《蜀道难》也好,也不论是程环老师执教的《临江仙・夜归临皋》也好,从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技术规范等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做得很好的。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对诗歌的朦胧美、古典美以及音乐美等几方面都做了淋漓尽致地阐发,并且也都把对诗歌的多元解读作为教学的重点,设计精到严谨,很有新意,也很有深度。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学生高度融入,参与度极高,自主探究学习的热情特别浓郁,课堂气氛非常好,值得学习,值得借鉴,同时也深受启发。
三、收获与启示
结合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谈谈自己的收获与启示。
首先是,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我们要特别重视“诵读”这个法宝。很多教师都知道,古典诗歌教学要让学生反复诵读,加强诵读的指导,但是恰恰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的老师常常做得不够。白茂盛老师也好,程环老师也好,他们都在诵读的基础上,达成了教学目标,哪怕是对诗歌文本的多元解读,也建立在学生的反复诵读的基础上。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诵读更能唤起学生内心深处的生命律动和情感共鸣的方法了!
谈到读诗时,清代沈德潜在《说诗语》里曾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曾国藩在家书中谈到诵读体会时,也说:“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美哉,诵读!妙哉,诵读!
其次就是,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还必须体现一个字,那就是“活”。钱钟书先生说,中国诗歌富于暗示,也就是,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钱先生的说法,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特征:含蓄蕴藉。诗歌的欣赏,讲究的就是要进入诗人在诗歌中精心营造出来的艺术境界。古典诗歌中,往往有内涵丰富精致的意象。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在诗歌的教学中,必须把握住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会误解诗歌,教“死”诗歌,从而搞坏诗歌蕴涵的丰富的美。
最后就是,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千万不要将学生当做古典诗歌的鉴赏家和古典诗歌的批评家。在高中阶段,我们对古典诗歌的教学,目的何在?我想,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趣味,提升学生的审美品质,熏陶学生的情感精神,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给学生年轻的生命里注入一些纯粹而高雅的东西,让学生以后的人生增加高贵脱俗的可能性。明确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学生对诗歌的诵读品味以及对诗歌的体验感知上,要尊重学生阅读诗歌的“原始感受”,切不可由老师来对学生强行灌输,更不能让学生信马由缰,乱说胡说。那种因为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而把学生当成古典诗歌的鉴赏家以及批评家的做法,是违背教学原则的,也是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
细细思量,高中语文的诗歌教学虽说没有定法,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人类文化的最初发展阶段上,诗歌、音乐、舞蹈是连结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诗经》作为歌、乐、舞的集合体,它是中国有诗以来的第一部乐歌总集,并且在艺术形式、题材内容以及艺术渊源上与中国上古诗歌一脉相承。通过对二者继承关系的探讨,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华古文化。
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和历史的前进,上古的神话、音乐到周代的《诗经》,中华古文化—歌、乐、舞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三者是一个整体。正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所证明的,在原始部落,也即人类文化早期,歌谣均是载歌载舞的。很少有舞而不歌或歌而不舞的,且“原始的抒情诗是合乐的,……最后,叙事诗或至少叙事诗的一部分,也不单单是记述的,是用宣叙歌唱出来的”。
《诗经》作为乐歌,它与中国上古诗歌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就《诗经》作为乐歌的性质,以及它对上古诗歌的内容形式的继承性方面加以探讨。
在上古社会,由于文字没有发明,人们的情感完全靠口头交流,为了使内心情感得以淋滴尽致的表达,就配之以舞蹈,并加以歌唱,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与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诗·大序》开篇即言: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吸叹之;吸叹之不足,故味歌之;味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用之也。
从而说明了诗、歌、舞是一体的。其实早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就是如此。如《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大禹治水不能与恋人涂山氏女相会,涂山氏女在等待时,便唱了一首恋歌:“候人兮猜!”这是现存最早最短的一首情歌,用歌唱代替语言,抒发内心的激动、期待之情。远古著名的乐舞有《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武》等等。在《礼记·乐记》中:“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协同分工构成一个整体。
《诗经》作为诗、乐、舞的集大成,虽然只有文字,音乐已经不可耳闻,但我们从字里行间及每首作品本身的内容结构方面仍可了解到那个时代丰富的民俗音乐生活,以及诗乐的一般特点和演唱概况。其艺术渊源就是上古与乐舞结合在一起用以传唱和表演的歌。在理清《诗经》与上古诗歌传统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诗经》作为乐歌的性质。
在“五四”时期,顾领刚在《论所录全为乐歌》中指出:
春秋时的“徒歌”是不分章段,词句的复杳也是不整齐的。《诗经》不然,所以《诗经》是乐歌。凡是乐歌,因为乐调的复奏,容易把歌词铺张到各方面,《诗经》亦然,所以《诗经》是乐歌。两汉六朝的乐歌很多从徒歌变来,那时的乐歌集又是分地著录,承接着《国风),所以(诗经)是乐歌。徒歌是向来不受人注意,流传下来的无名氏诗歌皆为乐歌;春秋时的徒歌不会特使人注意而结集入《诗经》,所以(诗经)是乐歌。
顾领刚从《诗经》章段的划分、词句的复沓以及歌词多方面的铺张等,证明了《诗经》全是乐歌。此外,张西堂在《论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一文中也提出论证了《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具体来说,《诗经》的乐歌性质可以表现在:《诗经》的兴、声韵、结构等方面,这将在下文中加以分析。
我们说《诗经》乐歌是对上古诗歌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诗歌内容上的传承和发展。
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诗歌常常以狩猎为内容,这也是当时生产劳动的需要,以《弹歌》为例:
断竹,续什,飞土,逐肉。
表现原始社会人们用竹做弓,发射石弹狩猎的内容。又如在《尚书·舜典》中记载有“击石柑石,百兽率舞”的乐舞,大约是人们以自制乐器伴奏,扮作各种野兽形状来驯服百兽的愿望或欢庆胜利的场景。
这一狩猎内容在《诗经》中得以传承,并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猎人形象,透过这些形象可以洞见先民祟尚勇力的朴素美。
田猎诗在《诗经》中分布广泛,在《国风》中有《周南·兔陪》、《召南·野有死糜》、《召南·验虞》、《卫风·有狐》、《郑风·叔于田)、《郑风·大叔于田》、《齐风·还》、《齐风·卢令》、《齐风·椅哇》、《秦风·骊戮);在《小雅》中有《车攻》、《吉日)等。有的讴歌猎人的勇猛,如《周南·兔陪》:
肃肃兔啥,标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陪,施于中过。赳赳武夫,会侯好仇。
肃肃兔借,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这首诗赞美了公侯卫士的英姿威武、勇力过人。正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的评价:“窃意此必羽林卫士,息哗游猎,英姿伟抱,奇杰魁梧,遥而望之,无非公侯妙选。”此外,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又说“《兔陪》,猎兔者武士自赞之歌”。
有的则是展现了一幅规模宏大的狩猎场面,如《郑风·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马。执誉如组,两珍如舞。叔在获,火烈具举。
担拐基虎,献于公所。将叔无扭,戒其伤女。 古代诗歌有进一步的了解。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移雁行。叔在获,火烈具扬。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磨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鸽。两服齐首,两移如手。叔在获,火烈具率。
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栩忌,抑仓套忌。
诗正面铺陈的描写,展示了射猎的全过程。场面特写历历如画,如“叔”聚众狩猎,猎火一起燃起,“叔”要开始捕猎,看他勇猛过人,敢于赤膊去打虎;他精于射术,驰马驾车的本领无人能及。正如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大叔于田),亦为赞美猎人之歌”。
除此以外,《诗经》中的《齐风·还》还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友好的猎人形象。
以上可以看出,上古诗歌中有关狩猎的内容在《诗经》中得以充分的继承并加以丰富。无论是在篇幅上,还是场面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远远胜于弹歌。
远古乐舞的演出形式,一种是“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之歌八阂”(《吕氏春秋·古乐篇》),另一种是“八信…皮弃素积,锡而舞大夏”。(《礼记·明堂位》)《诗经》作为乐歌在艺术形式上也继承了上古诗歌传统的特点,从而保留了上古诗歌的口传性和表演性。
西方学者帕里洛德有一个基本观点“早期诗歌的基本性质是口述的”,而《诗经》就是口传的乐歌,口头传唱的特点非常明显。按口传诗学的理论来看(诗经),就会发现诗中有很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这正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格式和套语又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联系在一起,也即“一花泯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正如《诗经》中存在着很多的重章叠句,这正表明了诗歌的民间性质,它是民间诗人依据固定的模式吟唱的,具有口传性。以《卫风·木瓜》为例: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据。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璐。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首诗从结构上来看,运用的曲调是单纯重复的方法,“一唱三叹”,这是我国上古音乐中最常用的曲调结构。此外还有《魏风·伐植》、(采葛)等都用这种复沓结构,具有很强的口头传唱性,从而继承了上古诗歌传统的口头性特点。另外,诗经中使用的是和原始劳动节奏相应的二二节拍的四字句。
上古诗歌艺术形式中的表演性,在《诗经》乐歌中往往表现为诗句起兴的动作姿态。
“赋”、“比”、“兴”是《诗经》最典型的结构方式,在钟嵘的《诗品》中可归纳为:“故诗有三意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指出:“有声无义,特发端之起兴也。儿歌市唱,触而多然。”由此可见,“兴”在《诗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初甲骨文学者对于“兴”字源和字形上的分析,指出了“兴”是一种集体性的动作,并且伴随着有节奏的声音。简单来说,“‘兴’的最初含义就是由群体实施的、伴随节奏的声音和动作”。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何其芳 诗歌创作 诗学观念
建国以前对何其芳诗歌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其《汉园集·燕泥集》的分析,以及延安时期对何其芳《诗三首》的争议、批评等。建国以后,对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的评论研究增多,同时在何其芳的诗学观念以及诗歌创作现象、心态情结、文化渊源、与同时代诗人的比较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建国后何其芳诗学方面的评论和研究做一些梳理和回顾。
一.1950年代何其芳诗歌创作与诗学观争鸣
1950年代到“”前,有关何其芳的评论篇目较少,主要集中于:对何其芳《回答》一诗的争论;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观点及民歌观点的争论探讨。
1.有关《回答》一诗的讨论。
1954年何其芳《诗三首》在《人民文学》第10期上发表,杂志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围绕《回答》一诗引发了不小的争议。1955年,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曹阳《不健康的感情——何其芳同志的诗读后感》、清一《为“回答”辩护》等数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评论了何其芳建国后的诗作《回答》。
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人民文学》刊载。盛荃生批评《回答》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在一个赞歌时代不够明朗、健康,与时代不协调,希望诗人从“我的河流里”航行出来,到亿万人的大川里,讴歌时代。与盛荃生的观点相似,叶高认为何其芳的《回答》让读者失望,批评《回答》里流露着忧郁的、消极的情绪,缺乏战斗的力量,赞扬《讨论宪法草案后》等另两首詩更健康。[1]
曹阳对何其芳《回答》的批评更严厉,认为该诗让人失望,阴郁,让读者迷惘,批评何其芳“诗人自己远离了人民的沸腾的歌声”,“诗人应该感激人民的关怀,努力用歌颂祖国、人民和人民美丽理想的诗篇来回答这种关怀。我们希望的也正是这种回答,而不是别的什么抒发个人不健康感情的回答!”[2]
1956年,清一发表《为“回答”辩护》,提倡要科学地对待诗人的作品,批评盛荃生、叶高等孤立、片面地看待诗歌中的一些细节,同时,也提出应接受不同艺术家的不同风格,缠绵的感情未必都不健康。清一肯定何其芳的感情是真挚、诚恳的,读者不应忽略诗歌整篇的情绪,以及诗人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3]
何其芳诗歌《回答》中传达了何其芳较多的个体的感受,但1950年代的时代背景,要求作家更多地创作歌颂英雄的时代、歌颂英雄的人民的诗歌,要求个体融于集体,“小我”汇入“大我”,读者对《回答》中所传达的微妙复杂的情感难以理解。经历了这种严厉的批评之后,何其芳后来诗歌创作渐少,残留的个性化色彩也在后来的诗歌中消失殆尽。
2.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观念与民歌观点的探讨。
何其芳建国后诗歌创作渐少,在新诗的诗学理论方面却颇有建树。总括而言,他的诗学理论建设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诗歌特点的界定,对写诗读诗的论述,对新诗状况的总结;二是现代格律诗观念的建构;三是对民歌、新民歌的相关论述。
何其芳1950年写《话说新诗》、1954年发表《关于现代格律诗》,提出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主张新诗顿数和押韵的规律化,而不是照搬五七言的句法,并认为“这种突破了五言和七言的限制的民歌体”可以作为诗歌的体裁之一而存在,同时认为“用民歌体和其他类似的民间形式来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生活仍然是限制很大的。”[4]
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正式号召大家收集和创作新民歌,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在提倡新民歌的时代大背景下,何其芳有关民歌的论述遭到片面的批评。公木在《人民文学》1958年5期,发表《诗歌底下乡上山问题》,指责何其芳“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引发了针对何其芳诗学观念的批评。随后,有张先箴《谈新诗和民歌》(《处女地》1958年10月)、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1958年10期)、仇学宝的《不同意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的意见》(《萌芽》1958年24期),萧殷《民歌应当是新诗发展的基础》(《诗刊》1958年11期),沙鸥的《新诗的道路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等十多篇文章批判何其芳对待民歌及民歌体新诗的观念。如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开篇即指责何其芳“‘处女地’上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探讨诗歌发展道路的文章,都流露着轻视新民歌的观点,而把我国诗歌前途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新格律’或‘现代格律诗’上。”[5]
《萌芽》当年组织“诗歌发展方向笔谈”栏目,组织工农兵作者发表意见,电话工人仇学宝,批判何、卞“为了反对学习民歌的形式,他们企图从《诗刊》今年四月号‘工人诗歌一百首’中找寻根据,以便证明工人诗作者并不喜爱民歌体裁。”[6]
李根宝的《不是形式限制问题》,则直接将形式问题上升到思想层面:“其实,这不是个什么形式限制问题,而是个思想问题,是要不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是要不要真正民族风格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唱什么歌的问题,是个‘什么时代唱什么歌’的问题。”[7]
张光年《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 在新事物面前——就新民歌和新诗问题和何其芳同志、卞之琳同志商榷》一文中,认为何其芳、卞之琳在主观上没有轻视新民歌,“可是,他们头脑里预先有一个比新诗和新民歌都要好得多的‘现代格律诗’或‘新格律’,相形之下,新民歌的艺术上的光彩不免因此而减色。”[8]
何其芳随后写作了长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反驳这些批判,比较详细地阐释了自己对待新诗和民歌的观点。[9]
二.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歌创作研究
“”期间,文艺萧条,对何其芳诗歌以及诗学观念的评论、研究几近于无,直到新时期开始,对何其芳的诗歌的研究才进入到全面、深入的阶段。
有对何其芳诗歌具体文本的分析,如孙玉石《梦中升起的小花——何其芳浅析》,周棉《三幅情趣盎然的画图——何其芳诗作(二)赏析》,费勇《爱情永远美丽——何其芳诗赏析》,常文昌《飘在空中的瑰丽的云——简论何其芳意象》,以及对《独语》、《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北中国在燃烧》等作品的解读,有对《雨前》语言特色的解读,同时有学者关注到《预言》的疑问手法,以及早期诗歌中的佳人意象。
有对何其芳某个时期诗歌进行论述的文章,如吕进《何其芳的》,卢风《试论何其芳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范肖丹《何其芳早期诗情智统一的特征》、邓礼泉《如烟如梦 娇妍圆融——何其芳早期诗歌艺术鉴赏札记》、卫奉一《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卢风认为建国后的诗歌创作,是何其芳诗歌的第三个里程碑,《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序幕和起点,何其芳以创作实践实现现实主义主张,并有两点意义:“一是抒情诗领域里颂歌传统的形成,把诗和时代、诗和现实生活、诗和人民的关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二是随着生活内容的急剧变化,许多诗人在原来形成的艺术风格上注入了新的内质……”[10]
孙玉石主要着眼于何其芳这一时期对爱情和青春的歌唱主题,并认为他“艺术化的情诗”不再是社会思想的载体,而是将“五四”后的爱情诗升华到一个新境界,人生境界的扩大和艾略特的影响,形成了何其芳诗中批判现实和反思自身的“荒原”意识。[11]
也有对何其芳诗歌总体上进行论述的,如邢铁华《何其芳及其诗浅论》、陈尚哲《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发展》、汪星明《从梦幻的云到灼人的火——何其芳诗歌简论》,陆耀东《论何其芳的诗》等。
陈尚哲将何其芳诗歌创作分为1935年前、1935年后、延安时期《讲话》前、延安时期《讲话》、建国后这样几个阶段,并分析了这几个阶段创作上的不同特点,总结了何其芳诗歌与人民、时代的关系,诗歌真挚的感情,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以及在诗体形式上所做的探索。[12]
此外,学界还从语言、情感、意象、叙事性因素、审美效应等不同的角度入手,分析何其芳诗歌。
如分析何其芳诗歌抒情、情智特色的,有王林《何其芳〈预言〉的抒情艺术》,罗振亚《何其芳的情思空间与艺术舒相》,叶橹《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范肖丹《试论何其芳早期诗情智统一的特征》,陈吉荣《论何其芳早期诗歌的认知性体验》;分析其意象特征的,有张岚《孤独者的夜歌——论何其芳早期诗文意象的“孤独美”》。
谢应光《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观点新颖,注意到了何其芳诗歌中的叙事化倾向,指出何其芳从《预言》到《夜歌》这个阶段,前期诗歌以陈述事实、抒情线索显在、对话式的内在结构和叙事望为特征,而后期变迁为叙事的堆积、对话式结构模式的变异和倾述的欲望。[13]
谭德晶的《何其芳考及审美效应分析》则探寻了《预言》的哲理意蕴,即爱情的美在于镜花水月式的张力形式中,以及《预言》的哲理意蕴与作者真实经历的关系,和复合感受所产生的审美效应。[14]
从诗歌语言入手的,分析诗人的历史处境的有谢应光《何其芳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李遇春《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
李遇春文章认为:“在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实践中,何其芳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并超越当时正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其中隐含了主流权力话语重塑或改造诗人主体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排除程序’和‘提纯程序’来制约主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何其芳的话语困境植根于他的心理困境,也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15]
李遇春的文章探讨了何其芳晚年写旧体诗的复杂因素,并分析了何其芳自嘲、自叹、自责、自励的复杂心态,以及何其芳旧体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尤其是与李商隐诗歌之间的艺术渊源。[16]
卞之琳的《何其芳晚年译詩》,是最早评析何其芳诗歌翻译的文章,作者回忆了何其芳晚年译诗的动因,以及对诗歌韵律的精益求精,指出晚年何其芳试图在诗歌翻译中实践自己的格律诗主张。[17]
三.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学理论研究
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学理论研究,主要有雷业洪的《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何其芳诗歌定义管窥》,谢应光《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夏冠洲《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於可训《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霍俊明《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陈本益《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论三个要点评析》。
雷业洪称赞何其芳的诗歌定义“是人类诗歌史上首次跨入比较科学、比较完整的诗歌定义”,何其芳的诗歌定义中包括了反映现实的集中性特点以及诗歌的音乐性特点。[18]
夏冠洲在《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中,回溯了何其芳从延安时期尝试用古诗五七言体创建新诗格律体,到建国后在《关于写诗与读诗》中明确提出建立新格律诗概念的过程,分析了何其芳新格律诗的立论基础:诗歌生命节奏的基础,是以“顿”构成的;否定中国五七言诗作为新诗发展基础,因为古汉语单音节一个字多,不适应时展;不同意在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因民歌体新诗表达现代复杂生活受限,同时民歌也以五七言体居多。[19]
於可训的《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提出何其芳是中国新诗“二次创格”的主要代表人物,分析了何其芳创建新格律的动因是基于中国新诗与中国优秀诗歌传统脱节,何其芳创建新格律主张的核心是“节奏的规律化”,但在1950年代那种特殊环境中,何其芳的格律诗学只能是一个虚拟的诗学理想。[20]
四.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歌创作现象、心态情结、文化渊源及与同时代诗人比较分析研究
周良沛在《何其芳和他的诗及“何其芳现象”——》一文中,则认为“何其芳现象”是因为何其芳后期关在书斋,处在失去诗歌写作权利的状态,少于从现实生活中获取鲜明、生动的印象,同时习惯逻辑思维而需要形象思维的“形象”时,后期艺术创作产生困境。周良沛肯定何其芳参加革命之后的《夜歌》,与《预言》相比“后者不雕琢却朴素,失去原有的精致,却有不假修饰的自然”,“有免去脂粉气的‘真’,[21]有不赖华词丽句的‘真’,有其为‘真’而自然的节奏、韵味与力度。”[22]同时,指出晚期近似打油的新诗,比较粗陋。
江弱水《论何其芳的异性情结及其文学表现》、张洁宇《梦中道路的迷离:早期何其芳的神话情结》两篇文章立论新颖,发掘了人们很少关注到的一些领域。
江弱水的文章,分析何其芳诗歌《扇》、《风沙日》,结合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以及莎士比亚《暴风雨》,指出诗中诗人的自我身份是女性人物;同时,“何其芳的对于异性的企慕,在《预言》和《画梦录》里表现无遗”,“直到晚年,何其芳对于异性的企慕未尝稍解”,1976年9月何其芳一连写下8首绝句,追忆引领他灵魂的“永恒女性”。作者还提出了何其芳身上是否也具有“雌雄同体”的“双性人格”,而何其芳的异性情结,不仅构成了他的“梦”的重要内容,也使他早期的诗文风格,具有词一样偏女性化的、“精致”的美学品格。[23]
学界还就何其芳与新文学史上的众多诗人做了分析比较。如与其他诗人比较的文章,有李元洛《山灵与秋神——痖弦与何其芳(二)对读》,翟大炳《何其芳与“九叶”诗人陈敬容的创作轨迹——兼说库恩范式理论的借鉴作用》,薛传之《时代·气质·诗风——何其芳、戴望舒、邵洵美比较研究》,王鸣剑《何其芳与方敬早期创作比较》,李岫《现代的两位诗人——方敬与何其芳》,曾纪虎《哀婉沉郁与清新异美——艾青、何其芳诗比较》,骆寒超《戴望舒与何其芳诗歌世界的比较——一场从创作同源到分流提供的思考》。
何其芳诗歌创作与中外古今文化的关系,也是何其芳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类文章有探讨何其芳诗歌与中外诗歌关系的文章,如李光麾《试论何其芳对中外诗歌的继承和创新》,章子仲《何其芳早期诗歌在艺术上的渊源》,任南南《论象征主义对何其芳早期创作的影响》,尹少荣《论何其芳早期创作中的象征主义特色》,谭德晶《何其芳后期创作与艾略特影响》;有探讨何其芳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契合的文章,如董乃斌《超越时空的心灵契合——论何其芳与李商隐的创作因缘》,任南南《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何其芳诗歌与古典诗歌传统》。
注释:
[1]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均发表在《人民文学》1955年4期。
[2]曹阳《不健康的感情——何其芳同志的诗读后感》,原载《文艺报》1955年第5期,收入易明善等编《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
[3]清一《为“回答”辩护》,《人民文学》1956年11期。
[4]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原载《中国青年》1954年第10期,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何其芳全集》(第四卷),2000年5月1版,第298页。
[5]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1958年10期。
[6]仇学宝《不同意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的意见》,《萌芽》1958年24期。
[7]李根宝《不是形式限制问题》,《萌芽》1958年24期。
[8]张光年《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 在新事物面前——就新民歌和新诗问题和何其芳同志、卞之琳同志商榷》,《人民日报》1959年1月29日。
[9]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10]卢风《试论何其芳建国后的诗歌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4期。
[11]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文学评论》1997年6期。
[12]陈尚哲《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1期。
[13]谢应光《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文学评论》2003年2期。
[14]谭德晶《何其芳考及审美效应分析》,《求索》2006年9期。
[15]李遇春《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1期。
[16]李遇春《论何其芳的旧体诗创作》,《长江学术》2007年3期.
[17]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读书》1984年3期。
[18]雷业洪《何其芳诗歌定义管窥》,《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4期。
[19]夏冠洲《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新疆大学学报》2003年4期。
[20]於可训《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汕头大学学报》2004年1期。
[21][22]周良沛《何其芳和他的诗及“何其芳现象”——》, 《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6期。
[23]江弱水《论何其芳的异性情结及其文学表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3期。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第5篇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无论是咏物还是怀古,都会寄寓着诗人一定的思想情感,因此,对诗歌情感的把握是鉴赏诗歌的重点。其中,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主要有:不畏艰难、忧国忧民、建功立业、思念家乡、想念亲人、壮志难酬、凄清哀婉、热爱自然、豁达豪迈、愁苦孤寂、恬淡自乐、离愁别绪、怀才不遇等。
解题金钥匙
阅读一首诗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初步揣摩诗人的情感:
一、知作者,明风格
诗歌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抒情作品。在同一诗人不同的诗歌中,往往能体现出诗人相同的情感体验。对此,我们可以根据诗人所属的诗歌流派及其创作风格,对诗歌进行初步分析。例如: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追求雄奇夸张;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作品中往往体现出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多表现边塞将士的雄风;豪放派代表苏轼拥有旷达的胸襟;婉约派代表李清照的情感细腻;田园派诗人陶渊明向往闲适自由的生活等。但同时也应注意,所谓的创作风格是指诗人写作的主调,并非没有例外。比如婉约派李清照同样也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壮诗篇。因此,在诗歌赏析中要视情况灵活变通。
二、看提示,定基调
提示就是诗歌的标题、背景介绍、注解等,它们会给我们理解诗歌的情感以重要提示。例如: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其中“左迁”一词是被贬的意思,暗示了诗人被贬后的怨愤或惆怅之情,从而为我们把握全诗的情感基调奠定了基础。
三、抓意象,悟情感
通过具体分析诗歌中意象的特点,发挥想象,进而领悟诗人的情感。例如:“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秋词》)和“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 秋思》)中,同是写秋,两位诗人选取的景物不同,所抒发的情感亦不同。前者所写之景:“天”为晴空,“鹤”则排云而上,这两个意象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秋高气爽的明媚画面,情与景和谐统一,抒发了诗人进取、乐观的精神。后者所写之景:“古道”“西风”“瘦马”“夕阳”“断肠人”,这些意象所组成的画面,萧瑟,凄凉,抒写了天涯游子的孤独心境。
模拟训练题
1.下列对杜甫的《望岳》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
A.一、二句写远眺之色。以距离之远烘托泰山之高,表现了诗人初见泰山时激动喜悦、惊叹不已的心情。
B.三、四句写近望之势。着一“钟”字,特设泰山奇景:挺拔的山峰使得山南山北,一明一暗。
C.五、六句写细望之景。山中层云缭绕,使心灵受到涤荡。极目远眺,只见一只眼眶受伤的飞鸟还巢,可知诗人望泰山之专注。
D.七、八句写企盼登山之情。似写登山,实为明志,巧妙地以脚下群山的渺小反衬泰山的雄伟,蕴涵深刻的哲理。
2.阅读下面这首诗,回答问题。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唐]韩 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这首诗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描写早春,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趣味。请把该句所呈现的景象描绘出来。
(2)全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
(3)下列对本诗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
A.诗中真正写景的是一、二两句,诗人抓住早春特有的景物――小雨中的草色来写,富有诗情画意。
B.“草色遥看近却无”是全诗中最精彩的一句,草色若隐若现,似有似无,萌动着无限的生机,以此景写早春最为恰当。
C.诗中三、四句转入议论,运用对比的表现手法,指出满城烟柳之景是早春最迷人的景象。
D.诗人将此诗送给好友张籍是希望他能走出家门去感受一下早春气息,“最是一年春好处”也含有激励人们珍惜早春这一美好时光的意思。
3.阅读下面这首词,回答问题。
长相思
[南唐]李 煜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开,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