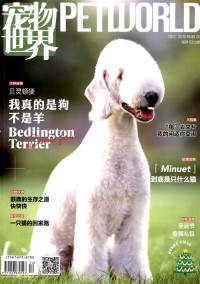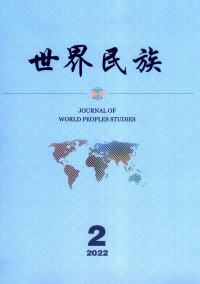世界文化概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世界文化概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世界文化概论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现实生活世界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内容与精髓,而是要探索《概论》的精髓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在我们看来,《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体现,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总结基础之上的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中国刮起了一股重实践、抓实践的强风,各大高校也无不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回应这种时代的主旋律。尤其是在高校中从事两课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更是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之中。当今中国,一方面,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迅速国际化,西方一些剥削阶级的生活价值观逐渐渗透,这样的社会现实严重地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官员腐败问题居高不下,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塑造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概论》的设立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对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实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的目的。这既是完善大学生知识体系的要求,也是培养大学生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前提。然而,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实践就无法证明理论的正确,也不能丰富、扩展、创造出新的理论。但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理论告诉人们,理论是独立的,具有预见性和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概论》就是这样的理论,而且是、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理解《概论》,首先就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理论界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也没有过统一的观点。邓小平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经验可循,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实践也证明,邓小平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因为他反复告诫人们,“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问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因此,有人就感慨,邓小平一方面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又没有说如何避免两极分化,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只是摸索如何实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把避免两极分化的思想搁置了起来;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实践——实事求是,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工作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好贯彻。比如,某保险公司的老总,他可以自豪地去领取6000多万元的年薪,其理由就是他感觉自己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把一个小的保险公司发展成了大的上市公司,他根本不去思考保险公司不仅是一个赢利的企业,也担负着社会求助的社会责任,即不能以赢利尤其是暴利为目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实践操作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明显不足,他们片面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许多观点。比如,针对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一些人就认为,只要经济工作做好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理想状态——通向共产主义。也正是这种现象的出现,高校的两课教师,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两课教师,越来越被边缘化。至于一些社会实践的践行者不去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学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邓小平理论只会背离时代的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社会实践将继续拉大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比如,有人主张彻底实现三权分立,用西方的宪政体制代替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第二,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对许多问题都没加以论证,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解释,社会主义的建设只能靠每个践行者对马克思本人提出的一些思想的理解去实际把握。
《概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邓小平理论在理解上的以上种种不良现象,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笔者认为,首先,《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一生的研究都是围绕推翻资产阶级私有制所展开的,从实践上看,马克思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基于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至少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天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第二,共产党人享有和人民相同的利益,“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第三,共产党人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据此,《概论》理应体现这三条原则,只有如此,《概论》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再现,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论,任何背离马克思这些原则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质上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概论”,而且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的亵渎。从这层意义上看,我们必须认清,通常亵渎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那些不信仰众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人,而是把所谓众人的意见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任何背离人民主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都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玷污。其次,《概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在1882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里,针对俄国的具体情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国家都能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不断地发展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验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国情并不仅仅是属于“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说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测量国情,因此,中国的许多领导人也误判过中国的国情,如“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对中国国情的严重误判。以此为教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去理解和分析中国“真实”的国情。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概论》正是这种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成果体现。
二、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根源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曾表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被黑格尔解释得精妙、准确。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关系,其理论也就摆脱不了沦落为乌托邦幻象的命运。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史背景,马克思才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实际上,尽管有人评价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但并不能否认,马克思做到了一生都能够坚持将自己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渊源的历史维度出发,这种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出发点”,就应该、也必须是《概论》的立意依据,即现实生活世界是《概论》的根源所在。
现实生活世界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国情,用海德格尔的理论解释就是“实存”而非“此在”,即不能用简单的感性认识就可以把握的现存世界。首先,现实生活世界是人类世界,是赋予人的价值参与其中的世界。每个人都生活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世界作出自己的体认和改造,这种特有的实践方式的根据就是人的价值。只有把现实生活世界理解为赋予人参与的世界,才能区分开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从而实现理论思维与人类世界的本质统一,找到人能够“改造世界”的基本依据。然而,人类的思想史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遮蔽了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性,不仅把人存在的价值停留在以物质生活满足为主要目标的境界之中,而且对于人类寻求自身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阻碍。这样理解,我们就能够感悟和支持高尔基的观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其次,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时刻被人们否定着的世界,想抛弃的世界。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来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和阶层斗争的历史,不论哪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组织形式多么完善,都有着要被革命或改革的领域,因为人们不满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实际。面对这种现实,统治集团往往把原因归咎于人们的私欲、贪欲和不感恩等,至于现实生活世界主要是围绕统治集团的意志所运行,他们无意或有意间剥夺了他人的自由,统治集团并不去深究或予以忽视。总之,不论原因在哪里,迄今为止的现实生活世界都是要被革命或改革的现实,却是不争的事实。再次,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功能多样的整体性世界,知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真正认识其本来面目。之所以如此理解,是源于对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否定,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国家或民族改革中出现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与庸俗唯物主义有联系,即陷入了知性思维的误区之中。庸俗唯物主义是l9世纪开始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并在德国流行开来的思想观点,它把意识直接归结为物质,社会意识直接归结为社会存在,完全陷入机械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比如,法国的霍尔巴赫就认为,“让我们服从必然让我们听命于自然顺着自然给你划就的必然道路放心走吧”。最后,现实生活世界一个历史性范畴,是要被新的“现实生活世界”取代的暂时性世界。马克思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即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出发,现实生活世界就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动态的世界,它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追求新的合理状态。实践也证明,诸如所谓“千秋万代”的现实生活世界等观念,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概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围绕如何理解现实生活世界和解开现实生活世界之谜而展开的。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来看,马克思的理论学说都是根源于他所生活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对他那个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总结。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理论的初期是资本主义处于大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为了写作理论,他深人工厂、农村进行走访调查,密切注视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及其工人运动,与各个资本主义的理论代言者们进行论战。除了写作理论,他还亲自组织了工人协会,参与了工人国际协会,并且为工人运动的开始起草了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理论学说都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完成的,社会的各种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当前的社会实践来看,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处的现实生活世界所做的全面反省与本质概括。邓小平对现实世界全面反省的理论出发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姗。邓小平理论能够成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还在于邓小平理论完成了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处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概括。比如,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所做的深层次解答等。
三、超越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诉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十分重视,仅基本结构就先后变过多次,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解而来的,这一变革教材的形式无疑是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学生的影响。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统一起来,再加上“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的《概论》,同样是为了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实际需要。要真正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进”,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概论》本身具有吸引力。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和著作一经面世,立即被广为传播和争相传阅,没有任何的外在压力,即使马克思的敌人也不敢给以忽视。之所以如此,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但马克思的无私精神,使得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同样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吸引力。《概论》要实现这一本质性目标,就必须摒弃自己的理论只是为了对现实生括世界进行理论解释或理论总结的思维,而是要坚定地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前提,以超越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勇气构筑《概论》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因为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任何现存的现实生活世界并不是终极真理的社会形式。
首先,《概论》之所以能够超越现实生活世界,在于《概论》构筑的不是意见、建议或报告,而是理论及其体系。众所周知,“意见”、“建议”和“报告”可以有多种多样,可以随各人以及其他条件而变化,但“真理”却只能有一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意味着,不能将《概论》降格为意见、建议和报告。
事实上,现实生活世界降格《概论》尊严的思想从没有消失,有一些学者认为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把自己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装修队,即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注解。表面上看,这是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建设,事实上却难脱不积极参与其中、不敢承担责任之嫌。《概论》中的内容必须是真理,意味着《概论》涉及的一定是理论知识和具有严密的体系。因为只有理论研究才是实现通向真理的唯一合法性道路,这已经被许多思想家的论证所证实。比如,伽达默尔就认为,理论之所以具有通向真理的能力,是因为能从事理论活动的能力可以令我们“在某个事物上忘掉我们自己的目的”,即理论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局限性。这里所指的理论不是指现代科学异化了的“工具理性”,而是指能够让人们保持超越“现实”本身的一种崇高精神诉求,当然,这里的理论也不是脱离实践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世界文化概论范文第2篇
都是从"合理的"(rational)一词的具体运用入手,对表达以及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
的主体的合理性前提加以澄清。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合理性"这个概念具有个体
主义和非历史的特征,因而用处不大。
如果要对个人的合理性加以评断,仅仅追溯到这样或那样的表达上头,显然是远远不
够的。问题的关键毋宁说是在于,a或者b,或者任意一个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其行为是否
具有合理性,人们是否可以期望其表达具有充分的理由,以及其表达在认知层面上是否确
切或有效;在道德-实践层面上是否可靠或明智;在评价层面上是否深思熟虑或明白易懂
;在表达层面上是否真诚或具有自我批判精神;在解释学层面上是否可以理解;一言以蔽
之,在所有这些层面上是否具有"合理性"。从这些角度来看,如果出现一种超越不同互动
领域、跨越较长时间(甚至超越生活历史)的整体效果,那么,我们也就说存在着一种生
活方式(lebensfuehrung)的合理性。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文化前提所衬托出来的,
或许还不是个人所独有,而是集体所共有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性。
为了阐明合理化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个复杂的概念,我们将从交往理性概念
(begriff der kommunikativen rationalitaet)入手,对生活世界的结构加以研究;对
于个体和集体而言,有了生活世界的结构,也就有了合理行为的指南。当然,生活世界这
个概念是十分复杂的,因此,我在导论当中无法对它作出令人满意的阐述【71】。为此,
我转而先来讨论文化解释系统或曰世界观;文化解释系统或曰世界观,构成了社会群体的
背景知识,并且确保其各种行为取向之间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我想先来探讨
一下指导行为的世界观结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说那些分享这样一种世界观的人们应
当能够过上一种合理生活的话。我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会促使我们不得不从抽象
的分析转到经验的分析,并对世界观当中通过符号表现出来的合理性结构加以探讨;另一
方面,则会促使我们不能在未经检验的情况下就假定,决定现代世界观的合理性结构具有
普遍有效性,而必须从一定的历史角度对此加以考察。
我们想依靠"合理的"一词的具体运用来解释合理性概念,因此,我们必须把现代意识
结构当中的前理解(vorverstaendnis)当作分析的基础。至此,我们的前提一直都很简
单明了,亦即:意识结构表现在现代世界观当中,并隶属于一种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因而
从根本上确保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我们在使用西方世界观(okzidentales
weltverstaendnis)的时候,已经悄悄地给它添加了一种普遍性(universalitaet)要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普遍性要求的具体内涵,我们不妨把西方世界观与神话世界观作一
比较。在原始社会,神话所发挥的是一种典型的建立世界观认同的功能。与此同时,在我
们所接触到的文化传统中,神话又同统治现代社会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神话世界
观远远不能作为我们合理行为的指南。就上文所说的合理生活方式涉及到内容而言,神话
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之间形成一种对立紧张关系。因此,现代思维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揭示
出来的一些前提,在神话思维中肯定会有所反映。
可是,过去关于列维-布留尔(levy-bruhl)的"初民思维"【72】观点的讨论,却不
允许我们假定,"原始"思维是认识和行为的"前逻辑"【73】阶段。伊文思-普里查特(
evans-pritchard)对非洲桑给巴尔(zandes)部落的巫术信仰曾经做过非常出色的研究
,他的研究表明,神话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没有逻辑层面上的差别【74】。世界观合理性
的水平显然不是随着指引个人行为的认知发展而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承认,原始部族中成
年人基本上和现代社会成员一样,可以掌握同样的行为方式,尽管较高层次上的潜能在原
始部族那里不太经常表现出来,在运用过程中也比较具有偶然性质,也就是说,只限于较
小范围内使用【75】。世界观的合理性不是用逻辑学和语义学来衡量的,而是取决于个体
用来解释世界的基本概念。如果源于古希腊形而上学传统的"本体论"概念不会被压缩成为
一种特殊的世界关联,即与存在者的世界的认知关联,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谈一谈扎根在
世界观结构当中的"本体论"。哲学当中没有形成一个相应的概念,用以建立起与社会世界
、主观世界以及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就是要弥补哲学的这一缺失。
我想首先来概要地描述一下神话世界观。为了简单起见,我将仅限于讨论列维-斯特
劳斯的结构主义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戈德利尔(m.godelier)所强调的那部分内容为主
(1)。这样就可以把构成现代世界观的一些基本概念揭示出来,我们从直观上也就熟悉
了这些概念,从而也就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与上文所阐述的合理性概念接上联系(2
)。温奇(p.winch)在他的那篇富有挑战性的文章中对科学理性的常规特征作了讨论,
它将有助于阐明现代世界观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提出普遍性要求(3)。最后,我将采用皮
亚杰(j.piaget)的"解中心化"(dezentrierung)概念,来对进化论加以阐释;我们如
果想和韦伯一样,坚持世界观合理化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我们就会采用进化论的观点
。因为这个普遍的历史过程已经进入了开辟生活世界合理化道路的世界观当中(4)。
(1)戈德利尔所说的神话世界观的结构
我们越是深入到某种神话世界的解释网络当中,就越加强烈地感觉到原始思维的总体
性力量【76】。一方面,神话当中加工并保存了有关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的大量详尽的信
息,也就是说,神话当中存储着丰富的地理知识、天文知识、气象知识、动植物知识、经
济知识和技术知识、以及关于错综复杂的血亲关系、祭祀、宗教活动、战争等知识。另一
方面,这些经验的组织方式有些特殊,不是把任意一个现象的典型特征和其他现象相比拟
,就是把它们相对照。有了这种类似关系或对照关系(aehnlichkeits- und
kontrastbeziehungen),丰富多彩的观察就形成了一种总体性。
"神话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观照系统,使得人和世界的形象在其中永远相互映照,并
在自然和文化关系的多棱镜中不断分离和重叠……通过类比,整个世界获得了一种意义,
一切都变得很生动形象,并在符号秩序中表现了出来。一切实证知识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在
这个符号秩序中都显得完美无缺"【77】。
结构主义者对神话的这种综合能力的解释是:原始思维比较具体,它一般只看到世界
的表面,并用类比和对照的手法把这些感知归纳起来【78】。现象领域之间被划分为同质
和异质、等值和不等值、同一性和差异性等不同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世界
既丰富又空洞。类比化的思维把一切现象都网罗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相关网络中,但它的解
释并没有透过直观表象而进入本质。
直观思维的具体论(konkretismus)和类似、对照关系的建立等,是原始思维与发生
认识论阶段上的认知可以相提并论的两个方面【79】。相反,神话世界观的范畴或基本概
念源于经验领域,对于经验领域,则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一方面,血亲系统的
交互性结构以及家庭之间、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付出和获取的关系表现为一个可以反复
使用的解释图式:
"事实上,抽象的神话形象生活在其中的想象社会不断消失和复生,从而获得了一种
建立在血亲关系和结盟关系基础之上的组织形式,其来源既不是纯粹的思想原则,也不是
任意一种自然模式"。【80】
另一方面,行为范畴对于神话世界观具有一种构成意义。行为者与行为能力、意向与
目的的设定、成功与失败、积极与消极、进攻与抵抗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处理原始社
会基本经验的范畴:这是一种毫无戒备地把自己奉献给无法主宰的周围偶然世界的经验【
81】。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风险是在所难免的。这样也就有必要通过想象对偶
然性大潮加以遏制,也就是说,有必要加以澄清,尽管这样做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通过类比,那些产生和主宰人类自身之外的世界(自然)和人类自身的世界(文化
)的无形原因和无形力量也就具有了人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人类看来,它们的存在有
意识,有意志,有权威和有力量,一句话,它们是和人类相似的存在物;但区别在于它们
知道人类所不知的一切,它们能够做到人类所无法做到的一切,它们主宰着人类所无法主
宰的一切,结果就是它们凌驾到了人类头上。"【82】
如果我们对以下内容有所思考:即这些范畴从血亲系统当中反映出来的,可以用来解
释与超验力量之间的互动经验,但是,它们如何才能和直观类比思维的操作方法共同发生
作用呢,那么,我们就能对神话世界观当中众所周知的神秘-泛灵特征有更好的理解。我
们觉得,最最值得惊奇的是不同现实领域之间的那种独特的平均化:自然和文化被放到了
同一个水平上。自然和文化之间不断相互同化,一方面导致了自然的人格化,并进入社会
主体的交往网络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变得人性化了;另一方面则出现一种在一定
程度上自然化和物化的文化,它被吸收进了无名力量之间客观的相互作用当中。在文明人
看来,野性思维产生了双重错觉:
"……一种是对于自身的错觉,一种则是对于世界的错觉:之所以说一种对于自身的
错觉,是因为这种思维认为它所创造出来的理想物存在于人类之外,并且独立于人类,这
样一来,这种思维就在其世界观当中(自我)发生了异化;说是一种对于世界的错觉,则
是由于它用类似于人的想象物来装饰世界,这些想象物既能接受也能拒绝人的请求"。【
83】
根据这样一种世界观,任何一种现象经过神话力量的作用,都可以和其他一切现象发
生联系,这样不仅出现了一种运用叙事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且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在想象中
能够把握世界的实践。影响世界的魔术是人与世界、自然与文化等两种视角相互神秘作用
的逻辑结果。
在对神话思维的基本特征作出概要描述之后,我想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即这样的
世界观结构为何不能接受按照今天一般的标准来看堪称是合理的行为趋向(
handlungsorintierungen)。
(2)对象领域的分化vs 世界的分化
我们处身在某个现代生活世界当中;我们感到糊涂的是,在一个经过神话解释的世界
当中,我们无法或不能充分准确地把握构成我们世界观基础的那些分化。从涂尔干(e.
durkheim)到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家总是不断地指出,自然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独
特的模糊关系。这一现象我们暂时可以称之为两个客观领域的混淆,即:物理领域与社会
文化领域的混淆。神话不允许从基本概念上把物和人、可以操纵的对象与当事人,即我们
认为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明确地区分开来。如果神秘实践不能认识到目的
行为与交往行为、从一定的目的出发对客观环境的工具性介入与人际关系的建立之间有所
区别,就只能出现上述【物和人不分的】结果。目的行为在技术上或治疗上的失败原因,
可以归结为不够成熟(ungeschicklichkeit),而这种不成熟和违背现存社会秩序的错误
互动的道德规范罪责(schuld)属于同一个范畴;反之,从概念上讲,道德的失败和肉体
上的失败是一致的,罪恶和伤残是一致的,善则和健康、优越等是一体的。反过来看,世
界观的解神秘化,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非自然化。
这样一个过程在直观上是很容易理解的,通常用描述就可以解释清楚,但它并没有得
到深入细致的分析;它看上去似乎导致了自然和文化这两个客观领域在基本概念上发生了
分化。当然,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客观领域,就其自身而言,相互之间在范
畴上的区别取决于一个分化的过程,要想深入分析这个分化的过程,最好从人们对待世界
的基本立场出发。"力量"的神话概念和"诅咒"的巫术概念,完全阻碍了对待某个实存世界
的客观立场与对待某个受人际关系调节的世界的一致立场或不一致立场之间的分化。作为
客观领域,自然和文化属于事实世界,对此可以作出真实的陈述;但是,一旦我们要明确
给出物和人、原因与动机、发生与行为等相互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深
入到对象领域的分化过程当中,而且要深入到对待实存的客观世界的基本立场与对待社会
世界的基本立场之间的分化过程当中;在社会世界当中,可以合法地对有必要或有可能存
在的事物提出期望。我们要想在概念上把自然的因果关系与社会的规范秩序准确地区分开
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我们从观察或操纵转向遵守或破坏合法的行为规范时所完
成的视角和立场的转变。
不管如何,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模糊关系决不仅仅意味着,客观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在
概念上的混淆,而是也意味着语言与世界的分化,亦即意味着作为交往媒介的语言与语言
交往过程中达成共识的内容之间的分化;对于这种分化,我们缺乏深刻的感受。通过对神
话世界观的整体考察,我们看来很难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某个语言表达的符号根基、其语义
学内涵与言语者通过表达可以涉及到的符指(referent)十分准确地区分开来。名称与对
象之间的神秘关系,以及表达意义与表现事态之间的具体关系充分说明,内在意义关系与
外在实际关系完全混淆了。内在关系存在于符号表达当中,外在关系则存在于出现在世界
当中的实体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因与结果之间是一种内在关系,起因与效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是一种外在关系(物理上的因果关系vs.符号学上的因果关系)。神话世界观和
主宰世界的神秘力量可以相互紧密结合,因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在概念上是同一的。显
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现成的概念能用来表达,我们在符号表达中提出的非经验型的有
效性。有效性和经验效果互为前提。这里我们不能想到有什么特殊的有效性要求,因为神
话思维当中的不同有效性要求,诸如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和表现的真诚性等,根
本还没有分化开来。即便是有效性这个模糊的概念,也还没有完全从复杂的经验当中解放
出来;象道德性、真实性这样的有效性概念,和象因果、健康等经验秩序概念,是融合在
一起的。因此,语言建构起来的世界观和世界秩序本身是十分切合的,以致于无法看出它
是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容易出错并且可以批判检验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与文
化之间的模糊关系获得了一种把世界观具体化的意义。
语言交往以及贯穿在其中的文化传统表现为一种不同于自然和社会现实性的独立现实
,但前提是,形式的世界概念和非经验的有效性要求之间必须区分开来。今天,我们在交
往过程中的出发点是共同的假定形式(formale gemeinsamkeitsunterstellungen);这
些共同的假定形式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们,我们才会与客观世界当中所有观察者都能鉴
别的事物以及我们主体间所共有的社会世界中的事物发生关联。命题的真实性要求或者规
范的正确性要求,使得这些共同的假定形式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表达都具有实际意义。因
此,表达的真实性意味着,事态在客观世界中是实际存在的;在某个规范语境中适用于某
个行为的正确性意味着,人际关系作为社会世界的合法组成部分得到了认可。有效性要求
基本上是可以批判检验的,因为它们的基础是形式的世界概念。它们假定,所有观察者都
能够识别出来的世界,或所有成员共同分享的世界具有一种摆脱了一切具体内容的抽象形
式。此外,有效性要求相互都采取一种合理的立场。
提出有效性要求的行为者,必须放弃从内容上预先对语言与现实、交往媒介与交往内
容之间的关系作出判断。从形式的世界概念和普遍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出发,语言世界观的
内容必须同假定的世界秩序本身分离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化传统概念、一种
历史文化概念,并从中认识到,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解释以及对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
的意见和评价等是不断变化着的。相反,神话世界观禁止自然和文化在范畴上发生分裂,
因此,神话世界观不仅在概念上把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混淆起来,而且还使语言世界观具
体化,结果就是,世界概念充满了教条主义的客观内容,而没有了合理的立场以及对这种
立场的批判。
至此,我们所说的自然和文化混合形式中的自然,都是指外部自然或客观世界。现实
领域之间类似的混合也可以用来说明文化与内部自然或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内在世界或
主体性得以形成的前提是,为客观存在的事态建立一种外在世界概念,而且是一种客观形
式的世界概念,并且要为有效的规范建立一种社会世界概念。只有在客观世界的背景下,
通过可以批判的真实性要求和有效性要求的检验,意见的错误性、行为意图的盲目性、思
想的枉然性和想象性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在常规现实对象的背景下,通过可以批判的规范
正确性要求的检验,意图、愿望、立场、情感等的非法性、奇异性以及局部性和主观性才
能表现出来。由于神话世界观主宰着认知和行为取向,主体性领域看来是无法确定了。情
感同其常规的表达形式密不可分,同样,意图和动机同行为及其后果也是很少可以分开的
。就此而言,以下观点显得比较重要:原始社会的成员高度依赖神话所记载下来的详细的
集体知识以及宗教仪式的各种具体规定来确立他们自身的认同。他们很少拥有世界概念形
式,来确保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在不断解释文化历史传统过程中具有同一性;同样,个体
也很少具有可靠的自我概念形式,来确保个体在面对不断变化的主体性时能坚持其自我认
同。
在日常语言中,内在世界概念与外在世界概念是相互对称的;我们用日常语言就可以
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区别开来。当然,"世界"一词在这里容易引起误解。
主体性领域与外在世界之间相互补充;外在世界则有主体和其他主体共同分享。作为事实
的整体性,客观世界被假定是共有的,所谓事实是指,关于相应事态的存在的陈述"p"是
真实的。作为人际关系的整体性,社会世界也被假定是共有的,这里的人际关系在所有参
与者看来是合法的。主观世界则相应地构成了经验的整体性,而只有个体才能掌握这些经
验。当然,主观"世界"这种说法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所有参与者都共同假定,相对于
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而言,还可以区分出来一个非共有的领域。主观世界概念和它的互补
概念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这也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对基本立场和有效性要求作进一步的
探究,来对主观世界概念加以分析。
主体以放弃思想为代价,提出了自己的表现立场;从中可以看出,主体希望把这样一
种情感表达出来,即他愿意把他的主体性部分地暴露在其他人的面前。值得注意的是,这
样一种主体的表现立场,不同于操纵和观察事物的主体的客观立场,也不同于符合常规期
望的互动参与者的一致(或不一致)的立场。此外,我们也把表现性的表达和可以批判检
验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要求联系起来。因此,主观世界作为特殊的非共同领域,可以
包括在公共交往范围之内。
至此,我们从以下两个角度对神话世界观的"封闭性"进行了探讨,即:一方面是从对
待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基本立场缺乏区别的角度,另一方面则是从世界观缺
乏反思性的角度。这里的世界观不是通常所说的世界观,而是等同于文化传统。神话世界
观没有被相关成员看作是依赖于文化传统的解释系统;文化传统是由内在意义关系构成的
,通过符号和现实发生关联,并用有效性要求同现实保持着这种关联,因此,文化传统遭
到了批判,并且能够进行修正。这样看来,在原始思维那充满矛盾的结构中,实际上已经
具有了现代世界观的重要前提。当然,至于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可能具有的合理性是否不
仅反映了科学文化的特征,而且也提出了一种普遍性要求,这在其中还没有被具体涉及到
。
(3)温奇之后发生在英国的合理性之争
到了19世纪末,当人们开始对历史科学的基础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很现
实了。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讨论的焦
点是理解的客观性问题,伽达默尔对哲学解释学的研究是这场讨论的继续【84】。与此同
时,在历史主义问题名下,所讨论的主要是文明和世界观的独特性和可比性问题。这部分
的讨论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不是已告结束,而是刚刚开始【85】,因为当时对历史主义问
题还未能有充分的把握。此外,或许还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精神科学的对象领域,特
别是有文字记载,并经过文人加工的高级文化繁荣时期的证据并没有象神话传统、祭祀、
巫术等那样在下面的基本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冲突:即合理性标准(科学家本人至少在直观
上遵守这个标准)是否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提出普遍有效性要求。这个问题在文化人类学
中一开始就具有一种重要的地位;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又成了社会科学家和哲
学家的中心论题【86】。这场讨论是由温奇(p.winch)的两部著作引起的【87】。我在
这里只想对和我们的讨论有关的论证线索进行追述【88】。为了简单起见,我把这条线索
按顺序分解为六组支持和反对普遍主义立场的论据。这样的顺序当然和讨论的实际进程并
不一定吻合。
a)第一个回合还没有进入讨论的正题。卢克斯(steven lukes)先前就已经断定,
争论本身毫无必要:
"当我们发现一种信念是以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我应对它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
应当采用责备的态度,就是说,应把他当作关于信念的不合理的表达,并试图解释他们为
什么会被运用,他们是如何被用来躲避正当的批评的,以及他们的后果是什么等等。或者
,我应当宽厚地容忍这样的信念?从展示给我的假定开始,当假定的内容被充分理解后,
不合理的假定是否也会被解释为合理的呢?更主要地,这个问题是否可归纳为有两种可选
择的合理性标准呢?"【89】。
卢克斯假定,面对一种十分涩难解的表达,人类学家可以选择是否放弃从解释学角度
阐明其意义的努力。此外,他还断定,对于解释学程序的决定,是以接受或然的合理性标
准为潜在前提的。对于这两个观点,温奇可以用充分的理由加以反驳。
如果现有的非理性表达彻底拒绝分析,分析者自然可以转而借助于因果假设和原始条
件,比如,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对经验事件的发生这样一种难以理解的表达进行解
释。麦金太尔(a. macintyre)就持这样一种立场,并以此来反对图尔明【90】。在这样
一种研究策略中,卢克斯的论据是十分有力的;但是,从一种十分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讲
,卢克斯所坚持的或然性是不存在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符号表达要想得
到确认,就必须经过描述,而描述涉及到的是一个行为者的行为趋向(及其可能具有的原
因)。因此,分析者的唯一选择就是去考察,如果我们对行为者在其处境中的先决条件作
出解释,那么,一种并非一直模糊,但在某些具体方面比较模糊的表达是否会表现为不合
理性: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切都是他所做的。而且,从中我们应该领悟到,在他所掌握的
信念和准则与他在新的行动中所产生的信念和准则之间,是存在着不连续性和矛盾性的。
他的行动不仅与我们所确信的事物发生了矛盾,而且根据我们所知,也与他自己所确信的
相应事物发生了矛盾"【91】。
从值得追问的表达所假定的合理性出发,以便尽可能地逐步对其不合理性加以明确,
这对分析者来说并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仁慈问题,而是一种必须具备的方法。对于自身的
先决条件,只有解释学的严格性才能保证他不会在没有进行自我批判的情况下作出批判,
从而使他避免犯英国人类学家已经犯过,并曾经遭到温奇正确批评的错误,亦即人为地把
自己文化的一般合理性标准简单地套用到其他文化头上。
此外,正如卢克斯所认为的那样,这样一种方法论立场决不会导致一种关于不同理性
标准的前见的出现。如果分析者赞同某个行为者就其表达所给出或在合适的情况下所能给
出的理由,那么,他自身也就迈入了这样一个地步,亦即:他必须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
性要求表明立场,究竟是赞同还是否定。所谓好的理由,一般要看在历史(包括科学历史
)进程中不断变化的范畴而定。范畴是受语境限制的,根据这些范畴,处于不同文化中的
人在不同时期对表达的有效性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真实性、规范正确
性以及本真性等这些只是在直观上决定选择范畴的理念同样也受到语境的约束。通过解释
学来领会客观领域,并不能从肯定意义上来对此问题预先加以明确。相反,如果只是想对
意义理解问题追根究底,那么就必须从一种普遍主义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加以解答,而卢
克斯想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主义立场。对此,我还会进一步加以探讨。
b)伊文思-普利查德(evans-pritchard)对于非洲桑给巴尔部落的巫术、神谕以及
魔法等的研究是最好的例子,它充分说明,面对模糊表达,人们完全可以用解释学的关爱
,而不会得出卢克斯认为这种方法会遇到的相对主义结论。我想用伊文思-普利查德的论
据来介绍第二个回合的讨论。伊文思-普利查德对巫术崇拜以及相关魔法实践根由作出了
详细的解释,读者从中完全可以了解桑给巴尔部落世界观的内在本质。同时,作为人类学
家,他也坚持科学理性标准,并以此来对该部落的观念和技巧进行判断。伊文思-普利查
德区分了对桑给巴尔部落巫术信仰继续存在下去的逻辑要求和方法论要求,在我们看来,
关于自然的经验知识以及对于自然的技术干预都应当满足这些方法论要求;由此看来,神
话思维显然不及现代思维:
"科学概念是符合客观现实的,但既要考虑到前提的正确性,又要考虑到由命题得出
的结论……而逻辑概念是这样,按照思维推理的准则来看,如果它的前提是真实的,那么
它就一定是真实的;而前提的真实性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一只沙锅在烧的过程中坏了
,这也许要归罪于沙砾。让我们查看一下沙锅,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这就是逻辑的和科
学的思维。如果认为疾病是妖魔在作祟,一个人病了,我们就会按照语言来寻找谁是妖魔
。这就是逻辑的而非科学的思维"【92】。
这位人类学家分析了土著人的表达,他所涉及到的既是不同的表达,又是世界上的事
物。就第一个层面而言,他可以依赖两方面同样都适用的规则系统--直观上所把握的形式
逻辑的基本原理。而从世界关联层面来看,这位人类学家在遇到疑难的时候,必定会还原
到运用规则并没有问题的表达所处的层次。由此,他认为,所有参与者都从同一个实体性
的世界概念出发,因此,在具体情境下,土著人的感受以及他们对处境的分析或多或少和
他本人是一致的【93】。
但在这里,双方不能象逻辑学那样,把主体间普遍有效的解释规则的断言命题当作自
己的论证起点。围绕着命题的真实性以及干涉的有效性一旦出现不同的意见,人类学家就
必定会依靠验证的方法(pruefmethoden),这种方法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只有在经过科学
的改造之后,才会具有普遍有效性。起码我是这样来理解伊文思-普利查德的。
温奇则用源于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主义的语言概念来反驳伊文思-普利查德。温奇认为
,所谓"语言",就是语言所构成的世界观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中蕴藏着文化知识
,依靠文化知识,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又来分析各自的世界。每一种文化都用它的语言建立
起与现实的联系。因此,"现实"和"非现实","真实"和"不真实"等概念是所有语言都共有
的,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语言中有这些概念,而其他语言中则根本没有。但是,每
一种文化都在其自己的语言系统中对这些范畴加以区分:
"现实性并不是通过语言所感受到的东西。何谓真实、何谓虚假,是体现在语言所表
达的感觉中的。此外,真实和虚假间的区别、现实性的论点概念等都是属于我们(各自不
同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如果我们想理解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就必须研究这些概念在
语言中所起的真正作用"【94】。
可见,桑给巴尔人和人类学家所说的显然是不同的语言;人类学家为了分析必须付出
巨大的努力,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伊文思-普利查德本人指出,桑给巴尔部落的语
言表现出了一种独立的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一样,这种世界观也从范畴上对现实与非现
实进行区分,但是方式有所不同,并且明确观念与现实之间是否吻合,这和我们是一样的
。在温奇看来,假定两边都从同一个世界概念出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家没有权利用科
学理性作为标准,来衡量巫术信仰和魔法等。伊文思-普利查德之所以认为他有这个权利
,只是因为他从靠不住的假设出发:
"在科学论证自身范围外,"现实性"的概念必然被认为是可理解的和可接受的,因为
科学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而非科学概念之间却没有。尽管伊文思-普利查德强调指出
,按照桑给巴尔人所信奉的神秘观点看来,科学文化部分地具有不同的现实性概念。但是
,他试图把这种情况完全记录下来,加以明确区分,并最后加以阐明:在神秘的概念不起
作用的范围内,科学的概念是符合真实的现实性的"【95】。
c)第三个回合想揭示出温奇疑义的缺点之所在。但在此之前,我想先来说明其优点
。语言、由语言构成的世界观以及生活方式等概念,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因为语言、世界
观以及生活方式仅仅以复数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总体性:同一个文化中的成
员,其语言的界限就是其世界的界限。他们可以无限地扩展其生活世界的空间,但永远都
不会走出这个空间;因此,每一种分析同时也都是一种同化过程。由于不同的世界图景具
有总体性,尽管它们可以修正,但它们作为世界观的不同环节是不会消失的。因此,它们
就象是一幅画像,要求把整个人都表现出来。
画像既不是象地图一样的临摹(abbildung),可以用精确不精确来衡量,也不是象
命题一样的事态再现,能够用真和假来判断。画像呈现的不如说上一个瞬间,在此瞬间,
画像中的人有着独特的表现。因此,同一个人可以有若干幅画像;它们可以从完全不同的
角度来表现人的个性,而且同样都会让人觉得确切、真实或吻合。同样,世界图景也确定
一个基本概念的框架,在此框架内,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具体分析。和画像一样
,世界图景也很难用真和假来加以衡量【96】。
另一方面,世界图景和画像之间又有区别,主要表现为:世界图景可以促使个别表达
具有真实性。因此,世界图景具有一种真实关怀,尽管是间接的;温奇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由于具有总体性关怀,世界图景无法根据真值范畴作出有力的判断,甚至于选择用于判
断陈述真实性的范畴也受到世界图景抽象语境的约束,尽管如此,由此并不可以就认为真
实性观念本身具有特殊性。不管我们选择何种语言系统,我们的直观出发点总是:真实性
是一种普遍有效性要求。如果某种陈述属真,那么,不管它是用何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它
都能够获得普遍认同。因此,针对温奇的论点,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论据:我们不仅可以从
内在性、深刻性、经济性以及完善性等角度出发,也可以从认知的准确性角度出发,对不
同的世界图景加以比较。一种由语言构成的世界图景的准确性是这种语言系统能够给出的
真实陈述的一种功能【97】。
当然,温奇马上就会反驳认为,上述异议是一种认知主义的误解。语言建立起来的世
界观和社会化个体的生活方式,亦即社会化个体的日常实践是交织在一起的,具体表现为
不能把这些世界观还原为认识和支配外部自然的功能:
"语言游戏是由有生存能力的人所从事的--生存包含着广泛的、变化的不同利益,而
各种不同的利益又是彼此联系着的。正是如此,一个人在他所从事的活动中,说什么或做
什么,都会对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对其他人的生存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我们通
过研究其他的文化可能学到的,不是做事可能采用的不同方法,而是其他的技术。更重要
的是,可以了解到人类生活中可能产生的不同意识,以及关于一个人要完成的一定的工作
这种重要性的不同看法,从而试图把自己生存的意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仔细的思考"【
98】。
在世界观范围内,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就他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内容达成
理解。我们如果想把不同文化解释系统中的理性标准加以比较的话,就不能局限于我们的
文化所揭示出来的科学技术范畴,也不能把取得真实陈述和有效技术当作是合理性的标准
;各种世界观的相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都可以发挥意义。世界观揭示的是一切文化中永恒
的主题,诸如生和死,病和难,罪和爱,团结和孤独等。它们都可能是"人类生活意义的
源泉"。这样,它们便构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其价值有着差别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不
能被还原成奠定其基础的世界观的认知准确性。
d)尽管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在形式特征中反映出来,可
是,温奇用这个论据还是错过了许多核心内容。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会解释清楚,温奇
在什么地方错过了关键问题。世界观的认知准确性,亦即世界观中可能存在的命题的相干
性和真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计划的有效性等,在生活实践中同样也有所反映。温奇本
人接受了伊文思-普利查德的观点,认为桑给巴尔部落可以用巫术信仰来解释一些显而易
见的矛盾现象,比如两种咒语之间的矛盾,预言家的预言与实际事件之间的矛盾等等,但
他们的解释是有一定限度的。伊文思-普利查德用魔力的遗传观念为例,来讨论唯灵论世
界观的基本观点之间难免会出现的一些矛盾。他丝毫也不怀疑:如果让桑给巴尔人参与耐
力测验,他们一定会觉得这样做非常荒唐。但是,这样一种要求是被转嫁到他们头上的,
而不会从他们自身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如果是由于人类学家才使得他们面对这样一种要
求,这就充分说明他们缺少这样一种要求。可是,难道拒绝容忍矛盾的做法就意味着生活
方式具有非理性吗?难道我们无须认为仅仅靠排挤矛盾才能确定下来的行为取向具有非理
性?对此,温奇表示疑义。
温奇引用了伊文思-普利查德的如下观点,即:即便把上述问题明确地告诉桑给巴尔
部落,他们对此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理论兴趣:
"现在,我们有确切的理由来谈论作为思维出现的、超越桑给巴尔人思维的、高级的
欧洲人的推理,后者包含着一种矛盾性。但是他们并不想改变,甚至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
性。不过无论怎样,这种矛盾性是在欧洲的思想方式中被认可的。而桑给巴尔人的思维事
实上真的包含一种矛盾性吗?按照伊文思-普利查德的解释,一个桑给巴尔人是不会被迫
去思考关于在巫术中自己是否包含在矛盾性中的问题的"。【99】
温奇认为,如果桑给巴尔人已经有了自觉性,我还要他们坚持,那就不对了。他得出
了这样的结论:
"对歪曲理解负有责任的,是迷恋于把思考非自然产生的矛盾强加于桑给巴尔人的那
些欧洲人,而不是桑给巴尔人。这些欧洲人实际上是在制造一种错误的范畴"。【100】
巫术信仰不能和伪理论混为一谈;因为桑给巴尔部落是想用 资 信仰来把握世界进程
,与现代物理学家或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医生的客观立场不是一回事。
e)有人指责欧洲人类学家犯了范畴错误,这点可以从强弱两种意义上去理解。如果
这种指责仅仅认为,科学家不能把自己对于解释不确定性的兴趣强加给土著居民,那么就
会出现这样的反问,即土著居民缺乏理论兴趣的原因,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桑给巴尔部落的
世界观所确定的合理性标准不是那么十分严格,因而也就比现代的世界观缺乏合理性。由
此也就展开了第五轮的争论。
波普尔区分了"开放心灵"(offene mentalitaeten)与"封闭心灵"(geschlossene
mentalitaeten),以及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霍顿(r. horton)
则由此阐明了这样一种论据。他同意温奇的观点,认为虽然世界观的结构表现在生活方式
当中,但他坚持认为可以对世界观加以评判,评判标准如果不是其认知的准确性,便是工
具-认知的学习过程在何种程度可以得到促进或阻止:"要想进一步地获得知识,我们既要
有正确的理论,也要有对待这些理论的正确态度"【101】。霍顿和温奇所依据的几乎都是
伊文思-普利查德关于桑给巴尔部落非批判性立场的描述;但是,霍顿并没有把这种立场
还原到桑给巴尔部落世界观所特有的,原则上与科学具有同等价值的合理性那里。相反,
巫术信仰表现了一种结构,多多少少把桑给巴尔部落的意识与传统的解释盲目地联系起来
,从而使得其他解释意识根本无法出现:
"换句话说,对于创立的理论信条采取绝对接受的态度,从而缺乏选择的意识,也远
离了对之进行质疑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用强制的力量,把已确立的信条强加
于信徒。这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信条作为神圣的事物来进行论证时所具有的威力……在这里
,我们具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封闭的"态度--这种态度突出地表现为缺乏选择的意
识,认为信念是神圣的,并担忧任何对它们的威胁;另一种是"开放的"态度--这种态度突
出表现为具有选择的意识,不认为信念是神圣的,从而也不为它们担忧"【102】。
有了封闭性和开放性这一对范畴,世界观合理性似乎也就有了一个脱离语境的标准。
当然,这样一来,现代科学又成了问题的关键;因为霍顿认为,封闭世界观的"神圣"特征
,亦即保障认同的特征对于不同的解释具有免疫力,从而与作为现代科学精神典型特征的
学习潜力和批判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即便我们完全承认,学习潜力和批判能力决不是我们的文化所特有的,但仅仅根据是
促进还是限制知性来评判世界观,总还是片面的。在这点上,麦金泰尔和温奇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老练地、正确地对可能发生的事物表示质疑,用巧妙的方法对待他们,至
少我们就不会再犯弗雷泽的错误。因为当我们接触到自己意识中不同流派的言辞和行为时
,对显示出的礼仪和常规会提出"它是应用科学的一个分支吗?它是象征的和戏剧的行为
中的一个分支吗?或者它是一种神学?"等问题。事实上,这些向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可能会对答案产生误导……因为这些言辞、行为及疑问,可能属于我们意识中的一种类
型,或者根本不属于。对于那些按常规行事的人来说,根本不会出现如何来解释他们的言
辞或行为这样的问题。这里,"解释"一词是指把某种实践或言辞纳入某种先设的类型(而
不是某种象征性的欲望表达),对之进行阐释。如果我们问他们,他们的谚语将做如何解
释,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个直率的答案,但实际上,我们仍是受了欺骗。也许因为我们参与
了提出问题的活动,从而促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了这种方法,而不是其他的方法来解释他们
自己的言辞。但是,在我们提问之前,也许并非如此。也许在这段时间以前,他们的言辞
一向就是含糊其词的。神话一向被看作是潜在的科学、文学以及神学。然而,要把它们作
为神话来理解,实际上就不能把它们看作是科学、文学或神学。因此,说神话是对现实的
歪曲本身就是谬论。神话当然很可能歪曲现实,因为神话并不力求表现现实,它只是神话
"【103】。
霍顿从理论选择意义上来定义"封闭性"和"开放性"。他认为,一种世界观单纯只和外
在现实,也就是说,单纯只和客观世界中可以感知或上手的事物打交道,它就是封闭的。
霍顿把世界观和与它多少可以一致起来的现实加以比照,这表明霍顿认为理论结构是原始
意义上的世界观。可事实上,世界观的结构决定的是一种生活实践,这种实践在用认知-
工具态度与外在现实相处过程中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从宽泛意义上讲,世界观是沟通过程
和社会化过程的构成要素,在沟通过程以及社会化过程中,参与者打交道的对象包括共同
的社会世界秩序,各自的主观世界体验以及客观世界的进程。如果神话思维还没有从范畴
层面上把认知-工具的世界关联、道德实践的世界关联以及表现性的世界关联区分开来,
如果桑给巴尔部落的表达对我们来说充满了含混性,这就表明,我们不能仅仅根据面对客
观世界的立场来描述桑给巴尔部落的唯灵论世界观的"封闭性",也不能仅仅依据科学精神
的形式特征就认为现代世界观是"开放的"。
f)这样的反驳已经完全偏离了温奇的论证路线;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要动摇,而是要
更加巧妙地维护普遍主义立场。因此,普遍主义立场在第六回合和最后一个回合可以说是
有了长足的发展。格尔纳也警告说,霍顿用"理论选择的意义"范畴来把握世界观和生活方
式的封闭性和开放性,这样做视野过于狭隘了【104】。霍顿所提到的现象,甚至根本就
不适用,它们需要有一种更加复杂的关系系统,可以包容三个形式世界概念在相同时间内
的分化。
霍顿和格尔纳(e. gellner)的观点【105】与形式语用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在
上文,我就是用这种形式语用学的观点来阐述神话世界观的封闭性以及现代世界观的开放
性的【106】。他们两位一起用诸如"复杂的动机与简单的动机"以及"认知的高级分工与低
级分工"等关键词,来描述范畴层面上越来越明显的分化,包括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
主观世界之间的分化;认知-工具问题、道德实践问题以及表现问题之间的分化;特别是
可以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不同有效性之间的分化。接着,霍顿和格尔纳又强调,语言世界
观与现实之间有加速分化的趋势。他们根据诸如"对待语词的巫术态度与非巫术态度"以及
"实际的理想与理想的理想"等,来对不同的方面加以了探讨。所谓"实际的理想"与"理想
的理想",是一种标志,涉及到的是内在意义和外在关系的分化问题,格尔纳后来又称之
为"特殊规范的价值"。最后,"反思性思维"与"非反思性思维"之间的对立问题涉及到"第
二等级的知性活动";这些"知性活动"不仅使得象数学、逻辑学以及语法学等形式科学成
为可能,而且也使得我们可以从系统角度和形式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不同的符号系统。
但是,世界观不仅对于沟通过程具有构成意义,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构
成要素。世界观发挥的是建立和保障认同的功能,为此,它赋予个体以基本概念和基本立
场。如果不侵犯到个体以及社会的认同,这些基本概念和立场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种保
障认同的知识在从封闭世界观向开放世界观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形式化;它所依赖的结构也
越来越没有需要加以修正的内容。格尔纳认为,现代思想浓缩成为一种形式定量依靠的是
"稳定的制度"(entrenched constitutional clauses):
"如果我们按照固有而神圣的规定进行划分,野蛮人与现代人思想体系间就存在着系
统的差别。在传统思维体系中,神圣的或决定性的因素更多、更混乱分散和更普及。而在
现代思维体系中,神圣的或决定性的因素则较少,范围也较窄,因为这些因素建立在易于
理解的基础上,更为简洁,而不至于扩散到具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一些体系是上天决
定的,或来自于别的什么。,不少生活结构和社会信念是依据神圣的和固有的信条起作用
的"【107】。
霍顿把这种发展过程归结为"保护性立场与破坏性立场之间的对抗",并由此认为禁忌
是一种制度,一旦频繁出现不协调的经验,基本区别快要受到威胁,禁忌就对世界观的范
畴基础加以捍卫【108】。
我们如果从形式语用学的角度,对霍顿和格尔纳关于波普尔的"封闭性"与"开放性"概
念的理解加以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一种视角,来阐明温奇对于科学理性假设的怀疑,
以免得出草率的结论。科学理性属于一种复杂的认知-工具理性,它的确要求超越具体的
文化语境,具有普遍有效性。但在我们对温奇的观点加以讨论和批判之后,就会发现,温
奇有一股激情,而这是我们所没有的:
"现在,我的目标并不是从道德上进行解释,而是确定"学习"这个概念,在研究其他
文化时,是与博学这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09】
我们这些现代社会中的人难道不能从其他生活方式,特别是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当中学
到一些东西?难道我们不应注意到--我们不能把以往阶段浪漫化,也不能把陌生文化异国
情调化--现代化的独特途径所带来的巨大损失?霍顿也认为这个问题决非毫无意义:
"作为一位科学家,当他把传统的非洲思维与科学的思维进行比较时,他或许就会感
到非洲思维是贫乏的,有局限的。我认为,这种印象的产生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
人,我选择生活在一种仍然是强烈的传统式的非洲文化中,而不是生活在一种有西方科学
化倾向的亚文化中。这是为什么呢?这里可能有许多可疑的、不祥的、没有公认的论据。
但是发觉生活在传统文化中肯定是一个理由。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思维中,就有一种
强烈的诗意的成分和一种真实的享受,就是说,具有一种用追求纯粹的感情和进步的信仰
来摆脱复杂的西方生活方式的享受"【110】。
从"追求动机的纯洁性"一词当中还能看到世界概念与有效性之间的分离,而这是现代
世界观的源头。霍顿在他的注解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这些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多么的重
要;但是,如果他们疯狂发展,以致于超越了它们的极限,那么,它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灾
难!",这样,他就从自我批判的角度强调了自己的普遍主义立场。西方文化的固有特征
不是科学理性本身,而是科学理性的假设,它表明的是一种文化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的模
式,助长了认知-工具理性不仅在与外在自然相处过程中独占鳌头,在世界观和日常交往
实践中也占据着垄断地位。
我们或许可以把论证过程归纳如下:一方面,温奇的论据不够有力,不足以支持这样
一个观点,即任何一种语言世界观和文化生活方式当中都蕴藏着一种独特的合理性概念。
另一方面,他的论证策略又很有力,足以证明现代世界观中表现出来的合理性具有一种普
遍性的要求,并足以反对从非批判的角度认为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就在于对外在自然的认识
和征服。
(4)世界观的解中心化(皮亚杰) --生活世界概念导论
英国的合理性争论得出结论认为,一般的合理性结构虽然为现代世界观奠定了基础,
但现代西方社会所带来的却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理性观,它专注于认知-工具方面,因而具
有片面性。最后,我想把这样一种理性概念的一些内涵揭示出来。
如果从形式语用学所确定的封闭-开放模式可以断定世界观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我
们就可以认为世界观的结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对此,不仅可以从心理学、经济学,或社
会学等角度,也就是说,借助于外部因素予以澄清,同样也可以用内部可以重构的知识增
长来加以说明;而且同时也可以看作是问题的解决,因为根据内在的有效性前提,我们就
可以作出全面的估价。普遍主义立场导致了一种起码具有纲领性质的进化论观点,认为世
界观的合理化是通过学习过程而得以实现的。这决不意味着,世界观的发展必定是直线性
的,或者象唯心主义因果性那样直截了当。发展动力问题在这个观点中并没有预先得到明
确。如果我们想把不同结构的解释系统之间的历史转变理解为学习过程,那么,我们就必
须满足于要求对意义关系作形式分析,因为这种形式分析允许我们把世界观的经验排列当
作是一系列的学习步骤而加以重构,而且,在参与者看来,这些学习步骤是非常井然有序
的,主体之间可以相互检验。
针对温奇(peter winch),麦金泰尔(macintyre)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些认知的发
展必须被解释为非连续性的跳跃形式:
"我谈到那些从一种信仰体系到另一种信仰体系的演变,有必要提出温奇所否认的这
类问题来加以鉴定。例如,在17世纪的苏格兰,是不可能提出"有没有巫术?"这种问题的
。如果温奇问,在什么社会生活方式内,在什么信仰体系下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那么,
唯一的答案是:问题是由处于另一文化体系,并且有能力遵循独立的评判标准的人们提出
的。许多非洲人今天还处于类似的状况"【111】。
当然,麦金泰尔的这一异议反过来又给他的普遍主义立场背上了论证的负担。根据麦
金泰尔的普遍主义立场,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家如果不把促使神话向普世宗
教转变,或促使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向现代世界观转变的学习过程(大体上)重构出来,
他也就无法认真领会桑给巴尔部落的巫术信仰,甚至也无法认真领会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件事【112】。
在第二章里,我将根据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尝试从形式世界概念的形成这一理论出发
,来把握宗教世界观的发展,也就是说,把宗教世界观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学习过程。在这
一点上,我将使用一种皮亚杰用以阐释意识结构个体发生学(ontogenese)的学习概念。
众所周知,皮亚杰区分了认识的不同阶段,各个阶段不仅内容翻新,而且学习能力的结构
和水平也有所改变。在出现新的世界观结构时,情况也是如此。神话思维方式、宗教-形
而上学思维方式以及现代思维方式之间的突变(zaesuren)表现为基本概念系统不断发生
变化。不管已经被克服的阶段内容如何丰富,对它的解释都随着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而失
去其范畴价值。不再让人信服的不是这个理由或那个理由,而是这种理由或那种理由。解
释和论证传统的力量的降低,在原始文化中表现为神话-叙事思维方式的退化,在现代则
表现为宗教思维方式、宇宙学思维方式以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退化。这样一种贬值的动
因似乎与向新的学习水平过渡有着联系;这样,无论在客观思想中,还是在道德-实践认
识中或是在审美-实践的表达中,学习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皮亚杰的理论不仅可以用来区分结构性的学习(strukturlernen)和内涵性的学习(
inhaltslernen),而且也可以用来理解涉及到整个世界观的发展过程;所谓涉及到整个
世界观,意思是说,发展同时波及到世界观的不同层面。严格意义上的认知发展牵涉到思
想和行为的结构,而这些结构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积极介入外部现实,亦即介入客观
世界而获得的【113】。
但是,皮亚杰从"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形成"的角度来追究认知的发展过程;这样慢
慢地就会在"客观世界的结构与主观内部世界的结构之间做出一种区分"【114】。个人在
成长过程中通过与对象以及自己的相处,而同时获得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概念。这里,
皮亚杰把与物理世界以及社会世界的关系区别了开来,也就是说,"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同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区分了开来"【115】。外部世界也就相应地
分化为可以感知和可以把握的对象世界,和可以规范调节的人际关系世界。与外部自然的
关系是靠工具行为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使得人们能够积极获得"智性的规范系统",而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则为人积极习得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系统"铺平了道路。学习机制,
即适应能力以及调节能力,在这两种行为方式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如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这两种行为方式加以,那么,个别主体之间的任
何一种相互作用无疑也会对它们。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自成一个整体,并且通过对
个体的精神结构加以转化而获得新的特征"【116】。
所以,皮亚杰得出了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认知,它不仅是一种外在宇宙的结构,而且也
是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同时分化的关联系统的结构。认知的发展一般来说就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解中心化。
只有在三个世界的形式关系系统彻底分化开来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一种反思的世界概
念,合作者为了共同解释所处语境而运用的媒介才能把握住世界。主观世界概念使得我们
把自身的内在世界以及他者的主观世界与外部世界区别开来。自我可以思考,一定的事实
(即他所说的客观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事态),或一定的规范期待(即他所说的共同所有的
社会世界的合法部分),也就是说,从他者的视角来看,作为其主观世界的组成部分,是
如何出现的;他还可以继续思考,他者本身在思考他所说的实际事态和有效规范在自我的
眼里,也就是说,作为自我主观世界的组成部分,是如何形成的。参与者的主观世界或许
只是客体、规范以及其他主体任意用来反映自身的一面镜子。但是,形式的世界概念的功
能恰恰在于阻止共性的组成部分在相互比照的主体性隐遁之后烟消云散;并且使得第三者
或非参与者的视角能够被共同接受。
任何一种沟通都可以说是主体间为了相互承认语境而相互合作解释过程的一个部分。
三个世界概念在其中充当的是共同设定的协调系统,其中的背景井然有序,以便参与者能
够达成共识,并可以把这种共识当作事实或有效规范以及主体经验加以对待。
在这里,我首先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用来作为沟通过程的相关概念。交往行为的主体
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些背景
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但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疑难。这样一种生活世界背景是明确参与
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通过解释,交往共同体的成员把客观世界及其主体间共有的社会世
界与个人以及(其他集体)的主观世界区分开来。世界概念以及相关的有效性要求构成了
形式因素,交往行为者可以用它们把各种需要整合的语境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明确的生活世
界协调起来。
生活世界里储存着前代人所做出的解释努力;任何一次的交往过程都存在着异议的风
险,相对而言,生活世界则构成了保守的均衡力量。因为交往行为者只有通过对可以批判
检验的有效性要求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才能相互达成理解。随着世界观的解中心化,
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储存文化知识的世界观越是解中心化,就越是难以一开
始就用一种可以批判解释的生活世界来满足交往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如果越是必须用参与
者自身的解释活动,亦即一种由于具有合理动机,因而充满风险的共识来加以满足,我们
也就越是希望行为能具有合理的取向。因此,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会表现为"规范共识
"与"交往共识"的冲突。文化传统越是预先决定,哪些有效性要求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
必须被某人接受或必定遭到某人反对,参与者本人也就越是没有机会对他在采取肯定或否
定立场时所提供的充分理由加以阐明和检验。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文化解释系统,就会看得很清楚,神话世界观为何会表现
为一种特殊情况,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由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世界都可以用神话世
界观来加以解释,因此,单个成员就被卸下了解释的负担,当然同时也失去了达成批判共
识的机会。只要皮亚杰所谓的世界观还以社会为中心(soziozentrisch)【117】,客观
存在的现实世界、有效的规范以及具有表达能力的主体之间就不会出现分化。语言的世界
观成为了一种世界秩序,而不是一种可以批判检验的解释系统,能够让我们一览无余。在
这样一种主导系统里,行为根本无法触及到批判领域,而在这个批判领域里,交往共识取
决于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独立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
由此可以看出,要想使一个得到相应解释的生活世界具有合理的行为取向,甚至要想
让这些行为取向能够凝聚成为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就必须具备以下形式特征:
a)文化传统必须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准备好形式概念,必须允许有
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存在,比如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主观的真诚性等,并且必须
促使基本立场有相应的分化,比如客观立场,规范立场以及表现立场等。只有这样,才能
在一种抽象的水平上创造出符号表达;这些符号表达不仅有着不同的理由,而且可以得到
一种客观判断。
b)文化传统必须与自身保持一种反思的关系;它必须彻底放弃其教条,以便让传统
的解释能够接受人们的考问,并加以批判和纠正。这样,意义的内在联系才能得到系统的
处理,不同的解释才能在方法论层面上得到探讨。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第二等级的认知
活动,如:客观思想领域里出现的通过假设建立起来并经过论证的学习过程,以及道德实
践观点和审美感受等。
c)文化传统必须把它的认知部分和评价部分与特殊的论据重新紧密地结合起来,以
便相应的学习过程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得以制度化。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就会出现科学、道
德和法律、音乐、艺术和文学等文化亚系统,也就是说,可以形成不同的传统。这些传统
不但经过牢靠的论证,而且还经受住了不断的批判,最终才得以稳定下来。
d)最后,文化传统还必须这样来解释生活世界,即让目的行为能够摆脱通过交往不
断更新的沟通命令,以实现至少能够局部地与交往行为区别开来。这样,一般化的目的就
有可能具有一种目的行为的社会机制,也就是说,合理的经济活动和合理的行政管理就有
可能具有一种受到金钱和权力控制的亚系统结构。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马克斯·
韦伯认为,c)和d)所说的亚系统结构是价值领域的分化,对于韦伯来说,这些价值领域
构成了现代文化合理化与现代社会合理化的核心。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根据皮亚杰的解中心化概念,来揭示世界观的结构、作为交
往背景的生活世界以及合理生活的可能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还是会遇到交往理性概念
。交往理性概念把解中心化的世界观与话语兑现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可能性联系
了起来:
"论证的合理性"并非像温奇、麦金太尔、卢克斯以及其他人所阐述的那样,是"最"底
限度的合理性概念意义上的一个合理性的"合理"概念。这种最底限度的合理性概念,是在
没有矛盾的情况下由法律派生出来的,并无法以假设连贯的形式表达出来。现在,"论证
的合理性"不仅仅是表示一个特殊的"附加"在最底限度的合理性标准之上的合理性标准,
而且作为同样的、特有的合理性标准,在古老的巫术或现代的经济体系中都是有效的。"
论证的合理性"明确表示(a)非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发展中的一种独特的支配不连贯、
矛盾和分歧的方法,以及(b)一种形式上的通过一个"界定的"、"实体的"合理性标准起
作用的方法,而这种实体性合理性标准又是卢克斯所认为的由一个最底限度的合理性标准
派生出来的【118】。
魏尔默(wellmer)认为,这样一种合理性概念已经相当复杂,足以把温奇的合理疑
虑作为问题接受过来,无论是他对于现代理性片面的认知工具解释的怀疑,还是他为了把
握现代自我理解的局限性而向其他文化学习的动机,都在接受范围之内。
如果我们象理解解中心化概念那样来理解自我中心主义(egoismus)概念,并且认为
,自我中心主义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会不断地翻新,那么,系统谬误的阴影就会笼罩着学习
过程【119】。于是,结果或许会是这样:随着世界观的解中心化,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幻
想,以为客观世界的分化意味着把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从合理的交往领域中彻底驱除出去
。
对于这样一种物化幻想,我们还会进一步加以探讨。现代的一个附带谬误是乌托邦主
义(utopismus)。乌托邦主义认为,我们从解中心化的世界观概念以及程序合理性概念
当中,"同时也可以得到一种理想的合理生活方式"【120】。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由世界观
构成的--从结构角度,我们可以根据解中心化的程度对世界观加以分类;也不仅仅是由属
于公正领域的制度构成的。温奇有理由坚持认为,生活方式是具体的"语言游戏",包括日
常实践组成的社会结构、集体认同、文化解释模式,社会化形式、潜能、立场等。试图从
特定的合理性角度,对这样一个综合体,即对生活方式的总体性做出判断,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不想放弃我们用以判断一种生活方式的成败得失的标准,健康与疾病或许是一
种的典型情况。我们根据规范标准对生活方式和生活历史一起做出判断,但规范标准不允
许我们进一步接近理想的临界价值(grenzwerte)。我们不妨换一种说法,称之为相互需
要补充的环节之间的一种均衡,认识、道德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一种和谐。
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给出一种好生活观念的等价物,不过,不允许根据程序合理性概
念(程序合理性概念给我们留下的只是解中心化的现代世界观),推导出一种好生活的观
念:
"因此,我们只能给出一种合理生活的具体形式前提--如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普遍
主义的法律,已经具有反思性的集体认同等;但是,只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具有实质意义的
合理生活的可能性以及具有实质意义的合理认同的可能性,就不存在用形式结构可以描述
出来的理想的临界价值;相反,有的是追求好生活的成功与失败,在追求过程中,个体的
自愿认同与个体之间的主动接受共同构成了一种可以体会到的现实性"【121】。
当然,尽管魏尔默提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合理生活"概念,他也并没有回过头来追溯
具有实质意义的合理世界观的抽象性。但如果必须放弃这一点,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对
与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有着双重联系的立场加以批判了。双重联系表现为:对其传统的
贬低以及对片面的认知工具理性的臣服【122】。
如果可以证明,世界观的解中心化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社会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的
话,那么,交往理性的程序概念自然也就能够作为这样一种批判的基础。只有把理想的生
活方式所具有的高度完善的交往基础与现实生活方式的历史特征混淆起来的做法,才具有
空想主义的味道。
注释:
71,请参阅本书第二卷,第182也以及下两页。
72,列维-布留尔(l.levy-bruhl):《原始思维》(la mentalite primitive),
paris,1922。
73,卡西尔(e.cassirer):《符号形式的哲学》(phli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bd.ii:《神话思维》(das mythische denken),darmstadt,1958;r.
horton,levy-bruhl,durkheim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r.horton,r.
finnegan(eds.),models of thought,london,1973,第249页以及下两页。
74,e.e.evans-pritchard,witchcraft,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xford,1937,frankfurt am main.1978。evans-pritchard在其《论列维-布留尔的原
始思维理论》(levy-bruhl"s theory of primitive mentality,bulletin of the
faculty of arts 2,1934,第1页以及下两页)一文中对列维-布留尔有如下批评:"我们
认为,下雨仅仅是由于气象原因造成的,而在野蛮人看来,上帝、神灵或巫师都会唤风呼
雨。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我们的大脑在功能上和野蛮人的大脑有所不同
……这个结论我不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推论得出来的;事实上,我对雷雨天气知之甚少。
我只是接受了我们社会中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这就是下雨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野
蛮人则相应地认为,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巫术条件下,巫术手段对下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野蛮人这样认为,并不能说他们就欠聪明。他们这样认为,并不是他们自己观察和推论
的结果 ,而是他们接受过来的文化遗产,这和他们对其他文化遗产的接受方法没有什么
不同:也就是说,他们是其文的产物。我们的思维模式都是我们所处社会提供给我们的。
认为我们对下雨的看法是科学的,而野蛮人对下雨的看法带有神话色彩,是毫无意义的。
两种观点都伴伴随着心智过程,同样都具有思想内容。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我们对下雨
的看法具有科学的社会内容,并且和客观事实是吻合的;而野蛮人的观点则具有非科学的
社会内容,因为它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只要它承认存在超感官的力量,它就具有神话色
彩" 。转引自:基彭贝格(h.g.kippenberg):《关于理解他者思维的争论》(zur
kontroverse ueber das verstehen fremden denkens),载卢克西(b.luchesi)【编
】:《巫术论》(magie),frankfurt am main,1978,第33页以及下两页)。
75,m.cole,j.gay,j.glick,the cultural concept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n.y.,1971;p.r.dasen,cross-cultural piagetian research,载:j.cross.
cult.psych.,1972,第23页以及下两页;b.b.lloyd,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harmondsworth,1972。
76,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结构人类学》(strukturale
anthropologie),bd.i,frankfurt am main.,bd.ii,frankfurt am main.,
1975;及其:《野性思维》(das wilde denken),frankfurt am main.,1973;此外
还有:w.lepenies,h.h.ritter(hrsg.):《野性思维的定位》(orte des
wilden denkens),frankfurt am main,1970。
77,戈德利尔(m.godelier):《神话与历史》(mythos und geschichte),载:埃德
(k.eder)(hrsg.):《阶级社会的形成》(die entstehung von
klassengesellschaften),frankfurt am main,1973,第301页以及下两页;此处引文
请参阅第316页。
78,关于野性思维的类似特征,请参阅s.j.tambiah,form and meaning of magical
acts,载:horton,finnegan,(1973),第199页以及下两页。
79,j.piaget,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london,1930。
80,godelier,(1973b),第314页。
81,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了这一动机,请参阅其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1922。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只有在知识不够用,理性方法达到极限的情况下,
trobtiand archipel的渔夫才使用巫术,请参阅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巫
术论》(magie,wissenschaft und religion),frankfurt am main,1973。
82,godelier,(1973b),第307页。
83,godelier,(1971b),第308页。
84,伽达默尔(h.g.gadamer):《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
tuebingen,1960。
85,特洛尔奇(e.troeltsch):《历史主义及其问题》(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tuebingen,1922;曼海姆(k.mannheim):《历史主义》(
historismus),载:《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uer sozialpolitik),第52期,
1924,第1页以及下两页;及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bonn
,1929;关于整个背景情况,请参阅吕森(j.ruessen):《一种更新的历史学》(fuer
eine erneuerte historik),stuttgart,1976。
86,b.r.wilson(ed.),rationality,oxford,1970;horton,finnegan(eds.)
,1973;k.nielsen,rationality uand relativism,载:philo.soc.sci.,6,
1974,第313页以及下两页;e.fales,truth,tradition,rationality,载:phil.
soc.sci.,6,1976,第97页以及下两页;i.c.jarvie,on the limits of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in anthropology,curr.anthr.,1976,第687页以及下两页;r.
horron,professor winch on safari,arch.eur.soc.,17,1976,第157页以及下两
页;k.dixon,is cultural relativism self-refuting?brit.j.soc.,1977,第
75页以及下两页;j.kekes,rationality and social science,philos.soc.sci.,
9,1979,第105页以及下两页;l.hertzberg,winch on social interpretation,
philos.soc.sci.,10,1980,第151以及下两页。
87,p.winch,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london,1958;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66;及其understanding a primitive society,wilson,1970,第78页以及下
两页。
88,这里,我参考了th.a.mccarthy,the problem of rationality in social
anthropology,stony brook studies in philosophy,1974,第1页以及下两页;及其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ergen habermas,cambridge,1978,第317页以及下两页;
魏尔默(a.wellmer)的未刊讲稿对我启发颇大,在此深表感谢:a.wellmer,on
rationality,i-iv,1977。
89,st.lukes,some problems about rationality,载:wilson,1970,第194页。
90,a.macintyre,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载其:against the self images of
the age,london,1971,第211页以及下两页;及其rationalit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action,同上,1971,第244页以及下两页。
91,macintyre,1971b,第251页以及下页。
92,引自p.winch,载:wilson,1970。
93,m.hollis准确地描述了这些形式共同性假设的地位,请参阅其: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载:wilson,1970,第214页以及下两页。
94,winch,载:wilson,1970,第82页。
95,winch,载:wilson,1970,第81页。
96,我要感谢罗蒂(richard rorty)把帕特里克·伯克(patrick burke)的《真理与世
界观》(truth and worldviews,1976)提供给我,这部著作提出的这个比喻显然受到了
魏特根斯坦的启发:"世界观,像图景,是一些"观察到的"事实。当我们成功地看到一些
事物或其他事物的总体概要时,我们就掌握了一种世界观。我们没有必要举出各种信息的
全部数据。因此,从某种感觉来讲,一种世界观一定包罗万象;但从另一种感觉来讲,则
并非如此"(手稿,第3页)。
97,我曾经把这样一种"准确性"范畴用来揭示具有理论意义的语言系统,请参阅j.
habermas,(1973c),第245页以及下两页。
98,winch,(1970),第105页以及下页。
99,winch,(1970),第92页。
100,winch,(1970),第93页。
101,r.horton,african thought and western science ,载:wilson,(1970),第
153页。
102,horton,(1970),第154页以及下页。
103,a.macintyre,(1971c),第252页以及下页。
104,e.gellner,the savage and the modern mind,载:horton,finnegan,1973,
第162页以及下两页。
105,以下内容,请参阅horton,(1970),第155页以及下两页;和gellner,1973,第
162页以及下两页。
106,参阅上文第85页。
107,gellner,(1973),第178页。
108,horton,(1970),第165页:" 也许禁忌在传统的非洲文化中所产生的最主要的副
作用就是乱伦。乱伦是对确定的范畴体系进行明目张胆的挑战的一种行为。因为如果一个
人把母亲、女儿或姐妹当作妻子来对待,他就犯了罪。禁忌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多胎的
诞生。在这里,这个范畴包括与动物相类似的人类的多产。禁忌的另一个非常普遍的目的
,就是使死人作为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东西统治非人的土地。平等而广泛的禁忌是这样的
人体的排泄物,像粪便和经血,统治着同样的在生命和无生命间的非人的土地。禁忌的副
作用常常是在最陌生的东西或新生的事物之中发生的;而这些是不会在已确立的范畴中发
生作用的"。
109,winch,(1970),第106页。
110,horton,(1970),第170页。
111,macintyre,(1971b),第228页。
112,由此看来,欧洲现代发轫之初盛行的巫术信仰也可以说是认识上的倒退。关于这方
面的内容,请参阅r.doebert,the role of stage-models within a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illustrated by the european witchcraze,载:r.harre,u.j.
jensen(eds.),studies in the concept of evoution,brighton,1981。
113,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大纲》(j.piaget,abriss der genetischen
epistemologie,olton,1974)对此有概要论述;此外还有j.h.flavell,th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f jean piaget,princeton,1963;h.g.furth,
piaget and knowledge,chicago,1981;b.kalplan,mediatation on genesis,hum.
development,10,1967,第65页以及下两页;n.rotenstreich,an analysisi of
piagets concept of structure,philo.phenm.res.,37,1977,第368页以及下两页
。
114,皮亚杰(j.piaget):《认识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erkennens),第
3卷,stuttgart,1973,第179页。
115,piaget,(1973),第190页;请参阅j.m.broughton,genetic metaphysics,载
:r.w.rieber(ed.),body and mind,new york,1980,第177页以及下两页。
116,piaget,(1973),第190页。
117,piaget,(1973),第229页。
118,wellmer,iv,ms,第12页以及下两页;亦请参阅k.o.apel,the common
presuppositions of hermeneutics and ethics,载:j.baermark(ed.),
perspektives on metascience,goeteborg,1980,第39页以及下两页。
119,爱尔金德(d.elkind)从个体发生的角度对自我中心主义各个阶段的特殊形式曾经
作过详细的描述,请参阅其:《青春期阶段的自我中心主义》(egozentrismus in der
adoleszenz),载:丢伯特(doebert),哈贝马斯(habermas),温克勒(
nunner-winkler)(编):《自我的发展》(entwicklung des ichs),koeln,1977,
第170页以及下两页。请参阅第177页以及下页的概述:"在婴儿阶段,自我中心主义表现
为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对象与自己的感知是一致的;随着符号功能的养成,这种形式的自
我中心主义能够得到克服。在学龄前阶段,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为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符号
包含着和它代表的对象相同的信息。随着动手能力的养成,儿童可以区分开来符号与所表
现的对象,这样也就可以克服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少年阶段的自我中心主义认为,自
己的思想观念对应的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感觉现实。随着形式-操作性思维能力的养成以及
提出反现实的假设,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也就消失了,因为青年人能够认识到其思想观念的
随意性。最终,在青春期早期阶段出现了另外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认为其他人的思想都是
集中在自己的自我上面。青年人相互之间针锋相对,随着冲突经验的养成,这种自我中心
主义也就不见了"。
120,维尔默(a.wellmer):《论理性,解放和乌托邦》(thesesn ueber vernunft,
emazipation und utopie),ms,1979,第32页。
121,wellmer,(1979),第53页。
世界文化概论范文第3篇
一、经济社会的概念
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 L. 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 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 market society)、市场机制 (the market mechanism) 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 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 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 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 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 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 “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 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 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 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 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 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 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 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 Robert L. Heilbroner, Making of Economic Society, Prentice-Hall, INC. 1962, p.29.
[4] (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 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 Thomas C. Cochran, Economic History, Old and N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74, No. 5, pp.1561-1572.
[10] 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世界文化概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化;潜政治:真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34-05
无论怎么界定,世界华文文学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概念,其差异所在只是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出怎样的理解。由纷争到共识,也标志其正在从一个学术概念转为一种学科概念。然而,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概念,还要从学科性与学术性的角度进一步确认和辨析几个基本问题。
一、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大文化”概念
世界华文文学既是一个大中华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几乎成为一种常识性的理解,而对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辨析。
中华概念是一种文化属性,地域概念是一种空间属性。如果作为大陆本土文学,二者之间是一种文化种属关系,表现为大文化与其同属的小文化的差异。而对于世界华文文学来说,则包含更多的异质文化元素。在异质文化的生存境遇中,作家思想和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对抗性就更加明显。自从世界各民族文化体系逐渐成熟之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就始终处于一种激烈复杂的冲突之中。同时,也正是这种冲突促成了人类文化的迅速融合与同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成和发展的世界华文文学便包含了特别的文化意蕴和情感倾向。应该说,在中国文学和学术领域还没有哪个学科具有如此强烈而复杂的文化符号特征。
无论是华人写作还是汉语写作,从世界范围来体现中华文化的一统性和多样性特点。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基本内涵和重要价值。这也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促进了整体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世界华文文学的文化独特性。正如刘登翰等人所说的那样,世界华文文学“具有不同于其他语种文学创作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是迁移性和孤立性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中国文学的简单延伸。应建构独特的华文文学的诗学”。它不同于本土文学,也不同于异域文学,是一种由于空间变化而导致作家情感和文学属性变化的文化表达。
同时,世界华文文学还应该是一个世界文化概念,世界意识、人类意识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意识。
毫无疑问,地理空间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概念的一个前提,其作家作品正是以地域分布作为基本身份特征的。然而,世界文化概念不只是在空间上构成中国文学的世界化特点,而且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要具有世界的前沿性,特别是思想的前沿性,从而使世界华文文学成为中华当代文学中领风气之先的领域。世界华文文学具有先天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特性,中国文学和文化面对世界时所具有的诸多问题和现象都首先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体现出来。所以说,这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性转型和世界化过程的试验场。在此之中,从个体生命体验中提供了不同于中国的世界性生存体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变异过程。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和主体体验,经过当地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首先成为促进世界文化融合交流的先行者,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
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并不只是在于文学生产的世界性存在,更在于写作者和文学内容的世界意识。我一直认为中国本土文学中最为欠缺的主题就是人类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是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五四新文学发生后,个人意识也有所体现。但是,只有人类意识却是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而纵观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处于世界性存在环境之中,却也同样欠缺人类意识。相反,由于华人的生存境遇,我们从思乡和怀旧中看到的是更加强烈的文化对抗意识。像1960年代吉林作家鄂华的国际题材小说创作,就是在用本土政治意识来理解和表现国际问题的,把阶级论扩展到了世界文学领域。最终海外华文文学也只是变成了一种域外题材,主题都是预定的,而且都是与本土文学一致的。不容否认,这种主题也是一种适应时代的理解,而如何理解和表现当下时代也是每个作家的义化权利,但这至少不是一种完整和全面的时解。在一种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我们习惯于向某种信仰致敬,但却很少为普遍人性所感动。
严格来说,一些海外华文作家是通过海内读者和学界而产生和发展的,即为国内——不一定只是读者——写作,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出口转内销”。这甚至成为许多作家从事创作的主要动力和目的。因此,在写作中许多作家必然极力去适应国内的价值尺度,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块文学“飞地”。这是海外华人坚持汉语写作的一个主要原因。严歌苓坚称:“我不想从属,永远保持这种状态。”“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我的写作可以不必考虑任何后果,因为我本来就不属于那里的主流社会。”然而,如果不能提供超越以往和现在的常见思想和艺术形式的话,世界华文文学恰恰可能会失去国内读者和市场。
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最伤感的审美概念。在异文化境遇中,文化冲突和文化屈辱所产生的愤激心理,成为海外华文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这也是出国前后诸多知识分子立场转换的心理动因。应该从怀旧怀乡的情绪之中提升为一种世界意识。中国文学从来就欠缺这种意识,本来海外华文文学在西方和世界大视野下,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但是由于空间的间隔,反而导致更加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
长期以来,我们太习惯于二元对立的族群义化立场,纠结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困惑,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创作过多采川中西文化冲突的理解模式,总是努力搜寻和读解海外作家作品中所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民族对抗意识,1980年代王小平的小说《刮痧》发表后,文化冲突主题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模式。也成为一种真实而经典的解读和批评模式。近年来在意识形态回归和海外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种文化对抗意识在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更加突出。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多数研究论著中可以看出,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意识。说到底,对抗的文化立场除了生存的境遇之外,这种理解是来自于华人作家在本土所受到的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当每个人都具有同一种思想的时候,原因就一定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环境或者体制。所以说,批评模式往往就是一种思想模式,无论面对的是多么不同的作家作品,都可以作出同样的理解。即使文化对抗是一种真实的意识,但是对于体验者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立场,不如说是一种审美情感,与其具体的生存状态并不完全相关。有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被同化或者主动认同之后的小感慨而已。不能把复杂的思想经过提纯后变成为一种普遍的批评模式,必须让理论服从现实,而不是相反。否则,脱离现实的甚或违背现实的理论就成为虚假的话语体系。
在这样一种文化情境下,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和评价要淡化文化对抗和对立心理,解构固定化的批评模式。首先必须认同人类文化的普世价值。近年来对于普世价值的否定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悖人性悖现实的思想逻辑。如果没有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21世纪如何成为“中国的世纪”?“中国模式”又如何成为世界模式?绝不能笼统地否定普世价值,只能说普世价值观具有不同的民族国家立场和选择而已。即使是对于国内的社会需要来说,没有普世价值就没有思想统一与社会和谐。中国当下社会的无序状态除了制度的欠缺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共价值体系,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普世价值是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的,在坚守“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民族意识绝不能成为人类意识之外的甚至是与之对立的意识,不包含人类意识的民族意识不是现代的民族意识。因此,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不能始于文化冲突而终于文化冲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事实来看,文化冲突的最后结果是文化融合。而从当下来看,冲突的意味明显多于融合的意味。
二、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潜政治”概念
文学总要承担具体的政治功能。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自古而然的,这一思想传统在近百年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也是中国文学真实的历史存在。因此使用这种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作家和文学是具有特别的有效性的。正如曾敏之先生所说的那样。香港文学对于香港社会的影响,对于“人心回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最初的阐释开始,世界华文文学就被赋予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政治价值。在此之中,研究者的政治意识比作家的政治意识要更加明显。在许多研究论著中,研究者往往透射出要把华文文学发展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意识,把文学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文化样本来解读,甚至做了“文化统战”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在中国文学解读中是具有历史的惯性的。“文以载道”、“文章大业”、“文以治国”的价值观与传统的国家伦理是一脉相承的。早年提倡“联治主义”国家观:要从“邦联的世界”到“世界的联邦”,认为政治国家形成之前,首先要成为文化联邦。很明显,意在通过文化融合使民族的国家成为世界的国家。应该说,在政治策略上,官方的与民间的,政治的与文学的差异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
长时间以来,中国学界各个学科都在呼吁要建立某某领域的“中国学派”,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与世界相争而获得应有的地位。坦率地说。现在还不是畅谈中国学派及其世界影响的时候。如同当下中国社会一样,更多的是要确立和认同人类共同性的思想意识和普遍价值观的时候。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当下弥漫于中国各界的热点话题。从中国特色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再到世界价值,展现了当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渐强化和扩张的精神历程,来自于中国经济总量的高速发展,来自于对于周边世界的自我危机感,更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膨胀。其实,在经济成功的背后,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并不同步。文学的本土经验与世界意识应该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本土经验要以承认和表现世界意识为前提,至少不能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对抗。
本土经验要具有世界性价值,首先要得到世界的认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种本土经验,并不是所有本土经验都“具有世界价值”,即使可能具有传播的功能。例如张艺谋的电影,对其思想和人生价值观的认同才是接受的基础。每一个时代的发展最终都是以同一性为取向的,文明的发展过程都是如此。像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一样,中国文学提供给世界并影响世界的精神价值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文学中多的是阶级意识、本能欲望、消费娱乐、民族主义。
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既要承认其中所渗透的家国意识,同时又不能对“文学——文化——政治”的功能环节作普遍的和夸大的理解。例如在台港文学研究中,往往存在着本土意识和统一意识两种政治评价模式的纠葛,有时候甚至成为一种批评的禁忌。其实20世纪中国文学史对于台港文学的最初书写,就包含有“一个中国”的政治思考。从文学史文本的内容结构上把台港文学的纵向发展过程作为独立的一章。不仅造成了文学史完整性的破坏,并且分明告诉人们:大陆文学和台港文学分属两个独立的部分,政治上的考量多于文学上的考量。在大中国文学史写作中,无论哪一个区域的文学选择,都应该以“融入”时代文学为原则——这是一种结构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尺度。不管是大陆文学还是台港文学。都以同一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来进行选择,并融入相应的时代。这样既构成了大中国文学史的完整性,又弱化了文学史写作的政治意图。
世界华文文学首先是人的文学、民族的文学和人类的文学,批评中应该更多地从人性和族群出发,尽量淡化政治意识形态,因为政治的功能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强化政治性来实现的,有时候恰恰是通过淡化政治本身来获得的。政治的功效可能是短暂的片面的,而文化的功效则是整体的长久的。过于强烈和鲜明的政治性恰恰阻碍了政治目的的实现,因为文化取胜才是最终的胜利。从五四新文化落潮至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是因为只解决了政治甚或政权问题,而没有妥善解决文化问题。要知道,政治的胜利和经济的翻身不等于文化的成功。因为政治和经济的效能是即刻显现的,而文化思想的效能是滞后显现的。
华文文学创作主体的思想传播具有民间性,具有深刻而长期性的影响。这种传播特性使华文文学天生地承担起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的使命,并成为“中外文化深度交流和全面合作”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文学政治功能的强调不能有太直接的功利主义诉求,文学不能等同于政治,文学创作和研究不必直接进入思想判断和国家诉求,应该在审美层面和个人感受阶段多停留一会,而这个阶段恰恰是最具人性共鸣和人类认同感的过程。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大学文学教育大多采取了政治功利主义的原则,让文学过于直接地承担社会功能,最后反而使人们疏离了政治。也疏离了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承受着格外的历史重负,本土经验、中华意识与世界价值是其整个内涵。但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意识的文学领域,不能简单地承担过于重大的政治主题,家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应该是潜在的,不是显在的。政治意识越鲜明,得到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就越小。由政治概念转化为一个潜政治乃至文化概念,评价世界的尺度最终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
三、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真学术”概念
一个领域要成为学术对象。不只在于其是否有学者研究,是否使用学术语言和学术方法,关键在于其对象和研究本身要有学术价值。中国当下有许多伪学术:预定的对象、预定的结论,学者只是一个身份,研究只是一个形式,结论或者是老百姓都已知晓的常识或者是老百姓不认同甚至嘲笑的反常识,以至于民间流传着“绝不相信没有经过专家否定的消息”的说法。
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学界对于各自学科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成为一种热潮。而包括近年来的一些争辩在内,这种“回顾与展望”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学科的理论常识。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说明了教育管理者们期待发展的渴望,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等于无视世界大学发展的1000多年的历史。况且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人类大学教育的创新和创造,而是故意放弃和回避已有的基本常识和成功经验。像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样,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教学,华文文学仍在讨论学科的属性甚至名称问题,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其学科性还不够成熟。但是,一种人类社会制度的建立,可以走现成的桥;而一个新的学科的建立和成熟,往往确实要摸着石头过河。这表明了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必然过程和一般规律。
在学科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科的特殊性原则。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是一种社会需求,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决定了学科的消长。没有特殊性就没有学科建立的存在价值。同时,更要注意学科的一般性原则,要得到学术上的认同。没有广泛认同,便没有成熟的学科。中国的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成长是极为艰难和复杂的,一个新的学科成立与否,关键是看这个学科能否为中国学术提供独到的贡献。世界华文文学包含了太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民族的和个人的、历史的和当下的信息,具有极大的学术空间。移民历史、文化融合、个人传奇、跨国婚恋等民族与个人的故事都在其中展示。这些都构成了这一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当然,学科发展和确立不是自为的而是自在的,必要的呼吁是应该的,但是关键还是要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实绩。
世界华文文学需要有学科自信和学术宽容的心态。对于这一领域的评价,中国学界并不是不存在学科偏见的。其实,由于学科建立的历史和发展的实际不同,各个学科之间是存在着价值差异的。学界中流传的“搞不了古代搞现代,搞不了现代搞当代,搞不了当代搞比较,搞不了比较搞海外,搞不了海外当领导”的笑谈,表明了这种学科差异和成见。
首先,要打破学科偏见。学科发展是需要保持生态平衡的,由此才构成学科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在比较和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各个学科的发展。
其次,要有学科自强意识。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本身就有着无限成长的发展空间。如何使一个普遍的学术对象成为一个公认的学科领域。首先就要确立一个国家性和世界性的评价尺度。要利用同类比较的价值判断方法,对世界华文文学进行必要的经典化塑造。我认为,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性都不能成为学术价值差异的理由,价值标准是公共的和恒定的,不能因人论文。前些年,与大陆“女作家研究热”相一致,文坛曾风行“海外女作家创作研讨会”。女作家的创作实绩确实是一种事实,但是如此之热难免还是令人存在一丝怀疑。“缺少系统完整和具有相当说服性的成果”,自身理论体系的欠缺和不明确是本学科不甚成熟的根本标志。无论学界如何评价,世界华文文学同仁要有学科自我强化意识。
再次,还要扩大研究视野。近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热点不断。其实这一现象往往是由于过去研究范围过于狭小所导致的。从地域分布来看,我们对于欧洲、北美华文文学的关注较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地域的华文文学创作成就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更关注“第一世界”,甚至说明学术研究存在着的政治和文化的功利性。相比之下,对于非洲、南美、东北亚、澳洲等华文文学的创作关注明显不够。而对于欧洲、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还是在移民作家,本土华文文学被相对忽视”。从已有的创作来看,相当多的仍然是时空交错文化冲突中的体验叙事。
世界文化概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现象学
【正文】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这两个概念,与现实生活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受到国内外哲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着重阐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同时把它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最后还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看法。
“生活形式”(lebensform)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语言游戏”这个概念紧密相连。在前期著作中,“逻辑形式”这个概念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语言之所以能够表现实在,正是因为语言和实在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到了后期,生活形式这个概念取代了逻辑形式这个概念的地位,因为此时维特根斯坦已不认为语言和实在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转而强调语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在提出“生活形式”这个概念之前,维特根斯坦还使用过“世界”(welt)、“世界图景”(weltbild)、“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以及“环境”(umgebuug)这几个概念,它们与“生活形式”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相似。wwW.133229.COm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喜欢用“世界”一词。他在该书开头部分侧重于从本体论角度说明世界与事实的关系:“世界是所有发生的事情。”[1](p189)“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1](p189)“世界是由事实规定的,是由诸事实即是所有的事实这一点规定的。”[1](p189)“因为事实的总和既规定了发生的事情,也规定了所有未发生的事情。”[1](p189)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把“世界”与事实的总和等同起来,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等同起来,与逻辑空间中的各种事实等同起来,它既包括所有已发生的事情,也包括所有尚未发生的事情。在此书的后一部分中,维特根斯坦侧重于从语言和逻辑的角度来考察世界,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1](p245)“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它的界限。”[1](p245)并且把世界与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世界与生活是一回事”。[1](p246)这里需要指出,他不是从生理学或心理学的意义上使用“leben”(“生活”或“生命”)一词,因为他在《1914~1916年笔记》中声明:“生理学的生命当然不是‘生活’,心理学的生活也不是。生活乃是世界。”[1](p160)
在其后期著作中,维特根斯坦使用“世界图式”、“环境”等概念。例如,在《论确定性》一书中,他提出“世界图景”这个概念,把“世界图景”看作我们所继承的那个背景,它是我们赖以生存而必须接受的一切,也是一切语言游戏赖以进行的基础。他说:“但是,我得到我的世界图景并不是由于我曾经确信其正确性,也不是由于我现在确信其正确性。不是的:这是我用来分辨真伪的传统背景。”[1](p208)他把世界图景比喻为一条河流,河岸的一边是不发生变化或者变化很小的坚硬的岩石,另一边是随时随地可能被水冲走或者淤下来的泥沙。他用这个比喻表示世界图景既是固定不动的,又是流动不息的。他有时把描述世界图景的命题看作语言游戏的规则,他说:“描述这幅世界图景的命题也许是一种神话的一部分,其功用类似于一种游戏的规则,这种游戏可以全靠游戏而不是靠任何精确的规则学会。”[1](p208)
在《关于颜色的评论》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提出“环境”这个概念,他说:“一种颜色在一个环境中发光(如同一双眼睛在一张脸上微笑)。”[1](p290)他举了许多事例说明颜色对环境的依赖性,例如,一块绿色的玻璃把绿色赋予了它后面的物体,使得它后面白色的物体变成绿色的物体,红色的物体变成蓝色的物体,如此等等。“因此,一个东西上只有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才是灰色的或者白色的。”[1](p341)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还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环境”一词,谈到“语言”这个制度以及它的整个环境,认为如果没有语言这种制度以及它的整个环境,我们就不能说“设想雨很快就要停了”,并且意指这件事[1](p204)。在这里,“环境”这个词的含义似乎与“生活形式”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辽阔。
不过,在他的后期著作中,特别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使用得最多的还是“生活形式”这个词。他没有对这个概念作明确的界定,但说过许多关于生活形式的话。在《哲学研究》中,他往往把期望、意向、意谓、理解、感觉等等心理活动都看作生活形式,它们是由于人们共同生活和使用语言而成为生活形式的。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能说话,人具有语言能力,而动物不能说话,不具有语言能力,至多只掌握语言的一些最原始的形式,如吼叫、呼啸等等。动物不能说话,是因为动物没有心智活动;人能说话,是因为人有心智活动。他曾对此举了这么一个事例:我们能够设想动物会发怒、害怕、高兴或不高兴等等,但能否设想动物会期望、怀疑或者推论。一条狗可能会想像它的主人目前在门外,但它能否想像它的主人明天会回家来。他认为狗不能如此想像,人却能如此想像,即能推测某人可能何时回来。这个事例说明动物没有心智活动,人类才有心智活动。他强调说,心智活动,如命令、怀疑、期望、意向、推理等等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些重要的生活形式。这些心智活动是以人使用语言的能力为条件的,没有使用语言的能力的动物就不会有这样一些心智活动。他说:“是否具有能够说话的人才能够希望?只有掌握一种语言的用法的人才能够希望。这就是说,属于希望的种种现象是复杂的生活形式的一些变体。”[1](p244)
不过,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或语言活动才是最重要的生活形式。他明确指出:“我们不难想像一种只是由战斗中的命令和报告组成的语言。——或者一种只有问句和表示肯定或否定的答句组成的语言。——以及其他无数种类的语言。——想像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1](p14)在谈到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时,他把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与生活形式的多样性直接联系起来考察,指出“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p19)这两段引文都谈到语言与生活形式有关,只是在用法上略有差别:前者把语言本身看作一种生活形式,后者则把语言的说出、即语言活动看作一种生活形式。不过,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这种差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在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人的全部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始终是处于动态之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他始终把语言本身看作一种活动,语言就指的是语言活动,语言由于作为一种活动而成为一种生活形式。
由于语言活动与生活形式有如此密切的联系,由此可以说生活形式是语言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把一种语言与作为它的基础的生活形式隔离开来,就无法对这种语言作出正确的理解。例如,我们来到一个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部落,完全听不懂他们所说的那种陌生的语言,情况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我们不了解那个陌生部落的生活形式。当我们在那个部落生活了一段较长的时期,从与他们的交往中逐步了解他们的生活,我们就会逐渐懂得他们的语言。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语言表达式作出大不相同的理解,或者对同一种生活现象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式,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要正确理解一种语言,就必须正确理解作为那种语言的基础的生活形式。他说:“我们是否对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的某个词作出正确的理解和翻译,这取决于我们是否理解那个词在这个部落的全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说,取决于它被使用的时机,取决于在通常情况下与这个词相伴出现的那种情绪表达,取决于这个词所引发的印象,如此等等。”[1](p136)
他还认为,不同的部落、民族或国家里的人们尽管使用不同的语言,但他们仍然能够通过翻译交流思想,这正是由于不同的语言植基于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中,而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之间存在着许多或人或小的相似之处,他把这些相似之处称为“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他说:“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是我们借以解释陌生语言的一个参照系。”[1](p144)因为,任何语言活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语言规则,而语言规则是以生活形式的一致性为基础的,因此语言活动也以生活形式的一致性为基础。他明确指出:“语言现象立足于规律性之上,立足于行动一致之上。”[1](p261)试问:人们的意见一致是否决定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回答说:“人们所说的事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人们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取得意见一致,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1](p123)
维特根斯坦还强调说,语言活动或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主要内容,但不是生活形式的全部内容。因此,生活形式是一个比语言活动覆盖面更为广阔的概念,除语言游戏外,生活形式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可以说,生活形式包括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制度等等,包括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他说:“一种游戏,一种语言,一条规则,就是一种制度。”[1](p254)“‘语言’、‘命题’、‘命令’、‘规则’、‘计算’、‘遵守规则’这些词,与一种技巧、一种习惯相联系。”[1](p264)这就是说,他强调语言是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一种社会文化。他说:“属于语言游戏的是整个文化。”[1](p331)这就是说,设想一种语言,就意味着设想一种文化。从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活动,或者说,来理解生活形式,就可以说:“那种必须接受的东西,被给予的东西,就是生活形式。”[1](p318)
维特根斯坦还认为,生活形式是人们的各种概念由此形成的基础,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形式之中,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概念。他说:“我们的概念好像受到事实框架的制约。”这就是说:当你以一种与事实本身不相同的方式去思考、描述这些事实时,你就再也想像不出某些概念的用法,因为这些概念的使用规则在新的环境中没有相似物。[1](p203)又说:“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教育的教育或许是一些十分不同的概念的基础。”[1](p210)因为,那里的生活形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所感兴趣的事物,他们未必会感兴趣。另一些不同的概念或许在那里不再是不可想像的。其实,从根本上说,不同的概念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是可以想像的。
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维特根斯坦把“生活形式”称为“生活事实”。他说:“与那些不可分析的、特殊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相同,我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活动,例如,惩罚某些行动,以某种方式确定事态,发出命令,作报告,描绘颜色,对别人的情感发生兴趣,都是事实。可以说,那些被接受下来的、被给予的东西,都是生活事实。”[1](p164~165)按照维特根斯坦强调家族相似而否认本质的观点,把“生活形式”称为“世界”、“世界图景”、“环境”或者“生活事实”,都是完全适当的,因为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家族相似,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间,“生活形式”这个概念不是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的。在他提出这个概念之前,德国哲学家斯勃朗格(f.e.spranger)已在1914年出版的《生活形式》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其后又有德国符号逻辑学家苏尔茨(h.scholz)在1921年出版的《宗教哲学》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用生活形式意指宗教意识的方式。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维特根斯坦读过这两个人的这两本著作,而接受他们的启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生活形式”这个概念之前,胡塞尔已提出一个与此十分相似的概念,这就是“生活世界”(lebenswelt)。胡塞尔在他后期的语言哲学中,试图从语言追溯到语言活动,并进一步追溯到更加原始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他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一书中,但在《欧洲科学危机的先验现象学》(1936)一书中才得到详细的阐述。
在前一本书中,胡塞尔侧重于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这一角度考察生活世界问题。他说:“我们把那个在他的经验中在相互理解中,在一致同意中形成的那个周围世界,称为交往的周围世界。”[2](p193)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进入相互交往之中,语言作为一种客观的结构出现了。可见,在他那里,过渡到生活世界意味着过渡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附带可以指出,胡塞尔的“周围世界”(umwelt)概念与维特根斯坦的“环境”(umgebung)概念在字形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在后一本书中,胡塞尔侧重于从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那个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所谓“生活世界”,他指的是那个“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体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3](p58)在他那里,科学与哲学的观念世界、实践活动的生活世界以及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有区别的。他试图利用他的还原法把科学和哲学的观念世界还原为实践活动的生活世界,表明科学和哲学的观念不过是生活世界中的理论和技术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然后再把实践活动的生活世界还原为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的世界,表明生活世界是纯粹自我的意识活动的产物。在这三个世界中,生活世界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一方面,科学和哲学的观念世界不过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为生活世界创造的一件“观念的外衣”,是各种观念化了的、抽象的东西的总和。在科学和哲学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一个前科学和前哲学的生活世界,人们已经有某种关于世界的看法,即某种前科学和前哲学的世界观以及与此相应的说话方式。在科学和哲学产生之后,那个生活世界依然存在,它本身没有改变,仅仅改变了一些对生活世界的描述方式,这就是用科学和哲学的说话方式取代了原来的素朴的说话方式。他说:“这个实际地直觉到的、被经验到和可被经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整个实践生活是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在它自己的本质结构和在它自己的具体的因果样式方面总是依然如故,不管我们进行技术化或不进行技术化。”[3](p60~61)另一方面,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的世界本身严格说来不是世界,它只是作为超越于生活世界的一个极而存在着,纯粹自我通过它的意识活动构成世界。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只存在一个世界,即实践活动的生活世界,它是人们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的总和。
胡塞尔还强调生活世界与文化历史世界之间的区别,认为生活世界是文化和历史中各种差异性和偶然性的基础,是一切可能经验的一般视野,是现象学的真正主题。生活世界始终是作为基础起作用的,它是文化世界中相互交流成为可能的条件。生活世界是包罗万象的,它把一切特殊的世界都吸收到自身之中,构成一切世界所共同的那种客观性的基础。文化世界是事实与本质的一种特殊混合物,生活世界本身则是纯粹的本质,因而成为现象学的惟一合适的主题。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十分相似,这两个概念都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在概念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是一切语言活动和一切语言现象的基础。不过,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等同的,因为胡塞尔侧重于从社会角度考察生活世界与科学和哲学的观念世界的关系,从哲学角度考察生活世界与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则侧重于从语言角度考察形形色色的生活形式如何成为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的基础。
至于维特根斯坦在提出他的“生活形式”这个概念时,是否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中受到启发,根据目前的资料尚无法对此作出明确的判断,至少维特根斯坦没有提到过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在与维也纳小组成员交往时期,石里克(m.schliek)曾向维特根斯坦询问胡塞尔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能否成立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这表明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著作有或多或少的了解。
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在其著作中直接提到胡塞尔这个人以及他的“生活世界”概念,但他多次使用“现象学”这个术语,特别是在30年代上半叶这段时期里,首先在1929~1930年间在剑桥所写的头四本笔记中,以及在1929~1930年间完成的《哲学评论》和1931~1933年间完成的《哲学语法》中。在他的《大打印稿》(the big typescript)中,还专门有一章以“现象学”这个词为标题。他还试图提出一种纯粹现象学的颜色理论,在他的后期著作《关于颜色的评论》中,他声明他所讨论的不是关于颜色的物理学理论,而是关于颜色的现象学理论,即关于颜色的语法。他还对其友人德吕里(m.o’cdrury)说:“你可以把我的著作称为现象学。”诚然,与30年代相比,他在40年代的著作中较少使用现象学一词,但他并没有否认现象学问题的存在。他说:“虽然没有现象学,但也许有现象学问题。”[1](p290)
根据帕斯特(b.c.past)在他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现象学观点》一书中所作的分析,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观点可能受到马赫(e.mach)和博尔茨曼(l.bohzmann)的启发。“现象学”一词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康德、黑格尔、皮尔士等哲学家都使用过这个概念,马赫、博尔茨曼、爱因斯坦、普朗克等物理学家也使用过这个概念。马赫试图建立一门普遍的、尽可能把各个物理领域包括在内的物理现象学,以便对尽可能广泛的物理事实作出直接的描述。他强调感官是对各种科学事实进行直接显示的惟一泉源,应当通过还原为感觉经验而不采取任何科学假设的办法来描述世界。例如,当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热这种物理现象时,就能形成一种现象学的热力学,它往往使用压力、体积、温度等等可以直接观察的、从而可以计量的量进行操作,而不像统计热力学那样超出我们的感觉经验之外,假设一些无法觉察的原子而对热这种物理现象作出解释。
与马赫相似,博尔茨曼也主张在考察物理现象时,只需依据我们的感觉经验,而不作任何假设。他说:“物理学必须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即对于每一个现象系列,都写出一些可以从数量方面对现象过程作出决断的方程式,而不求助于任何假设、模型或者力学说明。”他把这种方法称为数学现象学的方法,因为它主要使用微分方程式来表述物理事实。他把马赫的现象学称为普遍的现象学,而把自己的现象学称为数学的现象学,认为这两种现象学在描述物理现象时都依据于感觉经验,而不依据于任何假设。
与马赫和博尔茨曼相似,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头20余年内也强调在描述现象时要依据于自己的直接经验,而不作任何假设。在这段时期内,他主张使用现象语言或原初语言来描述直接经验,这种语言是一种用以描述现象的实际情况的语言,它描述的是直接所与之物,没有附加任何假设,只是纯粹的描述。到30年代中叶,他才从主张使用现象语言或原初语言转向主张使用物理语言或派生语言。从这种情况推论,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可能在现象学的这个基本观点上或多或少接受过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特别把博尔茨曼称为对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1931年写道:“博尔茨曼、赫兹(hertz)、叔本华、弗雷格、罗素、克劳斯(kraus)、卢斯(loos)、威林格(o.weininger)、施本格勒、斯特拉法(straffa)就是这样地对我发生影响的。”[1](p27)维特根斯坦在青年时期读过博尔茨曼的著作,甚至打算成为博尔茨曼的门生,只是因为博尔茨曼于1906年自杀身亡,才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博尔茨曼关于现象学只是描述我们的直接经验,而不附加任何假设的观点,对撰写《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颇有影响。博尔茨曼对于如何使用一种适当的语言去表述直接所与之物的探索,也许也对维特根斯坦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形式语言的想法有所启示。关于博尔茨曼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这个问题,还可以作专门探讨,这里就不多说了。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全集[m].保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