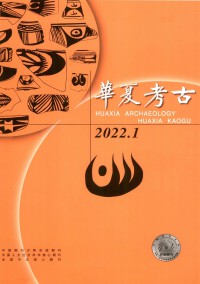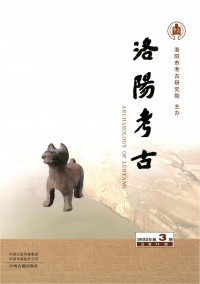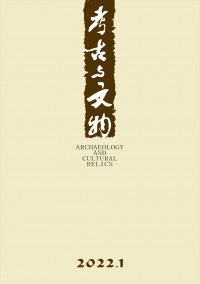考古发掘方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考古学;马衡;李济
近年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虽已平息,但我们对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和强大的史学传统依旧缺乏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对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西方考古学技术的应用方面。现以马衡、李济为中心,从考古发掘的技术层面,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爬梳,以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马衡生于1880年,幼时从业瀚受学。岳父叶澄衷曾资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书法、骑术等研究会的导师。同年秋,为史学系三年级讲授金石课程,这也是该系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设这门课。①1922年2月,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议升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马衡获悉后,迅速至新郑调查出土古物地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向马衡介绍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来发掘经过,“先后开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划定范围,南北长三丈五尺,东西宽四丈五尺,层层发掘,至三丈深,见有墓穴作椭圆形,上易明砂,中有残骸残玉,穴外环列各器。”②马衡到达新郑时,发掘己经结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旧坑北面新开一坑。马衡根据他人所言绘一《新郑县发掘古器物图》,大致标明发掘坑、墓穴、骸骨及遗物的位置。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详细报告了新郑铜器发现的时间、地点、经过、种类及其数量、制作材料,并绘制了图纸,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马衡偕同傅振伦、常惠等人,以《水经注》及顺治、乾隆年间的《易水传》为线索对燕下都作了实地调查,并于1930年组成“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姥台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③经过一个月的发掘之后,由于“东陵盗墓案”的发生以及时局的不稳,发掘工作遂告结束。
马衡从1919年任职北大以来,积极筹划各种考古事宜,不过,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组织田野考古发掘。综观马衡的考古学方法,我们会发现马衡非常重视实地发掘,虽然他仅参加过一次发掘工作。马衡注意的是地点与器物出土情形,知现在的出土地点便可推知古代何时曾称作何地。马衡认为实行有计划的发掘还可以观察出土物的种类、数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间的关系及当时的风俗制度。在数次考古调查中,马衡都很注意这一工作。当他参观朝鲜乐浪古墓发掘时,特意绘制了一幅棺椁布局图。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显受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殷墟发掘的启发。
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和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活动的负责人,“虽然,马衡缺少现代考古学训练,使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导致他在领导北大考古学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考古发掘,加快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由于他的努力也加快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步伐。不过民国以来的多数考古发掘,都与金石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作宾的殷墟发掘也是如此。到李济主持安阳发掘时,“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张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发掘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因为这次发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正如陈淳所说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献资料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为史学传统的延续,从而影响到史前学的视野与研究。”④殷墟发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过作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起点,恐怕还要追溯到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
1925年李济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考古学课程,并于1926年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合作,对山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阶段。李济把山西作为考古发掘的首选,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济到达山西之后,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把发掘地点定在西阴村,除了这一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这些都表明李济在筹划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时候,研究目标和思路就鲜明地定格在史学范畴上,在学术定位上将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李济是一个古史学家,考古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寻觅文明起源的情节和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考古学迈出第一步时即已昭然”。⑤
关于李济这次发掘方法的得失,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赘述。总之,这是国人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创新之处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个坑分八“方”,分成两排,后面一排四个面积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学采用严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发掘还是采用探沟法,同时李济在发掘中还在各个探方中保留了关键柱,这也是一大创举。其次,采取了“披葱式”方法,即水平层位法来开展发掘工作,第三,李济用“三点记载法”,详细记载了出土物的情况,并用“层叠法”来记录常见的遗物,在当时都应该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图、地层图的绘制则是由参加过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来完成。李济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虽然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细节。当时的考古分析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他的分类只是中国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类型学。李济在“西阴村所实践的考古学方法也不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考古学范例,也不是即将取代近代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但总的看来,“李济的发掘是相当科学,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掘的较高水平。”
李济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对于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是以他在西阴村的发掘方法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首先,李济对殷墟的陶器进行研究,写成了《殷墟陶器初论》一文。此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遗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过去金石学的巢窠,而进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学中固有名称,结合功能原则,对考古发现中的陶器定名,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础工作,体现出金石学对考古学的影响;3、从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与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年代学的探索。⑥不过李济的陶器研究也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比如说,他主张从甲骨文以及后来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来确定陶器的名称,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与铜器比较,由铜器的名称,推定陶器的名称。其次,李济对中国考古学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类型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安阳殷墟第七次考古发掘开始,李济就脱离一线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对铜器进行化学分析,以确定其确切年代,然后对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同时对这些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当时国外先进理论来进行考古学的探索。
李济的考古学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西学的真义还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学者指出“李济先生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研究时力图打破宋人的命名分类体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几个部位标以字母符号,欲建立现代考古学类型学上的分类。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没有从结构上根本替代旧有的分类。”⑦“由于自信,中国考古学虽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类缺乏普遍认可的类型学。”⑧作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运用是有别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专家,同时他在美国也接受过人类学的训练,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自从梁思永加入到考古发掘中来之后,殷墟发掘才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在西学东渐中产生,无论在方法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在中国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以马衡和李济两位先生为例,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梳理,探讨他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于近代考古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希翼对当今的考古学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①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49
③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4)
④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⑦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4):27
⑧福尔肯霍森 著、陈淳 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世界》,1995:86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2篇
一、湖南文物考古档案保存状况简介
1.档案管理方法原始,资料查找困难。上世纪末,文物资料库房中拥有考古资料档案数万份,最早的发掘时间是建国后的1950年,这些资料分为单一性墓葬、单一性窑址和遗址。2000年以前,传统作业方式主要是依靠手工将这些资料按照遗址名称进行登记造册后,再按照发掘年代统一存放,信息的查询主要是依靠工作人员的记忆和经验,由于资料数量庞大,查询一份资料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而考古信息资料的查询长期束缚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极大地阻碍了考古事业的发展。
2.档案保存手段落后,资料利用效率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获得的资料都具有空间属性,一个考古遗址的位置和范围可以通过空间数据(如一系列点的坐标)来表示。但由于过去考古资料采集的手段落后,以往的考古资料都未能赋予这些信息,虽然单位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保存这些信息,但这些信息之间关联性不强,资料中附带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淹没在“故纸堆”,利用效率低下,有的甚至成为“死档案”,严重制约了考古成果的开发利用。
3.部分资料受损变质,面临损毁风险。由于年代久远,历年考古发掘照片、录像资料,这些考古资料与本体同样弥足珍贵,但原来的保存技术和手段落后,其长期保存和充分利用存在极大困难,部分资料照片、胶片已经老化受损,甚至面临变质损毁的风险,需要进行抢救性、再生性保护,保证这些珍贵资料的永久保存。
二、现有考古档案的开发利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性能扫描仪和各种数字化电子设备普及,其精确度和清晰度已经越来越高,对考古成果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已显示出其巨大价值和发展前景,但大量基础工作要从头做起。
1.传统考古资料电子化,以此建立田野考古资料数据库。我所数万份的考古档案,其保存的类型有文字、图表、胶片、影像和标本资料,其中信息完整、具有重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档案数千份。按照数字化信息采集、存储、管理的基本规范,运用高清彩色扫描仪、胶片扫描仪、红外扫描仪、三维扫描仪等现代化技术设备,对传统资料进行系统地整理、归类、电子化,并在考古资料电子化的基础上,开发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了考古发掘的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图书资料、器物标本、田野考古、简牍等6大数据库的建设,不但有效地实现了考古资料的保存,还可以按照发掘者、发掘地区、发掘时间、遗址名称、探方编号等多种方式进行资料查询,为研究者快速再现当年考古研究成果。该系统基本上解决了资料的保存、查询及简单的利用。
2.考古档案建设的创新发展。由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数据模型(简称“3S”)技术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手段应用在第一线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工作中,野外收集的考古信息资料被一一赋予了地理信息坐标,这为考古档案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2012年,我所在原有的资料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建立了湖南考古地理信息系统。
该系统为湖南考古资料档案建立了准确的时空维度,实现了集保存、查询、可视、定量分析研究一体的数字化考古信息群落,为“区系类型理论”的最终实现打下了技术基础。该系统具有如下的特点:
①野外资料采集的数字化。现代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以掌上电脑PDA为终端,集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先进技术为一体,实现野外数据采集的数字化。该软件系统的应用将改变野外考古调查的手工作业方式,实现野外调查数据获取过程的数字化,可指导考古调查发掘野外工作的效率及水平。
利用GIS技术将GPS定位结果反映并存储在掌上电脑的电子地图或遥感图像上,野外调查人员可用掌上电脑准确登记野外观察与描述的记录,可以在野外方便地采集遗址、遗迹和遗物的属性数据。系统集定位、导航、图形显示、漫游、路线显示为一体,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共享,可同时满足文物调查、野外数据采集、信息管理和科学研究等需要。
②多种方式的考古成果查询与展示系统。资料的查询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有时还可能一无所获。但是,在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中,由于野外考古采集数据被赋予了地理坐标,因此查询考古资料变为极为便利的事情。该系统各种资料的查询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工作区查询、工作单位查询、遗迹单位查询(涵盖墓葬查询)、堆积单位查询、绘图资料查询、影像资料查询、器物标本查询、旧石器标本查询、古生物标本查询、测定标本查询、工作日记查询、工作记录查询、工作报告查询、调查记录查询、工地检查查询、修改日志查询等16种模式,极大地便利各种信息的快速查找。
③考古遗址各种信息的分析和研究。由于该系统可以统计一定范围内某个时期或某种类型遗址的数目,量算遗址的面积、遗址与遗址以及遗址与水系、山谷、道路等之间的距离,通过空间分析的操作模块,能自动给考古工作提供多种智能分析,比如:不同时代遗址分布的特征、古代人生活距离河流的距离、众多遗址之间的聚落关系、古人择址的喜好等等,因而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大大地提高了综合考古研究及区域考古研究和专题考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④考古成果三维真实场景展示功能。该系统提供考古发掘的三维真实场景展示功能,提供放大、缩小、漫游、导航、飞行等基本空间浏览和测量功能,对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发掘过程、出土文物修复进行三维重建,通过虚拟动画效果,为受众群体及考古工作者提供多角度、多方位的观察视点,重现古人生活情景。
⑤考古专题分析。专题图功能:根据发掘成果产生各种基于遗址点的专题图,包括遗址点分布图、地质结构分析图、文物出土数量、遗址面积统计图等。资料输出功能:从考古数据库中将各类感兴趣的资料。输出到文字处理工具或电子表格,便于对考古资料进行研究,便于编制考古报告。可输出的资料包括遗迹单位记录、墓葬记录、考古标本记录、图形、照片、统计报表等。
新建的湖南省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不但改变了湖南几十年传统的资料管理的运行模式,还创新性地实现了地理信息系统和资料管理保存和利用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考古资料保存、查询、利用、展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齐乌云周成虎王榕勋.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类型.华夏考古2005(2).
[2]刘建国.数字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南方文物2007(1).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3篇
马王堆汉墓木俑研究综述
马王堆汉墓帛书分类探究
帛画《车马仪仗图》新解
益阳市复兴村战国墓发掘简报
《沅水下游汉墓》资料整理概况
马王堆一号墓漆棺的装饰艺术
徐州贾汪新城小学墓群发掘报告
马王堆汉墓漆器装饰艺术研究述略
从马王堆汉墓窥测西汉时期生态文明
试析马王堆汉墓生器变葬器的转换形式
长沙市青少年宫考古工地发掘情况简报
长沙市中南工业大学桃花岭唐墓发掘简报
2001年汉寿聂家桥武峰山M11发掘简报
徐州西汉合葬墓的类型、性质及埋葬方法
长沙市宁乡县大夫堂汉墓群调查简报
长沙市桂花坪印山坡东晋墓发掘简报
醴陵沩山窑遗址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
长沙开福区凯乐国际城古井发掘简报
试论湖南出土新石器时代玉佩饰
湖南长沙燕子岭唐墓发掘简报
试论中国南方不对称形铜钺的起源
马王堆汉墓帛画《神祇图》研究二则
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研究综述
马王堆汉墓《地形图》研究综述
湖南长沙坡子街7号地块H9发掘简报
攸县鹅公岭出土的一批东周时期青铜器
长沙潮宗街工地考古发掘情况简报
《春秋事语》(一至四章)新释文与注释
马王堆汉简《天下至道谈》校补
马王堆汉墓帛画《“太一将行”图》新探
马王堆汉墓出土服装命名相关问题考证
《五十二病方》“身有痈者”祝由语补疏
浅议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的“漆”字
副笄在首: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人首服研究
湖南省汨罗市归州山战国墓第三次发掘简报
浅谈DNA分析技术在人类考古学中的应用
长沙市开福区田家炳实验中学工地发掘简报
长沙市开福区泊富国际广场护城河发掘简报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研究综述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皇图岭镇鹅形岭东汉墓群
长沙市开福区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工地发掘简报
湖南华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特殊空间:马王堆一号汉墓北边厢空间的营造与利用
改扩建期间核心文物管理和保存状况的评估体系
湖南华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湖南常德南坪汉代赵玄友等家族土墩墓群发掘简报
关于马王堆古尸不腐神话及其保存关键技术传承的思考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4篇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梁启超对于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使得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