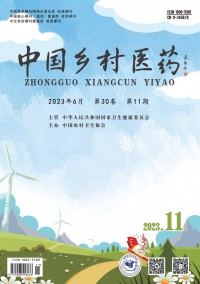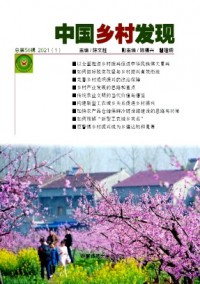乡村社区治安的途径设计

治理是在西方学者看到国家的失效和市场的失效后提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然而治理也可能失效。为了克服治理失效,西方学者提出了“善治”。“善治”也就是“良好的治理”(goodgovenance),善治的实质是治理的最优化,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10个:(1)合法性(legitimacy);(2)透明性(transparency);(3)责任性(accountability);(4)法治(ruleoflaw);(5)回应(responsiveness);(6)有效(effectiveness);(7)参与(civicparticipation/engage-ment);(8)稳定(stability);(9)廉洁(cleanness);(10)公正(justice)[3]。治理和善治理论是舶来品,能否照搬到中国适用,如何适用,我们必须分析中国的国情。著名的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指出:“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中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后才可以判定”[4]5,6。作为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和善治理论是建立在发达的民主制度、健全的法治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反观目前的中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公民社会也开始兴起,但是法治还不健全,公民社会离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下,要在中国适用治理和善治理论,一是要具体分析,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二是必须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否则会“水土不服”。即是一方面要分析公民社会是否有能力自治和多大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国家要在治理中处在主导地位,要成为社会主体的动员者、引导者。更进一步地说,其运作机制在于“行政吸纳社会”,恐怕这更符合当下的中国现实。
一、历史与现实———农村社区治安治理理论的引入
从历史上看,农村社区具有提供治安产品的能力,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社会基础。从现实看,政府大包大揽提供农村治安产品有很大困境,而治理可以很好突破这种困境,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动力。村民自治制度给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框架,这是治理引入农村社区治安的制度基础。
(一)从历史上看,农村社区具有提供治安产品的能力
我国自秦汉以来,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是行政嵌入的典型,中国传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则大多是内生的[5]。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村庄外部来看,帝国的统治能力是虚弱的,不支持其深入乡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村庄内部有自己的秩序生成机制。传统的中华帝国,其统治能力是虚弱的。费孝通认为:“东方的农业平原正是帝国的领域,但是农业的帝国是虚弱的,因为皇权并不能滋长壮健,能支配强大的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6]62马克斯•韦伯也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7]110。因为虚弱的帝国,加之疆域庞大,人口众多,交通与信息不发达,国家不可能直接管理社会。传统帝国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方面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教化人民;另一方面,国家借助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充当了官民的媒介,以便上意下达、下意上通,联络官民———无为而治地达到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在国家不能深入乡村,为乡村社会提供治安秩序公共品,乡土社会的治安秩序主要由乡土社会的家族及伦理来提供。以秦汉为例,帝国设置一个不下县的官僚体制和县以下的宗族组织与乡里制度,来实施对帝国的统治。然而,作为行政机构的乡里组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没有能真正健全并发挥维护乡村秩序的基本功能。乡里组织反而被家族渗透和影响。赵秀玲认为:“‘宗族与家庭’不仅是乡里制度的构成基础,也是乡里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时宗族制度就是乡里制度”。中国“乡里制度的建立与演变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以邻里为主的地缘,二是以宗族和家庭为中心的血缘”。“一部乡里制度的发展嬗变史也是一部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影响渗透的历史”[8]176,181,197。正如有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样,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9]27。对此,吴理财作出了一个简要的概述:“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自治之名,然确实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只延于州县,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10]。
(二)从我国当前农村治安现状看,治理可以突破政府大包大揽提供农村社区治安产品的困境
首先,对于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农村来说,农村的警力是有限的。据统计,目前全国派出所共有民警45万余人,其中有24万人分布在农村派出所,占总数的53.3%,有21万人分布在城区派出所,占总数的46.7%。但是由于农村面积大,人口众多,所以实际分到各乡镇派出所的警力很有限,警力区域比、警力和群众数比都很低,一人所、两人所不足为奇,致使农村民警压力大,正常警务无法有效开展。其次,农村财政能力有限,农村派出所普遍存在经费不足。“农村真穷”,就是指乡村两级的政府穷、集体穷,这使得农村能用于治安的经费相当有限。据调查,湖南省有5名警力以下公安派出所549个,无警车派出所418个,全都在农村,大大降低了其工作效率[11]。再次,国家包揽式提供治安产品,不适应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不利于警民关系和谐。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传统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动,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成为“流动的村庄”,现代性因素逐步植入农村社会,社会关系越来越动态化,农民对治安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包揽式的化解社会矛盾的做法无法回应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国家包揽式提供治安产品,缺乏和民众沟通,打击处罚重于服务,这不利于警民关系的和谐,甚至会造成对立。吉登斯认为“警察与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对象的分离常常会导致一种‘被围心态’,因为警方与普通公民之间缺乏经常性的联系”[12]91,92。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通过治安主体多中心格局的设计,能充分调动农村社区资源,可以突破单有政府包办所产生的资源困境;治理是以互惠合作为基础的网络协调机制,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力,而是主要通过吸收村民、民间组织的力量参与到社区治安中去,通过国家、村民和民间组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提供治安产品,这可以满足村民对治安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消解警察的“被围心态”。
(三)村民自治制度给农村社区治安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框架
首先,村民自治是治安治理一种很好的实践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就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形成了村内的自治运行机制。农村社会不仅有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还有负责议事、决策和监督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13]35。村里的大事由全体村民或者他们的代表集体商议决定;然后由村委会负责贯彻执行;执行后再向村民公布,接受群众的监督。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也从过去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变为现在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可以说,村民自治是治理理论一种很好的实践形式。其次,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为中国农村社会治安治理提供了基础。在体制之下,国家吞没社会,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延伸到每一家农户,支配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强制性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取代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及家族组织被瓦解,没有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后,国家从农村的社会空间里退出来,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空间。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乡村民间组织的数量(包括已登记的和尚未登记的)已达300多万个,约占全国非政府组织总数的2/3以上[14]。社区内的民间组织填补了国家权力退出后的真空状态,型构了各种关系,启发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自己管理自己,自发或自觉从不同层面维护社区秩序,实现社区自组织和稳定。因此,大量的社区民间组织是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基础。再次,村民自治制度使得农村治安防控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协调、融合。根据规则和规则体系的起源,农村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规则可以划分为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内在规则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变而来的规则和规则体系,农村社会的习俗、惯例等伦理性规则和乡规民约等都属于内在规则,违反这些规则会受到农村社会权威或全体成员的惩罚或自己内疚。外在规则是指国家通过理性设计出来的,表现为成文的法律、条例、规章等,外在规则是外在于农村社会的,是强加在农村社会之上的,其规则的违反会受到政府诸如警察等正式权力机构的惩罚。在农村社会,长期以来,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之间形成冲突和紧张:外在规则由于是外加的,没有受到农村社会的认可,内在规则也不被政府所重视。这种紧张和冲突使得政府的控制力量进入不了乡村,使得外在规则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形成农村社会的一种“分裂的整体”社会秩序的格局。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的运行所产生两种秩序颇类似于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所产生的紧张和冲突也使得农村社会越轨行为大为增加,因为受正式规则所惩罚的,可能正是内部规则所赞赏的。朱晓阳认为这仅是一种“法律的语言混乱”,是文化难以移植的表现[15]。因此,为了有效维护社会治安,我们要克服这种紧张和冲突,使得农村各种各样的规则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16]183。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使得内在规则如乡规民约具有了合法性,提供“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也给内在规则和正式规则的协调和融合提供了民主的框架。
二、农村社区治安的治理路径
因此,根据“治理”和“善治”理论,我们对农村社区治安防控设计时,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安主体的多中心格局及其间的协调
第一,要积极培育和引导农村社区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民间组织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组织,如村委会、共青团、妇联等;二是行政权力推动产生,而由民间主导的组织,如治安联防队;三是民间自发生长出来的组织如庙会、宗族组织等。对于二三种类型,农村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积极培育和扶持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关的民间自治组织,使之尽快发展起来,要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使之参与到各种社区组织中去。第二,要注意治安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首先,各治安主体之间是平等伙伴关系。在多中心治理视野下,主体多元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主体间的平等性。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每一主体的活动既相互独立,又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其次,各主体间形成功能耦合的圈层结构。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公安派出所要发挥引导作用,是维护农村社区治安的外在、最为重要层次力量。吉登斯认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象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12]89。正像所有的民主化进程一样,与它们的好处相伴而来的必定还有一连串的不利后果。如果不以一种权力的“向上”移交来加以平衡的话,权力下放很可能会导致分裂[12]82。因此,多中心治理既要克服政府和公安机关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又不能放任不管,而是有放有收,要积极做好农村社区内部治安资源的动员者、指引者、合作者、促进者。治保会、治安联防组织等是社区治安的中坚力量,处于圈层结构的中间层次。治保会、治安联防组织一方面要做好派出所的帮手,发挥其职能,成为维护社区治安的硬性力量;另一方面要引导、协调社区内其他组织,使其他社区组织共同一致维护社区秩序。最内层是社区内其他各种组织,在其自管理和活动范围内自发或自觉维护社区治安,主要起着社区关系、社区道德以及良好风尚的维护作用。三个圈层的治安主体功能耦合,最内层具有软约束的基础性作用,越向外,功能越正式,强制性越强,三层形成有机整体,共同维护社区治安。
(二)正式规则的设计、安排和执行要注意和农村内生规则的协调、整合
如上所述,农村社区的规则可以分为内生规则和正式规则。首先,正式规则的推进和执行一方面要注意和农村社区内生规则的协调,尤其是主要针对农村社会法律法规,要防止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另一方面,要积极普法宣传,积极引导农村社区内生规则如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制度的协调。其次,农村社区中的村规民约一方面要注意和正式规则的衔接和协调;另一方面,村规民约的制定在不与国家法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情况下,要充分考虑到社区风土人情,尤其侧重维护社区良好传统风尚,避免把村规民约制定成完全是对国家法律制度的执行细则。第三,农村社区治安维护中要以调解为主,要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因为调解方式较为灵活,可以充分调动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规则和关系资源。一方面调解主体可以是多元主体,既可以是行政主体的调解,又可以村委会、妇联、共青团等“官民二重性”的组织调解,还可以是社区内形形色色的组织如宗族组织的调解等和个人如邻里亲友的调解;另一方面,在调解规则上也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很好考虑到“国法”、“天理”和人情之间的协调,尽量避免正式规则的生硬执行①。
(三)农村社区治安治理要密切农村人际关系
密切的关系网络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实现治理的基础。贺雪峰和仝志辉借用涂尔干的社会关联,从处于事件中村民的所具有的行动能力的角度来关注村庄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对治安治理的重要意义。从农村社区治安的角度看,社会关联是社区居民遇到违法犯罪的侵扰和危害时,动用各种社会关系以避免侵扰和危害的能力。贺雪峰和仝志辉认为:“村庄社会关联构成了村庄秩序的基础,村庄秩序状况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的表征。”村庄社会关联具有“建设性功能”和“保护性功能”[5]。高度关联的村民们的一致行动对地痞的构成威慑,能有效对付地痞的骚扰,能够邻里守望,互帮互扶,确保一方平安。由此可见,社会关联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资源。如湖南省炎陵县船形乡东河村,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零发案的治安传奇,究其原因,与“和睦相处,守望相帮”客家文化密切相关。当下,我国农村社会人与人关系越来越淡漠化,而契约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因此,我们要积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动员组织农村社会力量,举办灵活多样农村公共活动,密切农村人际关系,提高社会关联度,进而提高治安治理绩效。
作者:何军张波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江苏警官学院侦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