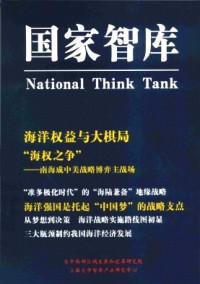国家刑权力调整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国家刑权力调整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内容提要]两权公约对我国刑法的影响是多个层面的,既包括对我国刑法规范的范式改造,也包括对刑法伦理精神的重新定位。而目前理论讨论过程中过分注重前者。我们认为,语词的相通只是相对的,由于语言的共融性,公约作为一个文化规范与我国现行的刑法规范乃至古代的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是符合的。但这并不能昭示法规范便与文化规范相吻合。在规范形式一致的情况下,其精神是分立的。公约的精神在于对包括国家刑法在内的一些国家强行法的重新定位,即刑法的意义首先在于限制国……
我国政府于近年来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近期则正在酝酿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尽管两《公约》本身不直接属于国内刑法规范,但以保障人权为使命的刑法,与公约存在实质的竞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我国代表就指出:“依法治国的实质就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在加强立法、普法和执法监督方面,特别是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修改,极大地完善了刑事司法工作中的人权保护”。(注:参见200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我国代表李保东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有关讲话。)这种相通性决定了《公约》将可能对我国刑法规范的价值进行改造,对刑法范式冲突进行调整。也正因为如此,《公约》对作为部门法的刑法理念启示意义是显然的。
《公约》与刑法的竞合——对公民固有权利不可侵犯性的设定
就刑法与《公约》的关系而言,体现了一种文化规范与法规范渊源关系。《公约》作为一种国际条约,是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公约》作为一种文化规范,应该是刑法的渊源。刑法作为法规范,一般被认为是国家观念的表达形式,而《公约》所昭示的文化规范则宣示了对公民权利的一般设定和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公约》对法规范的指导性和适应性对于缔约国而言是普遍的。原因在于:
其一,《公约》尽管带有一定的区域价值观的色彩,但大多揭示的是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以人权的普遍性是可以接受的。对此,主席与端士人士德赖富斯会谈中曾指出:“中国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时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社会制度不同,促进和保护人权必须与各国国情相结合,而不可能都遵循一个模式。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已加入17项国际人权公约,并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将在认真、深入研究之后正式履行批准手续。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问题,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注: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3月26日第1版。)我们认为,主席的论述包含以下的内容:首先《公约》中所涉及的内容体现了普遍性的人权,包括生存权与发展权,同时包含了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其次,人权的普遍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应当得到尊重的,只不过实现和保障的途径和模式存在差异。《公约》内容带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特征,但如何外化为法规范,尤其是刑法规范则存在方式区别。
其二,《公约》中大多数公民权利的普适性、基础性决定了《公约》缔约国将这种文化规范落实为刑法规范的必要性,这将是缔约国签署并加入《公约》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刑法作为规定公民最基本、最普遍权利的规范,其保障的权利内容与公约具有相通性。两《公约》作为人权法的渊源,对于法规范的缔造和发展存在着参照意义和认同意义。根据人权条约的规定,所有人不分性别、种族、肤色、宗教、语言、国籍、社会出身,等等,都有权平等地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缔约国有义务采取立法和其他措施,保证其领域范围内的所有人享有这些权利;在他们的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有权得到行政和司法的救济。国际人权法禁止种族灭绝、种族隔离、贩卖奴隶、施行酷刑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它们被认为是刑事犯罪,缔约国有义务予以惩罚。从上述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于缔约国而言,在承诺对公约存在信守义务的同时,存在着通过立法方式将这些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达成共识的文化规范物化为法律规范的义务。刑法作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操作性规范,忠实体现公约内容的义务是不言而喻的。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公约》与刑法规范存在着法律和文化意义上的双重渊源关系。
对《公约》的规定进行整合可知,《公约》始终贯穿着权利的法制性特征以及权利的平等性内容。而我国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同样遵循了上述基本准则,明确地在刑法中设定了符合现代法精神的一些原则和规范,与《公约》的文化内涵和目的具有较大的竞合,体现了刑法对人权普遍性的重视,体现了刑法对国家刑权力的制衡和规范,最为显著的表征是刑法形式上将罪刑法定原则和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的条文化。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罪刑法定原则被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规范加以规定,在直接涉及刑事法律规范的条文中贯穿该原则的内涵。如该《公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该《公约》第十五条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犯罪者,不得据以认为犯有刑事罪。所加的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规定。如果在犯罪之后依法规定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犯罪者应予减刑。”除上述直接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之外,其他的条文中始终将法制标准作为国家剥夺和限制公民权利的临界点,这实际上正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多元体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强调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承诺,更为重要的是罪刑法定原则为我们揭示了刑法新的意义,即刑法显示了法律的终极关怀——法律始终应该是国家权力的制衡工具。
适用刑法平等原则是我国1997年刑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形式竞合的又一基本原则。人权的平等性是人权普遍性的一种体现,它表达了人类从身份文明向契约文明发展的社会进步,同时也是当今公民政治、社会、文化权利的最为基本的内容,更是人类法制文明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公约》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公民平等权利的国际公约。《公约》中对身份的摒弃固然是平等权的内容,但诸如家庭权利、自由权利、儿童权利、法律上的人格权等权利的规定也都间接体现了《公约》对平等权确认。我国1997年刑法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其基本形式与《公约》的内容基本相同,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将平等权作为公民绝对权利的设定也是一致的。
但是《公约》作为外部性的约定,由于规范生成方式的自愿性、规范内在价值的文化差异性以及规范保障形式的弱效性特征,显示了与国内刑法的不同特点,如何进一步加以协调,将将是加入《公约》后需要应对的问题。
刑法意义的设定——对国家刑权力任意性的调整
如果承认了《公约》作为刑规范存在的理论渊源,作为刑法价值取向的选择基础,《公约》势必对刑法的意义提出新的要求。
现有的刑法理论大多将刑法功能界定在本体意义上,往往从法律文本主义观点出发谈论刑法的功能,将刑法作为国家强制性规范,将刑法保护功能的存在作为刑法功能的基础。刑罚是一种“政治约束”,在“自然状态”之下,出现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对立时,刑罚才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者而发挥作用。随着我国刑法价值观念的转型,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日益凸现,但是在强调人权保障功能的同时,很多人仍然念念不忘以保护功能作为基础。人权保障功能的弘扬不仅是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更包含着与立法权力以及司法权力对抗与限制。但保障功能的弘扬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发展,并不足以体现刑法整个基础理念的转型。《公约》所包含的思想为重新界定刑法的功能提供了另外一种境界。《公约》赋予了公民生存权利的至上性,包含生命权、免受酷刑权以及免受奴役权等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公约》还赋予了公民平等、自由等多项政治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足以保证权利不被践踏,并不足以说明权利的权威性,并不足以对抗国家权力被无休止地使用,《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应当保障公民绝对的生存权利,而对于相对的公民政治权利,只有在紧急状态或其他的相当情形之下,缔约国才能够科减《公约》义务,对公民的政治权利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所以,与其说《公约》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公约,毋宁说是制约国家权力的公约。《公约》的精髓在于:就形式意义而言,《公约》是要求国家对公民权利予以珍视和保障的作为型规定,就实质意义而言,《公约》是一部限制国家权力扩张的不作为性质的约定。
那么,作为实定法的刑法是否同样具有上述特征呢?传统理论主要将刑法作为司法法加以看待,因而答案是否定的。其将刑法的功能界定在防卫社会的基础之上。随着刑法价值观念的转型,刑法人权保障功能日益得到珍视并被弘扬。但是,在将刑法界定为一种积极的防卫或保障的同时,传统理论仍然将刑法的实体真实和实质理性奉为圭臬。其实无论是《公约》还是实定的刑法,其共同的功能是赋予国家刑权力的同时,规范、制约着国家刑权力的行使,使得国家刑罚特权有所为而不为。将刑法界定在防卫社会的角度则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隐含了给予国家无限制地动用国家刑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将国家权力赋予先验合理性的色彩。实际上,“在西方法学史上已经有许多学者反对将法律视为国家立法的唯一产物。他们认为应当从社会本身、组织化社会和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寻求法的真谛,他们在承认法的强制性的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强调法的非强制性。”(注:李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任何司法法都具有法律的规范性特征,但这只是法的任务的外在体现,并不足以说明法的功能和意义。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体现了对刑法功能认识的阶段性成果,但是人权保障的功能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唯一的。正象《公约》直接指向国家权力一样,人权保障功能只是刑法对国家刑权力的一种制约方式和途径(或者说是其中主要的一种制约方式),只能是一种刑法追求的阶段性结果,不能成为终极目的。
刑法规范对于《公约》中文化规范的认可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刑法是对《公约》中的保障人权进而制约国家刑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信守和承诺。刑法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制裁和预防犯罪,体现国家的意志,其实际上是国家刑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契约性或妥协性的结果,是国家对社会成员限制国家刑权力的承诺。而《公约》则是缔约国对限制国家刑权力的承诺。正如德国刑法学家宾丁所说,刑法的意义在于“是规定国家和犯人之间关系,而将具有刑罚权的国家置于一方,将依刑法而逮捕的犯人置于另一方的关系的法,今日之刑法是规定国家的刑法义务的发生、内容及其消灭的一切法规。(注:[日]竹田直平:《法规范及其违反》,有斐阁1961年版,第90-91页。)”刑法的意义在于通过设定国家与犯人的关系以及其他公民的权利关系,对国家的国家刑权力内容法定化、确定化、规格化,避免国家刑权力的任意行使。这同长期以来主流刑法理论对刑法的界定界不同的。规范刑法主义观点认为,刑法是国家立场的体现,是国家意志和价值的体现,这种观点特定情形之下带有合理性。但这种国家主义刑权力观并不带有普适性。刑法作为法规范,“就其效力来说,依赖于广大人民对其基本先决条件的接受。人民的接受,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机构是法律贯彻的决定力量。”(注:姚建宗:“信仰:法治和精神意蕴”,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转引自周光权著:《刑法诸问题的新表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刑法不应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而应当成为制约国家刑权力的宪章。
权力的无节制性是普遍存在的,由此权力的制衡性是必要的。国家刑权力作为一种剥夺性的权力,对其制约和制衡尤为迫切。不仅《公约》昭示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实际上即使是古代法中,刑法作为国家刑权力的制约特征已经昭然若揭了。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即阐述了成文法产生的缘起,即在古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命过程有极大部分都生活在族长的专制之下,他的一切行为实际上不是由法律而是由反复无常的一种统治所控制着,而法律的形成则是对无休止特权现象的校正。“在我所提及的几个国家中,到处都把法律铭刻在石碑上,向人民公布,以代替一个单凭有特权的寡头统治阶级的记忆的惯例……诚然,贵族们似乎曾经滥用他们对法律的独占,并且无论如何,他们对法律的独占权力阻碍了当时西方世界开始逐渐普遍的那些贫民运动获得成功”。“‘十二铜表尖’以及类似的法典赋予有关社会的好处,主要是保护那些社会使得他们不受有特权的寡头政治的欺诈,使得国家制度不致自发地腐化和败坏”。(注:[英]梅因著:《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11页。)梅因所论及的法律形式变更在我国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从刑律深藏于府、威不可测直至“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注:《左传·昭公六年》)将律例布之于众,实际上就是限制国家(或者执政阶级)滥用刑权力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法律纷争也正是围绕国家刑权力的限制而展开的。孔子对晋国铸刑鼎的批评正是基于成文刑法的公布使得特权被大程度的约束。“晋其亡乎?失其度乎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衍,所谓度也……尽弃其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以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再以我国近代刑法改革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具有某些继承性和保守性,但刑律的变更内容以及折射出的刑事法律思想则是针对特权现象的。沈家本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提出了刑法化除畛域,一体用科的观点,反对“刑有等级”,反对“比附援用”,主张“法律平等”和罪刑法定(注:《寄@①文存·载判访问录序》)。应该说成文法的公布和法律的近代化,是我国古代传统刑法最重要的解体和转型时期。不仅刑法的形式替代十分明显,而且刑法的价值取向替代更是法律转型的实质,但是在这种从结构形式至内容实质的替代中,唯一没有被替代并且指引刑法变革的就是刑法作为制约国家特权滥用的特性。所以我们在追溯法律的变更尤其是刑法的变更过程时,可以发现这些带有社会现实合理性的变更蕴含了一种社会内在要求改进的意愿。也就是说,刑法的历史创立和发展存在着理性动力,即刑法为制约国家特权(或者说刑特权)而产生。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刑法与当代刑法对于国家特权的限制表现为不同的实质,在古代法刑法中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表现为身份制约,在近代刑法中国家特权限制表现为一种契约限制,刑法是一种契约调解的结果。也就是说,刑法的发展同样也经过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过程。
从《公约》视角看死刑存废的合理性因素
死刑的存废问题不仅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乃至在世界范围之内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而无法回避的问题。近些年来,有关死刑存废的文章、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我国签署(尤其是批准)《公约》之后,死刑的存废问题将由过去的国内刑事立法的理性与非理性、异质法律冲突的选择转变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整合。死刑的存废问题也不再仅仅是一个从传统的防卫社会和人权保障角度进行探讨的问题,国民确信的传统认可以及对于重罪的预防和打击不能再成为死刑存在合理性的充分理由,国民确信本身的可定义性、真实性、确定性等需要重新审视,死刑对于某些犯罪的打压和预防作用已经被证明不起作用(至少可以说在耗费巨大的司法成本之后效果并不显著)。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的约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并且不能违背公约的有关规定和防止违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死刑的执行必须经合格的法庭最后判决。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第六条的任何部分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公约》第六条虽然直接指向对生命权的捍卫,但其意旨在于对国家刑权力的控制。这种控权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剥夺他人生命的国家刑权力进行剥夺和限制。二是对于缔约国在承诺遵守条约的范围内实施的国家刑权力进行限制。以此为切入点,死刑的设置一直是被作为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加以对待的,是作为国家用刑的一项权利而被赋予合理性的,而没有看到刑法中对死刑的设定是作为限制国家死刑用刑的权力而设置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死刑的扩张倾向是难以避免的。以死刑核准权为例,新旧刑法均规定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均由最高法院核准,但现实状况是,一些死刑的复核权力仍被下级法院所行使。其结果是高级法院既是二审法院,又是具有死刑核准权的法院。国家刑权力被集中在一个法院的不同部门内的同时,失去了对国家刑权力的外部制衡。
一种观点认为,死刑在我国当前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重典成为必然,死刑较大范围的适用和具有合理性。我们认为,此观点是似是而非的。死刑存在并扩张对于治安形势好转的作用微乎其微。再则,《公约》所蕴含的国家刑权力制衡的理念也为我们对于死刑的态度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那就是:废除国家适用死刑的刑权力或者在最大程度限制权力扩张的基础上赋予死刑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在后一种情况之下,死刑的适用是受到极大制约的,是极为审慎的。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现实状况是,对于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制度根源、思想根源研究不足,刑法的功用被过分夸大,希冀通过刑罚甚至死刑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念是极需要斟酌的,在体制本身或缺、观念没有完全更新、司法水平不尽人意的情形之下,死刑被最大程度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国家刑权力主体的本身权力已经制约失范(注:在最近重庆发生的大学生赵川“”事件中,令新闻记者震惊的已经不是执法人员的刑讯逼供问题,而是记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有多个证人证明赵川不在现场的证据时,警察人员居然十分自信、轻松地说:“赵川有证人,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万人证明赵嫖过。”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第9版。),才更有必要从国家刑权力本身进行约束。所以在法律对权力监控规范完整的前提下,死刑的存在或许并非没有合理性。但在当前权力监控不完善的条件下,更应该从制度上对死刑适用程序和范围进行极为严格的限制。否则死刑的消极作用将会非常突出(注:2000年7月15日《新民晚报》第3版刊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当事人杜培武因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被昆明中级法院判处死刑,1999年10月被云南高级法院判处死缓,最近昆明警方因破获杀人劫车系列大案,查获元凶。2000年7月11日云南高级法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相对于当地1997年出现的类似判决情况,这实际上已经无独有偶了。我们在认可这样的错案追究的同时更产生了深深忧虑,缘由不是因为现象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不是因为错案追究只能缘起于元凶的查获,而是在于刑事法律规范和价值观念没有真正转型和完善的前提下,刑权缺少制约机制的前提下,死刑的消极性是十分明显并且是无法遏制的。),对于大量的经济犯罪更是如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