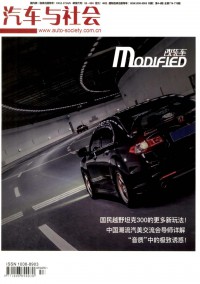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口增长;二孩政策;经济意义
目前,中国缓慢的人口增长速度,带来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社会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楼市泡沫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开放二孩政策能够在合理范围内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同时又保证人口在持续增长的状态,缓解老龄化情况,缓解社会经济因人口增长缓慢带来的问题。
一、全面开放二孩的相关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每年呈递减规律,我国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相较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压力、资源压力,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劳动力短缺情况会进一步导致人口增长率降低,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严重,我国人口结构失衡,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出现。相关人士指出,分布单独二胎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对社会劳动力的减少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要通过全面开放二孩正政策才能够缓解危机。
二、全面开放二孩的必要性
1.人口结构趋于正常化
按照国际标准,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指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数量达到社会总人口的10%及以上,或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达到社会总人口数量的7%。按照这一标准,本世纪初,我国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正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导致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社会老年人比例不断提高,我国社会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若二孩政策难以顺利实施,不能够全面展开,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速率的缓慢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的人口构成。我国社会老年人比例会进一步上升,青少年的比例会不断下降,中国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供养老人以及小孩,对社会经济、家庭经济都会带来重大的不良影响。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能够提升社会青壮年的比例,提升社会劳动力数量,对劳动力供养情况得到显著的缓解,对改善社会经济、家庭经济都有着重要意义。
2.经济发展需求
社会劳动力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才能够进一步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我国社会劳动力人口比例会在一段时间后得到显著的提升。只有劳动力数量的增多,才能够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科技水平之下,提升我国的社会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从而全面的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另外,二孩政策的推行,能够化解社保空账危机和楼市泡沫,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经济市场更好的发展运行。
三、全面开放二孩的经济意义
1.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社会人口众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人口红利的支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这其中人口红利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但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缓慢,我国的人口红利不断在降低,甚至有专家预测人口红利即将会消失,中国社会即将出现“未富先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极大的威胁。而开放二孩政策能够有效缓解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保证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主要体现在我国生育率的降低,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国情不相符,造成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隐形减缓”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二孩开放必然能够缓解人口红利下降设置消失的情况,避免经济下滑。
2.化解楼市泡沫
楼市泡沫现象是指房价不断上升,实际房价与社会实际可承受的房价不协调,出现了“泡沫假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严重虚高,并且这一泡沫现象正在不断的向中小型城市延伸。以北京为例,2004年至2014年,尽管政府已经对房地产企业以及二套房等等做出了各种缓解措施,但十年内北京房价增长幅度还是高达四倍有余,城市居民住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住房作为群众生活的必须物品,对社会和谐、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对于提升人口增长,促进居民住房实际需求有着重要意义。而住房实际需求的增加,是稳定房价的重要手段,能够解决目前我国严重的楼市泡沫的问题,对于稳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3.解决社保空账危机
为了解决我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带来的巨大的供养负担,也为了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社会保障制度开始逐渐在我国运行。然而我国社保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发展速度也相对比较缓慢,与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速度严重不符,造成了我国社保资金流入减少,甚至出现负增长,出现了严重的空账危机。而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情况,缓解社保资金的流出速度,缓解空账危机。
四、总结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人口增长息息相关,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目前学术界依旧争论不休,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孩政策的开放,必然带来社会劳动力比例的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存在众多积极意义值得深究。
参考文献:
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宏观影响 辽宁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渐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阶段。辽宁省作为全国的工业基地,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样日益明显。据辽宁省统计年鉴(2009)显示,辽宁省199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02%),提前全国5年,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来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从宏观层面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超前发展态势所产生的影响已渗透到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居民储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文化、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良性运行
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经验表明,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是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良性运行的关键性因素。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体现出来。已有研究大多显示,辽宁省从1982年开启“人口机会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为“人口暴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仅从劳动力资源的整体规模来分析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最终取决于适龄人口的“有效” 劳动供给。首先,从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看,目前辽宁省劳动力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1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41岁,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别提高4岁、8.1岁和11岁,劳动力结构老化趋势明显,限制了人力资本活力的发挥和有效劳动供给。其次,在劳动力参与率方面,随着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低年龄组人口与女性人口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辽宁省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数字为证,2000年,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个百分点。诚然,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劳动力增加,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劳动供给减少了。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在老年产业中就业,另一部分则是在家里和医院里照顾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特别照料和护理。
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人口现象对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的辽宁省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
经过多年努力,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从协整比例关系为主转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为短期内辽宁省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都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也在经济社会承载范围之内,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之青壮年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同时,因人口老龄化而兴起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龄产业也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具备吸纳从一、二产业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顺应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又阻滞着辽宁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刘柏霞(2009)通过选取1978—2005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辽宁省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系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因削减了劳动力人口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投资资金供给的相对减少,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处于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阶段,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而老龄劳动者无论在身体素质、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者低得多,对新产业、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水平变化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认为个体的储蓄倾向在一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加总的国民储蓄率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国民储蓄率会随之降低。经验也似乎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储蓄的。但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率却增势不减,使得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通过对历年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辽宁省的总储蓄金额和储蓄增长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间储蓄增长率的波动趋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辽宁省进入老龄化社会为界分成两段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总储蓄金额增加的同时储蓄增长率却在下降。1995—2011年间,辽宁省经济增长率在波动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较快,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储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断趋缓(见图1)。可能的原因在于,辽宁省目前的劳动力人口还比较充裕,老龄人口的消耗应该赶不上储蓄的增长,未来一段时期辽宁省储蓄额肯定还会增加,但增长趋势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来越缓。
四、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波动
理论上讲,人口消费水平与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需求。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作为纯消费者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能够推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上升。不过,在消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又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会使家庭的从业人口数变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大,进而导致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降低。从老年人口个体来说,其往往更加节俭,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费支出将会低于年轻人口。有关研究也表明,儿童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长远看,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未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用于社会交往方面的消费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医疗和护理方面的消费需求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当然,老龄人口的增多同样预示着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体正在迅速崛起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市场消费势力,从而带动和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产业——老龄产业,为老年市场提供无限商机。因此,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是多面向的,最终取决于一时一地的老龄化程度及其发展速度。
纵观辽宁省1980—2011年的消费变化情况,居民最终消费额每年都在增加且总量增幅明显,消费增长率1994年曾达到最高峰28.79%,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自199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消费增长率呈现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现逐渐回升(见图2)。可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龄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对消费需求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反而是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执行下少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较大。经验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消费将随之下降0.417%(陈晶、朱天星,2011);当前,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也并未强烈地改变消费增长的趋势,但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带来了显著影响,抑制了衣着、家庭设备与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2]。
五、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负担
养老保障负担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又一直接后果。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社会保障基金在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还得应对支付额不断增加的现实需求,两方面的挤压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沉重的社会负担。辽宁是东北三省的龙头,也是受深层次体制因素和结构性矛盾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之一,正处于老工业基地改造之中,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不仅增加了政府养老保障金、医疗保障金等方面的开支,加重了为老设施的社会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临改善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与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贫困的艰巨任务。养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加快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2010年,全省参保离退休人数472.7万人,比2000年增加191.7万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长速度5.34%;同期,养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亿元,增加585.3亿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长速度16.11%。养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参保离退休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医疗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镇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464.1万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员医疗费用支出139.3亿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可以预计,今后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数量不断增大且比重不断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经并将继续对辽宁省社会保障体系构成沉重负担和压力。
六、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文化变迁
自古以来,亲子关系都是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赡养父母是子女天经地义的职责和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由此孕育出来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社会化”特征明显,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4]。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换,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ageism)倾向[6]。2005年10月,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20余个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随着农村建设速度的加快,中青年农民中“重小轻老”现象非常严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无法得到忙碌子女们的生活照顾,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不适现象也已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对多姿多彩的社区文艺、“夕阳红”般的大众传媒节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会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社会老年文化的氛围会逐渐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预示着新一轮社会文化的变迁。
七、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安全隐患
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7]。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龄人口逐渐由个体形成群体,老年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由零散的碰撞逐渐演变为集中的社会冲突。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格局、消费需求结构、经济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老年群体的利益诉求等)很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所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将会对社会安定产生极大的打击。
参考文献:
[1]郭熙保等.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持久性影响[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7—17(06)
[2]王舒,李旻.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1(33):17—18
[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4]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5):48—50
[5]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6):131—149
[6]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J].人口研究,2008(4):57—65
[7]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and Neil Howe. China’s Long March to Retirement Reform: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ited [R] .Washington: CSIS Publications. 2009.3—17
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范文第3篇
德国目前是欧洲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被戏称为“欧洲的养老院”,因此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一直是德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2012年10月30日,中德老龄问题研讨会在曼海姆召开,两国近60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出席。德国前劳动部长、我会老朋友瓦尔特·李斯特作题为“德国人口形势发展及其对德国社保体系影响”报告。我会邀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教授对“中国老年人口的居住、健康与照料安排”进行介绍。中德报告人还就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中德养老体制比较、居家养老、城市规划中的老年社区、中医在老年护理上的优势以及养老保障类住房储蓄等题目进行了交流。
德国的老龄化进程从19世纪末开始,持续近百年。德国是“老年社保制度”的摇篮。1889年俾斯麦建立的“养老及伤残险”是现代社保制度的雏形。但随着德国社会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低出生率和寿命延长不断加剧人口老龄化进程,德国优越的养老保险体制遇到严峻挑战。多年来德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各界积极探索,并积累了有益经验。这对于“未富先老”且老龄化程度急速加剧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德国的社保改革措施之“李斯特养老金”和“护理险”
2002年,在时任德国联邦劳动部部长李斯特的倡导下,德国进行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保改革。具体包括削减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的福利待遇、稳定保险费支出水平和发展新型的私人养老保险。在这一背景下,具有补充性质的“李斯特养老金”计划出台,并成为继国家法定养老保险、企业附加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以外德国养老保险体制的第四支柱。“李斯特养老金”运行方式为投保人或家庭将年收入的4%拿出为“李斯特养老金”储蓄,而国家将对此进行补贴(夫妻每人每年可获补贴154欧元,孩子20岁之前每人每年300欧元)。
德国社保体制上的又一重要改革为1995年强制推行的护理险,规定所有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都须参加护理险,费率为收入的2%。护理险伴随人口老龄化过程发展起来,对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减轻被护理人员家庭经济和精神负担具有积极意义。
德国养老新模式之“以房养老”
作为对“李斯特养老金”的补充,德国在2008年推行了“李斯特住房补贴”,即个人或家庭在购买自用住房时,其贷款或储蓄均可得到国家补贴。这项政策性住房金融产品将住房储蓄的手段与养老保障的目的结合起来,受到德国人欢迎。目前约100万德国人签订了“李斯特住房补贴”合同。该计划的核心是,使老年人不必从退休金中支付高昂房租,而在自有住房中安享晚年,或将自有住房出售后支付养老院费用,缓解日趋严重的老年贫穷问题。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德国人传统上以租房为主的居住习惯,开始接受“以房养老”这种模式。
德国社会各界的努力
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老年贫困;社会养老保障;社会救助
据2005年全国l%人口抽样调查,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其中,近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我国将于2010年迎来老年人口的大爆发,老年人口年增长数量将达到800万人以上,到本世纪中期,全国老年人口将达4亿,其人口比重将升至20%以上。并在此高位上持续十年左右。换言之,我国正面临老龄化浪潮汹涌澎湃之势.社会老龄化中的民生问题亦日益凸显。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最为艰辛,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在演变为新的贫困群体。
一
与先行的老龄化国家比较,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有三大特征:一是时间短、速度快。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历程,并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快速推进。二是数量大、延续时间长。我国现有老龄人口已占到世界老龄人口总量的20%强,占亚洲老龄人口的50%,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的社会还将延续半个多世纪。三是未富先老。欧美国家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的,有财力和实力应对人口老化,而我国则是在人均l000美元时就提前迈过了社会老龄化的门槛,老龄社会的不期而至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有这些特征,在我国现实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较之城镇表现得更突出、更严峻,也更具危险性。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人城镇.农村留守人口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儿童组成。据对湖北省若干县的调查,老年人口约占农村留守人口的30%.该比例大大超过我国人口老化的平均水平,使得农村人口老化速度远远快于城镇。加之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村老年贫困问题。五普资料表明,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占绝对贫困人口的10%一14%,农村则高达25%一31%。可见,农村人口老化正在滋生着新的贫困群体.该群体不仅随人口增加而扩展,还随其年龄增长而加大贫困的程度。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农村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他们的生存状况往往被忽视,他们的愿望和呼声往往无处表达.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解决他们的困难应成为整个社会和各级政府必须关注的民生热点和焦点,消除农村老年贫困已成为当今社会反贫困的当务之急。
二
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客观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一是劳动参与方式。五普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城镇老人占87%,农村占50%:继续参与劳动的老年人为33%。众所周知,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我国城镇职工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大多都享有养老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则因维持着传统的劳动参与方式,没有建立起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是通过一家一户的劳动为自己提供收入保障.这种劳动方式没有年龄界限,一般情况下.是否退出劳动只能视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健康条件而定。有调查显示,城镇有七成老人能享受到离退休金,而农村只有4%的老年人拥有离退休金,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农业劳动收入的相对低下,刚刚满足温饱的农村家庭及其老年人难以顾及养老积蓄。这使得农村老年人退出劳动的时间更迟.参与劳动的时间更长。尽管现实农村老年人大多拥有承包的土地,从理论上可视为养老保障,但因为老年人丧失的正是劳动能力,加之土地流转难,使其在体力日衰后难以维持老年生活,而更易陷入贫困之中。由此可见,对于步人老年的劳动者而言,因劳动参与方式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就是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欠缺。
二是农村养老保障方式。养老保障方式可分为三个层次:社会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保障和自我养老保障前述城乡劳动参与方式不同,决定了现实的中国农村普遍缺乏社会养老保障。而通过储蓄和购买养老保险的自我保障虽然有助于老年生活.但因农村经济条件普遍欠缺,多数农村老人一生无积蓄或储蓄甚少,养老的自我保障仅限于少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和个人。只有家庭养老保障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农村养老方式的主体。
现实农村的家庭养老是传统养老方式的延续。虽然当前的农村老年人大多属多子女家庭,具有传统意义上养老的家庭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但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在急骤的社会变迁中遭受到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表现为,家庭的小型化使得老人与已婚子女分家.以及人口流动导致“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家庭养老长期以来完全依赖于个人自觉和风俗道德约束,随着农村代际鸿沟因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差异而加深,老年人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被边缘化,加之老年人维权意识淡薄,致使农村歧视老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等问题较突出,虐待、遗弃老年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子女甚至一味将自己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和社会,使得农村“有儿有女的老人不如无儿无女的老人有保障”(“五保”老人可享受社会救济和福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尊老敬老助老的和谐社会氛围缺失。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启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其待遇水平较低.能享受的还只是极少数人,大量老年贫困人口的生活仍然艰难,维系和支持家庭养老已成为农村新的社会问题。
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地理;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参考文献:
[1] Skinner M W, Cloutier D, Andrews G J. Geographies of ageing: Progress and possibilities after two decades of chang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5,39(6):776-799.
[2] Andrews G J, Cutchin M, Mccracken K, et al.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The constitution of a disciplin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7,65(1):151-168.
[3] Cutchin M P. The Geography of Aging: Preparing Communities for the Surge in Seniors[J]. Gerontologist, 2009,49(3):440-444.
[4] Rowles 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 and aged: Toward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86,10(4):511-539.
[5] Harper S, Laws G. Rethinkin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5(19):199-221.
[6] Hardill I. Introduction: Geographies of aging[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2009,61(1):1-3.
[7] Schwanen T, Hardill I, Lucas S. Spatialities of age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co-evolution of old age and space[J]. Geoforum,2012,43(6):1291-1295.
[8] Andrews G J, et al.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Mapping a 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J]. Geography
Compass,2009,3(5):1641-1659.
[9]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5[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2015.
[10] Kinsella K, Phillips D R. Global aging: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J]. Population Bulletin,2005,60(1):1-40.
[11] Mccracken K, Phillips D R. Internation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s[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36-60.
[12] United Nations E A S C, Escap T P.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5[R]. 2005.
[13] Phillips D R. Agei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M]. London: Routledge,2000.
[14] Warnes A M. UK and western European late-age mortality: Trends in cause-specific death rates, 1960
-1990[J]. Health & Place,1999(5):111-118.
[15]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Geographical studies in ageing: Progress and connections to social gerontology[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7-12.
[16] Davies A, James A. Geographies of Ageing: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Population Ageing[M]. Aldershot: Ashgate,2011.
[17] Bailey A. Population geographies and climate chang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1(35): 686-695.
[18] Goodman A C. Using Lorenz curves to characterize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J]. Urban Studies, 1987(24):77-80.
[19] Bean F D, et al.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mong the elderly[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4:319-355.
[20] Rogers C C. Changes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rural areas[R]. Washington DC,1999.
[21] Heleniak T. Geographic aspect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Russian Federation[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3,44(5):325-347.
[22] Moore E G, Pacey M A. Geographic dimensions of aging in Canada[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2004:5-21.
[23] Hiltner J, Smith B W. Intra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the elderly[J]. Journal of Geography, 1974(73):23-33.
[24] Flynn C B. General versus aged interstate immigration,1970-1986[J]. Research on Aging,1980(2):141-154.
[25] Golant S M. Housing America's Elderly: Many Possibilities/Few Choices[M].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1992:368.
[26] Hugo G. South Australia's Age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Nature[J]. Austra-
lasian Journal on Ageing,2000,19(1):23-32.
[27] Hanlon N. Geographies of ageing: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population ageing[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2013,19(5):645-646.
[28] Golant S M. The residential moves, housing locations, and travel behavior of older people: inquiries by geographers[J]. Urban Geography,1989,10(1):100-108.
[29] Scott P. Urba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J]. The Geographer,1971(18):1-16.
[30] Frey W H. Elderly Demographic Profiles of U.S. States: Impacts of “New Elderly Births,”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J]. The Gerontologist,1995,35(6):761-770.
[31] Mccarthy K F. The elderly populations chang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hange since 1960[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83.
[32] Mchugh K E, Mings R C. The circle of migration: Attachment to place in aging[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6,86(3):530-550.
[33] Lee E S. Migration of the aged[J]. Research on Aging,1980(2):131-135.
[34] Golant S M. Post_1980 regional migration patterns of the USA elderly population[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90,45(4):135-140.
[35] Serow W J. Return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USA:1955~ 1960 and 1965~ 1970[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78(33):288-295.
[36] Litwark E, Logino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1987,25(3):266-272.
[37] Krout J A. Seasonal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J]. The Gerontologist,1983,23(3):295-299.
[38] Rush C H. A survey of winter Texans in the lower Rio Grande Valley, 1982~1983[R]. Edinbury: TX: Pan
American University,1983.
[39] Longino C F. Changing aged non-metropolitan migration patternes,1955~1965 and 1965~1970[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82,37(2):228-234.
[40] Longino C F. Migration winners and losers[J]. American Demographics,1984(6):27-29.
[41] Wiseman R F, Virden M. Spati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intra-urban elderly mig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1977(55):324-337.
[42] Walters W H. Types and patterns of later-life migration[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2000,82(3):129-147.
[43] Milligan C. Bearing the burden: Towards a restructured geography of caring[J]. Area,2000(32):49-58.
[44] Glover J, Harris K, Tennant S. A social health atlas of Australia[M]. Adelaid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Unit,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99.
[45] Cutchin M P. Spaces for inquiry into the role of place for older people's care[J].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5,14:121-129.
[46] Wiles J. Conceptualising place in the care of older people: The contributions of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5(14):121-129.
[47] Rowles G. Place in occupational science: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 in the quest for meaning[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2008(15):127-135.
[48] Brickell K. ‘Mapping’ and ‘doing’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36:225-244.
[49] Andrews G, Phillips D. Changing local geographies of private residential care for older people 1983-1999: Lessons for social policy in England and Wal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2,55:63-78.
[50] Mazzei F, Gillan R, Cloutier D.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on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older adults in a purpose-built acute care dementia unit[J]. American Journal of Alzheimer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2014,29:311-319.
[51] Joseph A, Cloutier-Fisher D. Age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Vulnerable people in vulnerable places[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133-146.
[52] Rowles G D. 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78.
[53] Golant S.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Are We Expecting Too Much?[M]. Montre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2014.
[54] Holdsworth D, Laws G. Landscapes of old age in coastal British Columbia[J]. Canadian Geographer, 1994(38):162-169.
[55] Robison J T, Moen P.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housing expectations and shifts in late midlife[J]. Research on Ageing,2000,22(5):499-539.
[56] Phillips D R, et al. The impacts of dwelling conditions on older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Hong Ko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60(12):2785-2797.
[57] Michael Y L, Green M K, Farquhar S A. Neighborhood design and active aging[J]. Health & Place,2006,12(4):734-740.
[58] Jackson P, Penrose J. Construction of race, place, and na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
nesota Press,1993.
[59] Laws G. Understanding Ageism: Lessons From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J]. The Gerontologist,1995,
35(1):112-118.
[60] Laws G. “The Land of Old Age”: Society'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urban built environments for elderly peopl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3,83(4):672-693.
[61] Rogerson P A. The geography of elderl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1998,12(7):687-698.
[62] Cartier C. From home to hospital and back agai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end of life, and the gendered problems of place-switching health servic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3,56:2289-
2301.
[63] Wiles J, Rosenberg M W. Paradox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anada’s home care provision: Informal privatisation and private informalis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Special Issue,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Canada,2003,28:63-89.
[64] Cloutier-Fisher D, Joseph A. Long-term care restructuring in rural Ontario: Retrieving community service user and provider narrativ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0,50:1037-1045.
[65] Joseph A E, Chalmers L. Restructuring long-term care and the geography of aging: A view from rural New Zealand[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1996,42:887-896.
[66] Fortney J, Chumbler N, Cody M, et al. Geographic access and service use in a community-based sample of cognitively impaired elders[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2003,21:352-367.
[67] Peace S, Holland C K L.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in Later Life[M]. New York: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2005.
[68] Rowles G. What’s rural about rural aging? An appalachia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88,4:115-124.
[69] Rollinson P. The story of Edward: the everyday geography of elderly single room occupancy (SRO) hotel tenant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1990,19:188-206.
[70] Harper S. The kinship network of the rural aged: A comparison of the indigenous elderly and the retired immigrant[J]. Ageing and Society,1987,7:303-328.
[71] Elder G.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4,57:4-15.
[72] Milligan C.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People, Place and Care in an Ageing Society[M]. Aldershot: Ashgate,2009.
[73] Meijering L, Lager D. Home-making of older Antillean 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J]. Ageing and Society,2014,34:859-875.
[74] Cameron L, Forrester J. A nice type of the English scientist: Tansley and Freud[J].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1999,48:64-100.
[75] Watkins C, Cowell B. ‘Mr. Price the picturesque’:Critic, connoisseur and landscape enthusiast[J]. Walpole Society,2006,68:1-77.
[76] Said E.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Digital,2006.
[77] 高月罚吴丹贤,许泽宁,等. 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综述和研究框架构建[J]. 地理科学进展,2015,34(12):1480-1494.
[78] 李日邦,王五一,谭见安,等.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J]. 地理研究,1999,18(2):113-121.
[79] 袁俊,吴殿廷,吴铮争.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7(3):41-47.
[80] 陈明华,郝国彩.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136-141.
[81] 柴彦威,等.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82] 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 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J]. 人口研究,2004(6):53-59.
[83] 高晓路. 城市居民对养老机构的偏好特征及社区差异[J]. 中国软科学,2013(1):103-114.
[84] 于涛方,王瑾. 面向人口老龄化的城市规划应对[J]. 规划师, 2012(09):75-79.
[85] 杨林生,王五一,谭见安,等.环境地理与人类健康研究成果与展望[J]. 地理研究,2010,29(9):1571-1583.
[86] 戴俊骋,周尚意,赵宝华,等.中国老年人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20):4008-4013.
[87] 杨建军,汤婧婕,汤燕. 基于“持续照顾”理念的养老模式和养老设施规划[J]. 城市规划,2012,36(5):20-26.
[88] 詹运洲,吴芳芳.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2014(6):38-45.
[89] 陶卓霖,程杨,戴特奇. 北京市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J]. 地理科学进展,2014(05):616-624.
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