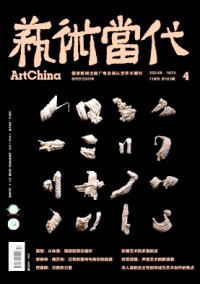当代装饰图案造型艺术研究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当代装饰图案造型艺术研究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内容摘要】研究女书文化视域下当代装饰图案造型艺术的目的在于探究女书这种神秘的图形文字的历史文化元素及其与当代装饰艺术的共通之处,并找到传承女书文化的途径。文章介绍了女书的文化背景,分析了女书的图案造型与当代装饰艺术的共通之处,探讨了女书在当代装饰图案造型艺术中的传承措施。
【关键词】女书文化视域当代装饰图案造型艺术
女书是湖南省江永县地区流传的一种十分特殊的文字,其起源基本可推断为战国时代荆楚、百越地区的古文字体系。这种文字极其神秘的原因在于其“传女不传男”的传播形式,只有江永县当地妇女之间以口头讲述的方法进行小范围的传播,甚至有异性在场的时候都不会进行传授。因此,这种文字又被称为“妇女文字”或者“女字”。不仅如此,由于女书的传授者与学习者数量稀少,且女书只用于江永地区妇女群体内部的抒情或叙事,当某位女书传承人去世时,其生前的女书作品往往被同时焚毁,故女书留传于后世的数量极少,存在的时间也相对短暂。
一、女书的文化背景
女书实际上是古代封建社会处于最底层的妇女阶层为了表达内心情感而创造出来的文字体系。封建社会的妇女由于普遍受“三从四德”等带有性别歧视倾向的传统礼教的影响,在人身自由饱受限制的情况下,往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从江永地区妇女在手帕上绣的歌词中就可见一斑:“中华女子读女书,不为当官不为名,是为女人受尽苦,要凭女书诉苦情”。可见,女书创作与流传的动机其实来源于封建社会给古代妇女带来的沉重压迫,这一极具悲情色彩的历史现实造就了女书特殊的传播形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女书成为荆楚古地特有的女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女书初被创立时,其实与古代女性人人必学的“女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江永地区的女书一般都以刺绣等形式存在,而非传统概念中文字总是出现在纸上。江永地区的妇女在大量织物上以女书作为装饰,缝制背包、背带、手帕等女性专用物品,甚至在当地婚嫁习俗中还保留了“八宝被面”作陪嫁的传统。所谓“八宝被面”,就是在新娘陪嫁的被面上绣制女书文字,将女书中常用的吉祥文字“万”“寿”“王”“草”等混合在吉祥图案“麒麟送子”“丹凤朝阳”中,使被面的刺绣纹饰中既有喜庆欢乐的花鸟图案,又不乏清雅脱俗的女书文字,仿佛自然与人文的宝物齐聚,故而被称为“八宝”。
二、女书的图案造型与当代装饰艺术的共通之处
除了起源于女红又被承载于织物的特殊性之外,女书与荆楚、百越古文字相仿的构造,也使其具有了兼顾文字与图案造型的特点。女书虽然经历了千年的传承与变迁,但本质上没有脱离荆楚、百越文字菱形字体的整体风格,普遍的构造形式是从右向左、由高至低。字形笔划中弧形曲线占多数,结合圆点与少量的直线,间或穿插少量的“S”型纹。在完全不了解女书的人眼中,这些文字远远望去如小树、小鱼、水波纹,造型优美、古朴典雅,形似娟秀、柔弱的女子,与其说是文字,却更趋近于图案艺术。随着女书文字的发展,一些以文字为基底,在造型上更接近于装饰造型的女书图案开始出现,如最著名的女书图案“八角花”。“八角花”是指被八角的弧形图框围在中间的一系列图案的集合,包括花卉、鸟兽、虫鱼等,也基本上以民间常见的吉祥图案为素材。这些被围在八角框中的图形都是线条画,一般会在中间形成一个中心点,再由左下角起画,逐渐经左上、右上、右下的顺序形成一个类似于顺时针旋转的图案模式。这些白描图案没有人工刻意雕琢的痕迹,而是较随意且流畅,更具有普通市井生活的气息,因而图案造型更显亲切、随和,也比传统文人画更具生命力。除了“八角花”这种面积相对较大的图案之外,女书图案中还有大量便于织绣为条形的“二方联”图案。这种“二方联”是若干独立女书文字的组合,有两两对称、整体菱形的特征。同时,文字与花卉或鸟兽图案交织在一起,远看时较易将其误认为叶片或者流水等实物图形,但近观却能辨认出实际是倾斜甚至“躺倒”的女书文字。由于是被织绣在条形织物上,这些女书图案大多出现了变形,以适应并配合花鸟虫鱼的造型。因此,文字显得极具动感,恍若舞蹈中的人的四肢或躯体。无论是“八角花”还是“二方联”,这些最初源于女红的文字经由江永地区妇女的巧手再次回到女红图案中,让人仅能窥视到女性内心最隐秘的点滴情感,却在这些沿袭自战国时代的古文字符号面前不得其门。这些以曲线和折线为主、亦文亦图的女书图案中展现的是江永地区妇女既柔婉含蓄、又刚毅坚强的女性特质。她们在日常织绣的过程中,既将女书作为装饰图案普遍应用在传统服饰中,又借女书图案静静展示着女性内心细腻又丰富的情感世界。相比女书图案,现代造型艺术中虽然也不乏众多能够代表女性特质的装饰图案,却很难如女书图案般上升到一种自成体系、凝练为文字高度的境界。因此,女书图案不仅与现代装饰造型在深层次的艺术上共融共通,而且能够为现代图案艺术提供一种积淀着厚重历史文化印迹的先导与参考。从女书图案中不难发现,这些流传于未接受过正统教育的江永地区妇女之间的古文字图案,既蕴含着造型图案的优美,又具备了成熟文字系统的抽象;不仅可以单独具备某一特定含义,也能够以组合的形式在美妙的图案集成中传达出文字独有的深刻底蕴与丰富内涵。现代图案装饰中能够集图案与文字二者之精妙的造型于一身的艺术并不多见。因此,当代造型艺术应当深入挖掘女书图案的深刻文化元素,在这些宜动宜静、且活跃且肃穆的密码文字中寻找能够为现代装饰艺术所充分借鉴的“养分”,使数千年来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厚积而薄发,在当代装饰图案造型艺术领域焕发新的青春。
三、女书在当代装饰图案造型艺术中的传承
(一)将女书融入现代旅游纪念品装饰艺术中
作为一种起源于古代文明的历史遗留文字系统,女书由于其传播方式的独特与区域的狭小,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失传危机。传承女书的方法必须借助于其本质上具有的图案艺术的性质,将其融入当代装饰图案造型艺术的创新与开发中。如充分利用时下较为流行的生态旅游模式,将女书图案艺术应用于织绣类的旅游纪念品中;或者采取扎染、手工印制等方法,将其作为旅游商品的包装图案等。在单纯以文字学习式的传承之路难以施行的情况下,将女书的传承侧重于图案装饰造型,利用现代造型艺术求新求变,能够使其以更加实物化的形式达到传承与延续的目的。使用女书图案装饰的旅游纪念品应注意遵循形式时尚、造型传统的原则,如织绣类旅游纪念品在外形上应符合现代人的流行审美趋势。如近几年都市女性中比较流行的四方型大披肩,尤其是羊毛类与针织类的披肩上可以充分利用女书亦图亦字的装饰特色,在为女性披肩增添更多荆楚古文化元素的基础上,突出女书的神秘感。而将女书应用在皮革类女包外装饰图案上,则能够突破相同颜色、相近款式的女包造型欠缺个性的局限,如同为红色长方型女包,若能够以黑色粗体印制上迥异的女书文字,则犹如给每个女包打上了独特的“身份证号码”,不仅个性立显,而且黑字在红包上形成的厚重历史感,也为普通的女包增添了庄重、典雅的色彩。
(二)重新定位女书,将其归入传统书法艺术
女书之所以濒临失传,原因之一在于流传区域过于狭窄、使用人数过少。传统的女书基本上局限于织绣类日用生活品上,没有完全定位于文字的层面,一旦某位女书的传承者离世,其生前的织绣品还会随主人一起被销毁,这必然导致女书传承之路越走越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位女书,将其归入文字行列,尤其应归入传统书法艺术行列。正如甲骨文、金文、小篆等早已不通行的古文字还能得以系统和规范的保存,正是由于它们属于文字变迁的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特定时代华夏文明的内涵而被重视,国内不少书法家或爱好者会不断地书写这些字体,使其得以保护和传承。女书作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女性专用文字,本身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历史与文献价值,重新定位女书在于为这种集中了古代荆楚之地女性先民智慧的结晶“正名”,使其隐藏在图案造型艺术表相之后的文字本质得以重新体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流传于某个地区、某个时间段的文字类型,如契丹文字,这种依照汉字独创出的少数民族文字在近年来的考古中屡有发现,可惜同样由于流传范围狭小、使用人数过少而失传。但女书从战国时代延续至现代,且至今仍有女性使用、传承,这本身已经是其具有传承意义的体现,如果当代人不能正视其作为文字的重要价值而任由其逐渐滑向灭绝的边缘,则绝不仅是江永地区历史文化的损失,更是中华文明的重大缺失。不仅如此,女书这种图案文字艺术现今尚存使用者,如果能够及时通过这些使用人系统地整理出女书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对应之处,则无论是古汉语界还是考古界,又多了一项了解荆楚文化的重要资料,可谓一举数得。
结语
女书作为仅仅流传于湖南江永地区妇女群体中的远古文字图案,在当代人眼中具有神秘而朴拙的气质。这种完全依赖女性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源起于女红,又在女性的织绣艺术品中展示与传承。作为既有图案造型功能又有文字表意作用的女书,与现代装饰造型艺术在本质上有着极强的共通性。因此,女书的保护与传承可以充分利用当下流行的旅游经济,在旅游纪念品的制作或包装图案设计上寻找女书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贺夏蓉.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女书及女书文化保护模式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70-74.
[2]贺夏蓉.女书及女书文化传承的演变及特征分析[J].文化遗产,2010(3):85-90.
[3]贺夏蓉.观展/表演范式下女书及女书文化传承场域变迁与文化变异[J].山东社会科学,2010(11):34-38.
[4]王凤华.女书文化资源开发的女性主义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23-128.
作者: 蒋莉 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