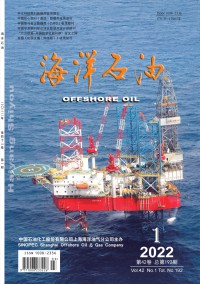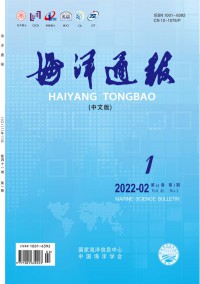海洋中的AOM及其效应

本文作者:孙治雷1,2何拥军1,2李军1,2黄威1,2李清1,2李季伟3王丰1,2作者单位:1国土资源部海洋油气资源和环境地质重点实验室2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3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AOM反应机理
1AOM产生机理及相关微生物
对于AOM的研究兴趣发端于甲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分布、温室效应与涉及其中的谜一样的生理学和地球化学过程。海洋环境中,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微生物介导的AOM作用假说[14~16],但此后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才证实该反应的可行性与现实存在。沉积物剖面上,AOM作用带通常是位于氧化带之下的甲烷(与更深的部位相比)与硫酸盐(与海水相比)均出现亏损的部位即所谓的硫酸盐—甲烷过渡带,同时在此作用带内,硫酸盐还原速率达到其顶峰[17,18]。因此,人们一般认为硫酸盐是甲烷在此作用带消失过程中的电子受体,通常的反应式如公式(1):CH4+SO2-4→HS-+H2O(1)不同海洋沉积环境中,SMTZ埋藏深度并不一致,从近海的数十厘米可以到深海的100多米,取决于活性有机质的埋藏速率、甲烷产出带的深度以及甲烷与硫酸盐输送速率与消耗速率[13]。在SMTZ中,甲烷从其下向上输送,而硫酸盐从其上往下扩散。甲烷在SMTZ带中被完全消耗,而间隙水中硫酸盐被消耗的比例则有所不同,如SannichInlet沉积物AOM过程消耗23%~40%的间隙水硫酸盐[19],而在纳米比亚上升流海区沉积物的研究结果显示几乎100%间隙水硫酸盐被AOM作用消耗[20]。在以扩散运动为主要传输方式的沉积物中,AOM作用的重要特征能通过反应物甲烷和硫酸盐以及产物硫化物和碳酸盐浓度曲线的典型形状而得以判断,其中甲烷和硫酸盐浓度的上凹曲线的交叉分布是指示AOM作用存在的典型特征[13],同时还伴随着甲烷氧化以及硫酸盐速率的明显增强,其甲烷和溶解碳的13C也出现互为镜像的较大偏移(图1)。通过向样品中注入经14C标记的甲烷来生成14CO2,人们加深了对SMTZ内这一作用的认识[18,21]。此外,在具有丰富的生物成因的13C亏损的甲烷环境中,因AOM作用而沉淀的碳酸盐中碳原子也相应出现13C亏损特征[21,22],这些事实均为AOM的机理阐释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通过原位检测,研究者发现了AOM作用带中普遍存在类异戊二烯结构的脂类物质,具强烈13C亏损,16SrRNA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它与甲烷八叠球菌目关系密切[23~25],这为研究者探究与AOM有关的微生物信息提供了重要线索。Boetius等[26]借助以16SrRNA为靶序列的荧光探针技术,首先观察到了这些微生物的形貌,发现它们由古菌中的甲烷八叠球菌属和属于δ-proteobacteria的脱硫叠球菌属—脱硫球菌属组成了一种共生结构。这种共生体的数量非常丰富,大约超过微生物总量的90%[26,27]。该发现证明,在执行活化甲烷功能的古菌ANME和提供电子的硫酸盐还原细菌相互协作的模型中,甲烷作为反应底物。此后,利用富含ANME的自然沉积物开展的室内实验成功表明AOM与硫酸盐还原作用偶联[28]。当前,通过离子探针质谱,已获得直接的证据来确认厌氧甲烷营养型微生物的微生物集合体具有极端的13C亏损特征,该结果与生标提取实验中获得的结论一致[29]。今天,所有已知的ANME均与产甲烷的广域古菌界微生物有联系[30],然而,迄今这些类群中的任何一种都未在实验室内得到分离培养。ANME代表着一个新的广古菌类群,目前至少包含3个簇,即ANME-1,ANME-2和ANME-3(图2)。ANME-1(分为a和b两个亚簇)与甲烷微菌目和甲烷八叠球菌目系统进化关系较近,但形成单独的分支。ANME-2(分为a,b,c和d四个亚簇)形成甲烷八叠球菌目中的一个较大分支。ANME-3是最近才鉴定出来的新类群,它与甲烷八叠球菌目的甲烷类球菌属的基因序列相似性较高[30,32]。ANEME-1与ANME-2古菌通常与SRB相联系[26,27,29,30,34]。ANEME-1通常以单个细胞出现,但也发现它可以与SRB组成菌席型互养体出现(图3a)[27,30,35]。球菌状的ANME-2最常见的生长形式是与SRB组成互养共生体,其内部核心由ANME-2充当,而其外部被SRB构成的壳层部分或全部包围(图3b)[30],形成一种壳体型互养体,而ANME-2通过数量和尺寸的增加而生长。除了与SRB耦合形成共生体,有研究也发现仅仅由ANME-2细胞形成的单一类型微生物的共生体(图3c)[29,35]。ANME-3古菌可能与属于脱硫球菌属的SRB有密切关系,但在较浅的含有天然气水合物的沉积物内也发现它与ANME-2a/Desulfosarcina(DSS)共生(图3d)[13]。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ANME紧密相关的细菌可能并非仅仅限于SRB,而具有较高的多样性。有研究者利用整个细胞的magneto-FISH方法对ANME-2c共生体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可与ANME-2成为互养共生体的细菌伙伴远远超出了δ-proteobacteria的范畴[36]。
2能量学及动力学特征
从生物能量学方面来看,有机质向甲烷和二氧化碳分解的过程是AOM活动赖以发生的基础[37]。由于AOM过程中,产甲烷有机物分解反应伴随的能量产出非常有限,这导致产甲烷微生物和各种不同的初级或次级(产醋酸盐的)发酵细菌类群必须结成一种互养共生模式来进行彼此的代谢过程[38,39]。例如,初级发酵作用产生的氢气分子在接下来产甲烷菌对二氧化碳的还原作用中能被用作电子源。尽管上述前一个反应是吸能的,但产甲烷菌对系统中所产生的氢气分子有效的消耗作用能保证接下来的反应趋向氧化方向进行,这是使合作双方的生长都获益的一种有效模式。最近,Alperin等[40]通过球形扩散—反应模型计算了AOM过程中的吉布斯自由能,结果显示,尽管互养共生体在AOM反应中的能量产出有限,但在理论上却能满足互养双方的最低需要。这与此前关于该反应在能量学上是不可发生的结论相反[41]。但这个反应的前提是互养共生体之间存在着中间电子传输介质(氢气、甲酸盐或乙酸盐),同时实验者还发现,共生体之间紧密相连的形式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量传输优势,与之相反,聚集体的直径越大,共生体之间能量的产出反倒会随着削减。这表明从能量学角度上来看,共生体的生长模式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还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Nauhaus等[42],Dale等[43],Orcutt等[44]讨论了AOM的动力学限制因素。标准条件下,AOM的自由能变化为:ΔG°''''=-16.67kJ/mol。据估算,在不同的原位条件下,AOM的自由能变化的范围为-10~-40kJ/mol[11,26~28,45~47],并根据底物、产物的浓度以及所处地层深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高富甲烷的通量能大大促进自由能的产出。Nauhaus等[28]发现,当将甲烷分压从0.1提高到1.1MPa时,SR的速率能提高4~5倍,表明AOM反应中甲烷的半饱和常数约为10mmol/L。硫酸盐反应的动力学参数迄今未知,但首次针对此问题的实验表明,当硫酸盐含量降至0.5mmol/L之下时,AOM就会发生明显的减弱。而Knab等[48]的研究则认为AOM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受能量学因素控制,而是首先受控于动力学因素。在甲烷和硫酸盐供应相对稳定的SMTZ带,AOM反应产生的能量变化低于理论下限(约-20kJ/mol)的情况很少,甲烷厌氧性古菌的在AOM反应过程中的理论能量范围仅仅为提供了一个限制反应方向的门槛值。
3反应底物
通过地球化学模拟、放射性同位素示踪以及富集培养实验,发现甲烷的消耗以及同时发生的硫酸盐形成硫化物的反应是大约以1∶1的摩尔比例进行的,这个比例也与AOM方程的化学计量特征一致。在不加入甲烷的控制实验中,就会缺乏硫化物的产生,这种结果似乎表明,除了甲烷,并不存在作为该反应电子供体其他类型的底物。但是在甲烷含量相对很高的SMTZ环境中,却发现硫酸盐还原的速率仍经常超过甲烷氧化的速率,这种情形在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的沉积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49,50]。因此,ANME或者SRB类群在它们所进行的部分代谢过程中,有可能利用了其他供体来源的电子。甲烷中C-H键的离解能量为+423kJ/mol,稳定程度仅仅低于苯中存在的C-H(+473kJ/mol)。包括乙烷、丙烷或者丁烷在内的长链烷烃与甲烷具有类似的离解能量(乙烷:+423kJ/mol;丙烷:+423kJ/mol;丁烷:+425kJ/mol)。连同甲烷在内的这些物质在能支持AOM作用发生的碳氢化合物储层内具有相对较高的含量,并且能作为ANME或SRB利用的电子供体[49,50]。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及接种培养实验表明,在缺少甲烷厌氧氧化作用的沉积物中,脂肪酸和包括长链烷烃在内的碳氢化合物能潜在地支持SRB的生长[49,51]。这些实验表明,SRB的不同亚种可能利用长链烷烃(比如,乙烷、丙烷和丁烷)作为电子供体来支持沉积物中AOM作用的发生,这些发现进一步扩大了AOM的研究范围和意义。
4中间产物和电子受体
人们研究了可能在甲烷氧化和硫酸盐还原过程中充当酶促作用的各种不同中间产物。然而,迄今未发现H2、甲酸盐、甲醇或者乙酸盐能作为其中间产物的证据[28,52],这表明,ANME和SRB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电子流。曾有研究认为特殊环境中,甲硫醇(CH3SH)可以作为中间产物出现在AOM共生体内[52],但这种观点可能并不符合实际,因为MeSH作为ANME类群的代谢产物,迄今在实验室与自然环境中的提取实验中仍未检测到。同时,在以MeSH化合物为底物富集SRB的实验中,研究者并未观察到与ANME类群互养的δ-proteobacteria的生长迹象。对甲烷标记后进行的脂类分析结果表明,硫酸盐还原细菌并未利用来源于甲烷的某种化合物,但却从CO2中获得了细胞生长所需要的碳[53],这个实验表明,此过程中仅仅转移了甲烷来源的还原物质而不是碳的化合物。一些硫酸盐还原细菌,包括与ANME细胞组成共生体的可培养的硫酸盐还原细菌,确实能通过自养方式生存[54]。理论上,AOM反应中,可能的电子受体将包括单质硫(S0)、砷酸盐(AsO3-4)以及Fe(III)或Mn(IV)。同时富集培养实验结果也表明AOM能与产生更高能量的其他电子受体偶联,包括硝酸盐(NO-3)和亚硝酸盐(NO-2)[47,55]。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未在海洋环境中发现ANME能利用硫酸盐以外的电子受体来进行AOM,直到最近在加利福尼亚EelRiver盆地甲烷渗漏区的研究结果颠覆了这一观点[56]。通过在该区沉积物分别加入甲烷、以13C标记的甲烷、CO2以及无硫酸盐的人工海水,实验者发现沉积物中的微生物在缺乏硫酸盐的条件下,能利用锰(水钠锰矿)和铁(水铁矿)来氧化甲烷,其具体反应机理如公式(2)、(3)所示。这表明海洋环境中的AOM的发生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和一系列氧化剂相偶联发生反应。同时,研究者还发现。在加入锰的平行实验中,细菌群落的锰还原菌发生的明显增加,表明在依赖锰的AOM作用中,细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并非单纯依赖古菌。既然河流每年为海洋输送巨量的锰铁,则该研究表明基于锰、铁而发生的AOM作用具有重要的全球性的意义。CH4→4MnO2+7H+→HCO-3+4Mn2++5H2O(2)CH4+8Fe(OH)3+15H+→HCO-3+8Fe2++21H2O(3)
海洋环境中的AOM反应模式
早期关于AOM的研究均聚焦于贫氧、甲烷以分子扩散为主的静态沉积物中[57,58]。而目前有关AOM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具有甲烷泄漏现象的沉积物,其中富甲烷的流体在水平方向快速的支持了繁盛的微生物群落。这两种环境中甲烷的含量和通量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图4)。在以分子扩散运动占主导(例如在阿拉斯加SkanBay[57])的沉积物中,AOM通常出现于表层分米到米级的层位之下,并位于硫酸盐带之下。在此环境中,甲烷具较低含量(~1mmol/L),硫酸盐含量与海水相比明显减小,同时大多数活性有机质已经发生分解(图5a)。与之相比,在天然气水合物赋存的甲烷渗漏区(例如水合物海岭[26]),甲烷氧化过程在接近表层的位置非常活跃,此处富含甲烷(~80mmol/L)、硫酸盐,同时化能自养群落生物菌席也为此过程提供了大量新鲜有机质(图5b)。这两种环境中物质传输的速率以及相应的能量流的通量具有强烈的不同。在水合物海岭的甲烷渗漏区,溶解甲烷向上扩散的通量是SkanBay地区的相应通量的100倍以上[40]。大量向上散逸的甲烷首先到达沉积物与海水的界面[59],之后被喜氧细菌所消耗并产生30倍于AOM的能量。总体上,高甲烷通量导致水合物海岭区产生的能量通量是SkanBay环境中产生的能量通量的3000倍以上。最近在墨西哥湾通过深潜器的原位观测显示,深海沉积物通过气泡羽流排放到大气中的甲烷通量远远高于早先的预测值,该区表层海水中甲烷的浓度值高出正常海水的1000倍[60],这显示渗漏区AOM在截流甲烷通量方面是相当有限的。计算模拟以及培养实验显示,微生物在静态海洋沉积物中与甲烷渗漏区对甲烷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机制。在图5a中,甲烷氧化在硫酸盐还原带(黄色区域)和甲烷产区(绿色区域)的界面上最为活跃。此处,甲烷的氧化机制最可能的解释是一种包括产甲烷古菌(红色)和SRB(绿色)的共同作用,其中产甲烷古菌将甲烷氧化为CO2和H2,而SRB则消耗产生的H2。同时,在此环境中,AOM与SR紧密偶联[61,62]。与之相反,在甲烷渗漏区(图5b),甲烷反应在近沉积物表面的位置最为活跃,其中涉及到的某些微生物集合体由似产甲烷古菌(红色)和SRB(绿色)组成。在此环境中,由于计算获得反应速率比任何利用可能化学物质的种间电子传输方式都大几个数量级,则人们推测古菌可能参与了与SR相耦联的AOM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某种可能的传导性丝缕结构(纳米导线)来进行种间电子传输而实现的。但是迄今为止,研究者并未证实这一推测的合理性。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一些ANME的细胞与其协作的SRB细胞并未紧密相连[29,30]。另外一种可能是,人们原先认为的氧化甲烷的古菌实际上是甲烷的生产者,它们利用高通量的H2以及该系统有机质的分解反应所产生的发酵产物[40]。通过这种机制产生的甲烷产物在其它高通量环境中已有较多的报道,比如在鱼类遗骸丰富的沉积物中。同时,AOM与SR并未显示出较好的偶联关系[49,50],这表明该环境中除了甲烷之外,石油或其他碳氢化物也可能成为硫酸盐还原的反应底物。
海洋环境中AOM的环境—气候效应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发现作为一个关键的地球化学过程[15,16],在厌氧、富甲烷以及硫酸盐的沉积物中存在的AOM能起到比甲烷需氧氧化更重要的作用[4],由于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环境效。应和气候变化甚至地外生命探索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科学意义,现代海洋环境中的AOM作用已经成为当前微生物生态学、环境科学以及地质学交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3]。首先,AOM在全球CH4的收支平衡中极为重要,并成为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的一环。据估算,AOM作用消耗了从海洋环境释放的大部分甲烷,相当于今天全球进入大气系统甲烷通量的5%~20%[31]。以全球最大的滞留水体黑海为例,由于存在有效的甲烷溶解和氧化机制,从其水体以及表层沉积物逃逸至大气的甲烷占其生产通量的比例不到2%[63,64],而由于水体中产生的甲烷不到全部的1%[64],绝大多数的甲烷是通过AOM而消耗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63~65],这表明AOM对于全球大气甲烷累积作用的调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对于海洋环境中甲烷释放(最重要的来源是天然气水合物)影响气候的具体机制仍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甲烷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能力是二氧化碳的23倍之多,当前人们已经将地质历史时期几次全球性的灾难性事件与甲烷(主要为天然气水合物来源)的释放联系起来[66,67],足以说明甲烷向大气的快速释放对于气候的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由此看来,海洋环境中的AOM虽然不能完全避免灾难性的气候或地质灾难的发生,但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对甲烷向大气中的释放起到了过滤截流的负向调节作用,有效地抑制了温室效应的作用,降低了发生重大地质灾难的几率。但迄今,对于海底不同地质单元、不同深度和有机质含量区域的AOM截流效率现在尚未有针对性的评估,AOM对大气系统最终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次,海洋环境中的AOM作用支持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并作为桥梁将碳循环和硫循环联系起来。同海底存在的热液系统类似,甲烷渗漏系统也支持了独特的海底生态绿洲的存在。通过与硫酸盐还原作用相偶联,AOM作用为包括细菌、古菌在内的微生物以及蛤类、管状蠕虫等在内的宏生物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来源,成为海洋环境中又一个基因宝库。不但如此,受AOM支持的该种生态系统在古代海洋环境中早有存在[68,69],当前人们从超过300Ma的石灰岩中已提取到证明AOM作用存在的生物标志物[70]。同时,由于太阳系中,甲烷是包括行星、卫星在内的许多天体大气圈甚至表层重要的物质组成,比如火星表面[71,72],以甲烷为物质与能量基础的AOM作用是否成为这些星体上生命存在的关键,成为天文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可以这样说,对于现代与古代AOM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地质历史时期古海洋演化以及包括其他星球在内的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等重要科学问题。
展望及启示
地球上甲烷年产量的85%以及消耗量的60%都是基于微生物作用发生的,而迄今,人们对于此过程中隐含的生物的作用以及它们关键的催化机制仍知之甚少,尤其是海洋环境中。在迫切需要解决的与AOM有关的问题当中,Knittel等[13]指出了当前AOM的未来研究焦点,与海洋环境有关的包括:海底环境中甲烷渗漏的区域范围及微生物对甲烷的过滤效率问题;微生物系统对甲烷消耗程度的有效性导致的未来全球气候的变化问题;ANME分布的限制因素与生长情况问题;AOM过程中与ANME相偶联的细菌的生长情况问题;AOM和甲烷驱动的SR中的关键酶问题等。这些都是当前亟需海洋科学及微生物研究者解决的问题。就本文的涉及到的内容而言,至少可以提供如下几点启示:
(1)在地球变为氧化性占主导的环境之前,甲烷营养型生物的生长受限于它们找到电子受体的能力。根据Mn,Fe的柱状综合光氧化速率(分别为5mg/(cm2•a)和200mg/(cm2•a)[73]),早期地球上依赖Mn和Fe发生的AOM氧化的甲烷可以达到的数量级为10000Tg/a。这意味着,原生代期间进入大气的甲烷通量的数量级可能在1000~10000Tg/a之间[74],很显然,依赖Mn和Fe的AOM作用有足够的氧化能力消耗地球早期的甲烷通量。因此,依赖Mn和Fe的AOM作用对地球早期生物圈而言,应该是的甲烷最重要的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能量来源。
(2)对于两种甲烷活动方式截然不同的海洋沉积物环境中,今后在开展微生物生态学与地球化学方面的综合研究时,首先要探究的是一个能量学上问题,即利用最低能量效应的反应(AOM)是如何执行对海洋沉积环境中的甲烷的有效过滤的作用的[12]。未来的研究最首要的任务是努力建立出一个通用的AOM反应机制,同时探索涉及其中的微生物的确切信息。如果在今后的研究中确实能证明另一类种间电子传输的方式(如纳米导线)是存在的,则此发现将成为人们深刻理解海洋环境中甲烷过程,揭开海底甲烷氧化之谜的关键。
(3)天然气水合物渗漏系统的AOM的运行机制及其对历史时期气候系统及环境的影响作用。如前所述,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的沉积物常常具有较高的甲烷泄漏通量,而除了在因水合物快速分解导致局部烃类压力过大,以气泡形式剧烈排放外,厌氧微生物在水合物—沉积物界面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环境[75],并能改变矿体与沉积物接触的边缘形态与甲烷运移方式,通过AOM对于大多数水合物赋存区的甲烷排放都可以有效过滤[49,50],并能影响较长周期的气候变化[76]。已有的研究发现,与上覆沉积物相比,水合物内部的AOM与SR依然具有较好的可比性[49],这表明微生物活动对于水合物矿藏的影响也将是非常重要的。这类研究对于精确评估全球水合物矿体的形成分解(尤其是微生物介导下的分量)对于地球及气候环境的影响效应至关重要,同时对于同样覆盖有水合物的其他星球的生命的探索也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但对于水合物矿体边缘甚至内部的AOM的研究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