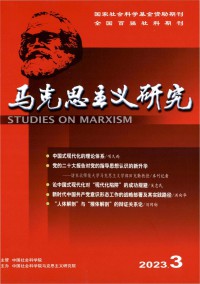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社会批判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社会批判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通过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结合,黑格尔把问题的解决诉诸理性神学的国家。通过指证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二律背反以及对其结合方式的神秘同一性的批判,马克思指明了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所存在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两个维度,即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分离以及世俗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通过对这两个维度的批判,马克思重构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指明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同时把所有分离和矛盾的根源导回到市民社会自身,转化为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实现了从政治批判向社会批判的转向。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二律背反;黑格尔法哲学;政治批判;社会批判
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地指出了他所得到的结论:“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既然批判的结果已经明确的呈现了出来,那么对批判的过程的分析似乎就不重要或不需要了,况且法和国家作为马克思已经扬弃了的东西,似乎就更没有研究的必要性了。然而,现实却是19世纪40年代的诸多思潮,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等,正以改装了的或变形了的形式活跃在我们当下的时代,而且,它们中间没有一方可以给予他方以致命一击从而占据领袖地位。旧的时代落下了帷幕,新的方向却晦暗不明。这不得不令我们要重新回到马克思对法、国家和政治的批判,重新回到19世纪,回到这些思潮的源头,去探讨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社会批判的过程和原因,以便能够真正地扬弃政治批判,进而进入社会批判。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或者说对国家哲学进行一次系统而专门地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给出了明确地说明,即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编辑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通过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一系列时评和政论文章,可以看出这些物质利益问题主要涉及到等级会议、行政权与官僚机构、立法权、各等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各等级与普鲁士国家之间的关系等诸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评述,马克思虽然借用了卢梭、孟德斯鸠、康德、费希特等人的思想,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彻底地和总地解决,马克思却是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而进行的,因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①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法和国家的问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它最终表述了这些问题。黑格尔的法哲学既超越了德国旧的国家制度,表述了莱茵河彼岸的英法现代国家制度,同时又通过对卢梭、康德、历史法学派等以往的和当时的法和国家学说的批判,系统地最终地表述了国家哲学。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既能处理教皇极权主义的普鲁士国家,又能面对现代自由主义的理性国家以及民主主义的理性国家。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内容而言,马克思援引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国家”章中的若干节并逐一加以评注。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章明确表述了关于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的内部国家制度本身,从而可以解答上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困惑,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问题在“国家”环节,尤其是内部国家环节中,上升为最为尖锐的问题。这是政治的根本问题,即普遍的社会存在于什么样的地方。在近代,它起始于政教分离以后,原本由神学所提供的整全性的保证转而全然依据人来思考和谈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对宗教的批判驳倒了神圣的彼岸世界,“哲学家又把我送回到了人类本身的面前,唯有人类才能做出决定来,因为全体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他们所具有的唯一热情。”②通过人自身如何回答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协调个体和共同体,如何构建普遍的人类社会,如何保证全体最大的幸福,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家通过对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利的分析与解释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近代政治思想传统一直致力于通过约定的平等或法律的平等来代替人与人之间自然上的不平等,以保证全体人类最大的幸福、平等和正义,“国家真正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用人与人之间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平等,来取代那无法消除的物质的不平等。”③然而,马克思却通过对国家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指明了单纯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以及“政治人”的抽象性和非人性,从而否定了单纯以政治解放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这使我们不得不深入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去研究其社会批判路径转变的原因。
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律背反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起始处引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国家章中的第261节:“对私法和私人福利,即对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来说,一方面,国家是外在必然性和它们的最高权力,它们的法规和利益都从属于这种权力的本性,并依存于这种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④这处引用明确地指出了贯穿黑格尔国家哲学的主要问题,亦即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这便是马克思在随后的评注中所指出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体系和(国家的)普遍利益体系的同一性”问题。⑤对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探讨便是同一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的逐步展开和详细规定。然而,马克思却依据这处引用指出黑格尔在这种同一性中呈现出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市民社会依存于和从属于国家,国家是外在的和强制的,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依照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由地使自身成为国家,市民社会成员组成为国家是内在自为的和自愿的。这便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二律背反。内在目的性是启蒙运动以来建立国家的主要原则,这种原则认为国家并非神授或启示的结果,而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个人转让自己的意志而约定为国家。个人在国家的联合中所服从的只是他自己,个人并不是由于强力而屈从于国家,而是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是自由地服从自己的意志。这种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形式“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①这种公约论的国家学说摧毁了教皇极权主义的国家,把国家从宗教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打破了中世纪的神圣国家,构建了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理性的现代国家。然而,黑格尔却指出了这种以内在目的为主旨的国家学说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在黑格尔看来,公约式国家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因为国家只是作为个体的“我”的共同支持的结果,我作为主人和主宰者,既可使它出现也可使它消灭。可以在瞬间推翻旧的制度,却无法确立新的制度,因为一部分人可以随便根据什么建立一个政权,而另一部分人也可以随便根据什么推翻这个政权。关于这一点,确证无疑的例子就是大革命时期的法国。
法国大革命沉浸于一种狭隘的自由概念,它摧毁了立于它面前的一切事物———教权、皇权、王权,它破坏了以往的伦理生活,却无法确立新的伦理生活,结果使法国沦为恐怖的狂乱和拿破仑一世的专制。正如洛维特所言,“虽然法国革命合理地摧毁了一个不再符合自由意识的国家,但却并没有给自由意识提供新的基础;它根据自己不完善的原则造成了一场巨大的变革,但却没有组织起新的共同体。”②以内在目的性为主旨的主观国家观的危险和恐怖在于,它易于使国家进而堕入混乱或暴政,无政府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深渊。黑格尔所要求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同一性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结合,正是基于对启蒙运动主观自由的反思,对于法国革命理性意欲自由的反思。尽管卢梭和康德都对启蒙运动的主观自由有所反思,卢梭否定了国家是单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主张有机联系的整体自由和全体最大的幸福,康德批判了追求自我利益的功利主义的自由观,主张要把自己和他人都看作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但是,黑格尔认为他们对整体和普遍的理解仍然是内在的,因而他们所追求的共同体或国家只能是一种内在国家,只能是通过对个体进行道德要求而达成,因而只能停留于理想或“应当”状态。现实的状况却是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对市民社会的表述:市民社会是需要的体系,个人主义是其原则,而他人只是实现自己需要的手段,人与人之间因经济利益而联系在一起。显然,市民社会的这种状况不能依靠道德途径来解决,因此黑格尔要求国家的外在必然性和客观真理性。正是“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③因而国家才不会沦为任意的、偶然的和主观的结果。而黑格尔所要求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外在必然性的同一表现为他所理解的伦理生活必须是绝对的伦理的总体,即理性与信仰,宗教和国家的统一与和解。黑格尔所要求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人与国家的同一也是卢梭和康德的要求,只是由于他们仅仅诉诸于个体意志的内在目的或先验的纯形式,因而普遍国家在他们那里只是作为主观的道德性而存在。黑格尔批判并否定了他们,主张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同一性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结合,把普遍国家落实为理性神学的绝对规定性,落实为绝对的客观性。然而,黑格尔扬弃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之二律背反的方式却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虽然黑格尔所主张的普遍本质与个体存在相统一的原则也是马克思的原则,但是马克思却反对黑格尔统一的神秘化方式,这种神秘化方式不仅没有扬弃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没有解决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反而是保留了这种分离和矛盾。
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现实分离
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理性神秘同一性在于“家庭和市民社会被看作国家的概念领域,即被看作国家的有限性的领域,看作国家的有限性。国家把自己分为这些领域,国家以它们为前提,国家这样做‘以便从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中形成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的精神’。”①从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过渡在于,市民社会把国家精神当作内在的本身东西,即公民的爱国心和民族精神的结合。市民社会被看作是国家的概念领域,市民社会结合为国家被看作是概念的生产过程。“它们是由现实的观念产生的。把它们结合成国家的不是它们自己的生产过程,而是观念的存在过程,是观念使它们从它自身中分离出来。它们的存在归功于另外的精神,而不归功于它们自己的精神。它们是由第三者设定的规定,不是自我规定。”②这样,市民社会自身的精神及其自身的自我规定消失在概念自我展开、自我运动的体系之中,市民社会不是自我规定的,而是由概念规定的,概念规定市民社会把国家精神当作内在的东西。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同一由概念展开自身为自在自为的体系来保证,从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是概念自我发展,自我圆满的结果,这便是黑格尔调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神秘方式。对于这种调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方式,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完全是把逻辑学的东西搬运到法哲学中来,法哲学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是根据在抽象的逻辑学中已经发展了的东西来发展自己的对象。从家庭和市民社会过渡到政治国家,这种“过渡不是从家庭等等的特殊本质以及从国家的特殊本质中引申出来的,而是从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关系中引申出来的。
这完全是在逻辑学中所实现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过渡”。③黑格尔完全是根据逻辑学中必然和自由的关系来处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过渡不过是逻辑学领域之间的过渡,黑格尔只是给他自己的逻辑学提供了政治形体。黑格尔以逻辑神秘主义的方式解决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二律背反的努力,不仅没有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同一,反而使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更为尖锐地呈现出来。在黑格尔之前,或者是君主专制或者是个体自由,然而,在黑格尔之后,我们在个体和共同体之间抉择,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挣扎。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我们作为人自身仍然是分裂的。对于黑格尔的神秘同一所导致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现实分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王权、行政权及立法权章节依次进行了批判,详细论证了在各个环节中所展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现实分离。就王权领域而言,黑格尔主张君主是国家主权的人格化,君主是国家理想和国家意志在一个单一经验的人身上的体现,而且君主作为绝对的国家意志的人格化,必须不能是推导出来的,而是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无条件的绝对,这正是体现了黑格尔对国家必然性和客观性的要求。对于黑格尔君主主权的批判,马克思又返回到卢梭,表现为一个卢梭的后继者,“如果国家的理想主义不代表公民的现实的自我意识,不代表国家的共同灵魂,而只是体现于一个人,体现于一个主体,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想主义呢?”④黑格尔要求绝对国家概念的经验化,以便化解绝对国家概念的抽象化,使其化身为人,但却不是化身为人民,而是化身为一个人。由之而来的是君主和人民的矛盾,君主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绝对,国家意志不是公意的结果,而是君主自我决断的结果。国家不是人民构成的国家,人民不是国家中的人民,黑格尔所要求的君主主权导致了抽象的国家和抽象的人民的分离。
行政权是对国王的决定、现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具体执行,“这种使特殊从属于普遍的事务由行政权来执行。”⑤行政机关与特殊事务打交道,主要是与本身不具有普遍性的产业等级所构成的同业公会(其成员主要是作为中产阶级的第三等级)打交道,使其服从于国家的最高利益。然而,马克思指出,官僚机构的存在本身就以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分离为前提,本身就表明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因为每个市民通过官僚机构而服从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因为,有了这些全权代表,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变成了法定的、固定的对立。国家被认为是与市民社会的本质相异的彼岸的东西,它通过自己的代表反对市民社会,从而确立自己的作用。”①国家是异于市民社会的彼岸,市民自身并不直接地在国家中,官僚机构的存在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对立的证据。而且,官僚政治在这种对立中,既不体现国家的目的,也不代表市民的目的,而是“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官僚政治是封闭的、神化权威的,是“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②这便是现代的官僚政治,而它正源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立法权本应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结合的最为紧密的领域,因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所划分的三个等级:地产等级、产业等级和行政等级均可通过参与立法活动而获得普遍意义。然而,马克思却指出正是在立法领域,普遍事务成了一种独占,个人与普遍事务是分离的,因为黑格尔主张的是立法权的等级制。黑格尔认为人民是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因而,他不赞成全体人员单个的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而主张国家通过等级制来保障公众的福利,人们通过等级来参与国事。黑格尔以等级为中介来沟通作为普遍领域的国家和政府以及作为特殊个人的人民,这是因为他认为由每个人亲自投一票是一种原子论的抽象观点,个人只有融入一定的等级,进入不同的行业部门,作为一个等级来投票才能扬弃原子式个人的对立。然而,一方是原子式个人,一方是抽象的普遍国家,黑格尔的中介思想恰好表明了双方的对立及其不可中介性。
三、政治国家根源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
通过政治改革,即通过市民社会成员全体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制改革似乎得到了解决。在民主制中,市民全体通过普选制同时作为国家公民而存在,市民社会本身作为政治存在获得了政治意义和政治效力,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似乎被消融了。然而,马克思却不是一个只停留在政治改革中的民主主义者。他对民主制的详细表述如下:“通过不受限制的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但是,在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市民社会把自己的政治存在实际设定为自己的真正存在,同时也就把不同于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市民存在设定为非本质的存在;而被分离者中有一方脱落了,它的另一方,即对方,也随之脱落。因此,选举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这个国家的解体,但同时也要求市民社会解体。”③可见,马克思所要求的民主制不仅要求等级制国家的解体,也要求市民社会的解体。普选制所带来的普遍政治参与,使得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二重生活在政治意义上得以和解,但是,马克思却指出这种和解也使得市民社会解体,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真正和解必须同时消灭二者。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个维度是对君主制、官僚政治以及等级会议的批判,这三者构成的政治制度所导致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表现为君主和人民,官僚和人民,等级和人民之间的分离和不平等。这种由特权所导致的政治的不平等是可以通过政治改革,通过由全体市民社会成员直接参与国家事务而加以消除的。
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另一个维度是通过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发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者本身的分离与不同,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从属于不同的领域:一方是世俗的存在,一方是抽象的存在;一方面是政治生活,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分离的实质是经验和概念、现象和本质的分离。黑格尔通过逻辑学概念演绎的方式构建了二者的神秘同一,即以理性神学为基础的国家。马克思借由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理性神学的批判解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神秘魔法,把政治国家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颠倒,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观念统一性的神秘性和虚幻性,指明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由于马克思已把黑格尔法哲学翻转过来,所以这个批判就成了他的发展中的一个绝对步骤:这个批判既使他对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有了与自由主义观点根本相反的新理解,同时也使他对历史有了新的看法。因此,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而主要是从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出发,摒弃了思辨哲学的。”①总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明了黑格尔法哲学中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矛盾与分离,这种分离表现为个体和共同体,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以及世俗社会和政治社会,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两个维度。
当然,这两个维度是结合并杂糅在一起的,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二律背反。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解决此二律背反的神秘化的同一方式的批判,重构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指明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同时把所有分离和矛盾的根源导回到市民社会自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金钱和私有财产的指责深化为《论犹太人问题》对私有财产的废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两个维度在《论犹太人问题》明晰化为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然而,社会解放并不是放弃了对第一个维度的问题的解决,即对个体和共同体,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关系问题的解决,而是转化为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社会批判来解决普遍的人类社会的可能性问题。
作者:姜海波 徐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