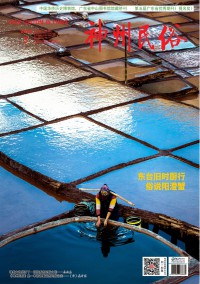民俗文化研究意义

民俗文化研究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美国 女性学 女性民俗学 女性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女性主义(feminism)和女性学(women's studies)研究的发展,女性民俗学(feminist folklore)研究在美国悄然兴起并不断完善。女性民俗学作为新兴的民俗学分支学科,不仅为女性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而且也推进了民俗学学科自身理论和研究的发展。在我国民俗学学界,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女性民俗”、“女性民俗文化”等提法,但有关女性民俗学研究的理论著述至今并不多见。了解美国女性民俗学发展历程及其理论方法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对当前我国民俗学,尤其是女性民俗学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一、美国早期妇女民俗的研究
美国民俗学研究发轫于19世纪中期。1857-1858年,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柴尔德(Francis J.Child)出版了八卷本《英格兰与苏格兰叙事民谣》,标志着美国早期民间文学收集的重要成就。此后,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纽厄尔(William W.Newell)在长期研究儿童游戏的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儿歌与游戏》,同时参照英国经验于1888年发起筹建了美国民俗学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并于同年创立了《美国民俗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美国民俗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日渐成为国际民俗学研究的重镇。
考察美国民俗学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民俗学研究者从未中断过对女性及其民俗的关注。1899年,《美国民俗学杂志》发表了张伯伦(Isabel C.Chamberlain)的题为《有关妇女民俗的书目》一文。文章整理了《美国民俗学杂志》创刊10年来有关女性民俗研究的相关成果81项,并对其进行了简要述评。该文是最早的有关美国女性民俗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这些研究,多以法文形式出版,多受此时期欧洲民俗学的影响,主要关注妇女口头传说故事,而其他的相关研究则比较少,且内容多局限于对不同文化中妇女个人魅力、妇女手工技艺及缝纫工艺、婚姻仪式等的探讨,没有涉及更多的妇女行为实践及其表述。其中,博厄斯(Franz Boas)、布里顿(D.G.Briton)、查尔斯(L.Charles)、波特尔(Rose Porter)等人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进入20世纪后,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及其弟子们相继担任美国民俗学学会主席,美国民俗学由此进入以人类学理论为主导的研究阶段,而博厄斯提倡的田野调查方法也为美国民俗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在20世纪前10年,妇女民俗研究基本承袭之前以口头传说和故事为主导的研究模式。西塞尔顿-戴尔(Thisehon-Dyer)的《女性民俗》一书是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20世纪有关妇女民俗研究的最早著作。本书分为37章,以“妇女的喜好”、“妇女的憎恶”、“年轻的少女”等为题分类,主要依靠谚语、歌谣等形式,描述、讨论与妇女有关的习俗,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怎样看待妇女的穿着、谈吐、婚姻,怎样评价坏女人、寡妇、新娘等。就研究而言,本书大量使用了文学材料,对妇女日常生活民俗的涉猎十分有限且描述较为简单。尽管存在诸多不足,本书仍被看作20世纪女性民俗研究的奠基性作品。至20年代,民俗学研究领域开始出现“The Folklore of”的命名方式(of后面经常以部落名、国家名等来填充),美国妇女民俗研究中由此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黑人和印第安部落妇女故事和巫术的研究。此外,20年代涉及妇女民俗研究的文章中开始使用田野调查中报道人的访谈材料。遗憾的是,大多数的研究均使用男性报道人所提供的田野材料。一般而言,女性报道人及其材料仅在男性报道人对某一话题显得无能为力并无法触及时才被使用。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研究中,相关研究成果经常以“妇女知识”(women's lore)或“妇女文化表述”(women's expressive culture)等为主题进行书写。在法尔(Claire R.Farrer)看来,此时期的妇女民俗研究,是一个“有距离的文化研究的时代”(an era of culture-at-distance studies)。在研究中,民俗学研究者关注的是整个文化,而女性民俗仅在一些和妇女密切相关的研究中(如儿童养育实践的研究)才被提及。就研究本身而言,他们强调的是文化,而不是某一文化内部的以妇女亚群(women subgroup)为特征的习俗和信仰。当然,此时期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男女两性文化表述行为方式的异同,但这类研究基本因袭米德(Margaret Mead)在南太平洋上的研究理路,即一个社会文化怎样型塑男女两性的性别与气质。20世纪50年代,研究妇女民俗的论文大量出现,其中在《美国民俗学杂志》上发表出来的相关论文的总数超过了30和40年代总和的两倍多。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极为重视田野调查的时期,很多有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在1960年之后陆续发表。至20世纪60年代,女性民俗研究一直着力谈论女性魅力、婚姻习俗、妇女生育实践等问题,尽管有些文章也开始关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女性角色,但此类文章屈指可数。此外,此时期大多数研究很少使用女性报道人的材料,即使被使用,也仅限于女性个人魅力、家庭健康、儿童游戏、信仰和巫术等方面。
综上所述,美国民俗学研究一开始就关注男女两性及社会性别,但是研究散见于婚姻、家庭、社会礼仪、信仰等的研究之中。这一时期的研究,女性被视为非主流文化群体,一直处于被观察的地位,女性及其女性民俗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女权运动及其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下,民俗学家逐步对以往的女性民俗研究展开反思,女性及女性民俗作为研究主体开始以全新的视角被纳入民俗学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开启了女性民俗研究的新时代。
二、美国女性民俗学的确立
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女性民俗学在美国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是女性学与民俗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产生,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及其思潮的深刻影响。它既是女性学为了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借用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女性学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女性主义影响下民俗学学科对自身学科理论及研究实践反思的产物。
20世纪60-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男女两性平等意识不断增强。“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波伏娃(Simon de Beauvior)和费尔斯通(Shulamite Firestone)等人的研究中不断被强调,从而导致了此时期诸多社会研究对几乎所有生活领域中女性权力的关注。这场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权益的运动引发了妇女研究的热潮,也刺激了民俗学对两性平等、两性差异及女性独特日常生活经验的研究。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女性主义(feminism)和女性学(women's studies)研究的发展,在民俗学学科内部也引发了有关女性民俗及妇女行为实践研究的激烈讨论。在诸多呼吁和讨论中,女性民俗学(feminism folklore)悄然兴起。许多研究者认为,没有人否认社会文化中性别要素的存在,女性文化和女性民俗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女性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存在,在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直处于被忽视、贬低的地位,女性民俗文化长期未被关注和提及,女性从而也被看作“没有声音的群体”,是“没有历史”和“没有文化”的,而“男性则被看作是传统、历史、真理以及事实的标准代言,由此男性的经历被看作是所有人的经历,甚至只要谈及‘人类’时,指的仅是‘男人’罢了”。但现实情况是,和男性群体一样,女性具有和他们一样同等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存智慧。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及其研究实践导致了对女性民俗文化研究的“漠视”或“忽视”,从而也导致了女性民俗文化的现实存在和学术研究领域之间的巨大鸿沟,由此女性民俗学研究者呼吁应当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及女性文化,建立一门新兴的女性民俗学学科。
除了受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之外,20世纪60-70年代民俗学研究者对民俗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的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民俗学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中后期,美国民俗学逐渐摆脱了欧洲民俗学研究的束缚,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发生了巨大转变。美国民俗学从对历史民俗的关注转向对当代民俗的关注,从对文本的研究转向对语境的研究,从对静态文本的强调转向对动态的表演和交流过程的强调,极力实现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总的来看,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一批美国学者所创立的新理论共同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些理论,包含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其影响已经波及世界范围的民俗学研究,有的甚至超越了民俗学的领域,广泛渗透到其他学科。在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过程中,研究者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田野调查,他们关注田野中的“个人”并将个人行动和表演的语境纳入研究和考察的视角。
在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大背景下,民俗学研究者也开始重视民俗学调查和研究中实际的“场景”和“布局”。他们认为,无论是主位(emic)描述还是客位(etic)描述,在实际的田野中,一个女性表演者(performer)置身其中的表演,就如同男性表演者表演时的场景和布局一样。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偏见:无论是鲍曼(Richard Bauman)描述的故事叙述场景,还是汉纳尔斯(Ulf Hannerz)所描述的“街角”(Street Corner),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过分关注男性群体的表演,似乎口头表述和文化表达只是男性单一性别的表演。在这样的研究状况下,有的研究者认为:“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应当同时搜集来自男性和女性的资料和数据,而不应在仅仅依靠建立在仅从一个性别得来的资料去研究和发展理论。因为尽管另一个性别,即女性的材料非常难以获得,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视它,我们没有理由这么做。”事实上,“显而易见的结构设置能表达男性对世界的看法,但是,在诸多更深层次上的模糊存在却表现了一个女性对世界的看法”。在学科研究实践的自我反思中,很多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民俗学研究者,首先开始关注田野中真实存在的女性群体及个人,女性民俗学研究者均认为“女性民俗的研究不应当只局限于对编织、缝纫工艺、家庭医药、饮食方式等的探讨,而应将其扩展到女性文化表达及其可能涉及的诸多有效类型和领域”,从而开始了对日常生活中妇女笑话、流言蜚语等的关注和研究,以前从不被关注的妇女们墙后的闲聊,关起门来的低声细语,家里的絮叨,朋友间的谈话,都被作为全新的“类型”(genre)被纳入研究视域。
1975年,法尔编辑出版《妇女和民俗》一书。该书是美国女性民俗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美国女性民俗学研究由此正式发端。克莱尔在本书前言《妇女和民俗:形象及类型》一文中指出,“女性形象及类型只有在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时才被关注……以往的研究从女性报道人那里获得的材料十分有限,而且还被局限在特定的领域。因此,至今为止的民俗学理论及其研究模式都是建立在单一性别,即男性的研究基础上的”。就民俗学研究而言,“以女性为主导的群体会有何作为?她们的行为和男女相性混合的群体或只有男性组成的群体有什么异同?在孩子学习和选择自我表述方式的过程中女性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文化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表述和实践方式?一个文化对女性的文化感知和角色期待在民俗中如何被表达?一个文化内部隐含的看待女性的观点怎样在大众媒体中被使用?在我们文化内部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形成的规则怎样影响了我们看待女性表述经历的观点?简单地说,女性民俗包含哪些内容,在其中女性形象和角色怎样被期待?显然,这些问题现在还难以回答”。作者认为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而“本书便是试着开始去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所收录文章均关注女性自己本身及其他者怎样看待她们的角色和形象。其中,斯图蒂(Beverly Stoeltje)关注边境妇女群体,认为其妇女角色和形象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边境环境、生活方式、生活经历及其先前的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边境妇女形象形成过程也涉及了边境男性形象及其角色的讨论,认为两性中的“自我”及“他者”都决定了彼此的形象。斯通(Kay Stone)则关注大众媒体女性形象的选择和使用,研究并讨论了《格林童话》故事集中美好的女性角色模型,接着又进一步讨论了“迪斯尼”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在比较了《格林童话》故事集及“迪斯尼”电影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后,斯通和有关妇女及孩子作了访谈,让其对电影及其他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及角色做评价。依内子·卡多佐-弗里曼(Inez Cardozo-Freeman)关注女孩对她们自身成人之后的女性形象及其角色的解释。1973年,她在墨西哥及墨西哥裔美国人中做调查,她的大多数调查材料来源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墨西哥女童的游戏。母亲和其他女性亲属所认同的内隐和外显的观点和想法在游戏中都得到运用和表达。她评价了游戏对于参加游戏的女童之当前及长远的影响。卡斯克(Susan J.Kalcik)的研究,十分重视田野材料的运用,但由于没有获得当事人的同意,她在田野中获取的很多材料未能出版。在她发表的有限的研究成果中,卡斯克描述和分析了女性的“合作性类型”(collaborative genre)。在咖啡馆、超市、公园或其他类似的地方,妇女们聚集起来照顾孩子并相互闲聊。此种类型的交流就是“合作性类型”的女性民俗形式。在这样的女性民俗形式和类型中,妇女角色的表演从一个群体穿梭到另一个群体。
美国女性民俗学自其发端,就批判民俗文化研究及其书写的男性本位倾向,着力研究民俗文化中的两性差异及其成因。针对以往以男性为主导的民俗文化书写及其研究范式,女性民俗学研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致力于探讨作为文化存在的妇女们的生存状态,力图通过对女性民俗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来探讨女性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女性民俗学重新把女性放在了“人”的视点上进行研究,是对以往民俗学研究忽视女性现象和用男权思想书写、解读女性民俗文化的一种反省和纠正。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民俗研究中,女性民俗形式的特征、女性对各种民俗形式的运用、女性形象的呈现和性别塑建等成为此时期研究的核心。但是,此时期研究还未更多涉及女性及其民俗文化研究中的“政治”、“权力”、“族群”、“认同”等问题,而这些关键词成为此后女性民俗学研究的重点。
三、美国女性民俗学研究取向及成果
1975年《女性与民俗》一书出版之后,美国女性民俗学研究中的“类型”(genre)一词成为学界讨论和研究的中心议题。在对女性日常口述、口头交流与表达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如妇女闲聊、流言蜚语等是存在于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全新的”、鲜活的女性民俗类型(women's genre)。他们认为,这一“叙述性类型”(narrative genre)发生和存在于女性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对这一类型的研究和探讨将有助于对妇女生活及其经历的理解。对这一类型的研究和深入有赖于田野调查的展开,由此,田野调查及其女性被调查者的主体地位等在诸多研究中不断被强调。此外,女性民俗学研究者还认为,这一“刚刚被发现”的“女性的声音”和类型扩展了民俗学研究原有的类型划分,它应当与神话、传说、节日等一样被视为民俗及民俗生活类别划分中的一项。当然,这里所强调的“叙述性类型”尽管以女性民俗学研究的角度被发现,但是研究者却不认为这一类型只存在于女性这一群体之中,它是一种可以存在于诸多群体内部的普遍类型。因此,70年代后,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出发,许多的女性民俗学研究着力寻求和探讨存在于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民俗类型”,并开始致力于对女性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1985年,由乔登(Rosan A.Jordan)和卡斯克(Susan J.Kalcik)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女性的民俗,女性的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论文集分为“私领域的妇女/妇女与妇女”(woman in private/women with women)、“公领域的妇女”(women in public)、“两个世界/一个世界”(two world/one world)三个部分,涉及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生活史(life history)、口头表述(narrative)、田野调查等诸多领域。约克(Margaret Yocom)在她《女性之于女性:田野和私人领域》一文中认为,“私领域并不是以往社会内部交往方式研究中所讨论的空间范围”,并试图通过自己的田野研究规制和定义所谓的“私领域”。本书诸项研究均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及报道人材料的使用,认为以往的民俗学田野调查大多使用男性的眼观来描述和看待妇女,这严重影响到民俗学材料的获取,应当重视田野中女性报道人材料的使用。在本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还提出,民俗学田野工作者的性别也会影响到他/她与报道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他/她在田野工作中看到(see)、听到(hear)和理解(understand)的东西。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有这样一种预设,即女性是没有权力的(powerless)。然而,在本书中女性的“权力”(power)被发现,女性不再被描述为男性权力之下的牺牲品。研究者们认为,尽管男性处于社会主导地位,但女性依然能够控制和主导她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凭借女性民俗文化,她们能获得一种真正的权力感,从而形成女性独有的口头表述及行为方式。例如,约翰逊(Geraldine Johnson)笔下的织毯女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和运用时间、空间,妇女们日常手工艺的抽象设计表达了一种潜在的个人行动力;约克则认为,女性故事讲述者运用她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实践来影响整个家庭成员及其之间的关系。在此,妇女具有一种控制和权力感,这种控制和权力通过日常规则、审美和文化表述得以实现。女性同样拥有她们自己的传统、生活故事和具有隐喻性的日常生活,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男性为主导的世界里妇女们怎么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另外,本书还从女性话语的功能出发,讨论了女性民俗与权力、女性故事讲述中的审美、男女两性世界观、社会性别及群体认同等问题。
除《女性的民俗,女性的文化》论文集外,1987年由以《民俗学与女性主义》(Folklore and Feminism)为题发表于《美国民俗学杂志》的特刊及1988年以《民俗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修正》(Feminist Revisions in Folklore Studies)为题发表于《民俗研究杂志》(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的特刊,也是此时期美国女性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
1987年出版的《民俗学与女性主义》专刊包含16篇论文,为1986年10月美国民俗学第98届年会“民俗学与女性主义”会议论文集。在此专刊中,研究者们分别讨论了女性民俗符号编码、仪式和社会角色,口头叙述表演及其功能等问题,其中很多论文也对女性民俗、女性主义、民俗主体等理论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多项研究被收入1993年由赫里斯(Susan Hollis)、珀欣(Linda Pershing)和杨(Jane Young)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女性主义理论与民俗学研究》(Feminist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Folklore)中。该论文集和由拉德纳(Jone Newlon Radner)主编的论文集《女性的信息:在妇女民间文化中编码》(Feminist Message:Coding in Women's Folk Culture),在女性民俗研究领域中至今享有很高的声誉。
1988年《民俗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修正》特刊,收录了三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涉及神话、史诗和节日等主题,关注具体文本、语境、事件中的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凯恩(Stephanie Kane)的研究,不仅对该神话进行了女性主义角度的阐释,而且还探讨了神话出版物系统性冗长赘述和情节遗漏现象的重要性,她认为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出版业造成了口头文学中“被抑制沉默的”女人的状态。在萨文(Patricia Sawin)的史诗研究中,展示了在民族史诗形成过程中社会历史及意识形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正如贝弗利·斯图蒂(Beverly J.Stoeltje)在该刊《导论:女性主义修正》中指出的,诸项研究分析表明,社会性别关系对民俗意义生成具有重要作用,而女性主义研究视角能够展示和分析这一过程。此外,民俗形式具有可塑性(plastic)和“可浸润性”(permeable),它能及时反映社会政治倾向,并在个人、群体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形成强有力的控制力。该刊文章均在关注民俗学家们熟悉的物质民俗类型,但研究也“让熟悉的东西不再熟悉”,以此来展示修正当前民俗学科传统研究范式“堡垒”的必要性。“这些学术实践可能具有开拓创新性,但也可能是倒退的,但都是尝试性别研究的有益实践”。“无论是‘文本’(text)还是‘事件’(event),其在建构或表演过程中,都存在认同的问题,这种认同包含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等。这些符号性的认同形式提供了一个问题的答案,即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我们怎样表达我们的认同并借此形成我们的权力、权威和性别关系”。这些研究旨在让大家意识到女性民俗和女性主义视角的重要性。女性民俗学应当在民俗学学科领域中占有合法性地位,并成为民俗学学科知识生产中一个具有生命力的领域。研究者们希望这些具有修正意味的女性民俗学研究成果能够对女性学研究作出应有贡献,在所有表象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女性研究的理论体系。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民俗学研究,更加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民俗“类型”(genre)和田野调查,并且开始批评和解构先前民俗学理论有关权威(authority)、主观能动性和权力分层等的研究,主张重新认识和理解“群体”(group)和“认同”(identity)的概念,力图对民俗学学科研究现状进行有效修正和补充。舒曼(Amy Shuman)在其论文《性别和类型》中重新对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提出的“民族类型群”(ethnic genres)进行探讨。她使用丹·本-阿莫斯的研究路径,再次探索了性别与权利的关系。她受鲍曼(Richard Bauman)表演理论和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著作《类型、文本间性和社会权力》(Genre,Intertextuality,and Social Power)的影响,主张将“类型”(genre)置入特定的语境中来考察“民族类型群”,并指出“可能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文本和中立的语境。到底是谁拥有定义‘类型’的权威,并又是谁规定的不同‘类型’之间的界限?这一过程又怎样影响了之后的研究?”,“女性主义对民俗‘类型’的研究(仅作为女性民俗学研究者诸多研究路径之一)关注社会分类系统对“性别”区分的不稳定性,正因如此,女性才得以实现协商博弈,并为实现她们的目的而形成恰当的传统和‘类型’”。此外,舒曼还提出,应当将“类型”也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性别区分的稳定概念。柯蒂斯(Deborah Kodish)在其《缺失的性别,沉默的遭遇》一文中则对以往的民族志书写传统进行了反思,认为民俗学研究者自身及其研究对象之间都存在着性别权力关系,民族志写作应当重视和阐释这些关系。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民俗学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和“近距离倾听”女性如何实现她们的文化表达及其表述的内容,而不局限在对女性民俗形式及其“类型”分类的研究和探讨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女性文化传统极少受到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重视,但是许多不同文化中的妇女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使用自己的手段对自身女性文化及其传统进行一定形式的编码,从而实现文化表达的目的。如同使用文字书写符号系统写作而成的文本一样,女性民俗文化也具有自己的文本,这个“文本”由女性个人或群体凭借其具有的特殊文化符号编码“书写”而成。而所谓的女性民俗(women's folklore),就是由女性口头表演、物质创造及其日常生活实践所共同形成的文化文本。这个“文本”蕴含着丰富的符码信息,通过这些文化符码,女性能够实现她们自身与不同“读者”和“观众”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对女性民俗文化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女性民俗文化的信息编码过程进行探索,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读者”和“观众”对不同女性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符码进行“阅读”和理解的过程。对女性民俗文化的研究和解读,不应当只局限于民俗学的研究,而应当形成跨学科的对话,在与各学科的对话中讨论解读妇女民俗文化编码的策略和方法。
20世纪80-90年代,女性民俗学研究成果卓著,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女性学者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此时期的研究,不仅重视民俗学传统的文本研究,同时更重视田野调查方法在女性民俗学研究过程中的使用。至20世纪90年代,女性民俗学研究渐渐出现新的转向,“权力”关系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性别”、“权威”、“权力”、“群体”、“民族”、“国家”等成为女性民俗学研究者的重要话题。这一时期的女性民俗学研究,不仅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上有了拓宽和发展,即从探寻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民俗“类型”到开始关注女性角色及其所连带的社会权力关系,从重视田野作业以获得女性报道人材料到关注研究者个人和文化主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及其角色关系,而且由于受到当时表演理论、人类学民族志、女性主义理论等的影响,在女性民俗学理论上也作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即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建立起适合女性民俗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使女性民俗学从经验研究逐步走向理论化。
四、美国女性民俗学的理论转向及特点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尤其是1993年《女性的信息:在妇女民间文化中编码》和《女性主义理论与民俗学研究》两本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女性民俗学开始走向理论化。如克萨里奥斯(Nicole Kousaleos)所言:“……1993年两本研究文集的出版,受到当时表演理论、话语民族志、非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叙事学理论和现象学理论研究路径的影响,试图呈现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适合女性民俗学研究自身的理论和方法。”此后,作为一个新兴的民俗学分支学科,美国女性民俗学在自身学术实践和理论方法研究上进行着积极探索,开始踏上了寻求自身发展的理论之路。
首先,就“女性民俗”和“女性民俗学”这两个重要学术概念而言,在美国女性民俗学研究进程中先后出现了以下几种代表性提法:“the folklore about women”,“women's lore”,“folklore of women”,“women's folklore”,“feminist folklore”。大多数学者认为,“the folklore about women”的相关记述很早就有,指“与妇女相关的民俗”,较早出现于一些小说、游记、故事文集、歌谣及民间谚语俗语之中。“women's lore”的提法在19世纪中期民俗学科建立之前被较多使用,指的是“妇女的学问/知识”,被提及时大多指妇女所掌握的家庭医药卫生等相关知识。“folklore of women”的提法首次出现于1906年,在西塞尔顿一戴尔《女性民俗》(folklore of women)一书中以书名的形式第一次被使用,但本书只局限于通过故事、谚语俗语等对女性进行简单记述。“women's folklore”作为一个概念和术语被使用,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民俗学学科建立以后,其在1985年出版的《女性的民俗,女性的文化》(Women's Folklore,Women's Culture,)论文集中被普遍使用并沿用至今。就“women's folklore”的含义而言,1993年出版的论文集《女性的信息:在妇女民间文化中编码》之导论对它做出过界定,即指“女性口头表演、物质创造及其日常生活实践所共同形成的文化文本”。这一界定将女性民俗看作是一个蕴含各种文化信息的文化系统,此种提法看起来并无偏颇之处,但仍然显得较为抽象。2009年最新出版的《女性民俗与民俗生活百科全书》就women's folklore(女性民俗)这一概念做出如下界定:“所谓女性民俗,既包含有关女性自身的民俗,也包含有关女性之外的其他人的民俗。在欧美,就如大家所知的那样,女性民俗经常与女性文化具有一致性。但是,女性民俗不仅仅指妇女家庭生活——母亲、孩子、食物等这些传统的女性领域。只有男性至上主义者会将男性文化看作是“人类的”,而将女性文化看作是特殊的,是单独属于妇女和女孩群体的。女性创造、表达和与他人博弈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涵盖了整个人类文化的范畴,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不同形式显示了女性控制她们自身生活和经历的不同方式和模式。女性民俗同样显示了女性的权力和反抗。事实上,在女性民俗中内隐或外显的对男性父权制的抵抗是女性民俗存在的最重要的特征。……女性民俗以意义的多样性为其特征,女性民俗中符号编码是外显的,其中蕴含的对男权社会的抵抗性则是内隐的。女性民俗具有明显的交流合作性、整合性和再生性等特点。”至于“feminist folklore”一词,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才出现的一个术语,它在两个不同层面被使用,既指一个独立的民俗学分支学科,又指一个以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的民俗学研究路径,在当前的女性民俗学研究中普遍使用。而当前对女性民俗学(feminism folklore)这一学科及其研究的理解,则认为女性民俗学研究不光是从女性视角对女性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是从女性的角度对人的重新解释。女性民俗学试图通过对女性文化的补写,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
其次,就女性民俗学学科特点及其学科定位而言,第一,女性民俗学以“人”作为思考和研究的中心。女性是一种现实存在状态,因此民俗学将作为“人的存在”的女性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关注女性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态,以此展示女性这一“人的存在”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存在”意义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出女性这一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以此论证女性存在的独特性和完整性。第二,女性民俗学始终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女性民俗学从“人的存在”的现实角度出发和描述女性,而“人的存在”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简单地化约为女性和男性的相互关系,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二者的相互关系基本上决定了人的存在的基本格局。此外,女性民俗学不仅为女性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推进并重建了传统民俗学领域中的女性问题的研究,而且也同时引发了民俗学对自身的反思,使人们以崭新的视角对许多“视之当然”的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女性民俗学研究者在考察知识生产,尤其是话语权威、命名、意义赋予等过程的基础上,对阶级、种族、族群和群体等的定义进行了质疑,并由此对身份认同、权力、日常经历和主观能动性等学术概念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解释,而这些具有反思性的女性民俗学理论研究也给现代女性主义及其理论带来了新的解释维度。例如,女性民俗学对流言蜚语、谈话等日常合作话语“类型”的分析,关注日常语言行为中语言与社会交往的关系,研究语言怎样反映了社会性别,研究女性意识、女性语言行为(包括说话和沉默)在社会政治和权力划分之间的关系等。女性民俗学的出现,使民俗学研究开始真正以女性为研究本体,不仅使得传统民俗学对女性研究的话题得到全新发展,而且使从女性视角出发的研究得到重新审视。
再次,就研究方法而言,女性民俗学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及个案研究的方法,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feminism ethnography)。主张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进入被研究文化主体的语境之中,以女性的视角去解读女性,真实地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及其女性文化。受反思民族志的影响,许多女性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如莱拉·艾布-卢高德(Lila Abu-Lughod)和罗丽斯(Elaine Lawless)等在女性叙事学研究中开始尝试新的民族志研究和书写方法。莱拉·艾布-卢高德认为,女性民族志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即作为女性和作为研究者,其所书写和呈现的民族志挑战了传统民族志写作的范式及权威。“女性民族志工作者应当倾听其他妇女的各种声音,并以一种不是学者主导的方式来描述日常生活,展示妇女对她们的社会和生活的看法。民族志写作,要书写彼此相关联的个人,研究者要参与其中并对研究对象关心和同情而不是以疏远的态度来写作,不要把自己置之于外。”而罗丽斯在她1993年出版的《神圣的妇女,完整的女人》中,将女性民俗学理论与民俗志方法相结合,分别讨论了社会性别、民俗文化类型、个人经历等问题,并在民族志研究和书写方式上作出了有益的实践。罗丽斯关注女性生活故事的“多声部”性,并对口头故事文本化过程进行探究,力图在民族志文本创建过程的研究中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她认为,女性的经历形成了她们的生活故事,形成了她们看待创建意义的方式。她试图去寻求“互惠民族志”(reciprocal ethnography)的方法论,即一种能够囊括女性生活经历不同表述和表达形式的民族志方法论。她认为,民族志文本并不是自己独自完成的,而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即“两个女人互相商讨意义、然后彼此认同并最终得以成为文本”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使自己的合作报道人去审视、修改民族志文本并在意义呈现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此外,当代女性民俗学研究也比较重视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法”使得不同地域、国家、族群的女性及其文化被全方位、大规模地关注和考察。目前,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妇女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的研究,用来揭示不同地区的女性及其生活状态。
民俗文化研究意义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民族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潮汕地区
中图分类号:K890;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4-0121-04
民俗体育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做出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以西方体育文化为主导的现代体育发展过程中,民俗体育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在一些地区甚至陷入了濒临消亡的危险。文化多元化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体育文化的多元化是体育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因此,传承与发展民俗体育应该引起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重视。近年来,民俗体育受到了我国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视角进行探讨,产生了颇具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具有共性特征的民族传统体育而言,民俗体育应该具有个性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特征,不同地区民俗体育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因为它与特定地区的民俗、民情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民俗体育研究所反映的是不同地区民俗、民情的个案,通过对各地区不同特色的民俗体育进行挖掘与整理从而形成我国的民俗体育体系。潮汕文化是我国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潮汕文化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移民文化、凝聚力、记忆文化、商业精神、主动性等方面[1],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潮汕民俗体育也应该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发展轨迹、表现形式和价值。
1 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简介
对我国现有的民俗体育研究进行归纳与总结,是推进潮汕民俗体育研究的重要前提。我们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自1991年至今的20年间,“民俗体育”的相关研究文献有240余篇。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内容:(1)民俗体育的概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研究。王俊奇[2]认为:民俗体育是指那些与民间风俗习惯关系密切,主要存在于民间节庆活动、宗教活动、祭祀活动中,是一种世代传承和延续的体育文化形态,具有集体性、传承性和模式性的特点。王铁新等[3]认为:“民俗体育是由一定的民众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使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习惯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具有类型性、继承性、传布性和非官方、非正式特征的体育活动事象与活动。”李艳茹等[4]认为民俗体育文化具有“活跃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丰富我国体育文化内涵,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促进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提高”等社会功能。(2)民俗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刘旻航[5]认为,必须认真研究民俗体育的认知过程,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民俗体育的发展规律,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认知、了解民俗体育;才能够让民俗体育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张国栋等[6]指出,目前随着各种民俗体育活动的日益增加,以及民俗体育与学校教育、旅游商贸的结合,民俗体育发展道路越发宽广;民俗体育的传承式微、功利化倾向是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挖掘整理、提高民众的认识、鼓励并引导良性变异将能够使民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存活并彰显活力。郎勇春等[7-8]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育应全面发挥多元功能、内容形式保持地域特色、科学传承并且和所依附的社会形态与时俱进。(3)区域民俗体育研究。如王俊奇等[9]的研究表明,江西民俗体育中的舞龙、赛龙舟和傩舞与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中秋迎龙神求雨,秋醮演地戏、重阳登高与道教又有丝连关系。此外还有浙江、湖北、天津、、闽台、河洛等地区的民俗体育研究,各个地区的民俗体育均呈现出不同的特色。(4)民俗体育学研究。如柯玲等[10]指出,民俗体育学是民俗学和体育学科交叉研究的新尝试,它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学科和现实意义。王铁新等[3]也指出关于民俗体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民俗体育研究的当务之急。此外,还有关于民俗体育资源开发、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当然,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如民俗体育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科学发展模式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民俗体育的经济效益开发及发展前景研究、民俗体育发展历程研究等比较缺乏。通过文献检索,我们尚未发现有关潮汕民俗体育的系统研究。为此,进一步深入了解以上的研究内容,增强对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现状的理性认识,无疑将有助于潮汕民俗体育研究的开展。
2 潮汕民俗体育研究的必要性
2.1 有利于丰富我国民俗体育理论体系
潮汕地区主要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汕尾4市,潮汕地区不仅有“海滨邹鲁”的美誉,也有“省尾国角”之称,在环山面海兼具封闭与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勤劳朴实的潮汕人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潮汕文化,尤其以潮汕饮食文化(潮州菜、功夫茶等)、潮汕戏剧文化、潮汕方言、潮州工艺美术等著称。潮汕民俗体育也别具一格,包括强体健身抗暴作用的武术、防病益寿作用的气功、南方水乡娱乐功能的龙舟、娱神娱人的节庆游行体育、具有地域特色的群体式情绪广场体育舞蹈等等,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异,共同构成了潮汕民俗体育文化体系。潮汕民俗体育文化既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是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对具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的潮汕民俗体育的整理与挖掘,有利于丰富我国民俗体育理论体系。
民俗文化研究意义范文第3篇
2.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彭牧
3.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分类乌日古木勒
4.多民族地区村落文化保护与社会发展的思考——以贵州荔波水族村寨研究项目为例李松
5.以年节和清明为例看传统节日的传承高占伟,叶涛
6.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申报制度陈华文
7.2001-2010: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点问题研究综述魏崇周
8.真武信仰在近世中国的传播王见川
9.论隋唐五代民间神灵崇拜的整合民俗研究 李浩
10.上海接财神习俗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黄景春
11."满洲国"的孝子——国家、宗教以及守墓行为的适应性变化杜博思,王乙
12.论皇会与清代天津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为中心的研究姚旸
13."影"、家谱及其关系探析——以陇东地区为中心刘荣
14.村落艺术活动研究:问题意识与文化视野吴晓
15.《民俗研究》来稿须知
16.民间工艺传承中的家族、市场与展演——以山东菏泽穆李面塑工艺调查为例杨帆
17."秃尾巴老李传说"的结构与意义祝秀丽,黄泽香
18.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末清初山东乡村日常饮食习俗魏红,郭新洁
19.山东方志所见岁时饮食习俗的文化解读秦炳贞
20."民俗学"入华考——兼谈近代辞典对学科术语的强化作用彭恒礼
21.周作人关于《广笑府》的一封佚札王鲁娅
22.民俗学研究的想象力与洞察力——从《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谈起于洋
23."牛鼻子"张从军
24.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刘宗迪
1.形象与想象:柏林的都市民族学沃尔夫冈·卡舒巴,安德明,WolfgangKaschuba,ANDeming
2.朝向民俗学的新视角安德明,ANDeming
3.侈糜、奢华与支配——围绕十三世纪蒙古游牧帝国服饰偏好与政治风俗的札记赵旭东,ZHAOXudong
4.西晋"二十四友"集团交游方式探析张爱波,ZHANGAibo
5.民俗研究 新疆哈萨克族女性民俗变迁韩慧萍,薛洁,HANHuiping,XUEJie
6.汉人的丧葬仪式:基于民族志文本的评述张佩国,ZHANGPeiguo
7.祖先何在:人类学视野下的坟墓风水观之争温春香,WENChunxiang
8."七七"丧俗考源刘铭,徐传武,LIUMing,XUChuanwu
9.吃与不吃:食物体系与文化体系彭兆荣,PENGZhaorong
10.乡土宴饮与民间规矩——山东滨州姜家街村"两道饭"宴饮习俗调查王东昕,姜志刚,WANGDongxin,JIANGZhigang
11.春节: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与空间元点陈建宪,CHENJianxian
12.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张勃,ZHANGBo
13.劳动的意义:希腊神人分离神话的哲学阐释傅辰彦,FUChenyan
14.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的传播——兼谈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的本土化及女性化特色邢莉,XINGLi
15.盂兰盆节与日本人的祖先信仰邢永凤,XINGYongfeng
16.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澳门庙宇神祇研究述评谭世宝,胡慧明,TANShibao,HUHuiming
17.从民俗信仰的视角剖析历史上的会道门赵志,ZHAOZhi
18.从家屋到宗族?——广东西南地区上岸水上人的社会贺喜,HEXi
19.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其村庄社会基础——深化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新视域宋丽娜,SONGLina
20.《民俗研究》来稿须知HtTp://
21.村落语境、民众情感与地域认同——山东省莱芜市南下冶村抬杠习俗探讨王加华,赵春阳,WANGJiahua,ZHAOChunyang
1.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民俗研究 高丙中,GAO,Bingzhong
2.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吕微,Lv,Wei
3.关于民间信仰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马新,MA,Xin
4.灵验与感恩——汉民族宗教体验的互动模式甘满堂,GAN,Mantang
5.从华府到洞天——东晋南朝墓葬形制解读张从军,ZHANG,Congjun
6.红枪会与近代乡村自卫(1912-1937)——以鲁东地区为中心杨焕鹏,YANG,Huanpeng
7.近代大泽山老母信仰与地方社会的构建——以日照庵香会碑为中心任双霞,REN,Shuangxia
8.论日本原始信仰中巫女的主体地位李广志
9.《民俗研究》来稿须知
10.从近世走向近代:华北的农耕结合与村落共同体张思,ZHANG,Si
11.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洽性"研究——以明清时期苫山村落为中心吴欣,WU,Xin
12.神鬼信仰意义域在仪式实践中的凸显与强化——以辽宁岫岩"太平香"祭祖还愿仪式为例邵媛媛,张登国,SHAO,Yuanyuan,ZHANG,Dengguo
13.村落间仪式性馈赠及交往的变迁——以京西黑龙关庙会为例徐天基,罗丹,XU,Tianji,LUO,Dan
14.声音的再发现:《捉季布传文》的知识考古冯文开
15.《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女性用名探析许浩
16.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黄静华
17.民俗镜语与影像建构——民俗在中国影视艺术中的运用及其审美价值张玉霞
18.中国人的民族性与孔子的典范人格简涛,JIAN,Tao
19.民俗研究 端午枭羹考陈连山,CHEN,Lianshan
20.从爱尔兰的布卢姆节谈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王湘云,申富英
民俗文化研究意义范文第4篇
随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带给思想界的多次淘洗,“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文化领域里备受关注的话题。无论是作为被批判的乌合之众,还是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大众及其日常生活都是思想领域中极具生产力的土壤。在德语国家,
西美尔、本雅明等思想家倾向于将大众当作受到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控制从而缺乏主体性文化精神的群体;史学界从底层视角和左翼的意识形态立场启动了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在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的视野中,人们习焉不察的普通日常生活中隐藏着传统强大的支配性力量,民俗研究是为了启蒙民众意识到自身生活所内在固有的价值和意义。《日常生活的启蒙者》这部作品通过鲍辛格与五位图宾根民俗学教授的对谈,勾勒出德国民俗学从研究“沉淀的文化遗产”到关注普通人当下日常生活,从研究“民族之精魂”到描述文化的动态历史建构过程的转变,在“日常生活”这个为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中走出一条视角独特的道路。
对德国的民俗学研究来说,鲍辛格在1968年之后将“民俗学”正式更名为“经验文化学”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以日常生活启蒙者身份出现的德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与深受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传统民俗学研究彻底分道扬镳。鲍辛格将他的“经验文化学”研究归属于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而在此学科建制下展开的诸多研究更是远远超过了民俗学科的涵盖范围。学科边界的日益模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领域的交叉性也正是当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鲍辛格和谈话者们谈论涉及话题无一不是当代思想文化领域中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鲍辛格在解释“文化”“传统”“历史”这些关键词时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立场也与现代哲学理论的发展直接相关。
鲍辛格带领下的图宾根民俗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平民视角。平民视角不只表现为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作研究对象,更表现为研究者本人是从平民的而不是精英的立场出发来解释日常生活。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家的目光中往往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种是作为被赞美对象的过分美化的民间,一种是作为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彻底丧失了主体性的被批判对象的大众;前者和传统的乡村生活相关联,后者则和现代的都市生活相连;前者浮现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后者则被以西美尔、本雅明等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批判性地塑造出来。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讨论者们的观点是如何深深地受到这两种倾向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当作被赞颂的对象还是被否定的对象,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中却隐含着一种共同的二元论思考方式和精英文化立场,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评价者从外在于被评价者真实日常生活世界的超越性视角做出的评判,大众日常生活里那些渗透着传统传承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具有惯常性和仪式化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却受到了忽视,由于这种历史性视角的缺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肯定性价值也受到了遮蔽,这是具有“普通人”“本地人”“小地方人”意识的鲍辛格所不能认同的情况。
1926年出生于图宾根地区的鲍辛格,对自己“小地方人”的身份意识保持着一贯的敏感。图宾根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求学与工作之地,他在图宾根大学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工作了32年(1960―1992年),并且是图宾根大学的荣休教授。鲍辛格坦承普通市民出身的自己最初之所以愿意选择民俗学,是因为发现唯有这个专业里涉及的内容能够让母亲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也不介意被人说成“心甘情愿的乡巴佬”,坦承自己身上有着小地方人的品性,不知道大城市为何物,甚至对大学图书馆里士兵般整齐列队又规模庞大的书架都心怀畏惧,直到大学毕业都不曾真正地走进图书馆。鲍辛格本人常常从本地生活中发现研究对象,坚持与地方公众的对话,因此在地方公众中影响颇深,这让他引以为豪。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自觉而清晰的身份意识决定了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具有真正的“普通人意识”,他的研究承担着日常生活启蒙者的使命,却并非一种精英式的启蒙,不需要从宏大的精英文化理论世界里找到合法性,而是要让普通民众感知到自己日常生活原本蕴含的内在价值,进而获得基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启蒙能力。《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娓娓对谈,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位真实生活着的普通人的“在场”,鲍辛格的学者身份和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从来就没有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
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语境中,“本土性”有时候会被当成保守封闭的代名词。鲍辛格不乏幽默地回想起他被聘为教授的那一年,为他颁发聘书的大学校长是如何满脸不情愿地站在面前,只因为他出自本校,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而未曾受过其他院校新风的吹拂。可是两三个星期之后,校长就满脸笑容地任命鲍辛格坐上大学学生处主任的交椅,仿佛之前的鄙视态度从未存在过,只因为不少学生生活的琐事需要一些对当地居民和当地学生特点非常了解的教授来加盟。“令人自卑”的乡下人身份一下子戏剧性地转变成了应对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品质,这种专业体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时时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琐事,由全球化和本土化或曰地方性的断裂与矛盾常常具体化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尴尬处境。鲍辛格从来都不愿意掩盖自己作为一个图宾根本地人的身份和真实经验,反而尝试从这种身份意识和经验出发展开理论研究,展现价值关怀,鲍辛格对他的研究对象怀有亲切之心,也让读者重新思考理论和生活、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关系。
与德国传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研究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的当下性,其次在于它的日常性。当下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旧时光中的旧事物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当代生活的研究;日常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奇风异俗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的研究,正如鲍辛格的一句名言“对不引人注意之事保持虔敬”。19世纪,作为对“在理性精神指引下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的启蒙运动”的反拨,德国出现了以“唤起早先的岁月,在民歌中倾听民众的声音,收集童话和传说,培养古老的风俗习惯,发现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研究‘印度的宗教和智慧’”[1]为内容的历史研究,仿佛过去是现代的失乐园,过去中隐藏着不断堕落的现代文明获得拯救所需要的全部智慧。这种浪漫主义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德国民俗学的发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但在鲍辛格看来,这恰恰是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所在,“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从研究对象上不得不和各种传统打交道。它的问题在于:一是倾向于把传统看成静止的、不接受任何改变;二是把民间文化中保留的传统从根本上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质疑的。”(第79页)
对于历史和传统,鲍辛格持有非本质主义的看法,所以即使是研究传统民俗学同样关注的事物,鲍辛格也能采用一种与当下相关联的新视角。比如,书中提到的狂欢节,核心不是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狂欢节的起源、形式和意义,而是关注狂欢节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发展,虽然狂欢节的宗教内涵在历史发展中已经渐渐让位于娱乐性,但它依然不失为公共风俗和地方认同感的打造者。鲍辛格的研究渗透着现象学阐释学的气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精神科学的本质都在于我们始终处于和流传物的攀谈之中,历史意识在一切精神科学的研究必不可少。在鲍辛格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民俗学研究中包含着对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真正挑战:他研究包含在当下日常生活之中的历史维度,历史作为当代文化的成因而受到关注;他研究作为历史绵延建构生成结果的日常生活,当下日常生活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真正的历史是作为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存在着,显现于人们的生活世界真正展开的地方。
除了研究像节日这类的古老风俗,鲍辛格对当下生活中仪式化的、惯常性的行为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成为德国民俗学研究中的新话题。在鲍辛格看来,当下生活正是历史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历史化根本无法避免。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做一些它们平时对此根本不加思考却强有力地主宰了他们生活的事情,在提出问题的这一瞬间,我已经处于历史的轨道上。”(第99页)越是具有仪式化和惯常性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可能蕴含着越深厚的传统力量,经验文化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要认识当下状况的历史性并让它们清晰凸显出来。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像“问候语”“摘帽子的方式”“散步”等原本最平常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这既大大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视野,也为当代文化研究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打开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
鲍辛格不赞同二元论思维方式,在被追问“日常生活”是不是代替了已经逝去了的、总体性的文化概念如“共同体”或者“传统”等时,他明确表示日常生活决不是充当旧的、自足的秩序或者类似事物的代替物。在鲍辛格看来,80年代一度出现的将民间文化视为主流文化的抗拒者的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画地为牢,肯定无法行之有效,因为在现实中,所谓底层文化也是在一直受到当权者上层的影响中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力图划定一个有反抗能力、封闭的自己世界的做法并不仅仅是民俗学问题……这样对立的模式存在着一种危险,它忽略了错构交结,它以错误的方式减低了事情的复杂性。”(第105页)除了日常生活这个概念之外,对地方或者乡土的研究,也体现出鲍辛格用超越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生成性、建构性视角来解释文化现象的努力。
“家乡”是鲍辛格的著作始终追寻的一个主题。但是鲍辛格对家乡的理解与法兰克福学者们的文化人类学观念不一样,对他来说,家乡或者乡土都不是一个有某种先在固定属性的地理空间,他反对那种地方决定性地影响着人的性格和价值观的“地方决定论”看法。在鲍辛格看来,乡土以及一切并非作为纯粹物理性空间存在着的“地方”都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所以研究乡土或者地方,其实是研究生活在这片乡土上的人,研究他们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如何使得某一片地理空间“成为”乡土或地方,这种看法又与受到现象学影响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不谋而合。鲍辛格经验文化学的地方研究不像传统的地域文化研究那样只研究静态的文化空间秩序,而是追问塑造某种“空间文化”的动态行为进程,研究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文化中经验空间和安排空间。不是空间先在地决定了文化,而是文化历史性地推进着空间的形成,并在推进空间形成的过程中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空间性由此成为文化的一种基本属性。从这种动态生成的观点来看,人与地方的纽带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乡土并非一个和全球化绝对对立着的封闭空间,政治学上的地理空间划分和人们头脑中的地域意识也可能并不一致。
60年代的德国有“边城僻壤无处不在”的说法,鲍辛格却是被批评的生活在边城僻壤中的乡巴佬的辩护者,他甚至发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大城市里的人也是多半生活在那些结构经常和村庄很相似的特定街区和地盘里。鲍辛格对地方经验和地方身份的珍视并非来自盲目的地域优越感,而是来自对人与地方在生存论上的根本性关联的意识。他的乡土研究表明,乡土处于不停的生成和变动中,但是人们对地方归属感的一种自觉的或者无意识的寻觅,却是在变动中恒定不变的东西。随着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家乡也许已经不再是出生的那个小村庄,但是无论人们身在何方,他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经验着家乡,也许是乡愁,也许是在新的生活之地重构家乡,即使不能回到最初的故乡,也依然会在新的生活空间中创造出一个让最初的故乡和当下的生活空间共同在场的家乡来。“家乡”这个概念不是地理学上的,而是生存论上的,如果说空间性是文化的一个内在属性,那么家乡也是人生存的一个内在属性。虽然鲍辛格主要围绕着巴登―符腾堡地区展开关于家乡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也可以视为他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一种具体回应,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能够引发读者对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地方的命运,以及与地方相关的个体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思考。
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包含对本国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语境的思考,图宾根的民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对纳粹历史的清算。鲍辛格深深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危险,他赞同马克思・韦伯将族群性定义为“被信以为是的共同之处”,从而将生物主义从对民族性的研究中摘除出去。“信以为是”而不是“先天就是”,表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有着确定本质的东西,经验文化学的任务就是要去研究文化如何通过人们的经验和想象而生成,而不是文化如何受到某种先天的地理性、生物性因素的决定而形成。鲍辛格和他的追随者们明确意识到经验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区别,在法兰克福,所谓的人的自然条件总是被推到前台,文化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是普世的人及其自然本性;而图宾根的经验文化学者却坚持没有所谓的普世的人,人的文化属性是历史性生成的产物。
在有着强大的哲学传统和理论思辨精神的德国,虽然鲍辛格和他的经验文化学似乎一直是一个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学科,但是也如鲍辛格所言:“我们专业从事的研究,无论如何不是孤独的拓荒,它们多方面地得益于相邻的学科和宏大的理论。”(第113页)在鲍辛格的理论研究中不难看出现象学、解释学的影响,以及与社会学、历史学的关联,经验文化学是一个不断走向跨境之旅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领域极其宽泛开阔而边界模糊,而它所研究的问题又极其具体细微,但是这也正符合鲍辛格的独特信念:“规矩越严密的地方,保留自由空间越重要。”在越来越等级森严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在让西美尔感到忧虑的客观文化压倒主观文化的现代文化世界里,一种能够对具有灵活变动性的日常生活做出直接有力阐释的理论风格,一种能够加强公众对日常生活的自我反思精神和理解能力的问题视野,与那一波又一波裹挟着理论界的宏大理论建构同样重要。理论家的行列里理应行走着这样一类人:他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心满意足地凝视着那些环绕身边的日常生活事物,他面带亲切而满意的微笑,对人们说:“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
注释
民俗文化研究意义范文第5篇
民俗民谣音乐作为艺术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我国《学校艺术教学工作规程》强调,艺术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和地方艺术文化传统,提高文化艺术素质,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辽宁本溪这块热土历史悠久,民俗民谣文化丰富多彩,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民谣艺术文化在民间广为流传,如评书、二人转、东北大鼓、秧歌、乡村乐队、喜歌等,以家乡特有的文化底蕴在这里酝酿生根。由于时展的今天通俗流行的音乐重金属元素占据初中生音乐思想意识,初中学生对地方民俗民谣音乐有抵触现象,这确实透视出本地区音乐教学与民俗民谣音乐传承之间存在着脱节的现象,直接导致学生对地方传统文化理解每况愈下。农村初中音乐教学融合民俗民谣音乐元素,更好的开发和利用当地的民间音乐和文化资源作为学校音乐课改校本课程的开发和研究,增强学生对民俗民谣多元文化的接纳与包容意识。因此,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和改进音乐文化教学融合乡土的民俗民谣传统文化熏陶。提高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民族复兴的需要,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
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曾指出的:“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学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地方民俗民谣音乐文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综合的具体体现,是各地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地方的民俗民谣音乐教学不仅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进行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教学的需要。大教学家陶行知说过“生活即教育”,本地区民俗民谣音乐文化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生活化,让鲜活生动的文化来达到教化的目的。挖掘、传承、弘扬本溪音乐文化,给我校音乐课堂注入鲜活的文化灵魂。我们农村学校要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逐步实现教学文化传递功能。让农村学生体验挖掘,收集民俗民谣音乐文化的全过程,从而使学生对民俗民谣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上升到理性认识,真正让学生喜爱家乡的民俗民谣,在音乐课堂上达到顺畅民俗文化,传唱民谣精髓的目的。
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音乐教学浪潮迭起,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民俗文化差异显著。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研究已成为世界各国音乐教学研究的新热点之一。世界各国研究成果浏览电子资源库可以发现,大量的研究以高校校园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学术问题,且以教育调查,教学实践等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的的占大多数,研究的结果较为客观、可信。由于我国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起步较晚,特别是地方音乐资源的开发、利用较为薄弱。从目前检索收集到的资料看,我国民俗民谣音乐教学的研究主要以理论思辨为主,针对民俗民谣研究具体实施欠缺,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缺乏地方音乐文化的挖掘,音乐教学缺少民族和地方特色。研究农村初中音乐教学融合民俗民谣文化只有少数研究者投以关注的目光,较少有学者参加研究队列,全国核心期刊也少有音乐教学渗透民俗民谣文化方面的论述。笔者认为,以农村民俗民谣音乐文化为切入点,站在优秀教育专家的高位,着力突破地方民俗民谣音乐文化融合音乐教学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实施音乐教学民俗民谣的有机结合:
1.确定目标和依据
通过研究,以“民俗民谣文化”为依托,结合当地音乐文化资源,运用恰当的方法和途径融合民俗民谣音乐文化,有效实施民俗民谣音乐文化教学,激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汲取精髓,提升音乐素养。提高学生对“民俗民谣音乐”的鉴赏和实践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利用多种有效手段和途径获得民俗民谣音乐文化信息,引导和鼓励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有特点的个性品质的学生。在了解欣赏学习本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分析我校音乐教育教学现状,宣传民俗民谣音乐知识,发挥师生的创造潜能,加强学生对本土音乐的实践体验,形成适合我校特色的音乐教学。
2.学科教学与收集、挖掘民俗民谣二者有机结合
调查了解本地区民俗民谣发展情况,对即将失传的民谣进行抢救和发掘;透视和补救学生惯性漠视乡土音乐的现状;通过收集、实践、筛选、整理四个实践过程,转变激活音乐教学。在音乐实践中融合民俗民谣音乐文化。组织参加艺术实践活动,如“每周一歌”,“乡俗乡音展演”,“校园民族风音乐文化讲演”等,逐步渗透地方民俗民谣音乐文化(如:东北大秧歌,二人转小调,节日祝福民歌民谣等),寓教于乐感染学生民俗民谣音乐的熏陶。在学科教学中融合民俗民谣音乐文化。利用乡土音乐资源,弥补音乐教学需求,把课外实践策略地转化成课堂教学正能量的渗透。
3.综合性内容提高要求
将音乐教学作为融合地方民俗民谣文化的平台,并确实收到实效。让过程体验作为提高农村学生对民俗民谣音乐鉴赏和创造的主要学习方式,利用各种渠道(如,调查、采风、音像、杂志、网络等)广泛收集做铺垫,吸取精华,弃其糟粕,使经典音乐为学生乐于接受,易于传唱,拓展音乐文化教学空间也是研究的实质所在,具有鲜明时代烙印,亟待深入发掘,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实施的可行性,对于新课程背景下区域性音乐文化教学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和经验。我们音乐教育者应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地方与学校的音乐教学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开发具有地区民俗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也是补充完善音乐教学中民俗民谣的缺失,使教材内容来源于生活,从而丰富了教材内容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