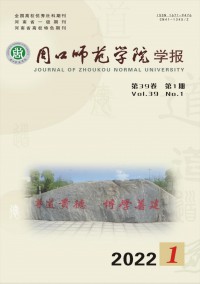老子的名言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老子的名言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老子的名言范文第1篇
2、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3、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4、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5、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6、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7、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8、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9、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老子的名言范文第2篇
文/大隐
带病延年是指那些身体患有某种疾病的人通过医治和保养也能够像不患病的人一样高寿。如皋坊间的说法就是“病秧子熬出了大寿命”。
我在长寿村接触了一个带病延年的老人叫郭英,已经90岁了,她患糖尿病有40年,现在除了每天注射胰岛素外,身体如同常人,精神状况很好,能说会道,还能唱京剧。郭英的母亲在村里也是有名的病秧子,身体骨瘦如柴,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常常感冒发烧,浑身酸痛,但她也活到了92岁。
老人带病延年的秘密在医学上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机体通过病症的发作产生抗体,免疫力得到了增强。疾病是人体与外界或身体内部的有害因素搏斗的复杂运动过程,在它们相互较量的过程中,人体获得了一系列防御、适应和代偿功能。常生小病对机体有一种持久的刺激,可以使体内的神经、内分泌系统活跃起来。人体内分泌的激素,也可以调整体内环境,保持机体的内外平衡。比如说,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因为经常受到疾病的骚扰,内分泌素不断产生调整作用,从而不使身体发生重大的病变。而不常生病的人体内的内分泌素时时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因而它的功能很弱,当病魔突袭时,不能进行有效抵抗。所以一旦发病就可能是大病。
从如皋长寿老人的实际情况来看,常生病的人之所以能带病延年,除了机体免疫系统受到刺激而增强了抵抗能力外,他们还具备了自我关爱的意识和养生技巧。带病延年的另一个秘密是“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所发挥的作用。
一般来说,体质较弱或常生病的人,出于本能,会小心翼翼照顾自己的身体,有意规避健康上的各种风险,以避免诸多因素对身体的伤害,他们以“巧”取胜,使生命细水长流,反而能延长寿命。而那些貌似健康强壮的人则高估自己的身体能力,肆意挥霍身体资源,造成身体的空前透支,使得抵抗力下降,给疾病以可乘之机。
在长寿之乡走访,您会慢慢体会到那些长寿老人在带病延年的过程中所传递出的生活哲理。我觉得,凡是能带病延年的长寿老人都是精通生活的智者。他们除了在饮食、生活起居、锻炼等方面形成良好的习惯外,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是他们战胜疾病的法宝。
四个方法提高短期记忆力
文/李柏
一、写购物清单
老伴刚说让你帮个忙,可你转身就忘了;医生反复叮嘱你用药须知,可一回到家你就想不起来了……这说明你的短期记忆力在变弱。这时,你可以尝试一下短期记忆训练。
1.拿出纸笔,记录一个购物清单,到了超市,先根据记忆去找要买的东西。当买全能记起的东西后,再拿出清单看一看,快速记一下还没买的东西,紧接着再寻找。
2.就这样不断反复,直到你买好所有的东西。可能第一次你只能记起两三个,但经过训练后,你就能记忆得更多了。此后加大难度,列出更多商品。海马于脑颞叶内,主要负责人的学习和记忆,人从外界接收到的短期信息大都由它负责存储。短期记忆训练可以不断刺激海马体,从而帮助中老年朋友提高记忆力。
二、算算收银条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种和超市购物相关的方法,那就是“心算购物总价”的训练。
选商品的时候顺便记住每件商品的价格,然后将它们的总额算一算。到了收银台,你就可以根据收银结果对照一下自己算得准不准确。这个方法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很难,即使你心算的数据和最终收银结果有出入,也不要灰心,养成习惯后你就能够算得越来越准确。
这项训练同时针对大脑的运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对大脑额叶、颞叶、顶叶等不同区域都有“修复”作用。而且这个方法简单方便,既不费时也不费力,轻轻松松地就训练了记忆,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三、复述话语
很多中老年朋友记不住别人刚刚说过的话或交代过的事情,那是因为没有在脑子里形成短时记忆的习惯。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复述”的方法。
你可以找个同伴一起来学习,一个朗读文字,另一个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如果没有搭档也没关系,像录音机、复读机、电脑都是不错的学习帮手。我们可以先说一段文字,用设备录下来,紧接着你自己复述一遍,复述完之后立即放录音检查有什么不一样,看看自己是否一字不漏地说出来了。
这个训练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你可以多多练习,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的记忆力就会有好转,到时候别忘了把这个方法推广给你的亲朋好友。
四、数字游戏
除了上面的复述训练,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训练方法,那就是记数字。今天就让我们来试试下面的方法吧!
1.用10秒钟来记忆这七个数字:4、9、15、16、28、38、42,然后把视线移开,按照顺序把它写下来。如果写对了,再接着记忆下面一组数字:21、34、7、16、82、15,同样用10秒钟的时间,如果还记得不错,那就再多写几组数字进行训练。
老子的名言范文第3篇
北京市工商局近日本周食品下架信息,共有11种食品被停售。哥俩好、牛排王、乡吧佬、小面筋等四家品牌的部分调味面制品成为本次检查出的主要问题食品。
本次共抽取样本706个,不合格样本11个,抽检合格率为98.44%,其中蔬菜、鲜肉、食盐、大米、食用油、食糖、水发产品、鲜奶、干菜、小麦粉、蜂产品抽检全部合格。日常烹饪调味品大料(八角茴香)出现在下架榜单之上。北京佳久发商贸有限公司生产的古福牌50克/袋的大料被查出二氧化硫含量超标,该产品在去年8月份就曾被查出质量问题。
取款机肮脏程度如公厕
人们往往认为公共厕所是最肮脏的地方,也是公共卫生最大威胁。然而,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最新调查发现,自动取款机(ATM)的肮脏程度堪比公厕。因此,下一次从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时,最好戴上手套。
英国某公司的专家用棉签在英国城市中心每天被无数人使用过的ATM取款机的数字键上提取标本,与从公共厕所马桶上提取的标本一起,在实验室里进行培养和观察。检验发现,ATM机键盘和公厕马桶标本都含有假单胞菌和芽孢杆菌(导致疾病和细菌性腹泻的病菌)。
明亮的灯光可缓解老年人抑郁症状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使用特殊设计的灯箱进行三周的光照疗法,可使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症状改善54%。除了可提高病患的情绪外,光照疗法也可改善睡眠,并使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的水平最佳化。血清素水平过低被证实与抑郁有关,且通常是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标的。此外,研究还发现,接受明亮灯光治疗的患者,压力型荷尔蒙皮质固醇浓度有所下降,其睡眠质量同样也得到了改善。明亮的灯光疗法为那些不愿意、拒绝或无法耐受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患者提供了替代的方法。
散装土鸡产蛋更具营养
在超市里,标明“有机”、“绿色”、“散养”等概念的高价柴鸡蛋为数不少,那么,它们与普通散装鸡蛋相比,到底有何不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刘华贵给出了答案:“产蛋鸡分为高产蛋鸡和地方土鸡。高产蛋鸡多为国外进口品种,目前许多品牌鸡蛋其实是高产蛋鸡所产,并不是柴鸡蛋。真正的柴鸡蛋应该是散养土鸡所产。土鸡属中国本地品种,其蛋孕育时间长,产量低,因此营养价值会更高些。因此选鸡蛋,首先要看鸡的品种。”
他说,在北方地区,被《中国家禽品种志》收录的北京油鸡属中国优良地方鸡种,已有300多年历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品种。其适合山地散养,但平均产蛋率只有笼养的40%左右,年产蛋量不超过120枚,饲养成本比普通鸡蛋高一倍多,因此市场价也比普通鸡蛋贵一倍。
刘华贵称,真正的柴鸡蛋与普通鸡蛋的区别有三:一是外形颜色不同,柴鸡蛋较小,一般在42至52克之间,大小、颜色深浅不一致;二是柴鸡蛋比等重的普通鸡蛋的卵磷脂营养含量高;三是柴鸡蛋口感比较香嫩,没有蛋腥味。
他提供的区别柴鸡蛋与普通鸡蛋的区别方法是:煮熟后不立即浸冷水蛋壳很难剥离,且易剥下蛋白的是普通鸡蛋;煮熟后不用浸冷水也很容易剥离,且蛋白更加透明的则是柴鸡蛋。
个别日用陶瓷铅镉超标严重
广东省工商局近日公布了2010年广东省流通领域日用陶瓷商品质量监测情况,在抽查的120款日用陶瓷餐茶具中,23款商品质量问题较严重,不合格率为19.2%。但令人担忧的是,在抽查的120款产品中,竟有72款是无厂名厂址商标的“三无”产品,占抽查总数的60%。其中检测出铅镉溶出量超标的商品8款,7款为“三无”产品。
专家提醒消费者,慎购无厂名厂址的餐茶具,陶瓷中的铅镉遇热、遇酸更易溶出,长期使用会引起慢性中毒。购买餐具时,纯白、无装饰的更安全。
母乳喂养的孩子学习成绩较好
澳大利亚一项新研究为“母乳喂养有益孩子智力发育”提供了新证据。研究显示,婴儿期接受母乳喂养6个月以上的孩子在10岁时的学习成绩要明显好于母乳喂养少于6个月的孩子。这一点在男孩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科研人员分析了1 038名澳大利亚儿童的学习成绩,并与他们的母乳喂养记录等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排除可能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其他因素,比如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以及家庭早教状况等,研究结果显示,母乳喂养6个月以上会对孩子日后的学习成绩有明显益处。这一点在女孩身上表现得不如男孩明显。研究人员说,这可能是因为男孩和女孩的发育情况有所不同,所以母乳喂养对男孩的大脑发育影响会更大一些。但他们指出,这并非说明母乳喂养对女孩不重要。
研究人员介绍说,母乳对于婴儿的神经系统发育十分有益,母乳中许多对大脑发育至关重要的营养成分是配方奶所不能提供的。他们之前的一项研究还发现,母乳喂养达到6个月以上的婴儿在儿童期不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鉴于母乳喂养的种种益处,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应大力提倡接受母乳喂养至少6个月。
老人上网更长寿
老人的长寿法则,不仅仅是清淡饮食、适量运动和早睡早起。美国护理服务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上网、写博客、玩电子游戏等时髦行为,一样能成为长寿秘诀。
以前不少老人都有“恐脑症”,觉得高科技产品太难学。其实,越是年龄大,越应该接受一些新事物。首先,老人每天上网浏览新闻,或是关注自己曾经从事领域的最新进展,可以防止自己的知识落伍,有助于增强自信。其次,聊天工具和社交网络有助于让老人和子女、朋友保持联系。再次,老人可以利用电脑写博客,或把家人的照片做成PPT等,这样可以把美好的回忆永久保存下来。最后,在搜索、打字、写博客等过程中,脑细胞活性能被充分调动,延缓脑力衰退,能有效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
不过,老年人上网跟应该注意有度,如果染上“网瘾”,一样会危害健康。
药监局曝光9种产品违法广告
老子的名言范文第4篇
作为中国古典哲学中主要范畴之一的“道”,最早是由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来的。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是中国古代两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善言天道,开创了中国古代的本体论学说。
老子对后世有着如此之大的魅力和影响,而他本人却是一个极为洒脱、淡簿名利的人。这是我在读完一些有关老子的著作后的第一感想。老子一生学术无数,却不追求功名利禄、富丽堂皇。他读书研究学术是为了完善自己,并通过一定的思考找出有力的治国方针。老子说他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甘愿付出不求回报,用行动来决定自己的人生。如此坦诚地面对人生的成败便可明知他研究学术靠的也是“洒脱”二字。这在当今社会看来是很难办到的。就我们中学生来说,再怎么坦然也是无法不去注重“成绩”二字,更多的是淡化了努力的过程而捧高了虚荣。或许我们真的应该摒弃“贵富而骄”,否则便会“自遗咎也”,而学会“功遂身退”,此之为“天之道也”。
老子的洒脱也可用他的后人亦是道家的另一伟人庄子的名言来概括:修身养性清净无为,思想像水一样,不怕后人的肢解,不会被历史湮没。老子亦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言论为后世千万人乃至国内外解构、剖析,无人不佩服,古今中外的许多名人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吸取了他的思想。
老子的洒脱表现在他的清净无为,而他的清净无为则又表现在治国和做人两个方面。
治国而言,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天下大乱。百姓都希望世间能够有一个明理爱民的统治者。老子当然也不例外,为各国君主们提供许多模范和道理,从而提出了道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他认为圣人――即他眼中理想的统治者应当是遵循自然规律,采取无为之治,任凭老百姓自作自息,繁衍生存,而不会采取干预的态度和措施。类似吴澄的话:“天地无心于爱物,而任其自生自成;圣人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而老子说:“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同时,他也提出清净无为的治国理念。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做到心境极其静定,洗清杂念,摒除妄见,懂得自然规律,加深自身的道德修养。一国的统治者,应当静、重而不应清、躁,如此,才能够“爱民治国”。
做人来说,在老子的人生哲学里,“自然无为”最深入人心,细细读来,颇能洗涤和启迪人的心灵。以水为例,老子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说明弱可以胜强,柔可以克刚的道理。老子便也是学水做人的,他认为最完善的人格应该具有滋润万物而不与争的心态与行为。即“善利万物而不争”,何等的洒脱!何等的做人理念!而“致虚守静”又是老子的另一道学。他主张人们应当用虚寂沉静的心境,去面对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坦然地面对死亡。“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人的死亡是“归根”“复命”的概念,是回归到大自然一切存在的根源,成为泥土的又一分子。如此简单完美。可我们仍在害怕生死离别,或许因为牵挂着情感,留恋、不放与不合,这真的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生命的真实意义了。但清净无为、为民而生而死确是一种幸福。老子的无为无畏也成就了一大批革命志士,、蔡和森、向警予和等便是受其影响。至于当今和平年代,或许我们没有机会萌生那种豪迈的昂扬斗志,但我们就没有清净无为的念头和行为了吗?不是的。在生活、学习和交际等方面,在决定做某件事情之前,我们都可以抛开世俗名利、功名利禄,真正地静下心来,想想事情的价值取向,清净无为的洒脱会让我们飞越世俗的瀑布到达真理的彼岸。
老子的名言范文第5篇
巍巍中华,源远流长。孔丘、孟轲倡儒家之“仁”“义”;老子、庄周尚道家之“修身”“养性”;墨子主法家之“兼爱”“非攻”。(此处排比使语言酣畅通达,生动有力,气势非凡。)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写道。的确,德才兼备乃历代君王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正所谓“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引用名人名言,典雅精致,极具感染力。)
张仪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纵横于天下诸侯,可怜的楚怀王,你怎能让张仪那如滔滔江水似的甜言蜜语蒙蔽视听?你只看到张仪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于是你心灵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屈原被放逐,张仪获得高升。殊不知,张仪乃巧舌如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无德、无行之辈。选择人才标准的错位,使楚怀王最后落得身死异乡的悲惨下场。(设问启发读者思考,使作者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更加明确,意蕴深厚。)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刘备以忠义驰骋天下,以肝胆照耀乾坤,选择人才亦是“忠”字为先,“德”字为首。
刘备惊叹关云长万夫不挡之勇与披肝沥胆之气魄,与之结义桃园。于是便有了关云长“为寻故主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和“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骋时无忘赤帝”的佳话。历史证明刘备当初对关羽既重其“良”又重其“驯”是正确的。(引用名人名言,文句精美,意味深长。句式长短变化,错落有致,富有感染力。)
春秋时期,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的故事流传千古,然而古往今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正是鲍叔牙博大的胸襟与高山仰止的品行,而对管仲才能的钦佩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知世人对“德”的崇拜是高于才的。(对比手法的运用,使事物的性质、特征等更加突出,语言色彩更加鲜明。)
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侠肝义胆的豫让虽身怀绝技,却能灭须去眉,吞碳为哑;娄师德,德才兼备不记私仇,十荐狄仁杰。他们是历代帝王所推崇的才,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良”有“能”,更由于他们有“驯”有“信”。(“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对偶使句式整齐有力,x来朗朗上口,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
由此可见,“德”是“才”的支配机器,“才”只有以“德”为主体,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正如大雾天的航船只有在灯塔的指引下才能驶入港湾;在沙漠中行走,只有在指南针的指引下才不会迷失方向一样。(比喻的运用,使语言更为生动形象,使说理更为透彻。)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评价人才,选择人才,注重才能固然重要,但高尚的品行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厚德才能载物,高尚才能有景行,马先驯乃有能有良,才能恒久立足于世。(引用名人名言,使文章意蕴深厚,回味无穷。)
点评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