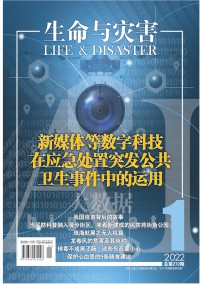生命之诗
生命之诗范文第1篇
一个失去了爱情的人
他有理由成了一个梦游者
世界粉碎了美好的情感
我们的灵魂里堆满了灰尘
沉默的人太多了
喃喃自语者太多了
背叛的人太多了
他把一个秘密锁进了抽屉
有一天他会死去
我们也会跟着他死去
这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手挽着手跨过了地狱的门槛
爱的上帝
爱的上帝
我刚刚从生活的狭缝中
钻出来一小会儿
这一小会儿是我自己的
如果你不介意
我想和你说一小会儿话
你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坐得很高
我尽力仰着头
也看不见你
如果我跪着
你会坐得更高
我现在站在屋顶上
接收来自你的信息
真的该死
人间的黑暗笼罩着我
我的钱包丰满
我的内心空虚
就是这一小会儿
我依然空虚
没有理由为生活辩护
爱的上帝
你的爱无所不在
但我不配享有
这人间的罪恶有我一份
我摸着伤口犯罪
充当知识分子的帮凶
在堕落中从不孤独
爱的上帝
我想抱住一块石头痛哭
我想在身体里点一支蜡烛
我想心中藏甲兵二十万
爱的上帝
我想两手空空
我想被你的智慧吞噬
爱的上帝
我想同时做一个儿童和老人
爱的上帝
我想和你再说一小会儿话
虚 无
深渊让我们分担命运的矛盾
天空是我们的死亡之所
你和我都是孤独的个体
生前没有拥抱
死后依然沉默
大风吹走我们的体温
灰尘落在我们的白骨之上
至高的事物呈现在我们的表象里
我们仿佛醒来
又被天空埋葬
解 脱
风从虚无的气息开始
它流动着
在我的手掌里
形成一座旋转的花园――
石头和山谷对峙
鸟鸣清洗一枚淡绿的铜钱
马匹在湖泊上空飞翔
牛羊满足青草的气息
仿佛我刚醒来
一个婴儿穿过我的身体
壳
在夜里,你独自品味悲伤
回家的路很深,舌头很深
灵魂没有痕迹,像你回到月亮上去
在我的视野里,不见一颗孤独的星球
那些下降的事物,在空旷中失重
像一层层打开包裹,露出白骨和栅栏
但你的伤痕一层层加厚,像坚硬的壳
小心翼翼地分泌火焰的汁液
自 述
我被夜里的冰雹震醒
披衣起坐
在黑暗中亲近黑暗
阳台上的花草
拼命咬住雷电的尾巴
把身体塞进饥饿
实际上我没有倾诉
我只是爬出自己的洞穴
生命之诗范文第2篇
看那小草
随风的方向
左右摇晃
看大树的枝叶
随着风的方向
来回来去的摇摆
风把我吹的也是左右摇摆
可是
不管风有多大
我对你的心永远不变
我永远的爱你
不会改变
尽管你不爱我
但是,不管怎么样
生命之诗范文第3篇
这些错误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前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倡的。最早这样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茶嗜之……。"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
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当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认为这"革命"是"失败"的。此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九二九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年)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创始者。在解放后的一些著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九六年),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一年)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六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一九六三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一九八年),孟祥才《梁启超传》(一九八年),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九八一年),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对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说:"他(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认为:"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认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⑤。
现在讨论前一方面的看法。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称《诗话》)中那一段话为根据,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则诗话联系起来。为说明问题起见,按照当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则诗话的原状,引述如下:
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贈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按,徙当作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又云:"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皆工绝语也。……⑥
梁启超从壬寅(一九二年)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则或数则。上面引述的四则诗话刊载于癸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则诗话,在此四则诗话前后另有四則,其内容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然据第八则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则诗话写于一九三年。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按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则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前后则诗话不一定有连贯性。这里,在上述的前三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况。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对于"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只指出:"盖当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新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堆积"经典语",或者"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
在第四則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回事。这里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间--一九三年--之前的近阶段,并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则诗话中所引麦孟华(孺博)的诗作于庚子(一九年)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而在第三则中云:"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即梁在第二则诗话中云"当时"、"数年前",而不云"近时"、"近年")的作品。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也就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当时喜欢作这类"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欢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实际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则诗话中,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应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类"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理解的,是"总结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当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如下:
他(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我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征,但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如果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叙述,不应当只字不提。此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当时作诗的情况,有二点尚可注意。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分别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当时"是极自然的。二、他们作这类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生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类诗改变诗体或当时的诗风。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类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般不难解的旧诗11。由此可见,他们偶尔作这类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说他们当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首先,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主要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孙中山于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事失败到日本后,开始采用"革命"这一口号12。但他传播革命思想对国内影响甚微。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內思想界的情况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据冯自由云:"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 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 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或所谓:"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他说:"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三、"诗界革命"是梁启超受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从上面引述梁启超及冯自由的话,可知倡"革命"论者"多习于日本",并且发生在戊戌之后。而"诗界革命"及"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也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革命"指改朝换姓的政治变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革命",即包含着推翻清朝,光复汉政权之义。而日本人译英语"Revolution"为"革命",如英人称其历史上一六八八年确立君主立宪的政变为"Glorious Revolution"(即"光荣革命")一样25,日人习称其"明治维新"为"革命"。梁启超《释革》云:"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26可见这里"革命"一词在政治上指"变革",已失去以暴力更迭旧政权的意义。康有为到日本不久,在《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一诗中,盛赞明治维新为"千年大革命"27,说明他对"革命"一词的观念已发生变化。后来梁启超在一度革命之后转向改良主义时,就是在这种"变革"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由于"革命"指广义的"变革",日人译名中常出现"宗教革命"、"道德革命"等。梁启超在《释革》申明白指出:"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28同样由于受日本译名的影响,梁启超于己亥(一八九九年)五月赞康有为发明孔教为"宗教革命"29,于同年十一月倡议"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30,于壬寅(一九二年)九月倡议"小说界革命"31。(梁启超初至日本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32,尚未提出"小说界革命"。)由此可证,"诗界革命"这一口号只有梁启超到日本之后才可能提出。第四,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自己有所论述。
《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记》)是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冬赴美途中所作的日记,其中谈到"诗界革命"。过去一些研究者在论述"诗界革命"时,曾引用过这篇材料,由于囿于成见,忽视了文中某些重要内容。经初步分析,这可以看作是有关"诗界革命"的最早文献。节录如下: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追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己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文芸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仓海《題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輸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于?要之,支邪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3。
在这些谈论诗歌"宗旨"的段落中,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其理由是:一、千馀年来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二、黄遵宪的诗"锐意欲造新国",但缺点是表达新内容的"新语句尚少"。三、夏、谭的诗"善选新语句","可谓新绝",但是"不备诗家之资格"。四、黄、夏、谭等"诸家"都是"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他们诗中的"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这无异宣告:不仅按照千余年来鹦鹉名士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殆将绝",就是按照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诗歌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同样"殆将绝"。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的诗歌当作"诗界革命"看待,所以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微也,夫诗又其小焉老也。"明确说明他上面所举的夏、谭、黄等"诸家"的作品都是诗界"革命军"的"月晕础润",而非革命军本身。(成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表示风雨将临的征兆,而非风雨本身。)
所谓"精神思想",即"欧洲真精神真思想"。由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言论上大力传播西方"自由"、"平权"、"独立"等资产阶级学说,这种传播促进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发展。因此他提出"诗界革命",要求诗歌在"革命之机渐熟"的时候,以"欧洲真精神真思想"为"诗料",开辟诗的新境界,实际上要求诗歌起到反映,推动革命思潮的作用。
梁启超又指出,夏、谭等"诸家"的新诗之所以不符合"诗界革命"的标准,是因为中国的"学界"尚未革命。所谓:"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换言之,只有学界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之后,"诗界革命"才能产生。因此,"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固然表示了进行这一运动的必要性,而从他"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以及预言诗界哥仑布、玛赛郎"出世必不远矣"这些话来看,实际上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还处于有待开展的"倡议"阶段。
附带指出,梁启超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后,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如力山遁庵《宿园先生属题选诗图》云:"骚坛近出哥仑坡(原注:"谓任甫师"),创为新诗觅新地。"34又如聘庵《赠別复庵》云:"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35所谓"自由篇",指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这些诗在鼓吹"诗界革命"时,都把梁启超作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而加以颂扬。另外,如邱逢甲《论诗次铁庐韵》之二有"迩来诗界唱革命"之句36。又如林辂存在写给潘飞声的诗中有"廿纪龙螭战斗纷,……诗界新编革命军"等句⑩。邱诗作于辛丑、壬寅(一九一、一九二年)间。林诗作于"廿纪",至少在一九年之后。他们诗中的"迩来"、"新编"等语,与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诗界革命"在时间上也相符。而梁启超本人在澳洲作《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一诗,其中有"我昔倡议诗界当革命,狂论颇颔作者颐"38等句。前句当指他二年前提倡"诗界革命"一事,后句指口号提出后得到响应的情况。
既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回头再看《诗话》中谈到夏、谭的语句,实在是梁启超站在"诗界革命"倡导者的立场上,对夏、谭"新诗"的批评,胡适等人据此认为夏、谭提倡"诗界革命"是错误的。所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也不是象一般误解的那样,似乎梁启超已把夏、谭的新诗称为"革命",而是针对梁自己在此前《汗漫录》中提出"诗界革命"使用"新名词"的主张。这一则诗话否定了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转变。关于这一点,当另作文说明之。
这些错误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缺乏根据的。由于不清楚"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有些人就把这一特殊的概念当成一个泛指的概念,将黄遵宪早年提倡"新派诗"和"诗界革命"混为一谈。实际上梁启超最初倡议这一运动时,以欧洲的思想学说为核心,而黄遵宪的"新派诗"与梁启超主张的内律有很大区别,这在上文分析《汗漫录》时巳经谈到。总之,黄遵宪不仅没创造"诗界革命"一词,而且他从未使用这一词。尽管他后来加入这一运动,并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对"诗界革命"这口号本身仍持保守态度。因此黄遵宪也个是"诗界革命"的提倡者。
综上所述,似可得到如下的结论:时下流行的关于"诗界革命"是由夏曾佑、谭嗣同或黄遵宪在戊戌前提出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根据目前所得材料,"诗界革命"是由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 注 释
①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康有为诗文选》、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等。
②见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多学史稿》、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
③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 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 ⑤麦若鹏《黄遵宪传》。
⑥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
⑦载于《新民丛报》第十号(壬寅五月)中《诗界潮音集》,题为《感事》,题下注云:"庚子旧作。"又载于麦孟华《蜕庵集》,题为《庚子感事》。
⑧见简夷之校点《饮冰室诗话·校点后记》。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⑩文中所引夏、谭之诗,与其它材料相参稽,和事实有出入,乃梁启超作此文:时误记之故。所谓夏"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今检《夏别士先生诗稿》(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有《赠梁卓如》三首,编于《丙申一日试笔》之后,知三诗为丙由春所作。其一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民皇终如归麟笔,天鬼婵嫣看染丝。西婉烟埃弥八表,欲将生死向天师。"(《抄本》后四句又作:"民皇大备三重运,人鬼同谋百姓知。且倒金樽谋遁世,天渊进退未因时。"《清议报》四句作"民皇备矣三重信,人鬼同谋百姓知。天且不违何况物,望先万物出于机。")其二云:"淫淫雾雨晓云寒,sx走单sx走单春秋揽镜看。百姓容容无所倚,九卿碌碌奉其官。天门虎豹当关戏,昔梦熊罢广乐阑。相煦波臣升斗水,可能容易劝加餐。"其三云:"江水湛湛枫树林,风弦袅袅女环琴。懵昭冥暗成千古,茅靡波流见素心。盍视吾良秋柏实,化为?草洞庭深。多情一撮神州土,贤劫来时何处寻。"梁文所引夏诗在上诗第三首。而粱所云"四首律诗"中另一首,在《夏别士先生诗稿》中题为《沪上赠梁卓如》,诗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蛇起陆,羔方婚礼鬼盈车,南朝丈酒韬乾战,西婉山川失宝书.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清议报》作;"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当起陆.轨非乾战且悬车。,东岱大微不可舒。公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梁启超于丙申三月出京师,赴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同办《时务报》,此诗当作于丙申三月后梁在沪之时。此诗与上面《赠梁卓如》三首中第一首同载于《清议报》第一百册.题为《赠任公二首》,署名"碎佛",题下注云:"丙申夏。"此二首又见于《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与夏曾佑并无往来,观《清议报》载《赠任公二首》,诗中字句与《夏别士先生诗稿》颇多歧异,故此二诗似粱凭记忆录出,题下注"丙申夏"。亦系粱凭记忆之语。今知一首作于丙申春,另一首作于丙申夏。
梁文所引谭嗣同"和作",见于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题为《似曾诗》,共律诗四首,梁文所引诗句属其中第二、三首。据《新民丛报》第四号《诗话》云:"余所见(谭嗣同诗)惟题麦孺博扇有《感旧》四首之三。"即《似曾诗》中三首,梁文所引为此三首中第一、二首。《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为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之作,《(似曾诗》作于丙申之后.据此可推知谭于丁酉年自金陵来沪时将其中三首题于麦孟华扇上。然观其诗题内容,似非和夏之作。据《诗话》语意,梁在麦孟华扇上首次见到此数诗,且云:"其言沈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若此数诗果为"和作",梁当知道,在《诗话》中似不当作此语。另据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赠梁卓如四首》,与夏诗内容及诗题俱相似。其一云:"大成大辟大雄氏,据乱升平及太平。五始当王讫麟获,三言不识乃鸡鸣。人天帝网光中见,来去云孙脚下行。漫共龙蛙争寸土.从知教主亚洲生。"《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云;"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夏诗《沪上赠梁卓如》中有"兽魄蛙魂龙所徒"之句,夏、谭诗中皆有"龙蛙"语,显属同类之诗,又梁启超《汗漫录》及《诗话》中皆将此二诗并提。由此可知,所谓谭之"和诗",实为此《赠梁卓如四首》。梁由于误记,将《似曾诗》当作"和诗"。 谭嗣同《赠梁卓如四首》似非在丙申春与夏曾佑唱和之作,而为其后来模仿夏诗之"和作"。理由是:一、夏诗有"龙蛙"语一首作于丙申夏,而谭诗第一首亦有"龙蛙"语,梁文云谭"和"夏诗,是必作于夏诗之后,故谭诗当亦作于丙申夏之后。二、《谭嗣同全集》载丁酉二月初七日《致汪康年、梁启超书》,中有"大致卓公似贾谊"之语,乃指《时务报》中梁之文章而言。此谭诗第四首有"少年今见贾长沙"之句,故此诗当作于丙申七月《时务报》刊出梁文之后。三、《诗话》云:"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据其语意,在"提倡"与"綦嗜"之间,前后似有一段间歇。总之,谭之四诗不似丙申春在京和夏之作,较可能的是,谭于丙申秋八月在上海与梁启超相见,因见夏曾佑于丙申夏赠梁之诗,遂有此依题模仿之"和作"。(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于一八九六年丙申条云:"八月到上海一行,十九日和梁启超、宋恕孙宝煊、吴嘉瑞、夏曾佑、胡惟志(仲巽)共摄一像。"其中将汪康年(穰卿)误作夏曾佑(穗卿)。《年谱》所据孙宝煊《日益斋日记》,或有误抄。今据《清代日记汇抄>所辑孙宝煊《忘山庐日记》,知为穰卿。 )
梁文又云他当时亦有"和作",然已忘却.然据梁启超《汗漫录》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记有一首云:'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按作于已亥,文中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则当在丁酉。观梁启超集中它处亦百"前年"一词,然与实际年份不合者.故不能据此以为谭、夏之诗皆作于丁酉。然而此类之诗实作于丙申、丁酉年间。非作于一时一地,故梁以"前年"约略言之。梁又云:"辄欲效之",意谓其见夏、谭之诗后,即欲模仿之,在"欲"与"作"之间,当有一段间歇。故梁诗似亦非丙申春在京中与夏、谭一起时相互唱和之作,而是后来见夏、谭诗后之"和作"。此诗与谭诗第四首同韵,抑为丙申八月见谭诗盾所作?11《夏别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出都别青来》(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作《丙申三月将改官出部和青来前辈》)一诗,其二云:"连天芳蓖送征轮,未免低回去国身。八百余年王会地.垂阳无语为谁春?"即为夏曾佑当时所作一般不难解的旧诗。其它尚有《白下寄内》、《抵郡》等,皆为此类诗。
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丁酉金陵杂诗》,其一云:"吴淞半江水,湘中一尺天.年来都翦得,持八秣陵烟。"另有《江行感旧诗》、《改官江苏诗》等,皆为无新语句之诗。
12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及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
13《新民丛报》第十七号。
14 26 28《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
15参见刘望龄《一八九六--一九六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补正》,载于《辛亥革命论文集》(一九八年十一月广东版)。
1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17《时务报》第四十册。
18《时务报》第四十一册。
19《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20关于梁启超等丁酉年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之内容,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又云:"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曰曰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没《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
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梁启超又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中云:"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又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云:"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不久,多患发热病,其所评学生文卷,辞意未甚偏激,不过有开议会等说而巳。惟随来助教韩君之评语,颇涉民族革命之意。"(《寒柳堂集》)又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云:"诸生人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旧派与学生初无恶感,亦无异言。及遇假期,诸生多数归省,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旧派哗然,大肆讥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二辑)以上所引文字,皆作于革命成功之后,故习以"革命"一词概括梁启超等人当时讲学内容之性质,并非他们在讲学或札记批语中直接出现"革命"一词。正如我们现在习称孙中山成立兴中会为"革命"举动,并称其宣言为"革命钢领",实际当时尚未采用"革命"一词。今观当时学堂札记批语残文中无"革命"语,且苏舆《翼教丛编》、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及戊戌、己亥间有关"上谕",皆言及梁等之"罪状",其最甚者为"民权"、"平等",若梁等宣传"革命",必无不列为罪状之理。
21《时务报》第十九册。
22《夏別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己亥年作《七里泷》一诗,中有"天心弃支那,民政不见容。归来钓大泽,遁世全其躬"等语,盖叹戊戌变法之失败也。
23夏曾佑与梁启超等论学甚契,然不属康党。夏元瑮撰《夏曾佑传略》云:"癸已、甲午之际,言新学者渐起。自南海康有为师徒出,而公羊学风行。新会梁启超、麦孺博诸子,常就先生言公羊。先生时服官礼部,有拟之为刘申受、龚自珍者,而先生不以公羊学家自居。"(《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所谓夏"不以公羊学家自居"者,抑欲与康党保持距离之故欤?故梁启超云:"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亡友夏穗卿先生》)戊戌政变后,夏未受谴。庚子后,选授安徽祁门县知县。后来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夏随赴日本,努力为清廷实行立宪政治。
24参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所载《东海公来简》。
25见Calton J·H·Hayes,ParKer Thomas Moon,John W·W- ayland撰《World History》(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1946)。
27《清议报》第九册。
29见《清议报》第十九、二十册所载《论支那宗教改革》。
30 33见《清议报》第三十六至三十八册所载《汗漫录》。
31见《新小说》第一号所载《沦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32《清议报》第一册。
34 见《清议报》第五十一册。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知作者为秦鼎彝。
35 《清议报》第九十册。
36 见邱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八,属辛丑、壬寅稿。37 见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二。
生命之诗范文第4篇
一、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中学生正处在身心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绝大部分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也有一小部分可能会或已经出现一些极端问题:有的学生过分欣赏自我和苛求社会,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有的学生心理失衡,把社会理想化,对自己缺乏信心。在学习生活中,他们或标新立异,或萎靡不振,不思进取;或认为自己不需学习就能得到好的前途。因此,对他们进行生命教育很有必要。生命教育目的就是要让中学生体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形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善待生命的生命意识。这样,我们的学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生挫折,都会活得有气节,有尊严,有价值,都不会轻易放弃或浪费、残害生命;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都能够享受到自己生命的乐趣――这就是生命教育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可以说,生命教育已成为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
二、利用中学古典诗歌教学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
古典诗歌在中华文化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今天提倡素质教育的新环境里,诗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从某一方面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告诉了我们怎样认识生命、面对生命。可以说,古典诗歌是社会人生经验的浓缩,是人类生命意识的结晶,是可以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的。教师恰当的利用古典诗歌,可以塑造青年学子美好的心灵及健全的人格,让学生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让学生的生命放射出应有的光彩。因此,古典诗歌具有重要的生命教育的价值和优势。
利用古典诗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学生的生命里有崇高。爱国精神是人类精神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精神,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诗人,他的诗歌所反映的正是诗人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担忧,这些诗就成为一首首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当我们读到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就会感受到诗人对官军收复失地的兴奋之情;当我们读到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就会感受到他对壮年英雄气概的回味。我们从陆游的诗里读出了壮志未酬,从文天祥诗里读出了忠肝义胆,从林则徐诗里里读出了执著,从谭嗣同的诗里读出了义薄云天……这些都集中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国家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挺身而出,奏响了一曲曲壮丽而豪迈的人生之歌。青少年学生通过学习爱国诗篇培养了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懂得爱国的学生,也必然懂得什么是崇高――崇高即以一颗赤子之心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奉献自己应有的忠心和力量。而崇高的生命是值得拥有的。
利用诗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力,让学生的生命充满浪漫。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雪融化了是水,雪融化了也可以是春天,诗歌教育就是要发挥想象力,让学生在超越常规中看到春天的希望,并且在欣赏诗歌过程中,培养学生纯正的审美价值取向。如学白诗,可以感受“燕山雪花大如席”“飞流直下三千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奇特想象;欣赏杜甫的诗,也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夸张,齐鲁大地春回大地、一碧千里的广阔景象,令人向往。沿着历代诗人的足迹我们可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可以“长风破浪”,还可以听到“羲和敲日玻璃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通过学习古典诗歌,可以使刚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增强求知欲和好奇心,用想象插上腾飞的翅膀,在诗歌的海洋中去探珠觅宝。这样,青春的生命不再沉闷,学生拥有了想象力和审美力,就有了发现美的能力,也就有了别样的浪漫。在诗歌的审美中度过青春年华,就是一种浪漫的人生。浪漫的生命也是值得拥有的。
利用诗歌培养学生的健全的人格,让学生拥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每一首古典诗歌,都代表着诗人的一段人生历程;每一首古典诗歌,都是诗人生命的一种诉说,是诗人生命体验的凝结和升华。读一首首古典诗歌,就像和一位位朋友做知心的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苦乐哀愁。读李白的《蜀道难》,我们知道了李白对朋友安危的牵挂,也知道了李白“谪仙人”的才华;读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我们知道了李白是多么的自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读李白的《行路难》,知道李白始终不放弃理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知道了他的铮铮傲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读李白的其他诗篇,可以感受到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从李白的诗中,我可以知道一个人可以这么有才华,有傲骨,有理想,有真情,有潇洒,有失意,有得意……真是令人敬仰。同样,读杜甫的诗,也能了解他独特的人生,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而读一千个诗人的作品,就是了解一千种人生。一千种人生必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促使他们人格的完善,积极追求合理的人生,珍爱生命,让生命更加完美。
三、诗教离不开审美教育
生命之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彭燕郊;《混沌初开》;象征结构;“全光之境”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七月派”老诗人彭燕郊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对读者来说,不仅他在70年的创作生涯中长盛不衰的艺术创造力是一个奇迹,也不仅他在64岁这样的高龄实行“衰年变法”是一个奇迹,而且他本人的生命经历在现代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无异于一个奇迹。建国前从新四军战士到左翼文化工作者,建国后从大学教授到被指控为“胡风分子”,在20多年的政治劫难中,彭燕郊先后当过木工、翻砂副工和油漆工,到晚年仍以赤子之心拥抱缪斯女神,成为当代先锋诗歌艺术的杰出代表。这种人生的变化轨迹正如评论家龚旭东先生所说的,是“一朵充满奇迹的火焰,一块晶莹剔透的结晶体,一个平凡的圣迹”。但发生在彭燕郊身上最大的奇迹,也许是他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所提供的一系列不同凡响的杰作和对于纯正的诗歌精神始终执着不移的坚守,尤其是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艺术试验,对于推动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混沌初开》在彭燕郊的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是其诗歌艺术探索的集大成之作。这是一部真正能把读者的灵魂托举到崇高境界的作品,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平凡而渺小的个体,在不自觉地变得丰满和强大起来,会感到自己的灵魂在极度的痛苦和欢乐中,随着诗意的展开而蜕变和更新,在“无涯际的空旷”中,“随心所欲地从中找到最能激发生命特质形成的日月精华”,在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作用下生长成一个“新我”。这是一部大悲悯、大悲哀的作品,同时是一部大欢乐、大解脱的作品。诗人在作品中的声音完全发自其灵魂的深处,却不仅仅是属于诗人个人的,诗人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洞察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以充满诗意和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混沌”图像指向人类普遍渴求的理想生命形式,探索人类的精神超越之路。
一、“你”与“我”:对话与对话的互生互动模式
作为一部气象开阔、境界深邃的长诗杰作,《混沌初开》一开篇就迸发出一种蒸腾性的力量,显示出超卓的想象力。在无涯际的空旷中,诗中的“你”似乎是横空而来的,与浩渺悠远的时空背景形成巨大的对照性落差,给人一种强烈的晕眩感。“你已置身在混沌中,混沌主宰一切。混沌不是幻觉,混沌比幻觉更美。”诗人以一种饱满的诗性精神,以一种直接乃至显得峻急的诗性方式切入作品所展开的精神背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比幻觉更美,主宰一切的“混沌之境”。读者在读到这个开篇的时候,最深切的感受也许是在无涯际的空旷中裸露自己的快意,并在这种快意中向自己的精神世界彻底打开,敞开内心的幽暗与隐秘,一种膨胀性的力量会使读者产生无限地接近混沌之核心的渴望,扑面而来的是刚健、博大,充溢着神性与雄性的混沌之美。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我们处身其中的世俗世界,也不是平常的幻觉,而是一个具有超验性的精神世界。这部长诗的基调正是建立在对这个超验世界的诗性追寻上,诗人把自身灵魂的痛苦和绝叫与人类的普遍命运联结起来,在对人类精神形式的高度概括中,显示出一种把握人类精神危机的深刻洞见与对于化解人性异化的深邃理解。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部旨在拷问人类的生存状况,解除人类精神痛苦的作品。
作为第二人称在长诗中出现的“你”,不仅具有贯串全诗,统领全诗布局的结构性意义,而且是读者进入诗歌,揭开全诗深层意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从表面上看,“你”是一个身份未明者,“你”何所来而来,何所去而去,这对读者起始是一个谜团。但随着诗意的展开和读者阅读的深入,“你”的面目隐隐地变得清晰起来,由一个“混沌之境”的神秘过客逐步还原为一个对生命本体的神圣叩问者形象,就此而言,似乎有类于屈子笔下上下求索的天问者形象。然而,“你”在全诗中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你’是谁”对读者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这恰恰见出诗人彭燕郊的独到用心所在。在笔者看来,“你”是一个多重指称的复合体,是“类”与“个”的统一体,包含着诗人对“一”与“多”、人类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从中传达出丰富的哲学信息。“你”不仅仅是“你”,还是“我”和“他”,从“你”的身上,折射出人类普遍的精神悲剧,同时,“你”对“混沌之境”的神往也折射出人类对摆脱精神痛苦的普遍渴望。因此,“你”在诗中作为一个饱满的诗性形象的确立,联结着诗人对于人类基本问题的思考,具有多维的象征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你”既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诗性形象,同时也显示出诗人自身个性化的精神特征。在诗中,显然有一个潜在的对话者“我”,这个“我”无处不在,却又无迹无形,是一个隐匿的诗性形象。这个“我”主要是一个发问者,一个隐匿的观察者,时刻不动声色地审视着“你”,乃至成为诗中一种弥漫性的氛围。同时,这个“我”是对“你”的补充,与“你”互为一体。在这部长诗的内在张力结构和象征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你”与“我”对诘与对话的互生互动模式。正是通过“你”与“我”之间的潜在对话,才促使“你”成为一个行动者和反思者,成为一个意义丰满的诗性形象。在“你”的身上,可以发现诗人对知识分子传统人格的修正,“你”在混沌中对自身的超越与提升,符合诗人对知识分子改塑传统人格模式的深切期望。如果没有这个“我”的存在,或者说,如果这个“我”在诗中是一个真正的缺席者,那么,诗中各种诗性形象的建构不仅没有存在的现实依据,而且缺乏化为行动的思想推动力和理性精神。因此,“我”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在诗中不仅是一个结构性的观察视角,而且是一个功能性的行动主体。
那么,如何理解诗人自己与“我”的关系,进一步理解诗人与“你”的关系,这对于理解这部长诗的深层意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混沌初开》所展开的精神背景中,流露出作者强烈的身世感,诗人在诗中的自我形象几乎是弥漫性的,是无处不在的。诗人的自我形象就是通过这个隐匿的“我”表现出来的,“我”代表诗人的内在精神诉求。同时,诗人的自我形象又与“你”处在一个对照性的结构中,诗人作为一个“他”者,与“你”有着深层的精神联系,实际上与“你”和“我”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精神复合体,因此,诗中强烈的身世感既是诗人自己的,又是“你”和“我”共有的,是属于人类全体的。在这一意义上说,《混沌初开》是诗人彭燕郊的精神自传,同时也是一幅对人类的精神画像。诗中有一句深沉的感叹:“你,属于人类,你却不了解‘人’,却不了解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你”的困惑,同时是诗人自己的困惑。这种真实的困惑无法掩饰,这是“你”的内心之痛,也是诗人的内心之痛。尽管在混沌之境“你将得到快乐”,但“你”必须跨越精神的炼狱,融入“全光”之中。固然不能把诗人与“你”简单地等同起来,把“你”视为诗人的化身,“你”作为已经摆脱世俗世界羁绊的诗性形象,具有理想化的形态,而诗人的超越之路才刚刚开始,但两者的精神取向却是共通的。因此,诗人才有这样的感叹:“你啊,你在无穷无尽里,在没有章法没有主旨里,反刍你短短几十年的莽撞冒失。这里没有永久和无限可以追求,这里就是永久和无限,这里没有灵魂和肉体的欢乐,只有永远和无限无意中培育你永远和无限的淡泊。”这里的身世感显然是诗人自己的,却又比诗人自己的身世感更博大和深沉,联结着诗人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同时辐射到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和文化困境之中。因此,“你”在长诗中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一种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和充满创造活力的诗性精神的确立,而且是一种直抵灵魂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的确立,“你” “在混沌中回归本真”的超越之路具有广泛的人类意义。
二、“第二我”与“非我”:美本体的化身和精神参照物的确立
在长诗中,“你”是一个不断推进和衍生的精神实体,“第二我”既是“你”的衍生体和精神参照物,同时又与“你”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精神实体中的互生互动结构和对照模式。像“你”一样,“第二我”的身份同样是模糊而暧昧的,在长诗中是通过象征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暗示出来的。一方面,“第二我”是在诗人的想象中出现的诗性形象,“你”与“第二我”的相遇和融合是诗人内部的精神事件,“第二我”是诗人在灵魂的历险过程中升华自我的引领者和对照物;另一方面,“第二我”又是一个存在于诗人想象之外的精神实存体。在诗人看来,在生命个体的精神结构中,自我的确立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确立,“第二我”是自我确立的依存物和互生物,同时是自我确立的内在动力机制和高级形态,同样具有本体论意义。根据长诗隐含的提示,“第二我”不是“我”,而是“分裂出去的‘我’,用‘我’的模式翻造出来的‘我”’,因此,可以“用‘我’想象第二我”,但“第二我”并不是“我”的转化形式,也不是“形象的巧合”,两者之间尽管有着极为隐秘的对应关系,却被诗人笼罩在一层神秘的光晕里而难以捉摸。在长诗中,“第二我”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诗性形象的确立,而是作为一个精神参照物的确立。在与“第二我”的对照中,“你”超越自身的局限逐步变得丰富起来,在创造的激情中提升灵魂的高度,反思“生活在规律之中”的盲目生命方式,并且在“第二我”的引领下去“面临一次新的奇遇”。在诗人彭燕郊那里,“你”与“第二我”之间的对话与对诘包含着丰富的对于人生本质意义的困惑与追问,“第二我”对“你”的质疑与诘问似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优势,“第二我”的发问几乎是天启式的:“那么你是怎样维护生命的创造原则的?”这正是生命的全部症结所在,也是当代精神困境的核心问题所在,使“你”在答非所问的难堪中豁然醒悟。这显然暗示着诗人的某种价值取向,“第二我”在这里是作为美本体的化身出现的,诗人一再强调“第二我”的美和美的超越性力量:“第二我不是魔鬼,但有魔鬼的美。……第二我却能以气流为跳板,向无涯际以上的无涯际跳跃,向翻滚旋转翻滚旋转。”从中可以发现,在彭燕郊的诗学观念中,美包含着对于庸俗的反抗,是诗人情感和意志力的诗性表现,而且美是运动的圆满形式,在静止中则归于寂灭和虚无。“第二我的美,你第一次看到的美,你的眼睛映现的第一次惊奇。人类应该具有的美的可能。”在诗人看来,美具有一种勃发的力量,具有创造进化的功能,是精神升华的内在动力,同时美又令人惊奇,并在惊奇中塑造人性的健全和丰富。诗人拥抱美的热切与灵魂的内在要求完全一致,他寄希望于通过美的塑造来作为化解当代精神问题的有效途径,另一面却表明诗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第二我”对“你”没有完成的诘问,在“非我”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非我”不是“第二我”,也不是“第二我”的延伸,“它好像是生命无意识的化身”,“是从第二我的消失中凸现的可触摸的幻影”,具有“多向度的单纯,多向度的丰满”。“非我”具有强烈的否定性内涵,在长诗中是以否定性的形式出现的,以对“旧我”的否定作为超越的起点。这是一个“历史中间物”概念,不但代表一种自我否定的身份转换,而且代表一个向死而生的新生过程,因此,“非我”是终结性的,同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是“旧我”的消解和“新我”的生成。“非我”在长诗中的出现同样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是“一场冒险的结果”和“混沌初开”的预兆,预示着“全光”的临照和“新的你”的确立,长诗的整体氛围在这里开始呈现出进入澄明之境的迹象。长诗对“非我”这一诗性形象的确立也是与“你”叠加在一起的,“你”与“非我”形成一个精神互生体。“非我”行踪无定,无法触摸,“你想看见它的时候看不见,它总是意外地出现在你面前,你很少看到它。你在想:能够和它有个默契就好。你想念它那像你自己说出的话的回音一般的语言。那声调像你自己的心跳一样沉着、清脆。”因此,尽管“非我”具有不确定的性质,却不是虚无的幻觉或幻象,而是一个奇异的精神实体,与“你”相生相成,合二为一,在“肉体的崇高的本真”和“心灵的悲壮的本真”的有机结合中,最后融入“全光”的混沌之中。在诗人那里,“非我”的内在规定性指向灵魂的召唤和命令,“非我”传递神秘的宇宙信息,具有一种奇异的提升力量,使“你”“不由自主地加入混沌,加入这狂热的自我搅拌”,从而复归生命和人性的本真形式。“你”与“非我”从相遇到融为一体的过程,对“你”是一个蜕变自新的过程,“你”终于从“可怕的可悲的自怜自保综合症”中解放出来,剥开浑身包裹的“一层又一层人造皮革”,在灵魂的犀利解剖和严肃拷问中,逐步升华为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之“我”。就此而言,“非我”不仅是对“你”的否定和提升,也是对“第二我”的否定和提升,是更高一级的生命形式,是诗人生命理想的诗化表现。在生命形式的这一转换过程中,诗人灵魂的自审与自新伴随着刻骨的创痛,在长诗中表现出来,就转化为悠长的叹息和叹息中的亢进之音。尽管长诗深处的悲凉和沉痛是极度抑制的,却仍然是蒸腾性的,弥漫为从容淡定的忧郁,另一面却展现为生命的乐观图景和对于“全光”境界的热切期望。
三、“全光”与“混沌”:全新的本体开发方式
长诗在最后的欢乐颂中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混沌初开,一瞬间无涯际落入全光,翻滚旋转卷入全光。”“全光”是大融合、大欢乐、大解脱的境界,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生命圣境。对“你”来说,“全光”的临照是灵魂救赎之所和重造之地,“你”在“全光”中“经历着最严格的生命检验”,“得到光辉的洗礼”而蜕变自新为“新的你”。“非我”也在“全光”中像着魔一般“再次出现”,元气淋漓,“还是那么闪闪的通亮的幻象”,它“只管向前,向前,到处都有它的踪迹,全光急急忙忙于吞食它的踪迹”,因此,像“你”一样,“非我”也“在全光中一点不剩地溶化”,最后化为“全光的一部分”。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一头栽进全光的混沌里,乐呵呵地,只管闪闪,只管发光”,在“这混沌的全光,全光的混沌”中,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生命由此在彻底的超越中进入大澄明、大宁静、大通达的境界。在诗人那里,“全光”作为生命蜕变自新的最高形式,是对理想生命形式充分敞开的诗性建构,成为诗人笔下的载“大道”之物,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哲理内核。
“全光”在长诗中的出现是灵魂探险的“高峰体验”,是“混沌初开”的理想状态和充分诗化的形式,寄托着诗人重造灵魂的生命理想。“你”从“混沌”到“全光”的灵魂历险,是“一种全新的本体开发方式”,“作为参与光”,“你”在“全光”中是“慢慢地适应的”,并且成为“一个光信号系统”:“在绝对清醒的梦里,你已经纯净,没有一丝多余的杂质,没有一丝皱折。每一朵光都可以透过你望见另一朵光。你敢于相信自己也是光源,你赖以生存的光里有你自己发出的光。”长诗“混沌初开”的主题指向在“全光”中得到充分的展开,最后归结为“全光”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普遍化解和灵魂的全面救赎:“你相信光,你得到光,你发光了。”在“全光”的临照中,“你将再次超越你自己”,这不仅是诗人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更是诗人对人类发展前景信心的确立。
在长诗中,“混沌”是贯串始终的总体意象,是宇宙开犹未开的初始状态,“混沌覆盖一切,混沌包容一切”,同时“无轻,无重”,是“无色、无形、无声的纯净”,是“全感觉的时空本体”。诗人心事浩茫,上下求索,在他的诗性想象中,“混沌”转化为精神世界的“客观对应物”,其象征意义指向理想生命形式的诗性建构。就此而言,“混沌”是诗人对生命深刻觉悟的内心产物,是由诗人灵魂探险转化而来的“心象”。另一方面,“混沌”又与“全光”同为一物,是“全光”的初级形式。“全光”是宇宙终极状态的诗性形式,是生命创造进化的理想状态,在艺术上则是一种天启般的独创性境界。由“混沌”到“全光”的超越历程,不仅是诗人灵魂的涅槃自新,是“新我”的诞生,同时象征着人类精神困境的化解和救赎。在长诗中,“混沌”与“全光”都是宏大和崇高之物,都具有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的性质,是“大无”“大有”之物,是宇宙中载“大道”之物的诗性化身。在“全光”中,时空具有全新的性质,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理想图景和灵魂自新的超越境界,“全光的创造者中有微小的你在内,全光中有你微小的位置”,“你”在涅槃自新中成为“新的你”,向更高的生命境界创造进化,生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创造进化之中。
四、神性本体的象征构架与诗性呈现
《混沌初开》是一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作品,诗歌的主题意向指向至深、至远的“全光之境”,诗人对于人类精神形式的把握显示出一种深刻的洞见和深沉的悲悯。在诗人那里,生命的本体即是“混沌”,生命之美即是“混沌之美”和“全光之境”,生命的诗性建构即在于恢复生命的神性本质和内在价值。“全光”指向一种至高、至远、至善、至美的神性本体,“全光之境”是理想之境,是理想生命形式的依存之境。诗人以一种极具个性化的审美方式,通过对“全光之境”的诗意建构,试图寻求解除人类精神困境的途径,如此高远的立意也许不无乌托邦的玄幻色彩,但却是从诗人的全部生命体验转化而来的,代表诗人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性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