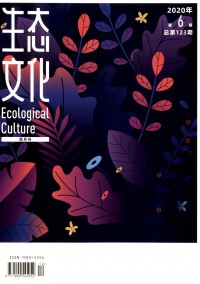生态文明下的资本主义研究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寻“生产性正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除了传统的导致经济危机的社会基本矛盾以外,更关注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力)和生产条件的矛盾,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性正义”,强调生产活动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公共条件上获得正当合理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以期生态和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一轮科技革命———生命科学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从线性经济、高能耗经济向循环经济、节能经济的转变,使得原本存在制度根源的资本主义社会正义获得了全新的生态学意义———“所谓正义社会这个概念也已将其关注视线从定量方面转向定性方面了,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了。”据统计,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由于实现了资源投入量的源头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呈明显下降趋势。由表1可知,单位GDP能耗是一国能源利用效率指标,而目前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主体。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内资源、环境基础之上对“生产性正义”的探索。
二“、后物质主义”和“红绿”思潮深刻影响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1.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发生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原则于20世纪80年代后流行欧美国家,是对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检讨和合理替代———从工业社会热衷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忽视精神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唯物质主义,转向对生态环境、生活质量、人权和公民自由等非物质价值的关注。除此之外,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自治市镇主义)、包容性民主理论等被称为“红绿”(绿色左翼)思潮与“深绿”的生态无政府主义、“浅绿”的生态资本主义一并使这种价值分层和变迁更加丰富和复杂,而在“新社会运动”中兴起的社群主义和社区自治理念也不断挑战传统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2.理性消费观对传统消费观的超越。长期以来,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规律的驱使,生产的无限扩张性和有产阶级对地位和权力的追崇培育了资本主义国家奢侈型、炫耀性和超前消费的方式和观念,“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异化消费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内在矛盾之一,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普及和深入,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的“绿化”,正在被逐渐解构:一是崇尚“低碳”。后工业时达的社会生产力使得物质满足的边际效益递减,人们普遍接受了“增加消费并不会使人们更幸福”“钱是自己的,但资源是社会的”这样的价值判断:欧洲民众开始践行后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崇尚“简单的饮食”和“朴素低碳着装”,酒店宾馆的管理逐渐告别“一次性”时代,出行“零排放”———北欧国家元首自行车上下班已成为风尚。二是抵制奢侈。生活在“质”上的增长是后物质主义的基本特征,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人们的等级观念日益淡漠,一种建立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基础上的质朴消费观、本色生活潮流兴起。官、学、民住宅设计的简朴化和建筑空间资源最优化,政府对奢侈型消费征收高额消费税等,变革获得了自上而下的形式。三是倡导“慢活”。对于片面追求效益而过劳破坏人的身体健康,使人与人的疏离感增加,心理健康和幸福指数下降,离婚率自杀率激增等现象,西方民众有着深刻的反思。意大利、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开始推行“慢活”活动,放慢生活节奏,享受生活和自然。这种重视休息和精神消费的观念变化甚至为缓解劳资矛盾提供了有效出口,如法国人“休假第一,工作第二”的工作准则更促成了法定劳动时间从1982年的每周39小时缩短至2000年的35小时。
3.对社会制度选择的重新考量。后物质主义和“红绿”思潮最具时代特点的衍生物,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生的制度变革要求。一些理论流派在生态经济学家、学者对资本主义利用新能源、回收利用极限、环保技术创新和经济可持续性解决环境破坏和全球性贫困等主流观点上不抱幻想,承认和确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资本主义的生态和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体系内无法调和的根本性矛盾”,持这些观点的理论流派和党派正在迫切渴望一种替代性的选择。2009年BBC在柏林墙倒塌20年之际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全球27个国家2.9万人的意见中,半数以上被调查者不满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反,社会主义思想愈来愈受欢迎。
三、绿色政治促进了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从政治学角度看,绿色政治除了上述绿色思潮以外还包括绿色运动和绿党运作。绿色运动首先是指19世纪后半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环境保护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末演进为“新社会运动”;而绿党是在该运动基础之上,绿色运动团体借助现存政治手段特别是议会制民主以实现自己理论信念与运动目标的政党化努力。
1“.新社会运动”赋予工人运动新的特点。绿色运动在内涵和形式上的扩展,演变具有实践和理论形态的“新社会运动”。由此产生的“新中间阶层”演变了传统工人阶级,体现为工人的白领化、多领化(从事环境卫生的绿领、高级管理层的金领、维修与营销人员的灰领和大量女工的粉领)、知识化、智能化、有产化,折射出社会结构的多元变迁。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福利制度,资本家利用产业转移离间了本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加之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意识的变迁,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工人阶级本身就是材料和能源大量浪费和工业污染的直接感受者兼受害者,以环境运动为先导的“新社会运动”赋予工人运动复兴全新的文化熏陶,使之产生新的时代特点:激进工会运动和生态学的合流,在欧洲和北美被人们描述为“工联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工联主义”。这种绿色的新型工人组织有别于传统官僚化工会,寻求自下而上的组织模式,斗争运动上摒弃传统工联运动的经济主义,拒绝大规模罢工、谈判、书面合同和普遍接受的贸易自治,采用新奇策略“直接行动”、“消费者阻断”、“减少生产”,强调“工人阶级除了妥协的历史还有着激进的运动史,工人群众并非总是顺从的羔羊”,这种“红绿”运动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2.政党“绿化”重组政党格局。在西方社会传统的政治色谱中,“红”与“黑”是两种基本底色。绿党出现、传统“左”与“右”二元区分式微,各党派“同质性”价值日益增多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生态开始逐渐“绿化”和“解意识形态化”,政党格局变化。一是绿党的崛起转换了西方社会政治发展主题。绿党摆脱了传统政治议题的束缚,其“倡导的主题———环境保护、女性平等、自助、分权化———在政治议程中已经赢得非常稳固的地位”,挑战了按阶级战线和传统意识形态划线的政党格局。二是绿党的出现直接改变了政党格局。20世纪90年代起,各国绿党纷纷进入本国政府和议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德国绿党还与社会组成“红绿联盟”,成为执政党,打破了西方(以欧洲为典型)社会左右翼两大政党垄断社会政治生活的格局,被誉为“新中间力量”。另外,绿党还在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建立了地区性政党联盟或议会党团,正逐渐成为一支世界性的政治力量。三是绿党的壮大革新了传统政党的生存和运作方式。绿党因主张生态保护、反暴力、无核化和基层民主的政治诉求一直拥有稳定的选民基础,为了赢得比较优势,绿党成为左翼和右翼选举中的争取和联合对象,其参政和执政改变了政治博弈的游戏规则,促进了政治民主化、政党决策科学化和执政亲民化。
3.政府转型扩大社会自主空间。二战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历了从传统军事、政治、法律领域拓展至经济领域的第一次职能转型,但是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绿色政治”主流化的态势驱动下,政府越来越重视其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见表2)。社会化程度提高,这必然带来在某些专业领域公共权力的下放(如环境保护和治理、社区管理服务等),“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愈发明晰。在上述政府转型的语境下,“新社会运动”使政府将大量的社会公共空间释放出来,让渡给绿色NGO或法人、社区组织承接运作,呈现公共事务管理民营化。在活动范围上,由于这些团体和组织的制度化和职业化、非对抗性和建设性,如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等组织的跨国化发展和全球环境(气候变化)正义运动,其超越国内政治界限而着眼于一种国际或全球性视野,不仅为传统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思想提供了实践范本,也成为目前广泛讨论的“建立一种全球公民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推手。
四、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
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环境问题被列入国际政治议程,环境问题由于其本身的全球性、不可分类、不可量化、不易解决、高风险和长期性以及与国家核心利益的密切性现已逐渐摆脱传统外交学“低端政治”的层次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大因素,甚至有学者提出环境问题导致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观点。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举行正式拉开了“环境外交”时代的大幕。
1.国际关系行为体努力构建国际环境治理的新范式。主权国家之间发展阶段和工业化水平的不同导致的“发展和环境的优先次序”是目前阻碍全球环境问题合作的根本原因,由此出现了目前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益主体、利益阵营的不断分化重组,既有欧盟与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在“绿色壁垒”和资金技术转让问题上的矛盾与妥协,又有发展中国家诉求冲突下七十七国集团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在气候问题上的博弈,还有由于跨国环境治理引起的双边和多边、区域性国家合作,这种动态的竞争与合作有利于打破传统“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更广泛的国际对话和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全新的话语体系和行动平台。国际组织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动力,根据UIA2004—2005的调查数据,目前全球政府间国际组织约有735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51509个。“环境外交”发端以来的40年间,环境、资源、人口等已经深刻植入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议题之中,使各类国际组织的“绿化”成为一大趋势,从联合国到欧盟东盟非盟,从国际红十字会到国际奥委会,都在为环境治理的全球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的民主协商方式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2.国际环境机制发展不断促进国际关系法制化进程。国际环境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国际环境谈判而达成的多边环境条约。国际环境机制的形成和维持理论与实践,打破了传统国际制度的“霸权稳定论”,尤其是全球气候机制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得以生效的事实证明,处理某个环境问题的性质、谈判达成的科学共识、替代技术和产品成本的高低以及强有力的正面领导是国际环境机制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没有霸权国的包揽,国际环境机制依然可以运作。现有的国际环境机制的基本模式是公约—议定书,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核安全公约、京都议定书等。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签约各国可以在有具体政策分歧的情况下先行签署,签署后的进一步科学研究或执行将受到世界舆论的监督和国内环保力量的关注,从而又对态度消极的国家产生巨大压力,进而促成原机制的完善。这一过程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突破,不单为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
五、对新变化的认识
1.新变化的出现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言:“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共同规律,当代资本主义在遵循自身特殊规律的同时,也不断在这一共同规律的影响下被迫开出人类文明的“花朵”,生态文明内涵中的“新因素”所具有的正义、平等、民主、互助、人与自然的和谐,继而获得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合理性等内在价值,正是社会主义价值的本质体现,可见,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的自我调整和扬弃,也是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机体内的不断激活,“两个必然”依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新变化是有限的“环境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总体来说,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形态下的经济和社会改良运动,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主张,法国左翼思想家、哲学家安德烈•高兹对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提出异议:“‘环境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合理性的自由运作施加新的约束和限制,但是这些约束和限制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只是扩展了经济合理性的范围。”即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局限于减少现有经济文化体制对环境的影响,但由于现有的、在体制内的调整,无法解决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的矛盾,最后也会由于被资本主义所接纳而迟早要结束———保护环境成为追求更高利润的权宜之计。因此这种自我调节依然使资本主义面临着包括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重新抬头的种族战争、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核讹诈和国际性资源分配之争在内的四大危机。另外,从绿色政治的角度来看,其主体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群众运动转向政党政治,然而绿党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和走向未来的道路迄今为止仍是不明晰不现实的,整体实力较弱,对“新阶级”的利益整合也无法完成有效的社会变革,故其对在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进步上是极其有限的。
3.新变化还未能触动资本主义世界原有的秩序惯性。由于全球生态问题的出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进程正在被最广泛地推进。生态文明的初步建构、新变化的出现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再一次获得了先发制人的优势,却使谋取霸权和顺从资本意志的顽疾复发,在全球环境问题的对话和合作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在争夺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依然在利用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进行的危机转嫁和巧妙盘剥,依然将解决资源、气候、核安全等问题还原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和军事利益诉求。在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这些“生态帝国主义”延续了原有的弱肉强食的惯性,继续制造国际环境非正义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现状,生态问题的全球意义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局限性而不断打折。
作者:杨柳夏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