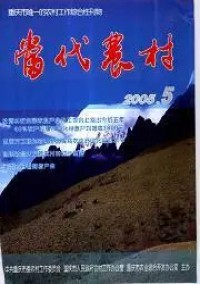农村承包制度目前弊多利少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农村承包制度目前弊多利少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形成,是不易改变的,小人物一旦得势,也会用他的思想作指导办自已的事,大人物一旦具有号召力,肯定用他的思想来决策国家大事,实现理想。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他在走城市道路失败后形成的。邓小平的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从与刘少奇开始,到江西农场的那条小路上的构思,就根深蒂固的形成了。所以,当他从第一代领导人到做第二代领导人后,他的这种思想就成了当今中国农村的国策了。
亿万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便开始自己的作业。主席是农民的儿子,同时又是大学问家,他深知农民的苦难,中国上千年的自然经济,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分散在土地上,象散沙经不起巨大的风浪,自然灾害就能使农民倾家荡产。于是他写了《组织起来》一文指导刚刚帮助共产党打江山的农民,走共同致富的“金光大道”。他说封建统治者统治农民的方法,就是将一家一户的分散在土地上,这是私有制存在的基础。不光是打仗带兵的行手专家,写出如《论持久战》等军事专着,指导人民军队解放全中国。但在种地上,他也胜人一畴。他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于是村村修水渠、打深水井、修建水库。为战胜自然灾害,做了非常牢固的设施,他信“人定胜天”,中国人“尽舜尧”。他深知刀耕火种的牛耕不是使农民摆脱贫穷与困苦的长久之计,他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于是广大农村有了东方红拖拉机代替牛耕马拉。韶山的煤油灯曾熏过他的鼻孔,在他的指引下,户户通电,村村有发电机组。农业要高产,全靠肥当家。他指出了“农业八字宪法”,指导农民科学种田。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让农民平整土地,便于机械化耕作。于是,相配套的工业也诞生了,如化肥厂、机械厂等,配合农业生产。而干部经常深入农村从事具体的生产工作,为农民主谋献策。至今,农业战线的好旗帜,河南的小刘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天津的大邱庄等仍然是他老人家创建的经济体制的榜样。
我们中国人集体失去了记忆,时代创造的辉煌,是同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周边布满了敌对势力,还要还债,后来宣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人多么自豪。可能有人提出吃不饱或发粮票布票,我们可以想想:新中国刚成立,国内需清反,又进行了对内对外战争,苏联在北陈兵百万,美国越南放枪,老蒋大叫。一边建设,一边对外捍卫领土与中国的尊严,一边勒着腰带还帐,又养活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不计划乱来行吗!那时的农民是何等的爱国,又出现了多少劳动模范。要不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创造财富,恐怕一星两弹也不好上天与巨响吧!
爱人民,所以人民才爱他。他免费为人民防治疾病,让“赤脚医生”盯着你吃防疫药、注防疫针,于是有了他的《送瘟神》诗作。他知道家畜类是农民的副业收入,同样也培养兽医下乡为农民服务。所以《东方红》响遍了全球,人民热爱他。
邓小平也是农民的儿子,他说他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他实施了包产到户制度,平整过的土地又变成了“井田”制,深水井填着了,大型机械被当废铁,水渠被扒走了,各种小型工业破产了,医疗队变成了个体营利门诊。不知有人计算过没有,自实施承包到户后,基础设施遭到多大的损失。人心现在也变了,满脑子的“私”字,毫无公的概念。农民象散沙一样,不能再组织起来。政府和农民最大最直接最唯一的关系再也不是服务了,而是赤裸裸的管理与被管理,收取税费的关系。政府官员再不为农民没法种地、抗旱、防涝、打井、修渠、吃药打针操心费神了。这些人只要往上级那跑勤点,报告写好点就足可以升迁。农村一旦遇上自然灾害,再没有抗拒的能力了。因为失去了抗衡的基础,水库的水是要掏钱买的,打井是要买单的等。
这也可能是“吃着肉,骂着娘”的原因吧?!但又反过来说:农村这种经济体制能算上一种经济制度吗?这形式能存在多久?农民就这样散沙一样,一家一户的生产着、生活下去?如果说这种形式好,那至今农业战线的好典型,为什大小报纸没见到报道一位?!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还该要不要?带着这种问题,我问过一位村级党支部书记,他说:“村支部完了!”是的怎么不完了,各管各了,东一个西一个的打工去了。那么实行承包以后的农民真的比承包前过的更好些吗?笔者引用一位网友的文章来作为说明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上连年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万元户。一时间,中国的农民好像已经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离开白际的那天,我们特地选择了从浙江那边下山,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2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至少说明,我们在安徽省农村所接触到的,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同时存在着。李昌平有关“三农”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总理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名次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进,已经创造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在注视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000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称作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朱总理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的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的决策时,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进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我们的采写工作又几乎是和这场改革同步进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一样的激动人心,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试点一样地停顿下来,作痛苦的思考,将原有的计划打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现在,当我们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故事的时候,便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知道只有平静与从容,才可能挽住我们心中曾经无数次涌动过的波澜……”这就是现状,中国农民的现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了增强政府服务职能,要从“全能型”转向“服务型”,这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上的重大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如果这种生产方式长期不变,势必与《决定》不属,也建立不起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党在农村的作用及威望会受到大大的影响,党的最基层组织也会慢慢的涣散。因此,我认为,农村承包到户的经济体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不是长治久安的大计。中国农业大国,农民最多,从出于社会治安、江山社稷考虑,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