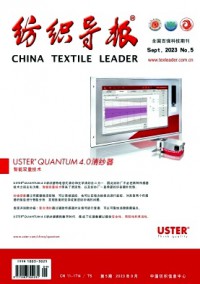纺织业的发展史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体育教师 职业化 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23-0124-02
一、体育教师职业化的理论基础
体育教师职业化,又称体育教师职业社会化,是指体育教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通过终身职业训练,依托专业组织,习得体育教育专业技能与体育教育规范,取得体育教师资格,具备专业体育教学知识及体育教学技能,表现体育职业道德,逐步提高自身体育教师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体育教师职业具有自身特有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体育教师职业化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对体育教师任职既有规定的学历标准,也有必要的体育教育知识、体育教学能力和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国家有体育教师教育的专门机构,专门教育教学内容和教育措施;国家有对体育教师资格和体育教师教育机构的认定制度和管理制度;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体育教师职业化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既是一个状态,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二、体育教师职业化的现实分析
1.体育教师职业化发展的文化环境
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师专业化素质要求, 认为教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对教师冠以“红烛”“ 春蚕”“ 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等,近乎“完人” 的神圣光环。然而,在大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体育教师职业的理解还是片面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下,体育教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是没有文化的职业的观念普遍存在,认为体育教师只能是运动者、教练、教官、指挥员的角色,还不是一个称职的、传播教育知识的、具有学术权威的理论家和教育者。
2.体育教师职业化发展的自我环境
体育教师的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是由体育教学的特殊性决定的。学校体育活动不仅仅包含了体育课堂的教学,还包含了体育课外活动、学校运动队的训练以及竞赛等。因此,体育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工作量大。体育教师只是疲于应付所担任的教学工作,这直接影响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专业化发展。许多体育教师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缺乏接受系统学习的机会,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的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教学理论以及现代信息教育技术,感到束手无策,无法深入学习,一般与教学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情境教学知识相对应的教育专业课程培训比例过小,班级管理、教育科研、教育评价、多媒体教学、教学实验等现代教师迫切需要加强的能力缺乏训练。
3.体育教师职业化发展的社会因素
当今社会变革的加剧和发展的迅猛,教育日益成为社会关注度高的领域。人们对教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继而把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厚重希望全部寄托在教师的肩膀上,“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成了人们要求甚至苛求教师的口头禅。当体育成了中考,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相应的学校也越来越重视体育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然而对体育教师的作用也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体育教师的职位还是低,社会大多人眼中的体育教师就是平时不注意自身修养,不维护自身形象,给人们留下一个“粗人”形象――松松垮垮、拖拖拉拉、吵吵嚷嚷,动不动就发脾气,没有文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甚至还有些张狂,对体育教师以偏概全,这些导致了体育教师在学校的尴尬地位。
三、体育教师职业化发展的策略选择
1.体育教师职业化发展的教育机制
随着现代教育人才市场流通机制的建立,体育教师对教育行政部门的依附日趋减弱, 教育行政部门对体育教师个体地位的限制也日趋衰弱, 使得教育行政部门对于体验营教师的流动也只是宏观上的指导作用。而现代教育人才市场机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 提供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机会和资源支撑的功能在不断增强, 体育教师的维权机构也日趋民间化, 使得教育组织机构越来越关注体育教师的职业化成长, 并将在体育教师的职业成长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体育教师以及校际之间的合作, 为体育教师提供新知识、新观念,开展有效的体育教师培训, 提高体育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完善学校发展机制, 提高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加强体育教师与主办学校的单位特别是民办学校联系, 推动学校和体育教师之间的良好合作机制, 为解决体育教师的后顾之忧创造条件。
2.体育教师职业化发展的社会支撑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2篇
摘 要 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劳动合同法等政策调整、原材料成本飞涨等综合因素影响,纺织行业生产成本普遍上涨了10%以上。宜兴的整个纺织业都面临着市场萎缩、融资困难、效益下滑等一系列问题,新形势的到来对我市纺织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如果企业能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调整企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则可以及时抓住机遇,增强企业实力,带领企业走向发展的道路。本文将从宜兴纺织业发展的现状、遇到的问题出发,对新形势下宜兴纺织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探讨,以此希望为宜兴纺织业发展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 新形势 宜兴纺织业 发展新思路
江苏一直是国家的纺织大省,对于宜兴来说纺织业也是我市的传统支柱产业。但近些年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市的纺织业发展严重受挫,陷入了困境,大中型企业大量亏损,小企业倒闭的也是非常多,最近啄暾个行业都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如何让我市纺织业摆脱这个困境,在新形势下能及时把握住机遇,再创新纪,为我市工业发展再立新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宜兴纺织业的现状及问题
(一)企业零散,规模小,不成体系
宜兴全市有近千家纺织工业企业,其中大型企业仅78家,其余的全是小型企业,数量上远大于中大企业,而从投入产出水平来看,小型企业则远远低于中型企业。据统计,宜兴的小型企业平均每家企业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资产总计、利润总额、利税情况等仅仅只相当于大型企业的3-5.5%,相当于企业的14-20%。但从利润来看,销售利税率数据:大中型企业8.5%,小型企业为6.7%,小型企业要低1.8个百分点。总的来看,我市的纺织业普遍存在规模小、集中度低、缺乏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普遍还没有形成“小批量、多品种、快交货、高品质”的反应机制。
(二)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
由于主要都是小的零散的企业,导致我市纺织产品科技含量低,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市规模以上纺织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中,新产品产值率仅7.64%,比平均水平低了4.8个百分点。而且我市无论大、中、小企业普遍无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低,在纺织、纺机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严重缺乏,产品的质量、档次、品种都没有什么国际竞争力。在出口产品中,也都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大品牌。设备上面来看也主要是靠引进,没有什么自主研发的,发明专利占比少。
(三)原材料的紧缺及人力成本增加导致产成本增大
由于城市的扩张以及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棉花、亚麻等原材料产量降低,材料的稀缺导致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就以生产资本的棉花为例,2005年左右是8000-8500元/吨,现在则是一万多,最近两年更是看着上升,就2016年11月棉花价格是14500-15500元/吨,到2017年1月棉花价格是15000―16000元/吨,短短2个月时间棉花的价格就涨了1000元/吨。即使如此,还出现了争抢原材料的情况,就简单预计,我省的棉花缺口应该在500万吨以上,供需差距导致了棉花价格节节上升。
二、宜兴纺织业发展的新思路
(一)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重点推动企业重组整合,鼓励企业做强做大,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支持和鼓励优势企业向上游整合资源,建设大型化纤原料基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向下游延伸,强化产业链协调发展,以市场需求引导产品开发,提高下游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升产业链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二)促进常规产品优质化,加快发展差别化纤维
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化纤工艺、装备及生产自动化控制水平,重点解决生产设备的柔性化、常规产品的优质化。加强化纤生产与下游应用的联合开发,加快发展高仿真、功能性、多功能复合等差别化纤维,并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
(三)优化产业区域布局,发挥集群发展优势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挥产业链配套和产业集聚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地区优势互补的区域布局。已形成一定化纤纺织集群规模的地区继续发挥化纤人才、技术及市场辐射的优势,着重加强研发创新、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及高新技术纤维,依托优势企业发展特色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3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方面,主要是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突破就是,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过去只提到,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现在提决定性的作用,一切按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市场价格来定。这就能够促使效率的最大化。再者,减少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就减少了的根源。这都是有好处的,效率也提高了。
另一个重要的,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应该门户开放,领域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并且改为混合所有制。要鼓励民营企业去参股国有企业,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也是一种变革。
第三个方式就是,有条件的地方陆续要建立,或者是发展成为职工持股制度,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所有这些都是创造制度红利的地方,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将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包括国企、民企,都走向混合所有制,也包括职工的持股制度,只有职工持股了,企业才能变革。这个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两个层次的改革。作为高层次的,是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因为重要问题在资源的配置。在这方面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每种资本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长期以来,人们惯用的是生产效率,投入产出关系,多投入就有产出,少投入效益提高了,有同样产出,这是生产效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界逐渐重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什么意思?假定投入是既定的,A方是配置资源有N的效率,B方是配置资源有N+1效率,这样的话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于是,资本市场的地位就重要了,产权交易平台就重要了,兼并重组就重要了,这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启发的。国资委管资本不要去管企业!遇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怎么改?人家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聘任总经理,这些起作用,你管它干什么?你不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置于一边了吗?不摆脱行政干预,行政管企业不如法人治理结构治理企业。它(国资委)管什么呢?就管资本的进进出出。短期的部门、新兴的产业,需要加强投资,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如果产能过剩了,如果是效益不好,国有资本可以撤出来,国有资本就用活了。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企业都是独立经营主体。
《水浒传》中写道,林冲发配到沧州,路上经过柴进的庄上,柴进就留他住下了。庄上有一个教头姓洪,洪教头趾高气扬、瞧不起人。人家说这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他说,现在混饭吃的教头太多了,他有本事敢跟我比吗?林冲不愿意比。林冲越不愿意比,洪教头就越趾高气扬。这种情况之下,柴进都看不过去了,就说这位洪教头最近才到庄上来,意思是他跟我没什么深交情,你就跟他比。跟他比,林冲打了一两个回合就不打了,跳出来我认输了。还没施展武艺怎么认输了?他说,我还戴着枷呢。犯人戴枷怎么施展武艺?于是请两个公人给把他枷解开了。一解开,几棍子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洪教头满面羞惭、离庄而去。我们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能搞好?它戴枷的。到现在枷没解掉,你怎么施展武艺呢?所以说,一定要改。要让国有企业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这就释放了更多的制度红利。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4篇
我国高等教育大力发展始于1998年,当年招生43万人,到1999年招生达到107万人,经过十几年的大力发展和规模扩张,到2012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达到1276所,招生325万人。但是由于适龄人口的下降,生源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既给高等职业教育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高职教育必须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这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目前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导致对物流人才的需求日益高涨,据我国人才培养的现状来看,物流行业人才的培养主要来自于两种途径,一种是社会培养,另一种是院校培养。尽管近年来高职院校和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培养大批量的物流人才,而这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况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毕业生所掌握的技能和专业能力与企业所要求的差距很大,形成就业的供求矛盾,加强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内涵式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2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发展的核心是内涵
2.1在与时俱进中传承
内涵式发展是高职专业在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办学实践中的不断传承与积累。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长期的积累与传承,即所谓的历史积淀。物流管理专业最早起源于军事,是从应用科学分支出来的,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物流起步较早,我国物流学科始于21世纪初,高职院校的物流专业大多开设于2000年初,很多的知识传承了西方物流学科知识体系,短短的十几年理论教学却面临电子商务、物资配送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当今的物流行业显现出时代的特色,比如京东、天猫淘宝的发展促进了物流管理专业发展的时代性。
2.2科学中形成系统性
内涵式发展是一种相对的历史发展过程,发展更多的是内在要求,必须抓住本质和规律性,按规律办,其发展道路主要是通过内部改革、激发活力、提高竞争力,在量变中引起质变。即所谓的本质属性。物流管理专业内涵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内涵丰富,内容多元化,涉及到运输、仓储、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包装及信息处理六大功能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而且系统发展还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即所谓系统发展。
3高职物流专业内涵式发展的路径
内涵式发展是建设高水平、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内涵式发展就是通过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引领的办学职能。在当前,物流管理内涵式发展的路径应特别关注以下问题:
3.1定位是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内涵式发展核心
专业设置定位是高职发展的灵魂和精髓,是核心要素。所谓定位是物流管理专业办学思想与过程的概括,是对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思考,是物流管理专业内涵式发展的理性认识,它决定和规范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活动,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并对教师、学生培养目标追求起到导向和激励作用。不在规模大小,关键是形成自己的定位理念和风格。物流管理专业更是如此,要培养快递员还是叉车司机,是一线的实操人才,还是中层的管理者。由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史较短,特别是一些高职院校建校时间不长,还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影响发展。因此,总结和凝炼符合经济社会要求、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和物流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理念,是今后一个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物流管理专业内涵式发展的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3.2课程建设是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内涵式发展的龙头
课程培养是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龙头,是最能体现专业发展特色的重要因素,加强课程建设是内涵式发展最直接、最现实的选择。
(1)实现无缝对接产业集群。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建设是以物流行业实操能力核心为导向,专业建设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高职物流专业建设,物流课程建设对接产业集群,全面提升专业课程建设水平,提升物流专业服务社会的能力。优化物流专业结构,以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明晰物流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定位,物流课程教学标准要与本行业标准相适应。
(2)集成物流专业群。高职物流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只有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才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依据物流产业集群或产业链而设置,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若干相关专业(方向)的集合。物流专业群以地域性发展为基础,能否适应市场的需求,也是区域经济发展联动性、资源性的集聚。
3.3物流人才培养质量是高职物流专业内涵式发展的根本
(1)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符合就业企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高职院校物流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掌握现代物流经营管理理论,熟悉现代物流技术、法规、政策,具有较全面的物流实务知识和操作能力,培养在工商企业物流中心和第三方物流公司从事物流经营管理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与企业人才需要的人才不脱钩,势必要真正了解企业的需求,目前德国的高职教育中的双元制,正是凸显企业需求,将所学与所用紧密联系的示范。
(2)强化物流实训育人环节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物流管理专业是高职专业建设中实操性很强的专业,仅仅停留书本理论传授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物流行业用人的需求,强化实践环节,在实践中建构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态度。要结合物流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制定物流实践教学标准,制定高职学生顶岗实习的管理办法,建立实践育人机制,确定物流实训教学必要的学分(学时);加大实践基地建设力度,保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实训、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支持高职物流专业走出校门,在教师指导下参加物流企业实习、工艺创新和发明专利等活动,及时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物流技能大赛,以赛促学,提高高职物流学生的技能水平;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者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和挂职锻炼等社会实践活动,提高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
(3)突出就业创业能力培养。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做为物流行业主要输送人才的来源,带动物流行业的发展水平,更是决定着相当数量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就业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将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学分、学时),通过课程、活动和实践,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完善物流行业相关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开展高职学生职业发展、求职方法和技巧、简历撰写、面试准备、模拟面试等就业咨询与辅导。开发物流专业创业课程,将创业教育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学分、学时),依托物流工业园区、物流产业园区,积极开展高职学生创业实践训练,搞好模拟创业、创业设计大赛等活动,传授创业知识,培养创业精神,锻炼创业能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突出物流专业就业创业能力培养,实现学生自主成长,成功就业创业。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5篇
葡萄酒富含白藜芦醇等多酚类抗心血管疾病的保健物质,是一种绿色健康的酒类,适量饮用,对于预防心血管等疾病具有较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近些年来,我国葡萄酒市场发展迅速,葡萄酒的人均年消费量逐年提高,2006年葡萄酒人均年消费量达到0.5L,预计到2010年我国人均葡萄酒消费量接近1.0L,到2015年将达到1.2~1.5L,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葡萄酒的消费量快速增长,在酒类消费中的比例不断提高,成为同期食品饮料行业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子行业。我国葡萄酒行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葡萄酒年产量超过60万t(吨),葡萄酒行业年利润总额30亿元,已经成为食品行业的朝阳产业,前景十分诱人。
2 我国葡萄酒业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目前,我国葡萄酒产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但在国际市场上份额少,出口量少,国内的市场正在被其他国家的葡萄酒产品占领,且主要占领着我国高中档市场。要稳固国内市场,目前面临着3个重要的任务:一是提高葡萄酒的风味品质;二是提高葡萄酒的安全品质;三是克服冬季埋土防寒而建立大规模化生产基地短期劳动力需求量大和生产成本高的难题。目前,我国栽培的酿酒葡萄品种主要是国外品种,尤其是原产于法国的品种。这些品种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地中海气候(夏季干旱和昼夜温差较大)条件下,采收时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正好适宜制作干型葡萄酒。但在我国除西北地区外,葡萄主产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葡萄生长与成熟前的一段时间里,加之昼夜温差小,大多数情况下成熟时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不到21%~23%,通常需要加糖才能达到要求的酒精含量,缺少应有的香气,因此生产的葡萄酒品质差。欧亚种酿酒品种在世界上的主要葡萄酒产区均不需要埋土防冻就可以安全越冬,但在我国的葡萄酒主产区,包括华北的大部及西北地区不能安全露地越冬,必须在冬天埋土防寒才能栽培。而葡萄埋土出土机械化操作困难,葡萄埋土防寒栽培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导致了埋土和出土期间进行规模化生产时短期劳动力极度短缺,也导致生产原料中劳动力成本增加,降低我国葡萄酒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主要葡萄酒产区雨热同季,而主栽的欧亚种的酿酒品种的抗病能力鞍弱,因此,生产过程中的病害防治任务较重,使用的农药次数多、量大,产品的安全质虽较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时,面临“绿色壁垒”的挑战。冲破这个技术壁垒的最好方式是采用高抗病的品种,生产有机葡萄酒。
3 发展有机葡萄种植是当前世界葡萄酒业重要的发展趋势
有机农业是指完全不使用合成化学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制度。按照有机农业生产方式生产的农业产品,统称为有机食品(Organic food),其中按有机农业生产方式生产的果品,被称为有机果品。按照有机农产品加工要求将有机果品加工成的葡萄酒,即有机葡萄酒,是安全食品中的最高质量要求的产品。由于按有机农业生产的有机食品是最安全的食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售价很高,其价格通常是同类普通食品的3~4倍。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有少量的有机葡萄酒生产。在美国,有机葡萄的种植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消费者对有机葡萄酒的兴趣也日益浓厚。美国有机行业协会估计,有机葡萄酒的销售正在以平均15%的速度增长。2005年,在加州大约有150个葡萄种植者和酒庄获得了加州有机种植者认证协会CCOF的认证,CCOF代表了加州有机农业的80%。许多德国和意大利的酒厂也拥有有机葡萄酿造的葡萄酒,如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La Spinona和法国卢瓦尔谷地的Clos Roche Blanche、Domaine de la Sansonniere以及Paulat。智利著名的安杜拉瓜葡萄园已经在培育有机葡萄,并着手生产有机葡萄酒。近几年,为了适应世界农业生产发展的趋势,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了《有机食品技术规范》,制定了《OFDC有机认证标准》,这些都为生产有机果品、发展有机葡萄酒业创造了条件。
4 培育适合有机种植的高抗病抗逆葡萄品种是我国发展有机葡萄酒的必然举措
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的有机葡萄酒的生产还很少,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缺少有机葡萄种植。我国目前酿酒葡萄原料生产的主要区域雨热同季,采用现行的欧亚酿酒品种进行栽培,其抗病性差,在完全不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农药的情况下,病害发生特别严重。我国目前要突破病害防治这个关键限制因子的障碍。唯一的途径是在品种选育上获得重要的突破,采用高抗病害的新品种。目前,全国一些葡萄育种单位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单位已经选育出了一些抗逆性和抗病性强、含糖量高的优良酿酒葡萄株系,将会为实现我国特色葡萄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不断提高国产葡萄酒品质的同时,可尽快消除同质化现象,表现我国葡萄酒典型、独特的风格,这对进一步完善葡萄酒产品结构,满足葡萄酒消费市场的个性需求意义重大。因此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立地条件的品种及其栽培模式,可促进中国葡萄酒生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国酿酒葡萄主要在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栽培,现在栽培的品种均需要在冬天进行埋土才能实现经济栽培。由于埋土造成土壤表面在冬春季处于的状态,成为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扬尘天气的重要尘源。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监测结果表明,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中,本地的贡献率达到20%~30%,农田地表是其中的最主要的沙尘来源。采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酿酒葡萄品种‘北红’与‘北玫’进行栽培,具有高抗寒、抗病性,在我国的华北地区、西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葡萄园冬季不需埋土,可节省大量劳动用工;同时还可以减少扬沙天气,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大量农药的开支,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和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有机栽培生产有机葡萄酒,增加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可实现我国葡萄酒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