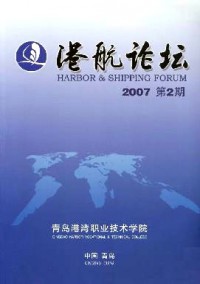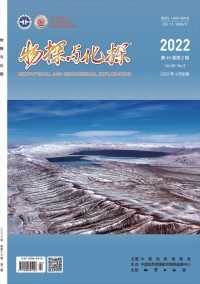谈谈对古代文学的认识

谈谈对古代文学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1] 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 [2] 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江??⒈?凇⒂φ病⑿茉丁⒊ ? 等亦著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将“亡天下”之罪一概归诸清谈。赵翼《廿二史??记》“六朝清谈之习”条亦溯其源,察其变,于清谈习尚之弊端致意再三。古今虽偶有持平之论, [3] 然终难翻案。
总之,古代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皆与政治有关,直至近代,人们对于魏晋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 1919 年的《清谈源流考》 [4] 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察波观澜,其所注意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谈的起源问题 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生动。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 [5] 话虽不多,清谈之起、承、转、衰无不一一点逗清楚。而清谈起源之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清谈的思想源头,二是清谈风气之肇端。对前一问题,学界不约而同追溯至东汉,但在思想渊源究竟出自王充还是马融则存在争议。 20 世纪 20 年代,钱穆以翔实材料和滔滔雄辩,率先接橥王充《论衡》一书对于魏晋玄学思潮形成的开创意义,指出:“寻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以助成之也。” [6] 40 年代,探讨和争鸣仍在继续。先是贺昌群 在《清谈之起源》一文中将汉末大儒马融作为清谈“一启蒙人物” [7] ,而孙道?N则认为“王充的哲学思想是魏晋清谈家之思想的唯一源泉,魏晋清谈家之思想,滥觞于王充,导源于王充之《论衡》” [8] 。两年后,杜国庠撰《魏晋清谈及其影响》一文,认为“清谈的滥觞也不能限自正始”,在东汉一些经学大师如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的身上,“已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清谈的作风和因素”。 [9] 近年来,范子烨又提出清谈“由西汉时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的观点。 [10] 其实,一味地上溯还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庄子,但也会使论题离清谈的思想实质越来越远。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孙道?N等人的“王充说”较为妥帖可靠。 [11] 对于清谈作为一种谈辨风气的形式肇端问题,学界大多持“汉末清议说”,陈寅恪、唐长孺、杜国庠等学者多持此说,几成定论。 90年代, 唐翼明在钱穆、余英时的基础上,力驳众议,认为汉末“清议”主要在于议论时政和品评人物,实无关于抽象之哲理,故可排斥于清谈定义之外,而清谈之风则源自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 [12] 尽管唐氏魏晋清谈之概念或有可商,但其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的确使许多前人无暇深究的问题得到了廓清。
(二)清谈的分期及流派 这一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对清谈起于何时、宗于何人、如何发展嬗变等诸多问题的回答。古之学者如 赵翼称“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以何晏、王弼为宗,“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论列清谈流变甚清楚,但尚未作出明确分期。(《廿二史??记·六朝清谈之习》)现代学者方始措意此一问题。陈寅恪根据与政治之关系将清谈分为前后两期,以“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魏晋南北朝史讲录》)视野宏通而略显笼统。缪钺则认为:“魏晋清谈之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冰茧庵丛稿》)线条清析而失之简单。同持“四期说”的还有无畏,他将魏晋清谈分为“正始”、“正元至景元”、“咸宁至元康”、“永和”四期,较为具体而有欠舒展。 [13] 唐翼明采用的是“三分法”,将汉末“游谈”及魏太和初作为清谈的“酝酿与成形”期,魏末至西晋至元康为“将绝而复兴”期,东晋及南朝为清谈的“重振与衰落”期,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均有拓展。范子烨在其新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综合 诸说,以年号和公元纪年两种方式出之,将中古清谈厘为萌芽( 147-239)、形成(240-249)、鼎盛(250-419)、衰落(420-589)四期,思路清晰,针脚绵密,遂将中古清谈演变之迹尽显其中。至于清谈的流派问题,一般在分期问题中就被涉及。通行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刘大杰的“名理”和“玄论”两派说, [14] 一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清议”和“清谈”两派说, [15] 一是汤用彤的“贵无”和“崇有”两派说。 [16] 三说着眼点不同而各有理路,特别是汤氏之说,将魏晋清谈各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机贯穿,乃最具通识之卓见。
(三)清谈之内容 清谈谈什么?自然是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其最著名者当首推汤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有关清谈的主要论题大都做了深入探讨。此后,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此一问题,较为深入的专著有王葆?的《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研究表明,清谈核心的内容就是由《老》《庄》《易》所组成的所谓“三玄”。“三玄”之说大概兴于南朝,而始见于《颜氏家训·勉学篇》,其文略曰:“何晏、王弼,祖述玄虚,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王僧虔《诫子书》也提到“诸玄”,亦当指此三书。在关于魏晋玄学家们的记载中,善言《老》《庄》《易》的说法屡屡出现,何晏、王弼都注过《老子》,王弼、钟繇钟会父子及阮籍等皆阐发《周易》,向秀之前,注《庄子》者已有数十家。可见“三玄”在玄学清谈中实有至高无上之地位。其它作为“言家口实”的尚有(1)本末有无之辨,(2)才性四本之论,(3)自然名教之辨,(4)言意之辨,(5)圣人有情无情之辨,(6)名家论理之学,(7)佛经佛理,(8)养生论,(9)声无哀乐论,(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众多所谓“理中之谈”。(详 见唐翼明《魏晋清谈》)清谈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玄学的内容,许多问 题已经 偏离了更具形式感和现象学意味的清谈文化本身,成为纯粹哲学思想史上的研究课题了。
(四)清谈的形式研究 此研究包括清谈活动的场所、阶层、程式、术语、道具等诸多方面的探讨,是最具文化色彩的课题。唐翼 明的 博士论文《魏晋清谈》专设一章,主要利用“清言渊薮”《世说新语》中的清谈材料,从参与方式、程序、术语、准备、理想境界、游戏与社交色彩诸方面勾勒了清谈论辩在形式上的大致轮廓。指出清谈“是一项精致的、学术性很强的智力活动,跟一般的游戏不同,即使有争胜的心理羼杂其中,而求真的本性始终未去”。 [17] 唐氏的研究细致而周到,有填补空白之意义。同样是对“清谈之方式”的研究,范子烨则拈出“口谈”一词,对口谈的场所、基本模式、音调、“番数”、道具等问题进行“历史还原”,生动翔实,别开生面。 [18] 此外,叶柏村、信应举等人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 20 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文化研究。
(五)清谈的评价问题 前面说过,“清谈误国”是古人对清谈的总体评价,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关怀,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随着时展和学术进步, 20世纪以来,学者观照清谈之意义,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入手,重新认识魏晋清谈的价值。除了从学术思想上做客观研究,不少学者还对清谈文化注入了主观感情,大作翻案文章。1934年,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开篇第一节标题便是:“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 [19] 从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这种思想几乎主导着整个学术界对清谈的认识和评价,如孔繁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 [20] 蒋凡也在其近著中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 [21] 于此,我们可以窥见 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到,魏晋清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牵动着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神经,吸引着历代知识阶层或艳羡或鄙夷的目光,对于清谈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从政治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不仅体现了认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也是当代文化生态在价值取向上日益多元化的一种折射。
(原载《学术月刊》 2005年第10期)
注释:
[1] 参见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10 月版,页 43 。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既没有采用清谈的广义的用法(即将魏晋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代名词),又排除了具体的“政治批评”(“清议”)和“人物批评”(“品藻”)的含义,从而将清谈的内涵和外延凸现出来。
[2] 参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及《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二文,三联书店 2001 年版,页 201 - 229 ,又页 47 - 54 。
[3] 如王通《中说》、叶正则《习学记言》、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及章太炎《五朝学》等,皆为之辩护,文繁不赘引。
[4] 《史学杂志》 30 卷 4 、 5 、 6 、 9 、 11 号 连载。
[5] 案:此段原文中有夹注,今略去。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六章《魏晋清谈》,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页 141 - 143 。
[6] 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
[7] 原 载《文史哲季 刊》 1 卷 1 期, 1943 ,收入《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8] 孙道?N 《清谈起源考》, 《东方杂志》 42 卷 3 期, 1946 。
[9] 原载《新中华》复刊第 6 卷 11 期, 1948 ,收入《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10]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 社 2001 年版,页 149 。
[11] 按:《后汉书·马融传》:“卢植……少与郑玄师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受章句。”贺昌群误读此句,谓指马融。故其以马融为清谈“一启蒙人物”,实于理难安。余英时对此已有驳正。详见《士与中国文化》,页 353 下注。
[12] 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13] 无畏《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 ,《中国文化 》 2 期, 1946 。
[14]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 1939 年出版,今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蓬莱阁丛 书”本。
[15] 宫崎市定《清谈》,载《史林》 31 卷 1 号, 1946 。
[16] 此说出自汤用彤《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一文, 原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后作为附录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魏晋玄学论稿》 , 2001 年版。
[17] 唐翼明《魏晋清谈》第二章《清谈形式考索》,页 37 - 62 。
[18] 参阅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篇《从黄金到土泥: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
[19] 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 方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30 。
谈谈对古代文学的认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整理。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谈谈对古代文学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谈判;烛之武;游说
在当代商务谈判中,往往需要用到不少谈判技巧和谈判方法。实际上,在我国古代很多经典著作中,往往富含谈判智慧。本文将尝试利用当代谈判学的原理和方法,分析我国古代经典谈判案例“烛之武退秦师”。
一、烛之武退秦师的主要内容
烛之武退秦师讲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郑国的国君曾经对晋国的国君无礼,因此晋国和秦国决定联合起来攻打郑国。晋国的军队从函陵进攻郑国,秦国的军队从锬辖攻郑国,郑国危在旦夕。郑国的大臣佚之狐对郑国国君说:“郑国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国有一位能人叫烛之武,如果请烛之武去出使秦国,去游说秦国国君,也许可以说服秦国退兵”。郑国国君听从了佚之狐的建议,去请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烛之武出使秦国。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烛之武一开始并没有立即接受郑国国君的邀请。烛之武推辞说:“当我正值壮年的时候,国君您并没有重用我,觉得我不如别人。现在我已经老了,就更没有能力为国分忧、为国效劳了。”在这里,从谈判的策略上说,烛之武采取的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技巧。从内心来说,烛之武希望能为己为国建功立业,同时自己也能因此加官进爵,享受荣华富贵。但如果烛之武很轻易的就答应了郑国国君的要求,那么有可能郑国国君并不能充分认识到烛之武的价值,即使烛之武帮助郑国化解了这次危机,郑国国君也可能不会给予烛之武高官厚赏。
郑国国君又是怎么回答的呢?郑国国君说:“我没有能够早一点重用您,现在国家遇到了如此危急的事情,我才来请求您,这是我的过错,请您能原谅我。然而如果郑国灭亡了,您作为郑国的臣子,对您也会不利呀。”郑国国君的回答包含了两层意思。
首先郑国国君承认了自己之前没有重用烛之武是自己的错误,向烛之武郑重道歉,并暗含:如果烛之武这次能够退秦师,那么郑国国君这次一定会充分认识到烛之武的价值,给予烛之武相应的奖赏和礼遇,国君再也不会低估烛之武的能力和作用了!这是郑国国君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的体现,这种灵活性也是谈判中非常需要的。
郑国国君的第二层意思是:烛之武通过出使秦国来化解郑国的危机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郑国国君和郑国,同样也是为了烛之武自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郑国如果灭亡,烛之武也将承受被殖民之苦。这里体现了说服别人的一个原则:要使得自己的建议触及对方的利益从而打动对方,而不是简单的请求。如果郑国国君只是一味的请求烛之武拯救郑国,那么郑国国君在整个谈判中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郑国国君在谈判中阐明:如果烛之武不帮助郑国致使郑国灭亡的话,那么对烛之武也是十分不利的。
二、烛之武的谈判策略
经过和郑国国君的一番谈判,烛之武同意出使到秦国的军队中,去游说秦军退兵。晚上烛之武趁着夜色,悄悄溜出城去,见到了秦国军队的主帅秦伯。烛之武对秦伯说:“如果郑国灭亡能够使秦国获益的话,那么我是不会来麻烦您的。但是请您认真想一想,郑国灭亡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
烛之武接下来就从秦国的角度分析郑国灭亡对秦国的影响。这种策略是谈判中经常使用的:就是从对方的利益出发分析问题。烛之武说:晋国和郑国国土相邻,而秦国和郑国国土不相邻。郑国灭亡后,晋国可以把郑国作为自己国土的一部分,但秦国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郑国灭亡后,秦国并不能得到郑国的土地。更加严重的是:晋国因为得到了郑国国土而实力大增,秦国实力没有增进。晋国和秦国都是势均力敌的大国。晋国更加强大了其实对秦国没有好处。
烛之武又强调:如果这次秦国不把郑国灭了,那么郑国必然非常感激秦国。今后秦国如果需要路过郑国,那么郑国必然给秦国提供足够的粮食、水等必需的物资,这样对秦国不是很好吗?
另外,在秦国和晋国联合攻打郑国之前,晋国许诺给秦国很多得胜后的好处。烛之武劝说秦伯说:晋国是一个没有信用的国家,以前晋国曾经对秦国做过背信弃义的事情,怎么能够保证这次晋国能履行诺言呢?
经过烛之武的游说,秦国决定不再攻打郑国。没有了秦国的帮助,晋国没有能力独自没掉郑国,晋国也只能撤兵了。郑国的危机得以化解。
三、谈判的启示
通常说来,谈判分为对立型谈判和合作型谈判。对立型谈判是指双方的利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在谈判中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合作型谈判是指谈判双方为了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相互合作,相互妥协,争取达到双赢的结果。而且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双方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有可能从对立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也有可能从合作关系转化为对立关系。因此,在进行谈判时,充分利用合理的战略和战术是非常重要的。
在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中,烛之武就充分利用了谈判技巧。在和郑国国君的谈判中,烛之武采用的是欲擒故纵的谈判策略,使得郑国国君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在和秦伯的谈判中,烛之武采用的是多方位的谈判策略,使得秦伯认识到秦国和郑国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另外,秦国和晋国的联合也是存在风险的,秦国没有必要替晋国火中取栗。具体说来,烛之武采用如下三种战略战术。
第一:烛之武从对方的利益出发说服对方。烛之武不是请求秦国不要攻打郑国,而是通过证明“郑国灭亡对秦国没有好处,郑国灭亡对秦国有坏处”这一点来打动秦伯。第二:烛之武还提出郑国对秦国的价值。秦国将来路过郑国时,郑国可以给秦国提供需要的物资。这一点在谈判中也很重要。要让秦国充分认识到郑国的价值和力量。第三:回顾历史,烛之武提到了晋国背信弃义的特点,让秦国认识到和晋国合作的风险。
烛之武退秦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谈判案例。中国古人已经具备了很高的谈判技巧,对当代谈判也具有借鉴意义。(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注:本文得到“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的资助。
参考文献:
[1]“模拟谈判法在国际商务谈判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赵青松,《对外经贸》,2013年,5月。
[2]“中国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梁勇、 东艳,《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4月。
[3]“谈判信心对审计人员谈判判断的影响“,周冉,《审计研究》,2014年2月。
[4]张黎.影片教学法在商务谈判课程中的应用[J]. 现代商贸工业. 2014(22)
[5]和伟.语篇对比分析下的中美国际商务谈判[J]. 中州大学学报. 2014(01)
[6]蔡亚飞.跨文化的商务谈判[J]. 黑龙江科学. 2014(12)
谈谈对古代文学的认识范文第4篇
一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
谈谈对古代文学的认识范文第5篇
一
1943年初的上海文坛,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古今》一周年纪念专号的出版。从初期的惨淡经营到获得读者认同,《古今》创办人朱朴与编辑周黎庵颇为欣慰。为了答谢诸位朋友的支持,继续扩大《古今》的影响,朱朴与周黎庵于1943年3月推出96页的《古今》周年纪念特大号,篇幅比平时足足多了两倍。
纪念号上除了、周佛海、赵叔雍等伪政府官员的文章外,北平、南京与上海等地的文人雅士也珠玉纷投,瞿兑之的《〈宇宙风〉与〈古今〉》、谢兴尧的《〈逸经〉与〈古今〉》、纪果庵的《〈古今〉与我》、徐一士的《〈古今〉一周纪念赘言》、文载道的《借古话今》、予且的《我与〈古今〉》、冯和仪的《〈古今〉印象记》与柳存仁的《年年有个三月三》等佳文纷呈,共同搭建起为《古今》祝寿的欢乐舞台,一时间很是热闹。众人在文中回顾了《古今》创刊一年的种种表现,对《古今》的文学追求进行了诸多褒扬。瞿兑之认为《古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谢兴尧则认为《古今》“扫除滥调,独创新格,故能得大多数之同情爱护,而为士林之精神食量。”众人固有为《古今》捧场之意,但作为学者名流、行家里手,其评价却大抵中肯实在,并无多少虚夸之词。
以上所提及的诸位作者再加上梁鸿志、龙沐勋、周作人、沈启无、陶亢德、黄裳等,基本上就是《古今》的写作班底。端详《古今》作者群,发现若干大小汉奸厕身其间,则不免令人尴尬。事实上,《古今》作为纯文艺刊物,并非汪伪当局的政治文化宣传工具。剔除《古今》中或显或隐的汉奸言论与媚日文字,《古今》指涉现实政治的文字并不多。否则就不会有人说《古今》“偏重于风土人情、文献掌故”多“怀古感旧、谈狐说鬼”了。撇开复杂的政治因素与道德谴责,回到文学场域中品评《古今》,不难发现置身于1940年代初通俗文学喧哗声浪中的《古今》,是一种独异的存在。作为一份严肃冷静的高雅读物,其“格调高古、掷地作金石之声”,是上海沦陷时期惟一不与通俗文学合流的文学期刊,其谈古论今的小品文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表现出了“高蹈”的文学姿态,传承的乃是五四“言志派”散文的文学观念,这使其成为1943年初五四新文学在上海沦陷区延续的重要血脉。
在《古今》一周年纪念特大号出版后的一个月里,《风雨谈》、《人间》的相继创刊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古今》成功的启示。时人认为《风雨谈》、《人间》等期刊的瓣香乃在《古今》可谓一语中的。尽管《古今》的政治背景遭人诟病,但其有别于鸳蝴派的文学趣味使其在上海沦陷区的文学期刊中独标一格,渐成为一种类型。其发行量从创刊号时的1500份已增之纪念号时的近4000份,远非其他刊物可比。但即便如此,与发行3万份的《万象》相比,仍有天壤之别。这说明:专走高雅文学路线固然狂狷,但阳春白雪往往曲高和寡,要想扩大销量还得另辟蹊径。
《风雨谈》从创刊号便开始连载予且的《迷离》、谭维翰的《夜阑人静》等通俗小说,显示了对《古今》文学观的超越。《风雨谈》虽不具有《古今》特立独行的文学品格,却比《古今》更善于审时度势,其雅俗兼容与各种文学体裁并包的文学姿态令其市场大开,终至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沦陷区最惹人注目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财力,柳雨生如鱼得水,《风雨谈》一出版便是156页的32开本。不久便集结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启无、周越然、纪果庵、谭正璧、谭维翰、潘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苏青等。与《古今》相比,《风雨谈》的作者阵容庞大许多。众多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在为“稻粱谋”的同时,也在《风雨谈》上找到了展示自我的平台,1943年的上海文坛从此增添了许多欢腾。在未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苏青的《结婚十年》、许地山的《玉官》、柳雨生的《怀乡记》、文载道的《风土小记》、周作人的《苦口甘心》、废名的《废名诗抄》、朱湘的《燕子》、卞之琳的《半岛》以及一些重要评论如谭正璧的《论苏青与张爱玲》等名篇将先后问世。《风雨谈》为此刻文坛留下的巨大身影使得日后的文学史家在考察这个阶段的上海文学时不得不频频回首。四十五年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收录期刊276种,沦陷区只有两种,《风雨谈》名列其中,这是柳雨生在1943年未曾料到的。
同月创刊的《人间》声势显然不及《风雨谈》浩大,主编吴易生既无日本人撑腰,与北平作家又不似柳雨生交厚,但能推出126页的16开本,其文学雄心却胜过《风雨谈》一筹。《人间》的文学取向较接近于《古今》,不同的是,它以散文为主兼载小说、剧本、诗歌与评论。其作者多为《古今》、《风雨谈》上经常露面的沪上名家,做足官瘾的创造社元老张资平也开始重操旧业执笔为文,北平作家只有周作人,此外则还有龚冰庐、陈大悲、章克标、傅彦长、胡兰成、林微音一干人等。尽管《人间》在世上只逗留了半载光阴,但其在1943年里驶过的文学之轮却在人间留下了辙痕。
二
《紫罗兰》于1943年4月复刊,表明了与上述期刊不同的文学选择,显示了1943年上海文学的又一面孔。主编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老将,也是通俗文学期刊的编辑大家,享誉一时的《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乐观》均出自周瘦鹃之手。1940年代的血雨腥风令人不寒而栗,一年前《乐观》的无疾而终,让周瘦鹃黯然神伤,平静安稳的创作环境何处能够觅得?作为职业作家,摆弄文字是其谋生的一种手段,文学创作既是娱人也是自娱,在坚守“趣味”的同时他们并未无视残酷现实,用文学带给生活在苦难时代的人们些许安慰,本就是他们的文学理想。于是,在爱好文艺的出版商林振俊的怂恿下,周瘦鹃欣然出马。复刊后的《紫罗兰》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周瘦鹃在复刊伊始便申明了刊物倾向:“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列,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并存”。此种思想意趣显然有别于以往鸳蝴派的“趣味”,反映了鸳蝴派作家顺应时代潮流,追求文学现代化的努力,但作为一份在老派读者心中具有很大影响的通俗文学期刊,《紫罗兰》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读者市场,主张新旧调和坚持新旧并举的策略显示了周瘦鹃精明的商业头脑与市场意识。《紫罗兰》的与时俱进以及兼容并蓄获得了成功,刊物周围不仅云集了当时诸多通俗小说名家徐卓呆、顾明道、范烟桥、郑逸梅、程小青、秦瘦鸥、胡山源等,创作出1940年代脍炙人口的诸多长篇如秦瘦鸥的《新秋海棠》、程小青的《龙虎斗》、胡山源的《龙女》、朱瘦菊的《金银花》、《新歇浦潮》等,还凝聚了一批年轻女性作家如张爱玲、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俞绍明、周玲、练元秀等。与鸳蝴派老作家多写通俗小说不同,这批年轻的女性作家创作的多是新文艺作品,如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施济美的《永久的蜜月》、汤雪华的《死灰》等。周瘦鹃是有眼光的,1940年代上海文坛女性作家群体的出现,他与《紫罗兰》功不可没。《紫罗兰》的成功转型影响深远,既拢住了一大批通俗小说大家,又培育了一批新文学的后起之秀,并依靠她们的创作实绩牢牢地抓住了新旧读者市场。
1943年值得一提的通俗文学期刊还有8月份创刊的《春秋》。《春秋》的编辑人陈蝶衣与周瘦鹃一样,都是鸳蝴派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有着丰富的编辑经验。两个月前为财务问题与老板平襟亚闹翻,愤而离开《万象》编辑部。离开了苦心经营两年的《万象》,陈蝶衣心有不甘,在冯宝善的邀请下毅然东山再起。陈蝶衣在《万象》时代就注重新旧文学的融合,使其成为此前上海最受欢迎的文学期刊。此番卷土重来,《万象》时代的老朋友与《万象》的编辑思路显然是陈蝶衣最重要的财富。《春秋》承袭了《万象》的编辑特色,注重知识介绍,并辟有《史地常识》、《风俗猎奇》、《科学研究》、《地方通讯》等栏目,在多个领域展开与社会的互动,旨在赢得各方面读者,这反映出40年代上海的商业性期刊的共性:在坚持文学趣味的同时注重文学的市场定位。《春秋》的文学创作与《紫罗兰》相似,作者群基本一致,由写通俗文学为主的老作家与写新文学作品的青年女作家组成。《春秋》“不谈政治,不言哲理,不作大言之炎炎,惟为小言之詹詹”的思想立场是其保护色,许多非沦陷区作家如茅盾、老舍、沈从文、何其芳、李金发等陆续出现于《春秋》,令上海读者耳目一新。在1943年8月以后的两年里,胡山源的《罔两》、张恨水的《世外群龙传》、茅盾的《老鼠》、巴金的《灯》、老舍的《过年》、冰心的《清宵之忆》成为时人的一份精神食粮,在带给上海读者精神慰藉的同时,也提升了这一时期上海文学的品位。
三
对新文学作家而言,1943年上海文学界最值得书写的事件当属7月间通俗文学期刊《万象》的“变声”。自1941年7月创办以来,《万象》的事业蒸蒸日上,3万份的销售量令其他期刊望尘莫及,此时已是上海文坛通俗文学的老大。陈蝶衣时的《万象》虽有丁谛、施济美、程育真等青年作家出没,但主要是包天笑、张恨水、平襟亚、孙了红、范烟桥、徐卓呆等通俗文学作家的阵地。1942年底《万象》接连推出两期“通俗文学专号”,积极开展通俗文学运动,对五四以来长期遭新文学打压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了高度评价,不无以通俗文学为旗帜统一中国的新旧文学之意。
1943年柯灵接替陈蝶衣主编《万象》,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此前,上海文学的话语权要么控制在亲日文人手上,要么掌握在鸳蝴派文人手上,新文学迫切需要自己的阵地。柯灵主编《万象》后,及时调整《万象》的编辑方针,《万象》的文学倾向从重“趣味”的通俗文学转移到品位较高的新文学创作。作为一个老编辑人,柯灵在编辑《世纪风》、《浅草》等纯文学期刊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与那些读者层次较高的文学副刊不同,《万象》3万多的读者涉及各个阶层,为了照顾这些读者的兴趣爱好与欣赏水平,《万象》版面焕然一新: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游记、书评、戏剧、电影、美术、科学小品,各种栏目应有尽有;此外还辟有“书画插页”、“作家书简”、“万象闲话”、“文艺短讯”等栏目,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新闻性相得益彰,令读者大增。借助此种编辑策略,《万象》既增加了销量,又有效地帮助了新文学的传播,还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对话与交融,为市民文学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元素。
《万象》“变声”后,汪伪作家不再露面,通俗文学作家也渐渐转移,一批新文学作家开始汇集,有沉默多时的王统照、耿济之、师陀、唐、傅雷等成名作家,有张爱玲、沈寂、郑定文、石琪等文坛新人,也有时在外地的沈从文、施蛰存、叶绍钧等作家。新文学史上的一些名篇,小说如张爱玲的《心经》、《连环套》,师陀的《狩猎》、《期待》,郑定文的《小学教师》、《大姊》,还有柯灵、师陀改编的话剧《夜店》;评论如傅雷的《评张爱玲的小说》等先后问世,使《万象》成为1943年及此后两年间上海文坛最重要的新文学期刊之一。
1943年的文学期刊蜂拥而起,以不同的政治面貌与文学理念打开了创作的僵局。或严肃或活泼的文学面孔、或高雅或通俗的文学姿态,为上海文坛奉献了一道道丰盛大餐,也显示了上海文学的新的发展态势:言说的不自由使文学不再承担“启蒙”与“救亡”的沉重使命,剥离了民族国家意识后,文学获得了对日常生活与人性的思考自由。对文学世俗性的认同使“五四”以来的新旧文学之争渐渐平息,新旧文学共生共容的态势已经形成,这为张爱玲、苏青等人铺设了锦绣前程,上海文学即将迎来它的辉煌顶点。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06JSDZW003);淮阴师范学院青年优秀人才扶持计划课题《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生产》(06QNZC001)。]
参考文献:
[1]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紫罗兰》,19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