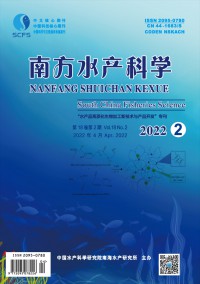贾平凹长篇小说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1篇
此间,王洁的散文集《六月初五》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贾平凹、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分别为本书作序,贾平凹同时题写了书名。《六月初五》分为“寸草春晖”“落花微雨”“含英咀华”“晨钟暮鼓”“拂云弄影”等多个章节,题材多样、风格多变。作者王洁系近年来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因多才多艺且又热心公益事业而广受赞誉。
她是“一个内心干净,行为大方,能激情,好幻想,永远有追求的人”,贾平凹一度感叹“世上还真有既是美女又是才女的人”。贾平凹表示,“之所以喜欢她,是她的那些散文既大气又细致,在质朴中又洋溢着浪漫的气息。尤其那些写儿时的生活,写奶奶,父母的篇章,亲情倾泻,又自自然然地发出那么多精妙的句子,如同水流到了哪儿,那里就有了河床,脚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了路。”
本书同题散文《六月初五》是王洁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很好,她已经亡故的奶奶,我以为会有一些常见的激情抒发,但是却没有,只录下了奶奶生前写给她的几封信。角度独特,文笔收敛,是我所喜欢的散文路数,于是就读了下去。”余秋雨对王洁创作的此类涉及亲情的文章颇多赞誉,“她写母亲,写父亲,都一味朴实真切,不涉虚华。”
“慢慢品味,文中的一字一句,一感一慨,一招一式,像是流淌着的潺潺细涓,柔暖如丝,宛若一古典美女从久远的历史风尘中款款走来,让你似乎依稀能触到一抹意切情深,一缕幽怨哀婉轻轻地拂过你的脸颊……”中国首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总策划张小可读过王洁散文《永远的长恨歌》后如是感叹。余秋雨则认为王洁作品“为《长恨歌》的演出提供了现代文本。”
与此题材相关,由王洁任总策划并亲自作词、主演的MV《霓裳吟》在2016年的年末面世。缘于对那段爱情传奇的独特会意和深度解构,加之自身气场不凡外形完美,使得王洁成为MV《霓裳吟》“女一号”的不二人选。导演评论称,“肤如凝脂、手如柔荑。时而双眉颦蹙,梨花带雨;时而浅笑焉然,轻歌曼舞。王洁版的杨贵妃,恍惚间如同穿越时空回归大唐。”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2篇
一、 《白夜》民俗性与神秘性的文化背景
商州成就了贾平凹,贾平凹也成就了商州。在城市生活了二十年的贾平凹“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界上许多作品的敬畏”,“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他对自己“深感悲哀”,于是想要写一部关于“城的小说”了。①在颇引人“性”趣的但并不十分成功的《废都》之后,贾平凹将笔从城市知识分子投向了普通市民,于是我们看到了更为成熟的现实性与神秘性、现代性与民俗性结合得更为圆融的长篇小说《白夜》。
《白夜》的故事虽发生在西京城,但这只是作者寄情托意的创作载体,作者立于西京城地界,用自己的全部心智复活历史与民间的生命律音,调动起自己多年的民情储备,在小说中为读者营造出一种朦胧氤氲而又清雅通脱的阅读感觉。
贾平凹独特的个性气质使得他在《白夜》中仍然固守着民俗性与神秘性这一“顽地”。“平凹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和家庭的连锁反应的遭遇中度过的。至于那些动人的摇篮曲呀,美丽的童话呀和动人的故事呀等等艺术一类的熏陶,与童年的平凹是无缘的。”②贾平凹先天不足,身单力薄,发育很慢,常遭小伙伴欺侮,于是他向书中寻求庇护,特别是对《红楼梦》入迷(我们在《白夜》中可以约略体味到《红楼梦》的风韵)。贾平凹的性格逐渐地内向、孤独、喜静、多思,只有山石与明月与他常相厮伴。童年少年时代的这一切,熔铸了贾平凹内敛而阴柔的独特气质,而这一气质特点又必然凝结于作品之中。在《白夜》里,不论夜郎吹埙,虞白操琴,抑或库老太太剪纸,再生人故事,诸般事象皆气脉相谐,在静然无痕的叙说中,分明流注着作者贾平凹的不二气韵,两厢如此地契合无间,浑然圆融。
《白夜》中对民俗和神秘性的关注也赖于作者创作心理的转变。贾平凹 在总结以往的经验和克服不足后,以更为圆融的包蕴着丰厚的民俗及神秘事象的文化视角切入《白夜》,这种切入并非对《废都》的重复,它的叙述立场和技巧、事象的密合程度、语言的流畅婉转、情节的自然过渡,在整体上高出《废都》。正是在这一视角的统摄下,《白夜》的民俗事象以其不可剥离的存在方式彰显了该作品的深层内蕴。也正是在作者创作心理转变这一内在因素作用下,《白夜》中的民俗和神秘事象消隐了此前作品中的斧凿和附着的痕迹而与作品的其它内容水融,显示贾平凹在创作上的深入。
二、 《白夜》传递的民俗性和神秘性
《白夜》并无起伏跌宕的情节,它只是叙述了西京城中一群普通人的平常生活故事。以富有神秘色彩的再生人故事开始,以民间目连戏《精卫填海》而结束,在这一叙事框架中并容大量近乎原生状态的生活故事。作者说:“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③其实无技巧即大技巧。在《白夜》中,作者以多种民俗及神秘意象的营造,为读者接通了阴与阳,生与死,历史和现实,俗与雅,酿就了作品的独特的传达方式和解读方式。贾平凹并没有对笔下的人物进行提纯,他让他笔下的人物拥有平常人应该拥有的一切。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个主要人物身上都包裹着一层神秘的紧身外衣。夜郎路遇再生人自焚,与虞白隔阂后的神秘夜游;虞白的焚香操琴,得再生人钥匙;刘逸山的奇方医术,测字算卦;陆天膺的格调高古等等。
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创造出成熟的聊天式的说话方式,一切自自然然平平淡淡。在家长里短的絮叨中有了故事,有了民俗,有了神秘,这是真切的生活。目连鬼戏的演出,既是一种民俗,又透露出神秘气息。在金矿主宁洪祥家演出时人为的差错,似乎与宁洪祥家稍后的系列灾变有着因果关联,在那缥缈的空中,好像有无形的巨手在捏合着人间的芸芸众生的命门。目连戏作为主导性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民俗事象贯穿终始,奠定《白夜》的叙述基调。不仅如此,这一民间戏的演出与文中多个人物相牵连,如一张网笼络着人们,任你如何挣扎浮沉,终无力逃脱命运的泥淖,只会陷入其中而无力自拔。其它诸般事象,只不过是这一剧情的填充和拓展,甚至于整个作品就可看作是一出目连戏。库老太太剪纸的天赋秉质及其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神神道道的迷醉状态;夜郎在古城墙上吹埙的思古幽情及其艺术效果的鬼气阴森,深夜梦游用再生人钥匙开竹巴街七号门而不成等,再加之诸如七月十七西京小鬼节,用黄裤带可禳灾免祸和纷繁的衣食住行等民俗文化的铺陈,就与目连戏的事象被有机地合成一个晶莹而通透的艺术整体,一个民俗性与神秘性的整体。在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世界中,生活正是如此现实而神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风俗和神秘中。透过《白夜》的民俗和神秘性悲剧的表层,我们能体悟到作家的外冷内热的生命真诚,这种生命热度又赋予了笔下的挣扎于时代和环境中的城市平民,同时也让我们倾听到那来自地壳深处的隆隆律动。
三、 佛理贯穿《白夜》增加神秘色彩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创作心态 身体 痛苦
在学校里,他因为矮小与孱弱在上体育课时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喜欢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不被人重视,愈是躲人;恶性循环,如此而已”。甚至,已成名的贾平凹在1987年回忆15年前进入西北大学时的情形仍说:“这是一个十分孱弱的生命,梦幻般的机遇并没有使他发狂,巨大的忧郁和孤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睁眼看世界。”此时的他仍对自己体力的孱弱非常敏感,在他的意识里,孱弱似乎已成为一种生理上的缺陷。
也因为病,贾平凹观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变得有些失常。以肝病之体验,醒悟到社会上人人皆病。别人之病虽不在身体,却在精神,在相互之间的关系隔膜;由玩牌悟到不是人玩牌,实则是牌在玩人;从对弈的文化记录又指出其不是比较技艺之高下而是斗智斗心。这些“病人的视角”于生活可能有些偏激,纯属个人之见,但于艺术却未必不能算一个独特的视角。在长篇《废都》的结尾,贾平凹把庄之蝶的下场设计为中风而不是猝死,这实际上就为后来的《白夜》留下一个很好的视角,所谓“病而不死”的角度。田珍颖说:“也许你是顺乎‘天地早有了的’安排了庄之蝶的命运,而我却觉得,这是你嚼透了庄之蝶们的心迹,嚼出了味道,于是也写出了味道——让他中风的味道,让他病而不死的味道。如果庄之蝶还会出现在你今后的哪篇小说中,他将是何种现象呢?你会让他怎样地中风却活着,活着却中风?我想,恐怕他会变成你新作品中的一个角度——奇特的角度,你将通过他的双眼,静静地、冷峻地看着繁华喧闹的人生,沉默却犀利地剖开眼前每一个人的五脏六腑。”
这个角度后来出现在废都的续篇《白夜》中,这就是祝一鹤的中风。的确,通过一个曾经有权有势的人忽然失势丢权的突发事件,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可自然显示。以往求他办事的人,得到好处的人现在一个个再不登门,而真正照顾他的却是那些最下层的普通人,在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中华民族有恩必报的美德。特别是在这篇小说中他以病态的眼光看出了全社会的种种病症。夜郎的梦游症和多疑症,祝一鹤的痴呆,虞白的贫血,宽哥的牛皮癣。连天也在生病,那雪花正如宽哥的牛皮癣,不是在脱皮?“真是怪事,白姐这回犯病,什么都觉得丑着好。说这桌子腿儿太细应该做一件憨憨笨笨的?”“什么都丑着好”的审美观点实际上早己渗透在贾平凹的所有观念以及日常生活中。如他收藏的石头,他的家具就连他给作品起的名字也都要憨憨的。另外,他把农村人的孤陋寡闻、自卑等也作为一种优点大加赞美:这一切无不体现了“病人的心态”。
他在作品中勇敢地坦露内心痛苦,又用轻松诙谐的笔调抒写出用痛苦咀嚼出来的人生别一种滋味,作家也会有难言的痛苦,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往往使人抑郁忧戚,苦闷悲愤。贾平凹经历了数年不愈的疾病的折磨。这种病简直如毒蛇似恶魔,使人谈病色变,把患者抛入孤独的深渊。于是他写了《人病》一文。人一旦患了此病,便“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一句不经意的自嘲,带着对历史的难忘和批判)”。尽管患病使作家原本复杂的生活一下子清静起来,“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地孤独和寂寞”。“唯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为了家人的健康,作家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把生活圈子缩小到最狭小的范围”。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泡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泡的、蒸熏的是我的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了。作家把自己焦虑、恐惧、失望的心情向读者暴露无疑,一种渴望关爱和救助的心声发于衷肠。然而使作家痛苦不堪的更为残酷的事实是骤变的人情!朋友和熟人的冷遇,使他自怨自艾又愤遗不已,这愤怒中包含了对社会冷暖的真切感受和强烈讽刺。在病院——“这个监狱似的天地里”,作家很快获得了新的生活,获得了在特殊环境中的一种人生体验:“我们失却了社会上所谓人的意义。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兴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带着讥讽和斥责歌颂了病院生活之后,作家又不无幽默地道出对疾病实质的独特发现:“或许,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方结合的,病便是灵魂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契合出了问题,灵魂已不能领导了肉体所(下转第11页)
(上接第9页)
致,一切都明白了吧,生出难受的病来。原来是灵魂与天地自然在作微调哩!”从作家身上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被痛苦久久地困扰,四顾无助之时,就必须从自身的信念中寻找解脱的途径,求得真正的“精神胜利法”,作《说生病》一文中,贾平凹又深有感触地慨叹道:“生病到了这个份上,真是人生难得生病,西施那么美,林妹妹那么好,全是生病生出了境界。若活着没生个病,多贫穷而缺憾,佛不在西天和经卷,佛不在深山寺庙里,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生病只要不死,就要生出个现实的活佛是你的。”看似无奈中的自嘲其实是以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人的主体意识——拯救生命,把握命运。这是作家对“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是对处于困境中的自我审视的思想升华。
贾平凹渴望精神的乐土,可对于现实,作家也无能为力,只能把宣泄体验渗透在不同风格的作品中,表面上看来是如此颓废、消极的情绪里。深藏在它的反面,是对生命的渴求和关注、对生活的执著。他永远都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意识和强烈进取精神的人。或许,他已经开始自己精神的漫游。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闲澹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2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杜,1992
3 高觉敷.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废都就是废都.关于废都的一些话.第1版.陕西日报,1993-7-17
5 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6 邰科祥.贾平凹的内心世界.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
7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8 张志忠.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2.4
9 黄志刚.论贾平凹小说乡土情节的发生发展.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2003.2
10 杨光祖.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文化心态论.社会纵横,
2003.5
11 叶君等.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现当代文学
评论,2004.1
12 王一燕.说家园乡情 谈国族身份.当代作家评论,2003.2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散文 气韵 古朴 和谐 悟 苦 恋
贾平凹从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发表散文,每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他在90年代中期以前的创作展现出他的既细腻又粗犷、既童心又通透的特点,作品中充盈着一种空灵静虚之美。内在的悲悯之心使他目光触及之家乡的人、物、事多呈现出一种古朴的和谐,多描写粗犷荒芜的西北生活,浸润的却有南方的温润灵巧。从这个时期他的散文的内在气韵上体察,大致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悟、苦和恋。
一.悟
贾平凹的散文中常见“悟”,且是“顿悟”,于常物常理中见出不同,如《丑石》末尾感受到的丑石的伟大,继而“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1]《静虚村记》中对“静”之悟,《观沙砾记》记中对小小的沙粒之悟,“世上什么东西生存,只有到了它生存的自然职工中,才见其活力,见其本色,见其生命,见其价值。”[2]
贾平凹尤喜月亮,认为月亮“是佛性的圆满,是了悟的透彻”,以《月迹》为题的散文集三十余篇散文中月亮成为主角。他把佛禅的理趣融化到对自然物象的觉悟之中,角度精准细微,异于常人,在顿悟中发现自然万象的禅趣,显示出特殊的格调。
二.苦
贾平凹出身于“深谷野凹”中的贫寒家庭,贫穷始终伴随着他的成长,一直到他工作多年后才慢慢发生改变。贾平凹在散文中不止一次地谈到父母在抚养自己和操持家庭时所受的苦,这种苦味弥散于他的心绪中,浓得化不开,如《读书示小妹生日书》中无钱读书之苦、《喝酒》中父亲担心儿子被流言所累之苦、《祭父》和《我不是个好儿子》中细数父母亲一辈子的劳苦和人生连绵的苦难境地,让人读之动容。
他的苦还来自于自己身体所患之肝病,《人病》中对那种因患病而被无辜歧视之苦和因患病不得亲近家人,自设障碍之苦写得极为细琐。
三.恋
从写对童年的回忆到写所寻访的关中乡镇,贾平凹显示出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如在《秦腔》《入川小记》和“商州三录”中显示的天人合一的和谐人间,古朴木讷的商山人甘于“洋芋糁子疙瘩火“的生活,并自诩这种生活“除了神仙就是我”,他们喝“包谷糊汤”,吃“搅团土豆“却自得其乐,优哉游哉。《通渭人家》中写连“火车都在说”――“穷,穷,穷,穷……”的甘肃通渭人家,吃水困难,无畜饮之水,不能用净水洗衣擦澡,但他们却一点不嫌弃自己的家乡,于待人接物中显示出他们“精神的高贵”,这一切使作者在离开通渭时已暗下再次来访的决心。
贾平凹所恋的是一种原初古朴的桃源式的乡村生活,他尽力追寻这种田园生活,《静虚村记》中避闹市而至“风止月瞑,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的“静虚村”,他可以“静静地坐地,静静地思想,静静地作文”。即使是写城市,也常写有保持了乡村特点的城市的小街小巷,如《五味巷》、《河南巷小识》等。
小说和散文构成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两翼,互为影响。199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废都》也给他的个人生活和处世态度都带来了非常大的甚至“灾难”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开始反映在他的散文中,并使他的散文逐渐从前期散文的追求空灵虚静的审美境界,以禅宗妙悟安抚内心转向了后期的灵魂焦躁,心灵的驳杂矛盾。这时期他创作出了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散文,如《说房子》《说女人》《说美容》《说打扮》《说花钱》《说奉承》《说孩子》《闲人》《忙人》《人病》《名人》等等。他写出了城市生活的种种怪诞病态,表达了对城市的疏离甚至厌恶。这些文章有精锐的感觉,能观常人所障,言常人所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国民劣根性的内容,但常顾影自怜地纠结于琐屑的事情,絮叨中显油滑,缺乏厚重感和透彻性,让人读来只感受到现代人生活和生存的逼仄和压抑。这类作品缺乏前期作品中宽容和仁厚,有时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个体的尊重。
对于前后风格的转变,贾平凹自己做了这样的解释:“生命个体在每个时间段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如草木在四季的变化。早期的散文写得清丽,有冲动,现在我写不了了,也不再想那样写了。五十岁的人经世已多,心态要紧是从容平和,所写虽混沌,但都是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能贯通世事的就是智慧,智慧在家常中、口语中。”[3]
90年代中后期的贾平凹在创作中显示了与城市和现代人的隔阂,城市和现代性本来可以成为他创作的一个生长点,可是他却摈弃了这个生长点,带来创作的局限与狭隘。
注 释:
[1]贾平凹著 《贾平凹散文选》第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贾平凹著 《贾平凹散文选》第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25页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5篇
>> 须一瓜中短篇小说的人性审视 论德莱塞小说中的人性美 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人性残缺美 欧・亨利小说中的人性主题 须一瓜小说的音乐性悲剧 论农村题材小说中人性的回归 论辛格小说中人性、信仰的重建 论鲁迅小说中的人名艺术 论新写实小说中的人文关怀 探讨霍桑小说中的人性和人的命运 从民俗视角看郭文斌小说中的人性美 须一瓜推出长篇小说《别人》 论迟子建小说悲悯的人性抒写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 人性美的张扬:论贾平凹商州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 浅谈小说中的人物鉴赏 约翰・拉贝:“中国辛德勒”的人性拷问 评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人性拷问 《圣殇》:拷问最深层的人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06年4月24日。
[5]黄灿然译,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同时:苏珊・桑塔格随笔与演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3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授奖词[N].南方都市报,2004-4-18.
[2]冯敏.无法回避的诘问[J].小说选刊,2003,(7).
[3]孟繁华.都市深处的魔咒与魅力――评须一瓜的小说创作[J].时代文学,2013,(9).
[4]须一瓜.我希望小说像把手术刀,2006-4-24.
[5]黄灿然译,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A].苏珊・桑塔格.同时:苏珊・桑塔格随笔与演说[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6]须一瓜.太阳黑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