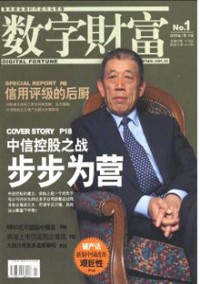数字反哺助推代际传播可持续发展浅析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数字反哺助推代际传播可持续发展浅析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家庭场域内子代青少年与亲代长辈对新媒体技术在理解、接纳与使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两者在代际交往与互动中形成明显的数字代沟。与此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消弭数字代沟的数字反哺行为在家庭场域中愈加普遍,并在创新扩散机制的作用下,子代实施的数字教辅行为促进了亲代在对数字技术的了解中产生兴趣,给予自我判断,使亲代最终在试验和采纳中强化自身的数字化生存能力。
关键词:代际传播;家庭场域;数字反哺;数字代沟
伴随着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化,社会在逐步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的结构转型。这些转型映射于家庭场域,则是亲代(父辈和祖辈)和子代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文化喜好的选择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或隔阂。此外,依托新媒介技术的迭代发展而诞生的一种主流生活模式(即数字化生存),更是加剧着亲代与子代间的差距。譬如他们各自的手机上网技能、智能手机的掌握和使用程度,以及对互联网繁杂信息认知度等的不同,都会造成家庭场域代际交往与互动中存在明显的数字代沟。与此同时,家庭场域内的数字反哺行为悄然而起(即由子代承担着教授新媒介知识的角色,让亲代更加了解和使用新媒介),并且以创新扩散机制努力缩小数字代沟,增强亲代的数字化生存能力。
一、数字反哺的由来及概念
数字反哺由于被看作文化反哺在数字技术及其使用上的行为表现,因此在探讨其概念内涵前,应追溯文化反哺的定义。文化反哺又称为“青少年反向社会化”,国外部分学者曾对此展开大量研究,且取得了相应成果。比如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提出了代际存在反向传承的可能,即在社会动力机制的力量驱动下,年老一代因受社会动力机制的力量作用,会越来越接受来自年轻一代的影响①。20世纪7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又提出了社会文化的传递方式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或称互喻文化)与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指的是亲代授予子代知识,并喻文化指的是向同辈人学习,后喻文化指的是亲代反过来向子代学习②。而我国文化反哺概念的出现是在1988年,由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在《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一文中提出。2000年,周晓虹教授又用“文化反哺”这一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观测家庭场域的亲代与子代,并发现父母极易受到子女包括价值观、消费观和审美观、日常生活行为方式、新科技及新潮流等方面的影响③。由此可知,数字反哺作为文化反哺的新形态,主要指数字时代的子代青少年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亲代长辈进行的教辅行为。
二、数字反哺机制形成的原因
(一)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亲代需求痛点
自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持续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也愈加暴露出老年群体在数字化生存中存在的极大的需求痛点。对此,深圳大学周裕琼教授给予相关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信息接触到筛选,从信息认知、态度到行动措施,中国家庭祖孙三代在新媒体获取、评估与分享健康信息方面均存在显著的数字代沟。尤其是疫情暴发初期,部分亲代因有限地触及数字媒介而对疫情防控信息知之甚少,在与子代发生诸如“新冠肺炎多么严重”“要不要戴口罩”等冲突中,表现出“不重视、不听劝”的态度。这也暴露出老年群体的数字化信息素养存在严重匮乏。而且,在各地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提前布防、快速行动以及核验健康码等举措为精准防控疫情提供了强大助力。在疫情抑制实体经济的大环境下,网络电商再掀热潮,部分线下活动及经济交易向线上转移。尤其是在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网络文娱和在线医疗等模式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老年群体的常规化生活模式被打破,他们在健康码、手机点餐、线上支付等数字化挑战中陷入了生存困境,进而被动地对数字技能产生强烈的诉求。
(二)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相互依存和制约
网络社会和新媒介技术的变革,在触发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变革的同时,也为人们的数字化生存提供了契机。但是,亲代中的父辈及祖辈由于成长期缺乏数字工具的陪伴,与身为数字原住民的子代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文化喜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和隔阂,以致在数字化生存中出现代际互动的沟壑。而代际传播及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促使文化反哺在数字化时代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即作为亲代最为紧密的接触者,子代充分利用数字原住民的角色优势,对有着数字生存融入需求的亲代进行新媒介技术及文化的反哺,进而消弭家庭代际互动的沟壑,让全民畅享的数字中国成为现实。
(三)家庭场域提供了实践空间
何为“场域”?它由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属于社会学理论———场域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并且,一个场域可以被界定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形构。往深一步说,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实践空间,其中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又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④。而家庭场域,毋庸置疑,有别于其他组织团体,并专属于家庭成员进行相互实践的空间。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及家庭观念中,“天伦之乐”往往是人最强烈而有意义的体验。亲代和子代共同生活在家庭场域的现实,恰为数字代沟下的子代对亲代实施数字反哺行为提供了实践空间。此外,伴随着数字时代下后喻文化的兴起,当前数字化生存模式的大众化在消解传统的“天伦之乐”图景的同时,也在重构着新型的“天伦之乐”的家庭价值观,即家庭场域中的亲代(尤其是祖辈)在意愿和兴趣的内驱下,虚心向子代学习新媒介技能及其文化,进而从自我的数字化融入困境中脱离,享受数字化生存的红利。而且家庭场域中的数字反哺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类技术和文化视角下的“创新与扩散”过程,需要家庭为子代和亲代展开反哺实践行为提供场域基础。
(四)被反哺者的需求与反哺者意识契合
美国心理学专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H.Maslow)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行为科学理论之一的需求层次理论,即将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⑤。其中,爱与归属的需求在人的心理需求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通过对中国知网有关数字反哺的实证文献的梳理得知,数字时代的被反哺者(尤其是祖辈)对情感的渴望及需求远远强烈于子代。这主要是祖辈由于年龄的增长而出现身体机能的衰退,并逐渐缩小了活动范围,以致家人和朋友成为其主要交往对象。因此,情感交流与信息需求的获取显然成为祖辈消除内心不确定因素的一剂良药。这也进一步说明,祖辈作为被反哺者,在数字反哺下实现借助新媒体与子代进行交流互动的同时,也得到了情感需求上的极大满足。为此,数字反哺的实践行为只有建立在亲代,尤其是祖辈的需求与子代的意识契合时,效果才能实现最佳。
三、数字反哺机制形成的路径
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于20世纪60年代在《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该理论认为,劝服他人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须经历了解、兴趣、评估、试验和采纳五个阶段⑥。此外,这五个阶段与家庭场域中的数字反哺实践行为相联系,因此,可以以此研究子代和亲代展开数字反哺的状况,进而探寻在反哺过程中亲代对数字媒介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的路径。
(一)了解阶段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贫困地区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得益于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行动持续推进,老年群体连网、上网、用网的需求活力进一步激发。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43.2%⑦。当前亲代,尤其是祖辈型的亲代,容易在艰难的数字化生存中产生互联网焦虑。他们逐渐接触并试图了解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即新媒介技术及其文化,以期适应社会与文化的深度媒介化。在了解阶段,大众传播的大量宣传及人际关系的广泛沟通等共同作用于数字信息,从而引起潜在用户即亲代的注意,促使他们接触新媒介技术这一新生事物,但由于他们并非互联网原住民,故知之甚少。在他们尝试了解新媒介之前,由于受个体特质(如对社会变动的一般态度)及社会体系规范等的影响而形成了自我的认知储备,进而以一种习惯的方式指引着他们了解新媒介的相关信息。
(二)兴趣阶段
早在20世纪40年代,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ld)等人进行的IPP指数研究就表明,受众的群体背景或者社会背景是决定其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的重要因素⑧。依存于传统媒体环境而成长的亲代,在以移动互联网及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生存环境的压迫下,会在选择性接触新媒介技术及其文化的过程中感知其所带来的生活便利,进而意识到数字时代的自我需求,产生了主动使用新媒介的兴趣。正是亲代这种对自我需求的认知程度,为子代的数字反哺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意愿产生和兴趣培养中,亲代有着对数字时代更为准确的自我角色认知,进而也暴露出兴趣与意愿驱动下的数字时代短板,即数字产品的短缺,致使亲代在评估阶段出现多种态度。
(三)评估阶段
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曾在《制码/解码》一文中提出受众解读媒介讯息时可能出现的三种立场,并称为“三个假象的解码立场”,分别是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抗立场⑨。针对子代的数字反哺行为,亲代会结合自身的需求偏向,比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数字产品采取不同的评估态度或称解码立场,进而影响着家庭场域内的代际互动成效。其新闻与传播中,若亲代对于子代的数字教辅行为采取的是主导—霸权的解码立场,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家庭场域中数字反哺行动的顺利开展。反之,亲代若采取的是对抗解码立场,子代可能会迅速终止反哺过程,造成代际互动的失效,亦称反哺阻抗。为此,虽然数字反哺已作为消弭家庭数字代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是消弭的程度如何,关键在于亲代,尤其是亲代中的祖辈,是否已对数字时代的到来有着更为确切的认知,并且在意愿和兴趣的驱动中理性探寻和评估符合自我意愿和兴趣的数字产品,以促进反哺环节的深化。
(四)试验阶段
试验阶段中的亲代,在子代给予的数字教辅行为实践过程中,会基于自我需求,对依托于新媒介技术生成的数字产品进行试验性的观察,而后主动将自我的想法和需求融入具体的数字反哺实践环节中。值得注意的是,亲代由于个体的生理、心理、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成长背景的差异,也会在数字产品体验所带来的情感和欲求上存在差异。例如,伴随着数字社会发展的加速,传统生活方式在向数字化生活转向的同时,也致使相当一部分的老年群体无法适应支付方式和购物渠道的革新,进而迫使他们在产生互联网焦虑的同时,对生活需求的满足有着更为迫切的渴望。再如,当前实证研究发现,老年人普遍有着情感、社交、文娱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老年人迫切需要一款能够表达自我情感、满足社交意愿、实现自我价值的数字产品,而短视频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诉求。
(五)采纳阶段
在亲代采纳子代数字反哺成果阶段,即掌握新媒介技术的基本使用功能和文化属性时,他们的行为则可能出现两种走势:一是在数字产品满足他们需求偏向的同时,助推其产品扩散至更为广泛的群体;二是亲代对于数字产品的需求仅限于对基本使用功能的掌握,进而终止被反哺。针对第一种走势,将会出现更为广泛的创新与扩散的新媒介使用景象,比如当前银发网红在体育、时尚、美食、娱乐、教育等方面崭露头角。而针对第二种走势,势必会将反哺的内涵局限在新媒介技术的器物层面,导致数字理念层面的反哺流于表面,不利于新媒介技术和新媒介文化的创新扩散。
四、结语
以代际传播的视角关注和探讨家庭场域中的数字反哺实践行为,主要是因为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存在相互依存及制约的关系,家庭场域为数字反哺提供了实践空间,被反哺者的需求与反哺者意识契合。此外,正是数字反哺行为的作用,才促使家庭权力的主体从单向过渡为双向,亲代在享受数字化生存红利的同时也增强了子代的家庭话语权,进而促进了家庭关系的代际和谐。同时,作为代际沟通在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最新演绎,数字代沟在数字反哺中得到消减。数字反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数字代沟而造成的社会压力,丰富了家庭和谐的内涵。
作者:彭水婷 严家秀 谢爱民 单位:江西科技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