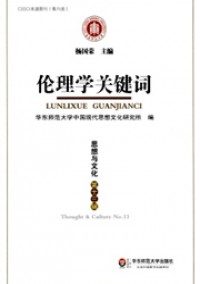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国哲学论文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国哲学论文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本真意义与现代转换的关系
与其他专业相比,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具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即很强的现实性。然而,中国哲学史却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形态,因此,历史上各个哲学家之思想的本真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针对现实感极强的思政专业大学生而言,“中国哲学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对历史上各家哲学思想的本真意义进行适度的现代转换,否则,该门课程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学生因为它只是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产生一定程度的隔膜感。问题在于如何进行适度的现代转换?我们认为现代转换的前提是真正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家之哲学思想的原始意义,通晓其本真精神。达到这个目标,要求课程讲授者首先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一个还原化的工作,即对历史上哲人的思想进行反观、还原,最大限度地接近其所思、所想、所欲、所求。而这需要课程讲授者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事实上,在了解哲学家之哲学思想的本真意义之前,所展开的所谓现代转换工作是缺乏根基的,由此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现代转换。本真意义指向历史本身,保证的是历史的延续性;现代转换指向的是当代社会,强调的是历史的变异性。两种工作同等重要。因为没有变异的中国哲学史缺乏现代眼光,其优良传统因此会陷于故步自封而失去现实性;而没有延续的中国哲学史忽视中国哲学本性,其现代转换也难以令国人从心底接受。举例来说,讲到孔子之“和”的观念时,在课堂中就可以与当代的和谐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而谈及孔子的和谐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和谐并不排斥差异,而是必须以之为前提;他讲“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则可视为以礼乐为和谐的外在制度安排;他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以看作仁德为和谐的内在道德理性。[3]这种讲法,既可以使学生看到中国哲学史上孔子的原本思想面貌,又不至于使他们感到其思想只存在于古代,而缺乏对其现代意义的感受。事实上,一定程度的现代转换也是中国哲学向前发展的必然路径。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在历史上主要是以经学形态存在的,而中国哲学史却是以近代意义的哲学形态登场。经学与哲学虽然存在交集,但是一为古、一为今的二者之间的张力也是天然本具。消解此种张力,无疑也需要处理好本真意义和现代转换的关系。
二、信仰与知识的关系
作为中国哲学史之主干的儒学,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就成为中国人行为处事的指导思想,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宋明理学产生后,儒学更是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中国古人的信仰所在,直到晚清,康有为仍然大呼立孔为教,即昭示了这一信仰在中国曾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后,除少数现代新儒家中的人物,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儒学已经不再是信仰,而转变为一种历史知识。那么,当代社会是否有信仰教育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质上就是一种信仰教育。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通过教育的途径灌输给学生,使之从知晓与理解到认同与接受,然后升华为信念信仰,最后化为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毋庸讳言,当代大学生处于极度的信仰危机中,他们大多把信仰概念过度狭隘化,从而简单地视之为宗教行为,而不能理解精神追求也是信仰的一种,由此造成信仰缺失,甚至反感精神信仰的灌输。在这种形势下,思想政治的信仰教育,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等,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为思政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就要摆正曾经是信仰而今已是知识的儒学与当代国人的信仰对象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诚然,儒学的一些观念是国人挥之不去也没必要完全去除的,但不能因此在课堂上教唆学生放弃当代信仰对象马克思主义、背弃党和政府,那样做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会导致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严重后果。
三、继承与批判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其中某些思想成分就不见得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要求。因而,我们要尊重历史辩证发展的事实,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既不颂古非今也不是颂今非古,因为这些都是片面、不科学、不正确地对待传统的态度。我们要与时俱进,对中国哲学史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1940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他提出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一般原则,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哲学史的批判和继承。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落后的思想糟粕,譬如男尊女卑、官本位、三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等,这些观念我们要剔除。中国哲学史上也有很多普遍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思想精华,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等,这些观念则需要我们继承,其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全球伦理原则。不止于此,即使对于我们认为需要加以剔除的思想观念,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这三纲,学界也存在着是继承还是抛弃的不同看法。早在激烈批判儒学的1940年代,贺麟先生就“发现了”三纲“与西洋正宗的高深的伦理思想和与西洋向前进展向外扩充的近代精神相符合的地方”。当代学者方朝晖先生则揭橥维护三纲的本义为“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但这一提法受到了李存山先生的质疑,他认为三纲的本义是“‘皆取诸阴阳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义的关系”。从这些争论来看,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都不能视之为一种单方面的行动,我们需要从批判中继承、从继承中批判地辩证思维。总之,鉴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特殊性,为其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至少需要顾及政治性与学术性、本真意义与现代转换、信仰与知识、批判与继承四个方面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教学效果,而且关系到国家思想稳定的大局。
作者:曹树明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