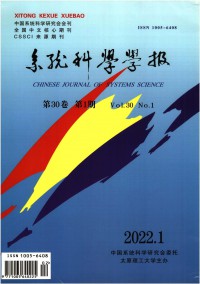辩证关节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辩证关节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关键词】/功过评价/方法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4-0025-07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立者、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者。他的历史功勋卓著、思想影响深远。但是,在晚年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是发动了被称为“”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会动乱,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评价的功过是非,已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有鉴于此,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共中央于1981年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20年实践的检验,证明《决议》对作出的评价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决议》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党内对的认识就已经基本统一了,更不能说社会上、海内外人士都赞同《决议》的观点。本文认为:党内、国内对功过的评价之所以存在着争论,有其复杂的原因,但评价时方法论的不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想提出几个重大的辩证关节问题加以讨论,试图揭开对功过评价的分歧之谜。
一、关于“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
把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奋斗历程概括为两次革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对应地说,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在建国以后引导我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是第一次革命了。在党的十四大上,对这两次革命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注:《中共中央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由此可见,两次革命是历史地联系着的。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它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但没有被否定,相反,得到了坚持和发展;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深入,它要解决第一次革命没有解决好的体制创新问题。如果没有第一次革命,就无所谓第二次革命,而如果没有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不但不能巩固,还将毁于一旦。只有这样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我们才能对功大于过的历史地位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计。
现在党内外、海内外、国内外否定的历史地位或认定过大于功的人,他们同我们党的分歧,主要不在于对“”的评价,我们党对“”也是彻底否定的;也不在于对“”等“左”倾错误的评价,我们党对“”、对自身的“左”倾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而主要在于他们对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随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伟大成就取漠视以至否定的态度。所谓“漠视”,就是在评价时不谈他对第一次革命的卓越领导;所谓“否定”,就是不承认那一次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甚至根本不承认那是一场革命。对于这些人说来,谈的功劳、谈他的功如何大于过,是根本谈不通的。对于蒋氏父子,能谈通吗?谈不通。他们是反共的,自然会根本否定。对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能谈通吗?也谈不通。他们根本不承认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当然无从肯定的功大于过。对于现在力图走“全盘西化”道路的人,能谈通吗?还是谈不通。为了证明中国必须走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他们就得从根本上否定当年领导人民所走的道路。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受过“左”的错误路线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上面所说的反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是善良的,同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主张取一致态度。他们受到晚年错误的严重损害,对晚年错误感受极深;同时,他们对领导人民革命的伟大功勋只有书本上的知识,缺乏像解放以前的工人、贫农和跟随打天下的老同志那样的切肤之感。二者相比,他们对持比较或过分严厉的态度就不奇怪了。
在科学认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关系,从而正确评价功过的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在理论认识或者思想感情上都为全党、也为人民作出了榜样。邓小平在理念上充分肯定领导第一次革命的盖世伟功,认为“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邓小平在感情上不受他在“”中两次被错误批判遭到严重伤害的影响,与广大普通百姓包括工人、农民、战士同其爱憎喜忧。他语重心长地说到:“对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页。)陈云在评价的问题上同邓小平有一样清醒的理念和诚挚的感情。他充分意识到,肯定在建国前28年历史中的伟大贡献对于全面评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说:“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被概括得更全面。”(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谈的功绩及其影响,对于我们教育至深。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上面所说的“第一次革命”包括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其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二是“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革命。对于这后一个阶段的革命,存在着更多的争论。全国解放以后,从1949年到1952年,我们经过了一个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同时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和巩固新生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斗争,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1953年6至8月,提出了“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对于这条总路线和它实行的结果,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总结。《决议》写道:“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注:《中共中央文献汇编》,第47~49页。)。
改革开放深入展开以后,许多人对上述《决议》所作的判断提出了异议。从感性经验层面来谈,人们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日——我们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初——我们何苦要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呢?从理性思维层面来论,人们援引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论点:“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而在1953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比1945年多了多少,为什么就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
本文认为:评价47年前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知其当初”,方能作出合理的判断。离开历史条件,抽象地讨论问题,要求那时就“早知今日”,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现代决策科学告诉我们:一项科学决策,一是来源于对客观环境的正确分析,二是来源于主体对价值要求的清醒自省,二者结合,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就产生应做而又可行的决策。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而言,客观环境是什么呢?一方面,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侵略,国内旧政权的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不断挑战(“三反”、“五反”中揭露出来的“五毒”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迫使党不能不考虑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一旦有了这种主体地位,我国也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农村中之后生长起越来越多的合作组织,已经显示出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逐步过渡的趋势。这就说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因时之需,因势利导。当时的主体价值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刚刚翻身解放的工人、农民要求迅速发展经济、要求做生产关系的主人。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世代受苦、现已摆脱了剥削的工人、农民;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单位中工作的工人,都向往着像国有企业中的工人那样做企业的主人翁,而一部分生产条件不足的贫苦农民确有组织起来的积极要求。对于这样的价值要求,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的制约性,盲目加以追求,就会作出错误决策;但如果同时考虑可行性,那就具备了作出科学决策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基本前提。
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但是当时条件下作出的大体正确的决策,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第一,它以国家工业化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相应地逐步改造社会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