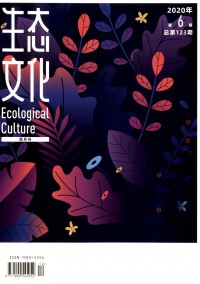生态法本位思想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生态法本位思想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与环境法的社会本位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从环境法的社会本位到生态法的生态本位势在必然,提出生态法生态本位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出发点、人类认识的发展趋势以及终极目标上,同时生态本位的提出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生态法;生态本位;理论基础;意义
一、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的提出
(一)生态法的界定
埃·海克尔(Haeckel)于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20世纪70年代初,它被引入社会领域,发展成为研究“社会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①]前苏联环境法学者们试图从生态学和法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重新考察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这一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从而为生态法的产生提供了生态科学的依据。后来,“生态法”这一词汇在前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法学界被广泛使用,人们用它作为环境法这一法律部门、法学学科和教学课程的名称。现在,“生态法”一词已经成为俄罗斯联邦法律科学领域里的一个专有名词或专门用语,全面取代了环境法、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名词。同时,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以及东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也大量地使用这一词汇。在这些国家的有关研究文献和教科书中,“生态法”一词也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专门用语。[②]
“生态法”一词在我国也逐渐引了起环境法学者的广泛关注。马骧聪教授在《俄罗斯联邦的生态法学研究》[③]一文中认为“生态法学的提出有其客观的基础和重大的学术及实践意义”。他把生态法或生态保护法定义为:“调整在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生态系统过程中所发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生态保护法以围绕生态因子形成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注重生态价值,以生态规律为核心形成统一的生态法律原则。生态保护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范围涉及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国土法以及其他法律部门中的生态规范。”[④]肖乾刚教授认为,“应该把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国土整治法结合为一体,称为‘生态法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⑤]曹明德教授认为:“生态法在生产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等方面均与传统的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环境资源法存在着重大差异。生态法的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把传统的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环境资源法统一到一个部门法中去,结束其各自为阵的局面”。[⑥]他还指出:“生态法是为了达到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并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调整人们在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人和法人的生态权利及合法利益方面所产生的生态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⑦]刘文燕等认为,“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完成人类在调控生态关系中所负的责任,就必须对生态价值观和生态社会调控机制进行一场根本的变革。这场变革表现在法律领域,有必要促进生态规律和法律规范的结合,建立起生态法学体系。”[⑧]上述对生态法涵义的界定,为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二)从环境法的社会本位到生态法的生态本位
王伯倚先生认为,法律本位乃指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按照目前理论界的观点,对于环境法的归属有两种观点,一是主流观点认为应归属于经济法的范畴,而经济法的本位主流观点又是社会本位。[⑨]二是认为应归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其本位当然的是社会本位。[⑩]
吕忠梅认为环境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11]其内容有两个方面:环境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环境安全(包括生产技术性安全和社会政治性环境安全)以满足环境法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可持续发展来维护社会整体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公平)。[12]该观点尽管兼顾环境利益,实质上仍是以人类己私为出发点,实质上是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陈泉生教授把环境法的本位总结为单本位或多元本位[13]。李艳芳认为是社会责任本位[14]。他们的理论基点是“法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忽视或者说尚未来得及把调整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环境法纳入自己的视野。
但是,我们也欣喜地发现,也有人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环境法纳入新的视野,为生态法提出生态本位做了铺垫。郑少华指出,“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法,与世界大多数国际一样,仍停留在社会法之范畴内,从目前的趋势看,似有不妥,应构筑一套环境保护体系,以因应生态环境危机。”[15]汪劲认为,环境法的目的是立法者通过环境立法表达的,为实现代际人类的权利及其利益,保护生物圈的共同利益的思想和需求。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了人类健康目的而保护环境;二是衡平代际人类的权利及其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保护人类的环境权与认同自然内在价值及其权利。[16]这种观点是针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值观向“生态利益中心”转变的现实而作出的一种回应,并认为生态利益中心是最终方向。范连星也主张环境法应以人类和环境利益为本位,并且将环境利益置于优先地位。[17]
总之,环境法的社会本位强调“人类利益”至上,主张以人类为中心,在立法上把自然界及其生物作为权利客体,即使法律规定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也是着眼于人类的功利主义立场,这最终导致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所以,提出生态本位势在必然。
二、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的理论基础
与传统的环境法相区别,生态法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其出发点、对生态伦理人类认识的发展趋势以及其终极目标三个方面。蔡守秋教授认为:“生态法与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或者环境自资源的区别,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提法上不同,而且存在内容上的、立法目的和理念上的差别,其价值取向、内在旨趣及其哲学和伦理学、生态经济学基础亦存在诸多的差异。”[18]
(一)从生态法的出发点看生态法的生态本位。
首先,生态法将人内化到生态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来考虑。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首先是自然的人,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员。当然,人也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是社会的生命物种。因此,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不同,就是人生活在两个世界: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前者是体现了人的自然生态特征,是反映人的自然属性;后者是体现人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反映人的社会属性。在这里,生态法把人的自然属性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其认为因为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就参与着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分享并传递着系统中的信息流。人类及其组织起来的社会持续不断地获取着自己生存、发展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同样,人类作为一个自为的存在,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自觉地遵循生态规律,并对生态系统良性运行施加自己有益的影响。人类只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他与非人类的自然物之间具有平等的天赋价值,这种平等的天赋价值赋予了他们之间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
其次,生态本位承认自然有其特殊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价值。按照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哲学传统理论,从主(人)客(自然)体价值关系模式出发,在总体上把价值规定为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将价值的来源完全归于人的主体性,他们主张把价值范畴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极力反对把它扩展到自然界,否认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价值,尤其是完全否定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由此推导出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的结论。与此相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论者认为,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迫使我们必须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非人自然的价值,主张把价值范畴由人的世界范围扩展到非人自然的世界范围,涵盖整个自在世界即整个系统;尤其是要承认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建立完整的自然生态价值理论。自然价值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杰出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在实践中,环境理论学的根本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在理论上,它的根本要求是确定意义深远的价值理论,以此为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自然界的价值,不仅仅是对人类需要和利益的满足,而且包括对一切地球上的生物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以及对地球生物圈系统整体的完善和健全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生态本位思想不仅强调自然为人类服务,同时,也重视自然本身的存在与发展;不仅考虑人类的利益,也考虑其他生物的利益。这就是两种价值观的区别。
再次,生态本位强调以生态为中心,以生态利益为本位,强调自然本身也是享有权利。深层生态学的观点的一个基本伦理规范,就是每一种非人类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理由人类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它生命。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权利的基础是“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生物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物种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而,人类必须把所有的生命物种都视为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的实体。生态整体主义认为,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生命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人类不仅要尊重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其它生命物种;而且要尊重这个共同体本身。毕竟大自然作为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其后来的加入者之一,自然不应仅仅是人的权利客体与价值评价对象,而具有其独立的权利与价值。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态本位法律观要求法律制度应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精心设计,既要体现人的权利,也要反映生态自然的权利。
(二)从人类对生态伦理认识的发展趋势看生态法的生态本位
人类关于生态伦理的观念经历了由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到非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c)的发展过程。生态法的产生,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出现密切相关,他为生态法提供了伦理学基础[19]。
首先,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的生态伦理观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人而且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他存在物都没有内在价值而只具有工具价值。[20]至于大自然,他们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它们不能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人类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义务,人们保护环境资源的义务是对他人所负的间接义务,环境本身没有价值、利益,环境价值、利益是人的价值、利益的折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主宰自然,无视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基础上,具有明显的“反自然”性质。
其次,非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c)伦理观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抨击。当代生态主义者批评人类中心主义者为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Speciesism),罗尔斯顿称其为“主体癖”(Subjectivebias)。达尔文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予关照。我相信,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谦虚和真实的。”他认为,“在精神能力方面,人与高等哺乳动物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21]他们认为,权利主体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再从动物扩展到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体,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同时,自然界的权利具有平等性,即地球生物圈中的各种生命物种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生态位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正是所有生命物种的相互作用和综合作用,创造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维持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及其它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因此,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只有平等性,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都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
再次,确立现代生态文明伦理观,也要防止“极端自然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该观点否认人的中心地位,主张以生态为中心,甚至将人的无节制发展喻为“宇宙之癌”。这种价值观将自然绝对化,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郑少华认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取向,大致有二:一是舍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揉进‘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因素,构成新的环境体系;一是彻底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观,采‘非人类中心主义’建立新的生态权利体系。……显然只能遵循第一条思路”。[22]这实际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他是一种新型的伦理观,它既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也是对当代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23]
(三)从生态法的终极目标看生态法的生态本位
人类对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生态,人类也有责任恢复和保护环境和生态,恢复和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必须有生态本位思想。
首先,生态本位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环境法的社会本位是以保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终极目标追求,生态本位强调以生态为中心,以生态利益为本位,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非相互对立。它认为,整个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与其它生命形式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地球生物圈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依存的有机性,即世界系统中人、社会和自然都是有机的生命体,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内在联系,人与非人自然的一切有机生命体,不仅是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而且是由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二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即这是一个由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现实世界系统中,脱离开自然的社会同脱离开社会的自然一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存在完全脱离社会因素的纯自然规律,也不存在完全脱离自然因素的纯社会规律。这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这就要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其次,生态本位终极目标在于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均衡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利益。人类的行为应以不破坏生物圈的生态平衡为限度,人类应与其他生命形式互惠共生、共同发展。这种法律观强调,为了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应保持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圈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生态进程,并在利用现存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时遵守最合适条件可持续获得收益原则,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对其进行开发利用。[24]正如郑少华所说:“法理念,从法本位到社会本位,再至生态本位,并不意味着个人放弃权利,意味着在生态危机冲击下,人类走向更高理性,放弃对自然界的掠夺性攻击,转而走向合作,……人与自然的真诚合作”[25]
再次,生态本位终极目标在于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到代际之间以保持整个生物圈永恒完善和健康。该观点强调不仅要将当代人纳入法律规范的范畴,而且必须将尚未出生的后代人和其他生物也纳入法律规范的范畴,以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法律观认为,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单个的人,也非作为社会的群体的人,而是作为与自然、非人类存在物相对应的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因此,生态本位要求,解决当今生态危机需要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不仅要突破国家与地区的界限,而且还要突破代际之间的界限。当代人作为后代人的托管人以及前代人的受托人,应当为后代人肩负起更多的维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其目的在于追求人类共同体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共存共荣[26]。
三、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的意义
(一)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是人类认识的重大转变,它重建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27],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视角,人类进化史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从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融化于自然的混沌同一性到人与自然存在区别,并不是混沌同一性而产生自治思想。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导致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从人与自然的完全对立、相互对抗、相互毁灭乃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体完全瓦解,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生息、协同进化,乃至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体。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又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如果说,第一次飞跃,人类认识自己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可以不受自然生态的限制,其行为的选择是无限度自由的话;那么,第二次飞跃正好相反,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的”,人类行为选择的自由必须限制在自然生态容许的限度内,即限制在地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这是生态“绝对法则”。
对应在生态法学中,是由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来中心主义的转变。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与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和谐相处与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次伟大觉醒。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生态觉醒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28]。这种觉醒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除了人与人的和谐以外,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29]
(二)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解决了理论指导的缺乏性,弥补了环境法社会本位思想的局限性,为生态法理论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生态法生态本位是一种全新的本位思想,传统的环境法的社会本位思想无法将其内容全部包容。环境法调整的结果,没有解决当代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进程,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这些难题正在逐渐演化成更多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坚持用社会本位思想解释新问题,就会显得力不从心,由此也引发了人类对自己行为的检讨和反思,增强了自觉向生物圈学习的主动性,产生了应当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向和行为模式的认识。因此,生态环境领域迫切需要生态本位思想作指导。如果没有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行动,就无法产生对生态自然法则的认同,也不可能确立符合客观理性的生态法学正义准则。[30]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必须打破以往的社会本位思想观念,确立生态法学的生态本位,填补生态法律本位的盲区,开拓本位研究的新领域,为生态法律实践服务。[31]
同时,以往社会本位思想是调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使人的主观意志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即使是这种发挥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也没有发现与控制,结果主观的臆想代替了客观的实在;随着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大,自然界理所当然要被纳入法律调整系统中。因此生态本位思想的提出弥补了环境法社会本位思想的局限性,大大地开拓了生态法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三)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回应了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解决了人类实践方面的难题
在现实中,人类不断面临新的环境问题,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运动也在不断兴起[32]: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掀起的反公害运动,喊出了“还我阳光”、“还我蓝天”、“还我清水”的强烈抗议之声,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性潮流。到1972年世界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使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形成高潮。它揭示了人类开展生态革命与创建生态文明的序幕。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全球征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交织一起,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直接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生存。人类需要进行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人类自身的命运和地球的存亡。于是全人类为进行这场生态革命采取全球范围的共同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环境、改善生态;从个人到家庭,从各种社会组织、各个政党和各国政府乃至全世界,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与重视,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为标志,人类全球生态环境运动达到新高潮。它反映了人类用可持续发展战略迎接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另外,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生态运动,即绿色运动。它向广度与深度扩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有力推动着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它极大地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高潮在21世纪必然到来。因此生态法生态本位思想正好回应了这些现实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另外,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案件,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如何从生态本位思想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法律的具体适用是处理生态环境案件的关键。如,有关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与内容原因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当事人诉讼请求的科学性,法律责任的承担,证明责任的确定,纠纷的解决途径和方式,惩罚与奖励的得失,损害额度的计算等等。可见,生态法学生态本位思想的产生是法律本位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法学理论尤其是实践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