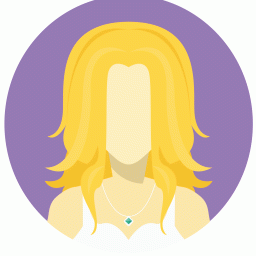国内科幻文学缺失研究

封闭的空间观
如果说隐喻化的宇宙观提供了中华文化生发的宏大背景,中央与四方的空间概念,则是其主体和框架和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轴心时期”殷商便奠定了中央与四方的“天下观”。葛兆光先生曾精确地把握到中国古代思想“通过一系列的隐喻,在思维中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3]19这就形成了中国式世界中心即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其余四方都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这理所当然地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夷、南蛮、西狄、北戎”的空间想象和空间结构。这种封闭空间观念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地缘是其中极重要因素。钱穆先生就指出“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籍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籍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4]5独特的地理结构与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相对封闭性的叠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极易产生出将自我等同于天下的结构,正如许倬云先生指出的“中国的秦汉帝国由中原逐步扩散,终于东及于海,西至流沙,北到长城,南逾岭表;中国之中国,以及其古代的极限”。[5]19地缘上的网状结构、政治疆域上的相对固定和封闭性,文化上在东亚的独占鳌头,历史上与中华文化势均力敌的他者的缺失,最终使得将中国观念与“天下”自然地划上等号:中国是世界和价值的核心,所有异域在文化价值上都是不足观的,中国之外都是未开化的蛮夷,构成了中国文化在价值和地理上的优越、先在结构。具而言之,中华文化传统中没有异的概念,万物都是一本万殊的,自然可以执一驭万,这就造成了其在空间结构上的划分:文明开化的中原(中华)与未接受中华文化的蛮荒之地(万邦)。这样就将中国置于地理和价值的核心,认为自身就是天下之本,各种源流皆从中而出,这使得任何一种新思想或事物皆不被重视,如有重视也会将其纳入中国文化的结构中来解释,将其说成如鲁迅先生所言的古已有之。没有异在(价值上势均力敌他者),易使一个文化走向封闭。它起初可能来源于其较为封闭的地缘结构,最终上升为封闭思想观念,没有异在与他者的存在,会导致某种文化认识的经验迟迟得不到更新,对已形成的思想观念,难以得到有效的反思,在空间、观念上的封闭就难以被打破。关于中华文化中他者,许倬云先生曾撰专文指出中国文化中他者是变动不居的,二者可以转化:“华夏与夷狄,不是对立,而是逐步转变”。[6]18换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与其势均力敌的异在,中国历史上的他者只是中华文化的补充,界限是变动不居的,二者可以逐步转化甚至是同化,在此结构中华夏始终是价值的主导者和皈依的核心。他者在价值上的虚悬,地缘结构生成的封闭空间观、价值的优先性与中国文化中的“父母在,不远游”的训诫共同限制了国人向异域探索的好奇与冲动,既然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是唯一文明开化之地,四方是蛮荒之地,四方在价值上自然无足观,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训则在道德和社会舆论上向人们施加了极强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国人对异域的鲜有涉足,偶有涉及亦当做猎奇,最终成为通过某种方式反证和强化自身文化中心和价值优势的证据。英国科幻文学研究者亚当•罗伯茨所言西方众多科幻文学研究者基本共识是:“科幻属于一种涉及了与读者实际生活的世界不同的世界观的文化话语形式。”[7]13换而言之,科幻文学必然涉及到一个与现实的世界不同的世界,即多个世界之间的对比,正因如此,亚当•罗伯茨才将西方科幻小说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他说“科幻小说的另一个重大特征是冒险旅行或者奇异旅行的喻象。它们在科幻小说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可以在古希腊文学中找到起源。”[7]33因此他者的观念和存在极其重要,正因为他者的存在我们才能从他者身上反思我为何物,我的本质是什么,进而明确世界是什么,除此在世界外,世界是否以他种形式存在。如果有,到底谁才是世界的本质?应该看到西方世界中对先验、超验、经验世界的划分使我们明确我们的经验世界并不是唯一存在的世界,这种世界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没有生发开来,虽有殷周文化中对死后世界的探讨,但也将其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这一点可以从殷周人对祖先的崇拜中看得很清楚,殷周人认为先祖死后上宾于天成为天帝旁边的宾帝,对人世祸福有影响,所以后人要定时祭祀先祖,通过宾帝而获得上帝的保佑以获得人世的幸福,这种思想为西汉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发挥到了极致,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成功地实现了“天、地、人”三界的整合,也使得本来作为超现实的存在的“天”变得可测可知,可从现实世界知天意,从而削弱、弱化并使得中国文化“基因”中的超现实的存在世界丧失,最终只有唯一的“现实世界”。在这种过程中,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并扼杀了中国文化中对彼此的探问②。如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四方的观念与中心的观念限制了中国科幻文学产生,其核心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言的“儒学确立的只有一重世界(现世),而没有两重世界(现世与超世)、三重世界(地狱、人间、天堂)。‘天’与人的本体同一,排斥了超验世界得以确立的任何可能。”[8]103曾作为中国文化的他者的佛学,为了在中国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对教义进行了调整即服从现实的统治,这种变革始于慧远,正如芮沃寿所言“慧远所诠释的佛教默许如幻世界中的政治和社会的设施:佛教改善、宽慰,但是它不寻求改革”[9]37这使得任何不同世界的比较从价值本原上就失去了根据,“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则将人的行动绑死,使得任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异域世界的探讨都失去了可能。
中国文学传统与取譬思维
中国传统文学有“诗言志”和“文载道”传统,“诗言志”按照闻一多先生解释:“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10]15所谓“记忆”和“记录”基本上是对国之大事的记载,怀抱则主要是吟咏性情,但无论是诗的前二义还是第三义,对现实世界态度要么倾向于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的记载已经发生的事情即对现实世界如实的临摹,要么倾向于完全不顾现实的天马行空式的幻想。文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另一支,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的“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各别文体的职能……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11]4由此看来无论是等级最高的文亦或稍低的诗都未以文学本身为本体,变成了一种工具。中国文化中的道体现为天、地、人三者的交互状态,这也就有了“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的思想,人道即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是由最高依据“天”给予的,人和天地之间的“天人感应”使得世俗政权以“上天”的旨意执行者的身份即“天子”身份出现,因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世界”思想,很容易使人将“文载道”中的“道”替换成世俗政治,于是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得文学丧失了自身的本体性和合法性,极大地束缚了文学对自身领域的开拓,限制了文学自身对异在世界的探求。这反映在中国当代就是学界对中国文学想象力萎缩问题的讨论,此方面已有研究者,从作家创作角度指出原因:“当代小说叙事仍停留在模拟现实的阶段……当代小说的题材狭窄,多滞留于写实的层面,未能处理好写实与想象的关系问题。”[12]该研究者从作家创作角度很好地阐述了中国文学想象力萎缩问题,但应该看到导致中国文学想象力萎缩的根本原因除了该研究者分析的,文学传统的局限和束缚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传统对现实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它与儒家的文学观相叠合,共同扼杀了科幻文学的萌芽。应该看到: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只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方法,其背后对世界的体认都是各不相同的,二者作为不同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无高下之差,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学中儒家文学观具有毁灭性的后果,正如莫宜佳指出的“对于叙事文学的作者来说,儒家的‘文如其人’的观点则是最具灾难性的。儒家极端分子将‘不道德小说’解释成为作者颇具反叛企图的危险个性……古代中国经常出现文字狱冤案,在法庭上,作品中的文字往往被当作判断作者有罪的证据。”[13]6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古代作家对文学本身的探索和挖掘,这种传统在建国后又与对现实主义压倒性的强调,使得本已薄弱的文学创作又雪上加霜,直接造成了中国科幻文学萎靡不振,停滞难前。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化具有先天的“亲缘性”,它与中国古代“取譬”式思维一脉相通:“在‘取譬’思维定势下,任何事物都被具体化,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有现实具体的东西与之对应,对任何概念的说明都首先使用类比法。反过来说,在儒、道、墨、名诸家的认识论体系中,没有产生出其自身就是独一无二之存在的思维存在世界。”[14]这种思维使得任何高于现实的世界都不可能存在,于是模仿和临摹现实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极大的思潮,现实主义作家“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认为艺术不仅可以模仿自然,而且它所摹仿的现实本身也是真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因素。”[15]5这使得客观性和真实性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标准,更为可怕地是它与中国儒家文学观中强调的“文如其人”在逻辑上是贯通的!这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中孕生不出任何高或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叙事世界,任何高于现实世界,都必然会被拖回到现实中来理解。正因如此,中国文学传统中产生不出科幻文学这一文学种类,虽然科幻文学与现实主义有相通之处,却有着内在差异:“科幻小说给我们一个象征主义的世界,它流溢着超验或形而上学式的芬芳,并对现实世界进行了重置……科幻小说是象征式的,但它通常采用现实主义的方式累积起大量细节。”[16]15可见,现实主义与科幻文学有相通的地方,但是相通不等于相同,正是对此的理解的偏差,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迟迟走不出对现实主义的“仿写”中,要么将科幻文学中世界等同于现实世界,要么将其作为现实世界的反面,无论哪一种离真正的科幻文学皆相距甚远。
后视的文化视野
中国文化就其主干而言,主要是儒道释三家互补,它们提供了中国文化中对世界的看法,但就其提供的文化视野而言均是“向后”的。儒家认为最好的世界和时代是西周,所以孔子要克己以复礼,其最终认为美好的理想的世界不在当下,不在将来,而在过去。道家比儒家更为激进,其上溯的历史更加靠前即老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这一状态就是原始社会,所以道家眼中最好的时代是上古,是人类文明未开化的原始状态。释家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幻影,都是不真实的,由于人被红尘迷惑才堕入现实,所以在现世要修行,力求早登西方极乐,无论是佛家的西方极乐还是由“三世因果”产生的六道轮回,就佛家的理想世界而言均不在当下,不在未来,而在永恒的过去,其世界是一种环状的永恒轮回,这意味着每一刻的未来都在力图回到过去。同时正如许倬云先生指出的“印度文明选择了出世与悲悯的意念”[5]17,这造成了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世界和对世界的看法均是永恒的回归,这就与科幻小说本身基于现世展开对未来的想象和对多个世界的探索,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异的。
中国传统对人的设定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限度,文化之间本无高下之分,但就对人创造性的发展上,是可以进行比较,是有优劣之分的。正如对某一目的通常会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比另一些更好一样。中国文化传统在对人的设计中将人纳入了“二人”的结构,正如孙隆基先生提出:“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17]13这必然导致了一方从属于另一方,中国文化传统则不断强化了这种倾向,这必然致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以某种现存的东西为主,这严重束缚人的想象力的高扬,同时也将任何高于现存世界的东西拖回到现实中来理解,这使得任何思维抽象倾向变得不可能,针对此,孙隆基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文化特色将人的一切活动都导向现实世界,因此出现没有任何超越意向的‘身体化’。”[17]26这种观念具体化影响至今仍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教学中,这正如黄全愈先生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绘画的教学中更倾向于“像”、“不像”的问题,并将此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逻辑思维或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现存的许多优秀的‘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18]19这种对人的设计,使得自我无从产生,更无法以自我为基点展开对异在世界的探求,并使所有能设想的世界均从属于现存世界,再加上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毁灭性的“文如其人”观点的冲击,使得任何的对超越现实世界的冲动皆被扼杀,正如亚当•罗伯茨揭示的“科幻小说通常比现实主义文学和其他主流文学拥有更为显著的想象力。”[16]15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文化对人的设计以及在日常教学中皆将想象力排除在外,这必然使得以想象力为根基的科幻文学无法产生,这也成为了当前中国科幻文学想象力受限的潜因,也是中国制造业中“山寨”泛滥的一个内在的“文化基因”。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隐喻化的宇宙观,封闭的空间观滞于物的思维和停留于现实世界的文学传统以及后视的文化视野和传统中对人的限定,共同形成一种格式塔式“完形”结构,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无法孕生出科幻文学这一文学类型,也造成了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落后的现状。我国的科幻文学如要健康地发展,必须对上述影响科幻文学产生的原因加以详细考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扬弃才能使中国科幻文学蓬勃发展。
本文作者:赵臻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