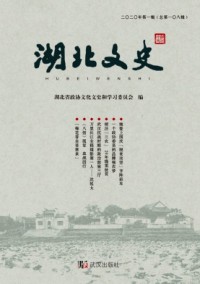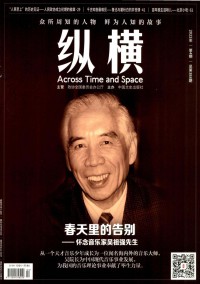回忆往事的作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1篇
在楼下,我们站好了队,艰苦的训练就这样开始了。
定立的训练使得我们好多的同学精疲力竭,好多都是爬着出去的,练到最后才是胜利者,为此我都是最后一个走出训练场,两脸通红通红的。
艰苦的训练之后就是吃饭,吃饭前大家一起来唱军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各班值日的学员把饭添好了之后,排队进入吃饭,假如有抢菜现象发生,教官就会罚他,别以为会不让吃饭,恰好相反,他力求把你撑死,给你一个清醒的教训——军校的饭有的是。
中午休息两个小时,假如有一天没有睡着,你就是不合格的学员,为此可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在下午的训练之后,在夜里,我们一起洗澡,一起洗一天的衣物,互相帮助挤干毛巾,倒也求地个快活。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2篇
也许大家认为我很美,有父母的陪伴,姥姥姥爷的照顾……但,并非如此。尽管这些条件我都有,可我的过去却十分无味。
当我茫茫然回忆这一切时,我有些悲伤。小时候,我独自一人在奶奶家; 而奶奶却去离她家几百米的小妹家去。当时我还不懂,当妈妈叫我去姥姥家时,我居然像奶奶说的那样,让妈妈去我不去。一次,我生日,奶奶都不知道,而姥姥却拎着蛋糕向我走来。我对蛋糕不感兴趣,所以就跑开了……可是蛋糕仍叫奶奶拿走了,他去给我小妹了。
……
这样让我如今想起痛苦不堪的事还有很多,我真后悔,后悔当初的我。我也因此常常伤心的流泪。也许大家也能通过我的作文看出来,我很伤感。我很苦!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3篇
“嘀。”20点钟到了,大家放下手中活,来到电视机旁边,我也不例外,看呀!像29个大脚印的烟花向“鸟巢”奔去,29个大脚印代表29届奥运会。开始表演了,首先,是倒计时击缶,有2008个演员击打2008尊缶,全场变黑,统一的数字由击缶的人慢慢地开始倒数,然后表演击缶。
接着是表演中国的造纸术 。突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画卷,几个舞蹈演员穿着黑衣服,右手拿着一支很大的毛笔,在那张画卷上画出了美丽的山水,他们画完了,那张纸不知怎么的,立起来了。我最喜欢这个节目。
接下来的表演都很好看,有的演的是古代的活字印刷术;有的演的是古代的指南针;还有的演的是丝绸之路,这些包括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快看!哇!天空上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奥运五环的烟花。真美!接下来的是队员出场:第一个是希腊,因为希腊是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接着陆续204个国家的运动员进入会场,过了好久好久,中国队最后出场,中国的选手好多呀!有1000多人呢,穿红色外衣的是男队员,穿黄色外衣的是女队员,姚明叔叔是旗手,姚明叔叔的旁边有一个小弟弟,他就是四川抗震救灾小英雄林浩,他在地震中,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许多他的同学。我真佩服他!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4篇
回顾刚升入初中的这一年,觉得一切都过得很快。
唯一不变的是:我还是我
沉淀的是在心中的记忆
当时光流过十五岁,希望留下一个值得回忆的我
曾经写过期待十五岁,可当十五岁真的来了,我却在期望留下一个值得记忆的我。
我很平凡。也许是长大了,认识自己更全面了,小时候的我可从不会这样说。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所以告诉自己:勤能补拙——没有天分,所以一定要更加的勤奋。
和每个青少年伙伴们一样,我有理想、有抱负,并有一颗执着、坚定的心,不怕遇上成长道路上的迷茫与挫折,并渴望能战胜它,迎接一个美好的明天。
和每个渴望超越对手的人一样,我享受超越的过程,力求那个更完美的自己。不知道这是否偏执?知道比来比去,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不过有野心一定要做到最好。
面对周遭的隐隐不安,以及那些混合着紧张、竞争、羡慕、嫉妒、恨的冰冷气氛,我学着淡定、学着面对我知道这一切无可避免,但我不想失去单纯、快乐、简单、耿直的自己,尽量,微微一笑吧!保持人生最美丽的姿态,出淤泥而不染不正是我追求人格的写照吗?
面对青春路上的年少懵懂,不是某种心动爱恋,只是一份无界线的纯真。所以,我选择不破坏这份栀子花含苞的友谊。当我再回首,发现往事已成为回忆,那么这将是一份最值得珍藏的礼物。
在这忙碌的一年时间里,自以为却并没有其他人想象中那么努力,尽管时间犹如漏沙般过得飞快。我学着珍惜。我知道人生短暂,如若不然,却也不想让失去的成为最美丽的,然后陷入后悔中不可自拔。所以我选择奋发进取,选择让曾经轻视我的人刮目相待,选择用努力缔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奇迹。我告诉自己:曾经的鄙夷与轻视不算什么,正如世界上有最后一排的座位却没有永远坐在最后一排的人。
我就是这样,在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中,不断更新着那个平凡的自己。
——十五岁留下一个励志的我
和每个学生一样,我喜欢放假、讨厌考试、讨厌老师留的许许多多的作业。这是从小到大从未改变的。
和每个同龄女孩一样,我喜欢写写自己的感受、喜欢幻想。
我喜欢聆听夜晚,曾写过这样的小诗:
夏夜/踏着微微的、迷失在空中的草木香/吮吸着大自然中清幽而又轻柔的晚风/听着知了在暑气未消中的鸣唱/看着家家通明的灯光/想象着每一束灯光下都有一个奋战的学子……
我喜欢漫步夕阳下,也曾感慨过黄昏:
傍晚的旋律是缓慢的/因为一天都忙碌着/现在已经太累了/正如灿烂了一天的花儿敛起笑脸的动作/正如鸟儿慵懒归巢的声音和人们晚饭后散步的脚步声……
望华灯初上/我扪心自问/这究竟是一天的尾声还是新的、夜的开始/在这个繁弦急管的世界/时间早已不受黄昏的约束/月亮和星星不知是被太阳烤化了还是满世界的灯光蒙蔽了人们的眼睛/也见不到了……
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我伤心过,也曾写过:
悼念那段曾经的友情/风中传来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是你最喜欢的歌/你的语音还是那么熟悉/而感觉已陌生/你的面孔还是那么熟悉/和我已成为陌路/一切还是那么熟悉/而现在俩颗心已背对背走远/那人/任在/时光/荏苒/那情/已逝
多想一霎间碰触到你的眼睛时还能换来相视一笑/像曾经一样/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那么/我们何必相识/十五岁的花季/我们为彼此留下这么深的伤痕
事情到了最后/已无谁是谁非/对与错已成浮云/重要的是再也回不到最初的美好了/彼此都不用后悔/或许/离去是解脱……
——十五岁留下一个感性的我
回忆往事的作文范文第5篇
题材取向狭隘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写记叙文的材料就差不多只有从“我”写起了,写与自己有密切关联的往事了,或顶多写写自己周围熟悉的人与事。自己的往事、自己的当前事成了学生写记叙文取材的重要内容。
题材取向狭隘,定会产生消极影响,即不利于发展初中生的前瞻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利于发展初中生社会价值的意识,不利于发展初中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因此,学生在取材方向上大部分只能向后看,只能写以自我为主体的文章。辩证地看,有好的一面,即因为取材贴近生活,学生觉得有话可说,有部分学生也能写出一些真情实感的文章来,能写出以前的或当前的那个“真我”。但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记叙文材料选择方向指导要有科学性,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取材导向应利有于发展初中生的前瞻意识和竞争意识。
以作文题《 _____改变了我》(07年江苏盐城市)为例,这是半命题作文形式,其提示语告诉学生,生活中的任何一种遭遇都可能改变了“我”的思想、性格、甚至是命运。如果这个作文让成年人来写,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可能有足够的存量可以总结和回顾,但现在让初中毕业生这样一群少年来写,有多少少年能够认知改变了自己“思想”的经历遭遇呢?更遑论“性格”和“命运”?
可能因为命题者在命题时希望学生有话可写,所以往往要求学生回溯往事。可产生的不利影响是:当我们频频要求学生追忆过去、回忆往事,并从往事中反思自己的得失时,学生的前瞻意识和竞争意识也逐渐淡化。人生什么时候会常常回忆往事?或山穷水尽,因无法直面现实而不断追忆,在沉湎于回忆中麻痹自己;或已“迟暮”,人生有许多得失可以回顾总结以利后人。而处于这个阶段的人,向前看的意识的是不那么强烈的。
当我们强迫我们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幼儿园或小学时代,我们的学生在潜意识里就不会成熟或干脆拒绝成熟,或最多假装成熟。在学生的作文里,有太多的“自己打碎了花瓶却赖在小猫或弟弟妹妹身上”“去买东西营业员多找钱要不要还而进行心灵斗争”“夏天钓鱼不幸掉进水里有幸被救”等等虚而假的材料。假如我们学生只会沾沾自喜于这些空洞虚拟的往事,这是何等可怕的事!
2. 取材导向应有利于发展初中生的社会价值的意识。
先讲一个事例,据中央电视台2010年1月14日播报了一则新闻《学生作业救了老师女儿》。说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女教师,给学生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主题是“疾病会影响人体的哪些器官” 的特征报告。一个叫约翰的学生完成的报告题目为《糖尿病病症的报告》。老师看了这份报告后,不禁后背发凉,因为报告中所提到的症状在自己女儿身上也有表现。于是把女儿送往医院检查,女儿被确诊为早期糖尿病。正是约翰的作业救了老师的女儿。
约翰的报告是有社会价值的。王充说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着,一章无补”,写作必须是有社会价值的。现阶段,据笔者的观察和了解,初中生记叙文在取材上,一般不太注重社会价值,更不能从社会文化积累和人的发展的层面来认识写作的功能。
长时间以来,我们老师一直注重于要求学生写一些身边的所见所闻所感的“小我”类文章。学生的习作中有太多的“我哭了”“我笑了”“我茫然了”“我苦”“我痛”……,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以“我”为中心的圆圈,学生仅有一点点的感情体验,因一次次的触摸而被无限夸大,越发的多愁善感,越发脆弱。习惯于这类选材取向的学生,难以站在民族的、人类的、自然的角度去感悟人生,他们无法满怀激情地去抒写对人类对自然的终极关怀。
当学生习惯于关注“家事”,而忽视了“国事、天下事”,忽视了作文的社会功能性,那么到头来,他对自己作文的认识肯定是茫然的。如果问一个初中生,为什么写作文?写给谁看?为什么写?他可能一脸困惑茫然,或干脆回答“还不是为了考试呗”。只为了应试功能而忽略了作文的社会价值功能,至少从写作角度来说,是不利于发展学生的社会价值的意识的。
3. 取材导向应有利于发展初中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当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要求学生写真人真事的记叙文时,对学生智力的开发就侧重于联想能力的开发而疏于想象能力的挖掘。
很多的卡通影片,像《米老鼠和唐老鸭》《哈利波特》《喜洋洋与灰太狼》等,不仅为孩子们所迷恋,也受到许多成人的钟爱。为什么呢?因为制作者大胆想象,赋于故事主人公各种超凡的神奇力量,才有如此吸引人的效果。在中小学所学的许多门课程中,最能发挥学生想象能力的是语言是写作,但如果我们在作文指导中不注重想象力的培养,这显然是错误的。在写作教学中,不宜太多的重复,太多的务实,在要求学生写真人真事,真实情感外,不妨多写一些想象虚构的文体,如童话、寓言、科幻小说、小说,这种形式上有些夸张、材料上有些新奇的作文,可促使发散思维能力的形成,刺激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