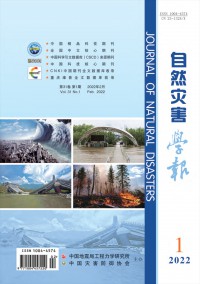略自然灾害和民间信仰关系

[论文提要]明清时期泉州自然灾害频发,主要有风灾、水灾、旱灾、地震和盐碱等。这些灾害在自然、经济和人文领域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泉州地区自然灾害与泉、台两地民间信仰特点之间的互动关系。为防范灾害,泉台两地人民曾经寻求民间神祗作为精神支柱,因而两地民间信仰有相近的特征。
[关键词]泉州自然灾害民间信仰明清时期务实性多元性难融性
本文所指明清时期的泉州地区是比较广义的、包含地理与人文的概念,大致包括有泉州府(含永春州)、及下属诸县(含同安县)。由于明清二朝泉州人民大量移居台湾,所以将泉州与台湾二府及光绪十三年单独建省之后的台湾作为研究的中心。泉州境内主要有泉州平原与戴云山脉、博平岭等山脉;该地区背山面海,加之又临近台湾、澎湖等众多岛屿,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也比较复杂,是明清福建经济发展相对迅速的地区。但是,这个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给人民生命财产及各项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当地民间信仰文化空前繁荣,在人文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明代泉州地区自然灾害及其特点
1、水旱之灾范围广泛,破坏严重
泉州地区水灾频繁,如万历十年(1582)八月丁巳,福建布政司奏:“四月多雨,水溢坏延平府卫城,没侯官、晋江、南安等处田禾、民舍,人畜漂流无算,存者不能聊生”。[2]成化十八年七月甲午“永春县大雨至八月丁酉,洪水泛滥,淤田畴,圮桥梁,坏官私序舍,滨溪民居淹没尤甚,民亦有溺死者”。[3]成化二十一年,整个地区大面积水灾,如志书所记:“自春徂夏积雨连月,晋江、同安、永春、德化、惠安五县,田庐禾稼多为所坏。”[4]。万历三十一年(1603)八月丁亥“泉州府等处大雨潦,海水暴涨,飓风骤作,淹没者万有余人,漂荡民居、物、畜无算”。[5]逾万人遭灭顶之灾,这在历代的水灾记录中也是十分罕见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壬午巡按福建御史李凌云奉命“勘过去岁八月由兴、泉、漳三府水灾情形,据实具奏,请将原题税银五万两或全或半存留赈恤”。[6]可见水灾大量发生在万历年间。因此明代在泉州府及下属各县产生了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主司防患水灾的信仰神祗。又如旱灾,成化十六年(1480)八月乙卯“免福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府去岁秋粮”101400石有奇,镇东等卫所子粒14800余石,“以旱灾故也”;正德五年(1510)八月乙酉“免福建银课一年,守臣以地方旱灾为请,故有是命”。[7]终明一世,干旱成灾的记录较少。
2、泉州沿海飓风频繁弘治六年(1403)七月初三日泉州大风雨,“自卯至申扬沙走石,开元寺西塔葫芦倾覆,折林木无数。城铺粉堞颓十之九,坏官私庐舍、商船、民船不可胜计”。[8]万历三十一年(1603)同安县陡起飓风,海水涨溢“积善、嘉禾等里坏庐舍,溺人无算”。是月初五日未时飓风大作,海溢堤岸,骤起丈余,浸没漳浦、长泰、海澄、龙溪民舍数千家,人畜死者不可胜计。甚至有大番船越过海堤漂入石美镇内,压毁民舍。泉州府邻近各县损伤十分惨重。[9]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辛未方从哲报泉州风灾:“昨日申刻天气晴朗,忽闻空中有声如波涛汹涌之状,随即狂风骤起,黄尘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及将昏之时,忽东方电流如火,赤色照地,广顷西亦如之。又雨土蒙蒙,如土如霰”。[10]摧毁民舍若干,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庚子福建巡按崔尔进奏言,三月二十一日福建长泰、同安二县大雨雹,“大如斗如拳,击伤城廓、庐舍、田园、树、畜”,压死百姓220多人,请截留洋饷2万两以赈济地方。[11]这是明代闽南见于文献记载破坏最为严重的风雨雹灾。足见明代闽南风灾肆虐。
3、地震的多发地带
闽南与台湾海峡均处于地质断裂带,时常发生震灾。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五月,二十九年(1396)十二月,泉州连续发生地震。成化十六年二月丙辰,“福建泉州府地震,有声如雷,屋宇皆摇。”宣德十年(1435)十一月癸未漳州府发生强烈地震:“日夜连九震,鸟兽之属皆辟易飞走,山摧石坠,地裂水涌,公私屋宇摧压者多,凡百余日乃止”。龙岩、漳平、长泰、南靖也发生了破坏力相近的地震。正德十五年六月庚甲夜,“福建福州、泉州二府各地震”。嘉靖四十三年(1564)正月癸巳朔“福建福州、兴化、泉州三府同日地震”。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泉州府地震”。万历三十年(1602)正月辛亥“寅时,南澳同时地震,有声如雷。盖闽粤交界地也。”万历三十二年(1604)六月初八日、初九日泉州连续地震十余次,“山石海水皆动,地裂数处,郡城尤甚。开元寺镇国塔尖坠,损扶栏。城内庐舍倾圮,覆舟甚多。”[12]这是当地极为严重的震灾。万历三十年六月戊申福建兴化、泉州同时地震。辛亥,“是日卯时福建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同日又地震”。[13]万历年泉州进入地震活动期。由于地震所造成的空前破坏,加之突然袭击,防不胜防,所以对泉、漳一带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恐惧之余,闽南乡民也塑造了许多与之相关的神。灵顶礼膜拜。
4、瘟疫万历四十一年(1613)泉州“郡城大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籍,有阖户无一人存者。市门俱闭,至无敢出”。此外,德化还发生大规模鼠灾,“田鼠害稼,一亩之田至有数千;春食秧,冬食谷,畔皆鼠道,草为不生。次年谷贵,人多饥死”。[14]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载永乐十七年五月“建安县张准言:建宁、延平二府自永乐以来屡大疫,民死”774600余口。瘟疫对社会、人口的摧残极大,人们谈瘟色变,因而在当地民间信仰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泉州地区瘟神崇拜盛行,明代泉州文人黄景方《温陵旧事》就把瘟神称作“五方瘟神”,以示其神通广大,监领五方。谢肇淛《五杂俎》卷六“人部”二也有所记录。他说:“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莙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余在乡间夜行,遇之则经行不顾;友人醉者至,随而歌舞之,然亦卒无恙也。”可见瘟疫造成了泉州人的极大恐慌,他们只好寄希温于“出海”等驱神仪式。
二、清代泉、台两地自然灾害的发生更加频繁,破坏更加严重
这个时期泉州地区,包括台湾府在内都进入了天气异常、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主要的灾害种类如同明代一样,但水灾爆发的频率及破坏的程度均明显超过了前朝。
1、水灾成为泉、台两地危害性最大的灾害
顺治初年,包括漳、泉二州也发生大规模的水灾。惨烈之状,令人无法卒读。康熙三年(1664)六月二十六日“泉州暴风雨,水骤涨,自辰至申水高丈余,城市肆湮没,溺死甚众,三昼夜乃退”[15]康熙十九年(1680)兴化灾情严重,斗米百八十余钱,“民有饿自缢、投水死者。明伦堂施粥,分西、南厂签给;南厂妇女幼丁,西厂壮男。初有三千余人,后八千余人,有死及生子厂中。督抚发银八百两到邑,一两谷一石,扣米五斗,分上中户采买”。[16]乾隆五年(1740)七月十二日巡视台湾兼理学政杨二酉等奏,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两日风雨交作,台湾郡城内外吹倒房屋”57间,营房7间;诸罗县“自二十二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台风连作,县城内外官舍军民房屋均有损坏。其盐水港、笨港二处,山水骤下,溪流涨漫,浸倒房屋二百余家。盐水港仓廒尽行倒坏,被浸仓谷现在极力晒晾”。[17]乾隆八年(1743)八月初四日福建陆路提督武进升奏台南城“六月初四夜戌刻狂风大雨,……本营及下溪水营各弁衙署以及营屋、塘房、望楼、旗杆等项虽多遭风雨吹淋倒坏者十中七八,而倒塌不堪者十中四五”。[18]乾隆九年(1744)十月二十九日福建巡抚周学健奏八月十六、七等日诏安、南靖及漳浦县云霄,平和县南胜,泉州府厦门“因山水骤涨,海潮上涌,有冲倒民房,坍坏城垣、堤岸、桥梁,淹溺人口之事”。[19]乾隆十年(1745)八月二十四日周学健又补奏:七月二十七日近城及东南低洼各村,倒坏民房1000余间;“城垣、学宫、营房、墩台均有坍塌”。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初四日福建巡抚潘思榘等奏:“八月十六日秋潮盛涨,沿海许茂保洲田漫淹”4000余亩,浸坍佃民茅寮39间;泉州“潮汛甚大,又遇大风,沿海埭田冲淹一千五百余亩。并据两县均称,前次七月内沿海被受风潮,正值栽插晚禾之候,俱已补种,今晚禾已吐花结穗,咸潮淹浸不能复长,现在分别抚恤”。[20]同年(1748)闰七月十一日巡视台湾陕西道监察御史伊灵阿等奏:“彰化县本月初二日半夜起至初三日酉刻风雨大作,山水骤涨,沿溪一带田园、庐舍俱有损伤……被水各村庄冲倒瓦草房屋”共1800余间,共赈银476两;淹毙男妇18名口,“照例赈给银两,饬令收埋”。[21]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九、十九、二十二三等自闽省地方俱有飓风,闻得台湾鹿耳门一带击破船只甚多,淹毙者不下一二百人,即澎湖、海坛、金门等处皆闻有船只打坏、货物漂流之事”。同年八月二十九日马尔拜奏:“七月十一日据铜山口委贞禀称,亦于是日飓风狂雨至次晚方息。有厦门水师中营哨船一只在古雷地方打破,其本港采捕渔船及外来商船”,毁船数十只,淹毙30余人。[22]乾隆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巡视台湾江南道监察御史书昌奏:“八月初八、初九等日因雨骤风烈,田舍、人船复有损伤失事”;其中淡防厅属田园内水冲者9甲5分、沙压者9甲4分、倒塌瓦草厝231间;台湾县属沙压40甲9分、水冲143甲2分、倒塌瓦草厝35间;凤山县田园沙压者12甲,水冲126甲,倒塌瓦草厝386间;诸罗县田园水冲122甲、沙压67甲、倒塌瓦草厝43间;彰化县田园水冲312甲、糖部3半张、沙压20甲、倒塌瓦草厝1513间。台防厅所管鹿耳门汛遭风船20只、淹毙舵水人等共10名。[23]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四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新柱奏:五月一日“同安县溪水涨溢,城垣倒塌两处”,淹毙27口、倒房1700间;另据喀尔吉善奏:“同安县坍坏民房”1182间,“淹毙大小男妇”28名口;各县水冲砂压田亩自数亩至二三百亩不等。[24]从清代文献记载看,当时对泉州各县造成大规模破坏的首先应是洪水灾害。因而泉州当地民间信仰中有相当部分神祗崇拜与防患水灾有关。
2、风灾上升为本地区的主要灾害
泉州地处季风区域,夏秋二季时遭台风、飓风袭击。有关澎湖地区的风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本人已有专文论述。[25]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台湾大风,刮坏民房庐舍无数,击碎商船100余艘,台湾知府方邦基所乘之舟至南日岛洋面舟毁身亡。方氏系七月戊辰登舟,八月乙亥自鹿耳门放洋,越己卯遭风,在海上漂流一昼夜后在福清地界的南日岛冲礁,舟毁人亡。随从21人中,仅4人获救生还。[26]又如光绪四年(1878)台湾府城(今台南)“于四月二十一日酉刻突遭怪风”,所过之处屋瓦齐飞,古树为拔,辕署照壁、旗杆坍折,署内房屋大半夷为平地,围墙倾倒;“署东箭道内兵房倒塌公压伤左翼练兵十六名。北城垛口摧坍十余丈。城内外民房当风过处多有倒坏,压伤数十人,压毙二人。”[27]嘉义县于四月二十二日寅刻“大风陡至,县署大门既署内房屋悉为平地,余皆倚斜;经查台北、彰化、南投等处虽先后俱遭风雨,情形较轻。”。[28]光绪五年(1879)台湾后山自九月二十二日起大雨狂风,连霄达旦,至二十五日始止。打马燕等处所垦田园有冲去一半或七八分者,禾稻杂粮俱有损失,营垒公所率多坍塌。[29]光绪六年(1880)台湾镇总兵吴光亮报称“山中南北三路,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风雨交作,二十三日异样狂风”。[30]光绪七年(1881)台湾、台北两府属因被飓风大雨,致使凤山县大乌山地方溪水陡涨,淹毙番民10余口。淡水、新竹两县海边草寮民房间有吹倒。宜兰、基隆倒房伤人;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又遭飓风大雨,尤为猛烈,台湾县安平及凤山、嘉义、彰化、恒春多受破坏,各口船只均有冲击飘沉。[31]光绪八年(1882)闽浙总督何璟急奏台岛风灾损失情况:“本年六月十六日起台湾、台北两府属大雨倾盆,加以台风势殊狂猛,接连数昼夜,以致台湾府城及安平海口民房、兵房均有倒塌”。彰化县城倒坏民房100余间,兵房30余间,城垣40余丈,炮台1座。文武衙署间有坍塌,压毙男丁2人。新竹县城倒塌民房草屋100余间,大甲迫近山溪,水势暴涨,灌入土城,冲坏草屋100余间。城垣衙署亦有倒塌,堤工溃决500余丈。铁篾等薪多冲入海。[32]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十九日台北、淡水、基隆、新竹同时遭风;“内地泉州府属之厦门,于七月初一二等日风狂雨骤,木拔瓦飞,官署民房类多塌损”,中外船只沉失200余艘,淹毙多人。[33]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十四、五、六等日福州、漳、泉、台、厦各口,台飓大作,拔木毁屋,伤损船只不少,为近十数年所罕见。[34]造成各地风狮、风神信仰盛行。
3、旱灾在内地山区与沿海平原频繁发生
清代福建特旱记录共有8次,分别在顺治五年(1648)、康熙四年(1665)、二十年(1681)、三十五年(1696),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五年(1825)、十六年(1836)、光绪九年(1883)。以康熙三十五年(1696)为例,有关府、县志称,泉州府的德化大饥。“乾隆二十二年春漳州大旱田无播种,二十三年泉州旱饥”。乾隆二十三年(1758)泉州因旱灾造成饥荒,仙游“大旱,斗米二百余钱”。直至浙江平阳海运大米船只迭至,米价才稍渐趋平;七月台湾府诸罗县大旱。[35]因而各地民众祭祀主司旱灾的旱魃蔚为风气。
5、泉州等地的瘟疫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
顺治九年(1652)正月,由于漳州潮水突涨5尺,郑成功军队得以突入海澄。同年漳州城被郑军团团包围,粮尽弹绝,以致“人相食,斗米值五两”。至清军解围之时,在城内收得颅骨73万;于是“疫大作,死者无数”。[36]乾隆十八年(1753)海澄爆发大规模瘟疫,“死者无算”;同年泉州府也有瘟疫流行,“至明年秋乃止”。[37]道光元年(1821)七月间福建全省瘟疫流行,患者均因吐泻暴卒,“朝人夕鬼”,不可胜数。[38]因而泉州乡民对于瘟神等神祗崇拜有加。此时泉州瘟神崇拜有所变迁。人们以为瘟神原系360名进士在明初屈死,上帝命其血食回方,泉州人尊称为“王爷”,常见的有朱、邢、李、池、吴、范、温、康、萧等100多姓。当地送瘟神的主要方式是“出海”,即以木船满载纸人、纸马等诸多神像及各种贡品,向海中放行。石码商民不惜花费“五六十万巨金”制作用以敬神的木船,浩浩荡荡直抵台湾西岸,台岛乡民或将之迎送,或建庙祀之。正如曾任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后卒于台湾道任上的周凯于道光十二年(1832)写就的《厦门志》“风俗记”所言:“吴越好鬼,由来已久。近更惑于释、道。一秃也,而师之、父之。一尼也,而姑之、母之。于是邪怪交作,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风,猜神疑仙,一唱百和。酒肉香纸,男妇狂趋。平日扪一钱汗出三日,食不下咽;独斋僧建刹,泥佛作醮,倾囊倒箧,罔敢吝啬”。周氏所言未免过于尖刻,但确实道出了明清时期闽南乡民对灾害的畏惧感和祈求神灵庇护的心态。面对灾害的频繁袭击,明清各级官员也确实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大量防灾抗灾和灾后重建工作。闽南各地民众也采取各种措施应对突如奇来的自然灾害。 三、各级封建政府的赈灾措施与灾区官吏、百姓的祈福禳灾
1、赈济与安辑、抚恤灾民
所谓赈济,即封建政府用钱粮救济灾民。此前首先要对灾情进行实地评估。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学士和珅等对闽南洪灾有一个全面的奏报:“一疏称石码等一厅四县,先经给过无力贫民倒塌瓦房”34868间,每间给银5钱;瓦披8144间、草房10002间,照例每间给银2钱5分;草披2175间,每间给银1钱2分5厘;“淹毙男妇大口”1893口照例给银1两,男女小口981口每口给银5钱。通共给过银24625两。[39]第二年福州将军兼署福建巡抚魁伦核准勘明漳州府属漳浦、海澄、诏安、龙溪四县淹田902顷50亩,共应赈灾户16451户,内大口共42192口,小口共32700口;并按“被淹田亩户口实数散给一月口粮”。[40]这次水灾后果极为严重,如《史料旬刊》第三十期所载,魁伦于乾隆六十年(1795)报:泉州一带“春夏之交,米价日渐增昂。现在每石粜钱七、八千文不等,合银五两以外。即省城米价,每石亦在四千七、八百文,合银三两以外。且春日各处雨水颇多,麦收未免歉薄。现在早禾虽经插遍,而低洼处所,亦因雨多之故未见及时茂发”,鉴于闽南水灾严重,造成漳泉二府乃至省城粮价爆涨,官府只得赴福宁府购入稻谷、薯丝,海运漳泉以期平抑粮价。
对于评估并未成灾的破坏,则责令地方官自行修建抚恤,如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十五、六、七、八等月“猝被风雨,经该道府饬据台、凤、嘉、彰四县,鹿港、淡水二厅陆续禀报,内如台、凤、彰三县,鹿港、淡防二厅禾稻并无妨碍。间有损坏官舍、营房、桥梁、道路以及房屋损坏之贫民已据该府查明,自行修理抚恤”。[41]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初二至初九日,泉州府属的晋江、同安、南安、厦门、马巷及金门,漳州府属的诏安、云霄等厅县均发生严重水灾。同安与诏安最为严重。同安县“风雨交作,兼之溪流骤涨,海潮顶阻,以致低洼处猝遭淹浸,水深数尺不等”;被水淹倒民房3848间,内无力修复者1402间,由县署捐给修缮费;城乡淹毙大小男女54口,由县给资掩埋。被水贫民1963名口“并经捐给口粮,现在次第归庄,不致失所”。[42]官方赈济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使嗷嗷待哺、流离失所的灾民安定下来,对于恢复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好处。与抗灾及赈济灾民活动同时进行的尚有各级地方官员携同当地士绅百姓社会贤达的祈福禳灾活动,容待下文论述。
2、蠲免与缓征所谓蠲免即免除赋税徭役。明洪武初年下令凡遇灾荒,须以实奏闻,不得隐瞒,按实灾蠲免。洪武七年(1374)又规定蠲免条例,即凡水旱之处,不拘时限,只要勘查属实,即可免除税粮。此后一省或数省,或单免夏粮,或只免秋粮,遂成通例。清代灾免推行于立国之初,但数量无定制。至顺治十年(1653)才将全部额赋分为十分,按田亩受灾分数酌免。受灾八、九、十分免30%,受灾五、六、七分免20%,受灾四分免10%。之后蠲免比率不断大幅增加,如雍正六年(1728)改被灾十分者免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具体做法一是查明应免钱粮数目,预期开单申缴藩司核实,然后发给各业户收执,并告示百姓周知;二是蠲免积欠,在高压政策下百姓难以拖欠赋税,积欠主要是灾害造成的。所谓缓征即指成灾五分以上州县可以缓征当年钱粮,顺延至以后年份。迨至明清二代也时常采取此项措施。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福建巡抚张伯行“题报台属亢旱请照分数免征疏”呈报台湾府属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当年入秋旱情严重,又遇上台风,经布政使金培生、台厦道副使王敏政实地勘查,三县被灾田园25373甲,共请免当年粟30154石6斗;而且因“台湾远隔重洋,风信靡定,报灾分数,案准部覆,不拘定限在案”。由于灾民还要承担“应征粟”107696石4斗,百姓不堪重负,台湾府知府周元文、台湾知县孙元衡、凤山知县宋永清等吁请朝廷将台湾县应征额粟33545石3斗“于四十七、八两年带征”。清政府予以批准。[43]这些措施均在客观上有利于灾后民生的恢复。
3.从台湾、浙江等地贩入米粮以平抑粮价,抚恤灾民
闽南因水旱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一般是由粮商自台湾、浙江、江西、广东等临近府、省购入粮食弥补。如《清高宗实录》卷1480记乾隆六十年(1795)闽南大面积水灾后,魁伦再奏朝廷:“据泉州府厦门同知及漳州府禀称,泉州府城十四日米价尚在六千以内,十六日有台湾商船贩米三万余石进口,米价顿减,每日粜米三千七、八百及四千文不等。厦门地方因石码、海澄等处收获较早,新米已多上市,无需来厦搬运。兼福宁府米船连艘踵至,米价亦减至四千以内。漳州府早稻亦已陆续收割,自十三日以后市价渐平,每石现卖四千上下。查自上冬以来贫民食贵已久,一时米价大减,舆情欢悦,如出望外各等语。同日又据派福宁府总运浙米之督粮道季学锦来禀,浙江头起米船已入闽境之南镇洋面等语,计日即可运到。加以早稻登场,粮价更当月减。”在专任督粮官员催办之下,名地粮食调入泉州受灾地区,粮价也得以趋平。道光《福建通志、台湾府》表明朝廷对闽南灾荒十分关切,特别是当台湾亦遭灾且无米可调运之时,更是严饬福建各府、州注意筹粮。如嘉庆元年(1796)上谕:“台湾一岁三收,今北路嘉义、彰化等属虽晚稻多有损坏,而南路台湾、凤山二县受风较轻,地瓜、番薯等项尚可有收。当劝谕居民广为播种,亦足以资民食。且风灾过后,勤于耕种,来春仍可稔收。尤当及时力作,不可稍有怠惰。再福、兴、漳、泉四府,夙藉台米接济;今台湾既被风灾,目下仅堪自给,明岁春收后或米谷充溢,可以运售内地,固属甚善;倘无余米可运,魁伦等惟当于各属丰收之处豫为筹备。并劝令百姓等撙节衣食,家有储蓄,不可再将米谷酿酒花费,致鲜盖藏,豫为明岁之备。”由于蔡牵集团的骚扰,台湾海峡洋面屡发劫案,造成台米难以输入闽南以解灾困,嘉庆十四年(1809)朝廷特此上谕:赛冲阿等称“闽南漳、泉二郡,向不产米,全仰给于台湾。从前商贩流通,食货赡足,皆缘商船高大,梁头有高至一丈数尺者;又准配带炮位器械,间遇盗船,克资抵御”;因蔡牵行劫,洋面不靖,“是以商贩不通,漳、泉米贵之由在此。”可见台湾输入闽南的粮食在抗灾渡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旦台米受阻,闽南即告粮荒。通过闽、台两地联合抗灾行动,两岸人民加强了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交流;这也有助于清代闽南地区的民间信仰在台湾的广泛传播与深刻影响。
四、明清时期泉州、台湾两地民间信仰的若干特点
由于以上所论证的明清二朝泉州地区频繁发生各种类型的自然灾害,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理念造成同时期泉州地区丰富多采的民间信仰文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泉州民间信仰的繁荣阶段,而且决定了这个时期泉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不仅具有全国城乡各地民间信仰的共性,即基本上与祈福禳灾、防灾减灾有关;而且具有若干特性,即务实性、多元性与人性化以及难融性。以下分别述之。
1.泉州、台湾地区民间信仰的务实性
面对层出不穷、接踵而来且破坏巨大的自然灾害,在防灾减灾手段十分落后的明清时期,泉州民众更是将祈求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形形色色的民间诸神,因而体现出更多的务实精神。就以泉州民众崇祀天后妈祖为例。由于明清时期中国又进入了一个灾害活跃的时期,水旱频繁,莆田在康熙初年的灾情就十分典型。如余颺《莆变纪事》“水旱”篇说:“甲辰自春不雨至于夏五月,官民步祷靡神不举。六月廾六日滂沱大雨,五昼夜不止。平地水涨丈余,庐舍漂流,无数居人攀木颠而处者。七日烟火断绝,积尸沟渠。城崩者三十余丈。……七月二日海波怒发,崩堤裂港,迤东一带数万余亩尽为鱼龙之窟。咸水入地,靡草不枯,又无颗粒之收。次年四月稍雨,五、六月又旱,斥卤之田十荒其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加倍地崇信天后妈祖,希冀妈祖能给闽南芸芸众生带来好运和生的希望。至康熙三年(1664),漳泉一带与莆田地界灾情更为严重:“春无雨,谷贵,每石一两银。四五月俱旱。五日十九日乃雨。六七月大水异常,城垣崩塌,石塞圮坏。八月初五日水灾,漳泉更惨。衙后林学绚发心弃产,收埋饿尸及暴露棺柩;有来报者不论远近,”均与土公携具前往收瘗。但是当地灾情益发严重,“康熙四年五月初一日道府厅县亦行捐俸,并会绅衿士庶劝殷实者量力乐输,在万寿宫分给。男女数千人纷纷道路,形容枯槁,衣杉蓝缕。少妇含羞手遮面而捉襟见肘;老人喘息,欲定神而前拥后推,扶掖而行,尚颠踬勉强进先仍落后。共放米四次乃止”。这一段时间水、旱灾反复侵袭漳、泉、莆各地,康熙朝陈鸿邦《莆靖小记》“康熙三十五年,自去秋亢旱,至四月谷价涌贵四钱五分。四月初小雨,洋田可播,高田无水”;以至各地官员百般无奈,除了求助于妈祖,又告禳于城隍:“步行至城隍庙设坛。是夜微雨一番。廿六夜大雨一次,廿七日午刻大雨,又晴,沟河竟无水。……众言须请黄石玄天上帝入城,可祈有雨”;多次祭神、反复折腾仍无济于事:“百姓奉神驾至东门外,竟大旱。谷价每石至五钱以上,贵不肯祟;肉价每斤二分,贱无人买。奉祀大洋大所张公圣君于凤山寺,用青白布制八角旌旗,次日小雨一番,次夜大雨二次,竟不济”。无奈之下只得向富户借粮:“各乡顽梗,查有积谷之家,数十为群,登门强借;不从,则居然瓜分而去。谷价至六钱以上,诸货皆贱,惟米独珍。近城诸井皆干,水亦甚贵”。[44]类似情形,惨绝人寰,史不绝书。闽台民间信仰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所形成的务实性、功利性特征,笔者另文已有所论述,可以参阅。[45]
2.泉州、台湾两地民间信仰的多元性与人格化
泉州人民包括包括移居台湾的泉人后裔在内,可以说将这个特性发挥得淋沥尽致。出于对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的恐惧与祈求平安的心理,人们将众多的民间神祗充分地予以多元化与人格化,也就是塑造多种分工不同的神灵,以应不同的防灾禳灾的需求。闽南与台湾人民所信仰的诸神名目繁多,都特别具有人情味,就这一点而言,似乎与其他省份、其他地区有明显的区别。凡是威灵显赫的神祗,都会得到闽南信众的虔诚信仰,信众们往往要给他们配一位夫人,以慰藉神灵苦闷的生活。如果某神已经配有夫人,自然就应该有儿子,所以还要增添王子或公主等神像。是此,就把想像中神的生活完全加以人格化,也就是与人类的生活完全相同,是人神同格的具体表现。神的配偶有二种,一种是由男女信众好心奉献给神的配偶,一种是传说中神本来就有的配偶。(1)奉献的配偶,如城隍爷夫人,由于掌管一方平安的城隍爷威灵显赫,信众们为了讨此神之欢心,通常都在城隍爷的后殿,供奉有城隍爷夫人。尤其是泉州的城隍庙,后殿更供有两位夫人,分别标记为城隍大夫人和城隍二夫人。又如土地妈,土地公是人们所最敬仰、又是家家户户最经常顶礼膜拜的神,因此信徒们也为其配有土地妈。不过据传说,由于土地妈不得人缘,所以原则上不将其配祀于土地庙中。只有特别同情土地公时,才配祀土地妈。再如西秦王妈,就是西秦王爷(即唐玄宗李隆基,闽南民间将其崇奉为戏神)的妃子,还配祀有公子。一般艺人为了能得好妻好子,往往要到这里来拜拜祈祷。(2)传说中的配偶,如圣王妈,就是广泽尊王(圣王公)的夫人。又如虺妈即保义尊王夫人,由于此神持别宠爱夫人,因而在祭典行列绕境巡行时,如果把夫人的神舆排在后面,就有惹起此神愤怒的危险;所以游行队伍只好打破男尊女卑的旧习,把夫人的神舆抬在前面。又如太阴娘,即太阳公的夫人。又如闪电婆,即雷神爷的夫人。再如盘古妈,即盘古公的夫人。闽南及台湾民间说法,广泽尊王(圣王公)的圣公妈,乃是此神自己所娶的夫人。西秦王爷(唐玄宗)夫人,是否就是杨贵妃则不得而知。其他更有王爷夫人、灵安尊王妈、有应妈、大众爷妈、开漳圣王夫人、三山国王夫人等。总之,闽南人塑造的神明特别具有人情味。
除此之外,为了使诸神不至于孤单,还有众多配祀。也可以分为二种:(1)与祭祀神职务有关的配祀,如城隍爷的配祀,有文判官、武判官;马将军、牛将军;延寿司、速报司、纠察司(阴阳司)、奖善司、罚恶司、增禄司;谢将军、范将军。除了以上各配祀神之外,还扈从有三十六军将与七十二地煞等神兵神将。再如青山王的配祀班子,则同于城隍爷。又如掌管瘟疫的王爷的配祀,就配祀有6位司官。大众爷的配祀,几乎和城隍爷相同,只因为是阴司,所以祭典时无神兵神将,仅和平日所祭祀的崩败爷神像有差别。福德正神的配祀为虎爷。司掌生育之神注生娘娘的配祀,按十二支配祀保母十二人俗称“十二婆姐”,各神像都抱一个婴儿。(2)与祭神史实和传说有关的配祀,如天上圣母的配祀有千里眼、顺风耳。关爷的配祀有关平太子、周仓将军。开漳圣王陈元光的配祀有辅顺将军、辅义将军。西秦王爷的配祀有田都元帅雷海青。佛祖释迦的配祀有韦驮、护法、伽蓝、监斋、十八罗汉。
此外还有挟侍,即站在主神左右的侍神。在佛教称为“挟侍”或“胁士”,不动尊的挟侍是制咤迦、昆羯罗,释迦的挟侍是文殊、普贤;道教也有挟侍制度,玉皇大帝的挟侍为太乙救苦天尊、雷声普化天尊。此外拥有帝号的神祗还挟侍有剑蓝、印蓝,拥有王号的神祗则挟侍有剑童、印童;文昌帝的挟侍为天聋、地哑,临水夫人的挟侍为左女娥、右女娥。这都是闽南民众根据主神的史实与传说而设置,信众为提高主神的品位,并使其更加人格化,才分别给各神祗配以挟侍。如皇帝格的神,配以剑监、印监;王爷级的神,配以剑童、印童;元帅级的神,配以神马、马丁;观音佛祖配以善才、良女;地藏菩萨配以左右佛童;祖师配以左右道童;妇女像的神配以左右宫娥,但仅限予妃以上的妇女像才能用宫娥,夫人以下的则不能称为宫娥;注生娘娘配以提粉、提花、提匣、提镜(即所谓香花女);魂身,配以金童(奴)、玉女(婢)。总之,明清时期的闽南信众为了从信念上抵御自然灾害的破坏,并修补以此带来的精神创伤,不断地塑造出多元化的众神并将之人格化,以应不时之需。
为了祈福禳灾和祭祀上的需要,闽南与台湾的民众还使用一种“分身”的方法,将闽南的神祗请到台湾或闽南其他地方,以供信徒祭祀;他们把寺庙主神和同一神像并祀在一个神龛内,但有大小新旧等级的区别;此外神像的敷彩也有所不同。例如,妈祖像的脸如果涂红就称为红面妈祖,如果涂黑就称为乌面妈祖,这就叫做“分身”。分身的数目很多时,就分别把各神像称为一王、二王、三王等;如果是女神则称为一妈、二妈、三妈等。如果主神是男神就称为“镇殿王”;如果主神是女神时就称为“镇殿妈”。除此镇殿王、镇殿妈的主神之外,都可以应信徒之请被迎奉到信徒所临时设的祭坛处,以便为信徒治病消灾与降福,完成任务后再由信众送回寺庙。由此可知,此类神祗的分身像,完全是为信众而制作,不过只限于威灵显赫的神才有分身像,因为只有这种神,信众才肯来招请,有时一个神能拥有十几座分身像。这主要是因为闽南各地灾害迭起,民众只得人为地给神灵分身,希冀在各地禳灾。
3.漳泉迁台移民的分类械斗与泉州民间信仰的难融性
福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难融性,或称之为文化的“碎化性”。尽管福建文化是多元的,但其中某些因素则如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是,互不渗透。特别在闽南民间信仰中能够体现出这种典型的地域特征。明清时期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与人多地少的基本格局,迫使闽南民众漂洋过海,去台湾谋生。来自闽、粤两地,乃至于闽南的漳、泉两地移民,由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而形成心理上的互不认同与严重对峙,从而导致依祖籍地而区分人群的分类械斗。“分类械斗”一词为湖南籍官员、曾任台湾鹿港厅同知的陈盛韶于道光六年(1826)成书的《问俗录》一书中提出,实际上始自康熙中叶台南的闽、粤移民之间为争夺田地、山林、水源等自然资源而爆发的大规模械斗。其后波及在台的福建漳、泉籍移民,乃至于在闽的漳、泉、莆等藉农民、绅士也大量卷入。曾任台湾道的姚莹坦言:“台湾大势,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广民在三四之间。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46]这里奇怪的是作为粤籍的潮州人反而认同闽南文化,所以在闽、粤移民械斗时,公开袒护闽籍移民。有时泉州一府各县间亦有械斗,即“分晋、南、安、惠、同”。[47]正如陈盛韶所言:“凤山、淡南粤人众闽人寡,余皆闽人众粤人寡”,但械斗中往往是闽人大败,主要是因为“闽人蠢而戾”而“粤人诡而和”、“不拒捕,不戕官”。[48]这些习性对于泉、台民间信仰的特征均有较显著的影响。由于台湾移民的祖籍地各不相同,因此语言、风俗、气质也就互异。同乡的移民团体就联合起来开拓新的土地,并且为了扩张势力范围,就奉祀故乡原有的神明;其目的是利用民间神灵信仰来加强内部团结,以便合力对付其他的移民团体。例如漳州人奉祀“开漳圣王”陈元光,而泉州人则奉祀“广泽尊王”,客家人更奉祀“三山国王”等,在民间信仰中有一定的不兼容性与冲突性。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造成他们极力地排斥外乡人。发展到后来,所有这些分类械斗并非是神明信仰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直接敌对,而是信众利用自己乡土的神明所进行的生存斗争。
我们知道,最早移民台湾的是福建泉州人,其次是福建漳州人,最后才是广东的客家人,而祖籍漳州的占80%。所有迁来台湾的三种人均具有强烈的乡土观念,于是乃演变成残酷的分类械斗。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康熙六十年(1721)漳州人朱一贵在台南发动的反清复明起义,闽南人起而应之并遍及全岛。这时居住在下淡水流域平原的粤人13大庄、64小庄,合计13000多人组织义军,号称“六堆义民”,以“拥清”为名与闽南人展开分类械斗。乾隆四十七年(1782)彰化县荆桐脚大道边上的,漳泉移民在此豪赌,由于在中发现有人使用“恶钱”(即劣币),从而导致漳泉移民之间大规模的分类械斗,彼此互相放火杀戳。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在台湾组织天地会起义,由于他是漳州人,其部下也多是漳州人,因此清军在募兵时仅限于泉州人和客家人。因而造成林爽文队伍对泉、客人的村落大肆报复。道光六年(1826)四月,彰化县东螺堡睦宜庄(今员林大饶)的客家人李通,由于偷了闽南人的一只鸡而成为导火线,闽、粤人之间大打出手,互相纵火烧杀,分类械斗的范围北到大甲溪之北,南到虎尾溪之南的嘉义县。把台岛上下一时搅得天翻地覆,人人自危。
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海盗蔡牵犯淡水,并攻打位于台南的台湾府城。时鹿港理藩同知黄嘉训担心蔡氏寇扰鹿港,就招募兵勇合力镇守港口。岂料所招乡勇全是漳州人,而鹿港居民多系泉州人,故次年二月乡勇入鹿港时,遂引发漳州人对泉州人的分类械斗。于是乡勇以讨伐土匪为名,对泉州人横加杀戳。当地泉人几乎陷入绝境,以致大量投海自杀。动乱之中,对方信奉的神祗便成了己方重要的攻击目标,例如台北漳泉人械斗时,泉州人便向漳州人的开漳圣王庙发动攻击,捣毁庙宇,掠走神像,并且挖掉神像的眼睛和鼻子,藉以迫使漳州人屈服。泉州移民还搬出福德正神来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志书曾载:“台北县三峡镇福安宫,主神福德正神。自乾隆五十年(1785)创建以来,神灵显著。嘉庆年间,漳泉人分类械斗,神助泉人,于双方严阵中,神凭童乩宣示:本神当出阵。次日果目击漳人阵中,忽现二十一斗士,纵横翻旗驱敌,致泉人战胜云。”[49]此类神话显系无稽之谈,但说明了两类移民文化的不兼容性导致了两者之间民间信仰文化的排斥性与难融性。咸丰三年(1853)八月,台北八甲庄的泉州同安人与漳州人合谋,企图攻打万华的泉州安溪人与晋江县、南安县、惠安县等所谓“三邑人”并加以驱逐,不料却招致对方反击,使八甲庄陷入兵燹之中。同安人势单力薄,落荒逃往大稻埕,同年十月再建新村落。之后又加入自新庄方向逃入的同安县人,才逐渐繁荣而形成今日之大稻埕。就是由于泉漳两府邑人世代的矛盾冲突,才使清末民初的大稻埕与万华人的敌对情绪难以缓解。咸丰六年(1856)与九年(1859),新庄的泉州人、漳州人与粤人发生械斗,泉州人中的同安人避难大稻埕,得附近泉州人之助把漳州人和粤人驱逐出新庄,漳州人出逃对面的板桥,粤人则亡命中坜。[50]以上仅举规模较大的分类械斗的例子。实际上整个有清一朝,台湾及闽南的分类械斗是层出不穷的。台湾的义民庙中,奉祀一些械斗中的丧生者,但是多为孤魂野鬼,他们暴骨荒野,后来多半被有应公庙收容。
甚至由于音乐流派的不同也会造成分类械斗之始作俑者。这就是起源于北管音乐团“西皮”与“福禄”两派的纷争。其由来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有林文章音乐师自基隆双溪来到宜兰,在此开乐馆收徒讲授音乐。而此前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有宣垦社通事漳州人吴沙,善于与居住此地的山地民族平埔人等沟通,因而立志开垦宜兰平原,他与当地土著逐渐将宜兰平原开发成功。至此,福建漳泉移民与广东移民陆续落户宜兰。由于吴沙祖籍漳州,因而在此定居者大多为漳籍移民。这些新来的移民青年多投奔林文章门下学习音乐。一时林氏名声大噪。但到后来,该乐馆竟分成两派即“西皮”、“福禄”,且两派对立日趋严重。原来福建地方的音乐大体上可分为“北管”与“南管”两种。其中北管又分成两派:一派的“弦仔”(胡弓)是用“提弦”和音箱(把椰子壳一剖为二)做成,另一派的“弦仔”是用“吊鬼仔”和竹子做成。前者奉祀西秦王爷,称为“福禄派”;后者奉祀田都元帅,称为“西皮派”。由于两派对立严重,且竞争异常激烈,以致宜兰地区的漳籍青年几乎全部卷入是非的漩涡,互相倾轧,不断打斗烧杀,对地方治安威胁极大。时至光绪年间,西皮派的首领简木根之徒,与福禄派的首领陈宝永之辈,纷纷在各地挑起械斗,从宜兰经头围一直波及基隆。宜兰知县林凤章抓捕两派头目各数名,并问以死罪,两派之争才略告平息。日据时期又死灰复燃,尤以基隆最为激烈。[51]这种因闽南信众崇拜不同戏神而造成血腥冲突,甚至绵延长达一、二百年之久的典型案例,实不多见。足见闽南文化因素中所蕴含的难容性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源的;并且与清代闽南地区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当然,泉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主要还是体现了追求平安、祥和的色彩。如厦门何厝就有早年遗留下来的风俗,该村顺济宫主祀妈祖,据宫中人说,每年农历的正月十六日,该村民众组织妈祖游神活动,均由邻近的关帝庙中的关帝爷前来“邀请”妈祖一起出游,因为在本地人眼中妈祖地位高于关帝爷。[52]这个习俗本身也充满了节日的喜庆和泉州人民的诙谐、善良。
注释:
[1]这个时期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已经发现的三个重大灾害群发期之一。即夏禹宇宙期(约4000年前)、两汉宇宙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明清宇宙期(公元1500年-1700年)和两个较小的灾害群发期,即清末宇宙期和20世纪60年代末迄今正在进行中的自然灾害相对频繁时期。参见高建国:《灾害学概论》,《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严重自然灾害群发期与社会发展》,载马宗晋等编:《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297页;任振球著:《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学出版社1990。
[2][5][6][7]《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3][4]黄仲昭:《八明通志》卷八十一“祥异、国朝”。下编第91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8][9][10][11][12][13][14][15][17]][36][37][38][43]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七一“明朝祥异”,卷二七二“国朝祥异”;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刊本。
[16][44]海外散人:《榕城纪事》;余颺:《莆变纪事》,收入福建省文史馆编《莆变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8]][19][20][21][22][23][24][29][30][31][32][33][34][37][39][40][41][42]水电部水管司科技司编《清代浙闽台地区诸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8年6月版。第298、303、305、311、339、348、349、376、418、432页。
[25]详见徐心希:《清代澎湖地区自然灾害研究》,《台湾研究》2003年第2期。
[26][27][28]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明清史料》戊编第九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5]详见乾隆《泉州府志》、乾隆《续修台湾府志》“灾异”篇。
[45]详见徐心希:《闽台民间信仰的功利主义特点探论》,《福建师大学报》1996年2期。
[46]姚莹:《东溟奏稿》卷四,台湾文献丛刊第四十九种。台湾银行研究室编印。
[47]刘家谋:《海音诗》。见诸家《台湾杂咏合刻》,台湾文献丛刊第二十八种。
[48]邓传安、陈盛韶:《蠡测汇钞问俗录》,“问俗录”卷六“鹿港厅、分类械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38页。
[49]台湾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1971年台北版第四册第276-280页。
[50][51]铃木清一郎著、冯作民译:《增订台湾旧惯习俗信仰》“绪论、寺庙祭神之地位”,第11页、第12页。台湾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11月版。
[52]详见陈衍德:《闽南粤东妈祖信仰与经济文化的互动: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76-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