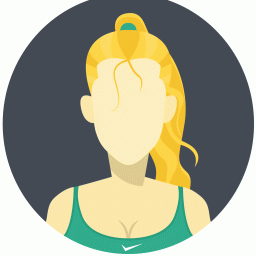环境保护传统治理的困境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环境保护传统治理的困境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国际合作,已经复杂到无法准确辨析孰是孰非、谁真正受益谁真正受损的地步。相互推诿、相互指责只能恶化全球性公约变为现实的困境。既然短期内这个全球公约无法实现,如果我们仅仅等待而不付诸任何行动,可能最终只能接受环境的恶化乃至最终的人类灾难。我们能否主动走出这个集体行动的困境?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环境保护治理,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成果的低排他性。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给出了非常悲观的推断,没有任何个体会自愿地增加自己的成本,比如改变自己在节能减排上的行动,以满足全人类在环境保护上的共同利益。因此理论认为一个外部的强制干预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期待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协议来引导全世界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京都议定书不仅没有达到一个全球覆盖式的公约,其本身的标准也受到许多批评家和环保主义者的质疑。可惜的是,全球层次上我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强权政府。因此,寄希望于“从上向下”式的集权治理是不现实的。实际中,在强权管理的期待之外,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自发治理机制。比如,虽然美国最终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已经有1026个城市自发加入了“美国市长级气候保护协商会议(U.S.ConferenceofMayors’ClimateProtectionAgreement)”,这个市长级会议的目的就是实现在1990年排放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减排5%。美国很多大学校园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激励机制,比如,在校园中进行在降低能源消耗和降低排放上各式各样的竞赛活动并把优胜者及时地公布于众,这种非经济激励的措施很好地实现了减排降耗的效果。据一项报告显示,这种非物质激励在一些大学中有效降低了32%的用电量。
在世界其他范围,也有很多地方性的自发尝试。比如,伦敦对城市中心区每天在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通行的车辆征收8英镑的拥堵费,这个基于经济调节的手段至少在初期确实改善了伦敦的交通状况,比如前三年(2003-2006)伦敦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20%。当然,后来规则上的漏洞抵消了经济调节的手段的效果。另外,各国政府也在探索碳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激励环境保护的行为。比如,美国从2005年起逐步在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区的10个州实施了“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GreenhouseGasInitiative,RGGI)”,这个RGGI实际上就是一个区域性质的“总量控制和交易(CapandTrade)”的减排管制方式。欧盟也建立了欧盟排放交易计划(EuropeanUnionEmissionsTradingScheme,EU-ETS),这种计划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授权和交易(CreditandTrade)”的减排管制方式。联合国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建立了碳汇基金(PrototypeCarbonFund)。这些都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探索自发减排尝试的典型性措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的各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措施仍然面临诸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污染的转移或溢出效应(Leakage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区位上的溢出效应,主要是污染从控制区转向了非控制区,而污染排放的总量没有任何减少。比如,欧盟排放交易计划和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实际上导致了将原本在欧洲或者美国的生产排放转移到了亚洲或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后者没有所谓的污染排放的控制政策。第二种是市场上的溢出效应,主要是从因为污染控制或补贴导致的目标区域内相关的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变化,进而影响到非目标区域的相关产品的生产行为。比如,因为在限制区内禁止砍伐导致的林木价格的升高,而价格的升高很可能会刺激其他未限制区的林木的过度砍伐。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这类环保计划不是全覆盖式,其效果就被降低了。另外,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激励为手段的环保措施还可能导致投机的现象。比如,京都议定书认定了几种高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值)的气体,包括R22和HFC23等。联合国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那些主动消除高GWP值的气体的个体获得相应的减排信用额度,而这种额度可以在CDM的市场中进行出售而获得补贴。比如,通过CDM机制,生产制冷剂的企业通过消除HFC-23而获得大量的核准的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ports,CERs),这些额度在欧盟等碳交易市场出售,从而给企业带来了“额外”收益。结果,这种补贴机制却诱致了一些企业的投机行为,即企业主动生产HFC23并销毁然后通过CDM获益,实际上这些企业对减少HFC23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这些以市场机制导向的环保措施出现的缺陷或问题,揭示了环境保护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是其正的或者负的外部性的不确定,还包括人类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地衡量和认知。这样,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增加,造成市场机制的失效。
综上所述,这些传统管理措施困境的本质原因就是环境保护这种公共物品的低排他性和不确定性,进而造成了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一旦这种行为过多,必然会损害更多人的合作意愿,结果就是使得环境保护落入了一种“公地悲剧”的结局。即使大家可能都有改变的愿望,但每个人面临的决策却类似于“囚徒的困境”。
二、治理结构的创新:超越传统的视角
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的悲观论调似乎终结了人类在环境保护合作上的一切希望。我们无法从自己挖的陷阱中走出,除非有人从外面帮我们一把。但是,这种传统的理论似乎过于盛行,以至于似乎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理论本身是否站得住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值得去思考传统的集体行动的理论是否是适宜的理论。第一,小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困境,总是有很多案例显示小范围的人类确实走出了困境;第二,环境保护的收益并不仅仅是一个“公共物品”,它确实也存在一些“私人物品”的特征,进而可能会引致合作的可能。首先,传统的集体行动困境缺乏一贯的证据支撑。近期有人专门回顾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集体行动的实证证据在详细审视见诸文献的个案研究、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中(既包括田野调查,也包括实验经济学或者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多智能体模拟等),发现即使有很多所谓的“搭便车”的现象,但也有大量的案例中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个体之间的合作。所以,这就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我们要解决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否真的只能从传统的悲观理论入手?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诸如温室气体减排的努力不是绝对的“公共物品”,它有可能是某种“私人物品”的副产品。比如,一个家庭在考虑是否买一辆节油的汽车,可能更多的因素是节油的汽车后期能够节省用车成本,但当该家庭购买了节油汽车时他们确实也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做出了贡献。一个社区为了提高整体的美观和降低生活成本,统一设计并安装了太阳能装置以及污水处理系统,这样不仅他们自己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也对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贡献。一个城市为了解决交通拥堵,对汽车的行驶进行一定的限制,在缓解了交通拥堵的同时,也对减少排放做出了贡献。一个国家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而淘汰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产业,在优化了自身的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减少了排放。这些例子还有很多,关键就是都给出了传统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不曾关注的问题:首先,集体中的个体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出现主动的合作;第二,集体行动不一定是以牺牲个体利益最大化为代价的,也可能出现在满足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同时实现了集体行动。这就给我们在解决当前环境保护治理上的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实际上可以不依赖于外界的强制规则来实现集体行动,我们也可以不等到环境污染对每个人切身利益产生影响的时候(即外部性被内部化或者类似于公共品被私有化),才来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之间有信任和互惠,当我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收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在强权管理和市场内化两者之间找到第三条路。这第三条路就是公共资源管理中常说的多中心治理的模式(PolycentricGovernance)。多中心治理模式最初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关注特大都市中众多的公共或私人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究竟是一种混乱管理,还是一种潜在的、高效的秩序安排。多中心治理,是指由在正式关系上相互独立的多个决策中心组成的,在一定程度因相互之间的竞争性而彼此关注,又会在一定条件下主动寻求合作,当出现冲突时还可以寻求一个共同的上级进行裁定。从一定意义上看,这样的“混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系统”。
多中心治理的模式,实际上为我们全球环境保护的治理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我们不再需要一个明确的外部强权,而是通过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组织和不同个人在保持独立关系的前提下,在面临着竞争和合作的诉求下,在满足个体利益的基础上,为全球的环境保护做出不断地积累性的贡献——全球的环境保护,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要实现的目标,而是一种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逐渐积累,既是指每个人在获得自身利益的同时,对环境保护的正的外部性;同时也指的是每个人在造成环境污染的同时,能够主动减少一些损害。个人、组织、地区、国家等在不同的层次上承担着多中心中的一个中心的角色。这些中心在特定信息和知识上具有特定的优势,同时也能够自动地去向他人学习,关键是他人也是在进行着不断的试错(trail-and-error)过程。当越来越多的中心加入了这个治理结构,所谓的集体行动中自私、缺少奉献、独裁、歧视等问题就可能被自动解决。多中心的方式在相互监督、学习和调整方面具备着值得肯定的优势。这种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在环境保护治理上至少有两点优势。第一,它避免了陷入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而无法自拔——我们可以放弃等待全球统一的规则而开始行动;第二,正如前面所说,当个体(子中心)认识到环保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收益,尤其是存在个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可能,而且虽是小范围的努力但却可以不断积累和放大,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断言未来在降低排放等环保措施上会有更多的自愿行为的出现。
三、中国当前的环境治理路径的选择
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不作为而等待全世界一致的行动是最危险的选择。与其那样,不如我们和其他有着类似认识的国家一起先行动起来——这已经是多中心治理的模式了。而对于中国来说,最主要的也是在中国内部形成类似的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规则。
首先,我们要理解中国的环境治理是属于世界环境保护多中心治理中的子中心,我们本身应该在与其他国家在环境保护上建立好一个独立、竞争但又合作的关系。我们既不做“冤大头”,也不能做一个自利的国家。我们能做的是,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世界环境保护的正效应,在各国之间的相互学习过程中树立自己的地位和榜样。
其次,在国内我们也应该从中央强制性的集权管理思路中跳出来,理解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可能效果会更好。这种多中心的模式是发挥地方、企业、个人的主观意愿,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让大家认识到自身利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同向联系,避免个人利益的无限膨胀,同时在相互学习中形成互利互惠和信任。
再者,对当前的以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为导向的非合作行为,政府既可以运用强制性的干预措施,改变行为人的预期,也可以通过一种积累性的非经济利益导向,培养一种合适的环保的价值观。这些包含在了当前政府的环境保护的管制措施和公益宣传中。可能很多人会质疑上述建议的有效性,但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一种积累性和渐进性的活动。我们不必要纠结某种具体的措施的效果,只要坚信长期上必然的价值。建立一种多中心的治理机制,实现合作的分权化和市场化,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信任的产生。单个中心针对自己面临的问题进行有限理性的设计,然后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而不断“摩擦”、“碰撞”、“消耗”、“协调”。更高层次的决策者只需要建立一个利于“摩擦—碰撞—消耗—协调”的机制,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则可以相对低成本地就地解决了。
作者:谭荣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