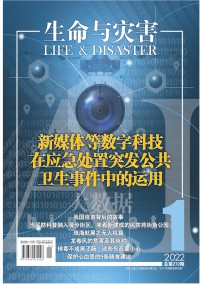生命界限哲学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生命界限哲学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永生不死”无疑是伴随人类发展始终的一个诱人的话题,其中蕴含着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历史和浪漫的想象。随着“知识论”的对象化、因果性、合逻辑性、经验性的对对象的认知方式成为人类主要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永生不死”的问题渐以其“形而上”的玄学特质遂淡出了人们的认知界域,其话题的意义也就仅限于宗教和神秘文化。韩东屏先生在《克隆转忆人——供人类思考的思考》一书中,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对“克隆人”的解读中,依据哲学之“我”逻辑意义的理性规定,提出了“克隆转忆人”的概念,并在“我之克隆可以是我”的论证中为传统的“永生不死”的问题注入了知识论的逻辑,在现代科学知识概念系统中,为“永生不死”的问题找到了新的位置,“永生不死”的问题重在知识论的意义域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这个背景下重提“永生不死”的话题,背后或许蕴含着人们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某种超越性思考,本文的主旨是想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对“克隆转忆人”概念所引发的“永生不死”的话题做一些思考,力图解读问题背后的文化意义。一、“永生不死”观念的历史轨迹与问题的逻辑设定虽然克隆技术的应用还仅限于人之外的生物界(继韩国黄禹锡克隆人类胚胎于细胞造假丑闻之后,近日,面对是否应该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的伦理学争论,美国哈佛大学宣布将开展克隆人类胚胎于细胞的研究,这说明克隆技术开始走近人类本身),但“克隆人”这个虚拟的概念却把人的世界搅乱了,人们在克隆技术是否应该应用于人类的繁殖,“克隆人”的出现会给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等价值评判上进行着广泛的争论。“克隆人”之无性繁殖以及遗传密码的转移使“永生不死”的话题重被提起。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不同的命题:“我之克隆非我”,抑或“我之克隆是我”。前一个命题实际上得到了论战各方的一致认同,而对后一个命题的论证来自韩东屏先生的《克隆转忆人——供人类思考的思考》一书。韩东屏先生依据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资料说明“记忆,就是保持‘我之为我之物’”。他指出“记忆,是对个人自我意识的保持,是对个人习获知识的保持,是对个人思维方式的保持,同时也是个人对以往经验、实践的确认,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自己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关系的确认。一句话,是对自己以往历史的自我意识。”……“我之所以是我,乃是由于我有由记忆维系的历史。”依此为理论论证基础,提出了“克隆转忆人”的概念。其内涵即为:我之克隆+我的记忆移植=我的转世(或复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理论模型的基本思路在于以“我之克隆”作为“永生之身”,以“记忆移植”作为“永生之心”,从而以身心合一的永恒性来论证“永生不死”这个命题的合理性。“永生不死”的话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作为有着“永远”诉求欲望的人而言,总是希望人的生命能永远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永生不死”之路经的想象,可以说,关于“永生不死”的不同观念记载着人类对自身生命意义认知的历史。从思想的历史来看,关于“永生不死”的话题大致有三类不同的解释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围绕着对“身”、“心”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解释而形成的。这三类模式是:道教”文化中的“长生不老”的模式。道教重生恶死,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久世。张伯端说:“世人执其有身,而悦生恶死,黄老乃以修生之道,顺其所欲而导之。”(《悟真篇后序》)认为人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就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因此也就产生了许多修炼方法:炼丹、服食、吐纳、胎息、按摩、导引、房中、辟谷、存想、服符和诵经。可以说,在道教文化中于个体生命上求丹养生成仙是其主要的精神诉求。在历史上,这些思想影响了秦始皇、汉武帝等都试图通过外在的灵丹修炼达到长生不老。尽管长生不老只是想通过人的身体的机能延长生命,但其在思想的出发点上还是对“永生不死”的一种向往。道家文化崇尚自然,对于人的生命个体的认知上是把生命归之于人之身,从而强调强身健体之修身之道,养生就是修身。葛洪讲修仙“其事在于省思寡欲,其业在于全身久寿”(《抱朴子内篇·释滞》)道教崇尚的自然之境界就是人道一体,天人合一,物我不分。从“永生不死”的话题来看,道教仙学的“长生久世”(“永生不死”的一种模式)是建立在以身统心的观念基础上的,其求永生之路只能是“内丹仙学”。这种观念支持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敬身为上”的意识。其对身之永生的祈盼在形而下的视阈中可能性越来越小,其所建立的“永生不死”观念只能让位于形而上的玄想。2、“佛教”文化中的“三世因果”、“生死轮回”和“灵魂转世”的模式。缘起论与因果论是佛法的核心。所谓缘起就是“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有、无之缘起是“同时相互依存”,生、灭之缘起是“异时互相依存”。这种同时互存和异时互存关系,就是佛教的因果原则。在佛教看来,从时间上来说,由于无数的异时因果连续的关系,从空间上来说,无数的同时互相依存的关系,组织成为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交错网络,。这就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相续不断的因果律。依缘起和因果的原则,佛教建立起了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之说。即:“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在佛教看来,世界有成住坏空,众生有生老病死,万物有生住异灭。即:“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对现世而言,有生有灭,有生有死。但对三世(前世、现世、未来世)而言,则“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即:“诸法无我,涅磐寂静”。就是要用无常无我的观点,发心修道,断苦恼因,勤休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到了功行圆满,就能够了脱生死轮回,证得不生不灭寂静安乐的偏真涅磐境界。这是小乘佛教三法印的道理。可以看到,佛教承认生、死在现世的存在,但把生死看作是不实的幻像,所以要“诸法无我”,才能了脱生死的限制。正是在这种缘起论和因果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三世轮回”和“永生不死”的观念。从佛教的观点,生死的区别是将诸法无常执为真常,所欲执著是由于妄执有我。只有诸法无我才能了脱生死。另一方面,佛教依据三世因果的道理解释灵魂转世,藏传佛教中的转世灵童和《西藏度亡经》对灵魂转世的看法都缘于这个道理。可以看到,佛教对生死问题的了脱或消解思路,是承认“身”之生灭,把永生不死一方面放到对“心”(灵魂)的无住性把握,为灵魂转世和灵童现象提供解释;另一方面就是以“空”来消解生死问题的意义。也就是说,一方面在“有”界为了脱生死寻找一条“永生不死”之路;另一方面在“无”或空”界消解生、死或永生不死问题的意义。可以说,佛教对“永生不死”的看法具有逻辑上的圆融性,但已陷入一种神秘的不可解说的境域。3、西方知识论视阈中的哲学与科学的模式。实际上,从人本的生存愿望所生发出来的“永生不死”的欲求,在宗教中获取了意义。当这种欲求作为有无可能的问题时,就注入了理性的逻辑。作为科学的理性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是经验实证,一种是合逻辑的推论。对前者而言就是依据经验实证的原则,寻找到一种可操作的技术,延长人的寿命,以逐步接近“永生不死”的理念。现代生命科学中的许多技术都属于这种思考方式,如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纳米技术等。在乐观技术主义看来,通过越来越发达的纳米技术转变基因结构,以此来延长细胞生命是完全可行的。由于决定我们疾病、老化等情况的是基因,因此,如果一方面我们能不断地发现致病、致老的基因,另一方面努力找出抗衰老的因素,改变前者,利用后者,老死的自然规律不就可以被人类战胜了吗?对后者而言,就是在逻辑上为“永生不死”寻找到一种合理性的解释模型,依据狭义相对论“光速不变原理”对时间与空间的解释就是一种对“生命之永恒”的解释模型。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一个运动的物体,它的运动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时间就停止了,它的体积变作无限小,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越了四度空间。如果我们人能够以光速运动,没有了时空的规约,就可以长生不老。“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整个儿宇宙是从一个数学点,一个Singularity爆出来的,那个点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可以有超光速,也就没有生与死的区别了,因为在那里是九度时空。显然这是依据科学的逻辑原理的合逻辑的推论,这种推论并不能在经验中得到证实。从对“永生不死”观念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到,虽然有众多不同的对“永生不死”欲求的解释模式,但都是在人是作为以身统心,还是以心统身的不同理解中来思考的。道教和科学是把人的“永生不死”理解为“身”的永恒性;而佛教则是在“心”的永恒性中寻找“永生不死”的意义;“克隆转忆人”的设想则是想在人作为“身心统一”的视阈中找到“永生不死”的理由。应该说这些观念和认识表征着人们的生命意识,也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一种认知。就“永生不死”的话题作为“问题”而言,从人本身对“问题”之可能的把握能力来看,我们只能在可能的域限内发问,也就是说,要使得“话题”作为“问题”有意义,就不能超越我们可能的把握能力来发问。如此来看,“永生不死”问题可能衍生出这样一些问题:首先,从元理论的视角看,就有一个“永生不死”何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是说“永生不死”在什么语境中或意义域内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这是要确定问题的意义域。其次,从以对象化的知识论的发问方式来看,“永生不死”的问题就可以分解为:什么是生命?生命的本质规定是什么?生与死的界限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如何超越?有没有什么手段使生命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延长生命是一种量的问题吗?永生不死在技术上有无可能?其三,从哲学之自我意识的“问答逻辑”来看,“永生不死”何以可能?其作为人本的欲求价值意义是什么?作为人的“自我”与生命的关系?哲学对人作为“身心统一”的思想,何以能够从观念的逻辑设定确定问题解决方式的合理性?“永生不死”对人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其四,从宗教之“以信求知”的意义确定模式看,“永生不死”在信仰的语境中是无可怀疑的,无论是佛教的“三世轮回”、“灵魂转世”,还是基督教的“再生与复活”,抑或是道教的养生之道而长生不老,都说明“永生不死”是人对人之上的世界的一种意义确定方式。无论是“神”的世界,还是灵的世界,都是对“永生不死”的一种观念上的解释模式,只不过这种观念是以“信”的方式确定的。从历史与逻辑的同一性中来看“永生不死”话题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宗教、哲学、科学上对生命的认知,实际上是人对自身的一种自我意识。从科学实证的视角确定其是否可能,还取决于我们对“可能”的观念,以及对“具有实证意义的“现实”的意义的确定。所以,“克隆转忆人”的概念也是对“永生不死”问题在观念上的一种拓展,即对“永生不死”的问题要在“身心之统一”的视阈内来把握。二、“死”的存在意义在于为“生”作为人的第一价值原则划界人是否能够“永生不死”,从逻辑上看,只能有“能”或“不能”两种选择,其如何选择取决于如何对生与死进行定义,就是说取决于人们关于“生与死”的观念。依据某种知识论对生死的定义去寻求某种以延长生命为指归的对“永生不死”的诉求,作为一种科学的信念无可厚非,这种诉求对因果律制约下的生物学意义的生命的探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其“是否可能”的疑问所带来的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概念的质疑,追寻的是“何以可能”的哲学逻辑。我认为“永生不死”的话题,背后隐藏着的是人类文化的遗传密码。人类是否可能改变原有的天道和自然逻辑,可以留给科学家在因果律作为“信念”的宗教性情感的支配下进行探索,我们只对“永生不死“话题中的生与死的观念做哲学意义上的诠释。为什么人会有“永生不死”的愿望?为什么要寻找能够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为什么寻求“永生不死”在观念上的更新?为什么要“复活”?为什么要“轮回”?这些问题会引导我们走进“存在”的境域来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这些看似有些幼稚的发问,却包含着人类存在的两个底线原则,一个是这种发问是基于人类独有的从“同一律”演绎出的因果律原则,由此人们才会有“为什么”的发问方式。另一个是基于“生”与“死”的存在性。就是说我们的发问是建立在生与死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作为对人的规定。所以思考“永生不死”的话题首先要讨论生与死的存在意义,而“永生不死”则是依据“生与死”的存在而衍生的一种愿望和观念。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生与死作为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规定,是人作为人的原始的自然与逻辑起点。从文化的起源看,各种文化形态无不是以人的“生生之道”作为逻辑上的原点。我们知道,任何文化都首先从我们和世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开始思考问题,无论是西方文化中的“创世纪”,还是中国文化中的“盘古开天地”,抑或是印度元典《奥义书》用梵生空、空生风、风生火、火生水、水生地、、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从泰勒斯的“世界的本原是水”开始了西方理性文明对“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探索。从《周易》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方有几千年来中国“实用理性”和“血缘亲情”制约的“伦理政治”的不懈传承。宗教、哲学、伦理、政治、科学等文化形态无不是发源于“生与死”对人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因为有了生生之道,就有了对来源的寻觅,有了“死亡”的划界,也就有了到哪里去的思考和期望。因而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可以说,人类的文化离不开人的生与死这个前提和原点。从哲学的存在论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中有“有无之辨”,西方哲学中有“存在者”与“存在”本身的区别。巴门尼德讲过,“……只有哪些研究途径是可以设想的。第一条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遵循真理。另一条是: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因为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可以说,中西哲学在存在的意义上由不同的进路形成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界域。中国哲学的“有无之辨”讲究的是“生生之道”,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第一章)此为生生之始,即道之为有、无。由此才有“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的宇宙发生论。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则以“是什么”的逻各斯追问存在的本原,即要为存在本身贴上“是什么”的概念标签,依此去说明世界万物的逻辑因果,世界万物的存在何以如此?这种为世界万物寻找归宿(不管是本源之规定还是本体之规定)的努力都是人们的“生”的存在所启示意义的变形。可以说,“生”的存在为由“区别”的规定构筑的由一而多的世界建立了前提。“生”不仅在自然律上有“生命”的创造,而且在文化的语境中,使人们对区别中的两个世界有了说明解释的欲望。也就是说,“生”的意义缘于先民的“生殖崇拜”,即何以由我“生”出个“非我”,这个“非我”还是“我”吗?与原来的“我”有何干系?这种“自然之我”上升为“概念(观念)之我”,就有了意识上的“自我”与“非我”的区别,这个区别非同小可,因为在说明与解释欲望的驱动下,就有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界域的划分,就有了应该与否的价值选择与评判。从而就有了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乃至科学。可以说,“生”的存在意义就是人的世界的第一价值原则。“生”作为价值原则是以“死”为界的,我们很难设想没有界限的无限的“生”。与“生”相伴,也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死”和文化意义上的“死”。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也具有存在性,这种“死”为“生命”划定了界限。从宗教的眼光来看,由“死”划界的“生命”在时空中的存在是一个定数,因而“生命”具有宿命性。从“死”作为人的这种存在者的有限性和终极性来看,它为其存在划定了界限。如果说“生”为人的存在指出了“应该”,则“死”就为人的存在划定了“不应该”的界限。在海德格尔看来,在解释学的视阈中,只有当缘在就在活着的或者生存着的时候达到了死亡,“活着经历死亡的可能性”就是作为意识根基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存在论化。所以,缘在就是“朝向死亡的存在”,从生存于世那一刻起就活在死亡这个最不可避免的可能性或缘分之中了。就是说生与死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相伴的。可以说,没有“死”的划界,就没有了“生”的意义。“生”的意义在于面对可能性的选择,而如何选择则要依赖于“应该”的设定,“应该”与否则要从“生”的存在出发来确定。但这些应该如何的价值原理不能离开“不应该”之设定的“死”的存在性。所以说,“死”的存在意义在于为“生”作为人的第一价值原则划界。“生与死”的存在意义在于使人就是人,人不是上帝。“永生不死”表征着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并不满足于仅仅是人,他还想成为上帝的愿望的本性。当这种愿望转化为“灵魂不死”的观念,则如康德所言,就有了人类道德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根基了。三、结语综上所论,在不同的视阈中,“永生不死”的话题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依据因果观念寻求作为“身”的“永生不死”的科学认识无可厚非,它可以找到延长“生命”的时空意义的方法,对人的自然存在有积极意义。“克隆转忆人”的概念,在“身与心”的统一上寻求“永生不死”在观念上的超越和更新,也是逻辑上的推衍和设定,它在新的视角上把握“生命”的意义无疑更新了我们的生命观念。如何在“身心统一”的视阈中为“永生不死”寻找到合乎人们日常信念的观念支撑,不仅需要科学视野的扩展,更要有思维方式上的更新,弗洛伊德在“身心统一”上所展现的思路可能对我们有所启示。不论是在哪个意义域中思考“永生不死”,都离不开作为人本身独有的理性自我解释系统的“同一性”的逻辑要求。可以说,“永生不死”的话题体现了“同一性”逻辑的无矛盾性的欲求。但“生与死”在存在的意义上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思想想象空间。我们是存在的,我们需要“生”赋予的创造给予世界以多样性,从而确立“应该如何”的价值原则;我们也需要“死”为人的有限性和终极性划界,以确立我们的“不应该”的价值边界,我们也需要“永生不死”为道德形而上学找到先验预设前提。可以说,“生与死”的“应该”与“不应该”确定了生命的意义,为生命划定了界限。也可以说,有了“生与死”,有了“永生不死”的观念,才有了文化,才有了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