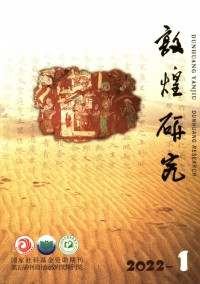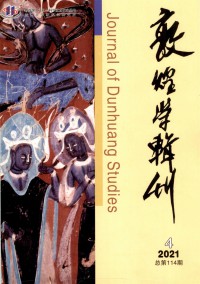敦煌文学论文:敦煌文学表达特性探究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敦煌文学论文:敦煌文学表达特性探究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本文作者:赵蓉刘为民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特性的介绍见诸众多文献。学者们大多借助“民俗”(民间文学)理论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由广大民众集体口头创作,能表达他们的共同心声,并在广大民众中世代流传的文学艺术,具有民间性、生活性、传承性等基本特性鲎。我国著作权法则从法律角度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性概括为区域性、集体性、传承性等。对此,本文以为,无论是从文学艺术本身特性抑或法律特性方面,回归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本源——区域民族性、民间本真性与集体创作性,是界定和区别不同种类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内涵之基本要素。而传承性则是其受法律保护的前提。这对分析和考察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而言,也是如此。和南道“三条线路”鲕。伴随着中西经贸繁荣,西域诸国及中亚的宗教、歌舞由此东传内地;中原的歌舞、汉文典籍也随丝绸、瓷器从这里传播世界各地。此时的敦煌,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已然担负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的重任。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区域和文化环境,使得敦煌民间文学艺术从产生时起,即“具有了鲜明个性,显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这种鲜明的个性,首先表现为敦煌民间艺术表达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体现了本区域民族文化特征。即使是对敦煌石窟佛教文化艺术而言,它也是“东传的佛教在一个具有成熟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地方的特有产物,是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宗教刺激下出现的新形态。”一般而言,形成于某地的民间文化艺术,其本民族范围内认同感更强烈。但是在长期的文化流传过程中,一些反映人们精神追求的共性的东西,也往往会突破地区、语言的障碍,流传到另一个民族地区,为当地民族接纳和吸收后,以当地域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表达并随之流传开来。当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考察印度佛教文化艺术在敦煌的传播过程时,也发现存在同样的轨迹。无疑,佛教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固有敦煌乃中西贯通之咽喉,最先接触佛教之先驱因素;有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民众寻求佛教“出世避祸”的现实需求;但更有与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义思想宣扬的社会基本人性、道
(一)区域民族性
敦煌民间文学艺术的创生源于独有的内外环境,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孕育与滋养。我们只有从这一大前提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敦煌民间文学艺术产生的历史脉搏。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枕祁连,北通大漠,处于我国古代境内外各民族交往的十字要津,扼居中亚、西域,交通华夏中原的关口。公元111年,汉武帝平定匈奴,“分置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鲑。后历经各朝政权,通过迁徙汉人居住,保持汉族戍卒,调整民族关系等积极措施,河西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得到了与中原汉民族文化同步发展的历史契机。汉晋文化在此生根和发展鲒。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有地域性性质。”鲔其间,敦煌作为历史上羌戎、乌孙、月氏、匈奴、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粟特、于阗、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先后聚居的地区,与汉民族共生共息,共融发展,形成了农业定居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特征。农业定居文化为中原文化的进入与渐居主流地位奠定了基础,而游牧民族文化则为中西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提供了土壤。这一多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敦煌文化开放与守成的双重性。而从敦煌文化艺术的外生环境看,经贸的繁荣,也为中西文化交汇提供了可能。隋时,“炀帝西巡”,遣使节出使西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形成了连通西域,“总凑敦煌”的北道、中道德、秩序主旨相吻合的内在关联。人们祈求佛陀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邻友好、健康长寿,人们崇敬三宝(佛、法、僧),尽心尽力开凿洞窟,修建庙宇,布施师僧,燃灯浴佛,把佛事活动作为尽忠尽孝的一种重要方式,故佛教的传入非但未受到世俗政权、百姓的排斥,反而得以推崇。如《魏书•释老志》所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伴随着这种融入传统中原儒教伦理思想的本土佛教文化观念的逐渐形成和深入民间,宣扬世家儒家文化的忠孝观和中原文化开始出现在壁画艺术中。“北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洞窟共18个其壁画多为佛本生故事和千佛为主要题材。北周时期的洞窟共10个其壁画内容则首次出现了讲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壁画中不仅有为“观佛修行”目的各类佛教画,还有描绘民族神话传说的神怪画。如莫高窟第249窟、285窟中集中了伏羲、女娲、龙、凤、朱雀、飞仙(羽人)、飞廉、方相氏、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形象,它们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形态。段文杰先生对此评价道,“这类土生土长的题材经常和佛教故事画在一起,形成了‘中西结合’、‘土洋结合’把道家的‘羽化升天’和佛教的‘极乐世界’形成了一体,这正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逐渐‘民族化’,和道家、儒家思想逐步融合的反映。”她“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看,由于物质文化的创造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过程,因此,人类的精神文化,如风俗、习惯、禁忌、道德、宗教以及政治制度等,其本身虽不属于物质文化的范围,但它对物质文化的价值取向,却会发生十分强烈的影响。它可以决定物质文化的具体发展方向,甚至对其发展起推动或阻碍作用。故此,史苇湘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不仅是敦煌文化艺术的基础,而且是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其内容与形式以及对内地和西来的各种艺术风格选择取舍的主要决断力量。”与此同时,敦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在坚守自己传统文化、本土文化的同时,还展示了其文化开放和包容精神,表现出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独有文化艺术魅力。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例。石窟寺的建造源于天竺,但敦煌石窟的建造却是在崖面凿窟的同时结合了我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特点。不但石窟内部,而且其外面同样有用木头修出来的窟檐、柱子等,“等于是造一个房子把这个石窟盖在里面”。至于后来敦煌石窟发展出的“殿堂式的石窟,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寺庙了”。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则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又一杰作。“飞天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为一的结果。”可见,敦煌文化艺术是在长期多元文化交流中,汲取中西、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有益成分,创生出的一种更具本地域民族文化色彩的独有的民间文化艺术。
(二)民间本真性
敦煌民间笃信佛教,但更注重“用重于信”。当敦煌民众通过艺术手段塑造一个个佛陀、描绘一幅幅“净土世界”时,他们把对世俗生活的热情和美好向往融入了对“佛国世界”的理解和想象,使得敦煌民间艺术表达为反映现实生活的率性需要而创造,凸显了其民间艺术的“本真性”。例如,敦煌石窟壁画艺术中,小孩“聚沙成塔”皆可成佛(而不是“累世苦修”)的《法华经变》;环绕在弥勒佛周围的“一种七收”、“树上生衣”、“路不拾遗”、“女子五百岁出嫁”、“送八万四千岁的老人入墓”的《弥勒上生下生经变》;一心念佛,“九品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变》;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无救、无归、无医、无亲、无家等待苦难皆可得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药师变》等等。这些表达当地普通民众修行佛法的美好向往,抒发他们的心声的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佛教的信仰,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使这样的艺术表达更真实、更亲切,他们甚至将世俗劳动生活的场景,也“搬到”壁画中。如,人们在壁画世界中描绘的“弥勒净土世界”同现实世界一样,要耕地、播种、收获、收割、打谷、扬场,要向地主和官府交租(第445窟);有行走在千里迢迢的丝绸之路之上的风尘仆仆的商旅(第296、302窟顶、420窟)与泛海商途中陷入困境行劫的风险(第45窟南壁);有儿童在学校读书(第231窟)、牧羊女在圈棚边挤奶(第159、9、61等窟)、官府在拷打百姓(第159窟)、男女谈情说爱(第85窟)与嫁娶婚礼(第12、85窟)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众生实相”,“早已超越了宗教信仰,真正成为了充满无穷活力,透着浓浓生活气息的民间艺术。”
(三)集体创作性
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具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还表现在,它并非某个个体的创作行为,而是群体智慧的结晶。从历史看,世居敦煌的人口中有本地少数民族、中原移民,也有西域各民族,在这样一个民族大融合的环境中,各民族基于对共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追求的认同和精神生活需要,集体创造着适应本地域多民族共同精神生活需要的民间文学艺术。以敦煌石窟艺术表达的创造为例,虽然体现了捐窟人个人目的和需要,但真正凿窟、绘壁与造像的无疑是具有高超技艺的民间画(塑)师、心存虔念而又以画(塑)技艺谋生的穷苦匠人、有一定打窟经验的下层工人等构成的庞大的创作群体。这在敦煌遗书中有大量记载:“选上胜之幽岩,募良工而镌凿。”(P.3405《营窟稿》)“更凿仙岩,镌龛一所,召良工而朴琢,凭巧匠以崇成。”(P.4638)“乃召巧匠、选工师,穷天下之谲诡,尽人间之丽饰。”(P.2551)“匠来奇妙,笔写具三十二相无亏;工召幽仙,彩妆而八十种好圆满。”(P.3556《康贤照赞》)。对这些民间艺术创造者的行为,史苇湘先生充满激情地予以了评价和肯定,“谁是莫高窟艺术真正的创造者?广义地讲,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地方普通的农牧民、手工工人、下层士兵和各族劳动者。他们是敦煌佛教的基本信众。莫高窟的建造,他们不但是物质条件的提供者,是凿窟劳役的承担者,更重要的是那些工匠,他们是敦煌壁画、彩塑艺术美的直接创造者。”当然,强调民间文学艺术的集体创造性,并非一概否定民间专业艺人的存在。事实上,在民间文学艺术的长期创造和传播中,特定范围的世家或师徒相传往往是民间文学艺术不断被创造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往往是一批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民间艺人队伍。敦煌壁画的画师中,也有一些职业画师存在。如瓜沙归以军节度使军府里设有画院、上置都勾当画院师、下置知画行都料、都画匠、都塑匠等。此外,还有当地寺院画家和来自西域或中原的画师等。《节度押衙董保德建造兰若功德颂》就有对敦煌画师董保德的技艺的记载:“手迹及于僧繇,笔势邻于曹氏。画蝇如活,佛铺妙越于前贤;邈影如生,圣会雅超于后哲。而又经文粗晓,礼乐兼精,实佐代之良工,乃明时之膺世。”可以说,正是这些民间专业艺人的加入,使敦煌石窟艺术有了更为生动和丰富的表现,成就了敦煌民间艺术表达的辉煌。综上,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是由敦煌这一特定文化区域内的多民族,在坚守我国传统、本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艺术,集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艺术成果。区域民族性系其第一特性;民间本真性系其第二特性;集体创作性系其第三特性。
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外延:多元化类型与多维度表现样态
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十分丰富,不仅有民间口头、语言表达;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宗教信仰、神怪故事与传说;民间服饰艺术表达;还有民间壁画、雕塑、建筑技艺;木刻版画、葫芦雕刻、壁画剪纸技艺;石窟壁画、雕塑、建筑美术图像艺术表达等等,体现了成果类型的多元化。在表现方式(载体)上,既有通过口头、肢体语言表现,还有平面、立体三维表现,特别是敦煌壁画、雕塑、建筑图像美术艺术,这种实物表达形式既是这类民间艺术的客体呈现,又是承载表达内容的有形物质载体,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多维度表现样态。为清晰表述上述内容,本文以敦煌民间文艺表达的成果客体的多元化为中心,区分非石窟和石窟两类表现载体,将敦煌民间文艺表达的成果类型分为文学艺术作品与类非作品表达两种。图例归纳与说明如下:
(一)敦煌口头说唱文学、语言表达
典型的敦煌民间口头文学有: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等讲唱文学。例如,河西宝卷即是至今流传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的民间讲唱文学的代表。它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文学。河西宝卷盛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主要有佛教类、历史故事类、神话传说类、寓言类四种类型。内容的主题多谴责忤逆凶残,宣扬孝道和善行。裕固族语言则是口头流传的民族民间语言的又一典型。裕固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由于其文字失传,口头语言不仅是裕固人民相互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是其文学传承的主要方式。一般来讲,一个民族只有一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而裕固族却有着两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言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这种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较为少见。裕固族的两种语言中保留了许多古突厥语特点,是回鹘语言的“嫡语”,与古代维语最接近,是流传至今的活的语言,对研究我国古代西部民族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二)敦煌民间音乐、舞蹈
敦煌民间音乐、舞蹈是敦煌乐舞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敦煌乐舞体系主要由敦煌遗书中的乐舞文献史料和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乐舞图像,以及敦煌现实生活中的乐舞文化艺术三部分所组成,三者共同构成繁盛的敦煌乐舞气象。其中,敦煌现实生活中的乐舞艺术是敦煌乐舞文献史料记载、敦煌壁画乐舞图像表达的基础,敦煌壁画乐舞图像表达虽有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夸张表现成分,但总体未脱离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敦煌民间音舞艺术的生动描绘。例如,酒宴著辞作为敦煌民间比较文雅的一种宴饮方式,在敦煌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宴饮歌舞场面在唐五代壁画内容中也有生动反映,如,莫高窟五代第61窟的宴饮图中,包括维摩诘在内的7人坐在食床两旁,食床上放有装酒的器皿和其他餐饮具。其中两人在奏乐,一人在翩翩起舞。以罗庸、叶玉华、王克芬、柴剑虹为代表的学者在对藏经洞所出“敦煌舞谱”残卷进行分析后指出,这些舞谱残卷所记录的舞蹈系汉、魏“属舞”和唐人酒宴上的“打令舞”,说明民间筵宴舞蹈很早就在敦煌地区流行。如今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酒筵游戏场合,为欢歌助兴,营造热烈气氛,酒宴著辞、敬茶、献酒邀舞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娱乐节目,也是地方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敦煌节日音乐风俗中,还保留了古代西凉乐舞的遗风,如古代军旅出征乐舞的遗存——“凉州四坝滚鼓子”(民间鼓乐舞蹈)以“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气势,如今仍活跃在凉州北乡一带。此外,还有婚庆乐舞、春节社火(如凉州的民间社火);大量的劳动和生活歌谣,如放羊歌、奶牛犊歌、割草歌、擀毡歌、哭嫁歌等。
(三)敦煌民间宗教、神怪故事、传说
在敦煌佛教文化题材中,有许多为民间百姓所熟知的宗教或神话故事。即便是宗教故事也都加入了本地信众的理解。例如,《敦煌变文》中记载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讲述目连救母的故事;《舜子变》讲述舜子至孝的故事;《董永变文》讲述董永遇仙女的神话传说故事等。那一幅幅精美的敦煌壁画更是讲述着一个个神奇动人的故事传说。如为民间百姓所熟知的水月观音经变、千手千钵文殊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等;描绘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普行六度的种种事迹与善行故事,如尸毗王割肉贸鸽;九色鹿拯救溺人;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睒子孝养盲亲等。同时,我国传统神话中的西王母与东王公、伏羲与女娲、凉州民间司农之神天公与天母的故事;创世神话、善恶神话;远古历史传说、地方风俗传说、风物传说等也在敦煌民间流行。
(四)敦煌民间服饰艺术表达
服饰是一个民族或民族群体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郭沫若曾说,“由服饰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敦煌作为多民族汇聚地,各民族服饰文化多姿多样,例如,裕固族妇女的头面和红缨帽、保安族男子服装的腰刀配饰、不同地区的藏族服饰等。这些民族服饰反映了本地域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传承、人生礼仪、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它们以美观大方、色调和谐、格调独特的敦煌民间服饰共有特征,反映了该地域民族独有的审美观念和丰富的文化艺术内容。
(五)敦煌民间壁画、雕塑、建筑技艺,木刻版画、葫芦雕刻技艺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壁画最多的石窟群。石窟艺术源于印度,但印度传统的石窟造像以石雕为主,敦煌莫高窟因岩石坚硬、砂石疏松,故以泥塑造像为主。除南北大像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的彩塑尊像。敦煌彩塑艺术的制作方法可分为圆塑、浮塑、影塑和悬塑四种。无论何种塑形,第一步都是制作出塑像的大体轮廓。轮廓完成后,接下来的程序是用泥。用细泥塑出人物的表层细部,诸如衣褶、佩饰、五官等;再下来便是剔除、增补和修改,主要是对一些细部如脸部、头部、衣纹等的刻划;最后是敷彩。千姿百态的塑像显示了敦煌“塑匠”们娴熟的技艺、就地取材(如用当地主要野生植物芨芨草塑出形体,用细泥塑出人物表层细部)的超人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石窟壁画的绘画技艺中则基本保留了我国传统的壁画艺术制作步骤,如一朽(行话叫做“摊活,即用炭条打稿”)、二落(行话叫“落墨”,即勾线)、三成(行话叫“成管活”,即着色与完成)。同时对一些壁画还进行了特殊处理,——“沥粉贴金”,如菩萨、飞天的花冠、璎珞、法器等,以增强画面的立体造型感和丰富的视觉效果等。在“白描稿本”和相对约定俗成的“画诀”使用方面;在金色制造法、立粉法、涂色法和晕染法等民间技法方面,也都运用了民间传统技法。在绘画颜料的制作和调配上,更有独到的选料和工艺,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来自进口宝石、天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选用这种用矿物颜料绘制的壁画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褪色。随着敦煌旅游业迅速发展,近十年来以敦煌佛教艺术为题材的木刻版画、葫芦雕刻、壁画剪纸等手工艺品产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如今,超过500名民间艺人进行当地手工艺品的创作与销售,民间艺术产业已成为敦煌旅游的新名片。
(六)敦煌石窟壁画、雕塑、建筑美术艺术表达
本文关于“美术艺术”的称谓,是专指以平面或立体方式呈现的敦煌石窟壁画、雕塑、建筑图像艺术。它们不同于其反映的主题艺术内容——乐舞艺术。同时,也要与前述的敦煌壁画、雕塑、建筑技艺区别开来。技艺是呈现敦煌美术图像艺术的手段,美术图像艺术则是技艺展现的结果。敦煌壁画现存约5万平方米,最大画幅40余平方米。时代从十六国到元代,千年不衰。莫高窟壁画内容丰富,堪称“墙壁上的美术馆”。分为佛教画、我国传统神话画及装饰图案画、社会风俗画三大类。其中,佛教画中有包括各种佛像及菩萨,如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佛、贤劫千佛、文殊、普贤、观音、势至,还有天龙八部等说法图933幅、佛像12,208身;有水月观音经变、如意轮观音经变、千手千钵文殊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福田经变千余壁;有绘述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为菩萨时忍辱牺牲、教化众生、普行六度的种种事迹与善行的本生故事画;有讲述释迦牟尼成佛后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画和描述释迦牟尼佛从入胎、出生、成长、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槃等被神化了的佛传故事画;还有佛教史迹故事画。第二类中国传统神话画,主要有第249窟、第285窟表现东王公、西王母驾龙车、凤车出行;伏羲、女娲;白虎、朱雀和“雷公”、“雨师”等众神的壁画。莫高窟壁画中的装饰图案画主要是平棋和藻井,属于建筑顶部的装饰。社会风俗画中有供养人画像、出行图、山水画等。这些壁画多数是依据佛经绘制的佛教宣传画,但在造型艺术表现时,古代艺术匠师们却是根据当时社会生活现实塑造神灵和人物形象、生活场景,因而它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社会历史、民间生活。敦煌石窟彩塑,是“东方雕塑”的又一大杰作。它是在泥塑外层干后敷彩施色,故称彩塑。莫高窟彩塑保存着自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等10个朝代的彩塑(包括影塑)3000余身,其中圆雕2000多身,浮塑1000余身。除此外,敦煌石窟彩塑还包括榆林窟、东西千佛洞彩塑。敦煌彩塑的对象有:身披袈裟,头有肉髻,耳长及肩,眉间有白毫,指间有蹼,脚掌有法轮,手印随说法、降魔、苦修、禅定的佛像;头戴花冠,身着天衣,腰系长裙,肩披长巾飘带,袒上身,胸前挂璎珞,腕饰钏镯,面容端庄文静,肌体丰满圆润,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菩萨像;以大弟子迦叶(老者形象)和小弟子阿难(少年姿态)为代表的弟子像;威武神气的天王、金刚力士像等。莫高窟的石窟建筑艺术。莫高窟的石窟唐时有建筑千余洞,现存石窟492洞,其中魏窟32洞,隋窟110洞,唐窟247洞,五代窟36洞,宋窟45洞,元窟8洞。其石窟建筑艺术主要指其形制及其造型。敦煌石窟中,最能体现其地域民族特色的石窟形制及其造型有中心塔柱窟,又称塔庙窟,是指建在洞内的寺院。它的出现除受印度、新疆造窟形式(宗教礼仪中绕塔礼拜的习俗)影响外,还与汉地寺院以塔为标志的习俗有密切关系,是石窟艺术逐渐汉化的产物。另外,覆斗顶形窟也很像我国传统房屋布局中的布“帐”。这种形制在印度以及新疆地区很少见到,一般认为也是受汉地墓葬形式影响而致的本地产物。此外,还有殿堂窟、大像窟。莫高窟初唐第96窟(即北大像窟,又称九层楼,弥勒佛像高33米)是依山崖而坐,内为石胎,外面敷泥赋彩而建。大像窟的建筑形式是我国传统木结构的殿堂建筑与印度石窟建筑结合的典型产物。由于佛像通体的高大和窟檐外观的气派,大像窟成为了敦煌石窟建筑的中心和象征。
总之,在敦煌石窟图像艺术当中,雕塑是石窟的主体,壁画因塑像而成,建筑则为雕塑和壁画的绘制提供了框架支撑。三者结合,相互辉映,层次分明,共同构成了独具敦煌地域与民族特色的石窟立体艺术。上述多元化的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成果或者以作品形态存在,如那些独立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或者以非作品形态(如符号、素材、装饰图案、技艺表达等)存在。这里,本文未采用著作权法的一般分类标准,是因著作权法只有对作品的分类,而无非作品的类型概括,如果沿用一般作品的分类标准,则无法涵括体现敦煌民族民间艺术特征的多元化类型。例如,那些为艺术创造而存在的民间技艺,甚至不属于文学艺术范畴,但却实实在在地被创作的艺术表达联系在一起,甚至就是其艺术创作要求和必经的步骤、艺术表达形式本身。即便不能用作品的标准去衡量这类技艺成果,也仍应归属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成果之列,因为从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范围划定看,民间技艺即涵括在其中。
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传承:动态化承继与多样式表现
由于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创生至今已逾千年,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是否传承,以何种方式传承,不仅法律角度探讨阙如,对敦煌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有待认真分析。有学者认为,敦煌石窟艺术“始于4世纪,而终结于14世纪”(颜廷亮)也有学者认为“敦煌艺术的下限既不是元代,也不是民国时期,而应是清末”(易存国)。这些观点对敦煌石窟艺术在元代走向衰弱。清末凿窟行为停止的历史做了阐述,但对之后敦煌民间文学艺术是否传承,实际并未言及。对此,本文的理解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断不能以偏概全,以“石窟凿窟行为的停止”来否认敦煌民间艺术的客观存在和传承,因为二者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和必然的联系。如前所述,敦煌民间文学艺术不仅仅指敦煌“非石窟文化艺术”。还应当包括敦煌地区民族创造的诸多流传在民间的“非石窟文化艺术”,如,敦煌民间筵宴舞蹈、凉州鼓舞等至今还在民间延续和传承。仅以“敦煌石窟凿窟行为的停止”为例证,来说明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止步”,不具种概念对属概念外延的周延性。进一步而言,“敦煌石窟凿窟行为的停止”是否意味着其敦煌石窟民间艺术表达的“止步”,也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自1900年敦煌藏金洞发现以来,敦煌就进入了学术层面的新时期,虽然略有重修、重绘、更多是出于维修而非主动的创作。故此,敦煌石窟艺术的下限只能定于清朝末年。”(易存国)这实际又为敦煌石窟艺术表达的延续划定了第二条标准,即一定是原样态的创作。对此理由,本文也不敢苟同。这里首先涉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传承的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厘清,是“艺术表达本身的传承”或是“艺术表现方式(原样式)的传承”?本文以为两者有实质的不同。从历史视角看,“随着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文化艺术表达本身和传承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会有所不同,呈现动态变化。”多样式表现正是其动态变化的必然反映和客观要求。我们无法要求某类民间文学艺术固守原有的表现形式或传承样式,否则会遏制民间文学艺术生长。为此,固定于某种外在表现方式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传承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看待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传承,是看它的民间创作源头及仍在民间不断延续创作的艺术表达,追求的是无论采取哪种传承方式再现的民间艺术表达,只要保有本地域民族民间艺术属性和其艺术表达的基本特征,反映了本地域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习俗,都应当将它们视为一脉相承的文学艺术,即贯彻了“艺术表达本身的传承”。我们不妨将此归结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动态传承性”。而这种随时代而变的动态传承性,反过来又证明了民间文学艺术被不断创造的属性。实践证明,愈是能够动态传承的事物,愈印证着其长久的生命力。这对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而言亦然。如前所述,敦煌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丰富,表达成果类型多元化。在延续千年的历史中,因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经济背景不同,其艺术风格和形式、手法千变万化。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不是出于同一艺术表现形式,而否认这种艺术的同质表达。例如,对那些壁画艺术而言,“属于何种教派,采用何种经典,参照何种论疏,请哪一派画师,作何种形式的构图,使用何种笔墨,形成何种色调,都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或单纯的艺术技巧问题,而应该看到这些艺术背后有着共同审美观念、生活习俗、历史传统等。”可见,我们在判断是否是某类型敦煌民族民间艺术表达的传承时,注重的是这种艺术表达的同质性,而非传承方式的唯一性。以此观照敦煌石窟艺术的传承。敦煌壁画在元代或清末之前,历代曾在原壁画基础上进行过延续创作,甚至是利用原敷面进行再绘制,有的洞窟被后代多次重修和维护,使其保有了原实物表现形式的再现和技艺的再延续。虽然因历史和社会变迁,清末造窟停止,继续在敦煌鸣沙山崖壁上开凿石窟、绘制壁画、进行雕塑等已客观不能且遭法律禁止,但敦煌石窟美术艺术的传承并未完全走向“终止”。从民国至今,对敦煌石窟的修缮、维护,就涉及到了对壁画、雕塑的重修、重绘活动。不管是出于艺术研究或维护的何种目的,基于客观条件限制,以敦煌学家张大千、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石窟壁画的“仿真临摹”,在现行著作权法看来,就是一种艺术创作。至于将这种创造看作是对民间艺术表达的传承创造或是演绎创作,都无损其“创作”的性质。由于它们与敦煌传统壁画表达艺术“一脉相承”,因此,就是对敦煌壁画美术艺术表达的“活态传承”。再从石窟艺术表达的基础——技艺的传承看,敦煌壁画中运用的“白描稿本”和相对约定俗成的“画诀”、金色制造法、立粉法、涂色法和晕染法等民间技法,仍在民间运用;泥塑艺术(技艺)作为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从陶器塑到佛像塑,从古至今也未绝迹。敦煌文物研究近年来对敦煌壁画、雕塑的修复,即运用了这些古法,做到了“逼真”。一些民间手工创作的“敦煌飞天”、“反弹琵琶”壁画、雕塑艺术品,也沿袭了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艺术表达手法和技艺。可以说,它们与石窟壁画、雕塑艺术表达系“一脉相承”,是对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包括传统技艺)的动态传承。当我们运用“动态传承”的标准,进一步将敦煌民族民间艺术表达置于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做一番宏观考察时,我们发现,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非但未因岁月冲刷完全消亡,相反,却呈现出另一番旺盛景象。这些悠久而古老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一部分至今仍以口授、身传表达方式,流传在民间。例如,凉州狮舞就是长期流传在武威(古称凉州)地区,一种古老的民间舞狮艺术的典型代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在《西凉伎》中对这种“长啸”长安城的“狮子舞”有过精彩描写,“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如今成为了河西凉州地区群众庆祝节日喜庆的必备活动。而另外一部分敦煌民间文学艺术则既通过书面文本、建筑、雕塑、壁画等实物形式得以记载和保存,如在敦煌壁画、雕塑、建筑艺术表达中呈现(或是其表达技艺)或被敦煌遗室文献资料所记载,同时,也通过实践活动、技艺延续、不断创新传承表现方式,动态流传在民间。例如,敦煌乐舞,被视为敦煌艺术的永恒“标志”,成就了敦煌艺术的辉煌。如前文所述,自汉、魏时就敦煌乐舞已流行于民间和宫廷,至今在河西走廊各地等地仍能见到留有敦煌舞遗风和特色的民间舞蹈,如“凉州舞狮”,“酒宴著词乐舞”、“打令舞”等。它们不仅在敦煌那五余万平方米的石窟壁画被塑造,在敦煌遗书“敦煌乐谱”和“敦煌舞谱”中残卷被记载,而且敦煌乐舞的艺术表达传承如同敦煌乐舞艺术蕴含的“开放、时尚”精神,在逾千年历史的长期演变中,还不断创新。现今,根据敦煌乐舞壁画以及敦煌舞谱、乐谱资料整理,由我国音乐舞蹈家“复原”的“敦煌舞”成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舞种的新流派,敦煌古乐也“翩然流眄于今日之舞台。”以《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千手观音》、《敦煌韵》等为代表,根据敦煌舞乐改变的一批现代敦煌舞剧的面世,更使流传千年的《霓裳羽衣舞》、《西凉乐舞》、《唐韵胡旋》、《水月观音》、《妙音反弹》、《千手观音》等敦煌乐舞形象表达广泛展示在世人面前。其中,那“妙音反弹”伎乐天(反弹琴瑟形象)、飘逸神往的飞天,至今仍绽放着无与伦比艺术魅力,扎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艺术中,成为了本区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这些鲜活的实例验证着,在两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敦煌民间文学艺术非但未因岁月冲刷完全消亡,而是以其独有的方式顽强生长在民间,即以不断创新的表现方式和多元化的活态传承,延续着其延绵不断的旺盛生命力。
结语
鉴于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灿烂历史和博大辉煌,本文只能采撷其中一二,对敦煌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形成、表达成果的法律特性予以分析和考察。不过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典型代表性,仍能帮助我们从知识产权视角认知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法律内涵与外延范围,把握其动态传承特性,进而为实现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成果权益和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提供前提和依据。这也正是本文作为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成果权保护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的目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