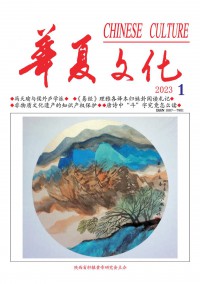清明的诗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清明的诗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清明的诗范文第1篇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吴钧陶英译《清明》((韵式aaba)
It drizzles thick and fast on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I travel with my heart lost in dismay。
"Is there a public house somewhere, cowboy?"
He points at Apricot Village faraway。
许渊冲英译《清明》((韵式aabb)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
蔡廷干英译《清明》((韵式aabb)
The rain falls thick and fast on All Souls' Day,
The men and women sadly move along the way。
They ask where wineshops can be found or where to rest ----
And there the herdboy's fingers Almond-Town suggest。
孙大雨英译《清明》((韵式aaba)
Upon the Clear-and-Bright Feast of spring, the rain drizzleth down in spray。
Pedestrians on countryside ways, in gloom are pinning away。
When asked "Where a tavern fair for rest, is hereabouts to be found",
The shepherd boy the Apricot Bloom Vill, doth point to afar and say。
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清明》((无韵译法) (古诗苑汉英译丛《唐诗》,外文出版社,2001)
It drizzles endles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
Travelers along the road look gloomy and miserable。
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
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
万昌盛、王中英译《清明》((韵式aabb)
The ceaseless drizzle drips all the dismal day,
So broken-hearted fares the traveler on the way。
When asked where could be found a tavern bower,
A cowboy points to yonder village of the apricot flower。
吴伟雄英译《清明》(韵式aabb)
It drizzles thick and fast on the Mourning Day,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When asked for a wineshop to drown his sad hours?
A cowboy points to a hamlet amid apricot flowers。
万昌盛、王僴中(《中国古诗一百首》,大象出版社,1999)
The ceaseless drizzle drips all the dismal day,
So broken-hearted fares the traveler on the way.
When asked where could be found at avern bower,
清明的诗范文第2篇
【清明节的谚语和诗句】
麦怕清明霜,谷要秋来旱(云)
清明有霜梅雨少(苏)
清明有雾,夏秋有雨(苏、鄂)
清明雾浓,一日天晴(豫)
清明起尘,黄土埋人(晋、内蒙古)
清明响雷头个梅(浙)
清明冷,好年景(辽、冀)
清明暖,寒露寒(湘)
雨打清明前,春雨定频繁(鲁)
阴雨下了清明节,断断续续三个月(桂)
清明难得晴,谷雨难得阴(鲁)
清明不怕晴,谷雨不怕雨(黑)
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黑)
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黑)
清明宜晴,谷雨宜雨(赣)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华东、华中、华南、四川及云贵高原)
清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冀、晋)
清明无雨旱黄梅,清明有雨水黄梅(苏、鄂)
清明南风,夏水较多;清明北风,夏水较少(闽)
清明一吹西北风,当年天旱黄风多(宁)
清明北风十天寒,春霜结束在眼前(冀)
清明刮动土,要刮四十五(苏)
【清明节的诗句】
《寒食野望吟》
白居易
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
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
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
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清明日狸渡道中》
范成大
洒洒沾巾雨,披披侧帽风。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
石马当道立,纸鸢鸣半空。(土番)间人散后,乌鸟正西东
这首五律有如广角镜头,摄下了清明春野的全景。书生们潇洒的游春,空中风筝争鸣,鸟雀啄食(土贲)间祭品。哀欢相映,这真是一个极具特色的节日。不过,清明墓祭凄清悲切固然有,但至唐宋,宴乐游赏的风气也已形成。
唐诗人顾非熊的一首《长安清明言怀》诗道尽其间关系:
《长安清明言怀》
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
清明的诗范文第3篇
关于清明节祭奠的诗句《冬夕书事》作者田锡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苏幕遮》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蝉吟槐蕊落,的的是愁端。病觉离家远,贫知处事难。《与友人会》
熹欢就不要放弃,放弃就不要后悔
庄园打开,春天在音乐中到来
母称儿干卧,儿屎母湿眠。《劝孝歌》
爬上属于我的那座高峰,那个梦想
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
鸡鸣咸阳中,冠盖相追逐。丞相过列侯,群公饯光禄。
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周邦彦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liancom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绝句》
戈船破浪飞,铁骑射日光。——《江上对酒作》陆游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
春蚕到死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自矜胡骝奇绝代,乘出千人万人爱。
我欲乘风归去爱恨已过黎明任我多感惆怅静思明日晨雾
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千帆过尽,皆不是我心所爱;三千弱水,哪一瓢知我冷暖
关于清明节祭奠的诗句精选《寒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关于描写清明节的诗句之一:
清明夜
【唐】白居易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
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清明日送邓芮二子还乡
【唐】戴叔伦
钟鼓喧离日,车徒促夜装。
晓厨新变火,轻柳暗翻霜。
传镜看华发,持杯话故乡。
每嫌儿女泪,今日自沾裳。
清明后登城眺望-【唐】刘长卿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清明日曲江怀友-【唐】罗隐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
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
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关于清明节祭奠的诗句推荐郊行即事
(宋)程颢
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
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寒食-【唐】孟云卿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清明即事-【唐】孟浩然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清明-【唐】孙昌胤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清明日忆诸弟-【唐】韦应物
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
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
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
唯恨乖亲燕,坐度此芳年。
长安清明-【唐】韦庄
蚤是伤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清明的诗范文第4篇
1、《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清明夜》白居易,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3、《清明日园林寄友人》(唐)贾岛,今日清明节,园林胜事偏。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杜草开三径,文章忆二贤。几时能命驾,对酒落花前。
4、《长安清明》韦庄,蚤是伤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来源:文章屋网 )
清明的诗范文第5篇
清明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祭扫墓园与缅怀先人。
唐代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一诗勾画出当时的扫墓情形:“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清明时节,漂泊异乡的诗人墨客,更容易滋生思亲与思乡之情。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垒垒,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诉尽了生死离别。
北宋黄庭坚的《清明》一诗别有一番深意:“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由清明扫墓进而探讨人的生死的意义,有感于人的价值,表现了诗人旷达之中包含的不愿与世俗沉浮的孤傲之气和对仕途贤愚混杂的愤懑之情。
但清明也不光是肃穆的祭扫与缅怀,也有祥和欢快的另一面。清明自古就有踏青的习俗,又叫“踏青节”,古时也叫行青、探春、寻春等。古时清明,人们也聚亲约友,在大好春光里四处游玩,甚至围坐野宴,抵暮而归。
唐代诗人顾非熊作过《长安清明言怀》一诗前四句:“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记录了当时唐都长安清明节万家车马出动,莺啭芳菲的盛况。
北宋欧阳修的《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云:“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同为“唐宋家”的苏辙也曾作《踏青》一诗,展现踏青盛景:“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桥没水不胜重,野店压糟无复清。”南宋吴惟信的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展现出当时的人们外出郊游,尽兴方归的场景。
古人踏青爱骑马。唐代皮日休曾作《襄州春游》一诗曰:“信马腾腾触处行,春风相引与诗情。”表现出初春骑马漫步的悠闲。薛昭蕴《喜迁莺・清明节》描绘了举子们于清明雨后骑马踏青的得意之情:“清明节,雨晴天,得意正当年。马骄泥软锦连乾,香袖半笼鞭。花色融,人竟赏,尽是绣鞍朱鞅。日斜无计更留连,归路草和烟。”
古代的很多诗人也像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一样,清明前后会周边游或远游,目的地大多偏爱江南。
李白去扬州踏青,满眼的江南风情,留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白居易最爱钱塘湖:“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早已成为千古佳篇,对春游的描写令人神往。
韩愈与张籍(唐代诗人,时任水部员外郎)同游当时的著名游览胜地曲江池(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是隋炀帝开掘的一个人工湖),看到无限美好的春光,还不忘写首诗调侃白居易:“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排行二十二,又曾任中书舍人,故称“白二十二舍人”)大致意思是:曲江上春水弥漫两岸繁花千树,你有啥事那么忙一直不肯来?
除了踏青、旅游,古人在清明节还喜饮酒。唐代杜牧的《清明》脍炙人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宋代高翥《清明日对酒》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宋代诗人王禹曾写过一首名为《清明》的诗,头两句是“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苏轼在左迁密州后,写下《望江南・超然台作》,下阕为“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一碟小菜,一壶老酒,吟咏诗词,烹茶论道,快活逍遥。宋代程颢的《郊行即事》表现了踏青野炊、把酒共话春风的潇洒 :“芳原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古代,清明节与寒食节本是两个节日,寒食节这一天要禁动烟火,等到清明要“乞新火”。但后来人们往往将这两个节日合并起来过。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地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唐代韩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描绘了一幅寒食节长安城内富于浓郁情味的风俗画。
古诗里的清明还有更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时令价值的其他内容,比如“折柳”、“插柳”、“蹴鞠”、“放风筝”、“荡秋千”等。
清明诗句多以柳寄情,说明“柳”是清明节习俗的一个重要元素。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清明节春风和煦,绿树成荫,古时踏青、扫墓、上坟曾有戴柳和家家户户门口插柳枝的习俗。传说,当年晋文公和群臣徒步登山祭拜介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并且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上,以示纪念,群臣纷纷效仿,相沿成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人们认为柳枝有灵性,有“鬼怖木”之称,在柳条发芽的清明时节插柳可以避邪驱鬼。关于民间“清明插柳”,还有一种说法是从隋代开始流行,隋代运河刚贯通南北,河堤需要年年植树,巩固河堤。而柳树有强大的生命力,容易成活,又喜湿润,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加上清明又是适宜植树的季节,因此插柳习俗从那时起渐成风俗,并延续至今。更有一种说法称清明节插柳和宋代大词人柳永有关,据说柳永常往来于烟花柳巷之中,当时的歌妓无不爱其才华,他一生为仕途所不容于襄阳贫困而亡,每年清明节,歌女们都到他的坟前插柳枝以示纪念,久而久之就成了清明插柳的习俗。
蹴鞠是古代的足球,也与清明节有重要的联系。唐朝诗人韦应物《寒食》咏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描述了清明寒食之际,人们在园中蹴鞠。而唐代的另一位诗人仲无颜在他的《气球赋》中更生动地记录了人们蹴鞠嬉戏的场景:“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闹,或略地以走丸,乍凌空似月圆。”这颇具现场感的描述,正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端倪的一个形象写照。
放风筝也是清明前后的习俗。唐代高骈的《风筝》说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描写了风筝竞放的情景。清代吴友如的《清明节放风筝》:“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唐人韦庄的诗句,说的是清明“荡秋千”。北宋秦少游《满庭芳・晓色云开》一词曰“秋千外,绿水桥平”。张先《春门引・春思》也有“那堪更被月明,隔墙送过秋千影”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