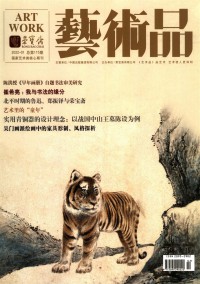金农艺术品和文人商品化的形成原因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金农艺术品和文人商品化的形成原因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艺术品进入市场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而发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促进了艺术品的“商品化”。金农晚年在扬州多以梅花题材鬻画也是商品的发展符合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
1.艺术商品化
十八世纪,由于扬州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艺术品局域性“商品化”现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其典型就是“按质论值”。如李斗记载当时扬州大东门等处的书场按日敛钱,“钱至一千者为名工”[1];再如丁敬篆刻“白锵十金为镌一字”;华新罗画每人“或得高价与之”;最具典型的案例当属郑板桥制订《板桥润格》,公开润笔收费标准,如《鸥陂渔话》中记载,“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條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2]另外,在扬州卖画“岁获千金”的金农也有其他两宗收入,就是将古砚和纱灯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特别是将“八分书”题写在工匠制作好的纱灯之上,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用品,使之变为一种高雅的装饰商品出售。这种艺术商品化现象归根结底上是由于书画等艺术品的消费群体不断壮大,这既包括巨商大贾,还涉及到小商小贩。这些消费动机既有巨商大贾不满足于奢侈的物质生活,寻求精神生活而“附庸风雅”,也有小商小贩为经营生意,吸引客户而“托名风雅”。总之,在商品交换的环境下,一切事物皆以“价值”的尺度来衡量,书画的使用价值也被交换价值所取代,致使书画的交易“社会化”,也无怪“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社会风气了。墨梅在中国自古被赋予“坚韧不拔”与“洁身自好”的品格,被看做士大夫精神的“物化”,墨梅自华光和尚始,至宋、元、明、清,其样式在“文人关照”下层出不穷,为扬州时人所喜好,所以梅花题材在扬州地区也是炙手可热的。而当时扬州画梅名家亦是不少。除了金农外还有高翔、汪士慎、李方膺和罗聘。汪士慎(1686—1759)是扬州八怪最早投身于绘画市场的画家,其擅画梅,早在乾隆元年(1736)已是画坛画梅最有名的画家,金农提到:“巢林画繁枝,千花万蕊,管领冷香,俨然灞桥风雪中”。而此时金农则刚经历“博学鸿词风波”而扬州;高翔(1688—1753)同样为画梅高手,金农称其曰:“西唐画疏枝,半开軃朵,用玉楼人口脂抹一点红”;李方膺(1695—1755)则“善作大幅梅花,古干横空,蟠塞夭矫。”此三人的画梅在书画市场的销路给了金农直接的动力。金农在《冬心先生画竹题记》中说:“舟屐往来芜城岁三十年,画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杨補之、丁野堂之流”[3]。金农于乾隆十九年(1754)开始大量画梅。与此前后,汪士慎在乾隆十七年(1752)因双目失明,无法书画;六十六岁的高翔于乾隆十八年(1753)病卒于于扬州故宅。于此,扬州花坛流逝两位画梅高手;不久李方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因患“噎疾”归乡南通,后去世。于此,扬州书画市场梅花题材的供给便出现严重短缺的趋势,这个时期金农梅花画作便大量被订制,以满足扬州画梅市场的“供不应求”。在乾隆十五年(1750)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辞世前,金农的画梅在书画市场已经可与郑板桥当年“兰竹”的销量相媲美了,这也成为金农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
2.文人商业化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下的商品经济早在明代就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明中期的吴门地区就有文人画家将自己的诗、文、字、画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买卖,致使部分文人有“商业化”的趋势。如唐寅“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沈、文、董、陈等文人更好为人撰序、祭文、祝寿词、墓志铭等“商品化”文章。到了十八世纪的扬州,诗文书画更是变成了文人赖以生计的技能,艺术家公然卖画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这就使得部分文人趋于商业化。如《鸥陂渔话》中描述郑板桥“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的从商趋利心理[4]。可以看出画家已经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视为满足社会心理需求的精神劳动成果。再如金农“多方所求润笔、开拓外地市场、雇佣、固定‘母题’批量化生产”等行为,也充分说明文人的“商业化”。母题生产,以应四方所求,如现分别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三册《杂画册》,由题款可知其同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绘制,这三页杂画册无论在内容、构图、造型语言及款识内容上几近相同。由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那幅杂画上左边的提款可知其为“乾隆二十四年又六月,意林先生自杭寄书以此册乞余作画”而绘制的。这三幅画都为应酬之作。举两例加以论证:如前文已提及金农卖花灯之事,金农还请袁牧在南京代售纱灯,以开拓外地市场,史学家全祖望曾于《冬心居士写灯记》中说他“卖砚、卖灯,迎和商人”。再如金农晚年绘画的问题,由于晚年画梅销路较好,其作品多有弟子罗聘、项均,以应四方之酬、满足市场需求,“项生均,初以为友……近学予画梅,梅格戌削中有古意。有时为予作暗香疏影之态,以应四方求索者。”[5]这种文人商业化的表现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必然产物。直接原因是由于自明末清初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开始不及“商”,文人也开始觉察到商人的社会作用,从而改变了对商人的看法,于是将自己也于潜移默化之中“商人化”。例如曾中举人、进士,且当过县官的郑板桥更将“士”视为“四民之末”,“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不可得也。”这就一改传统上对商人的政治歧视、打破了自孟子以来对商人“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成见。这些人大多书香门第出身,抑或者饱读诗书,更有甚者出入官宦,最终都成为文人“商业化”的典型代表,文人的“亦文亦商”与商人的“亦商亦儒”就由艺术商品作为纽带而产生交集,建立起各取所需、相互供求的社会关系。
金农写意梅花形式的别具一格,是文人画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必然产物。其雅俗共赏的审美风格也直接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艺术界“艺术商品化”和“文人商业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