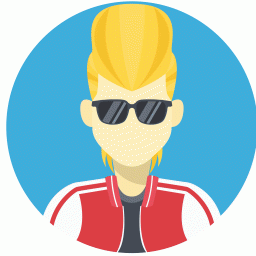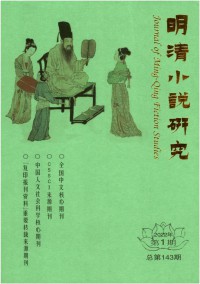明清徽州市镇和社会转型兼和江浙市镇对比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明清徽州市镇和社会转型兼和江浙市镇对比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明清市镇史的研究,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江南平原市镇,却鲜有涉及江南山地者。本文拟考察江南山地的徽州市镇,并将其与平原地区的江浙市镇对比研究,进而探讨不同的自然人文条件下市镇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一
与江南平原地区相似的是,徽州市镇的萌芽可追溯到宋元,而其真正勃兴却在明清时期。如渔亭,宋时就已设治建里,并因其他当孔道而设有驿站,商业也较繁兴。明中叶以降,随着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七省通衢”、依山傍水的优越地理位置的经济意义充分显示出来,成为黟祁两县的重要集散中心,由杭州或屯溪转运而来的货物多由此登岸转输黟祁各地;而两县的农副、土特产品也多在此汇集,运往外地。渔亭的商业盛极一时。又如深渡,北宋时只是姚姓单姓定居之地,因地处新安江畔,已有商业活动,然仅一村市而已。明末时,深渡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店铺上百家,客户百十家的中等市镇了。居民结构亦从原先的一姓发展为姚、詹、鲍、胡、余、吴六姓共居。再如岩镇。岩镇乃徽州著名古镇,宋绍兴年间设镇,元时已是“商旅每旬以三、八日会集贸易”[①]的集市;明中叶以降,岩镇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无尺土之隙”[②]。太平天国时,岩镇毁于大火,其经济中心的位置才为屯溪所代替。屯溪兴起始于明嘉靖年间。此外,龙湾、流口等小市镇也都是明中后期开始繁兴的。徽州市镇的勃兴,并非偶发的现象,而是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合拍的。在明成弘以前,徽州虽有出贾之习,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静态的农业社会。“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婚嫁依时,闾闾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③]”此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即所谓“操资交揵,起落不常”,“东家已富,西家自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④]。贫富分化造成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休歙两县“其有业者大都什不二三,而其失业者什七八焉”[⑤]。由于职能所限,府县治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外出经商外,大量游民就近涌入市镇从事工商业。随着徽州对外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以军事和行政为主体职能的府县治已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在沿江交通便捷之地,作为农村商品交易中心、农副产品加工中心、货物集散中心的市镇便兴起与发展起来。徽州市镇经济繁荣表现如下:
从市场的规模看,徽州山区市镇的规模并不亚于江南平原地区的市镇。有些徽州市镇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军事、政治中心的府县治所。万安镇南临横江,交通便捷,市况发达,一直被列为休宁九大街市之首,民间有“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之俗语。屯溪原先也不过休宁一街市,后竟成一方重镇,其规模与繁华远非县治海阳镇所及。这是由市镇的主导职能决定了。与府县治所军事、政治的职能不同,市镇职能是商业性的,因而聚集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规模自然随之膨胀。然在徽州,象岩镇、屯溪这样规模的市镇是不多的,更多的是深渡、万安、渔亭、流口等中小市镇。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徽州毕竟是万山环抱的山区,人口密度大大低于平原地区,市镇密度变比江浙平原低得多。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除府县城外,徽郡计有街市53个[⑥],而其六邑总面积为13870平方公里,其密度为1/262,即每262平方公里1街市。而杭州府市镇数为130个,面积为7334平方公里[⑦],其密度为1/56,远远高于徽州的市镇密度。市镇密度的差异显示了江南山地与平原地区的差别。
市镇的交易一般以“常日为市”为主要形式。此外,有以某一商品为主干的季节性集市贸易。如深渡的茶市、枣市、枇杷市等。庙会集市也是明清徽州又一重要的贸易形式。徽州地处山区,交通不似平原地区方便,市镇分布也不似平原地区普遍,且多集中在沿新安江一线,物资交流比较困难,因而一年一度的庙会集市便成为农村重要的贸易方式。如岩镇的上九会,每年农历正月的初八、初九、初十岩镇祭祀唐代张巡、许远两忠烈,四乡农民烧香礼拜的同时,还进行贸易。一时商民云集,竹木器材、日用百货、备耕农具应有尽有。江南的平原地区,庙会亦十分普遍,但较之徽州,其集市贸易的功能是居次要的,因其市镇体系十分发达,庙会的娱乐性功能却较徽州浓厚得多。
市镇的兴起推动了周边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深渡便是很典型的例子。深渡地处徽州与江浙经济联系的结合部分,是一重要码头,周边武阳、三阳、中村、苏村、杞梓里、霞坑等地枣农,将枣子送至深渡加工并转运外地。土特产“三潭枇杷”也是在深渡加工、外销的。久之,深渡与这些村落间形成了一种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人们都赶至深渡办货,俗谓“深渡担”。深渡也由此而成为歙县南乡和东乡的商业中心。再如屯溪,因地处平原与山地交接处,又是率水、横水汇流之所,商业十分繁荣。《清史稿》称其“在(休宁)县东南,为茶务都会”[⑧]。但其腹地却大大超过了“县东南”这一隅之区,也不仅仅是茶叶都会了,而成为徽郡最大的水运码头、商品集散地和“一邑总市”[⑨]。
市镇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兴盛。徽州本是“朱子阙里”,文风极盛,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国”的美誉。在此背景下,市镇文化事业又因其强大的物质保障而尤为发达。如岩镇,《岩镇志草》称其“甲第如鳞”,“人文之盛,甲于乡邦先进。”早在宋代,岩镇便建有友陶书院;明初有潜虬书院;明中叶有南山书院;清代有檀山书院、百榆社等。从唐至清,岩镇共出了4个状元、36名进士、81名举人,其中供州府职者47人,授予“府学”“县学”职者58人。其他如万安、渔亭等古镇也是文教兴盛发达之地。文教事业的发达,无疑也为市镇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智力保证。
二
与江浙平原地区市镇相比,徽州山地市镇在其布局、功能、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1)市镇布局。徽州市镇多沿江沿河而设,形成线状结构的布局。这是地球环境造成的。“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⑩],峰峦耸峙,山势陡峻,陆路运输十分困难,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水路。“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①①],即新安江与阊江。其中新安江是徽州最大水系,有率水、横江、练江、深渡河等大小支(源)流30余条,流域面积达6751平方公里,是徽州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所谓“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①②]适应徽州对外经济联系的需要,市镇多分布于新安江及其支流上,如深渡、屯溪、龙湾、渔亭、万安、岩镇等等,从而形成了徽州市镇布局上的线状结构。这与江浙地区市镇的网状结构迥然不同。在那里,市镇亦多依水而立,但与徽州不同的是,江浙一带河汊相交,水网密集,江南五大镇之一的濮院镇,在其周围40里之内,就有硖石、石湾、新塍、王店、乌青、屠甸等镇,且彼此间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又如双林,东至乌青36里,东北至南浔36里,西到菱湖亦是36里。在如此繁密的市镇网络覆盖下,村落无一例外地卷入市镇经济之中。而在徽州,街口距深渡23公里、深渡距屯溪55公里、屯溪至万安18公里,而万安又距渔亭38公里,这种线状结构不能形成网络覆盖周围地区,故而市镇对农村的影响力要小于江浙平原地区。
(2)市镇功能。市镇的功能有两种,一是以生产或加工为主体职能,称为专业型市镇;一是以商品的集散与流通为主体职能,称为商业型市镇。
江浙地区的市镇,专业型的居多。例如嘉兴府,根据陈学文先生的研究,属手工业专业市镇的有:丝织业的濮院镇、王江泾镇、青镇、王店镇、新塍镇;棉织业的魏塘镇、风泾镇、王店镇;建筑器材与日用品业的干家窑镇、陶庄市;五金用品业的炉头镇;竹器加工业的陈庄镇、新塍镇;油漆工艺与玩具生产业的斜塘镇;属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市镇有:蚕桑、原丝销售市场的青镇、石门镇;油料加工业的石门镇;生姜销售地新丰镇;盐业生产地鲍郎市;属于交通枢纽的市镇仅有王江泾镇、半逻市、皂林镇、陡门镇、乍浦镇、澉浦镇、广陈镇[①③]由此可见,嘉兴府的市镇中属于专业型的占大多数,即便是那些商业型的市镇,也往往兼有专业型市镇的色彩。王江泾镇是江浙十分著名的商品集散中心,但其居民也“多织绸,收丝缟之利”[①④]。反观徽州,虽说市镇也有生产或加工的功能,但其集散与流通的功能一般都占主导地位。深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商业型市镇,担当了徽州重要集散中心的角色。虽然深渡亦有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业,却只是藉其集散功能才在此加工的。本世纪30年代,徽杭公路通车,陆路取代水路成为徽州对外联系的主要方式,深渡的商品集散功能丧失,其枣加工业遂就近迁至杞梓里。徽州另一个重要的集散中心是屯溪。为对其集散功能有一个具体、直观的了解,下面对30年代屯溪往返船只运送之货物作一考察[①⑤],尽管时间并不吻合,但考虑到近代徽州社会经济发展迟滞的因素,它大致能反映清中叶甚至更早一些的历史实情。当时,船民组织是以“保”为单位的。屯溪保,负责屯溪和渔亭间的货物运输,下行,主要从渔亭运瓷器到屯溪;上行,则从屯溪运百货渔亭。屯上保,负责屯溪和上溪口间的货运,下行,从上溪口运茶箱板、杂货、干笋、柴炭到屯溪;上行,从屯溪运食盐、布匹、杂货到上溪口。屯龙保,负责屯溪和龙湾间货运,下行,自龙湾运木炭、雨伞、茶叶、笋叶、纸、香菇到屯溪;上行,自屯溪运食盐、石灰、百杂货到龙湾。屯杭保,负责屯溪和杭州间货运,下行,从屯溪运茶箱板、箬皮、寸板、枕木、冬笋、桐油到杭州、上行,从杭州运食盐、布匹、油粮、鱼、杂货到屯溪。上述可以看出,屯溪的集散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渔亭、龙湾等也都是集散中心,只不过规模较小,从属于屯溪罢了。
(3)市镇文化,与江浙平原市镇文化的强烈世俗性不同,受整个徽州大环境的影响,徽州市镇文化呈浓厚的宗族文化色彩。据《岩镇志草》记载,岩镇以一镇之地而拥有21个祠堂,充分展示了宗族文化的繁兴。从建祠年代看,除两个无考外,正德间建1个,嘉靖间建7个,隆庆间建2个,万历间建6个,顺治、康熙、雍正间各建1个。嘉隆万三代占建祠年代可考祠堂的78.9%。这恰与史志所载“自嘉隆以来,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的繁荣经济局面在时间上相吻合,从而说明了市镇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对封建的宗族制度造成冲击;相反,却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从宗族活动看,每年的春秋二祭是各宗族内最重要的活动,每逢此时,全族集会,沐浴斋戒,齐集祠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祭祀活动。清明扫墓一般也要先至祠堂祭神主,再各自祭扫。此外还有公共社区文化活动,如遗爱祠、名宦祠、逸民祠、义士祠的春秋二祭,双烈庙的祭礼活动(即上九会)等,旨在“联邻里族党之欢”[①⑥],保护各族的共同利益。宗族间又往往通过联姻,左右市镇的发展。在泊浙平原地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由地方豪宗强族创立市镇的例子。嘉定的罗店镇,“元至升间罗升创市”[①⑦]。太仓的璜泾,成化间赵壁创市,时称“赵市”[①⑧],等等。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市镇的宗族组织迅速瓦解。清中叶的濮院镇“有祠之家,千百之一二”[①⑨],这与徽州市镇的“族必有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庄镇亦如此,“宗祠为近地所鲜,故祭礼愈略”[②⑩]。作为宗族制度重要象征的宗祠的稀少,反映了平原市镇宗族文化的淡化的实景,而世俗性、商业性色彩则愈发鲜明起来。从商人组织看,平原市镇上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已取代血缘性的宗族组织而在市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浙市镇上往往聚集了大量的外籍人口,为保护同乡或同业的利益,会馆、公所次第建立,如双林镇上就有泾县会馆、金陵会馆、新安义团和米业、药业公所等商业色彩很浓的组织。从市镇设施看,茶楼、酒肆、旅馆等娱乐性、商业性设施也作为市镇繁荣的附属物兴建起来。濮院镇“茶酒肆不啻百计,……新丝时更甚”[②①]。但在徽州市镇上,却很难看到如此繁荣景象,“城市无茶馆、酒肆。冲处仅有之,亦苦茗一盂,……不足言馆”[②②]。
徽州山地市镇与江浙平原市镇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差异,是它们处于不同地理及社会经济环境所致。同样,徽州市镇不能如江浙平原市镇推动并实现社会转型,根子亦在于此。
三
美国学者牟复礼认为:“中国工业主义滥觞于各市镇,而不在大城邑”[②③]。这在江浙平原市镇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石门镇的油坊,采用雇佣制经营方式,已具备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无徽不成镇”。徽在江浙市镇的蓬勃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徽商桑梓之地的市镇却未能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例子。徽州市镇经济的发展为何不能推动本地实现社会转型呢?
“徽州介万山之中”,域内山高谷深,山多田少。土质又极差,“地隘斗绝,厥土骍刚而不化”[②④]生态环境亦恶劣,“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②⑤]。因此,徽州粮食生产不发达,“即丰年,谷不能二之一”[②⑥]。这使得徽州有极强的对外依赖性,“百货皆仰于外”[②⑦]。
此外,徽州又因江水流域的不同而划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新安江流域区,包括歙县和绩溪、休宁、黟县的一部分;阊江流域区,包括祁区、婺源和黟县的一部分;青弋江流域区,主要在绩溪北部。各自然区域的形成,本利于地域分工与交流。但徽州陆路交通不便,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很薄弱,它们各自依水路展开对外经济联系。新安江流域区对浙江,阊江流域区对江西,青弋江流域对宁国。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在社会生活方面亦有反映,如妇女服饰,“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②⑧]。徽州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松散性决定了它不能在经济上实现全区域的整合,未能形成区域性市场。域内市场的狭窄对徽州市镇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由于陆路交通不便,徽州对外联系只得依靠水路,但水路亦非通畅之途。由于徽州地势较高,水位落差大,民间素有“一滩高一丈,新安在天上”之谚,水势奔流,险滩迭出,“东涉浙江,险滩三百六十;西通彭蠡,险滩八十有四”,故而“旅之往来,殊非易事”[②⑨]。此外还有“坝脚牙侩”、“街蠹地棍”甚至地方官的人为阻滞。对外联系的不便,又大大限制了徽州市镇的域外市场,制约了市镇的进一步发展。
而江浙一带的平原地区,水网密布,交通十分便利。对外联系亦称便捷,南北有京杭运河,东西有长江水道,又滨邻大海,发展海外贸易,得天独厚。便利的交通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至迟在明代,苏、松、杭、嘉、湖地区已形成了一个有内在经济联系的区域整体。洪武三年六月的一则上谕即以“苏松杭嘉湖”连称[③⑩]。此后,这类并称在公私著述中屡见不鲜。以涟川沈氏这一经营地主为例,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湖苏四府六县[③①],可见其区域经济整合之一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镇发展自有徽州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如双林镇的丝绸贸易市镇近则江南五府,远则闽广等地,所谓“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③②],有“通行天下”之称。徽商虽“几遍禹内”,但并不代表徽州商品有如此广阔的市场,事实上,从事徽州与域外市场联系的毕竟只占徽商总数的小部分。
市镇是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明清徽州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其市镇勃兴的最根本动力。而徽州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其推动社会转型的功能的实现。
徽州商品经济尚局限于自然经济补充的水平,这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发达的基础上的。明清徽州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十分低下的,“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人不当其半”[③③]力田者,依然“耕获三不瞻一”[③④]。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出于以副助农的目的,一些商品性农业、家庭或家族手工业及小商业得以发展。许承尧在谈到歙县明清社会风俗时曾说:“陆南山多田少,食资于豆与粟,而枣栗柿橡之产副之。[③⑤]”万历《休宁县志》亦曰:“良民犹免于冻馁,而樵采树艺者,用积储以阜其家脱也。[③⑥]”婺源“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入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③⑦]”。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落后,农民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生存,不得不进行商品性的农业生产,以期“佐所不给”,“免于冻馁”。徽州手工业发展亦相类似。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商品性大生产的例子,但采用家庭或家族手工业的形式以工助农的小商品生产则更为普遍。至于商业,徽州虽有“藏镪有至百万”的富商巨贾,但毕竟“千百中不一二焉”[③⑧],何况他们一般都靠经营国家专榷商品——盐而致富的,而非以徽州本土为依托。商业利润也“十一在内,十九在外”[③⑨]。在徽州,绝大多数还是那些迫于情势,“以贾代耕,不能不糊口于转毂”[④⑩]的小商人。他们春出冬归,以微薄的商业利润“求哺嗷嗷之数口”[④①]。这里,商人的经济活动和那些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家庭或家族手工业的小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其目的亦无非以商助农。因而从总体上说,徽州的商品经济只能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徽州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徽州对外商品交换之需而建立的。由于徽州的山区地理环境,作为商品交换内容的,多为茶、木、枣、笋等土特产品,而这类产品对加工业的要求一般很低。因此,市镇的集散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的功能。以集散为主体功能的市镇与周边农村的联系虽也很广,却较专业型市镇则要松散得多。前文所述的深渡虽可吸引几十里外的农副产品——枣到镇上加工、集散,但一旦其集散功能丧失,市镇与乡村间的这种联系便宣告结束。而江浙市镇,由于其生产功能较强,市镇与乡村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如王江泾镇,不仅周围接战港、渔家漾、南江市、栖真寺、油车港、盛家廊、龚家湾等都是“居民大半织絍为业”的专业生产村落(市),而且“左右三十里内,各乡悉统于泾镇”[④②]。可见,江浙市镇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发展,形成了市镇与乡村一体化发展格局。但在徽州,这种一体化格局始终未能形成,市镇与周边农村联系的松散性及商品经济本身的局限性,使市镇未能突破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藩篱,实现社会转型。
徽州市镇上的浓厚宗族文化氛围是阻碍其发展的又一因素。徽州是一个宗族制度极发达的地域社会。在传统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型中,宗族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启动与发展,从而对市镇的繁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与商品经济与其载体——市镇毕竟是异质的,在促进商品经济及市镇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它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实现。这种阻碍表现在许多方面,现仅从宗族文化氛围对徽商心理的影响这一角度,略呈管见。
且从商人在徽州的社会地位谈起。“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④③]”若离开商业,整个徽州社会就难以生存。故商人的经济地位在徽州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但商人的社会地位呢?商人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价值观整合了徽州社会?虽《歙事闲谭》云: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④④]。但切不可估计过高,笔者以为这种整合是十分有限的,且从属于徽州宗族文化。将《岩镇志草》与江浙的市镇志相比较,就可以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岩镇志草》连篇累牍大谈宗族、节烈、功名,有一种浓重的宗族文化氛围,对市镇的繁荣、商业的发达只略略带过,全然没有江浙市镇志中关于商业的详细记载。在徽州府县镇志和族谱家乘中,有关商人的记述虽然不少,却多散见于“义行”、“孝友”、“质行”等门类中,且对商人的商业活动所甚简,对其所谓义行,则不惜笔墨。在他们看来,商人的商业活动本身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因其商业利润加固了宗族伦理关系才值得褒扬。而那些“为人奴者”,即使“盛赀厚富”,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在这种浓重的宗族文化氛围熏陶下,商人往往把行义举、善举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岩镇大商人佘文义“操奇赢”而“振其家”后,“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族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又独资兴建佘翁桥,故《岩镇志草》褒扬他“年逾八十而义行不绝”。竟还有行义举而不惜败家破产者。渔亭商人杨乃贤不过中等资产,乾隆二十四年,他捐白银2000两,在渔亭兴建“永济桥”,功未毕而人去世,其子杨天培毅然将商号一片片拍卖以维持开支。桥建成,杨天培即宣告全面破产。岩镇商人佘文帽斥资重修“佘翁桥”,也是“桥成而家竭焉”[④⑤]。可见,宗族文化已深深扎根于商人的思想意识中,并内化为自觉行为,“见义勇为”[④⑥]成为其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途径。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教伦理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这一伦理的要义就是教徒有增加自己财富的责任,而增加财富本身就是目的,诚实、信用、勤劳只有符合这一前提,才能称作美德。正是这一伦理滋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④⑦]。徽州宗族也要求族人经商致富,但商业活动本身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只有宗教义举才是其出发点和根本归属。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徽州市镇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这里是一片沙漠。
在明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同处江南的平原市镇与山区市镇最终还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江浙平原市镇推动了社会转型,虽然这种“传统内变迁”在清中叶时为西方列强打破,但它却很快适应了政治、经济的变革,继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徽州市镇却因种种原因,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格局,从而造成徽州近现展的滞后。
注释:
①洪炎祖:《延祐新安后续志》,见弘治《徽州府志》,卷3,《食货·财赋》。
②①⑥《岩镇志草·发凡》。
③④《歙志·风土》。
⑤《金太史集》,卷4,《与歙令君书》。
⑥《徽州地区简志》,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42页。
⑦杭州府的行政区划变化大,这里是笔者对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谭其骧主编,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和《浙江省地图册》(浙江省测绘局编制,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而得出的大约面积。
⑧《清史稿·地理志》。
⑨休宁《赋役官解全书》。
⑩《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2》。
①①②⑦康熙《徽州府志》,卷8,《蠲赈》。
①②③④康熙《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
①③见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①④万历《秀山县志》,卷1,《风俗》。
①⑤《安徽省航运志》。
①⑦光绪《嘉定县志》,卷1,《市镇》。
①⑧弘治《嘉兴府志》,卷14。
①⑨(清)金淮:《濮川所闻记》,卷2,《坊巷》。
②⑩光绪《周庄镇志》,卷4,《风俗》。
②①《濮院琐志》,卷6。②②嘉庆《黟县志》,卷1,《地理风俗》。
②③转引自《民生的开拓》,第333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④②⑤顺治《歙县志》,卷1,《舆地·风俗》。
②⑥同治《祁门县志》,卷5,《风俗》。
②⑧③⑤④④《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②⑨《徽商便览·缘起》。
③⑩《明太祖实录》,卷53。
③①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文中对《沈氏农书》的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
③②唐甄:《教蚕》,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7。
③③《天下郡国病书·江南20》。
③⑥万历《休宁县志》,卷1,《风俗》。
③⑦光绪《婺源县志》,卷3,《风俗》。
③⑧④①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
③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1,《赠程君五十叙》。
④⑩《太函集》,卷14,《谷口篇》。
④②唐佩金:《闻川志稿》,卷1,《疆域》。
④③《二刻拍案惊奇》,卷37。
④⑤《岩镇志草》。
④⑥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
④⑦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文档上传者
- 明清之际几何原本内容
- 浅议明清文学演变
-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加强
- 明清小说花园意象
- 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纲
- 明清易代的思想史探讨
- 明清满汉女子发型形制演变
- 明清君主专制历史教案
- 明清以来广东生态农业类型
- 明清少数民族经贸文化
热门文章排行
相关期刊
- 明清历史论文
-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
-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
-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