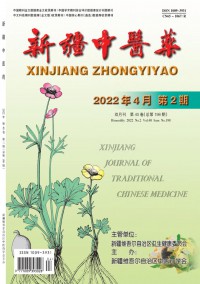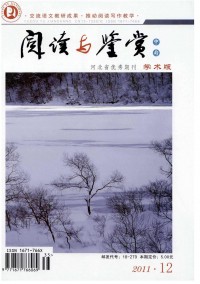林清玄语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林清玄语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林清玄语录范文第1篇
1、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呐。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最后,连角落都不给我们躲藏了。——几米
2、选男人,还是选个疼你的好。爱,原本就是个挺虚的词儿。它不只是简单的形而上,更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呵护。爱一个人,得给对方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在乎。一万句柔情蜜意,不如一句“放着,我来。”——苏芩
3、透支了眼泪,我们便会没心没肺的笑。如果有人可以依靠,谁会愿意独立。——千与千寻
4、比我菜的都在尽力,比我棒的更加努力,因此,我只能坚持、不放弃。
5、今天扫完今天的落叶,明天的树叶不会在今天掉下来,不要为明天烦恼,要努力地活在今天这一刻。——林清玄
6、没有人可以带走你的痛,所以也别让任何人带走你的幸福。
7、花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你就少了时间去爱自己喜欢的人。
8、水深无声,浅而叮咚。好的情感亦也如此,因默而沉。
9、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气馁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即便深陷困苦,也要让自己相信: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10、那些荒谬的往事,那些疼痛的爱情,那些生命里出现过又消失的人。他们影响了你,塑造了你,完善了你。终有一天,你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更好的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这就是青春的价值,这就是恋爱的意义。
11、有些人过去就过去了,不用追;有些事忘记就忘记了,不必悔;有些青春逝去了,是用来沉淀的,不用念念不忘;有些风景看透了,才能真正释怀,心不再累。我们总朝生活索取,却未必懂回馈,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进一出,生生不息,你要想相信,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付出,等待,终有硕果累累。
12、不要悔,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愿。
13、如果你觉得他特别光鲜、特别高大帅气、特别神通、特别有口才,那可能是他做给大家看,是他撒的网,而不是因为爱你;只有你看到了他颓废、阴郁、无助、木讷,别人看不到,而唯独让你看到时,他可能就已经爱上你了。
14、即使爱,也要爱得高贵克制。不矜持,不造作,不彻底,不窒息。没有人能把爱进行到极限,再爱你的人,也会对你存有保留。它意味着,一些心事不会与你分享,一些过往不会让你知道,一些生命中重要的人,不会让你遇见。
15、人和人在肉体上没差别,都是一百多斤肉,在生物学上是一样的,差别是在灵魂上,你的精神世界有多大,你的视野就有多大,你的事业就有多大。一个人事业的边界在内心,要想保证事业的边界不断增长,就必须扩大你心灵的边界,因此,学习是唯的一途径。——冯仑
16、没有人是傻瓜,只是有时候,我们选择装傻来感受那一点点叫做幸福的东西。
17、人生最糟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
18、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恐惧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嘲笑中长大的孩子,个性羞怯。羞耻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自信。宽容中长大的孩子,能够忍耐。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李开复
林清玄语录范文第2篇
――方文山
最近在想,信仰究竟是什么?是宗教救赎还是哲学领悟?不同的人对信仰的理解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信仰给予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正视自己。我们是谁?能做些什么?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相信这些都是有理想有梦想的人经常所反思的。我们都说希望青春无悔,但是我们的青春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昔日的梦想你实现了吗?是被现实压低了头,还是中途逃避放弃?在我们逃离的时候,是否也曾仰望那满天星光,找寻内心残存的力量?无数疑问盘旋,我们驻足,迷惘。柴静曾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我们孤独的思考着,可世上孤独的人又只你一个?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有多少人咬着牙坚持着,就算疼痛也忍着,就是不服输的成就了今天你所仰望的人。
《开讲啦》是央视一档演讲类节目,由撒贝宁主持,以公开课的形式传递青想的力量。嘉宾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各界名人:冯小刚、陈可辛、周杰伦、阿信、王伟忠、俞敏洪、廖智、徐静蕾……导演、歌者、词人、舞者、作家。他们是我们眼中光鲜亮丽的成功者,是崇拜的偶像。温馨的课堂氛围,台上嘉宾人生故事的讲述,与十位新锐青年代表进行交流,冲撞出有价值的思考,传递正确价值观,精彩的青春叩问感动着也激励着你我。
为了将梦想的力量传递,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蓝狮子策划的双册书籍《开讲啦》也已出版。书中不仅有三十五位名人的演讲内容,还有一些幕后小故事,小撒说,总结帝小撒,提问花絮等等,精彩部分以蓝色笔勾画,方便读者阅读。
不论是节目还是书籍,这都是一种美好愿望的汇聚。在书中,阿信和我们讲述他们如同笑忘歌的青春,黑曼巴科比拥有的能力、野心和永不言弃的精神,成龙父亲离开他时的忠告、梦想家林志颖的快乐来源……
当你在为摔倒痛哭流涕的时候,科比对你说:“我早就习惯了受伤”,成龙对你说:“我满身的伤数不清”;如果你在孤独寂寞独自怅惘的时候,李健走过来对你讲:“孤独导致幻想,幻想导致了他创作。”;在你被无数声音否定的时候,蔡依林会告诫你:“丧失自信心的时候,别人的质疑就会进入你的心里面,你就可能会迷失自己。”……
你看,那么多人陪着你,那么多人都是你的榜样,还有什么借口要停歇追求呢?
若说信仰是什么,我想,梦想就是最有爱的信仰。卢梭说:“我们也许没法依照预定的日子如期抵达我们的港口,但终归航行在正确的路上。”就让这股梦想的力量不断敦促着我们,向心中的圣殿前进吧!
小资对话撒贝宁: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创造力
Q=小资CHIC! A=撒贝宁
Q:对于接档《开讲啦》演讲类节目,是否心里没底?
A:第一次录制那会,我始终无法在脑海中想象这个节目最后是怎么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对象,它不像我在15年前主持《今日说法》,他们会很明确的告诉我:“这是一档法治栏目。”
Q:在录制的过程中有被震撼到吗?
A:有,在录第一期的时候,我一下子被现场的气氛所震撼了。因为“演讲”,“讲”是一方面,大家听不听的进去才最重要。当嘉宾在上面讲的时候,底下的观众真的会跟着内容的节奏心潮澎湃,跌宕起伏,那一刻所有人的节奏都在一起。
Q:你觉得节目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
A:自由。我可以和嘉宾用最自由的方式去沟通,可以和他开任何玩笑。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对话的节目,不会让人用一个固定思维去思考去表达。台下观众和嘉宾互动达到一定契合的时候,主持人已经完全无需控制节奏了。
Q:现在国内独创的节目很少,广受关注的很多是买国外的,是我们的创造力低吗?
A:我有时候也会感到痛苦,自己的创造力越来越弱。对于艺术创造和收视率我们也在探讨,我更希望遵循一个“美好的理念”,千万不要丢掉创造力。我不希望一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国外买来的电视节目。我们是做电视的,我们是在表达我们的思想,表达我们的情怀,我们不是流水线上的组装工人。吸收借鉴别人的经验可以,但不要太长,我们自己的创造力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
Q:在节目中你有那些新的创意吗?
A:节目现场我也有些临时创造,萧敬腾人称“雨神,我们就在现场给他下了场雨。大导演巴兹・鲁曼来的时候,他特别相信预兆。我就叫工作人员赶紧去买玫瑰花,在他闭眼祝福票房大卖的时候,天上的花瓣就哗哗落下,他就感到很惊喜。
【书摘】众星梦想语录――出发,我们一直在路上(PS:看版面,一个人配相应头像,和语录,排不下可删除部分)
阿信:我以前骑车的时候,要路过一条自强隧道。隧道不长,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短暂。所以我告诉自己,在我骑出这条隧道的时候,无论如何,我要把我所有的不安跟烦恼统统卸掉。
科比:无论任何人,都必须了解自己的能力,了解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只有充分了解自己,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王伟忠:沉迷要比用功重要。用功如果用不到对的方向上,那将痛苦无比。当你用功用到对的地方,你更笨感受不到过程的辛苦,所以我说沉迷比用功更重要。
赖声川:走自己的路没错,但走自己的路最重要的本钱,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如果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谁,不要难为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只要你愿意去花时间去寻找,你找到之后,了解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个什么位置,你能够做什么事,那你的潜力就可以真正发挥出来。那个时候,你的路就完全属于你,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李健:任何一个伟大的人,他们的伟大是用卑微来换取的,他有很多的闪光之处,他一定也有很多暗淡的时光,你所经历的今天他都会经历。所以,不要老看到这个人有多么大的能量,有多么了不起,其实人都差不多,每个人的成长阶段都是一样的。
周杰伦:人就是要有想象力,很多人都觉得我天马行空乱想东西。但我觉得,我们都该去找寻自己身上跟大家不一样的那一个点,并把他放大。
陈可辛:我真的不觉得我们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表面上改变世界。你可以事故,可以原话,只要你内心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必须要知道你要什么。
蔡依林:不要害怕犯错,因为很多人跟你们一样,也是从跌倒当中站起来的。没有跌倒过的人也许没有你们这么幸福,因为当你知道怎么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厉害。
林清玄:当别人攻击我的时候,我不回应,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的状况,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相信时间终有一天可以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态度。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