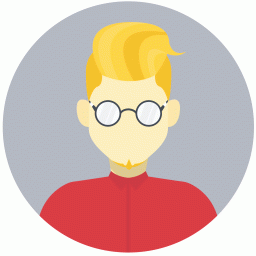管窥民族生态伦理的思想

一、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内涵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内涵的认识基本已达成共识,即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作为特定形态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一种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伦理相对应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一种以伦理的方式对待自然界及自然物的态度、意识、观念和行为模式。由于侧重点不同,学界对这一伦理内涵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从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各少数民族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而形成起来的对待自然的特定伦理观念及生活方式。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于边疆高山、高原、河谷、盆地和密林地区。为了生存,人们在适应和改造这些复杂的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了农耕经济为主,农、林、手工业、畜牧业共生互补的经济形态,也形成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作为各少数民族在这一过程中积累和形成起来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知识,蕴含和表现在他们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就是各少数民族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产物,是他们建立起来适应自然环境的“风俗习惯以及伦理道德态度和文化”。如哈萨克族保护草原的各种禁忌和处罚规则,维吾尔族禁止伐木、禁食猪、驴、马、骡、狗、猫及所有食肉类的猛禽和异兽的禁忌等。从研究对象上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伦理不同,而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伦理。它把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扩展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把自然看作是与人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里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物都是自然整体中的普通一员,具有同等的生存权利,因此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就此而言,人们应该重视生态平衡,尊重生物的生存权利,应当把人类的伦理道德推广到自然界中去。蒙古族萨满教就主张,生命并未有类的区别,更不存在高低上下之别,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而值得尊敬的。这突破了抽象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或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传统伦理学,深入到了生产生活中从实际生存环境出发,承认了价值主客体的双重效应:既承认了自然界对人的效用价值,又承了认人对自然界的效用价值。尽管如此,这里的伦理主体仍是人,其评价的终极尺度仍是各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满足,它遵循的仍是各民族的生存原则和发展原则。从价值观上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站在民族生存利益的高度引导和规范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行为,所以它不仅要求人们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还要在认识和把握自然的生态属性和规律过程中实现人类自身的善,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各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是“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由此形成的生态文化是“以调适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的文化”。如蒙古族生态伦理的核心就是“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和谐共存”。这种和谐是“天人和谐———无灾无害,风雨调顺;人事和谐———没有死亡,永葆青春;天人和谐———只要人世间没有蟒古斯之流的危害,那么天灾也不会发生,草原、河流依然碧绿清澈,人们依然幸福安康”。在这类生态伦理引导下,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思想追求和行为准则是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周边生态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从文化构成上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不同文化领域生态伦理总和。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内含于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方式中,内化在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心态中,形成于他们的认识、观念、意识和信念中,并最终诉诸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据此,我们可知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包括三方面内容:精神生态伦理、物质生态伦理和制度生态伦理。精神生态伦理包括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节日文化等;物质生态伦理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制度生态伦理包括禁忌、乡规民约、礼俗、政治制度等。如纳西族禁止在河里洗屎布,禁止向河里扔废物或倒垃圾,禁止向河里吐口水,禁止堵塞水源,不得在水源地杀牲宰畜,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毁林开荒,立夏过后实行“封山”,禁止砍树和打猎;再如哈萨克族禁止铲除丛生青草,住房附近、水源旁、礼拜寺、墓地周围不能大小便等。
二、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特征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不仅具有丰富内涵,也具有不同于一般伦理的特征。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对少数民族伦理特征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地域差异性生态观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各少数民族在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苏日娜就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当地特定时期的生态条件密切相关。不同的生态条件是不同民族的生态伦理意识形成和流行的基础之一;民族生态伦理意识又反映或体现了生态状况,透过千差万别的习俗,我们可以洞窥到中华民族生态伦理意识的差异。安颖也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由产生它的自然地理环境承载的,不同的地域滋养和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如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充分利用河流纵横、沟渠密布,各地普遍设有水利灌溉系统,广泛种植水稻,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稻作生态文化;哈尼族也根据云南亚热带山区气候垂直分布和植被立体分布特点,创造了堪称人工生态系统大创举的梯田农业,建构了一整套系统的生态文化思想。
2、尊重生态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观
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可选择及其对人活动的限制,各少数民族在与当地自然环境长期交互影响中自发遵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规律安排本民族的生产生活,在促进适度多样化利用资源实现低水平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在减少污染、绿色消费、较少破坏自然及野生动植物等方面维系生态平衡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贺瑞金等人就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遵循生态规律,要求人们把握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违背生态规律,以牺牲民族的生态环境及资源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将导致整个民族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在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下能够长期生存、繁衍和发展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清真’的饮食习惯、可持续的农耕方式、农牧工(手工业)商相互依存的复合经济形态、民居中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厚养薄葬的方式维持了当地生态平衡,促进了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间接地符合生态规律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哈尼族、傣族、侗族在适应与利用当地山高林阔、高温多雨的自然条件中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了‘林-水-田’的生态模式。它与其所处生态环境及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互动,体现着人与自然环境的融洽与和谐,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
3、天人一体、和谐共存的生态观
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在与当地自然环境的不断调适中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同源共祖、共生共荣的天人一体、和谐共存的生态观。如回族伊斯兰教中的人与自然都是真主创造的生命体的和谐共存的生态观,纳西族的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兄弟的生态文化观,藏族的人与自然混融一体的认识,普米族的人与自然是朋友的观念,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中的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和自然崇拜所包含的文化与自然一体融合的思想等,它们的具体内容虽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体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本源,都是大家庭的兄弟姐妹,是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共荣共生的。因此,人们应该尊重生命,善待自然万物,应该与各种生命和睦相处,共同生存发展。由此,善待自然就成为各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模式。这一模式既反映了人与自然原始的直接同一性,同时又蕴含了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
4、敬畏自然的适度消费生态观
随着对自然不断索取而感受到自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和报复,各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敬畏自然的适度消费生态观。“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促使人们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畏”显示的是一种警示的界限和自省的智慧,告诫人类应“厚德载物”,有所不为。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当人类对资源利用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因而他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根据自然资源的数量与季节,有选择性地控制对动物资源的使用,适度的动植物消费,适时利用自然资源,适度人口繁殖,使自然能保持自我循环,即适度消费的生态观。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适度截取方面:“他们从不把植物的果实摘光,也不把地下的薯类掘尽,不是无节制地猎杀动物,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这种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认识自然并调整自身行为而形成的生态观,有效防止了人们过度猎杀或采集动植物,从而避免了动植物资源的迅速灭绝,保护了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界平衡。
5、万物有灵的普遍约束生态观
由于对自然依赖和时常受到自然威胁,各少数民族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希望得到自然的庇护并通过某种方式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某种力量,就产生了对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种种虚幻认识和崇敬心理,形成了“万物有灵”观念,并以巫术、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形式表现出来。萨满教就认为万物有灵,山川树木、风雨雷电、日月星辰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狩猎的运气等等都由神灵主宰,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湖,一鸟一物,处处也都有灵,因此时时处处都需小心谨慎,不触犯自然,也就不会触犯神灵。结果,蕴含这一观念中的生态伦理虽不像专门法那样具有明确的系统和规范,但对人们的行为却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人们敬畏自然就是对神的尊敬,破坏自然就是对神的冒犯,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就很好地保护了当地自然环境,维持了生态平衡,美化了环境。
三、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逐渐显示出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价值和优势,在养护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作用,学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
1、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和我国生态多样化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作为各少数民族适应特定自然环境的生态文化,养护着当地生态环境,并促成了我国生态多样化。贺瑞金等人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遵循生态规律,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把握少数民族经济社会问题,“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少数民族和自然的关系”,就使民族发展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伦理道德与生态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了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宁夏南部山区的回族就积极探索创造了一些适合高原地区的耕作技术,实行倒茬、歇地、换种、套种等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作物物种多样性协调机制和歇换张弛来改善土壤和保持土质,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就体现了回族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注意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识。正因为如此,“综观生态环境较好,生物多样性的地区,都是民族生态意识牢牢根植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地区”。“民族生态意识浓厚的地区和时期,生态就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反之,民族生态意识失效的时候,就会造成生态的灾难”。
2、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
少数民族伦理思想是我们克服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资源。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表面上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后果,但实质是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所致。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看成是惟一的、绝对的,把自然看成人类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可以任意使用,这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人们在传统物本论发展观影响下,对自然肆无忌惮地索取和掠夺,造成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为了克服人的自我神话化和对自然的轻视,走向科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然要以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原则建构和谐生态伦理观。而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就为我们克服人类沙文主义,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和谐生态伦理观提供了思想借鉴:人与自然物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都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只有和谐相处、协同发展,才能建设美好家园。不仅如此,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作为各少数民族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独特方式和文化机制,还是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基础。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只有在扬弃他们的生态伦理传统并在价值理念层面与之相融合,才能获得本民族理解和认同,贯彻和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因此,要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必然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他们的生态伦理传统,使其引导他们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3、有利于维护民族地区团结稳定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作为建立在各少数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心理认同基础上的道德体验,不仅是维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文化机制,而且是形成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因素。它对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安全感,维护民族心理整合凝聚起着重要作用。白葆丽认为,“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规定着人生态度,规范着人们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从而形成共同认知和心理,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通过教育和引导使各少数族人民自觉维护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并由此维系民族内部团结,从而保护了该民族繁衍生息和社会不断进步。在这种生态伦理引导下的自然经济则造就了各少数民族社会在群体利益至上的前提下,维护个人利益与人际关系,促成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体贴和宽容,这有效地保障民族成员的权、利的统一以及社会互动的和谐。
四、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虽在促进当地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陷入生态危机,他们的生态伦理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而被挤压得支离破碎甚至遗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对人与自然认识上,随着唯物主义世界观
和科学知识广泛普及,各少数民族建立在经验直观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直接统一的天人一体观念和万物有灵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人与自然生命同根、价值同等的意识也逐渐被“人与自然相对立和人类有能力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等”的意识所取代。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开始命令自然、征服自然,打着相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以及向自然界进军的口号不适当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这不仅使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也使民族生态伦理传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敬畏自然和保护生态的传统逐渐被人们漠视、丢弃、遗忘。
2、在生产方式上,随着科技的推广、经济结构
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各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适度多样化利用资源以维持低水平持续发展的模式,代之以机器化大生产为依托,通过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资源来追求高水平富裕生活的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日益显现出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不相适应甚至冲突而逐渐被忽视和淡忘。这表现在它虽蕴含着科学、辩证的合理成分,但都是自发、朴素、直观的感性观念,它维持的是一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等亲缘关系”和“人地关系所限定的亲生态”的动态脆弱平衡,当生产发展突破这一条件走向工业化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伴随着城市化而不断扩散时,这种生态平衡模式就被打破,人们也“被纳入到人与生态、族群与他者的对话体制中”,其传统生态伦理随之受到抑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流失。
3、在生活方式上,随着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
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增加和外来文化的冲击,适应特定生态环境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区管理、民间组织、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缺乏理解和认同而逐渐不被社会接受,同时本民族对它们又缺乏文化自觉并加以创新而导致对其缺乏自信心。结果,它们日趋式微,逐渐被各种流行方式、西装革履和现代推进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标准化、批量化建筑所取代,其生态伦理传统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日益被人们忘却。为了有效利用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传承和创新这些生态伦理,使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组织形式和全球市场体系紧密结合,从而转变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生态伦理。
①.在看待人与自然上,“应该在尊重自然、礼敬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性和生态伦理的基点上”,实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无神论思想与各民族人与自然浑融一体的宇宙观和万物有灵信仰之间相互尊重。为此,我们要承认自然力量的神圣性和庄严性,必须接受人类行为受到自然约束的事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掠夺和被掠夺关系,而是相互给予、平等索取关系。我们在普及科学知识时,也应持有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价值理念;在主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积极给予自然等量的甚至是超量的回报。
②.在生产方式上,在现代科技支撑下,要让各民族多样化利用资源的生产方式能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获得较高经济利益,以满足各民族群众既保护自然与文化,又尽快脱贫致富的要求。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应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多元性和科学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特征,更多地把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合理成分融入传统生产生态系统,将其传统的“弱势生态文化”改造成为“强势生态文化”,从而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具体而言,就是要使各民族认识到只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坚持天人合一的产业结构,努力搞朝阳产业,进行绿色革命;要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必然存在隐患。
③.在生活方式上,各少数民族要“通过依靠自己的文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唤醒其文化自觉意识”。同时,要通过编写相关传统生态伦理乡土教材、举办传统节庆活动对各民族成员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要他们知道,良好的生态不仅关系当地经济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还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由此使这些生态文化逐渐深入人心。
④.在民族社区治理上,“坚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文化、习俗、宗教和法律等多重保护自然资源意识,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村民自治”。同时,从民族传统社区环境治理功能的现代化兼容、扩展与重塑角度出发,建立兼容“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驱力与现代化进程外驱力”的长效组织机制,以民族社区创新运作为核心进行“生态文化变迁及生态治理载体”的重塑,寻找符合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且共享现代化成果的生态建设模式。
五、结语
学界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涵盖了它的内涵、特征、传承和创新途径及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等方面,体现了人们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自觉。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内涵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前提还需进一步追问。其次,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特征,学界更多地拘泥于材料搜集和整理上,缺乏理论提升。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以素朴、经验的形态呈现出来,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需要梳理其内容,辩证分析其合理因素和不足之处,科学揭示其特征。再次,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价值的揭示明显不足。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同发展,我们需要充分揭示和阐明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对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使其成为可有效利用的思想资源。最后,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本身缺乏学理性辩证分析,对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日益凸显出来的局限揭示不够充分,相应地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传承和创新的具体途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些都是今后研究需要努力去突破的方面。
作者:王景华刘东英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