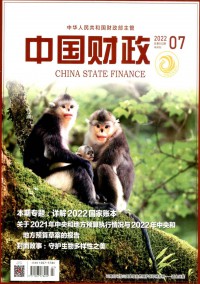三十六记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三十六记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三十六记范文第1篇
每一天都会告诉自己要好好控制情绪,不抱怨,谨言慎行,这不是将自己变得懦弱和没有性格,而是在慢慢地提升自己。凡事不以恶意揣度别人,不以私利给他人添堵,不妄自菲薄,也不诋毁他人,这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微言语
遇到喜欢同一本书的人,总比遇到喜欢同一件衣服的人来得更有默契感。个体和个体是很独立的,书是很好的介质,让彼此知晓是同类。信赖跟心灵有关的东西,而不是跟皮肤有关的东西。
微言语
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来,处之以淡,方不为快心所惑。
――
微言语
你只要尝试过飞,日后走路时也会仰望天空,因为那是你曾经到过,并渴望回去的地方。
――达・芬奇
微言语
要放浪游戏,年纪未免太老;要心如死灰,年纪未免太轻。
――歌 德
微言语
当人生经历一段困难的日子、一个毫无生气的时期,我总是这样做,坚持某几句话,表达某种见解的几句话。即使这些话已经过时并毫无意义,我知道生命一定会回归,从而使它们重焕生机。
――多丽丝・莱辛
微言语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
――龙应台《目送》
微言语
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不管陷入多悲惨的状况,如果能够一笑,就会有重新充电的感觉。
――伊坂幸太郎《金色梦乡》
微言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微言语
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过都不会被人忘却。
――茨威格《心灵的焦灼》
微言语
遇见是两个人的事,离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遇见是一个开始,离开却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离开。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微言语
三十六记范文第2篇
有人说,三十六计要会运用,不会运用,就会被整死。这句话一点也没错。古代的精明将士用它战胜敌人,现代的xx中学xx班学生用它整老师,老师用它整学生。
请听我介绍几种常见的:
借刀杀人—某某同学和xx同学有矛盾,某某同学故意恶整xx同学,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告诉身体肥壮,头脑简单的yy同学:“xx同学说你有老年肥胖症,还说他鄙视你。”结果,成功让yy同学恶揍了xx同学一顿,事后,某某同学再次采用“打死不承认”的方法完美地结束了“借刀杀人”。(真阴!)
三十六记范文第3篇
一、借刀杀人。一个人的理财智慧永远是有限的,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完全没有必要躲起来殚精竭虑挖空心思想到头发都白了。你可以广泛征求亲友的意见,参考理财专家的建议,解决理财难题。
友情提示:你须有识别好“刀”的慧眼,也得有自己的主见。另外,借来的“刀”不宜反复使用。
二、以逸待劳。理财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等待和创造机会。尤其当市场波动时,千万不要盲目跟进,自己乱了阵脚。要静观其变,集中资金,伺机而发。
友情提示:“逸”是积蓄能量,等待时机出来,不是“懒”的借口,“逸”过了头,就会失去理财的激情。
三、趁火打劫。此计适用于各大商场超市逢年过节酬宾、开业店庆赠送、相互竞争降价之时,一定不能放过此等良机,最好全家倾巢而出,带足money,分头行动,各购所需。
友情提示:同样要有识别好货劣货假货的目光,过度“打劫”当心会被“火”所伤。
四、暗渡陈仓。不是谁都有科学的理财头脑,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的理财手段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但谁手头都会有一点闲散资金,我们完全可以以小博大,神不知鬼不觉地投入到见效快的行业中去,说不定某天幸运之神会光顾你,那么就没事偷着乐吧。
友情提示:做你该做的事,工作生活一切照旧,业余时间别忘了多打听、了解你所投资的项目资讯。
五、调虎离山。你的储蓄日益增多,而银行利息却日趋减少,随着政策的不断利好,你完全可以放心地把银行存款拿出一部分做投资:股市、保险、房产……这样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否则,一旦发生意外,你银行的存款可就损失大了。
友情提示:适当留几只小虎储蓄“镇山”还是最保险的,否则一旦家庭出了意外,“山”也不保了。
六、擒贼擒王。理财手段有许多种,但并不是每一种都适合你。一定要反复比较,权衡利弊,根据自己家庭收支状况和其他条件来选择一种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法。抓住事物的根本和关键,理财难题才可能迎刃而解。
友情提示:不管擒贼还是擒王,关键要有财可擒,所以工薪家庭最重要的还是要广开财路,想方设法多多赚钱。
七、混水摸鱼。水至清则无鱼,因为如果取得收益的方法太简单,同时就会有很多人也能想到做到,留给你的蛋糕自然不会太大。有时不必等到理财思路太过清晰,凭直觉看好的赚钱之道,而且投入不是很大的方法也可以一试。
友情提示:不管清水混水,前提是你得有摸到鱼的过硬本领。
八、金蝉脱壳。如果你掌管家庭财政期间出现了赤字或投资出现了负效益,你的家人纷纷指责你的不是时,你可以忍气吞声,作出深刻检查,或者随便抱怨点什么,在家人对你放松警惕时,暗中却留意一切可能赚钱的机会,广结人缘,也许一笔生意就能弥补你之前的损失哦。
友情提示:记住前车之鉴,同一个地方不能跌倒两次。
九、空城计。如果有人找你借钱,只要不是生命垂危、火灾地震,你就不要勉为其难,轻易把钱借出。要知道人家以后能还你钱就不错了,即使若干年后还了,也许利息都够不着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哭穷,表现出捉襟见肘、列举数十条自己钱不够花的“惨状”,让借钱之人于心不忍、自动离去。
友情提示:此计主要针对那些没有信用的人。
十、连环计。理财包括很多计谋,需相互配合、多计并用、环环相扣,这样才能相互弥补不足,发挥各自优长,获取最大效益。
友情提示:别连环晕了,关键时一计足够,但练就这些计谋,要用时方能得心应手。
三十六记范文第4篇
关键词:谋略;状态;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以《易经》的阴阳燮理,推演兵法的奇正,刚柔、攻守、进退、主客、虚实等的相互变化,“可谓集前人战术心理精华之大成”。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为三十六计注入新活力,其思想必然会为教育的发展找到一条新出路。
一、谋略――三十六计的核心思想
谋略为军事用语。“谋”的本义是通过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谋略意识起源于人与大自然的抗争,也即用少的付出获得多的收入,对多与少的研究也正是社会能发展的根本所在,这也“使得教员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的问题得以解决。
谋略是认清局势后的权衡度量的筹划过程和分析利弊定夺方略的过程。它要求三点,一以“知己知彼”为前提。二要深思熟虑。对敌我力量反复论析,精心设计取得最终胜利。三以最终胜利为目的。《三十六计》总说中认为“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正是此意,在筹算中可以寻求谋略,而谋略的确依靠周密筹划而成,这需要相辅相成原理的运用,但临机应变不可凭空安排。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教学方法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笔者认为,教学方法是师生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而采取的有效组织和利用教学环境的方法,它是谋略在教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应用。
如,瞒天过海能保证德育工作顺利进行。军事上瞒天过海是巧妙利用假象迷惑敌方。讲究储玄机于庸常,教育者以此反思,可发现部分德育工作存在一些弊端:(1)工作独立化,与现实脱节。(2)工作不注重思想升华,而流于形式。瞒天过海在德育工作中使用必须以真实为前提,这里是反用战计。从学生身上出发,德育工作要走进学生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达到德育工作目的。
又如,暗度陈仓可以丰富德育工作。军事是指迂回战略,其思路是采取正面详攻,当敌军集结固守时,我军则向敌侧后迂回,以行突袭。反思此计,我们会发现其根本用意在于转移注意力。落实到具体开展德育工作就是要避免单调、枯燥的局面。例如,开展比赛,这类“明修栈道”实则寓教于乐的计谋高明之处在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二、状态――《三十六计》的基本特征
《汉语大词典》中认为状态有两层含义,一是“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二是“在科学技术中,指物质系统所处的状况,也指各种聚集态”。
状态引入教学,其含义更倾向于一种活动的准备,表现为:(1)储备:指师生原有的知识储存量和学习习惯等一些为顺利进行教学活动提供保障的条件。(2)认知:即对教学活动各因素及其关系的认定。(3)态度:指师生对教学活动构成因素的看法和心理倾向。(4)选择:指师生估价,选取有价值的能力倾向。论语中有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示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愤与悱即为一种学习状态,它来自对知识的需求和对自身认识力的了解程度。
以往教师只注重知识的传播,而忽略了学生的准备情况,其结果不容乐观。笔者主张改革教学方法,帮助、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即状态教学法。“进入状态,进行教学”是该教学法的基本特征,也是主要思路,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比如,运用打草惊蛇帮助学生健康发展。原意指打击一处,惊动了另一处。现指做事不加保密,使对方有所警戒而事先做了防备。在教学中运用打草惊蛇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个别犯有同类性质错误学生,对典型的予以严肃处理,并间接予以他人警告,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但切记要信息准确。在学生德育工作中,教师发现学生存在问题的信息量少或不完全,可用此计试探虚实,针对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进而开展德育工作。
让教学成为一种寻求快乐的途径,那么就必须把教学与战争看得同等重要。师生关系平等、民主,教师仅以谋略处于主动,并以此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进入状态,再进行教和学,这就是《三十六计》给我们的反思。
参考文献:
[1]无谷,译注.绘图三十六计.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03.
[2]李秉德.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杨得志.中国军事大辞典.海南出版社,1992-10.
三十六记范文第5篇
第三十六集
中秋宴
(下)
人物:金紫燕、穆双毅、隋世兵、霍智广、屠天信、李瑞瑞、陶玲、刘莉莉、程波、火药妈、吕荣、丁兰、文文、文文妈、命运、工人两名、雪荷、赵大海。
时间:9月23日,晚。
(晚,歌厅。最后的几位客人离开歌厅。李瑞瑞、陶玲在发赠券给出门的客人。每人一张。)
李瑞瑞:谢谢,辛苦了。
陶玲:每张赠券送两瓶啤酒。明天请早。
(客人们拿了赠券都走光了。)
(刘莉莉、程波一起收拾桌椅。)
刘莉莉:(边干活边小声说)瑞瑞越来越霸道了!发那么多赠券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程波:(干着活小声说)一张赠券只换两瓶啤酒,没什么关系。
刘莉莉:今晚的客人没一百也有八十。一百多两百瓶啤酒不少钱呢!我们歌厅的客人本来就少。
(李瑞瑞、陶玲送走客人,关门,走去刘莉莉身边。)
李瑞瑞:(接刘莉莉的话)这话没错。歌厅除了一些爱好看出事的老客人之外,很少有人敢来。我也是想借火药妈来参观的机会,多请一些客人来充场面。有这么多客人,火药在母亲面前也会有面子。他会回报的。你们也应该知道,七个歌手里,站在我们这边的人越多,局势越好控制。发赠券虽然很多,可回头再来的客人又怎么会只喝两瓶啤酒。如果只和两瓶啤酒,我们就吃大亏了。你认为我会做吃亏的事吗?眼光放远一点。(看刘莉莉)我想的还不够周到,你有没有补充?
刘莉莉:我只说了一两句。你就说了几十句。还让我补充。明摆着是给我小鞋穿。
李瑞瑞:是又怎么样?我是歌厅经理。我决定的事还用不用问过你呀?
刘莉莉:当然不用。我辞职!(要走)
陶玲:(拉着刘莉莉)莉莉,别闹义气,工作不好找。
刘莉莉:我不在这受气了。三天两头的给我小鞋穿。
程波:别只说瑞瑞,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不想自己受委屈,先别伤害别人。
刘莉莉:(对程波说)你也教训我?!
程波:辞职是你最后一招吧!你去别的地方能找到我们三个这样的好朋友吗?到别的地方你敢用托盘打人吗?不会努力创造机会,只会在有变化的时候发牢骚。老老实实的活得了!还不干活去!收拾桌椅,去呀!
李瑞瑞:不用了,莉莉,你不用干活了。(很不满意的样子)去吧台自己拿双薪回家吧!
刘莉莉:(怕了)你真要开除我?我只是随口说说的,不是真的要辞职!
李瑞瑞:我可不是随口说说。去自己拿双薪吧!
陶玲:瑞瑞,你别跟莉莉生气了。她走了,我们在这也没什么意思。
李瑞瑞:(笑了)快过节了。我让莉莉去作帐,这月我们发双薪。
刘莉莉:你是经理,你去作帐吧!
李瑞瑞:我去了,你们别说我没干活?
陶玲:歌手也发双薪?
李瑞瑞:给他们五十块钱买月饼好了!(走去吧台)
刘莉莉:(小声说)总是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吓唬我!
陶玲:算了。你别说了。(干活)
刘莉莉:(干活)我不说她几句,她会给我们发双薪吗?
程波:(干活,训刘莉莉)好了伤疤忘了疼。小心瑞瑞翻脸真的开除你。
刘莉莉:(心里怕,嘴上不说)她想的是比我想的多!我要是当经理也会用这些小心思。我就不信咱们三个比不过她一个。
陶玲:我可不参与。当经理有什么好!也不看看什么环境!都是些什么歌手!贪心不足蛇吞象。就不怕那只象发疯把蛇踩死?
(李瑞瑞在吧台记帐,算帐。准备钱给四人开双薪。)
(晚,别墅。霍智广的房里。火药妈坐床上。霍智广搬了两张桌子进来准备打地铺。)
火药妈:儿子,你先把桌子放下,妈有话说。
霍智广:(拼了两张桌子)说吧!我听着呢!(往桌子上铺毛毯,床单)
火药妈:你这一天天的,就是吃四顿饭,晚上去那个歌厅哼哼哼,唱两句半歌。你就这么打发日子?
霍智广: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唱歌怎么是哼哼呢?你没看见有多少人听。他们特别喜欢我!
火药妈:你想气死我?我看那些人,十个里有九个是男的。招他们喜欢有什么用?妈想抱孙子了。
霍智广:我就知道来了,不仅仅的过节。还有什么一起说吧!
火药妈:你爸让我带你回去。
霍智广:我回去干什么啊!
火药妈:跟你爸学干石匠。你爸岁数大了。身体也不比以前了。
霍智广:别干石匠了!让那些石头在山里睡着吧!石头睡的好好的,非把它们挖出来,一个个打个粉身碎骨,变成石子,变成沙。现在治理沙漠呢!
火药妈:(看着霍智广)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征兵那年,你不是说当不上兵就跟你爸干石匠吗?你学得都差不多了。你忘了?你这个脑子除了能记住打架,还能记住什么?
霍智广:我不回去。回去也是找那小子打一架,然后再回来。敢娶我对象!我忍了他快四年了,我怕回去忍不住失手打死他。
火药妈:人家儿子都生了。你还想着她有什么用?
霍智广:就想!这事在我脑子里。我想什么,你管不着。
火药妈:洗脚,睡觉!(烦了)
霍智广:我去放洗澡水。(出门去卫生间)
(客厅。金紫燕给霍智广左肩上的咬伤换好药,贴好纱布。医药箱在身边。火药妈洗完澡。出卫生间回房间。正好看见。)
(金紫燕看见火药妈后飞快收拾好医药箱,提起来飞快上楼去。)
(火药妈一直看到金紫燕跑上楼去。)
霍智广:妈!你别看她了。
火药妈:(强调)妈又没说什么!(回房间)伤口不疼了吧!
霍智广:子弹不找我换药,我都忘了。(去卫生间)
火药妈:她还很细心。(进房去开着门)
(金紫燕悄悄下楼,站楼梯上。)
(霍智广悄悄走过去两步,站住,不再靠近。)
(金紫燕伸右手勾食指,让霍智广过去。)
(霍智广摇头就是站着不动。)
(金紫燕又挥拳又瞪眼的威胁霍智广。)
(霍智广耸肩张开双手,表示无能为力。不在乎。)
(金紫燕退回楼上去。)
(霍智广的房里。门关着,灯开着。火药妈睡床上。霍智广睡桌上。)
霍智广:妈,晚安。(伸手要关灯)我关灯,睡吧!
火药妈:跟妈回家吧!
霍智广:(烦)不回!
火药妈:这有什么好的?妈用你寄回家的钱给你盖了房子。
霍智广:我往家寄的那几千块钱能盖多大的房子?
火药妈:妈在家前边给你盖了三间大瓦房。
霍智广:把那点钱买东西吃了穿了多好!费那么大劲非要给我盖房子。我不回去。
火药妈:你就这么过一辈子?
霍智广:现在是暂时的,再过一段时间等乐队彻底..(自语)彻底不准确。等乐队安定一点,我们几个一定能闯出名堂的。到时候我把你和爸接到这来住。
火药妈:我的羊怎么办?你爸也离不开石头。
霍智广:都是麻烦事!等我闯出名堂,把我的歌出了专辑,那时候我也买个别墅,让你和爸住。养点袖珍羊。雕一些袖珍石头。雕玉石好了!
火药妈: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吹牛呢?让你爸雕玉石,他一锤子下去,什么玉石也都碎了!出专辑是怎么回事?
霍智广:简单一点的说就是把我的歌录到磁带、光盘里,满大街的卖。
火药妈:满大街的卖“长角的狮子”?
霍智广:是一个有着狮子心的羊。
火药妈:那不把羊都吃了!
霍智广:有着羊心的狮子?
火药妈:那不饿死了!儿子,你从小就说话晚。妈和你爸都觉得你傻傻的缺个心眼。还好认识了法远和尚,多亏了他教你。不然真不知道你要傻到什么时候!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娶个媳妇,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唱那些羊啊,狮子的,小孩子都不会喜欢的。都这么大了,连麒麟都不会写。
霍智广:我现在想起来了。
火药妈:你小时候跟比你大的孩子打架都能打赢。中午怎么让房东按在地上咬,不敢还手呢?
霍智广:这就是“出生牛犊不怕虎,长了犄角反怕狼”。家那边我那些朋友还好吗?
火药妈:都成家了。
霍智广:(自语)不问好了!
火药妈:你一开口就是狼,羊,狮子的。你平时都说这些?
霍智广:我困了。
火药妈:你回家雕一对麒麟,那两个字就不会忘了。
霍智广:我记得有一次我打完架,人家父母找上门来。你也是抓了个什么东西,把他们打跑了。
火药妈:你没看到自己被打的惨样。
霍智广:我是打赢了的。我打架就没输过。
火药妈:你除了打架有本事以外,还会什么?
霍智广:我现在吉他弹的很好。我还自己写歌词。
火药妈:还敢说那两句半歌词啊?
霍智广:妈,早点睡吧!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火药妈:几点?
霍智广:四点就得起。
火药妈:那早点睡吧!那么早有人照相吗?
霍智广:冰有摄象机。我们自己拍。
火药妈:这样好。
(早上四点,隋世兵房里。隋世兵睡在床上。霍智广走进来,开着门,推醒隋世兵。)
霍智广:(推醒隋世兵)醒醒,起来。
隋世兵:(勉强睁开眼睛)几点了?
霍智广:四点了。
隋世兵:做早饭还早!(闭眼睛想睡)
霍智广:陪我和我妈去看升国旗。
隋世兵:我看过了,你们去看吧!
霍智广:开车送我们去。再拿上摄象机。
隋世兵:不去!滚蛋。你敢碰我,我咬你!
火药妈:(走进隋世兵房间)你再说一遍?
隋世兵:(飞快坐起,瞪大眼睛看着火药妈)阿姨,早上好。
火药妈:你再把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隋世兵:我不敢再咬火药了。我保证,我发誓。实在亲戚,我说的话你也信不过?
火药妈:你要是再敢咬我儿子,我把你的牙全摘下来。
隋世兵:我镶钢的,合金钢。连骨头都咬得断。
霍智广:妈,咱们出去,让他穿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