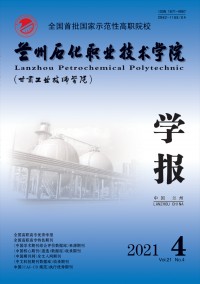窦娥冤教案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窦娥冤教案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文教学;高效课堂;构建;途径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开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激发和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与思考,实现课堂教学最优化,这是每一位教师在改革与探索中追求的目标。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那么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激发学生求知欲,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启迪学生的智慧,让语文课堂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建立互动的新课堂
和谐的师生关系是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积极性的前提。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是一种催化剂,它能活跃学生的思维, 让学生敢于想象、敢于发问,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传统的教学观认为教学活动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围绕着教师转,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和占有者,对于求知的学生来说,教师就是知识的宝库,是活的教科书,是有学问的人。没有教师对知识的传授,学生就无法学到知识,所以教师是课堂的主宰者。所谓教学就是教师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学关系就是:我讲,你听;我问,你答;我写,你抄;我给,你收。在这样的课堂上,“双边活动”变成了“单边活动”。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就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交往和互动,因而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与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见解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观念和理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发展,从而达成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二、精心设计教学目标,建立有效学习的课堂
语文教学的目标是语文课堂的灵魂,它既是教师教的指南,又是学生学的指标,也是语文课堂评价的依据。首先语文教学目标要明确,一堂课要达到什么目的,教师上课前就要“瞄准最后的结果”,这个目标要根据教师选取的教材内容而定,这就要求教师吃透大纲精神,用好教材,研究学生,写好教案,做到脑中有纲,腹中有书,目中有人,胸中有案。其次,目标越明确,课堂教学过程的组织就越紧凑,教学效果就越明显,教学的目标要重点突出。一堂语文课不能面面俱到,目标确定了,讲什么,练什么,既要全面又要保证重点。所谓全面,是指在课堂40分钟内能够解决的最大范围;所谓重点,是指从面面俱到的任务中找出占主导地位的任务。例如讲《荷塘月色》重点在散文语言的品味;《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教学目标为:在掌握文中出现的重点文言词语、语法现象和特殊句式上学习廉颇、蔺相如的为人,培养学生以大局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再次要做到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优化教学目标,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能够既掌握了知识与技能,又培养了情感态度价值观。最后语文教学设计要以学生发展为本,对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提出不同要求,对知识、情感、学法、实践技能提出相应目标。通过一节语文课的教学让不同的学生都有所发展,在不同的学习领域都有所提高,真正实现语文课堂“三高”目标。
三、建立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新课堂
传统的学习方式是接受性学习,即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老师把自己的知识强加给学生。新课标下的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和主角,教师只不过是一个参与者和组织者。因此在上课时,老师应该创造条件,让学生自主地学习、合作地学习、探究地学习。
在教学中,我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主动发现问题,探索新知,这对学生自己来说印象和感受最深,理解得也最深刻。改变过去课程实施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学习的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而富有个性的过程。这样让学生在合作与探索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到学习的快乐。
四、运用多媒体手段建立“信息多向交流”的新课堂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手段就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最多加一台录音机,教学手段单一、呆板,课堂气氛沉闷,很难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在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老师应该充分调动所有学生的力量,更多更广泛地搜集有关信息让大家共享。因此新型课堂的信息可以由老师流向学生,也可以由学生流向老师,还可以由学生流向学生,从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合作共享集体备课探究学习高效课堂
2010年秋季,贵州省普通高中全面进入新课程改革。新课程实施后,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教育教学的评价等都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课改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如小组互助学习,讨论,共同探究等,面对这样的课堂,教师该怎样应对才能构建高效课堂呢?为此,我们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做了些改革,我任教的学校语文教研组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共享”,其核心目标有两个:一是“成立备课小组,集体备课,优势资源共享,共同提高。”二是“于合作中努力实践课改理念,精心营造实效课堂。”语文组的老师们通过共同努力,总结外出学习的经验,并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精心打磨课堂细节,探索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做法:
一、 成立集体备课小组,优势资源共享,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每学期开学伊始,我们在组长的组织下集体备课。
以高中语文必修四为例,我们的做法如下:
第一单元:介绍戏剧的一般知识;引导学生掌握阅读剧本的基本方法。重视学生的文学欣赏活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体验和认识。
第二单元:介绍有关词这种文学样式的一般知识;引导学生学习欣赏宋词;指导学生诵读;
第三单元:介绍随笔、杂文的文体知识;引导学生理清文章的思路,提炼和概括文章的观点;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四单元:介绍传记的基本知识;介绍传记的读法;引导学生注意课文多样的叙事写人的手法;积累常用的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
根据每篇文章的特点,我们在集体备课时讨论了人教版高中新教材必修课本的编写意图、体例和特点,掌握并熟悉教材中各个专题及各篇课文的内容,为顺利完成高中语文必修教学任务,稳步迈进新的课程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还讨论了教法、学法、课型以及文本的课件制作,譬如第一单元:《窦娥冤》《雷雨》为课件讲读课,《哈姆雷特》为概括故事梗概课;第二单元为宋词鉴赏课。
为了使参与新课改的教师更快地把握新课改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在进行集体备课,集体研讨的同时,认真组织新课改的教学观摩课。从而达到优势资源共享,共同提高,共同发展的目的。
二、努力实践课改理念 , 精心打造实效课堂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在阅读中探究,品味个性化和集体化阅读的乐趣
老师教学新的文本的时候,应先摆脱自我,不借助任何参考书,同时把前人的、他人的甚至自己以前对文本的种种理解暂时“搁置“,重新对文本进行陌生化的处理,走进教材,仔细阅读,读出新意、读出个性,记下自己初读时的理解、问题、感想、感悟等,然后在集体备课中进行交流、探讨,灵活取舍,提练出大家的共识部分,再针对存在的不同意见,进一步阅读教参等参考书,把交流探讨的结果与教参中的解析结合进行对比、融合,这样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感悟等融入到教材中,再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
(二)在细节中打造精彩,实现“不教而教”的最佳效果
我想:备课的充分是为了课堂教学的精彩,而精彩则需要细节来成就。因为能否及时捕捉预料之外的学生思维火花闪现的那一瞬间,很可能会书写一节课的成与败。
我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有一个环节是“林冲怒刃奸人,奋起反抗”的情景再现。角色扮演,同学们事先已经分配好了角色。但我在观察中发现有一个学生着急中带有跃跃欲试的神情,于是果断改变原有教学设计,请那位学生来演林冲。学生的精彩的表演让我们始料不及,阵阵的掌声中有师生诚挚的赞美,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达到了“不教而教”的最佳效果。由此可见,如何把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预料之外的盲点、闪光点、疑惑点、疲倦点等等的关键点转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亮点和精彩点,使课堂闪烁着智慧的亮光,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三)研讨课堂提升水平,成就备课组整体的提高和发展
集体备课不仅仅是语文科组的老师集中在小组备课室里关上门讨论完教案和课件就完事了,集体备课的全过程还包括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中心发言人要先授课试讲,其他老师听课。听课的老师要从试教的中心发言人的教学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再集中提出修正;而对于其优点就要学习借鉴,力求使课堂教学效果达到尽善尽美。试教的中心发言人通过课后评课来改正缺点,积累经验,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语文的集体备课是要通过经验加反思来完善的。因此,我们组每周一次公开课,进行研讨活动。
研讨课动中,我们组首先确定探究点和预设成果,一是通过探究点的确立,明确研讨课需要探索解决的、具体的、有价值的学科教学问题;二是通过预设成果,明确本组的努力方以及可实现的结果。
在每一次研讨课后,主讲教师都认真研究同事意见,明确修改目的和理由,从而突破每节研讨课的一探究点,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正是全组教师积极的主动学习和反思行为,成就了备课组整体的提高和发展。
(四)在“研磨试题”中思索,努力实践课改理念 , 精心打造实效课堂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